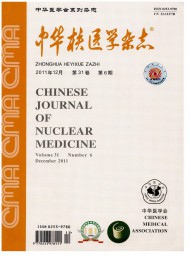我国第一部诗歌范文
时间:2023-04-11 08:08: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我国第一部诗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周朝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诗歌,总共305篇,
2、它产生的年代,大约在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六世纪)五百余年间。经春秋后期孔子审订、整理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本。被后世儒家尊为经典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楚辞》可以说是楚地的《罗摩衍那》,《罗摩衍那》形象地反映了宫廷内部争夺王位的阴谋和罗摩等英雄人物抗暴的斗争。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1、爱情,原来是含笑饮毒酒。——香港女作家张小娴
2、爱情,是我们都相信的谎言。——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壹周立波秀》
3、习俗是爱情的天敌。——英国小说家布尔沃·利顿
4、男人和男人的关系更加长久,像一种没有肉体的爱情关系,也许就是因为没有肉体才更长久。——原名吴红巾,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左小祖咒
5、无酒之处无爱情。——尤里披蒂
6、爱情只能用爱情来偿还。——爱·芬顿
7、朝随而出,暮隐而入。——唐代诗人元稹《莺莺传》
8、芳横无终日,贞松耐岁寒。——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望江亭中秋切》
9、先自掘坟墓,再埋葬爱情。——原名张辛,华裔女作家六六
10、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隰桑》
11、爱情不过是一种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
12、爱情须用爱情来报答。——尼日利亚作家约翰·克拉克
13、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
14、爱情是不讲法律的。——圣哲罗姆
15、有情不管别离久,情在相逢终有。——北宋词人晏几道《秋蕊香》
16、真正的爱情,绝对是天使的化身;一段孽缘,只是魔鬼的玩笑。——台湾女作家,原名陈懋平三毛
17、为爱情而赌气,就丧心病狂了。——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
18、爱情的野心使人倍受痛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
19、爱情的萌芽是智慧的结束。——布霍特
20、真正的爱情故事从来不会结束。——RichardBach
21、爱情从爱情中来。——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
22、爱情往往从小事开始感觉。——
23、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焦仲卿妻》《焦仲卿妻》
24、爱情没有特定的法则。——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25、爱情是我最大的骄傲。——香港女艺人刘嘉玲
26、爱情是理解和体贴的别名。——印度诗人,作家,哲学家,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
27、爱情不是索取,而是给予。——荷兰语言学家范戴克
28、勇气如爱情,需要希望来滋养。——法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拿破仑
29、培育爱情必须用和声细语。——古罗马诗人奥维德
30、爱令智昏。——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哲学家培根
31、热得快的爱情,冷得也快。——威瑟
32、失去的爱情,总是令人怀念的。——台湾女作家,原名陈懋平三毛
33、爱情和智慧,二者不可兼得。——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哲学家培根
34、爱情怎么他妈的就贬值了。——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
35、在我的眼里,你是我的一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镀金时代》
36、爱情总是无言地迫害着友情。——台湾绘本作家,本名廖福彬几米
37、没有爱情的人生叫受罪。——英国剧作家威·康格里夫
38、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北宋词人晏几道《阮郎归》
39、拌着眼泪的爱情是最动人的。——英国历史小说家和诗人司各特
40、爱情和战争都是不择手段的。——弗·斯梅德利
41、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
42、他和你玩暧昧,就是不够喜欢你。——中国知名主持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师何炅
43、爱情像条狗,追不到也赶不走。——原名陈矗台湾女作家琼瑶《夜玫瑰》
44、一方素帕寄心知。——《山歌》《山歌》
45、有钱,爱情就能长久。——卡克斯顿
46、舞蹈音乐是爱情之子。——美国政治家约·戴维斯
47、爱情是无邪的,神圣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48、爱情比软件还要难开发!——美国微软公司的董事长比尔·盖茨
49、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五代词人牛希济《生查子》
50、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
51、爱情是两颗灵魂的结合。——约翰逊
52、恋人的争吵是爱情的更新。——古罗马喜剧作家忒壬斯《安德罗斯女子》
53、爱情献出了一切,却依然富有。——英国作家菲·贝利
54、爱情是一种宗教。——台湾作家罗兰
55、怕爹是孝顺,怕老婆是爱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化学者于丹
56、爱情是生命的盐。——约·谢菲尔德
57、爱情耻笑了锁匠。——科曼
58、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氓》
59、爱情的欢乐中掺杂着泪水。——英国“骑士派”诗人罗·赫里克
篇4
关键词:《诗经?国风》 第一人称代词“我” 语法特点 语法功能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共160篇。我将深入探讨《诗经?国风》中第一人称代词“我”的特点。
首先,简要阐述第一人称代词“我”的语法特点。古代汉语的语料中,第一人称代词有“余(予)”、“我”、“朕”、“卬”、“吾”、“台”等,其中“我”出现的最早,使用最为广泛、存延时间最长。“我”常用来表示复数,译为“我们”,如,予惟曰:“襄我二人,如有合哉。”(《尚书?君奭》);有时也用来表示单数,译为“我”,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随后,“我”表示单数的意义不断扩大,获得大量使用和推广,而且 “我”的句法功能不仅能做主语、宾语,还有能作定语。作主语,如“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尚书?多方》);作宾语,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周易?蒙卦》);而作定语时,如“天降割于我国。”(《尚书?大诰》)
其次,根据第一人称代词“我”的语法特点,详细的论述《诗经?国风》中 “我”的单复数形式特点。
《诗经?国风》一共160篇,当中有74篇不同程度的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我”,共计274个。在所有篇目中使用一个“我”有16篇,两个有15篇,三个有18篇,四个有8篇,五个有2篇,六个有3篇,七个有2篇,八个有3篇。而《邶风?北门》《鄘风?桑中》《齐风?还》《豳风?破斧》中分别有9个第一人称代词“我”,《邶风?古风》《卫风?黍离》《豳风?东山》分别有12个,这几篇目使用“我”的频率相对较高。
从“我”的复数意义上分析,如
①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有子七人,母氏劳苦(《邶风?凯风》)“我”,指七人。句子意思为,母亲贤惠而且慈祥,但我辈不成材……(母亲)有七个孩子,生活辛劳艰苦。“我”在此表示复数的含义,代指母亲七个孩子。
②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唐风?羔裘》)“我”与“人”连用结合为一个词,相当于“我众人”演变为“我人”。此处“我”做复数表达“我们”,句子意思为,穿着羊绒做的外套和豹绒的袖子,使我们姿态高傲。
《诗经?国风》里将“我”用作“我们”的意思并不多,而大部分是解释为单数“我”,如下:
①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召南?虫草》)
②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王风?黍离》)
能列举的例子很多,当中“我”都代称吟唱者本人,是单数意思。
在《诗经?国风》当中使用相当多数量的第一人称代词“我”,表示“我”、“我们”的单复数意思,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风》是《诗经》当中描写风土人情的篇章,属于“风土之音”(《通志?总序》),即是各地的民歌,而十五国风就是十五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多是出自乡间百姓之中,描绘他们的生产生活场景。出于这种情况,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主要是百姓自己,他们抒发对生活的感慨、对爱情的向往和社会的压迫等。百姓抒发自己的情感,当属要使用“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来吟唱诗歌,才能达到直接抒情的效果,充分表现自我的感受。
第二,大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突显自我意识的扩大。这是由于在古代原始社会阶段中,对于神和宗教的信仰,强调以神灵为思想主体,但发展到周民族,“我”的观念增加,自我的意识和想法以及强调自己的概念不断扩大。这样使得百姓关注自己的想法,通过抒发自我的感受来表达生活状态。就此情况,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使用数量增加也是情理之中的。
另外分析《诗经?国风》中 第一人称代词“我”的语法功能,这包括“我”的主语、宾语和定语的用法。
在《国风》当中“我”作主语的情况相比较更多,例如:
①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唐风?蟋蟀》)
②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秦风?渭阳》)
第一人称代词“我”作主语时,处在句子开头,以直接抒情的方式的表达思想感情,描写生活场景。
“我”作宾语时,是作为受事对象,如:
①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邶风?日月》)
②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邶风?泉水》)
而“我”作定语时,表示“我的”或者“我们的”,如:
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魏风?硕鼠》)
②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秦风?渭阳》)
(代词“我”在《诗经?国风》中使用广泛,不做一一列举。)
第一人称代词“我”语法功能使用的范围广泛,不仅能用作主语,还可作宾语、定语,而且数量颇多。具体在《诗经?国风》里“我”使用在主语位置较多而且集中,宾语和定语的位置则分布较散。例如,《豳风?东山》中出现第一人称“我”12个,全部都出现在主语位置;而《王风?兔爰》中“我”6次都出现在主语位置上。
由于重章叠句的歌唱形式,将内心感情反复吟唱,令同一词汇出现在相对固定某一个位置上,这是《诗经》本身语句形式的影响。不仅“我”作为主语时有这种情况,而“我”出现在宾语或者定语的位置上时,整一首诗歌的代词“我”也将多出现在相同句式的同一个位置上,例如《秦风?无衣》中第一章: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第二章:王于兴师,修我矛戟。第三章:王于兴师,修我甲兵。这三句分别属于三章节中,同时作为同句式的定语。再如《豳风?破斧》中“我”作为定语出现9次,位置也相对固定。《秦风?黄鸟》和《秦风?晨风》中“我”都使用3次,都固定出现在了相同句式的宾语位置。
第一人称“我”并不像“余(予)”一样主要用作主语和宾语,也不像“朕”一样主要用作定语。“我”的语法功能包括了“余(予)”和“朕”的用法,作主语、定语和宾语的功能都可以,没有太多的限制,使用起来对语言的掌握更加方便简单。因此,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使用数量不断增加,渐而渐之,替代了“余(予)”和“朕”作用,一直广泛使用至今。现在的第一人称“我”也有单复数的形式,与古代“我”的内涵没有太多改变,延续了古代“我”的使用方法。
在《诗经?国风》中第一人称代词“我”的用法特征可以概括为:在诗歌当中既出现单数形式的“我”,也有复数形式的“我”,使用次数频繁;原因为《诗经?国风》以地方百姓抒情为主,并且周朝时期的自我意识比过往社会阶段要大幅度的提高了。“我”的语法功能广泛,在《诗经?国风》中既作主语、宾语,也作定语;因为《诗经》的重章叠句的形式特征使“我”在一首诗歌中出现的位置相对固定。总体上讲,第一人称代词“我”因语法功能强大,在社会发展中的使用越来越多,直到现在社会, “我”仍是表达第一人称最主要的词语。
参考文献:
篇5
先圣孔子非常喜欢水,每见大水必观,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水文化因子。
“智者乐水”语出《论语・壅也篇》。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我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经为之作注:水性活泼流通无滞碍,智者相似故乐之。山性安稳厚重,万物生于其中,仁者性与之合,故乐之。孔子乐水,绝不仅仅是陶醉流连于水的自然之趣,而是通过对水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从中领略人生的真谛,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在回答学生子贡的提问时,孔子就曾以美德、正义、坚强的智者品格喻水。望着滚滚东流的河水,孔子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这既是对消逝的时间、人世万物犹如流水般挽留不住引发的思考,也是对时间、运动、变化、永恒等哲学问题的感悟,同时还是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内心表白。
不独孔子,作为智者的先秦诸子大都是乐水的,对水都有深刻的思考和精辟的议论。例如:老子说, “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心不善,如水之倒流。荀子认为,水“发源必东,浩浩乎不屈”,有理想,有追求,坚韧不拨。管子认为,水,人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告子在论及“性无善无不善”时,曾巧妙地以水作喻:“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五分于东西也”。还有庄子、孙子、墨子等,无不对水具有自己的哲思。
水对于中国文学的启迪作用也是巨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有着湿漉漉的水意,充满了对水的柔性、水的灵性、水的奔放浩瀚的吟哦与歌咏。人类的情绪、意志以及个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思维乃至意识与哲理的升华,甚至包括所有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都被以水为载体而表达得淋漓尽致。
中华民族的诗歌是从水边开始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向人们展示了先秦诗歌依水而生、伴水而在,寓情于水、以水传情的文化取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优美诗句,已经成为千古绝唱。至于后来的汉代乐府、魏晋诗歌、唐诗宋词,以至明清小说,也常常是借水寄情,以水言志,以水载思。例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恬静、温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阳刚、大气;“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的别致,精巧;“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鲜活、清爽;“春来江水绿如蓝”、“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绚丽、深邃等。笔者以为,智者之所以乐水,是因为水不仅养育滋润着人类,给人们带来富足,而且它有着许多的优良品质,可以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借鉴,给人以激励,给人以效法。
篇6
猕猴桃是我国一种古老的野生藤本植物。远在公元前10世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诗篇记述过它。唐代诗人岑参也有“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的诗句。
1906年,新西兰的园艺家从我国引进猕猴桃后,经过精心培育,改良品性,不断增加甜度,降低酸度。1940年开始了商品化生产,栽种面积近万亩。由于猕猴桃的果形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基维”,因而给它取名“基维果”。目前,新西兰生产的猕猴桃占全世界总产量的90%以上,成为该国水果之大宗。
除了新西兰之外,俄罗斯、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多个国家都纷纷引种猕猴桃。猕猴桃在国外还有不少新的名字,例如英国叫“中国鹅莓”,美国叫“中国醋栗”,日本叫“中国猴梨”等。
酸甜可口利保健
猕猴桃之所以风靡世界,是因为其果实柔软、酸甜可口、营养丰富。猕猴桃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果品,其含有人体所需要的12种氨基酸,且维生素C的含量特别高,比苹果高19~33倍,比梨高22~135倍。
猕猴桃的药用价值也令人注目。唐代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说,猕猴桃“去烦热、止消渴”。年代更早的《食经》(北魏)也说,猕猴桃“和中安肝,主黄疸,消渴。”
现介绍几则我国民间猕猴桃的食疗方法,供读者试用。
鲜猕猴桃 鲜果90克,生姜9克,同捣烂,榨汁,每日早晚各1次。适用于孕妇妊娠呕吐。
猕猴桃汁 鲜果200克,去皮绞汁,每日早晚饮服各1次。可治疗小便短赤涩痛,也可用于内热、关节疼痛。
猕猴桃膏 鲜果500克,去皮捣烂,加适量清水煎煮30分钟,然后加入500克蜂蜜,收膏装瓶备用。每次1匙,每日2次,有延年益寿、预防疾病之功效,还可辅助治疗烦热、消渴等症。
篇7
嫩如金色软于丝。
——白居易《杨柳枝词》
惊蛰过后,听着优美的音乐,我沿着河边徐步缓行,去寻觅、去感受那阔别已久的春天的气息。放下所有的学习与工作,很轻松地走着。
一丝柳条拂过脸颊,我惊喜地发现,之前还是光秃的柳树枝桠现在已经发出了嫩嫩的芽儿,里面还夹着些许黄色。也许是刚发芽,有些柳芽竟淘气地堆挤在一起,就像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刚刚发芽的枝条,在微风下轻轻拂动,让人看了就感觉春天真的来了。经过了夏日的考验,秋雨的洗礼和冬雪的磨砺,这些杨柳渐渐长大了,变得高大而美丽。那柳树下的地面上还掉落着干枯的柳枝,想必是经不起风雨的吹打洗礼而被柳树撇下的。墨色的柳叶也零落在地面的各个角落,不动地躺在那里,有的和其他的落叶混淆在了一块;有的直接掉落在河水里,随着水流打着旋向下流飘去,直至不见了任何踪影;还有的已经被过往的行人碾碎,和泥土来了个近距离的亲切拥抱。
天空中还是那样烟雾蒙蒙的,虽然风不是很猛烈,我整了整衣裳,但还是感觉到阵阵寒意。可是尽管如此,也压不住这无尽的生机,芽儿竞相着生长。它们有的像小鸟尖尖的嘴巴,微微张开;有的像毛毛虫弯曲着身子,甚是可爱。
记得老师跟我们讲过,春天柳树刚长出的嫩叶,是前一年秋天就开始生长的。冬天,这些嫩叶芽都包在层层鳞叶内,避免冻伤,因此,春天刚长出的嫩叶是黄绿色的,等叶片渐渐长出来之后,经过阳光的照射,叶子内的叶绿素会不断增加,叶子就将变成深绿色。
河边有一排好长的杨柳树,蜿蜒到看不到尽头,每一棵都摆着不同的姿势,看这一棵,很俊吧;再瞧瞧那一棵,它也很帅。它们把丝绦伸进河水之中,跟湖水热情地打着招呼。也有的在微风中翩翩起舞;和着斜风细雨在与过往的行人抚摸着。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的美丽奇特。
这整棵柳树上镶满了嫩芽苞,迎风含羞,含着苞儿,就像待字闺中的良家少女,在等待着心中的白马王子来揭开那层纱巾,才舍得向人们展示妩媚妖娆的身姿。欣赏得入迷了,不知不觉,天空已经下起了霏霏春雨,就如软绵的丝绒那么纤细。随着轻柔舒畅的风在天空中飘飘洒洒,轻轻缓缓地落在杨柳上,听不见一点淅淅的响声,也感觉不到雨浇的淋漓。古语有云:花无含露而不娇,柳不舞风而不媚。在洁白雨丝的洗涤上,仿佛浑身披上了柔软的轻纱,变得如此清秀雅洁,妩媚可爱,岸边的杨柳也轻轻地随风摇曳起来,婀娜多姿,曼妙娇羞。这情景,感觉就像是一幅刚刚落笔的水墨画,云雾缥缈,似有若无,让人顿时就能忘却尘世的不顺之事。
杨柳啊!你可知你俘获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心啊!
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杨柳”这是一个情思缠绵的常见意象,含有这一意象的名篇佳句俯拾皆拾,不胜枚举。比如唐·刘禹锡《竹枝词》、王昌龄《闺怨》、白居易《忆江南》、北宋·秦观《江城子》)、·欧阳修《蝶恋花》)……这些都是吟咏你的佳句。
其实,“杨柳”一词早在成书于先秦时期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出现了,该书《小雅·采薇》篇中便有这样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之句,其意境只有垂柳才可以担当。于是乎,诗人们或咏柳喻人,或借柳送别,或缘柳抒情,或道人生哲理……凡此种种,“柳”成为中国诗歌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杨万里就曾对你吟唱到:“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情只浅黄。”一抹淡淡浅黄,朦胧可见,袅娜舞姿,跃现在眼前,甚是醉人。你就是春姑娘的使者,淡青的柳色,引领春天涂抹出绿的主色调。
诗人高鼎又对你发出感慨:“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如烟柳色,丝丝缕缕,沁人心脾。我仿佛听见杜甫又在说:“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是柳条。”杨柳吐青,春光乍泄,多美的意境,弥漫着春的羞涩,春的缱绻。微风吹过,河水微漾,柳影摇曳,心也随之摇曳。
篇8
关键词:语文;小学教育;国学;素质培养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09-00
近年来重新兴起的国学热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全社会需要在传统文化和中华思想文化中寻找和汲取精神文化营养的表现。国学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国家国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体现和概括,是国家民族的性格表现和智慧结晶。中国人最早在课堂上接触国学是在小学的语文课堂上,而在小学课堂上较早对学生教述国学的思想对于养成学生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建立起学习热情,弘扬国学文化都非常重要。
一、语文教育的特点
语文是学习组织和传达语言知识和文化的统称,是学习其他文科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最基础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交流思想和保存传递知识经验的载体。哲学上对语文的认识是:进行表述、记录、传递的口头或是书面的文字言语的物质存在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事实、引证思维、陈述思想、表达意志、抒怀等。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简称。在系统地训练和教育小学生时,不仅要进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更要注重蕴含在语文中的文化和哲学教育。语文的概念是解放后,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将“国语”和“国文”两门课合二为一而称为“语文”。
二、语文课堂与国学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一般是概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学术。广义的国学是我国历史所有文化与学术的集合,包括思想、哲学、戏剧、琴棋书画、数术、中医、星相、农艺、宗教、礼教、伦理、文学、史学等等。而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接触到的国学是以文学为基础的凝练着国学思想和道德文化的文学作品。
三、适合小学语文的国学内容
(一)三字经
三字经是宋朝时期创立的,至今已经七百多年了,是家喻户晓的国学经典入门文章。其三字一句的经典形式朗朗上口、极易成诵,是公认为的国学入门教材。其中包涵了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人文、地理、民间传说等。
由于三字经创立的目的是为了初学的儿童,因而历朝历代都是儿童学习文化知识的入门教材。三字经虽然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但是其引经据典、引用扩展的知识非常多,其本身是优秀的小学语文教材,其引申出来的典故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底蕴更是扩展小学生知识面和稳固道德观、价值观的经典教材。三字经可以说是小学生国学教育的启蒙和宝库。三字经不仅可以是国学的入门经典还是儒家思想的入门经典,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知识更是小学生了解和掌握国学基本思想的重要启蒙知识。
(二)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时期周兴嗣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的一千个字做成的文,其中一千个字没有一个重复(据考究,重复了一个“洁”字,实为999字不同),千字文中以999个不同字写成的叙事性很强的启蒙性文章,是以999字勾画出的一部完整中国地方文化简史,是我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的最高水平。千字文的文风和目的就是指引儿童的行为习惯,按照我国传统文化的塑造素质行为,进而为小学生的人格养成灌输我国传统国学的营养成分。
(三)千家诗
现代概念中常提到的国学启蒙教育读本是“三百千千”即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其中的《千家诗》为明朝时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著,其实际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格律诗,其中大多为唐宋名家诗句,较为广泛地反映了我国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唐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千家诗作为我国诗歌文化的入门教材在小学生国学入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同于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叙事性文体,千家诗是精选的唐宋名家名句的精华诗篇,是小学生欣赏传统文化魅力和古典文学魅力的启蒙之作,更是培养小学生文学素养和提升对国学关注的重要经典。
(四)论语
论语是教师之祖孔子的言行语录,由其弟子整理完成,是儒家思想的入门材料。其中以语录的形式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同时论语也是教育学的经典教材,其中提起的因材施教、学而时习等教育思想也是教育的经典理论。
论语作为儒家四书五经中四书的第一部,也是四书五经中写的较为浅显、句子较为简单的书籍,是最适合小学生学习阅读的国学经典教材。其中朗朗上口的句式也适合作为小学生早读诵读和背诵的段落。
(五)史记
史记是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不朽明珠,由司马迁撰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史记由于其纪传体的特点,与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历史性、文学性和故事性都较强。其中可以采取“糖葫芦”式的教学方式,引入史记纪传体的小段历史故事在给小学生讲故事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传递蕴含在传记中的民族性格、道德观念、做人道理。
(六)诸子百家
我国传统思想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百家是我国春秋时期各派别的总称,其中最为显赫的派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在我国的国学教育中儒家思想传播广远,但是诸子百家中其他的一些流派如墨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也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诸子百家的精神也相互渗透,共同在我国传统文化留下了精神的烙印。
(七)西游记、三国演义
我国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中,较为适合小学阅读并且广受小学生喜爱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具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其中的故事学生早已通过电视剧熟悉了知。老师们需要做的是在熟悉的故事情节基础上提点出故事中蕴含的道理和文化。把故事情节扩展既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又起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
[2]田立君.小学阶段国学教育及其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成因[J].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3(04).
篇9
一、教材分析
本课教材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介绍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形式和成就。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2.了解诗、词、歌、赋等各种不同的知识内容和形式。知道和掌握一定数量的名家作品。
3.拓宽文化视野,提高赏析和运用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材料以及自己的日常积累,通过阅读、讨论、分析、评论,了解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特色。
2.通过阅读、观察、练习、欣赏、表演、评论、创作等方式积极参与教学;通过独立思考或合作学习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比较,概括和阐释;学会合作学习和相互交流。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美感教育。通过对文学家、诗人及其文学作品的分析,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三、重难点突破
(一)本课重点是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文学的重大成就。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结合教材小字资料和学生本身具有的文学常识进行,提高学生的兴趣,增加学生的成就感。
(二)本课难在如何揭示一定社会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使用对比的教学方法,举例:同为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为何在内容上会有不同?婉约派李清照前期的词与后期的词词风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利用学生已有的语文知识分析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出现的原因。总结时探究“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举例说明,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三)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指导学生完成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一览表,培养学生归纳概括能力。
四、教学方法
为更好地体现课堂教学的新理念,可以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针对重点难点设计探究问题。指导学生围绕问题自主阅读教材,理--清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讨论,合作探究。文史联系比较,情景创设。增强教学的直观性、趣味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生成主题(导入新课)
师:名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引入新课。这句诗出自哪里?
学生答:《诗经》。
师:那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同学知道自古以来我国文学的主要形式有哪些?
(1)指导学生阅读引言《弹歌》了解诗歌的产生:语言―歌谣―诗歌。
(2)学生列举:先秦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
(二)多向互动,合作探究(新课讲授)
1.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结合所学,如《卫风氓》《硕鼠》等名旬,概括《诗经》的地位、时间、内容、特点、影响?
学生归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孔子整理编定。
特点: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语言丰富,内容古朴,现实感强(现实主义)。
价值: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五经之一)。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2.创设情境,合作探究:
(1)师: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谁?能对他做一简单介绍?他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是什么?有何特点?
生: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
楚辞: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创作的一种新诗歌体裁,亦称“骚体”。
特点:采用楚国方言,句式灵活,易于表达情感。
《离骚》:屈原的长诗,楚辞的代表作,具有浪漫主义风格。
(2)结合43页学思之窗,讨论除了文学,《诗经》、楚辞是否对其他方面也有影响?如果有,你能举例说明吗?
3.教师讲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和“子虚乌有”成语的由来,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汉朝时,楚辞盛行。文学家以楚辞为基础,创造出了一种半诗半文的综合文体一赋。(定义)这种文体有什么特点?著名的佳作是什么?
学生:特点:辞藻华丽,手法夸张的,内容丰富,气势恢宏,表现出当时宏阔博大的文化气度、豪迈勇进的时代精神,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佳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
(过渡)师:在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当数唐朝。其原因是什么?
4.唐诗――诗歌的黄金时期
师:(1)唐诗繁盛的原因?(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归纳概括从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入手回答)
生:①国家统一、国力强盛;②国内外文化交流频繁;③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④科举以诗赋为主。
(2)唐诗繁盛的表现
学生回答自己学过的唐诗,师生互动,教师可以按时期(初唐、盛唐、申唐、晚唐)归纳;也可以按诗人的名句提问,引导学生思考诗句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探讨李白、杜甫诗风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出示诗句引导学生自己分类,分清边塞诗和山水诗的风格。
教师播放歌曲《水调歌头》,过渡导入下一知识子目。
5.宋词
(1)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完成课后的探究问题“词曲为什么会成为宋元流行的主要文学形式?”(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考虑,①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增加;②适应市民生活需要;③两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
(2)利用课后的学习延伸,列举宋词的两大派别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名句,分析苏轼与辛弃疾、李清照前期和后期词内容的不同就是时代的反映。突出一定社会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
6.元曲
(1)利用学生正在学习的语文知识《窦娥冤》组织教学,元曲成就最高的代表之一,请学生介绍关汉卿的生平,教师展示关汉卿的《铜豌豆》活化关汉卿的性格。
(2)什么是元曲?特点?(结合教材分析,语言风格可以用《寞娥冤》中的语言来体现,这是学生要求背诵的部分)。
7.明清小说
(1)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学生看书归纳、总结)
魏晋南北朝――兴起(志怪小说);唐朝――(传奇,情节曲折离奇的短篇小说,适合市民欣赏);宋代――(话本,把中国小说创作推到一个新阶段,为后来小说的繁荣奠定基础);明清――空前繁荣。
(2)探讨明清小说繁盛的原因?表现?
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历史必修一、必修二所学,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
生:①封建专制越来越强化,封建社会走向衰落;②手工业、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③市民阶层扩大,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
表现――四大长篇古典名著、文言短篇小说集和讽刺小说。
(可以结合同学们正在学习的《林黛玉进贾府》及学生积累的语文知识组织教学)
(三)知新整合,拓展主题(小结)
1.完成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一览表的制作。
2.结合本课所学列举“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
[教后反思]
1.知识体系构建明晰、合理。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因此,在让学生对本节所学主要内容进行总结时,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准确无误地完成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一览表的制作。
2.本节课始终贯彻“教为主导,学为主体,思维训练为主线”的教学思想,紧紧围绕教学目标。注重基础知识的落实和学生分析概括能力的培养,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注重语文知识、政治知识的结合。
篇10
通过观察,我认为“诗性语言”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大量修辞手法的使用。汉语的诗性语言中,比喻、引用、夸张、互文等修辞手法使用频繁,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语言的美感。例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运用了比喻,将“愁”比作了“一江春水”,化无形抽象的“愁”为有形,使抽象的情思具体化了,让读者能深切的感觉到“愁”之深、之切。而其他比喻的使用,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将原本静态的红杏写活,将其人格化,表现出一派春天的生机勃勃之景。又如,“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引用的使用不但能借典故生动的说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能使文章显得典雅精炼。再比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愁”,同样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会对读者理解句意产生影响。就如上面例子中,“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引用手法,而机械的对其进行翻译,就很难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而对于“白发三千丈”一句,有些人单纯从客观事实角度出发,就会说,一个人的头发怎么可能那么长,从而,忽略了对作品内在含义的理解而片面的探讨作者的写作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有修辞中倒置的使用,如果不能应从修辞角度的去理解,注意到倒置的使用,就会影响意思的理解。例如江淹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其实际顺序应为“孤臣坠涕,孽子危心”,若未能注意到修辞手法的使用,进行翻译,就会出现错误。
二、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一方面,正如前一点中“倒置”修辞手法的使用,并未遵循固定的句法结构,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却收到特别的表达效果,像杜甫的“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和《诗经》中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句,改变了句子原有的平淡,增加了诗意,增强了韵律感、节奏感,也使语意变得错落有致,而由于中断了语流,使人们更加注意关注语句含义。但也正如上文所说,对句子的理解造成困难。
另一方面,在很多古典诗词中,作者很少,甚至是不使用连词、介词等,仅把多个意象连缀起来。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只是简单的将“枯藤”、“老树”、“昏鸦”等几个意象连缀到一起,却成功的描摹出一派秋天的萧瑟凄凉之景,表达出作者的孤独之感与思乡之情,并收到了电影中蒙太奇的表现效果。这种通篇意象的列举,而无句法关系的连接,可以说是中国诗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从一般的语法角度看不合规矩且缺乏连贯性,但从诗的角度看,语言凝练、简洁,形象鲜明、突出。
三、多使用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等语法结构。诗性语言的这一特点主要是炼字的要求,正如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手法的使用,无疑会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的“乐”,它们分别使用了形容词的动用,以及动词的使动用法。这种用法,比单纯的用“春风把江南岸变绿了”和“使她快乐”要显得凝练,而且更具有表现力,达到古诗文中,炼字的要求。
四、语言凝练,表意的形象。这一特点,源于诗性语言中,意象的使用。
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用简单的两句话,几个意象,就使一幅清晨送别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如身临其境。在诗文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五、感情丰富而含蓄。诗性语言讲求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性语言的应用,不但使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而且能够在有限的字数中表达超过一种的情感。
例如,范仲淹在《苏幕遮》一词的上片中,仅通过“碧云”“黄叶”“斜阳”“芳草”等一系列意象,不着一字,便抒发了深厚的思乡之情,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体现出诗性语言中,“借景抒情”这一手法的运用。再如苏轼的《水调歌头》,前一部分通过写“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高处不胜寒”等,曲折的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之情,而后面又以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抒发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