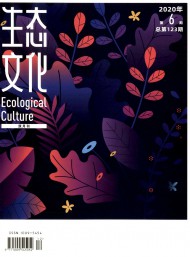文化经济政策十篇
时间:2023-11-10 17:41:16

文化经济政策篇1
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切实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中央和地方都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步增加必要的投入”的精神,以及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关于“要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各类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认真研究制定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给予必要物质支持”的要求,在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对文化事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保障,以使文化事业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为此,就当前急需解决的有关文化经济政策问题,经与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建设部、国家税务局等有关部门协商,提出以下意见:
一、各级政府要真正把文化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政策上加以引导,资金上予以支持。要逐年增加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逐步改变文化经费紧张的状况,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二、各级文化部门要制定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文化经济政策,加强队伍建设和财务管理,注重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要发扬勤俭办事业的优良传统,合理调整文化经费支出结构,挖掘内部潜力,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合理地组织收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合理使用事业经费,提高经费的使用效果。
三、各级政府对文化设施建设要列入议事日程,切实予以安排。要将群众需要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统一建设。“八五”期间,要努力做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各地建设住宅小区,要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要求,统筹规划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实行同步建设。小区级非营业性文化设施的投资,可列入小区住宅建设投资。
四、要适当增加文化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每年应有一定的文化基建投资基数并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逐步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使之与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投入保持适当的增长比例。各级计划部门对当地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的确需建设的文化设施项目,不应当作“楼堂馆所”加以限制,应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在年度计划中安排落实投资。“八五”期间,经过调整改革后的艺术表演团体,在充分利用社会上现有可供演出场所的前提下,要视各地财力情况逐步建设自己的演出场所。
五、当前各地现有的剧场、影剧院严重破旧的问题十分突出,要抓紧进行维修改造,充实设备,改善条件。所需资金除由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定的维修费,拨给文化部门统一掌握使用外,还可采取其他办法筹集,如从电影票价附加和纳税后的“以文补文”收入中提取等。筹集奖金的具体办法,由各地文化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报国家规定的具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后施行。
六、切实解决各级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紧张的问题。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同级文化部门,根据图书馆的规模、编制、藏书等情况,核定其经费预算,并将购书费予以标明,实行专款专用。在核定正常经费和购书费时,既要严格控制人员编制,避免人员经费挤占业务费,又要充分考虑工资、物价、书报刊价格上涨以及外汇升值等增支因素,逐年予以增加。
七、对艺术表演团体要继续贯彻整顿、改革的方针,合理调整布局,精简冗员。对整顿后确定保留的艺术表演团体要给予必要扶持。要认真贯彻落实文化部、财政部联合颁发的《艺术表演团体财务管理暂行办法》(文计字【1986】第1227号)。各级财政部门和文化主管部门对有实验任务的剧团,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剧团,少数民族的剧团、文工团(队),具有浓厚艺术传统和较高艺术水平的某些古老稀有的艺术品种,排拣演出反映现实生活和重大题材剧目的团(队),在核定其差额补助费时,要给予照顾。对各类剧团的大型修缮、设备购置补助费,要根据财力可能尽力予以安排,并单独编报预算,专项补助。对离休、退休人员经费实行单列,专款专用。对舞蹈、杂技、武打演员及管乐演奏员,按月发给“艺术工种补贴”。为鼓励多演出,对超额完成演出场次和收入计划的剧团,可按规定发给“超额补贴”。发放补贴的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文化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八、为繁荣舞台艺术,对那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具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功能的优秀剧(节)目的创作、排练、演出,要予以扶持。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文化主管部门应设立“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的补贴和奖励。专项资金除从各级文化部门的文化事业经费中调剂和各级财政酌情补助外,也可采取社会集资的办法以及从“以文补文”收入中适当提取。对“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的使用,各级文化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对优秀剧(节)目的奖励,全国性的奖励办法由文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各地的奖励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九、根据艺术表演的特点,对已不适宜上台演出而不到离休、退休年龄,需要转业到其他部门或提前离退体的演员,可实行鼓励他们转业或提前离退休的政策,发给一定的转业、退休费。由于各地情况不同,目前不宜制定全国统一的转业、退休费标准,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部门会同同级人事、财政部门根据当地情况制定,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文化经济政策篇2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对改革宣传文化管理体制和完善宣传文化机构内部经营机制,促进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宣传文化设施建设,改善宣传文化机构的物质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宣传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年计划的建议》中关于“继续实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增加对重要新闻媒体和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的精神,深化宣传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在“*”结束后,要继续执行《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国发[*]37号)及相关文件并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对现行的各项文化经济政策加以调整和完善。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继续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
(一)各种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卡拉OK歌舞厅、音乐茶座和高尔夫球、台球、保龄球等娱乐场所,按营业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刊物等广告媒介单位以及户外广告经营单位,按经营收入的3%缴纳文事业建设费。
(二)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在征收娱乐业、广告业的营业税时一并征收。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后全额上缴中央金库。地方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缴入省级金库。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分别由中央和省级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管理和使用,继续按照财政部、《关于颁发〈文化事业建设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文字[*]243号)执行。
二、对下列出版物的增值税继续实行先征后退的办法。违规出版物和多次出现违规出版物的出版社不得享受此项政策。
(一)中国共产党和各派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二)各级人民政府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三)各级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四)新华通讯社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五)军事部门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
(六)大中小学的学生课本和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刊物。
(七)科技图书和科技期刊。
三、全国县(含县级市)及县以下新华书店和农村供销社销售出版物的增值税,继续实行先征后退的办法。
四、继续实施下列发展电影事业的五项经济政策。
(一)对经批准成立的电影制片厂销售的电影拷贝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电影发行单位向放映单位收取的发行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从电影放映收入中提取5%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电影行业的宏观调控。
(三)从电视广告纯收入中提取3%建立“电影精品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电影精品摄制。
(四)从进口影片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电影制片、译制。
(五)特别重点影片的创作生产,可个案报批财政补贴。
五、继续增加对宣传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
(一)中央和省级财政继续按宣传文化企业上年上缴所得税的实际入库数列支出预算,建立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中央和省级财政要继续在预算中安排部分专项经费,纳入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二)适当增加“万里边境文化长廊”补助经费。在民族事业费和边境建设费中安排一定数量扶持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事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应逐步增加对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投入。
六、建立健全专项资金制度。为促进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增强调控能力、保证重点需要、规范资金管理,中央和省级要建立健全有关专项资金制度。
专项资金的来源为财政预算资金和按国家有关规定批准的收费等预算外资金。财政部门要做好专项资金的预算安排,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征收预算外资金。要进一步完善“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和“出版发展专项资金”等专项资金制度。专项资金是财政资金,要按照有关财政法规的要求健全制度、加强管理,保证专项专用并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监督检查。
七、继续鼓励对宣传文化事业的捐赠。社会力量通过国家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或国家机关对下列宣传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经税务机关审核后,纳税人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0%以内的部分,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一)对国家重点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歌剧团、京剧团和其他民族艺术表演团体的捐赠。
(二)对公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捐赠。
(三)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捐赠。
文化经济政策篇3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超越国界的世界经济活动。世界经济活动具体是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它是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和经济国际化的新阶段发展生产。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化程度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的提高,进入到了世界的舞台中。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客观规律,有力地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进入90年代,现代技术革命在更深的层次推动着世界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演进。世界经济活动主要由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所组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源泉。
三、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生产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是国际生产领域中分工合作及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这种分工方式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构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这种现代的分工方式已经不是在国家层次上的综合分工,而是深化到部门层次和企业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其次是产品国际化,也就是出口生产所占生产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具体表现形式是现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增加。几乎所有国家的众多企业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国际商品交换。最后是投资金融国际化,随着生产和产品的国际化不断发展,使国际间资金的流动日益频繁,从而促进了投资金融的国际化。为了适应于国际化的大浪潮,各国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投资金融的管制,还提出许多鼓励措施,促进本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对于我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浪潮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流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的经济来说,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快。但是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承受着全球背景的巨大压力,甚至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
五、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不断的会有问题发生,因此,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主要问题如下:
(1)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职能在经过很多次的转变之后还是不完善,尚未完全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
(2)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法适应行政法制建设。长久以来,对管理经济的手段主要是运用于行政手段,这就容易使行政管理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缺乏法律保障。
(3)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地方行政部门的层级过多,部门之间的职责不清,协调能力差。对于行政机构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解决对策
健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模式,就是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中,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的需要,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为重点,完善经济法律制度。
(1)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重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社会和经济的有序运行,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地调控经济,做好市场监督,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2)设置适当的规模,明确责任,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明确各级职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宗旨,建立适度规模的政府。
文化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经济政策;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F31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由于我国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势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变化速度较快,针对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了保障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必须采用对应的措施,不断强化国际宏观调控,并对相关政策进行正确的调整,让国家经济向着预期目标发展。从2011年上半年的发展进程来看,根据多样化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经济情况,国务院实施了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的过程中,朝着宏观调控发展。2011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4459亿元,与同比价格相比,直接增长了9.6%。由于国内外环境复杂,很多政府都存在财力紧张、无钱可贷的现象,进而出现一系列的钱紧、钱荒、钱流、钱多现象。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为了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必须及时调控经济政策。
一、我国经济政策调控原则以及发展现状
从当前的经济政策实行情况来看,为了保障经济政策落实力度,必须以坚持主题、落实主线为原则,从根本上保障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在这过程中,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的形势,主题则是科学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程度是影响经济政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坚持相关原则不动摇,在大力推行国民经济改革的同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持久性进行全面分析评价,争取得到更有效的改革方法,辅助国民经济发展。
为了满足国民经济以及相关政策发展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整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转换成适当宽松的货币形势;第二方面是将稳健的财政方法转变成积极稳定的财政策略。调整后的经济发展策略,主要包括扩大内需、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等相关措施,也就是“国十条”。第一条是,加快农村经济文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第二条是,增强建设性居民的保障住房策略;第三条是,增强居民自主创新以及国民经济文化建设力度;第四条是,增强机场与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性建设策略;第五条是,增强灾后相关区域重建工作;第六条是,增强医疗卫生事业以及文化教育发展;第七条是,努力健全生态文化建设过程;第七条是,进一步完全生态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第八条是,增强金融单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持力度,进而逐步代替我国各种银行的信贷限制;第九条是,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第十条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转型增值税的改革策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次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将遏制国民经济下滑、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放在各个工作的第一大位。从我国经济政策改革过程来看,近十年不可能达到经济形势的完全转变,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必须以相关经济策略、基础制度为依靠进行对应的调整。从经济政策发展侧面来看,不是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制度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拉大内需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战略发展。一旦经济增长速率太低,就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带动我国经济政策改革的建议
为了达到社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目标,必须以经济政策改革为基础,从各方面推动经济文化建设。
(一)努力实行科学发展观,扩大内需与供给。在经济政策改革中,为了带动经济增长,必须努力实行科学发展观,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在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环境中,为更好的实行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首先,在扩大投资规模时,必须不断优化投资结构,而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投资利润与数量,进而忽视投资结构转换。其次,在投资方向与投资项目选择中,为了避免一哄而上造成的不良局面,必须有压有保。对于高污染、高成本、高能耗的项目,必须坚决抵制,在将重复性项目过剩削减的过程中,注重大规模数量以及质量投资,并且各种项目必须拥有对应的可持续性与技术含量。在严格禁止豆腐渣工程的同时,充分调动私人、企业与政府的投资积极性。
在供给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必须扩大供给,增加供给能力;在供给改革中,必须对供给总体需求与总供给同时发力,以带动经济发展。
(二)扩大投资消费,调整财政政策。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但是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更加注重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过程。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已经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很难改变,所以必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扩大投资力度与消费需求。
在财政政策调整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带有很多负面影响,如果政府只注重发展,而忽略了钱的实质意义,就会出现钱“贵”的局面。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坚持积极的发展战略,在财政改革的同时,以国家财力为后盾。因此,在实施经济发展策略时,必须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带动国民经济积极发展。
(三)调整货币政策与税收政策。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大企业已经感受到融资压力,并且融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与经营目标。很多银行也存在存款、贷款的双重压力,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借贷或者高利贷现象,这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针对这类现象,我们不仅要努力健全货币政策,更要及时调整相关制度,在“双高”与“低差”并存的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企业、单位金融结构备金率。
对于国家税收的调整,很多地方仍然存在非法税收的现象。针对这类现象,我们不仅要调整税收结构,更要减少税收项目区,在提高财政收入的同时,进行闺房税收改革,进一步强化税收扶持力度。
经济政策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持续的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以政策改革为根本,在完善改革策略的过程中,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靳卫萍,尹晓菲.滞胀威胁下的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J].经济纵横,2008(11):9-12.
[2]李武军,黄炳南.基于政策链范式的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研究[J].中州学刊,2010(5):35-38.
文化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文化消费;政策;缺失;治理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86-05
一、文化消费政策的内涵
文化消费主要指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采取的以不同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是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使用等。政策通常是指国家或者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和执行其路线而制定的活动准则和行为规范。严格来讲。政策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等存在明显区别。但是基于中国以规范性文件为代表的政策与法律法规相比具有绝对数量优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产生某种影响。以及文化领域在历史上多由政策进行专门调控等特殊性考虑。本文以政策为视角对文化消费展开讨论,且并不排斥相关法律法规。
所谓文化政策。即社会公共权力主体在特定情境中,为达到一定的文化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其作用是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表达形式包括除法律法规之外的行为规范、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讲话、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规划、计划、行动方案及相关策略等一切具备规范性的文件和形式。消费政策是指权力机关为实现经济领域的消费目标而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包含宏观消费政策、微观消费政策和与消费相关的政策的政策体系。在这一语境下,文化消费政策体现为以调控、干预文化消费为目的的各种政策手段。
学者威廉斯认为文化政策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具有展示意义的文化政策,具体表现为通过国家或权力机关的意志表达宣示民族身份或国家权力;其二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文化政策,具体表现为体现经济价值的文化调控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区分文化政策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尽管二者的区分并不绝对。文化消费政策侧重体现经济价值。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文化的部分。集中体现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主张、文化意志,无疑是我国文化政策最权威的组成部分。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讲话,尤其是其精神实质,往往确定了文化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具有“元政策”的意义,即“关于政策的政策”。而中央政府(国务院)、有关文化的各部委、各省市等颁发的规范性文件。则是一些实践政策或具体政策。这一文化政策体系中关于文化消费政策的部分,是各种以经济指向为主要目标的政策、规范、指示等的集合。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的文化消费政策是以积极扩大文化消费为首要目的的各种政策手段的总和。
文化消费政策具有如下本质性特征:一是本身体现出强烈的规范性,有利于建构社会文化消费秩序;二是行为表现为政府或社会权力组织对文化消费的干预,目的是改变市场资源配置、引导市场行为、提升市场效率;三是作用对象限定于特定的文化消费领域。包括文化消费市场的各相关主体、消费对象以及消费关系;四是相对于法律、习俗等其他社会规范,文化消费政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适应性和强制性,在调控文化消费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二、我国文化消费政策的历史概况
我国的文化消费政策首先隶属于文化政策这一宏大主题,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党和国家对于文化整体认识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文化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被认识和建设的。随着改革开放,文化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逐渐显现出来。《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等诸多政策的,文化经营管理、文化市场、文化经济、文化产业等概念逐渐从文化的大概念中独立出来。其中,文化产业的发展自新世纪以来广受支持。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首次明确出现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2000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较为系统地制定了鼓励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同一时期,《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制定,也为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后,《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若干政策》《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等专门性文化政策文件,和《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相继出台。文化产业由此受到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文化产业的发展因其具有典型经济特性而备受重视,文化消费作为与文化生产相互促进的领域也迎来发展机遇。2009年9月26日,《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指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八项重要任务,其中第五项就是“扩大文化消费”。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扩大文化消费,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日益凸显了文化消费在政策导向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经济增长结构将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消费结构将进入快速升级期。居民用于吃、穿、用等实物性消费比重逐渐下降,消费结构由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居民对汽车等高端消费耐用品和文化教育、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等服务性消费的需求明显增加,消费观念也开始由传统消费型消费向超强型消费转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出现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同时。2011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比2002年分别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我国已经开始进入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期。这一时期有两大表现: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加为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改变提供了保障;二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带来了文化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历史机遇。
然而,以“国际经验”推测当前中国文化消费总量,应当已经达到4万亿元。但事实上,在中国人均产值超过3000美元的2007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仅仅有0.6283万亿元,人均文化消费为476.73元;到2011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也只有1.0126万亿元,人均文化消费为753.36元。而《半月谈》杂志社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间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百姓对支化产品、文化服务表现出越来越高的需求。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民众平均每月用于文化活动的消费支出比较少,低度消费的迹象明显。文化消费存在的现实与预期的巨大落差急需国家干预。考虑到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必须通过制定、实施新的、专门的政策等方式加快促进文化消费的制度安排。
三、我国文化消费政策的缺失
目前我国文化消费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文化消费的相关政策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缺乏高层次、总体性、整合型的文化消费政策
我国专门、系统规范文化消费的政策文件尚不多见,经笔者查询“文化政策图书馆”,截至2013年1月31日,专门性的文化消费政策数量为0,而文化政策中包含关键词“文化消费”的数量为138。究其原因,在于文化消费只是消费领域之一,同时文化消费往往被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步骤予以讨论和规范,加之我国多年来在经济领域保持“重出口、重投资”和“轻消费”的态势,直到近年消费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得到重视,文化消费才成为消费和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文化建设和促进消费的重要命题。目前文化消费的政策规定主要是《决定》中文字数量较少、内容较为原则、缺乏具体手段的表述,其后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扩大文化消费”的内容仍然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尽管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对于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工作意见,但是对于文化消费这个跨部门、跨地区、需要在国家层面出台特殊政策、需要由上至下形成执行效率的领域,尚缺乏高层次、总体性、整合型的专门政策予以支持。
第二。文化消费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缺乏深厚积累,难以形成体系化、具体化、高质量的文化消费政策
相对于一般物质消费而畜,文化消费具有精神满足和意义实现的含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对于消费者的物质基础、认知能力等条件有较高要求。同时,与一般物质消费相比,文化消费的需求弹性空间较大。此外。文化消费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表现出政治辅助、经济推动、文化渗透和社会建设功能。进一步而言,文化消费作为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活动,横跨多个学科和领域,不深入对其进行综合研究难以取得明显成果。而目前梳理文化消费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不少成果体现出学科视角单一、研究范式陈旧、研究深度不足、现状分析较为表面、缺乏有质量、突破性政策建议等特点。尤其是文化领域和消费领域的研究互动不够充分,使得在政策制定方面还存在不少认识分歧,对制约、影响文化消费的体制、机制和其他因素等认识不足,因此难以形成体系化、具体化、高质量的文化消费政策。
第三。与现有其他政策相比。文化消费政策的主要任务、工作目标、具体手段、保障措施等内容尚未凸显
我国现有的政策文件多在格式和体例上存在一致性。如文件或问题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工作目标、具体手段、保障措施等内容,有的甚至还有明确的分工和责任。由于以党和政府为代表的权力运行体系存在强大的强制和约束绩效,因而政策文件中的目标、任务、手段、措施、责任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而现有的文化消费政策,如“创新商业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服务消费,提供个性化、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等扩大文化消费的政策措施,多为纲领性、概括性、指向性、倡导性的表述,对究竟如何促进文化消费。在当前社会形势下应当主要在哪些文化消费领域着力。采用哪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解。非常缺乏像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节能补贴、家电下乡、小排量汽车补贴等消费刺激政策。在任务分工和责任落实等方面更是没有形成统一部署和职能协调,因此还没有形成政策合力。
第四。未能将文化消费作为消费文化的一个层面加以整体分析,文化消费政策的软环境整治尚未得到重视
消费文化是指各种消费行为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各种文化意义上的总和。与文化消费中的“文化”特指某些具体文化产品或活动不同。消费文化中的“文化”则因消费体现、表达或者传递某种意义、价值或者规范呈现出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的特征。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外,还存在第三种调节方式,即“习惯和文化道德调节”。经济学家刘诗白指出,经济市场化深度发展使文化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基于前文分析,消费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已经体现出文化意义,而文化消费作为一种典型的心理和精神需求,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消费,是受社会文化意识、文化行为、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变化的。不但作为个体消费者的消费受到自身文化的影响,作为社会成员消费者的消费受到各种文化形态以及亚文化、跨文化的影响,而且文化消费者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其消费行为指向的对象就是具体文化符号,因此文化成为参与制定、实施文化消费政策全过程的重要因素。但现有的文化消费政策尚未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没有将文化消费纳入消费文化进行整体性分析。没有从文化属性上对社会文化意识、文化行为、文化生态等软环境加以整治和引导,仅仅对文化消费进行经济性的调整,因而效果并不明显。
四、我国文化消费政策的治理
治理作为一种政策选择,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共需要,其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基于对我国文化消费政策现状的考察和影响文化消费的居民收入、产品价格、社会结构等因素分析。我国文化消费政策的治理举措应当包括:
第一。改革涉及居民消费的相关制度,破除制约扩大文化消费的基础
当前影响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障碍包括: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城乡消费差距较大;市场准人制度与竞争机制不完善;体制机制阻碍城市化进程;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监督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公共产品投入不足;税收体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等。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上问题:一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严格控制城乡收人差距,积极促进劳动就业,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充分利用再分配机制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乡居民消费预期。通过中小城镇的建设带动农村增收和提高农村收入水平,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三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善消费环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人、改善政府监管职能、推动市场充分竞争、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支持和扩大热点消费领域;四是完善消费政策体系,保持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加强政策统筹和协调。调整引导消费发展的策略和手段,打破地方、行业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
第二。培育文化消费市场的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加强文化消费市场主体建设的政策支持
消费行为是由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经营服务的接受者共同完成的活动,完整的文化消费行为主体应当包括文化市场的经营主体和文化市场的消费主体。因此,治理文化消费市场需要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人手。加强文化消费市场主体建设,首先应当着力培育文化消费市场的经营主体,一是鼓励、引导文化经营者以各种商业组织形式开展文化经营,二是为文化经营者提供教育、培训、交流等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三是对文化经营者出台形式多样、涉及全流程的专项优惠政策,四是以多种方式激励文化经营者壮大实力,五是为文化经营者的规范经营提供全面、完备的保障。其次应当加强培育文化消费市场的消费主体,一是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消费者进行文化消费的实力和意愿,二是对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加强引导,三是对个人、社会组织等文化消费者加强文化消费的教育和保护,四是为消费者进行科学的文化消费提供尽可能的支持和便利,五是通过政府扩大文化消费总量等方式带动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增加文化消费。
第三。强化文化消费市场的产品供应和消费方式革新。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客体建设的政策调控
文化消费的客体是指文化消费的具体产品或者服务。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客体建设,首先应当促使文化消费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结构与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相适应,一是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有效增大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品种和数量供应,二是依据文化消费的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改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结构。三是积极开发适应社会文化消费市场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模式,四是大力推动热点文化消费、特色文化消费领域发展,以点带面促进文化消费市场全面活跃。其次应当通过消费方式的调整更新消费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一是以消费观念、消费文化的变革,推动消费行为、消费方式走市场化、多元化发展道路,二是鼓励网络消费、信贷消费等新消费方式,扩大消费市场产品和服务规模,三是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加快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平台和终端建设,四是在文化消费方式的规范调整与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
第四。妥善应对文化消费市场的若干重要矛盾关系。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关系建设的政策约束
目前我国文化消费市场存在若干矛盾亟待解决。其中重要的矛盾包括: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与文化消费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总体消费领域中文化消费与非文化消费之间存在矛盾:文化消费市场的治理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矛盾:文化消费市场的结构中城乡、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存在矛盾;文化消费市场的消费结果存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等。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关系建设,首先应当对未来一段时期文化消费在社会总消费当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保持充足信心,以政策文件等明确文化消费对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将文化消费作为启动消费市场的重要领域,给予重点优惠政策支持。其次应当理顺政府和市场在社会文化消费活动中的关系。明确政府推动文化消费的工作职能和职责,充分发挥市场能动作用。再次应当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群体差异明显等特殊国情,分别采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和激励措施,推动文化消费活动更加活跃。最后应当有机统一文化消费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文化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第五。完善文化消费市场的市场环境治理。加强文化消费市场环境建设的政策保障
文化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财政与金融政策;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01
财政与金融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各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财政与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的提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我国财政和金融政策务必要保证资源优化配置为前提,优化现有的社会生产力,大力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要通过实施一系列积极有效的财政与金融对策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下面将对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与金融对策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财政与金融政策概述
财政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指体制化的财政措施,实现国家财政职能。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依据某个阶段的经济形势和发展状况指导财政分配活动,以及平衡各级财政分配关系的准则性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财政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金融政策是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对货币、利率和汇率水平进行调节,从而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财政与金融政策体系的都不是单一的存在,分别包含各自的庞大的体系。财政政策分为七个政策内容,包含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以及补贴和出口政策。金融政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财政与金融政策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与金融对策
(一) 转变发展理念,确立清晰的指导思想
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只是在单纯的追求经济发展,没有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当前,促进经济发展务必要将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出发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要任务,加快步伐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推进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社会。开辟新型工业化道路,重视人们群众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应该将社会的客观需要和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有效结合,具体表现为充分利用国家财政和金融政策,尽可能大的加大财政投入,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是良好的,保证经济市场的公平竞争,使得社会群众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要优先考虑到政府的财政金融的供给能力,做到量力而为,保证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要适应当地政府的实际财政金融能力。
(二)增强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优化和壮大财政金融基础
财政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首要是要改变以往单纯的依靠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采取体制调节和政策指引等财政金融手段,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传统的经济的产业转变为具有一定科技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财政和金融政策要注意渐渐的推出具有一般竞争性的产业,加大力度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财政与金融政策还需要考虑重点扶持国家服务行业,在服务行业中大力发展物流,信息服务以及金融保险等产业。财政与金融政策大力支持农业,对农业产业化生产进行重点扶持,将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组织有效结合,保证优势农产品经济结构得到有效调整,逐步形成优势产业经济区,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三)财政与金融政策大力支持社会事业建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短期内通过有效的财政与金融政策也难以调整到平衡状态。所以,社会事业的发展对需要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但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段,政府的财力投入是有一定限制的。财政金融支持社会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注重着力点的寻找。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例如,税费优惠,财政补贴,货币政策的运用,积极有效的促进我国非农业产业较快发展,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扩大我国就业市场,保证一定的就业能力。充分有效的发挥财政职能,完善管理体制以及各项社会保证制度,加大社会保证的覆盖率。严格贯彻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保证财政金融支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有效控制不同层次的人们收入差异的合理性。调整财政金融支出结构,增强财政金融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支持力度,保证社会公共事业积极有效的发展。
三、结语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财政与金融对策的有效实施,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财政与金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科学合理的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对于国民经济,国家产业机构调整,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尽管我国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相信有效的利用国家财政与金融政策一定会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最终使得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看文献:
[1]陈国绪.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财政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6(8).
[2]王京芳,杨艳,李振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的对策研究[J].西安,2009(2).
文化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波士顿矩阵 经济政策 社会政策 协调安排
党的十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明确了奋斗方向。为满足这一总布局要求,顺利实现奋斗目标,在政策安排上必然要求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政策进行统筹协调,实现同步发展。
经济社会政策的不同视角
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达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为增进经济福利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而社会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
从性质上看,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增进经济福利,也就是人们的各种欲望或需要所获得的满足和由此感受到的生理幸福或快乐。从个人角度看,经济福利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个人收入的高低,个人收入高,个人福利的数量就多,个人收入低个人福利也就少;从公共角度看,经济福利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投资的多少,政府投资多,由公众共同无偿消费的公共产品多,公共福利就多,投资少公共福利也就少。而社会政策的目的在于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国家依法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
由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性质侧重点不同,其目标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通常认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效率,经济政策主要就是为了加速经济发展,为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增加政府公共积累从而加大政府投资服务。而社会政策的目标在于平等,社会政策主要就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公民平等地享有一定生活水平服务。
因此,虽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但在侧重点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政策安排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必然也有其各自的侧重,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安排组合。
经济社会政策的平衡
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安排实践过程看,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改革开放,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由政府统一配置社会资源,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实施都由国家一手包办,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效率与公平的对立,即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分野还不是那么突出,或者说没有太多引起人们的关注。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政策的实施上,包括少数民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较多地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安排在相互对立的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平衡,造成社会政策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的认识和现实。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人们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随着社会的转型,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促进社会公平的意义日益显现,人们对体现公平的社会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政策安排上,社会政策的认识、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了进一步解释,提出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已经提出,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没有出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007年党的十七大,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并且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2012年党的十,科学发展观正式列入党的指导思想,报告中也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所以从政策实践看,改变社会政策次要、从属地位的思想,促进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的平衡和协调是现实的选择和发展的必然,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从实践结果看,不同的政策安排组合有不同的利弊,经济政策优先模式,即首先考虑效率,公平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或经济发展后再解决公平的模式有其局限性,结果就是经济取得了发展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给社会政策造成压力。而社会政策优先模式,即首先体现公平,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解决公平后再发展经济的模式也有其不足,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公平的物质基础,这种公平也是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公平。所以,在政策安排组合上,需要结合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具体运作,最佳的组合安排应该就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同等的组合安排,协调作用,效率与公平同时兼顾,二者共同发展,没有偏废。
基于波士顿矩阵的经济社会政策安排
(一)经济社会政策现状指标选择
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析指标很多,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衡量指标,从综合角度看,比较可行的是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很好地体现经济、社会政策的现状,因为:第一,指标涵盖面广。指标体系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等六个方面共23个具体指标。就社会政策的范畴而言,广义的社会政策包括国民福利、就业、住房、健康、文化、教育、人口、婚姻与家庭生活、社区及社会公共环境以及宗教等。所以这些指标涵盖面非常广,基本上涵盖了经济与社会的主要方面,能较好地体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现状。第二,指标依据与政策目标一致。国家统计局制定统计监测指标主要的依据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也是经济社会政策协调安排、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最终目标。第三,指标选取协调性强。指标选取全面、客观,可操作性、逻辑性强,指标选取考虑了经济、社会各方面,既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也考虑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要求,概念明确、内容清晰,能够实际计量或测算,且整个指标体系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统一整体,各个指标之间相互制约、协调一致,符合经济社会政策协调安排的要求。第四,数据来源权威。其统计监测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和政府依法公布的官方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地方监测数据也来源于各地方政府正式的官方数据。这些数据能够得到公认,符合经济社会政策安排的权威性要求。第五,指标数据容易获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后,国家统计局和地方各级统计机关每年都会对全国及各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进行统计监测,并正式统计监测结果,指标数据获取渠道正规、固定且比较容易。
(二)经济社会政策现状指标计算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考虑到六个方面23个指标权重因素,按照经济、社会政策平衡协调的要求,将指标体系重新划分为经济、社会两大类(见表1)。将指标体系中经济发展5个指标(权重29)、社会和谐5个指标(权重15)分别作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现状指标不变。将生活质量方面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权重6)及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权重5)、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权重6)和资源环境方面的单位GDP能耗(权重4)等四个指标归入经济政策现状指标,其余指标归入社会政策现状指标。调整后的指标为反映经济政策现状类共9个,权重50,反映社会政策现状类共14个,权重50。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设定的标准值和各地区实际值,按照监测指标指数(实现程度)的计算方法,可以分别计算23个经济、社会政策具体指标的实现程度,并依此可计算出经济政策实现程度和社会政策实现程度,也就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现状。
经济政策实现程度=,社会政策实现程度=,其中:Zi为xi的无量纲化值,xi为第i个指标的实际值,wi为指标xi的权重。
(三)基于波士顿矩阵的经济社会政策安排方法
波士顿矩阵(BCG Matrix)又称市场增长率—相对市场份额矩阵、四象限分析法等,由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波士顿咨询公司创始人布鲁斯·亨德森于1970年首创,是一种用来分析和规划企业产品组合的方法。波士顿矩阵一般以销售量增长率和市场占有率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产生四种不同性质的产品组合类型,形成不同的产品发展前景并采用不同的战略对策,核心在于解决如何使企业的产品品种及其结构即产品组合类型适合市场需求的变化,使企业的生产有意义。经济社会政策的安排可以借助这一分析原理,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当作波士顿矩阵的产品,以经济政策实现程度和社会政策实现程度两个因素作为衡量依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形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同的政策组合类型,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经济、社会政策决策,来使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数量及结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波士顿矩阵的修正。将某一地区经济政策实现程度和社会政策实现程度进行组合,在坐标图上,以横轴表示经济政策实现程度,纵轴表示社会政策实现程度,各以80%作为区分实现程度高、低的中点,将坐标图划分为四个象限,依次为“问题”、“明星”、“金牛”、“瘦狗”。在使用中,各地区按经济、社会政策实现程度归入不同象限,使各地经济、社会政策现状一目了然,同时可以通过政策现状所处不同象限的划分,使各地政府对处于不同象限的政策现状作出不同的政策决策,以保证其不断改善政策安排,保持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协调组合,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
在经济、社会政策实现程度高、低的中点确定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纳入监测的六大方面实现程度都在60%以上,最低的文化教育方面实现程度为68%,高的已经达到90%以上,民主法制方面的实现程度已经达到93.6%,而各地的实现程度也大多在60%以上,所以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衡量标准,在波士顿矩阵修正中可以将经济、社会政策实现程度高、低点确定为100%和60%,相应的实现程度中点确定在80%。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在以后的运用中,可以修改评价指标的标准值,提高标准值的目标要求,同时也可以对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调整,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实现程度高点、低点和中点的衡量标准也就随之调整。
2.四象限政策组合安排决策。按照修正的波士顿矩阵,可以构建如图1所示的经济、社会政策组合安排矩阵图,图1中分为明星政策、金牛政策、问题政策和瘦狗政策四个象限。通过各地计算的经济、社会政策实现程度的数值,根据横坐标上经济政策实现程度数值和纵坐标上社会政策实现程度数值相互交叉的点就可以在矩阵图上确定相应的象限,并可以依据不同象限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安排对策。
明星政策:它是指经济、社会政策指标实现程度都高的象限内的政策安排。这一组合表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协调、平衡安排,符合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后续政策安排上需要采取保持策略,继续实行经济、社会政策协调安排的对策,不断加大和协调经济社会政策安排,让经济社会取得更大发展。
金牛政策:它是指处于社会政策指标实现程度高而经济政策指标实现程度低的象限内的政策安排。这一组合表明该地区实行社会政策优先的政策安排,虽然能够体现公平,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但经济发展程度不够,缺乏强有力的物质支撑,无法在社会公平上发挥较大作用。在后续政策安排上需要采取经济政策优先策略,在保持社会政策发展的同时,优先加强经济政策的安排,让经济快速发展,为社会公平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问题政策:它是指处于经济政策指标实现程度高、社会政策指标实现程度低的象限内的政策安排。这一组合表明该地区实行经济政策优先的政策安排,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物质积累较多,但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公平的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程度不够,社会公平得不到保障。在后续政策安排上需要采取社会政策优先策略,在保持经济政策发展的同时,优先加强社会政策的安排,建立健全体现社会公平的保障制度,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社会公众。
瘦狗政策:它是指经济、社会政策指标实现程度都不高的象限内的政策安排。这一组合表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发展都存在不足,一是发展程度不高,在指标上都达不到80%的实现程度,二是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没有同步发展。在后续政策安排上需要采取刺激经济、社会政策快速协调安排的策略,一方面要花大力气,加大经济社会政策安排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协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安排,让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单项政策的安排决策。虽然在政策决策中需要考虑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组合决策,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受具体指标的影响,因此,除了对经济、社会政策进行组合安排决策外,还需要通过对23个具体指标实现程度的计算,对各指标进行具体研判,按照各指标标准值的要求,找出实现程度与标准值之间的差距,进而采取相应的政策决策,实现程度低的指标需要在政策安排上加大力度,作出政策上的倾斜和照顾,加快指标所反映的经济或社会快速发展,直至达到标准值的要求,最终符合经济社会政策协调安排,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
(四)基于波士顿矩阵的经济社会政策安排的作用
借助修正的波士顿矩阵四象限分析,对科学研判各地经济政策安排现状,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政策安排组合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明确经济社会政策现状衡量指标。利用新划分的国家统计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可以对各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现状进行定量评价和衡量,改善以往经济社会政策衡量指标定量性不足的问题,为各地对政策安排和决策进行定量分析打下基础。可以提供经济社会政策安排评价方法。通过波士顿矩阵四象限分析,可以对各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安排现状进行研究和评价判断,弄清楚各地在政策安排中属于明星政策、金牛政策、问题政策还是瘦狗政策安排,进而分析政策安排优点及不足,从而使各地对经济社会政策现状有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为后续政策安排决策提供依据,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可以提供经济社会政策安排决策策略。在不同的政策安排现状分析基础上,可以结合各地实际,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安排策略,明星政策需要采取保持策略,金牛政策需要采取经济政策优先策略,问题政策需要采取社会政策优先策略,而瘦狗政策需要采取刺激经济、社会政策快速协调安排的策略。
可以改善经济社会政策安排现状。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但由于受传统经济体制和各地区发展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在传统政策架构和具体政策安排实践中各地都以效率优先和经济发展为导向,普遍存在政策安排中经济政策多而社会政策少的问题。通过政策组合安排的科学分析,可以改善当前各地政策安排中普遍存在的不足,促进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协调安排。
总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要求,在政策安排上需要科学统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协调,促进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文化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政府;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功能配置;功能缺位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日渐式微以及布尔迪厄、费瑟斯通等为代表的消费主义走向高潮,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得以解困,代之而起的,是世界文化市场的利益竞争潮起潮涌和文化产业财富效果的万众瞩目,各国政府或先或后地在文化消费时代选择其以利益为核心目标的文化政策取向,哪怕是困境自知中的“像奥地利这样一个小国,被巨大的文化产业伙伴国家所包围,面对全球化的文化产业和欧洲媒体集团,既无经济实力也无资源优势与之竞争,尤其无法与利益兴趣仅仅在于巨大市场的美国相提并论”①,也不得不被动性地深度卷入到文化产业的在场状况之中。同样也就在类似的卷入事态中,作为小国家的韩国创造了文化产业大国的奇迹,创造了“截止2006年初,韩国的文化产品,包括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等等,已为亚洲观众所广泛消费” ②的所谓“韩潮”(Korean Wave)时代。
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在经历了港味、台风、美国大片和韩潮等阵阵流行文化风暴的冲击之后,终于在渐缓渐进中接受了文化产业观念和文化消费方式,继21世纪初旗帜鲜明地选择了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之后,又于2009年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编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样一种历史大跨越,不仅在于革命性地转折于从前单一性的“为人类文化进步不断创造新的贡献” ③,而更在于极度夸张地亢奋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归根结底在于支撑这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是否有活力。因为,只有第三产业中的新兴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才能带动这个国家的经济朝着创新、现代、高层次、不可复制的方向提升,也才能使一个国家从资源匮乏、能源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苦恼中解脱出来” ④。
正是由于转折的非线性进程和亢奋的非理性情绪,使得中国文化产业的存在现状体现为既轰轰烈烈又乱象纷纭,至少在政府与文化产业的结构关系上枝蔓纠缠甚至暧昧牵系,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因而也就有必要在政府的文化制度创新中重新拟设政府文化产业治理的功能编序,并在广义产业引导命题下形成有效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从而使政府在应有的主体位置聚焦对文化产业推进的制度保障力量,以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作用保障中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顺利实施。有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围绕边际明晰的广义产业引导命题,讨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制度支撑究竟何在。
全面审视各级政府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就会不难看出,其着力点恰恰就在于政府与文化市场之间关系十分暧昧,文化市场的市场主体性和自衍功能结构在政府文化产业推进行动中被完全漠视,政府的政策主体性以及对文化产业的有效调节在文化市场的非规范性利益追逐面前,其产业导向作用微乎其微,文化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经济政策的重要构成单元,其所应该具有的“通过政府的想象力实现对事态强有力而且异乎寻常的穿透” ⑤以及“通过诸如利率变化等调控手段来达到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增长稳定性” ⑥等能动作用,都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挥。其被动结果就是,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缺位之下,文化产业主体到处充斥政府文化事业单位权力操作“事改企”型制的文化翻牌公司,规模性资本在文化产业风险系数N不确定值面前望而却步,产业边际模糊和产业框架支离破碎背景中产业链难以形成和延伸,已经出台的文化产业政策没有无缝隙化的内置谱系和功能嵌合的外部制度接口,改革开放30年经济体制改革所积累起来的产业治理经验尚未在文化产业的政策面得到全面落实,主要主管部门空洞口号多而实证性、可操作性和标准计量性的具体政策内容少,诸如此类,成为推进中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产业制度障碍。
导致现实格局形成的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但经过梳理还是能够寻找到几个关键性纽结,那就是(一)叠合型政府治理结构及由之产生的文化产业政策功能配置紊乱,(二)缝隙型政府治理结构及由之产生的文化产业政策功能配置遗漏,(三)权力型政府治理结构及由之产生的文化产业政策功能配置失灵。
(一)叠合型政府治理结构及由之产生的文化产业政策功能配置紊乱
叠合型政府治理结构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矛盾显现,是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并产生文化产业分工后的必然产物,因为政府文化主管的叠合结构是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高度统一背景下的历史产物。在意识形态文化治理模式中,不仅文化领域被拟定为“阶级对抗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都是对立的思想和意向激烈斗争的战场” ⑦,而且文化治理的目标也单一绑缚于“社会主义文化需要而且包括对人类价值整体体系的发展、塑造、适应和了解,所有这些社会主义人文价值都要在具体化中发展、吸收并纳入到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之中来加以认识。这些价值决定着社会行动的本质的而且是首要的目标以及走向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不断地被托举到高度精神化和充满激情的存在水准” ⑧。
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文化治理中出现机构叠合、职能叠合、政策叠合乃至操作程序叠合等,不仅不会影响政府效率诉求的“通过最有效的选择和最节省的成本达到治理目标” ⑨,而且还会由于同一过程的不断强化形成“文化战线”更多“文化战士”的“战斗”合力,从而更加有利于政府文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市场经济转型尤其是文化产业命题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完成其合法化确证以后,政府文化治理的极端意识形态原则和单一计划方式让位于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原则和多元化市场博弈方式,文化市场所链接起来的无论是生产主体还是消费主体,都会在公共文化品介入层面共同建构消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均衡维系力量既有来自政府的一极亦有来自市场的一极,多样化以及普遍参与的公共性文化事态,迫使政府文化治理成为该事态中的一种博弈力量,也就是只能有一个主体、一种声音和一以贯之的政策出场。
当叠合型政府文化治理结构面对新兴文化产业之际,就会显现为多头政府的重复介入,这种重复介入的直接后果:
一是政出多门,即不同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都在给定的权限制订相应的文化产业政策出台,这些政策或者指向不同的文化产业具体领域,或者指向相同的文化产业具体领域,而对于规模以上多种经营并且涉及多个具体生产领域的文化企业而言,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来自相同指向或者不同指向的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它们的政策主体。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主体分置的权力利益单位会形成“各自追求对政策制订权利的占有……特殊利益影响政府决策” ⑩,这些共同文化产业指向和不同文化产业指向的政策内容之间往往失去功能均衡以及操作协调,特殊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政策主体之间的所指冲突,导致公共文化事态和文化产业领域政府施政的混乱局面。之所以网络游戏业管理中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行政程序和监管尺度彼此多有抵牾,之所以全国各地各种名目的所谓“国家文化产业基地”竟来自中央政府完全不同的文化治理序列,之所以同一文化企业在面对不同文化产业政策文本来源之际经常会莫衷一是,说到底就是政府文化治理结构中政出多门的必然产物。
二是行政损耗,即文化市场不仅表现为宏观存在结构的统一性,而且表现为微观存在结构的产业链完整性,对于文化生产、文化生产者和文化生产企业来说,生产目标、生产方式、生产成本乃至生产过程等是他们所关注的核心所在,而文化样式、符号介质和产品归属等,则完全根据市场行情和消费需求变化等给予动态性任务调整和灵活的生产安排。
例如,不同文化生产领域的“关于文化产业劳动过程的批评相对较少”B11是针对所有文化产业领域而非某一文化产业领域。但是在文化产业治理的叠合政府结构中,政府强制性对统一的文化市场进行拆分管理,同时也把有机完整的文化产业链进行行政主管的行业切分,由此就出现当一个特定的文化企业进行《西游记》的产业化开发生产,其舞台产品形态隶属文化部,纸质印刷产品形态隶属新闻出版总署,影视产品形态隶属广电总局,而网络游戏产品形态,其隶属的政府主管部门除此三家之外还将延伸出更多的管理方。
这样一种治理结构,不仅会给文化产业秩序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而且会给政府文化治理带来严重的行政耗损,其耗损本身既包括产业监管中执行力的弱化,也包括不同主体所形成的政策内容之间内在的决策力抵消,还包括行政责任诉求中产业主体的政策受益成本及其政策影响效力。行政耗损的负面后果不仅会波及到政府失灵,而且会波及到市场效率减值,例如涉及到产权问题的“政府的另外一个职能就是所有权的界定,而所有权就是得到政府保护的可利用且可交换的权利”B12,如果由于行政耗损而使这种界定滞缓或者模糊,就将直接给文化企业的文化生产与市场营销带来一系列根本性的障碍,从而也就形成政府与文化产业关系中的体制掣肘,所以巴西早在1931年文化产业起步阶段就“颁布一项政令,赋予国家在基于民族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广播服务,建立特殊制度和程序,定义特殊产业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B13。
(二)缝隙型政府治理结构及由之产生的文化产业政策功能配置遗漏
缝隙型政府治理结构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矛盾显现,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非同步性的必然产物,因为政府一方面迫切希望文化体制获得对文化产业的制度支撑功能,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达到与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平行性体制换算的改革水准,于是作为新兴产业类型的文化产业兴起之后,就很难嵌入国家产业体系的整体格局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型产业链。就市场经济的总体原则而言,文化市场不过是市场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的市场游戏规则及其支撑市场的基本经济政策,同样也就是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制约力量和维系功能。与此相一致,文化产业不过是一个国家整个产业框架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一截链条,共同的产业环境及其支撑产业的基本产业政策,同样也就是这一环节或者说一截链条的动力所在。
正因为如此,政府的市场治理结构和产业治理结构也就必须保持其系统性、严密性和整一性,其制度张力和行政治理程序同样也必须保持其全称覆盖和连续稳定性,由此确立政府与市场和产业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其监管合法性,而且确保边际内市场竞争和产业竞争强度与稳定性所需完整市场结构的“共同占有统一市场均摊”B14,确保“政府直接抑或间接对产业领域进行补贴并提供贸易保护”B15时能够公平性排序。
当一个生产性文化企业进入国家产业布局宏大结构之后,就受到整个产业结构所面临的诸如市场准入政策、公司治理政策、投融资激励政策、税率优惠政策、价格调节政策、经营监管政策、进出口贸易政策、劳动就业政策乃至生产安全政策等一系列谱系化政策内容的运营覆盖,任何文化企业在进入这种运营覆盖中都将经历市场适应,并进入在嵌位性适应后寻找自身理想的附加值效应,其中包括加价与整个产业背景和市场现状间的允诺可换算性,即所谓“很多清晰区分的价格模型能够被引用,用以解读每一种产业怎样确立其附加值,在所有情况下,附加的确定似乎都取决于公司运营的制度环境”B16。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产业的全面市场化和在市场中自然衍生其产业链,必须以既有大产业背景及其产业政策的谱系完形为存在前提,必须使文化产业政策的创新部分与宏观市场经济政策框架全面接轨和嵌位性包容,这意味着专属经济政策与普适经济政策将在新型的文化产业进程中产生市场化前提下的功能链接,所以产业经济学家谆谆告诫文化产业进入者们“当经济版图如今更加扩张,创意文化生产者们从事着高尚的努力,去颠覆或者抛弃‘纯粹的’资本价值――通过创设创意性的录音公司、艺术雕塑室和画廊、时尚屋、咖啡厅、美术设计、书店、新媒体企业等等――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这些创意性的产品具有高附加值,但仍然不能把资本的可怕力量降到最小化”B17。
按照这一问题脉络,中国文化产业当下的症结性问题之一就在于,我们至少在政策层面过多地对“文化产业”命题作主谓结构的语义定位,而本题真相却是偏正结构的语用实践,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把“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体制支撑点而不是把“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体制支撑点,影响政策视野的是创意的浪漫及其所谓“作为商品,文化产业的产品遵循变化的法则,其变化原则的支配性在于文化的真正的创新”B18,视而少见甚至视而不见的是诸如宏观经济理论的“通过全时段典型生活经验的跟踪,消费价格指数(CPI)能监测特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当CPI增长得过快(大约超过年度4%),货币购买力迅速减少,借贷货币成本增加”B19,或者更加技术化的诸如拉斯贝尔斯指数(the Laspeyres index)的“P10≤P0X0/p0x0,同样原则的P01≤P0X1/p1x1”B20。
这种重心错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直接反映,就是文化部门按照文化意志为文化产业给定产业政策,而不是具体经济部门以及综合经济部门对文化产业行使政策导向和产业监督,于是绝大多数产业政策和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对文化产业而言就成了院外风景,经济领域里的许多常规经济技术分析都因此而未将文化产业纳入其可操作程序,对文化产业而言,一个细节性的负面后果就是产业规模、经济效益和环比增速等统计项目在中央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省市区之间都没有恒值性统计规范和一致性统计口径,足见文化产业隶属文化治理对象而非经济治理对象的歧义性之大。而这一歧义性的进一步事态还在于,由此带来文化产业在产业运行中的一系列政策缝隙,一系列市场活动中必须承受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一系列市场嵌位和产业并轨中的文化部门“热抱”与经济部门“冷抛”,由此不断出现文化产业政策配置中的功能遗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功能遗漏之一是指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具体的产业政策,因这种遗漏而失去对文化产业的有效功能覆盖。
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应对计划,在拉动产业经济止跌递进中实现“保增长、保民生”的战略目标,然而文化产业却不能占据其中重要的一席,总量投资份额中几乎没有文化产业的投资配额,尽管在这期间不少文化高官违背经济规律地呐喊“文化产业逆势而上”、“在拯救中国经济中已获最好的跨越式发展机遇期”、“全国范围分发文化消费券以刺激市场”之类的雄壮口号,但综合经济部门还是未能给予积极响应,毫无疑问,不管何种选择更加理性,其中的决策非协调性及其政策缝隙显而易见。
功能遗漏之二是指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产业方式,很多旧有的产业经济政策并不能在企业运营中达到功能嵌位的目标,这就要求必须根据新的问题焦点进行政策创新,综合经济部门如果不能适应创意产业的新变化,就将失去对这一新兴产业领域的有效治理能力。
明显的案例之一,就是网络游戏产业一方面提供了巨大的运营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却也带来诸多负面社会后果,如何在提高技术装备能力和技术控制有效性的同时,通过政策建构来全方位规范网络运营监管及预设负面社会后果防火墙,就成为中国网游产业摆在一切涉身者面前的严峻课题,而目前的情况,恰恰就在于这样的政策建构基本上缺失或者不能嵌位,从而造成全社会嘘声沸起的被动局面。
功能遗漏之三是指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从与其它产业经济部门的整体框架中分割出来并形成文化市场的独立边际维系,造成事实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完全覆盖、具体产业政策的缺位或者越位以及文化产业治理与监管中的陌生化和非规范性。
最大的案例之一就是,就中国的文化产业现状而言,整体上缺乏市场监管和产业规范的指标体系,诸如质量指标体系中信息质量测算的“数据质量通常运用传统的总体性质量管理评价来进行管控”B21、人力资源指标体系中薪酬结构测算的“不同工作(工作结构)的相对薪酬以及究竟支付多少(薪酬水平)”B22或者企业成份分析指标体系中所有权结构测算的“如果所有权结构适应了规范管理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可以设定,在这些跨公司结构中的差异反应了公司潜在本质的差异,以及它们赖以运行的条件的差异”B23,在文化产业的文化重心持论者那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这种忽略不计在目前各级各类主管文化产业政府部门的政策文本里得到充分体现。
(三)权力型政府治理结构及由之产生的文化产业政策功能配置失灵
权力型政府治理结构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矛盾显现,是中国问题背景下意识形态空间与公共性空间长期未能获得边际清晰切分的必然产物,因为政府在对文化产业作本体挪位之际就意味着极有可能在政策层面不断出现对公共利益坚守的诸如“政府机构如何进行财政管理,从而达到遵从法律要求、会计标准、财务控制,并且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最优化”B24给予淡化处理甚至悬置,转而在文化价值维度作意识形态重心取向的“鼓励艺术和文学表达的阶级意识形式”B25,于是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产业寻租的本体置换就导致政府循此走向权力型治理结构的文化制度设计和文化政策给定。
在对文化产业施以权力型制度文化治理结构中,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还停留在居高临下或者大包大揽的文化管理传统定势,还热衷于项目审批、基地命名和宣传效应等行政化乃至意识形态化的调节手段,还诉求着在激励与权威均衡的“在走向共同对象的生产中所有个体及其团队变得更加自我约束”B26中展现文化行政权力对文化产业的支配作用,即吻合于韦伯《支配社会学》所描述的“‘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的确,并非所有的共同体行动皆含有支配的结构,然而,在大部分种类的共同体行动中,支配仍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尽管乍见之下似乎并不明显”B27。
正是这种支配性意志的制度性存在,使得政府在文化产业治理中总是按照主观意志和理想发展方式去规划文化产业进程,去实施文化产业超常规而且跨越式的经济振兴行动,去组建不同规模的产业主体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制性地催生“事改企”之类的翻牌文化企业,去塑造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和产业升级换代形象,总之,政府作出种种支配市场的努力。
但问题恰恰就在于,政府既支配不了文化市场,亦支配不了文化产业,它在监管和支撑过程中只不过是市场博弈力量中一个重要的力量维度而已,即使是文化产业制度或者文化产业政策,也只不过是市场大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关键性存在条件和运营环境,因而也就不可能根本性地决定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前途命运,弗罗里达的文化产业“3T模式论”之所以引申出“社会资本、经济的地缘根性以及制度参与者的重要性”B28,就在于这一模式持文化产业的反支配论见解。
按照这样的问题思路,政府以支配姿态确立的权力型文化产业治理结构与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自衍系统之间,就形成了双向反弹的动力抵消格局,进而也就必然与之相一致地出现功能配置失效。
功能失效的表现之一,在于社会动员的宣传失灵。
无论是政府还是热情加盟的知识分子阵营,自文化产业的中国合法性确立直至今日,基本上都在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诸如文化产业的定义、意义、经济增长价值以及支柱产业目标等的学理宣传和社会动员,报纸和各种社会科学期刊上这类文章琳琅满目,专业座谈会和大学讲堂这类演讲比比皆是,关于文化产业的财富主义神话在风险危机避而少谈的渲染中一国为之亢奋,于是那些哲学知识身份、文学知识身份、艺术知识身份以及种种身份不明的泛文化身份者,摇身一变就成为动员官方同时又帮助官方动员社会的文化产业先锋甚至预言家,文化产业的社会动员呼声和社会动员行动由此也就像既往任何一次大规模宣传运动一样,成为不言此则与社会隔离的热门话题,成为自明性的“在从意识形态承诺走向自由市场中,基于市场指向的文化政策证明具有优先性”B29。
尽管这一过程已经经历了较长一段时期,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在自拟的统计口径下纷纷宣称文化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尽管关于文化产业重要性的文章成千上万而且大学里到处都在招收该专业的博士、硕士乃至本科生,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产业领域并未获得大规模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和风险资本的转移与聚集,各地宣传的要到国际文化市场参与竞争的产业航母其桅杆还未见露出遥远的东方地平线,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就业规模和消费刺激等方面还无法真正实现对文化产业的依赖和寄望,社会的文化产业响应甚至进一步的文化市场响应也不像预言家们所描述的那么具有逆势而上的热烈。市场就是市场,产业就是产业,宣传性的社会动员结果终究陷入无可奈何的宣传失灵,终究没有在这一领域同步性地出现本该出现的“依靠其人口、地理、经济增长以及军事实力,中国已经是东亚的重要角色,而且按照某些观察而言,它已经是最大而且最重要的角色”B30。
功能失灵的表现之二,在于直接参与的操作失灵。
当文化产业观念渗透进政府意志之后,各级政府的直接参与热情远远大于间接监管建构,不是积极为文化产业搭台唱戏而是纵身一跃自我表演,其目的在于尽快依靠政府资源将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甚至不排除新形势下某些变形政绩观隐匿其中。无论是新组建各种动漫集团、传媒集团、图书发行集团、演艺集团,还是“事改企”中成立各种经营性、生产性的文化翻牌公司,无论是政府公共财政的直接投入,还是国有文化企业银行贷款的政府担保,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文化企业主体和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不是交给市场去利益化主体自衍和博弈性产业聚集,而是政府直接充当生产经营与产权交易的操盘手,而且是一方面变身为运动员另一方面又倚仗其裁判身份,于是市场经济基本游戏规则的诸如“准入条件与产业聚集”的“qL=qc(1-1s ),在这里,qc对所有企业而言是边际成本等值价格所决定的竞争性输出,s是市场规模”B31也就不复存在。
但是,市场是严酷的,产业更加严酷。一段时间的政府直接介入之后,不仅不同程度地放弃了诸如“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基于CPI的指数比调节会降低利率和间接税收所带来的变化影响”B32,而且凭空添出许多烂尾文化产业园、银行里的政府性呆账以及“高价买体制”后仍然经营托底的翻牌文化公司,所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进化过程中政府所买过的产业教训单,如今在文化产业的操作性实践中又重新买了一遍,而且还有继续买下的迹象。这一事态从开始到现在,尽管不乏鼓舞人心的消息,然而总体体现的是政府在文化产业中的操作失灵,即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得心应手于“一种现实的、新的电影产业应运而生,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和成长,在人民的权力条件下发展和成长”B33。
功能失灵之三,在于条件缺位的政策失灵。
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在市场大背景下寄希望于政府的首先就是产业环境和政策给定的产业支撑条件,没有这些起码的条件,则文化产业就不可能在利益博弈的市场空间生长和进化。按照“政策是制度的输出”B34这一政策学命题,应对文化产业诉求并充分体现政府对文化产业制度支撑功能的,就在于提供功能化而且体系化的文化产业政策配置,为文化产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服务和市场监管,这既是政府的权利同时也是政府的责任。
但问题恰恰就在于,由于政府没有集中精力从事文化产业的政策建构,所出台的政策往往应时而作且彼此之间缺乏功能嵌合的内在联系,更谈不上对文化产业制度支撑的谱系完形,因而也就难以形成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条件。
例如在银行信贷方面,虽然大多数金融机构权衡国际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极其愿意给文化企业提供贷款,但是,文化企业固定资产的匮乏又缺乏自我担保条件,在传统的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和信贷政策框架内,几乎就绕结出一个困扰文化产业资本聚集的死结。
于此情况之下,政府就必须根据文化产业的产业特性,组织协调央行与商业银行积极制定新的信用评估体系和担保政策,使得“如果银行提前审视,则资本减持时贯穿商业循环中的周期性波动就能被预见到”B35,从而促使风险管理的诸如“全程非可控性及其累积性变量”的“如果赢利具有零意味,那么所见到的变量是贯穿那一时期从t上升到T的累积性变量的公正计算:可给出赢利R(S)的变量:O2(S):=E(R2(s))”B36,转化为政府托举意义上的政策支持,最终有利于风险分担后金融资本向文化产业的倾斜性输出和寻租性转移。
当然,这只是文化产业发展政策诉求的一个细节,就整个产业界面而言,充斥着无数急需政府给予有效填充的这样的细节,所有这些高密度的政策细节需求,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依托共同构成对文化产业政策的体系性要求,而目前政府在文化产业推进中之所以频频出现政策失灵,其根源恰恰就在于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的缺失,进而也就是市场环境和产业条件的缺失。
① Herbert Hofreither, Austria: Small Country with Grand Culture?――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Policy, Art Fund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Margarete Lamb-Faffelberger(ed), Literature, Film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 in Contemporary Austria, Peter lang Pulishing, Inc.2002, P.8.
② Doobo Shim, The Growth of Korean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Korean Wave, In Chua Beng Huat and Koichi Iwabuchi(ed), East Asian Pop Culture: Analysing the Korean Wav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
③ Bai Liu, Cultural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esco, 1983, P.55.
④ 邵培仁《文化产业经营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⑤ Joel S.Migdal and Klaus Schichte, Rethinking the State, in Klaus Schichte(ed), The Dynamics of States: The Formation and Crises of State Dominati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P.17.
⑥ Thomas R.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2, P.149.
⑦ 莫•卡冈著,凌继尧译《卡冈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9页。
⑧ Hans Koch, Cultural Policy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Unesco Press, 1975, P.10.
⑨ Grover Starling, Managing the Public Sector, Harcourt, 2002, P.127.
⑩ Michael E.Kraft and Scott R.Furlong, Public Policy: Politics, Analysis and Alternatives, CQ Press 2007, P.66-67.
B11 Mark Bank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5.
B12 Deborah A.Stone,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Decision Making, Nor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P.66.
B13 Scott Lash and Celia Lury,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The Mediation of Things, Polity Press 2007, P.155.必须指出,此处是指媒体产业化背景下的政策状况,巴西的广播业产业化,时至今日在中国仍然没有实施,各级电视台、电台或其它平面媒体的市场运作和产业性生产行为,基本上还是在十分暧昧的“双轨制”中进行,这实际上也构成对中国媒体业发展的保护性负面效果。
B14 Harold Demsetz, 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Firm: Seven Critical Commenta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9.
B15 David B.Yoffie, American Trade Policy: An Obsolete Bargain, in John E.Chubb and Paul E.Peterson(ed), Can the Government Gover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9, P.11.
B16 St phane Ngo Ma and Frank Sosth , Product Markets, in Richard Arema and Christian Longhi(ed),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 Springer 1998, P.375.
B17 Mark Bank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57.
B18 Deborah Cook, The Culture Industry Revisited: Theodor W.Adorno on Mass Cultur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6, P.29.
B19 H.Lee Martin, Techonomics: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2007, P.175.
B20 S.N.Afriat and Carlo Milana, Economics and the Price Index, Routledge 2009, P.230.
B21 Martin J.Eppler, Managing Information Quality: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in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s and Processes, Springer 2006, P.28.
B22 Raymond A.Noe, John R.Hollenbeck, Barry Gerhart and Patrick M.Wright, Human Resourse Management, Mcmillan-Hill Companies, Inc. 2006, P.364.
B23 Harold Demsetz, The Emerging, Theory of the Firm, Datapage International Ltd, 1992, P.42.
B24 Aman Khan and W.Bartlry Hildreth,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ory in the Public Sector,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4, P.1.
B25 Jaime Saruski and Gerardo Mosquera,The Cultural Policy of Cuba,Unesco 1979,P.22 1975, P.10.
B26 Marco Weiss,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Design: Balancing Incentives and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28.
B27 韦伯著,康乐译《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B28 Luciana Lazzeretti, Culture, Creativity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in Florence, in Philip Cooke and Dafna Schwartz(ed), Creative Regions: Technology, Culture and Knowledge Entrepreneurship, Routledge, 2007, P.174.
B29 Sarah Owen-Vandersluis, Ethics and Cultural Policy in a Glob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5.
B30 David C.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
B31 Jati Sengupta, Dynamics of Entry and Market Evolu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5.
B32 Yakir Plessner and Warren Young, Economists,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Israel: FromCrawling Peg' toCold Turkey', in Steven G.Medema and Peter Boettke(e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 P.304.
B33 Todor Zhivkov, The Cultural Policy of Socialism, Sofia Press,1986, P.72.
B34 Thomas R.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Pearson Education, Inc.2002, P.12.
B35 St phanie M.Stolz, Bank Capital and Risk-Taking: The Impact of Capital Regulation, Charter Value and the Business Cycle, Springer 2007, P.27.
B36 G nter Schwarz and Christoph Kessler, Dynamic Risk Analysis and Risk Model Evaluation, in George Christodoulakis and Stephen Satchell(ed), The Analytics of Risk Model Validation, Elsevier Ltd, 2008, P.151.
On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al Loss in Support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WANG Lie-sheng
(Center of Public Culture Policy Study,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文化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地方官员变更;政策不稳定性;经济增长;GARCH-in-Mean模型;
作者:杨海生
一、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发现,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稳定性对一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Barro,1991;Alesina&Rodrik,1994;Jones&Olken,2005)。以美国为例,由Baker等(2013)创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EPUIndex)显示,激烈的总统选举(多为执政党阵营转换时)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重大的危机事件,且这种由政权更迭带来的政策不稳定在近期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图1所示,2012年的美国大选使得当年下半年的政策不确定性大大高于过去25年,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选举双方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监管计划——奥巴马医改方案(Obamacare)——所持的针锋相对立场(1),以及对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财政悬崖(fiscalcliff)无望的拉锯战,致使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从上到下都充满了对政策稳定性的质疑。
图1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PUIndex):1985年1月~2013年3月
图1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PUIndex):1985年1月~2013年3月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mimeo。
资本市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最为直接,大选第二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2%,蓝筹道琼斯指数和大盘标准普尔指数也均创下3个月低点,国际油价更是重挫超过4%;据当时超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预测,仅财政悬崖带来的政策不稳定性便足以使经济增速下滑0.5个百分点。官员变更带来的政策不稳定性对企业投资、资本市场,乃至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同样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佐证(Julio&Yook,2012;Liu,2010;Durnevetal.,2012;Gulen&Ion,2012)。
在中国,政府周期性的换届和官员的人事变化,使得不同任期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宏观调控的具体手段都有所不同,从而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Imai(1994)发现,中国的经济周期呈现投资周期现象;Tao(2003)则进一步指出,自1987年以来,中国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四次峰值分别出现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召开的次年;张军和高远(2007)以及王贤彬等(2009)通过对省级官员变动数据的实证检验均发现,省长、省委书记的变更对其辖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曹春芳(2013)以及徐业坤等(2013)则进一步从微观企业投资的角度验证了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向联系。
事实上,除中美两国外,法国、俄罗斯、墨西哥、韩国、西班牙等56个国家均于2012年举行了政府换届大选(2)。不难想象,在这日显动荡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政府换届、内阁更替以及官员变动等政治事件的经济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的政治含义。因此,如何更准确地解读官员变更、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更稳定地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对更有效地实现各种经济调控措施的软着陆而言,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前瞻性与现实指导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1999~2013年全国近400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VAR框架下的GARCH-in-Mean模型,实证检验了市长及市委书记的更替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上述影响的政策传导渠道及作用机制。文章发现:(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2)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财政政策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短视性政策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信贷政策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3)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4)官员变更引起的财政风险主要产生于地方官员的执政阶段,而信贷风险却主要是在经济运行环节中积累催生的;(5)随着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地方政府的“计划性”职能特征逐步淡化,具有较强“市场性”特征的间接信贷调控职能正逐渐超越直接财政干预职能,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利用GARCH-in-Mean模型的创新设定,将政策不稳定变量及其波动率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实证模型,有助于区别考察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动因。虽然现有关于官员变更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均指出,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新上任官员急于刺激地方经济的“短视行为”造成的整体经济效率下滑(Bestley&Coate,1998;张军、高远,2007;钱先航等,2011),以及对政策变更的不确定性预期(Bernanke,1983;Ingersoll&Ross,1992;Panousi&Papanikolaou,2012;Pastor&Veronesi,2012),但当前的实证研究或者是将二者不加区别地视为一体,或者只是侧重考察二者之一。借助GARCH-in-Mean模型将解释变量的标准差同步引入回归方程的特殊结构,本文能够以官员变更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衡量官员变更造成的短视性行为和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更准确地考察影响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内在因素。第二,通过分解地方官员可操控的不同政策工具,更深入完整地刻画了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通常来说,从官员变更到经济增长波动,整个传导机制存在着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环节,即“政策工具选择”和“基础经济变量选择”。然而,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对后者已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大量文献表明,投资正是对官员变更所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最为敏感的基础经济变量(Julio&Yook,2012;徐业坤等,2013);但对前者的认识却仍存在相当大的空缺,李维安和钱先航(2012)利用市委书记与城商行的对应样本从银行信贷角度解释了官员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可以说是研究上述传导机制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环节的开创性工作。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本文通过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细致地讨论了不同政策工具在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建立起的纽带作用,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第三,通过VAR模型的构造,将政策不稳定性和经济增长作为相互依存的内生变量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尽管相当一部分文献都指出,经济增长对政策不稳定性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在中国特殊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之间甚至存在着“为晋升而增长”的GDP主义倾向(周黎安,2004,2007),然而实证研究却少有对这一现象的直接数据支持。本文充分考虑了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这种相互作用,利用VAR分析框架来考察二者的内在联系,完善了我们对二者关系的认识。
全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进一步的讨论;第七部分为文章的结论。
二、文献回顾
作为近年来最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课题,对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围绕着3个中心问题:(1)如何衡量政策不稳定性的程度?(2)政策不稳定性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3)经济增长又是如何影响政策不稳定性的?
(一)政策不稳定性的衡量:官员变更
目前,对政策不稳定性的衡量指标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响一个国家整体政治格局的宏观指标,包括战争、动乱骚乱、政变、刺杀、革命、起义、游行、政治清洗、国家分裂等(Venieris&Gupta,1986;Alesina&Perotti,1996);另一类则指的是在国家整体政局稳定的框架下对施政执政体系进行微调的微观指标,如政党选举、内阁成员更替、官员变动等(Glazer,1989;Perrson&Svensson,1989;Tabellini&Alesina,1990;Bestley&Coate,1998)。显然,后者的经济学含义远比前者的政治学含义更有助于我们解读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适合于分析类似中国这样的政权稳定的经济体。
事实上,由于决定经济增长的私人投资活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而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正是这些经济政策的直接制订者和执行者,因此可以说,官员变更是所有政策不稳定因素中对经济活动具有最直接也最强烈影响的一个变量。另一方面,由于官员的年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工作经验等特征存在本质区别,官员在其任期内的经济行为与政策决定大多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张军、高远,2007;王贤彬、徐现祥,2008;张尔升,2010),而这种异质性正是导致政策不稳定的一个直接根源。最后,进一步考虑到现有研究选取的衡量政策不稳定性的指标绝大多数均为虚拟变量(DummyVariable),只能定性地描述政策不稳定事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却无法定量考察政策不稳定事件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选取了可以进行连续度量的官员变动率作为我们的目标考察变量。
更具体地,目前虽然已有大量国外文献通过国家层面的“选举年度”事件来刻画上述的这一作用机制(Bialkowskietal.,2008;Boutchkovaetal.,2012),但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高度自治权以及宏观政策从制订到执行全过程的漫长时滞,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种变动对私人企业和投资者的经济决策来说显然过于宏观。特别地,在我国“政治分权”与“财政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下,城市层面的地方政府往往掌握着地方国企的经济管理权以及区域内行政审批、土地征用、贷款担保、政策优惠等重要资源,从而拥有了较大的“权力”去自主发展经济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傅勇、张晏,2007;周黎安,2007;Xu,2011)。与此同时,在相对绩效为核心的晋升体制下,地方政府大多承担着比上一级政府更大的经济压力,其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往往也就比上一级政府更加投入(Walder,1995)。因此,相较中央或省级官员而言,从地市级地方官员变更的角度来考察政策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疑更为直观和科学。
此外,由于我国城市层面的地方官员变更是一种常态,不仅每年均会发生,且每年发生的频率都不尽相同(王贤彬等,2009;李维安、钱先航,2012;陈艳艳和罗党论,2013),这种频繁性和差异化极大地完善了数据的统计特征,改进了时序研究的数据可获性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获得更为稳健的实证结果。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最终将实证研究的样本定位于地市级的地方官员变动。
(二)从政策不稳定性到经济增长
本文将分别从影响根源和政策传导工具两个角度来简要评述关于“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现有文献。
1.影响根源
当前研究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源自于两个因素。一方面,职务更替加剧了官员的短视行为,为了尽快和尽可能突出地在任期内做出成绩,多数官员倾向于采取诸如高投资或过度借贷等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短期刺激作用,但长期来看往往存在副作用的经济政策,本文将上述现象定义为政策短视性效应(policymyopiceffect)。这种由官员变更引起的短视性政策行为往往成为动摇经济体系稳定性的风险节点,降低了经济平滑运转的效率,并最终抑制了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通过检验官员任期时间与各种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绝大多数研究为这一政策短视性效应的存在提供了肯定的实证支持(Glazer,1989;Perrson&Svensson,1989;Tabelline&Alesina,1990;Bestley&Coate,1998;张军、高远,2007;钱先航等,2011)。
另一方面,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还会刺激微观经济个体形成政策不确定预期,进而抑制消费和投资积累,并最终拖慢经济增长的步伐(Barro,1991;Benhabib&Spiegel,1994),本文将这一现象定义为政策不确定性效应(policyuncertaintyeffect)。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官员变更往往会引起他们对未来可能面临的经济政策乃至政府决策机制稳定性的疑虑,因此,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一个理性的选择必然是观望和延迟投资(Bernanke,1983;Ingersoll&Ross,1992),进而延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遗憾的是,对这一影响根源的研究至今为止仍是相当零散和割裂的;更重要的是,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都找到了政策不确定性与微观经济活动负相关的实证支持,但却未能将政府行为推进到背后的实质性个体——官员,因而也就不能成为验证“政治观”的直接证据(钱先航等,2011)。
因此,为了更完整地考察政策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源,本文在借鉴Engle等(1987)以及Engle和Kroner(1995)思想的基础上,将政策不稳定变量及其波动率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实证模型,以直接考察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短视性效应和政策不确定效应的并存影响。
2.政策传导渠道
通常来说,官员的经济决策只有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才能最终传导至其决策目标——经济增长。因此,了解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是通过怎样的政策工具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政策工具来影响经济增长,是顺利解读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关键。实际上,已有大量文献表明,货币、财政以及其他监管政策的扩张行为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确有着显著的负效应(Friedman,1968;Hassett&Metcalf,1999;郭庆旺、贾俊雪,2009;吕冰洋,2011;王立勇等,2010;李连发、辛晓岱,2012)。
与中央官员相比,虽然地方官员可选择的政策工具相当有限,但随着以1994年分税制为标志的经济分权和行政分权改革的深化与推进,地方官员的决策力与其在地方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日趋显著。一方面,财政分权使得地方官员对地方财政收支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早在2009年就已超过了80%,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相应比重(3)。类似地,许多文献也从不同角度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以来地方政府支出的扩张性倾向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郭庆旺、贾俊雪,2009;赵文哲、周业安,2009;李涛、周业安,2009;方红生、张军,2009;李猛、沈坤荣,2010;贾俊雪等,2012)。另一方面,行政分权使得与企业投融资相关的各项政策都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地方官员的决策行为对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具有巨大的影响(周黎安,2004,2007)。由于“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官员有干预银行信贷的强烈动机,而投资最终也要靠金融资源来支持(巴曙松等,2005),银行信贷无疑是地方官员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张军,2006;李维安、钱先航,2012)。Brandt和Zhu(2000)、Bennett和Dixon(2001)以及Feltenstein和Iwata(2005)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认为受其自我利益驱动和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会更倾向于采用隐性担保、信贷干预等手段来扶持地方企业投资,进而导致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可见,尽管地方政府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并不拥有所有权优势,从而无法对信贷供给构成有影响力的控制,但通过贷款担保、信贷优惠、土地征用、行政审批等信贷干预政策,地方政府却可以极大地影响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将最终的信贷投放规模纳入地方政策调控体系。
本文从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两个角度来衡量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活动的政策影响力,既是从地方层面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大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工具的呼应,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政策不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
(三)从经济增长到政策不稳定性
在众多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持下,Alesina&Perotti(1996)早就总结指出,政策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当某个外部因素(如非经济相关的政治冲突加剧)提高了一国的政策不稳定程度时,投资和经济增长都会随着政治动荡的加深而下滑,并进一步加剧了该国的政策不稳定;反之,当某个外部因素(如非政治相关的贸易条件恶化)削弱了一国的经济增长时,该国国民往往会将经济衰退归咎于政府,进而加剧了该国的政策不稳定,并促使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类似地,周黎安(2007)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官员晋升制度存在明显的锦标赛性质,地方经济的增长速度正是这种锦标赛式晋升制度中最核心的考核指标。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将官员变更事件视为严格外生的解释变量,从而通过将其与经济增长变量进行简单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来研究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不仅忽视了二者之间存在内生性的事实,也有悖于OLS的基本假设条件,从而势必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
因此,结合关于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考虑,本文构建了一个VAR框架下的实证模型,以充分反映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三、理论假设
依据上文思路,本文将从政策不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源、政策传导工具,以及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性3个角度展开理论分析,并据以提出待检验的假设。
(一)政策不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源
正如大量文献所指出的,随着频繁的官员变更缩短了官员的平均任期,在任官员往往更有动力去最大化其可支配的任期资源,而不是着眼于辖区的长远利益(Ali,2001)。这种短视性行为的倾向会驱使在任官员提高对生产性资本的征税,或无节制地扩张支出,或大量举债以增加当期可使用资源,而这些政策举措最终都将导致经济运行效率的下降和经济风险的增大,进而阻滞了经济增长。更为严重的是,新上任官员同样会继承这种短视性行为的倾向。由于短视性经济扩张造成的问题大多只有在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才能得以逐步根治,而受任期较短与政策时滞的约束,为了尽快在任期内实现与前任相比更为突出或不同的政绩,新上任官员往往被迫采用更加短视的政策手段去刺激经济,以更迅猛的经济扩张来化解或掩盖前任遗留下来的各种经济隐患(王贤彬等,2009),可想而知,其后果必然是为后任官员留下了更多隐患。一旦历任官员的经济决策都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整体经济运行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面崩盘的严峻危机。因此,为了保证政策的稳定性,许多发达国家都为其负责主要经济决策制定的官员安排了相当长的任期,如美国联储主席的任期甚至长于其总统任期;而在那些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由政权更迭频繁所导致的政策不稳定性几乎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Gupta,1990;Alesina&Perotti,1996)。
与此同时,官员变更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额外的政策不确定性。首先,官员变更往往会带来政府工作的“断档期”,无论是由于任满干部卸任前故意将当前棘手或敏感的事情拖延至下一任以降低自己承担失误的风险,还是由于人心浮动的基层干部对日常工作关注度的大大降低,政策制订和执行的效率在换届期间都会出现明显下滑,且这种效率损失的发作时点与程度通常都是不可预期的。其次,官员变更还会造成政策的不连续性,这不仅是由于变更官员本身的异质性,更有相当一部分是源自于继任官员希望尽快突破上任官员留下的旧局面进而开辟新政绩的惯性行为,而二者均不同程度地向市场传递出了政策倾向不可预测的信号。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动摇了投资者对未来投资前景的信心,不仅有碍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使得私人投资活动以及资本流入变得更为审慎,并最终使经济增长速度受到了拖累(Benhabib&Spiegel,199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H1)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效应的主要根源为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短视性行为和政策不确定性预期。
(二)政策不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政策传导渠道
在中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体制安排下,地方官员对其辖区的经济增长已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首先,随着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日益提高,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财政干预力度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由于地方官员在决策链中更接近政策目标的最终指向者——企业,财政支出政策的认识、执行与生效时滞都大大缩短,以致财政支出政策得以在地方官员手中发挥出更为灵活有效的影响力。当面临任期短、任务重的晋升压力时,对短期政绩的追求以及对不确定未来的预期必然会促使地方官员采取以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的财政扩张政策,因此,当官员变更引起的财政支出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时,也必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出上述的这种短视性政策特征。从当前研究来看,也确实有很多实证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间的增长锦标赛大多是围绕其财政扩张政策展开的(郭庆旺、贾俊雪,2009)。
其次,由于投资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环节,地方官员的晋升竞争必然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而在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下,投资竞争的成败就在于金融资源(尤其是银行信贷资源)的支持(巴曙松等,2005),因此,地方官员必然有着干预银行信贷的强烈动机。虽然随着国有银行的垂直化管理改革,地方政府已不再拥有国有银行地方分行的实际使用权,而其能够通过股权直接掌控的城商行在整个信贷体系中也仅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从而基本失去了对信贷供给的控制力,然而,不断推进的分权制改革也赋予了地方政府许多隐性的信贷干预功能。利用行政审批、土地征用、贷款担保、信贷优惠等与企业投融资紧密相关的政策手段,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对企业信贷需求的调控来实现其对银行信贷的实际干预,进而逐步推动了其财政功能从“行政化”向“金融化”的转变,而地方财权的加重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运用这些信贷干预政策的能力及影响力(钱先航等,2011)。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H2)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会通过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类似地,政策短视性效应与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在上述两种政策传导渠道中都会有显著体现。
(三)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
本文关注的第三个假设是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也就是说,不仅官员变更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也有显著作用。一般说来,作为考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高速的经济增长与适度的经济风险总是被视为在任官员拥有正确的决策思路和良好的执政能力的标志。由于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避免因政策不连贯而产生的对投资活动的不利影响,也为了最大效率地发挥官员已获得的信息和经验优势,取得良好政绩的官员应当留任,而只有政绩不佳的官员才会被替换。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官员变更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经济风险越大,官员变更的可能性就越高,即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风险之间分别有着负向和正向的相关关系。
然而,也许是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更多地是采用“奖勤”而非“罚懒”的机制。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晋升机会,地方官员必须努力做出比同僚们更突出的政绩,周黎安(2007)所描述的“晋升锦标赛”现象正是这一“奖勤”机制的直接表现。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便未能在任上取得政绩的突破,只要不犯大错误,多数官员大多能平稳地度过其任期,甚至获得连任,诸如“39岁现象”、“59岁现象”等都是对上述“非罚懒机制”的最佳诠释。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对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证实了,1978~2005年,省级地方官员中至少有85%是来自直接或间接的晋升途径(其中,由本省和外省直接晋升而来的省长省委书记达71%);而省级地方官员离任后,至少有33%的省长省委书记会调入中央,且随着官员的年轻化和学历化,上述比例还有着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中国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官员获得晋升的机率越大,官员变更的比率也就越高。类似地,中国官员变更与经济风险之间则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经济风险越大,官员获得晋升的机率越小,官员变更比率也越低。
总结如上观点,本文提出了第三个假设。
(H3)经济增长速度与官员变更比率正相关,而经济增长风险则与官员变更比率负相关。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9~2013年全国近400个地级市(4)为样本,通过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和人民网公布的干部资料等权威媒体资源,手动收集整理了这些地级市每个月份内发生职位变更的市长和/或市委书记的总人数,并以当月全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职位总数为基数,计算得到了地方官员变更比率的月度数据。如图2所示,1999~2013年,地方官员变更的情形相当普遍,平均每年约有近三成的地级市出现了至少一位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变更,有近15%的地级市则面临着同时更换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局面。此外,除个别年份外,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变更频率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至少在地级市的层面上,市长和市委书记在政府决策体系中有着近似等同的重要性,因此,本文通过加总二者的职位变更来整体上考察由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是合适的。最后,我们还发现,地方官员变更比率存在着较大的年度差异,最高时可达到40%,而最低时只有12%,这一时序异质性无疑为本文将对波动率的考察作为分析重点引入实证模型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实际数据支持。
除此之外,本文还从中经网获得了关于GDP(5)、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的月度数据,并以2005年为不变价格将以上名义数据调整为实际数据。另考虑到宏观数据往往会受到季节变动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对这些实际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最后,鉴于这些时序数据中存在的非平稳(non-stationary)问题(6),我们最终依据单位根检验和平稳性检验的结果选取了这3个宏观变量的月度增长率作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
通过表1对月度官员变更率、GDP月度增长率、财政支出月度增长率以及银行信贷月度增长率的基本统计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在1999~2013年间,我国官员变更比率、GDP增长、财政支出增长以及银行信贷增长的波动都极不稳定;更准确地说,所有4个变量均呈现出了显著的非正态特征。因此,传统的OLS估计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为了准确地反映这一时序异质性,我们有必要在实证模型中引入GARCH结构(7)。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为了选择最合适的实证模型来检验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本文在模型设计时着重考察了如下3个问题。第一,考虑到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内生性,本文构建了包含官员变更和经济增长两个变量的VAR模型作为我们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诚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一个完整的VAR系统显然不仅限于两个变量。然而,正如Frankel和Romer(1999)在其关于贸易和收入的经典文献中所建议的,当我们关注的重点为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时,一个双变量的简约模型(reducedform)是最直观的一种稳定结构,更多变量的引入不仅无助于对结构稳定性的改进,反而可能因分化吸收原有变量的解释力而导致对这两个变量相关性的低估,从而违背了我们的研究初衷(8)。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逐一选取了“官员变更——政策工具——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的每个环节上所涉及的一对变量来分别构建双元VAR的简约模型。
第二,如上文所述,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将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官员受职务变更压力而催生的短视性政策行为,二是由官员变更衍生的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前者与官员变更比率直接相关,官员变更的平均比率越高,每个官员的平均任期时间就越短,官员所面临的政绩压力就越大,其政策行为的短视性也就越强。后者虽然也与官员变更比率相关,现有研究大多也不加区分地以“变动”来直接衡量不确定性,但事实上,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波动”而非单纯的变动,因此,以官员变更的波动率(即标准差)来衡量不确定性显然更为准确和直观。有鉴于此,本文将官员变更的比率(均值)和波动率(标准差)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了VAR模型,以有针对性地区别分析由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短视性行为以及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最后,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表1所描述的时序异质性,借鉴Engle等(1987)以及Engle和Kroner(1995)的思想,本文利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9)重构了各变量的方差结构,并以此为基础生成了作为解释变量的波动率序列,从而有了如下的GARCH-in-Mean模型(10):
与传统的VAR模型不同的是GARCH-in-Mean模型不仅充分考虑了被解释变量随时间变化的异方差特征,进而以式(2)所描述的GARCH过程来生成被解释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矩阵Ht: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上述方差—协方差矩阵Ht的对角线元素进行开方后,GARCH-in-Mean模型将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差向量直接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引入了回归方程(1),使得我们能够通过系数矩阵Ψ来直接考察波动率的影响。
在这一基本分析框架下,本文将依照如下步骤逐次选择适当的一对变量作为回归方程(1)中的被解释变量Yt,并运用准最大似然估计方法(QMLE)对上述的GARCH-in-Mean模型进行估计,进而对理论假设H1~H3展开递进式的检验与分析:
步骤1:官员变更经济增长(H1)。
为了检验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根源,本文首先选取了(官员变更比率pt,经济增速yt)这一对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向量Yt。依据上文思路,系数矩阵Γi中的γiyp衡量的就是与官员变更的平均比率直接相关的政策短视性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系数矩阵Ψ中的ψyp衡量的则是由官员变更的波动率所直接描述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由于前者可能涉及多个滞后期,从分析的直观性及其内在经济含义的全局性考虑出发,本文一方面将通过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检验来判断上述影响的显著性,另一方面则参照Grier和Smallwood(2007)的方法,通过构造官员变更比率系数的“长期均衡效应”指标γypLR(11)来考察政策短视行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对应地,本文也构造了官员变更波动率系数的“长期均衡效应”指标ψypLR,以便于我们分析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步骤2:官员变更政策工具经济增长(H2)。
对应上文分析,本文将依次选取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这两个地方官员可实施较大影响力的政策工具之一,与官员变更比率和经济增速分别组合生成了两组共四对新的被解释变量向量。其中,(官员变更比率pt,财政支出增长率et)(财政支出增长率et,经济增速yt)这一组被解释变量向量将用于检验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而(官员变更比率pt,银行信贷增长率lt)(银行信贷增长率lt,经济增速yt)这一组被解释变量向量则用于检验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信贷政策传导机制。
引入政策工具这一环节后,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通过“官员变更政策扩张经济增长”这一作用链来考察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短视性效应。然而,由于在此传导过程中,地方官员的短视性政策扩张冲动不仅会受到与其职务更替频率正相关的晋升压力的影响,其职务更替的波动性同样会对其产生正向冲击,故任一政策工具所传导的政策短视性效应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包含3个变量的复合链式法则。举例来说,官员变更的平均比率和波动率将分别通过γepLR和ψepLR对财政支出增长率产生影响,而这一影响又会进一步通过财政支出增长率的系数γyeLR释放到经济增长中去,因此,地方官员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短视性政策效应最终应体现为(γepLR+ψepLR)γyeLR。
类似地,我们还可以直观地通过“官员变更政策不确定性经济增长”这一作用链来考察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效应。由于政策不确定性直接体现为政策变量的波动率,而官员变更对这一政策变量波动率的影响是在式(2)的GARCH过程中生成的,故政策工具所传导的政策不确定性效应还将取决于GARCH方程的系数。根据Engle和Kroner(1995)对GARCH方程的设定解释,式(2)中的协方差自回归(AR)系数矩阵B和协方差移动平均(MA)系数矩阵A分别衡量了波动率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因此,结合政策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ψykLR(k=e,l,分别代表财政支出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官员变更的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可表示为(│bpk│+│apk│)ψykLR。
步骤3:经济增长官员变更(H3)。
该步骤与步骤1实际上是同一模型的两个对称的考察方向。因而类似地,以(官员变更比率pt,经济增速yt)作为被解释变量向量Yt,本文将通过经济增长率系数的“长期均衡效应”指标γpyLR以及经济增长波动率系数的“长期均衡效应”指标ψpyLR来分别检验经济增速与经济风险在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作用。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归纳如下。
(一)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一般性结论
表2汇总整理了上文步骤1和步骤3的主要估计结果,从中我们得到了关于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两个一般性结论。第一,官员变更的比率和波动率对经济增长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的确会通过刺激官员的短视性政策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这与假设H1是相吻合的。更具体地,我们还发现,官员变更比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将平均下降0.2766个百分点;而官员变更的波动率每增大一个百分点,GDP则会平均下降14.4818个百分点,约为前者的52.36倍。可见,在政策不稳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影响根源中,投资者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我们认为,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历来是最为敏感的,而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正逐渐成为影响投资决策最重要的不确定性之一;另一方面,虽然从长期来看,多数扩张性政策都带有政策短视性特点,但在一定条件下,扩张性政策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扩张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因此,研究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政策不确定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这与当前研究的普遍共识也是一致的。
第二,表2的估计结果也很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H3所提出的关于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比率有正向的刺激作用,经济增速越快,官员变更越频繁;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对官员变更则有着显著的负影响,经济风险越高,官员变更越迟缓。更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速度对官员变更的刺激作用要大大强于经济增长风险对官员变更的约束力,经济增长速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带来1.0902个百分点的官员职位变更,而经济增长风险每增大一个百分点,却只能对官员变更产生0.6359个百分点的约束力,仅为前者的58.33%。这一发现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我国地方官员晋升体系中的确存在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风险的激励机制,这与周黎安(2007)等关于“晋升锦标赛”的研究发现是相吻合的。
(二)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政策传导渠道
由于步骤2的估计结果较多,本文省略了表2的假设检验汇报,集中整理了主要系数“长期均衡效应”的计算结果,并汇报于表3。我们发现,与理论假设H2相一致,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都是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显著政策工具。
从财政支出政策来看,首先,官员变更比率的提高和官员变更波动率的增大都会显著刺激财政支出的扩张,而财政支出扩张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见,H2中关于财政支出政策短视性效应的假设是成立的。我们认为,一方面,随着官员变更比率的提高,官员的平均任期缩短,晋升压力的增大刺激了地方官员短视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另一方面,随着官员变更波动率的增大,对职务更替的不确定预期进一步强化了官员尽快实现政绩目标的短期扩张动机。这种短视性财政扩张带来了税负加重、挤出效应以及竞争效率扭曲等严重打击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负作用,进而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巨大威胁。事实上,已有相当一部分实证工作证实了,财政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刺激作用。如严成和龚六堂(2009)就发现,即便是生产性公共支出也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的实证工作也表明,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存在的竞争行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不利作用;吕冰洋(2011)则进一步指出,财政扩张同样是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从长期来看,旨在消除危机的财政扩张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其次,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力量还来自官员变更的波动率对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催化作用。这一发现与H2中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不确定性效应的假设是基本一致的,它表明,我国微观个体的生产性活动的确存在着显著的财政风险制约机制。作为政府干预程度的直接体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通过税收渠道扭曲微观个体的消费和生产计划,更会引发投资者对整体经济环境稳定性的担忧,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类似地,从银行信贷政策来看,无论是由官员变更比率的水平变化还是由官员变更波动率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银行信贷扩张均有显著的刺激作用,且银行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与假设H2中关于银行信贷政策短视性效应的描述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尽管信贷扩张可能在短期内因“货币幻觉”对总需求产生短暂的刺激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物价水平也会随着信贷扩张而急剧膨胀,而通货膨胀不仅会使得“货币幻觉”完全消失,还会使长期的消费和投资计划因风险的过度积累而受到打击,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事实上,很多现有文献也都对信贷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持负面观点。张军(2006)指出,由于更多的信贷分配给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中国银行部门的总体信贷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金成晓和马丽娟(2010)也发现,信贷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保持正向的,而是会随着时期不同而呈现出非对称的相关关系;王立勇等(2010)同样检验发现,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在不同的增长状态下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李连发和辛晓岱(2012)则指出,由于历次信贷扩张后都存在较持久的通胀压力,信贷总量适度的逆周期变化有助于减少宏观经济的波动和相应的福利损失。此外,由官员变更引发的银行信贷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同样十分显著,这一发现支持了我们在H2中提出的关于银行信贷政策不确定性效应的理论假设。事实上,由于信贷风险与货币风险密切相关,不确定的信贷政策不仅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的加速蕴积,对众多微观投资个体来说,更意味着其资金链的脆弱性提高以及融资成本的上升,这些不利因素都将对生产性经济活动产生抑制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政策工具对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分解后,假设H1中所提出的政策短视性效应和政策不确定性效应有了更为清晰的区别与解释(见图3)。在不考虑政策传导工具的一般性结论中,地方官员的短视性政策扩张仅受官员变更比率影响,而官员变更波动率则是通过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然而,引入政策传导工具后我们发现,地方官员采取扩张性政策的动机实际上要更为复杂。一方面,随着官员变更比率的提高,平均任期的缩短,面临更大晋升压力的地方官员必然有动机采取扩张性政策以尽快取得政绩突破;另一方面,随着官员变更波动率的增大,对未来政途越发不确定的担忧也会加剧地方官员对现有政治资源的争夺,而在当前的考核机制下,通过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在短期内的迅速增长无疑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官员面临不确定性时的这种加速支出的行动规则显然与微观个体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延缓投资的行动规则有明显的不同,我们认为,这种区别源自于二者在决策过程中承担的不同角色和地位。对微观企业来说,它们是其投资项目的所有者,对其投资决策承担长期责任,因此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企业有动力通过等待来实现长期的全局最优化;而地方官员仅是经济政策的执行人,对其政策收益并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故只承担其政策决策的短期责任,因此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为了实现短期的局部最优化,地方官员会更希望通过加速行动而不是等待来规避不确定性。考虑到官员变更波动率中包含的这种政策短视性效应,官员变更的政策不确定性效应显然要比一般性结论中得到的估计系数要小得多,而其政策短视性效应则相应地要比实际估计系数大得多。
进一步比较财政支出政策渠道和银行信贷政策渠道,我们还发现,在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速的抑制机制中,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均强于政策短视性效应,这与我们在前一节中关于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性结论是一致的。此外,表3还显示,财政政策的传导作用整体上要强于信贷政策的传导作用;但相对来看,政策短视性效应在财政政策渠道中比在信贷政策渠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则在信贷政策渠道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财政支出是地方官员直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银行信贷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受地方官员的间接干预,因而,这种“强财政弱信贷”的传导模式显然符合我们的直观事实。与此同时,由于财政支出政策是地方官员执政意志的直接体现,而银行信贷却只能通过一系列作用于投资需求的杠杆式政策间接进行调控,可以预期,当发生官员变更时,财政支出政策将成为受晋升压力刺激的地方官员推动短视性扩张政策的首要工具,而由一系列间接干预手段组合而成的信贷调控政策则会比财政支出政策面临更为不确定的波动状态,且其对投资者的不确定性预期也会有更强烈的影响。
(三)关于风险影响机制的讨论
除前文提出的三大假设外,估计结果还显示,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风险与经济增长风险之间也有着显著的内生影响,其中,政策风险对经济增长风险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增长风险对政策风险的影响(b2py>b2yp,a2py>a2yp)。这一方面表明,政策不稳定性可能已成为目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宏观风险之一,另一方面也再次证实了,我国官员晋升体系中存在着重增长但轻风险的特征。
此外,进一步考察官员变更的波动、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风险之间的影响系数,我们还发现,尽管财政支出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在其将政策风险向经济增长风险传导的过程中都具有逐步衰减的风险缓冲性质(a2ey<1,b2ey<1,a2pl<1,b2pl<1),但却依然都存在着关键的风险节点。具体而言,财政支出政策的风险节点在于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风险对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催化作用(a2pe≫1),而银行信贷政策的风险节点则在于信贷政策不确定性在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后的风险放大机制(a2ly>1,b2ly>1)。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作为能较好实现政策意图但却缺乏经济调控弹性的直接干预型政策工具,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更多地是产生自地方官员的执政阶段;与此相反,作为距政策制订端较远但却对经济活动有乘数效应的间接调控型政策工具,信贷政策不确定性却往往会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张而以倍增的速度膨胀。因此,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来看,我们应通过控制地方政府的高风险政策行为来监控财政风险,而通过调节信贷资金在整体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乘数效应来监控信贷风险。
六、进一步讨论
关于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二者的相关性是否会随着时间而演变呢?下面,本文将以动态溢出效应和换届选举为例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动态溢出效应
之前的检验和估计结果均表明,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那么,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究竟有多大呢?特别地,我们还发现,官员变更是通过刺激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短视性扩张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来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的。那么,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在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的相对作用孰大孰小呢?随着时间变化,上述的这些相互影响及相对作用又是否会保持稳定呢?我们认为,上述问题从新的角度更加审慎地考察了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这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稳健性检验支持,更是理解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参考依据。遗憾的是,GARCH-in-Mean模型本身并无法提供对这一溢出效应的直接衡量。有鉴于此,借用Diebold和Yilmaz(2009)的分析思路,我们通过分解被解释变量的预测误差中分别来自自身和其他变量的影响,进而测算出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溢出指数(SpilloverIndex)(13)。
选用3个月(即1个季度)作为溢出效应的预测窗口,我们测算得到了官员变更比率与经济增长、官员变更比率与政策变动以及政策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溢出路径。从图4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下几点。第一,除2007年底~2008年初因金融危机爆发而出现了一次突增外,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呈现整体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以及官员晋升制度中的经济考核特征正在削弱。第二,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财政支出政策传导渠道在早期(2006年前)表现得较为显著,但随着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地方官员的信贷调控倾向明显增强,虽然在危机后期(2010~2011年),随着两个“4万亿”政策的推出,地方官员通过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增长的倾向有短暂回升,但从整体来看,财政政策的传导作用依然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而信贷政策的传导作用则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到了近期(2012年后),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信贷联系纽带几乎已与其财政联系纽带同等重要了。第三,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信贷政策,官员变更与其政策工具之间的相关性几乎总是强于政策工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表明,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调控政策依然更多地是围绕着官员的执政意图而非最终的经济目标来制订实施的,但这种“以政治为指挥棒”的现象在2011年后有了明显的改善。最后,图4还显示,政策工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远比官员变更与政策工具之间的相关性稳定得多,这表明,相对政策工具自身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确定影响而言,由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风险才是宏观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风险来源,因此,改善官员晋升体系以降低政策风险也许是我们化解与防范经济增长风险的一个有益思路。
(二)换届选举的影响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选举出了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而这次重要的政府换届选举恰好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样本期间内。因此,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以选举换届后的2002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为新的样本区间,对上述的5个GARCH-in-Mean模型再次进行了估计,并将估计结果整理汇报于表4(14)。
我们发现,子样本的估计结果与全样本基本一致:(1)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其中,政策不确定性效应要强于其政策短视性效应。(2)从总体来看,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相对来看,政策短视性效应在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中更为突出,而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则在信贷政策传导渠道中表现得更为显著。(3)经济增长风险依然是官员晋升的负面考核指标,风险越高,职务变更的可能性越低。
与此同时,子样本也呈现出了一些与全样本相异的实证结果:(1)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减弱了,主要表现为由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减弱了;(2)经济增速对官员晋升的正向刺激作用变成了负向抑制作用,而经济风险对官员晋升的约束机制则变得更加强烈了;(3)财政政策工具的传导作用明显下降,而信贷政策工具的传导作用则有了显著提高。这些新发现表明,2002年底换届选举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都在逐步减弱,而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也在逐步弱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计划性”职能特征也在逐步淡化,具有较强“市场性”特征的间接信贷调控职能的重要性正逐渐超越直接财政干预职能,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这与前文的溢出效应动态演变路径的结论十分吻合。
我们认为,上述变化彰显了中国政府执政理念与施政方针的重大改进。以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上任为契机,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诸如淡化GDP指标、强调绿色GDP概念等执政新思路,成为了改革传统晋升考核机制的积极信号。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不再单一地以GDP作为政绩指标,而是将居民生活、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因素(15),这直接导致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不再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而是将发展经济的热情、精力分散到居民保障与民生改善等方面。因此,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短视性效应和政策不确定性效应都得到了有效缓解,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也就减弱了。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地方官员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方面具有法定能力,伴随着官员变更,地方政策通常会因新旧政府政策偏好的不同而发生难以预期的波动,而这种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受长期以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晋升体制影响,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也有显著影响,而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内生性进一步加深了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充分考虑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内生性,进而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政策传导渠道进行深入剖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国的经济增长规律,进而提高宏观调控的效力,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本文基于更加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的地方官员视角,利用月度地级市城市地方官员变更比例作为政策不稳定性的变量,在VAR框架下研究了1999~2013年间我国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及其风险的影响,同时考察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在这一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传导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官员变更会通过刺激地方官员的短视性政策扩张及加剧投资者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政策不确定性效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显著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这两种政策渠道的影响机制却并不相同,财政影响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短视性效应,而信贷影响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再次,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最后,官员变更引起的财政风险主要产生于地方官员的执政阶段,而信贷风险却主要是在经济运行环节中积累催生的,因此,在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应在不同环节对财政风险和信贷风险分别予以监控。
文化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地方保护;产业结构; 趋同;区域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章尺木(197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国改革与发展。李 明(197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国改革与发展。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调整,中央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格局,由此造就了目前特有的以地区行政利益为边界的市场竞争关系和经济增长方式,省级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各地目前的市场竞争便表现为以地区行政利益为边界的竞争,地方政府可采取的地方保护手段有:干预劳动力市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工商质检歧视、干预技术、价格歧视和地方补贴、干预外来企业原材料投入和干预投融资领域等。企业普遍认为省内法制、资金、市场和信用等经营环境好于外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保护的存在。[1](78-84)
来自巴黎国际研究与发展中心Sandra Poncet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2](44-48)当前我国的地方保护已到了相当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持续增高,①各省的国际一体化与国内市场的分割化同步进行。②由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削弱了市场和价格机制优化配置资源能力,不利于实行基于地区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更有甚者,还会造成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企业间 “三角债”纠结不清等严重的信用问题,扰乱市场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3](6-9)因此,地方保护问题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的热点。
一个与地方保护研究相关问题,是当前我国国内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驱动下,重复建设产生的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实。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各省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3.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9%。[4](295)在各地区制定的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将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省市,将机械、化工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6个省市,将冶金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4个省市。[5]③另外,随着各地高新技术产业纷纷上马,会导致新的重复建设和爆发新一轮的地区经济冲突。[6](16-19)
对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与地方保护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认为地方政府盲目发展“短平快”和“利大税高”的竞争性产业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进而引发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从理论上,基于个人利益的分散化决策和基于产品无差异的完全竞争,正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最佳途径和理想状态。实践也证明,在目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投资项目的选择大都是以私人分散决策为特征的,也许这种决策会更具投机性和盲目性,会导致产品雷同,但并没有出现国内地方、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
那么,在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实条件下,能否在省级地方政府追求相对独立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呢?本文拟采用博弈理论分析工具对此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两省之间进行地方保护的博弈模型;第三部分以模型为基础讨论存在地区间竞争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采取地方保护与合作两种不同策略时的模型验证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相应的结论。
二、模型建立
假设有两个省A和B,设每个省只生产一种产品且产量分别为QA和QB,鉴于当前我国各省产业结构相当趋同的事实,设这两种产品相互替代,其逆需求函数D-1(Q)为一阶线性函数:p=a-QA-QB,其中,p为产品价格,a>0为需求函数的参数。设各省最初生产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满足a>c>0,省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本地产业发展,比如完善省内法制、资金、市场和信用等经营环境,采取干预技术、价格歧视和地方补贴、干预外来企业稀缺原材料投入等手段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
令Zi为地方政府通过相应政策投入使本省产品单位成本降低的幅度,即由于地方政策投入,i省产品的单位成本变为:ci=c-Zi,(i=A, B)。随着政府政策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产品的单位成本不断递减,但由于进一步加大政策投入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或者牺牲其他更多的利益,即政策成本具有递增性,进一步,设i省政策成本为二次函数:cZi=λΖ2i/2,其中,λ为正常数。
我们将两个省之间的博弈过程定义为两个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采用逆向归纳法从最后的阶段依次向前求解。第一阶段为政策投入阶段,两省在政策投入上可选择地方保护或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它们能够判断政策投人对第二阶段收益的影响,并同时选择各自的政策投人水平以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第二阶段为产品竞争阶段,两省在各自给定的政策投入前提下,进行产品市场的古诺竞争,选择各自的产量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各省的收益函数为第二阶段的收益减去第一阶段的政策成本。
三、地区竞争与政策选择
(一)产品竞争阶段
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两省独立决定自己的产量。设第一阶段的政策投入使两省产品单位成本降低了ZA和ZB,则A省在第二阶段的净收益为:
RA=(pA-cA)QA-cZA= [a-QA-QB-(c-ZA)]QA-λZ2A/2
最大化其收益函数,求解一阶条件RA/QA=0,得到:
A省的最优产量为:QA=ZA+(a-c)3。
A省最大化收益为:RA=Q2A-λZ2A/2=[ZA+(a-c)3]2-λΖ2A/2。
类似地,B省的最优产量为QB=ZB+(a-c)3,最大化收益为RB=[ZB+(a-c)3]2-λΖ2B/2。
(二)政策投入阶段选择地方保护
在决定政策投入阶段,两个省都面临两种选择:地方保护或合作(经济一体化)。
当选择地方保护时,给定对方的政策投入力度,i省选择自己的政策投人水平cZi,可以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Zi,以使本地的利益最大化。均衡解由maxZiRi决定,求解一阶条件Ri/Zi=0,可得:
Z1=ZA=ZB=4(a-c)9λ-4;Q1=QA=QB=3λ(a-c)9λ-4, (显然应有9λ-4>0)
两省的均衡收益为:R1=RA=RB=[3λ(a-c)9λ-4]2-λ2[4(a-c)9λ-4]2=λ(a-c)2(9λ-8)(9λ-4)2
将社会福利表示为产品用户的消费者剩余和两省收益之和,即F=RA+RB+12(QA+QB)2,则,选择地方保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为:F1=RA+RB+12(QA+QB)2=4λ(a-c)29λ-4
(三)政策投入阶段选择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
选择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两省不仅相互开放本地产品和要素市场,相互协调政策投入力度,而且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会从双方的全局出发,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一个省制定的政策会对另一个省的产业产生“政策溢出”效应。进一步,假设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省的地方产品的单位成本相同,均为c-ZA-ZB,此时,相应第一阶段的均衡产量为:QA=QB=a-c+ZA+ZB3。
此时政策投入阶段的均衡解由maxZAA(RA+RB)和maxZB(RA+RB)决定,求解一阶条件(RA+RB)ZA=0和(RA+RB)ZB=0,可得:当两省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政策对产品单位成本的降低幅度、均衡产出、地区收益分别为:
Z2=ZA=ZB=4(a-c)9λ-8;
Q2=QA=QB=3λ(a-c)9λ-8;
R2=RA=RB=λ(a-c)29λ-8。
均衡解存在的条件是9λ>8。
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福利水平为:F2=4λ(a-c)2(9λ-4)(9λ-8)2
四、选择地方保护与合作两种策略下结果的比较
(一)两种策略下产量水平的比较
不难看出,对每个省而言,选择地方保护时的产出水平Q1=3λ(a-c)9λ-4,小于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的产出水平Q2=3λ(a-c)9λ-8,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更高的均衡产出。
(二)两种策略下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单位成本降低)有效性的比较
不难看出,对每个省而言,选择地方保护时可以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的幅度Z1=4(a-c)9λ-4,小于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的幅度Z2=4(a-c)9λ-8,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
(三)两种策略下各省收益的比较
选择地方保护时各省收益为R1=λ(a-c)2(9λ-8)(9λ-4)2,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各省收益为R2=λ(a-c)29λ-8,R2-R1=λ(a-c)2[(9λ-4)2-(9λ-8)2](9λ-8)(9λ-4)2>0,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增加各省收益。
(四)两种策略下社会福利水平的比较
社会福利水平F=RA+RB+12(QA+QB)2,因为R2>R1,Q2>Q1,所以F2>F1,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水平。
五、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并不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放弃地方保护政策,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仅能提高自身利益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改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本文对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意义在于:以往不顾地方经济利益,过分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地区投资项目选择,以及强行推动地区间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值得讨论。中央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能否成功,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积极响应,地方利益目标与中央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国家经济效益及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利益目标并非不能兼容。关键的问题是要满足本文的前提――完全信息,信息经济学认为,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的条件是完全信息。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实现,同样依赖于各地区之间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7](61-64)这就需要建立各省之间经济政策及其变化的信息交互机制,通过网络、传媒和其他信息渠道定期、规范、详尽地本地区的政策信息,并接受公众监督与查询,以促进各省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实现。
注 释:
①比如在1997年,中国跨省商品流通所遭受的贸易壁垒,相当于被征收了高达46%的“关税”,同欧盟成员国之间,或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不相上下。
②转引自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第44-48页。
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新世纪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善同等. 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 经济研究,2004(11).
[2]转引自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3]徐瑛,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与区域经济冲突[J]. 理论研究,2003(3).
[4]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出版社,1999.
[5]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新世纪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6]张可云. 预防新一轮区域经济冲突[J]. 战略与管理,2002(2).
相关文章
孝慈文化与当代青年孝慈观探讨 2023-05-12 09:01:57
地理标志的文化信息资源分析 2023-05-06 09:32:33
文化卫星账户框架设计 2023-03-30 17:03:00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社团思想教育 2023-03-30 14:45:44
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 2023-03-30 10:39:40
浅析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2023-03-24 17: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