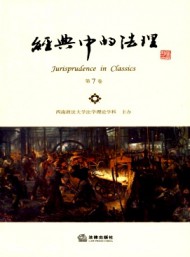经典五言律诗十篇
时间:2023-03-21 05:12:09

经典五言律诗篇1
【关键词】杨亿;七律;诗风转变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088—05
杨亿(974—1020)的诗学传承非常复杂,其祖父杨徽之是典型的晚唐体诗人,他登上诗坛时期正是宋初白体诗风盛行期,因此,他的诗风必然受到这两种诗风的影响,这从其早期的《武夷新集》中可以看出。在《武夷新集》创作期间,他偶然发现李商隐的诗,并沉迷其中,最终促成“西昆酬唱”,催生了宋初诗坛最有名的一本酬唱诗集,也促成了宋代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流派,却也因此被后世频频指责。其实,从杨亿诗风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宋诗风在学唐变唐过程中的艰难探索,杨亿应是促成北宋诗风新变的第一人,其历史地位应重新考量。众诗体中,七律最能代表其诗风,今以其七律创作为例,探讨其诗风转变及诗学意义。
一、杨亿对李商隐的接受
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所载:杨亿对李商隐诗的接受纯属偶然,他学商隐有一个从注重形式到逐渐体认内容的过程。如:
公尝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久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推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斑,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
据生平推算,太宗至道元年(995),杨亿应是21岁,恰是风华正茂的灿烂年华。而义山诗又大多是对“青春激情的表白”,在他的诗中,“大致不出现老年的哀愁”,再加上那幽微迷离的情感表达、曲折绵密的思绪、奇特多彩的意象、丰赡富丽的典故、华美绚烂的辞藻,这样的诗歌对一个同样多情而又年轻的诗人来说,无疑具有非凡的魅力。
如果只是仅有年少的感受,当然难以让人一生追寻,随着时光流逝而能执著如初,应当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他对李商隐诗的喜好,正如自己曾说过的,最初虽“意甚爱之”,但“未得其深趣”,这就说明他一开始对义山诗的喜好是先从形式着眼的。等到“西昆酬唱”时,已经从年少的喜好转向了对李诗底层意蕴的把握。到真宗咸平(998-1003)、景德(1004-1007)年间,他已认识到李诗的丰富内涵,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此,在《西昆酬唱集》中,他首唱的取材李商隐诗题材的次数最多,模拟李诗也最像。
杨亿非常喜好华美的词彩,在《西昆酬唱集·序》中,就曾直接表明“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对别人以文采造就的绚烂也往往称赏有加,或称“文采巨丽,俊发如此”,或言“奇彩彪炳,清词藻缛”,评李诗也认为是“富于才调,兼及雅丽”。但这种对语言美的追求却成为义山诗和昆体诗被后来评论者所批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历览遗编”的基本训练,使他在研读义山诗的过程中,大量运用典故,必然会有一种得于我心的。因此,他曾评价李商隐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久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换骨。”李诗中大量用典的创作技巧也为这位博学多识,才华满腹的诗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学的机会。但是,这种“包蕴密致”,于诗中见学问的作法却与对语言美的追求一样,都成为后人对西昆体喋喋不休加以指责的口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受到怎样的指责,他开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先河,这一特色,使得宋诗在学唐变唐的过程中,最终成为一个最鲜明的标志。
作为政坛人物,杨亿尽管少年得志,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作为颇受皇帝赏识的臣子,他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权,但也很可能招致非议。秉性耿直,不附权贵,使其政界生涯充满坎坷。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真宗委婉地表示对杨亿的不满,以致杨亿仓皇出走,不敢还朝。由此也可看出诗人心中怀着怎样的恐惧。但作为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和诗人,他对自己看到的不良现象又难以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因此,在诗作中其表达情绪就不得不采取一种婉而多讽,沉潜而幽微的手法。
“西昆酬唱”始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此年,杨亿入馆阁参编《册府元龟》。这时,他已过而立之年。从太宗至道年问最初接触义山诗到入馆开始“西昆酬唱”,他观摩学商隐诗已有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博闻强记的天才诗人而言,熟练掌握一种特色鲜明的诗风,并进行模仿学习,应是得心应手。因此可以说,人馆阁编书为杨亿推广一种富丽典赡的诗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再加上钱惟演、刘筠等人的推波助澜,北宋诗坛上,一位艳妆佳人姗姗出场。四库馆臣评论杨亿文集,有一个很精到的表述:“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舂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肯定其诗文“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实际上也就承认了他已逐渐走出唐风,而倔强地树立着宋调。
《武夷新集》所收为杨亿真宗咸平元年到真宗景德四年(1007)近十年问的诗文。也就是说,在《武夷新集》创作三年后,杨亿开始接触李商隐的诗,因此,这段时间可以看做是杨亿对李商隐的初步观摩学习期,也是《西昆酬唱集》的准备期。《武夷新集》也的确体现出明显的过渡痕迹。
二、《武夷新集》的七律诗风
《武夷新集》中,七律203篇,就数量而言,应当是杨亿七律创作的主体部分。
全祖望《西昆酬唱集·跋》引梁章钜语云:“昆体特文公之一格,《武夷新集》具在,未尝尽如西昆。”此段话说明杨亿诗风是多方面的,而典赡藻丽的昆体只是其中一种,至于还有什么样的风格,并未说清楚。
清代彭氏知圣道斋抄本《武夷新集》校后记言:“诗家多言西昆体,读集中诗与《小畜集》为近,决不类玉溪生,乃一时体格,好事者故作指目耳。”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祖望《西昆酬唱集·跋》的补充。他认为《武夷新集》的风格与《小畜集》为近,《小畜集》是白体代表诗人王禹偁的诗文集,也就是说《武夷新集》的风格基本为白体风格。从他将“西昆体”认为是“一时体格”,又说是“好事者故为指目”来看,似乎是贬西昆而褒杨亿,将《西昆酬唱集》仿效李商隐的作品称为一时之作。这种辩解无疑违背了杨亿本人的创作思想,也不符合杨亿创作的实际状况。因为在杨亿文集中,我们没有看到丝毫学李商隐的悔意,反而对其褒扬有加。从七律角度来看,《武夷新集》与《小畜集》风格也并不相同。但这段话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杨亿诗受白体影响的一面。也就是说,杨亿早期诗作受当时诗坛风气的影响,而当时的风气则是白体占主流,所以,在杨亿的创作上,正好体现了一个学白变白的过程。
从其203首七律的题材分布来看,奉和应制诗有10首,题咏之作有7首,咏物诗仅1首,咏怀等其他作品加起来也只有14首,其余皆为寄赠交游之作。《西昆酬唱集》中的唱和诗极少次韵,而《武夷新集》中的作品大多数是次韵诗。以次韵的寄赠交游之作为主,正是白体七律的主要特征。题材的类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创作方法及诗歌内容的类似。《武夷新集》校后记言其“与《小畜集》为近”,就题材选择而言大致不错。
《武夷新集》中有10首奉和应制七律,其中,有4首赏花钓鱼诗,有3首分别作于真宗咸平四年(1002)、咸平五年(1002)、咸平六年(1003),另一首未系年。可见,太宗朝形成的这一风气成为奉和应制诗的主要题材,用以反映君臣同乐的承平气象。这些奉和应制诗体现了杨亿“宣布王泽,激扬颂声”的主张。
《武夷新集》收诗自咸平(998)元年起。此年十月,杨亿参修《太宗实录》成,乞外任,知处州,咸平三年(1000)秋被召回。其诗集中从《初至郡斋书事》到《留别桐城主簿》为在处州任上所作,其中七律22首。他的7首题咏之作,有6首都作于此时。这一时期的七律,浅切流畅,用典不多,体现出一定的白体特征;但从其风格的“清峭感怆”,对仗的工整讲究而言,又融合了晚唐体七律的特征。他对晚唐风格的体认与学习,当是受其从祖杨徽之的影响。杨徽之是宋初著名的晚唐体诗人,喜好郑谷诗。对晚唐诗风的学习,应是杨亿的家学。此期七律与《西昆酬唱集》中典赡藻丽的七律判若两人之作。
杨亿不喜欢杜甫的诗,但他此期的部分七律,却有杜诗苍凉老成之感,如《次韵和衢州席刑部》、《早秋送张彝宪归乡》,这两首诗的风格用语,既不似白体王禹偁七律那样平易闲适,也不似晚唐体寇准那样清丽凄婉,反而体现出一种苍凉老成之态。这种诗风在北宋初七律中较为少见。较之王禹偁不意之间所作的类杜甫之诗,杨亿诗在用语及情调上都更像杜诗,只是笔力尚弱,缺乏杜诗的沉郁感。在抒情与写意方面,以上二诗虽然都有抒情成分,但其结句基本以写意收尾,这与杜诗以情为主也有差异,而写意正是宋诗的主要特征之一。可见,在杨亿早期七律诗作中,他受白体写意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也即是说他的七律是以晚唐工笔之法写意。
杨亿出任处州时期,正是他逐步接触到李商隐的诗,并开始观摩研练期,他的诗中很快就体现出李商隐诗歌的外部特征,即诗中用典逐步增多,方法也不像以前那样,在一首诗中起点缀作用,而开始整首诗密密地借用典故来表述意思,如《书怀寄刘五二首》之一的“病起东阳衣带缓,愁多骑省髯毛斑。五年书命尘西阁,千古移文愧北山”,一句一典,充满了浓浓的书卷气,已经与早期的白描抒情手法,意趣迥别。尤其是在第二首“四客高风惊楚汉,五君新咏弃山王”中,首句用商山四皓典言隐居的高峰亮节;次句用颜延之《五君咏》典。颜延之取竹林七贤作《五君咏》,以山涛、王戎贵显而将二人排斥出外。杨亿言自己宁愿作“五君”,不愿意因为贵显而被排除在外。这样的诗句已经完全没有唐诗一唱三叹的抒情意味,但作者巧妙地利用“惊”、“弃”二字,将典故的意蕴与自身的情感结合得浑融圆整。方回认为此句甚佳,并言“昆体未尝不美”,可见,这样的诗句已经逐渐显示出昆体的意味,只是“昆体”中的“平淡”者。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已能看出杨亿诗风的变化。他没有沿早期白描以写意的方向发展,更没有向杜诗写景以抒情的方向发展,而逐渐转向借用典故来抒情写意。这种创作手法为后来的江西诗派所继承,在某种程度上讲,江西诗派正是“昆体”之“平淡”者。
借用典故抒情写意,符合时代特色及杨亿本人的创作思想。首先,白体新一代诗人及晚唐体处士诗人的七律都以写意为主,抒情七律正逐渐退出北宋诗坛。其次,北宋右文政策的实施,在太宗朝后期已见成效。白体、晚唐体的浅切庸弱逐渐受到排斥,张咏就曾批评晚唐体诗人寇准不读书。重视读书风气在诗文中的体现就是大量使用典故。诗文在使用大量典故后,往往会有一种厚重老成之感。太宗本人后期的审美观念也由欣赏前期杨徽之的晚唐风格,变为欣赏有“老成之风”的作品,杨亿就被其认为诗有“老成之风”。第三,这种创作手法符合杨亿的创作思想。
《南史·柳恽传》载:“恽少工篇什,有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可见,杨亿不赞成“留连景物”之作。这是其后期七律“资书以为诗”,多用典故及人文意象而少用自然景物的原因之一。
从处州回京后,杨亿七律主要以次韵寄赠送行之作为主。这些次韵寄赠之作大部分是迎来送往的应酬诗,如《次韵贺阁长李舍人喜薛梁二舍人同时拜命之作》、《酬谢光丞四丈见庆命之什》,《次韵和盛博士喜梅大丞授户部郎中》等,从诗题上已可知道诗的内容。七律从唐代的抒情渐渐转向写意,与题材的演变有很大关系。在应酬性诗作中,使用典故恭维一下对方,即得体,又可显示自己的博学,关键是还容易成诗,这就是为什么北宋后期七律数量激增,常常一人有三四百篇,在创作数量上远远超过唐人的原因之一。
杨亿有大量送行之作,被送之人多为朝廷中出外任的官员。北宋官员多科举出身,本身就擅长诗赋,在出外任之时,常有同僚作诗送行。送行之作与酬谢之作相同,也大多采用七律的形式。这两大题材是杨亿此期七律创作的主要题材,也是整个北宋七律的两个主要题材。这类七律一般都是典型的叙述型七律。杨亿的寄赠送行之作中,还有不少是写给应举或下第的举子,这些诗唐代也有,但远没有北宋普遍,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北宋科举制度对文士生活的影响。
杨亿诗学李商隐的同时,兼学唐彦谦,唐彦谦七律本学李商隐,两者有相通之处。杨亿认为唐彦谦诗“清峭感怆”,他此期的七律颇有此特征。
《武夷新集》与《西昆酬唱集》中的诗还有同题之作。杨亿偏爱《七夕》,共作4首,其中,《武夷新集》中有2首,《全宋诗》从吕祖谦《宋文鉴》中辑出1首,《西昆酬唱集》中有1首。从诗的风格来看,四诗都典丽清华,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就内容而言,四首诗都紧扣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事进行生发,或写对人间能白首偕老的期望,或感叹孤枕难免的寂寥,或言天上乌鹊填桥之苦,从而发出不如人间的感叹。从立意上讲,最后一首出自《西昆酬唱集》的《七夕》诗最好。
从上述分析可见,《武夷新集》中的七律题材比较集中,基本以寄赠交游为主,是当时白体七律的主要题材,因此,有学者认为类《小畜集》。就风格而言,早期出知处州的作品,以浅切清新见长,体现出白体与晚唐体相结合的面貌。回京师后的部分诗作,开始大量用典,但语言仍然平淡质朴,因而被认为是“昆体之平淡者”。有些诗风格“清峭感怆”,对仗精工,颇类唐彦谦七律,也有一些诗风格典赡藻丽,已有“西昆体”的特征。纵观《武夷新集》,似乎是步步为《西昆酬唱集》作准备。在经过近十年对李商隐诗的观摩研练后,《册府元龟》的编撰给杨亿提供了一个演习的机会。在《西昆酬唱集》中,杨亿对早期的七律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从次韵变为和意不和韵,从寄赠交游为主,变为以咏史、咏物、爱情之作为主。风格上更倾向于典赡华美,连“昆体之平淡者”都很少见。
三、《西昆酬唱集》中杨亿的七律诗风
《西昆酬唱集》中的七律就题材而言,大致可分为五类:咏史七律有8次唱和共30首诗,咏物七律有7次唱和亦为30首,爱情诗有6次共28首,寄赠交游之作有8次27首,咏怀之作有13次共30首。其中,成就最高,特征最鲜明的是咏史、咏物、爱情三大类,这三类正是李商隐七律最擅长的题材,显示出杨亿在酬唱题材上对李商隐的取范。
咏史七律是《西昆酬唱集》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围绕咏史题材进行的8次唱和,全由杨亿首唱,体现出杨亿学商隐诗的用力之处。刘学锴称杨亿是“宋代最早提到李商隐的咏史诗并对它作出评论”的诗人。可见,馆阁唱和为杨亿进一步涵咏并模仿李商隐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西昆酬唱集》中咏史七律分别为《南朝》、《汉武》、《公子》、《旧将》、《明皇》、《成都》《始皇》、《宋玉》。从诗题上看,时间跨度很大,几乎涉及从秦、汉到唐的各个朝代。在取材上也很具有典型性,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以帝王为主、以典型历史人物为主、以典型的历史时段或地点为主,这三类诗的最终指向都与现实相联系,这与李商隐咏史诗一脉相承。西昆体咏史诗的取材受李商隐的影响十分明显,有许多诗题直接源于李商隐诗,如《南朝》、《宋玉》、《公子》、《旧将》。由此可见,杨亿在咏史诗的选材上结合了自己的现实政治需要与李商隐咏史诗的内容。
《西昆酬唱集》咏物七律有《馆中新蝉》、《鹤》、《赤日》、《再赋七言》(荷花)、《梨》、《泪二首》、《柳絮》,其中《赤日》、《泪二首》、《柳絮》为杨亿首唱。在杨亿首唱的三首中,有两首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李商隐诗,如《泪》与《柳絮》。以《泪》为题是昆体咏物七律中最特殊的一组唱和诗。它的首唱者为杨亿,且连作两首,和者也只有刘筠、钱惟演二人,亦每人两首。《泪》是李商隐咏物七律中比较独特的一首诗,其创作手法极具个性,杨亿以此为题,并连作两首,应当是看出此诗与一般咏物之作的不同之处。但义山《泪》诗因奇而好,以新奇取胜,当具有不可模仿性。模仿之作往往下笔便落俗套,招致效颦之讥。后世批评昆体诸公诗之堆垛故实,其《泪》诗常成为众矢之的。
《西昆酬唱集》中的爱情七律共28首,为六次唱和之作,首唱者皆为杨亿,这一点与咏史七律相同。这六次唱和中,有三次以《无题》为题,共14篇。《无题》诗是李商隐首创,其6首《无题》七律在其《无题》诗中成就最高。杨亿对其的选择及摹写,体现出他对义山诗的准确把握。
从艺术手法及创作技巧而言,在昆体诸公中,杨亿最得义山真传。纪昀曾言其《武帝》诗“此便欲真逼义山”。杨亿咏史七律从起句立意、用典内容到艳语人诗,都有明显拟作的痕迹。其用典多而善组织,对仗也更精工,昆体七律讲究用事及属对功夫的两大特征已表露无疑。
其《南朝》前六句都在堆垛史实,只是用不同的事例反复证明南朝君主的昏聩,只有尾联略能放开,言南朝人事已终结,而见证南朝事迹的长江却依然如故,颇有岁月无穷,人事易尽的感叹。这在立意上与李诗回收到自身遭遇以结束全篇不同。李商隐诗多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借历史以抒情,而杨亿诗则从史实本身出发,借历史以言意。这就是西昆体诗与李商隐诗的最大区别,也是唐风与宋调的分野。
就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李商隐的叙述性手法,多用于单句,以一句言一事,而整首诗的结构却用比兴手法,如《泪》、《牡丹》皆如是,因此,虽是铺排,却不堆积,巧妙地利用了七律的对仗,使全诗显得灵动多变。杨亿诗常常两句只言一个意思,只是搜罗典故,排比叠加,为对仗而对仗,极少变化,如《泪》诗,即使有比兴,也是简单的比附铺叙,显得呆板笨重。七律用赋笔铺排,除受李商隐影响外,更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西昆体崛起之前,白体占据诗坛主流,重铺排是白体七律的一大特征。但白体七律的铺排以简单的叙事为主,多用散文句式及流水对,呈现出“以文为诗”的倾向,而杨亿七律的铺排却以历史典故为主,多锻炼成精美的对仗,呈现出“以赋为律”的面貌。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杨亿的七律诗风从《武夷新集》到《西昆酬唱集》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他的《武夷新集》中七律早期多以白体的写实叙述手法为主,语言上融合了晚唐体的精心雕琢,后期开始使用典故,逐渐出现西昆体迹象。《西昆酬唱集》中杨亿七律较之《武夷新集》的变化体现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等各个方面。这些变化全都与杨亿对李商隐的体认与模仿分不开,其对宋诗学的影响亦不可估量,从很多方面兆示了宋诗的特征。
就题材而言,除咏物外,咏史与爱情题材始终未能成为北宋七律的主要选材来源,佳作也不多。尤其是爱情题材,在北宋七律中寥寥无几,显示出尚意的宋人对这一纯抒情题材的疏远,当然还有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爱情题材向词中的转移。这一选材倾向从反面显示出宋诗对唐诗题材因创作手法不同而不得不有所扬弃。
就风格而言,“富赡典丽”成为后世指责西昆体的口实。后昆体及诗新诗人正是在对这个风格的不断修正中确立宋诗的审美风向,直到江西诗派黄庭坚明确提出“平淡而山高水深”。
经典五言律诗篇2
一、要引导学生了解诗词的基本类别并将之归类
中国古典诗词与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流派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由诗到词,再由词到曲。
(一)以体裁而论,古典诗歌可以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前者如《诗经·关雎》等,后者如王湾的《次北固山下》等。近体诗又分为律诗和绝句等,前者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等,后者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等。律诗可分为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前者如杜甫的《望岳》等,后者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等。绝句可以分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前者如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等,后者如朱熹的《观书有感》等。在古典诗词中,词又称“诗余”、“长短句”、“曲子词”等,如李清照的《如梦令》等即是。曲是元杂剧和散曲的合称,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即为散曲。
(二)以题材而论,古典诗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田园山水诗,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等;边塞军旅诗,比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等;怀古咏史诗,如杜牧的《赤壁》等;咏物抒怀诗,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等;惜别送别诗,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闺怨诗,如李清照的《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等;讽喻诗,如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等;哲理诗,如朱熹的《观书有感》等。
二、要引导学生了解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并将之归类
复习古典诗词,还要引导学生了解教材中出现的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并将之归类。
(一)西周至春秋时期《诗经》之《关雎》和《蒹葭》等。
(二)东汉末年曹操及其《观沧海》等。
(三)东晋陶渊明及其《饮酒》(其五)、《归园田居》等。
(四)唐代古典诗词重要作家很多,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王湾、温庭筠、刘禹锡、杜牧、岑参、李商隐等,其重要作品分别有《行路难》(其一)、《春望》、《钱塘湖春行》、《使至塞上》、《次北固山下》、《望江南》(梳洗罢)、《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赤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夜雨寄北》等。
(五)宋代古典诗词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分别是:文天祥及其《过零丁洋》、苏轼及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及其《渔家傲·秋思》、李清照及其《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辛弃疾及其《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王安石及其《登飞来峰》等。
(六)元代古典诗词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分别是: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等。
(七)明清时期古典诗词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分别为:王磐及其《朝天子·咏喇叭》与龚自珍及其《己亥杂诗》等。
三、要理解古典诗词的内容并背诵、默写古典诗词
(一)复习古典诗词,必须弄清其字面意义。要弄清其字面意思,就必须积累古汉语常见词语的意思。因古典诗词是古代先人运用古汉语写成的,其中很多字词的意义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还要学会根据语境猜测、判断其意义。比如王湾《次北固山下》中的“次”,在此应该是“停泊”之意。还要熟记古典诗词中的典故。很多作者在古典诗词创作中往往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典明志。比如白居易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在颔联“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中连续运用了晋人向秀的《思旧赋》和晋人《述异记》中的典故抒情,表达自己对旧友遭受迫害的不满,暗示自己被“弃”时间之久和因人事全非而生的惆怅之情。
(二)熟读、背诵、默写古典诗词。鉴于历年来中考时古典诗词的默写分值均为5—8分的缘故,复习古典诗词还需要引导学生重视对其名言名句的默写,对于容易混淆或者写错的字、句等必须重点排查、逐一过关。比如,李清照的《如梦令》中“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中的“争”字和“鸥”字等,学生在默写时往往写成“怎”和“欧”等错别字;再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起舞弄清影”中的“清”,学生在默写时往往误写成“青”字。复习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此特别加以注意。
四、要掌握基本的鉴赏方法
复习古典诗词时需要引导学生掌握的鉴赏方法很多,但限于篇幅,我们只谈谈局部鉴赏与整体鉴赏相结合的品鉴式复习方法。
(一)品鉴动词。引导学生善于抓住能够为文本增添生动、鲜活、形象等美学意蕴的动词。比如,复习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应该引导学生紧紧抓住诗歌中运用最准确、最具张力的动词“争”、“啄”、“迷”、“没”、“爱”、“行”等动词进行赏析。因为这些动词既精妙独到地描绘了早春来临时的莺歌燕舞氛围,又描绘出了初春西湖的美丽景色,还抒发了作者对早春西湖的无比热爱之情。
(二)品鉴副词。引导学生深度品析诗歌中某些起修饰作用的副词。比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中的“渐欲”与“才能”两个副词,既富于动态又富于情态,生动鲜活地表现了初春时节乱花和浅草的勃勃生机,故此,“渐欲”与“才能”堪称这首诗的“诗眼”。所以,要引导学生对此细读深品,并牢记在心。
(三)品鉴叠词。叠词在古典诗词中可以增强语言的韵律感又可以起到反复和强调等作用。比如《诗经·蒹葭》中就使用了大量的叠词,其中“苍苍”、“ 萋萋”、“ 采采”三个形容词叠词既反复渲染了凄美的深秋意境,又暗含了时间的推移,从而含蓄地表现了诗歌主人公对心仪的“伊人”苦苦追慕却又求之不得的惆怅之情,当然更为这首古老的爱情诗歌奠定了朦胧的美学意蕴和具有悲剧色彩的情感基调。
采用局部鉴赏与整体鉴赏相结合品鉴式复习古典诗词时,应引导学生抓住诗歌中最能凸显景物特征、最能表现情感色彩、最能体现文本情感基调等的诗眼细读深品。
经典五言律诗篇3
【关键词】尚唐;唐诗诗体;李杜优劣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体裁、题材、风格多样,盛况空前,仅目前留存的唐人诗作有五万余首,有姓名可考者两千多人,散佚、失传的可能会更多。唐诗作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唐诗的巨大成就,迷人的艺术魅力,具体可感的艺术情境,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趣味,引起古今中外诗评家的广泛关注,刻苦钻研。“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1]不同情趣的读者可以从唐诗中各得所爱。朝鲜诗家南龙翼(1628―1692)就对唐诗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在其理论批评体系中形成了独具韵味的“唐诗学”。
1 学诗之法,一生攻唐
历代诗家对于怎样学诗、作诗,有自己的一番认识。杜甫认为应“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宋代吴可《藏海诗话》曰:“看诗且以数家为率……如贯穿出入诸家之诗,与诸体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诸体俱备。”清代王渔洋说:“为诗须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识见。”[2]对于怎样学诗、作诗,朝鲜南龙翼则有如下论述。“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咏,慕其格调,思其气力。五律则学王摩诘,七律则学刘长卿;五绝则学崔国辅,七绝则学李商隐;五言则学韦苏州,七言则学岑嘉州。”南龙翼在这里详尽地阐释了他的“学诗之法”,五律应该学习王维、七律学习刘长卿、五绝学习崔国辅、七绝学商隐、五言学习韦应物、七言学习岑参,这是就诗歌体裁方面而言的;而对于诗歌的本质内涵,南龙翼则主张学白、杜甫,“慕其格调,思其气力”。[3]
南龙翼崇尚唐诗,以唐诗作为学诗之标的,是与朝鲜李朝时期的大文人李B光、许筠崇尚唐诗一脉相承的,但在李、许二人的基础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南龙翼把唐(下转第103页)诗作为自己的学诗标准,更加看到“我朝诗名家,各有所尚”,指出朝鲜诗人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之法”。具体来说,孤竹(崔庆昌)、荪谷(李达)、芝峰(李B光)等12人是崇尚唐诗的,他说:“李芝峰一生攻唐,闲淡温雅,多有警句。”“郑东溟……至若七言歌行,则仿佛李杜,我国前古所未有也。”[3]
2 诗家各体,至唐大备
诗至唐代,古今体制尽备,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如果把古典诗歌比作一座宫殿,那么,体制宏伟、风格缤纷的唐诗就犹如重梁迭栋的大殿。南龙翼对唐诗体制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值得深入研究。“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古人各有所主。而以余之妄见论之,五言绝则王右丞‘人闻桂花落’、七言绝则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五言律则杜隰城‘独有宦游人’、七言律则刘随州‘建牙吹角不闻喧’等作,似当全篇之完备警绝者。若求于李、杜,则五七绝当尽在李,五七律当尽在杜,此则不敢论。”[3]“人闲桂花落”,语出王维《鸟鸣涧》;“黄河远上白云间”,诗出王之涣《凉州词》;“独有宦游人”,诗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建牙吹角不闻喧”,语出刘长卿《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在这里,南龙翼对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分析后认为它们是“完备警绝”之诗,而李白的五、七言绝句和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则是同类诗体中的佼佼者。
朝鲜李朝的李B光在《芝峰类说》中说诗人很难众体兼备,五律、五绝应推举孟浩然,七绝应推举王昌龄。他说:“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角,长篇则绝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3]
清代王士祯在其著作《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中说:“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云:“七言绝句少伯(王昌龄)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叶燮《原诗》云:“七言绝句推李白王昌龄。”严羽《沧浪诗话》推举崔颢的《黄鹤楼》为七律的代表作,胡应麟《诗薮》推举杜甫的《登高》为七律的代表作、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4]
从中可以看出,南龙翼和历代诗家在论述诗歌各体代表诗人诗作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都推举杜审言的“独有远游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五律的代表作;不同点:南龙翼推举刘长卿的“建牙吹角不闻喧”(《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为七律的代表作,历代诗家推举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为七律的代表作。
3 李杜优劣,自古未定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位星悬日月、高山仰止的伟大诗人,古今论诗者必称李杜,称李杜者则又不免要论及两人的优劣,这便是所谓的“李杜学”。李阳冰《草堂集序》称李白为“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杜甫自然排在李白之后。殷[《河岳英灵集》没有收录一首杜诗,此时杜甫已有《饮中八仙歌》《兵车行》等作品问世,可见其抑杜的程度之深。第一个标举杜甫超过李白的,是元稹,开了尊杜抑李的先河。他的《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李、杜的诗歌进行比较后认为“(李白)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到了宋代,“扬杜抑李”者就更多了。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李杜并重者也不乏其人。唐代韩愈、宋代严羽是其中的代表。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沧浪诗话》说:“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4]
南龙翼《壶谷诗评》认为李杜优劣,从古到今,并没有定论。他说:“李杜优劣,自古未定……m州评李、杜曰:‘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逸沈雄为贵。味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嘘唏欲绝者,子美也。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不足法也。’此诚不易之定论,而余犹有释然者,李、杜之五言古,如古风纪行可以相埒。而如杜之,李固不可敌;《北征》、《赴奉先》二长篇,又胜于《忆旧游》、《五屋山人》;则五言杜实优矣,而不论于神圣之中,至若七言歌行,李之《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忆秦娥》诸篇,杜亦无可敌,岂有神圣之别欤?”[3]
南龙翼先论述了一则关于李、杜优劣的论争之事,最后通过m州评李、杜的一段话,得出他对李杜优劣的看法,他认为李杜无优劣之分乃“不易之定论”,并且从自身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举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无家别》、《新婚别》、《遣怀》等篇,认为“李固不可敌”,五言诗杜甫要比李白优秀一些,“《北征》、《赴奉先》二长篇,又胜于《忆旧游》、《五屋山人》”;但是李白的七言歌行《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忆秦娥》等篇,杜甫也不可比拟,所以得出结论:没有神圣之别。
4 结语
南龙翼对唐代诗歌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唐诗的高度重视。他结合自己的诗评活动,对历代诗篇进行取舍、筛选,编选了诗集《箕雅》,反映了朝鲜历代汉文诗作的精华,为后代的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箕雅序》中他道出了选诗的标准,可以和他的唐诗论相得益彰,他说:“东文选,博而不精,续则所载无多,青丘风雅,精而不博,续则所取不明,近代国朝诗删,颇似详核,而起自国初,迄于宣庙朝,首尾亦欠完备,余皆病之。”作为当时主管文坛的重臣,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必然对当时及后世文坛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2]里克.历代诗论选释.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3]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
[4]陈良云.中国诗学论著选.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经典五言律诗篇4
中国青年社约我和另外几位同志写一些介绍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计划是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必要的简明的注释,详加分析,把好处指点出来,帮助青年朋友们培养阅读古典诗词的兴趣和能力。我欣然接受下了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一种有益的而且我也爱做的工作。青年朋友们现在都渴望把生活弄得丰富些,并且从祖国文艺传统里吸收些经验教训,来丰富自己的创作。青年朋友们要欣赏古典诗歌的希望是很深切而普遍的,只是古典诗歌对于他们多少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他们还没有摸到门径,不知道从何下手,或是怎样下手。因此,在介绍作品之前,对怎样学习古典诗词作一点一般性的入门的介绍,是必要的。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诗歌,从“诗经”起,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两千多年的传统是不断发展的,一线相承而又随着时代变化的。它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大阶段:一,周秦时代,即“诗经”“楚词”时代,这时代的诗歌大半来自民间,原来是与音乐舞蹈合在一起的。因为来自民间,所以它在创作和流传上都具有很大的集体性;因为与乐舞相伴,所以它大半可歌,有一定的音律。在这时期,四言体(即四字一句)占主导的地位,但变化比较多,到了楚词,句子就比较长些了。二,汉魏六朝时代,这时代诗歌经过了一个大转变,一方面乐府民歌仍然保持原始诗歌的集体性与可歌性,另一方面诗成为文人的一种专业,文人也吸收了民歌的影响,但不免渐向雕琢方面走,技巧上逐渐成熟,民歌质补的风味便渐渐减少,诗与乐舞也就渐渐分离了。在这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音律是五言体,但是七言也渐渐起来了。三,唐宋时代,这时期是文人诗的鼎盛时代,除了五古七古(即五言和七言不讲音义对偶的像汉魏时代那样的诗)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之外;承继六朝的影响,五律七律(即在声音和意义上要求成一联的两句互相对仗)两种体裁也由兴起而渐趋成熟了。原来汉魏以前,诗大半伴乐,诗的音乐主要地要从乐调上见出;魏晋以后,诗既渐与乐分开,诗的音乐就要从诗的文字本身上见出了。这是六朝以后诗讲四声(即平上去人;上去人合为仄声)的主要原因。词也在这个时期由兴起到鼎盛。词本出于教坊(职业歌唱者训练的地方),原来都有一定的乐谱,可以歌唱,后来落到文人手里,也就只是依谱填词,不一定能歌唱了。从诗的发展看,词可以说是从律诗变化来的。后来的曲子又是词的变化。唐宋以后的诗词只能算是唐宋的余波,新的发展很少。
这三大阶段中的作品是浩如烟海的。初学者最好先从选本入手。过去的选本也很多,但是选的人观点不同,大半不很适合现时代的需要。我们希望不久有较好的新的选本陆续出来(例如余冠英的“乐府诗选”)。在适合需要的选本出齐以前,读者不妨暂用过去几种流行较广的选本。我想到有三种卷帙不多的选本可以介绍给续者。第一种是沈德潜选的“古诗源”,选的尽是唐以前的诗;第二种是蘅塘退士选的“唐诗三百首”,选的尽是唐代各休诗;第三种是张惠言的“词选”,是唐五代宋词的最严格的一个选本(或用唐圭璋的“唐宋词选”亦可)。这几种选本选的都相当精,分量很少。我自己去看,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全看完。初学者看,时间当然要多费些。不必嫌它太少。学习一门东西有如绘画,先须打一个大轮廓,对全局发展变化有一个总的概略的认议,然后逐渐画细节,施彩色,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人物来。读了这几本选本以后,读者就可以看出哪些诗人是自己特别喜爱的,再找他们的专集去读。
古典诗词大半是用文言选的。读者初来难免 遇到一些语言的障碍。这种障碍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大,因为第一流的诗词作者所用的语言尽管精妙,总是很简洁的。有许多名著在过去都有些注本,读者遇到困难时不妨查注本,翻字典,或是请教师友。万一没有这种方便,也不要畏难而退。先找自己基本上能懂得的诗(这是很多的)去读,读多了,自然会找出一些文言的诀窍,了解的能力就会逐渐增加。凡是好的诗词都不是一下于就通俗懂透的。我从小就背诵过许多诗词,这些诗词我这几十年来往往读而又读,可是是否我个个字都懂了呢?绝对不是这样,有许多字义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有许多诗的背景我至今还是茫然。但是这个缺陷并不妨碍我对于那些诗词在基本上能了解:能欣赏,而且能得到教益。学习的过程就是变不懂为懂,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和努力。
我们对于古典诗词不可能马上就都彻底了解,但是必须要求彻底了解。凡是诗词‘都是用有音乐性的语言,刻划出一个完整的具体的形象或境界(可能是景,可能是事,也可能是景与事融合在一起),傅达出一种情致。读一首诗词就要抓住它的具体形象和情致。要做到这一点,单像读散文故事那样一眼看过去,还不济事。诗词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须加以反复回味,设身处境地体验,才可以逐渐浸润到它的深微地方,领略到它的情感。诗词的情致是和它的有音乐性的语言分不开的,要抓住情致,必须抓住语言的音乐性(例如节奏的高低长短快慢,音色的明暗等等)。语言的音乐性在默读中见不出来,必须朗读,而且反复地朗读,有时低声吟哦,有时高声歌唱。比如读一首歌(例如“歌唱我们的祖国”),只像作报告式地读是不行的,必须拖着嗓子唱出它的调子来,才能领会到它里面的情感。诗词和我们唱的歌只有一点不同:歌有一定的调子,而多数诗词或是本有一定的调子而现在已经失传,或是根本没有一定的调子。读者只能评自己体会到的情感,在反复吟诵中把它摸索出来。这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时时注意到吟诵的节奏和色调要符合诗的情调就行了。在这过程中读者会发见他原来所体会的那点情感还是浮面的,反复吟诵会使他逐渐进入深微的地方。中国诗词大半都不很长,择自己所爱好的诗词背诵一些,也是一种很有益的训练。
经典五言律诗篇5
【关键词】古诗词;高中音乐;开放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1-0328-02
1 古诗词的韵律之美
就艺术起源讲,诗、歌原本是一体的,或者说诗歌、舞、乐原本一体。《尚书 •尧典》所谓:“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又如《毛诗序》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我国最早的几部诗歌集如《诗经》、《楚辞》和《乐府歌诗》都来源于民间歌舞。标志着中国诗歌获得高度发展的唐代律体诗也大多是唱的(尤其七言绝句更是如此),“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丝簧,谐音节。”(谢榛《四溟诗话》)。
而古代诗歌与音乐也是孪生姐妹。《诗经》的风、雅、颂本是不同阶级于不同场合的骊歌,因此古诗都可以辅以管弦。魏晋南北朝时期沈括以“新体诗”开创了格律诗的先河,诗歌创作也就更注重声律。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五言排律的产生与发展,更是极大地丰富了“诗韵”的内涵。试想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妙句,何尝不是帝王之家辅以管乐吟唱的精品?
2 高中音乐学科开放式教学中对古诗词文化和流行音乐的融合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古诗词、传统音乐、现代音乐在当今的音乐课堂教学中很有其融合、借鉴的必要性。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把握这一点让学生获得更高的审美需求呢?
2.1 学科开放式教学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传统模式的音乐教学,往往是以教师为主导的音乐教育,教师机械地教,学生机械地学,日积月累,这种重概念、重技巧、轻感受、轻审美的教育思想,使学生离美好的音乐越来越远。
通过各学科知识的融合,在音乐课上让同学们不仅欣赏音乐,更要欣赏音乐以外的风景:江南小调中有小桥流水的风韵,京韵大鼓中有皇城根儿的气派;《阳关三叠》唱尽古人离别的愁绪,《黄河大合唱》尽泻国人抗日的激情;德彪西的《月光》虚实相间,和声色彩瞬息万变,与印象派的绘画一脉相承,贝多芬《庄严弥撒》庄严神圣,高耸入云的合唱声中透着哥特式的建筑美。如此听音赏乐,上通下达,点面结合,大千世界无不在音乐中显现,大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并使各相关的人文学科得以融会贯通。这样的音乐课,不管对教师或学生都是挑战,但更是享受与收益。
2.2 课堂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化,引导学生解读流行音乐:在课堂教学中,解读同主题音乐与诗歌、古诗新唱是实现艺术融合的最佳途径。而对流行音乐的客观理解也是课堂教学中应予以重视的主题。
(1)同主题音乐与诗歌鉴赏: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歌的韵律美是其最为共通之处。最典型的应该是诗、乐《春江花月夜》了。
《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旧,题属《清商曲吴声歌》。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来写,而又以月为主体。“月”是诗中情景兼融之物,它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在全诗中犹如一条生命纽带,通贯上下,触处生神,诗情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开头四句。
这首长诗的韵律节奏之美最为出色。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又平声韵起首,中间为仄声韵、平声韵、仄声韵、平声韵、平声韵、平声韵、平声韵,最后以仄声遇韵结束。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的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又是切合着诗情的起伏,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宛转谐美。
《春江花月夜》旋律古朴、典雅、节奏比较平稳、舒展,用含蓄的手法表现了深远的意境,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春江花月夜》的音乐构思非常巧妙,随着音乐主题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乐曲所描绘的意境也逐渐地变换,时而幽静,时而热烈,现实了大自然景色的变换无穷。此曲音乐意境优美,乐曲结构严密。它的主题旋律尽管有多种变化,新的因素层出不穷,但每一段都采用“换头合尾”的创作手法,听起来十分和谐。
两部《春江花月夜》作品让我们感受到诗含乐韵,乐融诗情的音乐文化特点。通过两者结合的欣赏,也更让我们认识到中国音乐特有的韵律美,浓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及中国音乐的博大精深。
(2)引导学生选择古诗词新唱作品:古诗词新唱这种方式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从清朝末年开始实行新式学堂教育至20世纪30年代,中小学学生在学校音乐课上唱的歌曲,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称之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中有一部分是倚声填词的古诗词歌曲(包括近代人用古体诗填词),如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送别》(李叔同填词)。
在流行音乐参差不齐而又极大冲击着音乐课堂的今天,选择部分古诗新唱作品做为课外延伸应该是不错的方法。但在作品的选择上应该注意几点:古诗词的声律(平仄)与歌曲旋律是否融洽;古诗词的文学结构与音乐结构是否相符;古诗词的内涵与音乐(旋律、伴奏)能否统一等等。
经典五言律诗篇6
一、感受韵律美、节奏美之读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诗歌最早是合乐吟唱的。所以,中国古典诗词不仅讲究韵律,还讲究鲜明和琅琅上口的节奏等美学特质。诵读中国的古典诗词,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古典诗词的声韵显示语言的抑扬,节奏显示语言的顿挫,正如郭沫若所言:“节奏之于诗,是她的外形,也是她的生命。”所以,在七年级上册教学古典诗词时,我就首先教给学生诵读古典诗词的基本方法,以此激发学生诵读古典诗词的强烈兴趣。其法:五言古典诗词通常只有3个节奏,比如唐代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七言古典诗词通常有四个节奏,比如唐代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春泥。……”而四言古诗的节奏一般只有两个,比如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在教会学生把握诵读古典诗词节奏的基本方法后,再引导学生采用全班齐读、小组读、个别读、高声吟唱等方式感知古典诗词的节奏美、韵律美、音乐美等,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轻松愉快的琅琅书声中完成对古典诗词上述诸美的体味、品鉴目标了。
二、感知形象美、意蕴美之读
教学古典诗词,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引导学生对古典诗词文本音韵美、节奏美的感知与品味上,还应该引导学生通过反复诵读的方式走进文本的深层意蕴,在读通、读顺、读懂古典诗词的过程中,收集和处理古典诗词文本中透露出的信息:读出古典诗词中蕴含的深刻道理,感知古典诗词中塑造的人物(事物)形象,感知作者在文本中运用的叙事、抒情、议论、用典等写作方式,体味文本中的主题思想和作者在文本中寄予的思想情感等。但是,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诵读古典诗词的指导,并非是句句领读,而是指导学生抓住古典诗词文本中的难点、重点和关键词、句来读,唯有如此,才会事半功倍。
比如,教学曹操的《观沧海》,我引导学生抓住诗歌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一体现曹操一统天下鸿鹄大志的既是描绘虚幻之美丽景色又是抒发个人远大抱负的诗句反复品读赏析。而后,我再对曹操写作这首诗的背景及诗歌的主旨等加以适当点拨:这首诗是曹操建安十三年(208)五月北征乌桓、消灭了袁绍残留部队胜利班师途中登临碣石山时所作,在这首诗中,诗人将自己北征乌桓胜利的喜悦、阔大的胸襟、一统天下的宏伟抱负等融汇到诗歌里,借对大海雄伟壮丽景色的描绘,表现诗人胸怀天下的进取精神。经此点拨,学生很快就沉浸在了这首古典诗词所营造的雄浑美丽的意境之中,全身心地去体味、感知曹操勇武睿智、文韬武略之高大形象了。
三、展开想象翅膀、创造新意境之读
雪莱说:“诗可以界说为‘想象的表现’。”中国古典诗词尤甚。因为中国古典诗词具有篇幅短小、语言凝炼、情感丰富、内蕴深远等美学特质,所以,诗歌创作时,作者唯有通过想象才能将复杂的社会生活、深沉而抽象的情思化为具体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而事实上,几乎每一位远古的诗人都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将有形的客观事物同自己丰富的主观情境等有机联系在一起,运用文字的功力将之组成一幅幅优美的、生动的、幻化的图景,从而使作者无限抽象的情思寄托在具体可感的意象之上,起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艺术效果。
经典五言律诗篇7
那么,如何才能使古典诗词教学水平有所提升呢?笔者以为,应该充分挖掘传统诗话、词话中的资料,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前贤时彦的评析,然后形成自己对诗词的感悟。也许有的教师在讲解诗词时会引用一些诗话、词话中的材料,但往往是随意的,缺乏系统性和明确目标,与本文这里所讲的专门利用诗话、词话进行古典诗词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近年来,已有人关注和重视诗话、词话在古典诗词教学中的作用,如钱士宽的《巧用诗评词话,搭建鉴赏桥梁》、陆精康的《诗话与唐诗教学》等文章探讨了中学语文中的诗词教学如何利用诗话、词话的问题。近年出版的一些教材如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蒋寅等人主编的《唐诗宋词选读》中都附录了一些诗话、词话中的评语,这对于我们利用诗话、词话进行古典诗词的教学大有裨益。
一、在诗词教学中利用诗话、词话资料的意义和作用
在教育技术突飞猛进、文学批评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诗词教学中搬出古代诗话、词话这些老古董呢?
首先,诗话、词话根植于本土文化,对诗词的理解与阐释最准确、最到位。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缺乏理论系统性,较为零散,“大半是偶感随笔”,甚至有的批评者认为它们过于“偏重主观,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1],其实这正是根植于我国的本土文化而形成的特色。先秦时期的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后来受禅宗影响出现的“妙悟说”,更重视主体感悟,物我合一,这就导致了诗词批评必然是主观感悟式的。事实上,只有这样的片言只语,才更能切中我国古典诗词艺术之肯綮,若是强行构建出一套类似西方文艺批评的体系来,可能会束缚阐释者的手脚。
在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中,有许多独特的诗词批评方法与范畴。比如,言及章法结构时,经常会提及“精思”、“诗眼”、“起承转合”、“断续之法”等;言及诗词形式时,经常会提及“炼字”、“换头之紧要”等。古人十分重视字词之来历,诗话、词话中有大量篇幅便指出如何“沿袭”、“点化”、“夺胎换骨”;古人看重佳句、警句,因而有许多诗话、词话都会集“警句”、“秀句”,进行摘句点评;古人持论较严,往往毫不客气地指出名家之作中的一些诗病、诗累、瑕疵等,……所有这些,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很少涉及,它们正是立足于中国诗词自身的特点,会使我们对古典诗词的理解更加准确到位。
其次,可以让学生了解该诗词的接受史。目前,各种教材中所选的古典诗词多是经典作品,正如陈文忠所言,“文学经典的意义整体始终处于动态生成和历史累积的过程之中”,而宋代以来的诗话、词话,“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接受文本”[2],也就是说,诗话、词话中对诗词的解读参与建构了该作品的经典性。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利用诗话、词话,了解和分析该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中的接受及评价情况,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阐释古典诗词。比如,我们在分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如果能把程千帆先生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进行展示,并结合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让学生了解《春江花月夜》一诗在宋元时期的忽视与误解及在明清时期的重视与褒奖,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一定会更加全面深刻。
再次,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国古代的诗词批评理论。目前,很多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时,往往会介绍一些空泛、枯燥的思潮、理论或发展史,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倘若在诗词教学过程中,联系具体作品介绍和引用一些诗话、词话的概念和范畴如“清”、“蕴藉”、“醇雅”、“浑成”、“极虚极活”、“欲露不露”等,一定会让学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当下我们的文学批评总是“跟着西方走”,始终没有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批评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认真踏实地分析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而是“空对空”地建构一种又一种新理论,结果只能是理论本身的重叠并最终走向坍塌。因此,通过古典诗词教学中对诗话、词话的挖掘和探究,能够更好地提炼、总结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与理论。
最后,有利于开展探究式教学,为学生研究古典诗词奠定基础。目前,全社会都在提倡创新教育。在古典诗词教学中,也应该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可以利用诗话、词话中的资料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短时期内积累部分材料,掌握研究现状,而诗话、词话中对作品的多元化评价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只要教师有意引导,学生很快就能展开对古典诗词的研究。
二、利用诗话、词话教学的方法与案例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该如何操作呢?大致来说,主要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收集诗话、词话中关于该诗词的评语。
这是准备资料的阶段。目的是通过阅读大量的诗话、词话,收集、汇编对该诗词的评价与评点。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浩如瀚海,怎么样去阅读和查找呢?目前,一些重要的、价值较高的诗话(包括诗论)、词话已得到整理和汇编,如诗话方面,以前有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丁福保辑的《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郭绍虞编选的《清诗话续编》,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和《明诗话全编》、张寅彭编的《民国诗话丛编》等,词话方面有唐圭璋编的《词话丛编》、朱崇才编的《词话丛编续编》等,此外,还有一些诗话、词话的单行本也已整理出版,查找和阅读起来比较方便。
然而,如果每讲授一首诗词,都要去翻阅这么多的诗话或词话,显然不太现实。当前出现了一些收集、汇编诗词评语的书籍,如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袁闾琨主编的《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王兆鹏主编的《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吴熊和主编的《唐宋词汇评》(两宋卷),周笃文、马兴荣主编的《全宋词评注》,钟振振等人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此外,还有一些书籍可资参考:(1)《中华大典》中“文学典”系列,如《先秦两汉文学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宋辽金文学分典》、《明清文学分典》等,其中列有后人对该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语;(2)集解、汇评性质的作家文集,如詹A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等;(3)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如《三曹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白居易资料汇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等。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艰苦甚至艰巨的工作,需要教师平时进行有意识地积累。教师应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随着教学时间的增长,必定会积累丰富的资料。同时,还可以通过提示和指导,安排学生去收集相关的资料,从而锻炼学生搜集材料与阅读材料的能力。
第二个环节,理解与阐释诗话、词话中的评语。
这个环节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将收集到的资料印发给学生,或以课件PPT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充分地理解相关的资料,并进行必要的阐释、归纳和总结。以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该诗为:“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古人的评论约有三、四十则,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中精选出以下数则[3]:
王a登《唐诗选参评》卷三:后四句言虽离远而情若对面,故不欲如儿女子之态。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
陆时雍《唐诗镜》卷一:此是高调,读之不觉其高,以气厚故。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一:钟云:此等作,取其气完而不碎,有律成之始也,其工自不必论。
黄生《唐诗矩》:前后两截格。前二句实,后六句悉虚,恐笔力不继,则易疏弱,此体固不足多尚。
凌宏宪《唐诗广选》:顾华玉曰:多少叹息,不见愁语。
范大士《历代诗发》卷八:后四句虽旷达,而意实酸辛。
卢、王溥《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卷一:陈德公评:通首质序,未免起率易之嫌。顾尔时开拓此境,声情婉上,正是绝尘处。陈伯玉之近调,高达夫之先驱也。五六直作腐语,气旺笔婉,不同学究。结强言耳,黯然之意,弥复神伤。
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七:此等诗气格浑成,不以景物取妍,“真”初唐之风骨。前解写别,后解言不必伤心也。
杨逢春《唐诗绎》卷十六:通首一气旋转,格局浑成,且纯是言情,不着景物,尤高妙。
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赠别不作悲酸语,魄力自异。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吴北江曰:壮阔精整(首二句下)。又曰:凭空挺起,是大家笔力(“海内”二句下)。姚曰:用陈思《赠白马王彪》诗意,实自浑转。
胡本渊《唐诗近体》卷一:前四句言宦游中作别,后四句翻出达见。语意迥不犹人,洒脱超诣,初唐风格。
俞陛云《诗境浅说》:一气贯注,如娓娓清谈,极行云流水之妙。大凡作律诗,忌支节横断。唐人律诗,无不气脉流通,此诗尤显。作七律亦然。
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这些评语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送别诗经常会铺叙景物,这首诗却未着力于此,纯为言情(《诗薮》、《古唐诗合解》、《唐诗绎》)。
2.这首诗抒发的情感“不见愁语”,翻出达见,实则酸辛(《唐诗广选》、《历代诗发》、《唐诗三百首补注》、《唐诗近体》)。这一点可联系王勃的生平进行阐发。
3.这首诗一改齐梁以来的软媚之气,虽言离别却洒脱超逸,积极健康,魄力自异,壮阔博大,气格浑成,风骨硬朗(《诗薮》《唐诗镜》《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补注》《唐宋诗举要》《唐诗近体》)。
4.虚实结合,章法独特,客中送客,如临其境(《唐诗选参评》、《唐诗矩》、《唐诗近体》)。
5.虽处于律诗初创之时,但气脉流通,工整精炼(颔联不对,为“偷春格”),转承自然(《唐诗归》、《诗境浅说》)。
6.“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源自曹植诗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但专注友情,用于此处亦更为契合浑转(《唐宋诗举要》)。
总之,通过分析这些诗话中的评语,无疑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此诗在抒情、题旨、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比以往单纯地讲解字词、意象、意境要更有深度,更富有吸引力。
第三个环节,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评判。
如果仅仅停留在体会、理解古人评语的阶段,自然是不行的,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缺乏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因此,还要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评判。仍以上面所引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诗为例,在理解了该诗之后,教师一定要追问:这些评价、评点准确吗?有没有道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王溥在《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卷一所引陈德公评语:“通首质序,未免起率易之嫌。”由于王勃此诗只言事与情,质实直叙,缺乏一种空灵蕴藉之感,故有“率易之嫌”。可以引导学生对此进行评判,表达自己的意见,还可以将其置于送别诗的发展长河中,与人们普遍接受的送别诗范式进行比较,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王勃此诗的艺术性。
三、教学反思
笔者在近年来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唐诗欣赏”、“宋词欣赏”等课程的过程中曾尝试和采用过这种方法,总体效果比较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大量引用古代的资料,与今天的生活和话语距离较大,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充满学究气。如果学生的文言功底不够扎实或理解有困难时,很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
第二,古代诗话、词话重感悟,点到为止,评语又极其简略(如“佳”、“妙”),对学生进行解释的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合适恰当的表述语言,即所谓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第三,许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习惯了接受标准答案,而诗话、词话中的评析异彩纷呈,甚至还有一些相反或抵牾之处,当学生面对这些多元化的评语时,常常不知所从,甚至会产生茫然失望感。
上述这些问题,相信会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并解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词教学应该尽量避免机械、琐碎的经院式讲解,也不可操之过急,强加解释,“填鸭式”地硬塞给学生,其实,学生有时在课堂上没有理解的诗词,后来会随着阅历的增加而得到自我开悟。笔者以前在课堂上曾给学生讲解过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一词,后来有名学生在毕业离校时告诉笔者,他觉得此词写离别最为真切。原来他要和多年的女友分手了,面临着毕业以后天各一方的境况,自然对词中“去意徊徨”的别情感同身受,对该词的理解比原来要深刻多了。
注释:
[1]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陈文忠《接受史视野中的经典细读》,《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第170―177页。
[3]主要参考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卞孝萱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凤凰出版社,2000年版)等。
经典五言律诗篇8
关键词:桐城派 方东树 诗歌史论 昭昧詹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86-92
郭绍虞先生曾指出:“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1如就诗学而论,作为桐城诗学代表作的《昭昧詹言》,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当有重要地位。该书在著述体例上,采用先总论各体,然后依体选诗,按时代先后排列作品进行分论。这种以“体”为经, 以“时”为纬的著述方式,使其具有明显的诗歌史论之特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该书实际上是一部诗歌史论性著作,体现了以方东树为代表的桐城诗派对诗歌史及其演变过程的基本看法。本文讨论其诠释模式与呈现出的批评形态,一是为揭示方东树诗学体系的展开方式,二是揭示其诗学批评的基本风貌,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诗学意义。
一
一般而言,采用什么样的诠释模式取决于诠释对象的性质及特点。不同对象,其诠释的方式也应有别,否则,会出现文不对题或似是而非的情r。作为诠释对象,《昭昧詹言》不同于诗学史上“以资闲谈”为目的、随意点评式的诸多诗话,它既有系统的诗学理论,又有系统的诗歌史批评。其理论的系统性表现在,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诗学批评体系。其中,诗歌观念是理论基础,诗歌史观为指导思想,诗歌史批评方法是具体的诗歌批评采用的批评策略。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三位一体,都是其诗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史学认为,“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1照此理解,《昭昧詹言》可以视为方东树依据其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对诗歌史进行批评而著述成的一部诗歌史,其中隐含的诗学理论就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诗学批评体系,这种认识是符合文学史学一般原理的。
就文学观来说,诗歌观念主要是对诗歌的性质、内容和形式、功用和价值、审美理想等的基本看法。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诗歌批评者,方东树总不会对诗歌一无所知,只要有所知,就有诗歌观念的存在。《昭昧詹言》作为诗学著作,其批评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诗歌体制,二是诗歌作品。就体制而论,只论及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七言律诗。就作品而论,每种诗体只论及具有典范性的几个诗人诗作。这表明方东树对诗歌史实是经过取舍的,这种取舍总是以其诗歌观念为基础的。方东树认为“诗之为学,性情而已”2,又说“诗以言志”3,在诗歌观念上除继承先秦“言志”传统和汉儒以来的“吟咏情性”之说之外,又从桐城古文理论出发,强调“诗与古文一也”4,不知古文不能为诗,在审美取向上奉持方苞“雅洁”之理想,崇雅贬俗,崇真黜伪。这些诗歌观念制约着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评论及致思方式,是其诗歌史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文学史观主要是回答诸如文学是进化的抑或是退化,文学与政治、经济及其他文化门类,特别是意识形态关系、文学史是否可以说是形式演化的历史,文学史是否有盛衰,盛衰是否有规律可循等问题。5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歌史观则主要是以对诗歌史上的“源流正变”、“通变”等现象的探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对此,方东树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中云:“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以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知正知奇,博学之以别其异,研说之以会其同。”6在他看来,“师法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是“文章之道”,其对诗歌史上诗家诗作的评论既是为了证明“师而不袭”是历代诗家创作之正道,又是为了指导后学,如何才能“师而不袭”。“师古”是为继承,“不袭”是为创新,对继承和创新间的关系,方东树提出要“善因善创”,这表明方东树有明确的通变观念,这是其评论诗家从因革关系入手的思想基础。他提出的“知正知奇,别其异,会其同”,又表明方东树有着明确的“正变”思想。方东树的“通变”“正变”观是方东树对诗歌史演变规律的基本看法,是方东树诗歌史观的思想内核。概括地说,方东树的“正变”观主要是对诗体“正变”的认识,持“变而不失其正”之立场。“通变”观上继承了刘勰的观点并整合了叶燮的“通变”思想,有以复古为新变的倾向。方东树的“正变”思想和“通变”观相结合,就形成了其“离合”论7,也就是其对诗歌史演变动力及其路向的看法。
诗歌史批评方法是对诗歌史上诗人诗作进行评论所采用的批评策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开展诗歌批评,取决于批评者的诗歌观念与诗歌史观。方法总是来自于观念,观念不同,批评方法就会不同。在文学史上,因为文学观念的不同,文学史研究就有“主题学”和“语言学”方法之别8。再者,批评方法的运用如无明确的诗歌观念、诗歌史观作指导,也易流于漫无目的、随意式批评,易使人感觉到混乱而不知所从。如在《昭昧詹言》中,由于方东树诗学观念上坚持“诗文一理”,在批评诗家诗作时,往往从古文的角度,采用人们所熟知的“以文论诗”的批评方法,借之达到正本清源、澄清诗史、导示后学之目的。这其中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确保了诗歌批评方法运用的针对性和批评过程的有序性。
简而言之,方东树就是依据其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对诗歌史上的诗人诗作进行取舍、组织并采用特定的批评方法加以评论,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诗学批评体系的。方东树对诗歌史诠释策略的选择必须服务于这一批评体系的建构。采用适当的诠释模式对这一批评体系的展开尤其重要,它为观点的合理性、论证的逻辑性的实现提供具体的途径。
二
《昭昧詹言》内含的诗学批评体系对诠释模式的制约主要体现在:方东树是凭借自己的诗歌史观来选择诗歌典范的。面对诗歌史上众多诗家诗作,方东树以其诗体“正变”观为标准,择其善者为典范,作为批评的对象。其次,依据其创作上的“通变”思想,对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关系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即为具体的诗歌史批评行为,而其理论依据正是其诗歌观念。据此可知,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采用是“正变-通变”批评相结合的诠释模式。
具体说来,方东树对诗歌史的批评是遵循先以“正变”辨体,后以“通变”辨流这一轨迹展开的。方东树的“正变”思想,旨在辨明体制,即辨清诗歌的“正体”与“变”体,弄清诗歌的源与流;其“通变”观念,则旨在评论创作,评析具体诗歌创作上的因革问题。在《昭昧詹言》中,方东树对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的体制先后进行详细的论究,并列出相应的诗歌典范,然后以“通变”的眼光来识别这些诗歌典范之间的源流关系,并以此为序依次加以评论,从而构成较为完整的诗歌史批评过程。如从《昭昧詹言》所评诗体来看,方东树对诗歌史批评实际是分体诗歌史批评,即由五古诗歌史、七古诗歌史、七律诗歌史组成的诗歌史批评系列。对诗歌典范及其创作上的因革关系的批评是其诗歌史批评的主要内容,因此,方东树基于其诗歌史观所建构的诗歌史主要是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史。
方东树本其“正变”观念,依体定人,确定典范,明其源流。再依源流先后,详论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关系。这种诠释模式呈现的是具体的批评活动,属于微观层面。如从宏观层面上看,这种“正变”与“通变”相结合的诠释模式又体现为由通论各体到个案分析模式,并被用于对各体诗歌史展开评论。
以七古诗歌史论为例,他先通论七古体制,分别论及七古的创作特点:以才气为主,以古文法行之;七古的语体风格:朴、拙、琐、曲、硬、淡,总归于“老”;七古创作方法及其运用:叙、议、写;七古的文法:命意深、下字典、取境远;七古章法:顺逆开合展拓,变化不测,着语必有往复逆势;1此外,对七古的用事、笔力、造语等方面也作出具体的要求。
在通论七古体制特点的同时,又结合自己的诗歌观念,对七古的创作典范亦作选择。李白、杜甫,“二千年来,只此二人”2,代表着七古诗歌创作的最高典范,是七古之“正”,而韩愈、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诸家的诗歌与杜甫“一灯相传”3,是七古之“变”。方东树按照七古流变先后次序,对李白、杜甫等诗歌典范进行个案分析,论其诗歌艺术手法、风格等,具体展现七古之流变过程。这种从通论到个案批评的诠释模式,还体现在单个诗歌典范的批评之中。他对具体的诗歌典范的批评也是先以翟蜃苈燮涫歌创作特点,后举其作品个案进行点评。如其在《昭昧詹言》卷五专评陶渊明诗歌,前十七则就对陶诗创作各个方面作了总论,从十九至八十五则评其具体作品,以证总论之观点。这种模式也体现在对组诗的批评中,如评杜甫的《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等。
通论到个案的诠释模式,成为方东树著述基本思路,规定了《昭昧詹言》一书基本结构。如从论证的角度来看,这种诠释模式是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后以论据支撑,观点与论据的充分结合,显然更有说服力。它与“正变-通变”相结合的批评模式一起构成方东树诗歌史批评两条路线,一从宏观层面规定诗学批评的基本方向,一从微观层面指导具体的批评行为,形成方东树诗学批评“复调叙述”,这使其诗歌史论具有诗学实践上的方法论意义。
三
方东树对诗歌史的评论主要是针对诗歌典范的评论,且又侧重在诗歌形式层面展开,从批评形态上看,其诗歌史论应属于文体批评,具有形式美学批评的特点。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分析,一是注重其诗歌的因革,二是注重诗歌的形式。注重诗歌的因革,这是其诗歌史论的题中之义,注重诗歌形式的审美批评,是其指导诗歌创作的需要。他本其“正变”思想,辨别五古、七古、七律诗歌体式,论其形式之别及创作上的特点,其意即是为了指导诗歌创作。诗歌体式属于诗歌形式,体式的因革主要指形式的因革,对诗歌创作而言,既有诗歌形式的创新,也有诗歌内容的创新,方东树强调“以新意清词易陈言熟意”1即是言此。但“意”随人变,人随时变,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的“意”自然不同,故其创新往往为易。而“词”相对稳定,其用易被约定俗成,尤当诗歌的“词”经组合,形成一定的体式,就有规范、约束之力,如不能有所突破,就会流于因袭,故创新实是不易。方东树于此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他对诗歌创作中的“合”与“离”的论述,多次强调其难,主要是对诗歌形式、技巧等而言。从其诗歌史批评来看,他是沿着由文体论、创作论至批评论这一思路来展开的,文体论侧重形式,相应的,创作论、批评论也侧重于形式,这是合乎其致思方式的。方东树指出:
读古人诗文,当须赏其笔势健拔雄快处,文法高古浑迈处,词气抑扬顿挫处,转换用力处,精神非常处,清真动人处,运掉简省、笔力崭绝处,章法深妙、不可测识处。又须赏其兴象逼真处:或疾雷怒涛,或凄风苦雨,或丽日春敷,或秋清皎洁,或玉佩琼琚,或萧惨寂寥,凡天地四时万物之情状,可悲可泣,一涉其笔,如见目前。而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至于义理渊深处,则在乎其人之所学所志所造所养矣。文字忌语杂气轻,既无根柢,又无功力,尚不能深清雅洁,无论奇伟。2
读古人诗,须观其气韵。气者,气味也;韵者,态度风致也。如对名花,其可爱处,必在形色之外。气韵分雅俗,意象分大小高下,笔势分强弱,而古人妙处,十得六七矣。3
他认为解读古人诗歌,主要从笔势、文法、词气、转换、精神、清真、笔力、章法、兴象、文字、气韵等角度来入手,评论其得失之处。而“义理”则存于作者之志之学,论其深浅须看其人而非其诗。这种认识,使得其对诗歌典范的批评侧重从笔势、文法等形式方面展开。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谈到作品接受时,提出“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4这“六观”中,除“事义”属于作品意义层面外,其余都属于作品的形式层面。方东树对前人诗歌的接受,“事义”关注不多,故主要是“五观”。
我们说方东树诗歌史论着眼于诗歌的形式层面,注重分析诗歌的用意、兴象、文法等形式要素,并不意味着他对诗歌的意义层面分析不作任何评论,他对诗歌的意义层面亦有点评,但并非主要,多服从形式批评之需要。如其评杜甫七律中《诸将》五首,先总论此组诗歌形式、技巧上的特征:
此咏时事,存为诗史,公所擅场。大抵从《小雅》来,不离讽剌,而又不许讦直,致伤忠厚。总以吐属高深,文法高妙,音调响切,采色古泽,旁见侧出,不犯正实。情以悲愤为主,句以朗俊为宗,衣被千古,无能出其区盖。5
他认为此组诗具有怨而不露、意蕴深曲、文法高妙、音调响切、采色古泽、字句朗俊等特点。接着逐个评论该组诗单个诗作,虽有对诗歌意义层面的评论,如纠正前人旧说、点评句意等,却为说明该组诗的上述特点提供证据支持。如评组诗其二云:
告河北诸将,以张仁愿勉之,极言借助回纥之非。何义门解之最当。回纥倾国而至,而异于太宗之用突厥。汾阳勋虽大,而此自为非。他日回纥助史朝义内侵,至三城州县皆为邱虚,遂有轻唐之心。其后虽复助顺,而所过抄掠一空。其后助仆固怀恩,侵至泾阳,虽听汾阳击吐蕃自赎,而唐之被侮亦极矣。公言肃、代之不如高祖、太宗也。笺失之。起四句,大往大来,一开一合,所谓来得凶猛,乾坤摆雷也。五句宕接,六名绕回,言后之弱,以思祖宗之盛为开合,笔势宏放。收点明作意归宿,作诗之人本意。此直如太史公一首年月表序矣。与前首同一章法,五六为开合,朔方与突厥,以河朔为界,仁愿乘虚,压漠南城。1
此评先集中于诗歌意义层面的分析,言诗义大略,后集中于形式层面,言其章法布置,文法高妙。文法高妙正是体现在诗义的巧妙表现,故言诗义正是为说文法提供证据支持。统观方东树对诗歌史上诸家诗作的评论,他往往不是作诗义的分析,而是径言诗歌形式上的创作特色,所以如此,是因为诗歌典范间的因革关系,主要是诗歌形式上的因革,而意义层面的因革则不明显,对诗歌学习者来说,诗歌形式层面的因革对其诗歌创作更具有借鉴意义,这是方东树的诗歌史批评侧重于诗歌形式批评的重要原因。
方东树的诗歌史批评注重形式与其诗教观念是有矛盾之处的。如果从诗教观念出发,像义理不能兼备的谢灵运、无血气性情的王维这样的诗人应该在其诗歌史之外,但事实是二者在其诗歌史上均居有重要地位,王维甚至是七律诗歌之“正宗”,是与杜甫相并肩的“二派”2之一。这一矛盾,除与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选择不完全基于其诗教观念相关外,还与他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认识分不开。方东树曾云:“昔人言《六经》以外无文章,谓其理其辞其法皆备,但人不肯用心求之耳。”3有以《六经》为文章最高典范之意,后人苟能用心深求《六经》,其诗文、理、义皆善,如杜甫、韩愈等,如不能直接深求于《六经》,其诗于“理”常有所失,而依其才狻⑻旆值鹊梦摹⒁逯善。如谢灵运、王维等。也就是说诗歌的“理”可以从《六经》中获得,但“文、义”则不一定,因其可以凭自己的天分、才气获得。而且“理”是不能通过天分、才气获得的,只能靠后天的学习。方东树将“义理”独立出来,说其存于作者的立志与学养,认为其与诗歌的文、义即形式因素、法度技巧无关。从指导创作来看,“有德者必有言”,作者能否深于“义理”固然对其诗歌创作极为重要,但这主要取决于其主观努力,如通过读书、问学来丰富自己的学问、提高自己的操守等,但这些并不能从作为典范的诗歌中直接获得,而诗歌创作的法度、技巧等则可以通过对典范作品的研读直接获得启示。谢灵运、王维等诗家之所以能进入方东树的诗歌史之列,就是因其诗在法度、技巧上的卓越,能同杜甫、韩愈等诗家一样给后人以启示。因此,方东树的诗教观念与诗歌史论之间矛盾的深刻根源,在于其将诗歌的形式层面因素(文与义)与内容“理”或“义理”剥离开来,不能将其创作主体的“本源”论4在诗歌批评中贯彻到底。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方东树注重诗歌的形式批评的原因。
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批评注重诗歌的形式、技巧,这使得其所理解的诗歌史表现为诗歌形式演变史,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律论倾向。但需注意的是,方东树对诗歌形式的批评与其对创作主体的批评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也强调“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批评,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因此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四
综上所论,《昭昧詹言》隐含着一种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和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潜在的诗学批评体系,此虽未见于方东树明确的理论表述,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它证明了方东树的诗学思想确实具有系统性,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缺少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1。受这种批评体系制约,方东树对诗歌史的批评采用两种模式,一是微观层面的“正变”与“通变”批评相结合的模式,二是宏观层面的通论-个案分析的模式,这两种模式保证了其诗歌史论的逻辑性、完整性并呈现独特的风貌。
其一,方东树诗歌史论诠释模式体现了历史原则与审美原则相统一。艾略特在《个人与传统》一文中指出:“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己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我打算把这个作为美学评论、而不仅限于历史评论的一条原则。”2“正变―通变”诠释模式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诗歌典范放入诗歌传统之中,辨析其创作与前人作品之联系,探究其作品独特面目的形成原因,这种批评就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诗人诗作作纵向的考察。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批评又着重从作品形式层面辨析,通过剖析作品气韵、气势、兴象、精神、章法等形式要素来揭示创作风貌并将其与同时代诗家作品作比较,这种批评是从审美的角度对作品作横向的探究。因此,方东树采用的诠释模式既是历史的,又是审美的。
其二,建构了桐城派传统诗歌发展史。“正变―通变”诠释模式本身含有正本清源之目的。方东树对诗歌批评史是有着深刻的反思的,“千百年除李、杜、韩、欧数公外,得真人真知者,寥阔少见,则何如求通其辞通其意之确信有依据也?3”在《昭昧詹言》中,他“信古求真,商榷前藻”4,力求做到不诬古人,不误来学。可见,求得对诗歌史的正确认识,是其著述的重要动机。其实现途径就是采用辨体析流的方式,考察诗歌史上诗歌典范的源与流,阐释其间的因革关系,进而明确诗歌创作之正道,诗史演变之轨辙。这种注重典范之间因革关系的诗歌史批评,实际上是对传统诗歌演变过程进行重新梳理,其结果是建构起一部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诗歌发展史。
其三,确立了诗歌典范在桐城诗学传播中的价值。重视文学典范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特征。其主要体现是文学选本的大量存在。中国古代文论家宣示自己文学主张、争取批评话语权、显现自己存在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选本。选本是由选者遵从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对既已存在的作家作品进行挑选并按一定的体例编纂的。这些挑选出来的作家作品是选者文学观念、审美理想的载体,并通过历代读者的阅读、摹仿发挥影响力。桐城派非常重视选本的这种作用,编选了大量的文章选本,著名的如姚鼐的《古文o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等。《昭昧詹言》就是依托王士祯的《古诗选》、姚鼐的《今体诗钞》,参以刘大《历朝诗约选》《盛唐诗选》《唐诗正宗》等诗歌选本,并经方东树熔铸改造著述而成的,其中集成了桐城诸老如姚范、刘大、方绩、姚鼐等人的诗学智慧,被视为桐城派诗学的代表作。方东树对其中的诗歌典范,从桐城古文的视角进行系统的诠释,充分揭示了诗歌典范在导示后学中的实践意义,指明了桐城诗学在薪火相传中的基本方向。此举虽在配合其师指导后进,却也收到借助两种选本的流行,宣示自己诗学主张的效果。方东树是以此方式参与了桐城派诗学理论建设的。
其四,争取诗学话语权,确立桐城诗学之地位。方东树认为:“凡著书立论,必本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1又说:“吾观古今才高意广、自矜大雅,而心粗意浮、蔽于虚妄,卒不登作者之堂、当作者之录者,如牛毛;则余此书虽陋,而亦无可诟病者。使言之失当而有误有,不可以质古作者,斯当诟病耳。”2《昭昧詹言》是方东树“不得已而有言”,因为诗学史上众多诗家“心粗意浮、蔽于虚妄”,所论多有失当,其言不仅无用,而有害后学。在他看来,诗学真理是掌握桐城诸老手中的,“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者”3,作为桐城后进,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对历代诗论多有批评,特别是对明清两代诗坛风云人物如前后七子、钱谦益、王士祯、袁枚等均有批判。可见,方东树对诗歌史的重新诠释,不仅是实现其师“存古人之正轨,以正祛邪”之目标,而且在客观上是在替桐城派在诗学领域争取话语权,从而确立桐城诗学在诗坛之地位。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and Critical Forms on Fang Dongshu’s Poetry and Historical Discussion
Guo Qing lin
Abstract: Zhao Mei Zhan Yan is a historical poetry works, which implies a set of poetry criticism system with the logic relation of itself.It is made from poetry concepts, historical view of poetry and poetry criticism approach . In the open way, Fang Dongshu uses“zhenbian-tongbian”criticism and “general theory-individual case analysis”combining interpretation model, Coming into being “ polyphonic narration ”from the micro and macro aspects; In the form of criticism,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m aesthetics criticism, embodies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principle and aesthetic principle. Thus, Fang Dongshu 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poetry development histor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ongcheng school, established the value of poetry model in Tongcheng poetic communication, who strove for poetic discourse and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 Tongcheng poetics.
Key words: Tongcheng school, Fang Dongshu , history of poetry,Zhao Mei Zhan Yan
1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69页。
1 董乃斌著:《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2 方东树著,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3 《昭昧詹言》,第2页。
4 《昭昧詹言》,第376页。
5 董乃斌著:《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6 方东树著,《考集文录》,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六卷。
7 参见拙作《方东树“离合”说及其文学史意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
8 陶东风著:《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1 《昭昧詹言》,第232页。
2 《昭昧詹言》,第232页。
3 《昭昧詹言》,第237页。
1 《昭昧詹言》,第17页。
2 《昭昧詹言》,第23页。
3 《昭昧詹言》,第29页。
4 范文澜著:《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
5 《昭昧詹言》,第404页。
1 《昭昧詹言》,第405页。
2 《昭昧詹言》,第378页。
3 《昭昧詹言》,第8页。
4 方东树论学,尤重涵养本源。在其著作中,“本源”有时作“本原”,如“文章之道……言不失本原”,本原即“本源”,见《姚石甫文集序》,《考集文录》,卷三。
1 刘文忠:《试论方东树的诗歌鉴赏》,《江淮论坛》,1983年第五期。
2 [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译:《个人与传统》,《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3 《昭昧詹言》,第537页。
4 《昭昧詹言》,首页前《述旨》。
1 方东树著:《书林扬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经典五言律诗篇9
[关键词]胡适;新诗传播;“矫枉过正”;重达文学史;“戏台内喝彩”
1919年《新青年》四卷一号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胡适、沈尹默等3人的9首白话新诗,白话新诗从而得以正式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之后,胡适白话新诗集《尝试集》从1919年10月初版到1922年10月第四版,印数累计达151300册,白话新诗在当时掀起的热潮足见一斑。即使从清末的“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心”开始算起,白话新诗从萌芽到生成,也不过二三十年的事情。而若是从胡适私底下试作被讥为“莲花落”式的白话诗算起,则不过是一两年间的事情。相较格律诗经过了从南北朝到初唐两百多年漫长的酝酿成熟过程,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能在“骤然间实现成功”,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这固然是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有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但直接促成的还是胡适等人对新诗不遗余力的倡导。假若孤立地解读胡氏当时的新诗理论与创作文本,似乎要解构这个新文学运动中的权威与经典并不困难。但任何历史都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阐释它的意义。因此,回到历史的现场来重新审视胡氏,我们会发现,在一些看似矛盾错讹之中,其实暗含着倡导者苦心孤诣的传播策略。
一 “矫枉过正”——开拓新诗传播空间
一种新观点的提出,好评如潮,应者云集固然可喜。但最大的可能是如泥牛入海,杳无声息,直至自生自灭。五四时期各种观点学说风起云涌,但能独领风骚、独当一面者寥寥无几,大多很快便销声匿迹。胡适的新诗主张最初成型于在美留学期间,但这时他和好友书信往返探讨这一问题,简直都未能在小范围内取得一致认同,更遑论形成有效的大众传播空间。因此,欲让白话新诗脱颖而出,引起广泛关注,不致淹没于学说的汪洋大海,与其立论公允、严密论证,不如先提出一些具有冲击力的口号更见成效。
胡适起初打出“文学改良”的旗帜,表面上似乎还比较审慎温和,实质上颠覆文学传统的态度十分激烈,丝毫不亚于那些高呼“文学革命”者。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那三个“推倒”固然很具代表性,而胡适断言“文言是半死的工具”,则针对性更强,更具振聋发聩的效果。
在倡导白话新诗时,胡适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律诗:“施耐庵、曹雪芹等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这明显是以白话、文言而论高低。在“骈文律诗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之后,又似嫌否定不够彻底,还加上一句“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
除了对律诗诗体形式在整体上加以否定外,胡适还对那些古典律诗中常用到的具体技法加以贬斥。在谈到古文不合文法时,专门举例说“不讲文法,骈文律诗尤甚”。他把古代诗歌中的倒装手法用现代语法的标准加以否定,说是对古典诗歌艺术的一种有意漠视似也不算为过。再比如在“文章八事”中赫然写着“不用典”。毋庸置疑,用典作为一种重要修辞手法,在任何一个有着文化传承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诗歌创作,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要着意避免反倒成了不自然的事情。便是胡适自己也未能避免,他倡导新诗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尝试”二字便典出陆游之诗。因此他不得不在“不用典”一条之下又加上许多注脚,举例说明用典“工”“拙”的区别,命题便由“为何不能用典”悄悄转换成“如何用好典”。
然而胡适对待古典文学,尤其是律诗真是这等轻视吗?似乎不然。刚去美国留学时,他就曾谈到“吾国之学子有几个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显然他很鄙视对中华古典文学不了解的人。他在晚年更是“晚来渐于诗律细”,以创作近体诗为主。甚至私下还谈到“做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功夫”。如果说这些只是代表他文学革命以前的看法和文学革命之后的觉悟,那么我们细细检读他在倡导文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说法,便更足以说明问题。
在《谈新诗》一文中,他先赞新诗运动是“诗体的大解放”。同时贬低律诗:“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三个“决不能”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对传统格律诗的全盘否定。可是接下来他在论及新诗的音节问题时,又均以唐诗宋词的例子加以说明。谈到自己作新诗的经验,更是直接拈出清代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里双声叠韵的做诗技巧作为标准。最后,为了说明做诗的抽象与具体之别时,又不遗余力地举出了从《诗经》到唐诗再到宋词、元曲等大量优秀古典诗歌作为正面例子。
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若是不放在文学革命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便很难理解。胡适由主张“文学改良”到后来和陈独秀等一起为“文学革命”呐喊,与其说是立场的改变,不如说是方式的调整。《新青年》读者张寿朋曾提出:“时势所趋,文学当然要改良,也不是一场什么大不了的事体。——诸君又何必要大惊小怪地树起一块‘文学革命’的招牌来呢。难道是杜工部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这位读者看出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微妙变化,却不知“出语惊人”正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要达到的目的。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结尾中提到:“此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维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偏激的内容正是要引来受众热烈讨论的。胡适当初看到林纾的反驳始则高兴,后见其反驳不够有力则失望不已,原因也即在此。因此,“矫枉过正”,这曾倍受读者指责的一点,其实正是胡适扩张新诗传播空间的一种话语策略。
此举后来在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手中运用更进一步,他们嫌论敌反对不够激烈,不惜导演出“双簧”戏,连胡适都觉得有些太过了。可是鲁迅先生仍旧认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见“矫枉过正”的确是文学倡导者有意而为之的。
二 重述诗歌史——谋求新诗的合法地位
白话新诗以与传统古诗诀别的姿态出现,的确极具令人耳目一新的吸引力。但要以之取代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典诗歌,却似乎还缺乏一点说服力。因此,就像胡适在《新青年》4卷1号《答盛兆熊书》中谈到的那样,“文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如何取得新诗的合法地位是胡适等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们面临解决的重要问题。
通过重新阐释文学史来刷新文学观念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主要思路,而贯穿其文学史叙述的理论支撑则是进化论。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里,胡适开宗明义:“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从《文学改良刍议》起,胡适就开始用他进化的文学史观来阐释中国几千年诗歌的变迁:“文学者,随时代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由“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得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的结论。借古喻今,本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常见的主题。胡适通过用进化的观点来讲述诗歌历史,进而展望诗歌发展的未来,这样既迎合了大众的接受期待,同时巧妙地赐予了新诗出场的合法性。
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进一步用“进化观”具体讲述中国诗歌诗体的演变,为白话新诗诞生寻求依据:“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所谓“诗体的进化”,具体而言则是“诗体解放”、是“自然”。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穿篇章,便更自然了。……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为词。……这是三次解放。……直到近了了他的“进化观”,更重要的是依照新的文学史观,白话新诗作为“第四次诗体大解放”的里程碑式的文学形态,成功地进入新的文学史的叙述。
转贴于
进化论本属自然科学范畴,胡适把它引入的文学史的叙述虽不乏其合理之处,但若只是把进化的标准简单定义为“解放”、“自然”,便难免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以“历史的眼光”论诗歌时,胡适曾经谈到:“此如七言歌行……其起于律诗同时。(律诗起于六朝。谢灵运江淹之诗,皆为骈偶之体矣,则虽谓律诗先于七古可也)”众所周知,由古体诗到近体格律诗演变其实是从相对自由到不自由,若用“诗体解放”的标准衡量,这便不是进化而是倒退。歌行的形成早于律诗,这已自不待言。但这一文学史实并不符合胡适所言之诗体向着解放、自然进化的理论。所以他先说“七言……起于律诗同时”,接着又来了句模棱两可的“虽谓律诗先于七古可也”。到后来的《谈新诗》时,我们会发现从古诗到近体诗的演进一环,在胡适的叙述中干脆被省略掉了。其实早在1916年胡适谈到文学革命时就曾说:“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
同样是作为“文学革命”之必要性的论据,对古诗到律诗的转变的价值评估的改变真是意味深长。
同样用进化的文学观统领的还有他的《白话文学史》,它脱胎于胡适1921年在国语讲习所讲授的《国语文学史》讲稿。这是胡适系统地从文学史出发,为白话文学争得正统地位的开始。尽管后人指责他的所谓“白话文学”的标准定得过于宽泛、似是而非,但它的意义实不全在从学理上廓清白话文学的真正含义,而在于昌明“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为白话文学树碑立传的话语姿态。
除了重述古代诗歌史,胡适还大胆地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名曰“五十年来”的文学史,但主要是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回顾了自己在文学革命以来的主要观点,重在通过对新文学尤其是白话新诗的酝酿、产生、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最后得出“白话诗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的结论。
以新旧来论文学之高下,即使是在当时也存在着歧见,今天我们更能洞见进化论确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胡适也毫不讳言:“在那破坏的方面,我们当时采用的作战方法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明确指出这种文学观的提出是“一种作战的方法”。在他晚年的著作《胡适口述自传》中更进一步分析:“用历史法则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命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一种新观念加以解释,似乎是更具说服力。这种历史成分重于革命成分的解释对读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都比较更能接受,也更有说服的效力。”通过重述文学史来建立新的史学评价体系,从而为新文学谋取合法地位,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旧的推出新的,这是胡适等人从自发到自觉运用的卓具成效的一种话语策略。
三 “戏台内喝彩”——自建新的“阅读程式”
所谓“阅读程式”是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读者在长期的阅读中形成的一种用以理解和阐释文本的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程式。胡适尽管在理论上论证了新诗成立的合法性,但对于读者大众来说,新诗仍然是一种非常陌生的文学样式,处于大多数人审美经验之外,尚未形成有效的“阅读程式”。要使新诗建立起广泛的传播空间,必须建立并普及新诗的“阅读程式”。而新的“阅读程式”要在短时间里形成,不能被动等待读者的自发行为,它必须有赖于有意识的阅读上的导引。
“学衡”主将之一梅光迪曾撰文批评胡适等人:“今则标榜之风盛行,出一新书,必序辞累篇……”的确,胡适之著述立说便惟恐“不在世俗之知”,这一点比梅光迪所说到的也许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的《尝试集》一版再版,最先是请“我的朋友”钱玄同作序,钱先生在序中着重鼓吹白话。胡适则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对自己的新诗作品来了一次较为全面的盘点。尤其在他认为大有可为的音节问题上,通过对自己作品的总结分析,得出“‘白话诗’的音节”一说。此后,文学史家陈子展在《申报·文艺周刊》上发表《略论“胡适之体”》(1935年12月6日第6期),胡适又在《自由评论》上以《谈谈“胡适之体”的诗》(1936年2月第12期)作答,谈到“胡适之体”的标准是:“第一是清楚明白,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这样,不管他的诗是否果真如此,但至少标准是很清楚了。
这种自我宣传、自我鼓吹的行为,当然是自言“深恶标榜,文不苟作”的梅光迪等人所不屑为。但他们不知,胡适之不避沽名钓誉之嫌者,其实意在通过阅读引导来建立起新诗的“阅读程式”。而用自己的新诗做例证来加以说明,引导读者,显然是不二之选。
胡适的论敌章士钊曾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虽然语涉讥讽,却也从另一个侧面见得胡适早在1923年之前就已经通过《尝试集》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评论,确立了其新诗的统治地位,为较大范围内的读者成功地建立起新的“阅读程式”。
不仅如此,胡适还在各种其他谈新诗的理论文章中反复援引自己的作品,通过反复品评来进行自我宣传。在他不到一万字的《谈新诗》中,便不惜引用了自己的《应该》、《鸽子》、《老鸦》等三首白话诗来向世人昭示好诗的标准,指点新诗品读的门径。
就在这篇《谈新诗》的结尾中,他说:“我们徽州俗话说自己称赞自己的是‘戏台里喝彩’。我这篇谈新诗里常引我自己的诗做例,也不知犯了多少次‘戏台里喝彩’的毛病。现在再犯一次……”可见他的“戏台里喝彩”实在是有意为之,不但不怕遭人诟病,反而有怕别人不够明白他的用意而要反复加以阐明的倾向。
经典五言律诗篇10
宋人所谓“晚唐”,其时间范围基本指从咸通元年至唐亡;所谓“晚唐体”,本指唐末(咸通以后)诗歌的时代风格,体裁形式主要为七绝和五律,至宋末元初又特指贾岛姚合及永嘉四灵的五律诗。“晚唐体”的总体取径倾向是轻快有味,具体包括:重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擅长写景咏物,高者清深闲雅,下者清浅纤微。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晚唐体诗人师法广泛,尤重学习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晚唐体”阴影笼罩有宋诗坛三百年,许多宋人对于“晚唐诗”口头上痛砭,创作上模仿。
【关键词】 晚唐体/唐末/时代风格
一 问题的提出
“晚唐”、“晚唐诗”、“晚唐体”,是宋人提出来的诗学术语,它不仅与我们对唐诗史貌、唐诗分期及风格流派的认识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宋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喜谈唐诗,提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等术语,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晚唐”这一时段,最早提出的术语是“晚唐”,议论最多的也是“晚唐”而不是“盛唐”或其他,可见,有宋一代的文人们对“晚唐”确是情有独钟。厘清“晚唐体”的来龙去脉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唐宋诗史与诗学至关重要。
何谓“晚唐体”?其本真意涵所指为何种体格风貌?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可靠的结论。元代以后很少有人提及“晚唐体”,当今一些文学史著作或论文大都是在论述宋诗的时候谈到“晚唐体”,多将其归结为贾岛姚合诗风或宋代学习贾岛姚合诗风者的诗体①,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亦如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晚唐体”是指贾、姚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②,唯有赵昌平先生解释为“指唐季沿而至于宋初之轻纤诗风”③。这些概括孰是孰非,各自有多少根据?
由于贾、姚是典型的元和诗人,将贾、姚诗称为“晚唐体”,与现行的唐诗分期概念抵牾。于是,有学者就这样解释:“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④,“当时人所谓‘晚唐’是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例如贾岛)”⑤。问题是,这样概括宋人的观点,符合事实吗?为什么真正生活在晚唐的温、李、杜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却不属于“晚唐体”作家?有学者以贾岛、姚合皆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为由,正式在权威性《文学史》教材里将贾岛、姚合列在晚唐诗人中叙述(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譬如白居易去世比贾、姚还晚几年,刘禹锡亦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也可划入晚唐吗?
为揭开“晚唐体”的神秘面纱,本文首先厘清宋人所谓“晚唐”一语的时间意涵和“晚唐体”的艺术风格意涵及其指称流变,其次,正面研究唐代“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最后讨论“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二 宋人所谓“晚唐”——“晚唐体”的时间内涵
在“晚唐”一词没有出现之前,宋初已频繁使用“唐末”和“唐季”。而最早指明“唐季”时间范围的是王禹偁。其《画纪》云:“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指祭祖之礼)尽废。”又其《送孙何序》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可见王禹偁所批评的“唐季”指咸通后(860年以后),初步规范了后来晚唐的时间内涵。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先使用了“唐之晚年”一语: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
其所谓“唐之晚年”的时间意涵,我们可从所举诗人周朴得知,周朴是活动在唐末(咸通以后)的苦吟诗人,因骂黄巢为贼,被黄巢所杀。
欧阳修的门人刘攽(1023—1089)在其《中山诗话》中将欧阳修的“唐之晚年”缩简为“晚唐”,最早使用“晚唐”一语: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其“晚唐”的时间内涵与欧阳修所谓的“唐之晚年”一致,因其所举作家是皮日休,也是典型的唐末(咸通以后)诗人。其后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中有四处提到“晚唐”一词,所指均为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如其中较有名的一条言论先说杨大年竟不知道《比红儿诗》的作者是罗虬,紧接着来一通议论: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卷一四)
其所谓“以小诗著名”而又读书灭裂(粗糙)的,正是唐末乱世中像罗虬这样的一批诗人。
北宋蔡居厚《诗史》中有两条论晚唐诗,“晚唐诗尚切对”条曰: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儿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所举晚唐作家为郑棨,还有《梅花》诗的作者崔橹,皆典型的咸通以后诗人。又一条曰: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崔鲁……张林……
所谓“晚唐诗人”崔鲁(橹)、张林,也是唐末人。
蔡启《蔡宽夫诗话》中也有两条谈到“晚唐”。“晚唐诗格”条曰:
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
标题称“晚唐诗格”,内容称“唐末五代”,显然是将“晚唐”混同于“唐末五代”,可见在他意识中的“晚唐”是专指唐朝衰亡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蔡启首次将“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这条言论为南宋末期人将“晚唐体”等同于“贾姚体”埋下了伏笔。
北宋杨龟山论唐诗之“变”,首次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三期,合五代为四期:
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⑥ 杨龟山所谓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时段难以从文意上明确判断,但“晚唐”之不含“中唐”明矣。
南宋初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六评“晚唐诗”曰: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其所谓“尽取晚唐之作”,明指“自咸通而下”的所有诗作。可见“晚唐”一语的时间范围在计有功这里再次得到了确指。
宋人对“晚唐”议论最多的要数杨万里了。他所夸赞称许过的“晚唐诸子”,写专文(诗)褒扬的共有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崔道融、于、刘驾等七人,全是咸通以后人。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一条曰:“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薛能于广明元年黄巢乱中被人杀害,也属于咸通以后诗人。《容斋四笔》有一条曰:“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所言“晚唐士人”也是举吴融、徐寅、黄滔三个典型的唐末作家为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有“晚唐诗人”一条,所举作家为韩偓、司空图、罗隐三人,皆唐末名家。
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话相当明确地指明了“晚唐体”的时间范围: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故体成而唐祚亦尽。
所言“体成而唐祚亦尽”就明显地将时间范围定位在“唐末”。
南宋后期,谈论“晚唐”最多的是刘克庄(1187—1269),他首次把唐诗分成“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三体:
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然,亦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的这则重要材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他也是和杨龟山一样从诗“变”的角度来划分盛、中、晚三“体”的,他所谓的“晚唐体”主要是风格概念,但既与“中唐体”并列,可见在他这里也绝不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
与刘克庄同时而稍后的大诗论家严羽,批评“晚唐体”的言论也有不少,其时间界定渐趋淡化,风格意涵尤为突出,他的意见对元明清人影响颇大。《沧浪诗话·诗体》依时段先后将唐诗分为五体:“依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严羽没有像杨龟山、刘克庄、俞文豹那样标出“中唐”,但比他们分得更细。严羽在前四体及本朝体的每体下附有小字说明具体时段,惟独“晚唐体”未作解说,盖因“晚唐”时段在宋人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羽“依时而论”将“晚唐体”列于“元和体”之后,可见有的学者所谓“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等概括在严羽这里也行不通;其二,有人据此认为严羽的“晚唐体”的时段应是长庆以后至唐末,未免武断,因为根据其他各体下的小字说明可知,各体在时段上也不是直接相连的。何况他的“晚唐体”同时也是风格术语。
到了宋末元初,陈著、方回等人更多地将“晚唐体”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名称来使用。他们时常将贾岛姚合、南宋四灵甚至宋初九僧等人直截说成“晚唐”或“晚唐体”,可见,“晚唐”在方回那里时间界域已经完全淡化,成为泛风格术语。到杨士弘《唐音》,干脆从时间上明确地将“元和”列为晚唐,到明高棅《唐诗品汇》则又因袭杨士弘《唐音》之说,在《总叙》、《五古叙目》、《七古叙目》中都将“元和”归入晚唐(高氏有时也将“元和”划入中唐)。直到胡应麟和徐师曾以后才又将“元和”复归中唐。
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一条重要材料,常为学者征引来说明北宋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实际是讹传误引⑦。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的时间范围,由王禹偁、欧阳修和刘攽所开创确定,大体指所谓的“唐末”(咸通以后),到南宋末期,当“晚唐”普遍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含义使用时,又时常包括“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甚至包括宋初九僧以及南宋四灵。但在有宋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里,“晚唐”一词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唐朝末年的大约四五十年时间,约从懿宗咸通元年(860)直至唐亡(907),与今天所谓的“晚唐”代表作家活动的时代(晚唐前期)有所不同。今天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的代表作家,像杜牧(卒于852)、李商隐(卒于858)、张祜(卒于854)、许浑(卒于858)、赵嘏(卒于852)、温庭筠(卒于866)、段成式(卒于863)、刘得仁(卒于860)等,基本上都不在宋人所谓“晚唐”的范围之内。宋人所谓“晚唐”为什么多指懿宗咸通以后呢?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从唐祚兴衰上看,唐王朝真正不可收拾的衰世就是从懿宗咸通开始的,这一点史有明载;再从诗歌兴衰上看,懿宗咸通以后,杜、李、许、温等诗坛大家相继辞世,唐末最后五十年诗坛上没有大家出现,总体上似呈衰落之势,不过仍然名家辈出,创新不断,而整体诗风又与温、李、杜时期明显不同,可以称为“后三大家时代”,抑或皈依贾岛的时代。至于有宋一代文人为什么对于“晚唐”这个名词、这一时期如此热衷,对这一时代的诗人诗作诗风赋予这么大的关注和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晚唐”时间内涵息息相关的是宋人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严格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唐说”在宋代确未成熟。但是,宋人论诗每每提及“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术语,特别是杨龟山、刘克庄二人都明确提出过“三唐说”,可惜长期被人们忽视。如果再加上严羽的“唐初体”概念,那么“四唐说”在宋代也已粗具雏形。
三 “晚唐体”的艺术风格内涵及其指称流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
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著名的“晚唐异味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
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俞文豹对“晚唐体”描述更详,《吹剑录》(作于1243年)曰: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尽矣,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又《吹剑三录》曰:
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俞文豹第一段话批评“晚唐体”的一些缺点:气象衰飒,气弱格卑;题材狭窄,偏重描写景物和细小事物;注重音律对偶,篇幅短小;风格清浅。第二段话指出宋人模仿“晚唐体”较成功的,其特点为“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失败的,其特点是“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刘克庄诗。
其他称赞“晚唐体”的还有陈必复(1180—?)、徐鹿卿(1189—1252):
予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陈必复《山居存稿序》)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
徐鹿卿从“味”的角度为晚唐诗辩护,不仅强调“晚唐诗”有“味”,而且指出晚唐诗的“多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晚唐”诗坛风格流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著(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著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著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高潮。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艳情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16)《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相关文章
国学经典诵读在语文教学的应用 2022-10-14 08:50:10
语文教学渗透国学经典诵读的模式 2022-07-22 09:00:45
教科书经典古诗汉译英研究 2022-05-22 08:30:16
谈文学经典的另一种形式 2022-05-20 09:16:47
谈百年经典文学作品的动漫表达 2022-05-17 09:59:36
经典诵读陶冶学生情操及美育教育效果 2022-04-29 11:1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