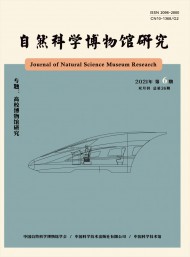自然科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16:38:3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14年度微生物学科资助面上类项目354项,金额1.8301亿元。其中,面上项目资助了143项,比去年有所减少,但资助率提高了9.01%,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85万元,比去年上升了约6.25%,经费12134万元;两年期小额探索项目资助7项,资助强度30万元,经费210万元;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65项,资助率比2013年度提高了4.05%,平均资助强度24.3万元,与2013年度基本持平,经费4012万元;地区科学基金资助39项,资助率提高了3.53%,平均资助强度50万元,经费1945万元。另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项,每项400万元,经费800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4项,每项100万元,经费400万元;重点项目6项,经费1952万元。“微生物代谢生理的系统与合成生物学成人员未签名或非本人亲笔签名;(4)中级职称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信,或者提供的同行推荐人身份不明,未注明单位或职称,或推荐人未签字。所以请申请者在以后的申请中要高度重视以上问题。今年,基金委继续对申请项目进行了相似度查询,包括申请项目与以往获得资助项目的相似度,申请项目与当年其它申请项目的相似度,申请项目与往年其他申请者申请过的项目的相似度。对于相似度高的项目,学部要求从严处理,对于相似度超过80%的项目,由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进行审查、核实和处理。研究”获得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经费600万元。另外,共有20个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获得资助,资助经费为1378万元。
2面上类项目创新性评价和资助结果统计
学科在对受理的项目进行分组的基础上,选择3位专家进行同行评议,对评议结果进行分析显示,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创新性评价为3A的比例占4.62%,较2013年度略有下降,但高于2012年度和2013年度(2012年3.53%;2013年5.49%);青年科学基金3A的比例为4.30%,比2012年度的2.63%和2013年度的1.99%都有较大上升;地区科学基金3A的比例仍低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建议资助为3A的比例占4.10%,与2013年度的4.42%基本持平,高于2012年度的3.06%;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为3A的由2012年度的2.30%和2013年度的2.76%上升至3.70%;地区科学基金3A比例都明显低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
3微生物学学科评审会前网络投票试点
为了提高同行评议后项目遴选的科学性、减少学科评审组专家的工作量、会务时间和评审压力,同时也是为了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基金评审程序和模式,2014年度,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会的统一安排,生命科学部一处在植物学和微生物学两个学科试行面上项目评审会前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果作为学科评审会的重要参考。科学处综合考虑了网络投票分组大小、指标设定、专家回避、信息保密、计票排序方式、投票平台、界面设计、专家时间等因素,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实施方案,在综合计划局、信息中心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逐步完善了网络投票方案并进行实施。在综合考虑研究方向和工作量等因素的基础上,学科将微生物学按分支学科分为4组进行投票。为了保证项目投票的合理性,学科按照专家的资助意见、创新性评价并考虑非共识、绩效、鼓励研究领域等因素,推荐了209个项目参与投票,推荐率为指标数的146%。每组选择13位专家进行投票,共有52位专家参与投票。每位专家平均审议投票的项目为50项左右。投票设置了各分支学科的最低和最高投票数,以保证每个分支学科的均衡发展。为了保证投票的科学公正,每个分支学科的投票均为差额投票,另外,所有投票专家都回避本单位和直系亲属的申请项目,做到了投票过程的完全回避。最后的投票结果按照同意率排序。学科按照网络投票的结果按序推荐建议资助项目,如果遇到赞成票比例相同而又难以做选择的项目,交由学科评审组讨论确定。在学科评审会上,赞成票达到2/3的项目不逐一讨论,专家如有疑问可提出讨论。第一轮投票前,只重点讨论赞成票在1/2到2/3之间的项目,第二轮投票前可以讨论所有的项目。对于创新性强的非共识项目,学科和学科评审组通过小额探索项目的形式进行了推荐和资助。从试行的情况看,网络投票可以大大缩短学科评审会的时间,也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专家的集体决策功能,但也存在由于专家需求量大而导致信息保密压力比较大的问题。学科对网络投票的做法征求网络投票专家和学科评审组专家的意见,81.55%的投票专家认为网络投票可以试行并完善后推广。
4面上类各分支学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微生物学学科涉及多个研究层次,各分支代码的申请和资助情况差异很大。在25个分支学科中,C010103、C010201、C010301、C010803等4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大,均超过100项,占总申请项目的43.71%;C010702、C010104、C010901、C010902、C010601等5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少,均少于15项,占总申请项目的3.16%(表4)。在申报项目多于10项的分支学科中,同行评议全同意比例较高的有:C010103真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的面上项目(35%),C010301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面上项目(37.33%)。在申报项目多于10项的分支学科中,全同意比例较低的有:C010101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面上项目(15.38%),C010101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青年项目(13.79%),C010501陆生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0.34%),C010502水生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0.00%),C010503其他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3.33%),C010602动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面上项目(9.09%),C010703人类病原真菌学青年项目(14.29%),C010802动物病毒学面上、青年项目(均为12.5%)。为扶持弱势学科,培养微生物分类学年轻人才,学科对从事微生物分类学研究的项目进行了倾斜。在平均资助率基础上,共倾斜资助项目17项,经费907万。其中,微生物分类学面上项目倾斜了7项,经费595万,平均资助率为54.5%;青年科学基金也倾斜了7项,经费168万,资助率为57.1%;地区科学基金倾斜了3项,经费144万,资助率为46.2%。同时,学科还对鼓励研究的领域如噬菌体(资助率31.6%)、支原体(资助率27.3%)、衣原体和立克次体(资助率36.4%)等进行了倾斜。
5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与2013年度相比,2014年度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从资助类型、数量以及金额上都有较大增加。资助金额由2013年的603.5万元,上升为1378万元,资助项目数量由10项上升为20项。其中,(1)组织间合作研究10项:NSFC-ISF(中以)4项,每项200万元,经费800万元;NSFC-NRF(中南)项目6项,每项80万元,经费480万元。(2)合作交流NSFC-RFBR(中俄)1项,经费9万元。(3)在华召开国际(地区)学术会议6项,每项5–8万元,经费39万元。(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3项,经费50万元。虽然国际合作的总资助经费有大幅提升,但是,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情况不理想,希望申请者在今后的申请中能够紧密围绕双方合作的领域选择合适的研究内容,突出双方互补的优势,体现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另外还要重视合作方案的的可行性。
6重点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的重点项目申请采取立项领域和自由申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公布的立项领域“人类重要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及致病机制”,受理了15项申请,经同行评议和学部评审会,最终“鼠疫菌致病性和传播性的遗传基础:质粒获得与基因调控重塑”项目获得资助。受理重点项目自由申请30项,最终资助5项,分别是“低温甲烷古菌对冷胁迫的转录后响应机制”、“从海洋疣孢菌属中勘探和挖掘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的小分子”、“放线菌全局性调控蛋白GlnR调控细胞代谢的分子机理”、“微生物合成聚羟基脂肪酸酯调控新机制研究”和“以活性(抗肿瘤和抗感染)与作用机制研究为导向的硫肽类抗生素的生物合成”。
7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4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数量较2013年有一定上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也有所增加,最终有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4人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由200万提高到了400万元。希望符合条件的年轻学者踊跃申请这两类项目,学科也将积极推荐,努力为申请者争取更多的机会。
8结束语
篇2
[关键词]地方文献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概念
[分类号]G255.9
地方文献是关于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地区长期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作为人类社会文献资源体系和国家战略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纵涉古今、横跨百科,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但作为个体地方文献而言,按其论述的学科内容,则分别属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各学科,如果将这些文献按学科门类划分,至少可分为社会科学地方文献、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三大类。
几十年来,我国关于地方文献的宏观研究一直停留在“整体地方文献”的层面上,在地方文献的实际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按学科进行地方文献的宏观分类研究至今无人涉足,特别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开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强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客观、正确地认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特殊价值与社会功能,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深发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1.1 自然科学概述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的起源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古代人类开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学便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成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现代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仅在宏观、低速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观、高速和宙观领域,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揭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认识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规律实际应用于人类的利益,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
现代自然科学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层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进。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的结构和物质运动的科学,担负着探索新领域、发现新元素、创造新化合物、发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务。基础科学是理论层次,包括数学、力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是将基础科学知识向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是研究技术理论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把认识自然的理论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综合科学都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如按基础科学的应用划分有应用数学、应用生物学等,按工程技术的通用理论划分有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等。应用科学研究的足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技术原理、结构、工艺等,如生物工程学、土壤改良学等。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现代科学既不断分化又广泛综合,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发展着的整体。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互补,表现为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与蓬勃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不断扩张,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献概述
地力。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文献认为,“地方文献古而有之,在文献出现之始即有地方文献产生……地方文献应该是人类社会所有文献的滥觞”。几千年来,地方文献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中,第一次对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及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论述。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献空间“区域性”的本质特征,而日,还表述了地方文献载体“多样性”和价值“史料性”的基本特点。按照杜定友先生当时的认识,地方文献包括的范围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文献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地方文献概念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其中以骆伟、邹华享为代表的学者将文献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为地方文献划分的唯一标准,即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这就将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内容与本地方无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之外,于是,这种“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方文献的“狭义概念”,与之相对应,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论则被称为地方文献的“广义概念”。换言之,狭义的地方文献专指内容与该地区有关的文献;广义的地方文献泛指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区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献领域“广义”和“狭义”两大学派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业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将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范围就太过庞杂了。因为任何文献都是由作者撰写或出版机构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机构都是有地域归属的,势必造成所有文献(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献,从而增加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难度,弱化了地方文献的应有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地方文献在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狭义”学派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并愈来愈被业界所认同和接受。
1999年,黄俊贵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献定义为“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一定义,既与国家标准关于“文献”的定义相协调,言简意赅、容易理解、便于记忆,又将地方文献内容的地域性和载体的多样性涵盖无遗,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地方文献的基本特征。应该说,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有关地方文献的定义。
1.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根据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结合自然科学的学科界定,笔者给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下这样的定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学知识的一切载体。其中,“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地域属性,指文献内容上带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学科范围限定,指文献记录的内容属自然科学知识;“一切载体”是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录和传播介质的概括,泛指文献载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凡以各种载体形态记录
和反映自然科学领域里内容与地域有关的所有文献信息均属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畴。
为了准确把握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要特征作进一步分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属地方文献范畴,同样具有地方文献的空间区域性、价值史料性、载体多样性和内容广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还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学属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载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与空间区域性共同构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最本质特征;②客观真实性,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更加注重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所记录的事实、数据一般是实地观察纪实或科学实验结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客观真实性;③实用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大都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土特产品、特有工艺和传统产业,记录了当地人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漫长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文献以其特有的客观真实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鉴及参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可以拿来即用,立竿见影,实用价值很高。
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
杜定友先生在谈及地方文献的范围时指出,地方文献由“史料、人物、出版”三个部分组成。时隔30年后,骆伟教授再度论述地方文献的范围时,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两者字面表现上颇为相近,由此,业界有不少人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观点一致,均为“广义”论者。其实,两位先生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杜的“史料: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骆的“区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区域内所存在、发生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位所指基本同义,这也是“广义”和“狭义”论者没有争议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关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劳模、烈士以及对于本地方建设有关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贤),他们的照片、著作、手迹、传记、纪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骆的“区域人物……对表述他们一生的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无疑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因此,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会活动等,都属于地方文献……至于地区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献?我认为应以是否反映该地区的事物作为划分的标准”,显然,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仅限于反映该地区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这正是“广义”和“狭义”沦者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三,杜的“出版:从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况、思想内容、制作方向,对本地方刻的古书,更应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骆的“区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对地可分为三类:①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②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③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我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不难看出,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区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则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地方出版物,这又是“广义”和“狭义”论者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以上分析可知,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范围有着很大的分歧,如果将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广义”学派的倡导者的话,那么骆伟教授则应是“狭义”学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驱。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样,同为“广义”论者,是对骆伟教授关于地方文献学术思想的莫大误解。
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显然要比地方文献的范围小。首先,记录和论述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在内;其次,上义述及的地方文献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区域人物”)和“出版”(或“区域出版物”)两部分内容也不必单列出来分析。因为:“地方人物评介”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部分,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论及的内容,因此,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只有自然科学的“地方史料”一项内容。那么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该如何认识呢?拙文拟从下列几个角度多方位进行分析。
2.1 从学科内容看
自然科学含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部分。基础理论科学一般是通用理论,含各种原理、定理、定义、公式、自然规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献不属于地方文献;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与通用技术部分也同样不属于地方文献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些与地区密切相关的特有技术、特有工艺、特有自然现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等的记录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包括:关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原始记录,关于本地区的旱涝灾害、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及其人们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项活动等自然事件的真实记录,关于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变化、医药卫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变迁的动态记录等。总之,凡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实地记录了本地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历程,对后人有借鉴、启迪作用的科技文献均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
2.2 从文献类型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有科技图书(含科技类方志、年鉴、手册、百科全书、学术专著等)、科技期刊和报纸、科技报告、科技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技术标准与规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产品样本和说明书、技术档案、自然资源和自然地理图谱、文物科技资料、科研手稿、笔记、信札等内容。其中,各类文献中既有公开出版发行的“白色文献”,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如内部书刊、政府出版物、会议资料、技术档案、手稿、笔记、信札等,这部分文献专指性、地域性强,动态性、时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价值高,倍受学术界青睐,理应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收藏重点。
2.3 从载体形态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既包括传统的原始材料载体,如甲骨、皮革、金石、简牍等,纸质材料载体,如印刷品、手抄本、复印件等,也包括现代的磁性材料、影视传媒、网络媒体等载体;既有各种静态性实体文献如:实物型、印刷型、机读型、声像型等,也有通过现代网络传播的动态性虚拟文献如:网上数据库、网络科技信息、多媒体资料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文献机构由于多少年来习惯于纸质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对新兴的影视传媒及网络媒体文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影视和网络传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会影响力广、传播超越时空等优势,已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2.4 从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依年代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献。各时代文献的时代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发展演进,其关系处于一种交互变化的状态。今日的古、近代文献是昔日的当代文献,今日的现、当代文献又是未来的古代文献,是未来研究今天的宝贵资料。历史的经验证明,即时性地收集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力度愈大,未来地方文献的体系就愈强,其作用与价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史料性”特征,不单单体现在古代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变迁的、包括现、当代文献在内的整体文献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价值
地方文献历来就有“存史、资政、励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献将其归纳为“服务政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振兴地方经济、深化科学研究、弘扬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十大社会功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以其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数据客观精确、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等特点,对地区生产、科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建设的重要基础资料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受到该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全面记录了有关本地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科研成果以及工农业生产发展变化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量基础资料和统计数据,凝结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是区域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系统史料来源和决策依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科学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在综合研究多年气候、生态、地质、地理环境等资料后,制定出冻土挖方段、风沙地段、长江源头区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设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设置动物通道与动物信息系统中转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的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东枣庄市齐村区北庆乡过去生长一种能“咬人”的怪树,被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1981年,当地政府从地方文献中得知这是当地自古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经过精心培育,现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大量事实证明,领导机关在借鉴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提供的基础资料和经验教训规划本地区总体建设与经济发展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造福乡里;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脱贫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产生和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的一门科学”。由于不同学科的地方文献其产生、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按学科进行的地方文献分类研究,必将成为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任何忽视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都将严重制约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作为地方文献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共同构成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学科,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各项业务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推动地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设想,随着地方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必将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3.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从地方文献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同属于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记录事实、数据客观精确,提供方法、措施科学适用,使用价值更高。
篇3
当前,课堂教学设计的改革仍然是教学改革的关键。如何促进课堂教学结构各个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促进小学生认知心理和智力的和谐统一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对课堂教学设计进行探索和研究。
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是将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其发挥最佳的教学效果。各个要素间相互联系形成系统的教学结构,不同的课堂设计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小学自然教学活动中,运用“教师、媒体、学生”三维双向反馈构成的信息交换系统促进课堂教学的优化组合,这一系统反映了主导、信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课堂教学设计必须考虑教师的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学媒体的选用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以《金属》一课的教学设计为例,谈谈小学自然课堂教学设计。
一、教师的教学活动设计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教师要避免单纯地靠一本教科书来灌输知识,必须把它转化为利用投影、实物、标本等多种教学媒体启发、引导学生掌握知识。通过教师的引导、主持、评价来激励和指导学生学习,完成教学任务。
1、指导观察,分组实验。教师首先要展示四幅反映实验内容的图片,指导学生仔细观察,然后让学生进行分组实验,寻找铜、铁、铝的四个共同特征,激起学生的求知欲。
2、启发引导,设计实验。教师要善于借助实验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根据已经掌握的第一组实验方法自行设计第二组实验,研究木棍、粉笔、瓦片与铜、铁、铝不属于同一类物体。这样,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开动脑筋,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
3、组织讨论,归纳总结。在学生已经完成两组实验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金属有哪些共同特征。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各实验小组讨论完毕之后,教师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出金属的共同特征。
4、强化记忆,扩散思维。为了进一步掌握金属的共同特征,教师运用了投影与实物相结合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从多种物体中辨别金属,既做到了新授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同时,也扩散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得到了提高。
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主要是通过指导学生分组实验、激发学习兴趣、启发设计实验、组织观察讨论、归纳概括总结、强化记忆、扩散思维等活动中完成。
二、学生的学习活动设计
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在自然课的教学活动中,应该通过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多动口、亲自动手参与做实验的活动,使学生更加热爱大自然,喜欢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分析、探索、研究,学会进行科学试验的本领,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成为真正的主体。
1、观察思考,分组实验。学生对教师展示的四幅反映实验内容的图片进行认真细致地观察,并大胆地进行实验。
2、自行设计实验过程。学生由第一组实验获取的知识联想与第二组实验之间的关系,然后各实验小组展开讨论,自行设计实验过程进行实验,汇报实验结果。
3、小组讨论,大胆发言,由于学生在获取两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掌握了知识,有话可说,就会踊跃回答教师提出的各种问题,主动参与实验小组的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形成一个课堂教学。
4、运用概念辩别金属。众所周知,教学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熟练掌握知识,在自然课《金属》中,教学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学生学会识别金属,由于教学活动组织得充分,学生掌握了金属的特性、共性,根据金属的共性、特色,学生能够很快从多种常见的物体中辨别出金属,并说出辨别的方法,教学目的实现就成为一种可能。
5、阅读教材,提出质疑。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认真阅读教材,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质疑,并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掌握新授知识,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学活动中主要是通过阅读教材、提出质疑、分组实验、观察思考、设计实验、小组讨论、大胆发言、辨别金属等活动中完成。
三、教学媒体选用的设计
教学媒体是传递教学信息的载体。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经常要用语言、板书、挂图、模型、实物以及幻灯、投影、录音、录像等来传递教学信息,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教学媒体,具有生动、形象、感染力强等特点,适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合理的采用媒体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又可以开扩学生的视野,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能够极大地提高感知效果,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
篇4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篇5
小学自然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自然教学要培养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即小学生学习、应用自然科学知识解决身边的一些实际问题时必备的能力。它主要包括初步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动手能力等。有意识地培养小学生这些能力,有利于开发他们的智力,启迪创造思维,为他们今后进一步学习科学、研究科学、从事各种科技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心理学原理表明,思维能力是人的认识能力(即智力)的核心,而抽象概括能力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以第七册《金属》一课为例,谈谈学生抽象概括能力的培养。
一、指导学生认真观察和实验,为科学抽象打好基础。
观察和实验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基本途径,也是自然教学的基本特点。通过观察、实验等实践活动,可以为抽象和概括准备大量的感性材料,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教学中,教师应尽可能创造条件,认真准备好与新授知识有关的“有结构”的材料,指导学生去认真观察或实验,去探索它、研究它,帮助学生获得对被探究事物的感性认识,初步形成对该事物的了解,以便于在教师的启发下进一步通过头脑的加工、语言的交流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相应的科学概念。
在《金属》一课教学中,为了组织好学生在课堂上的探究活动,师生共同准备好用于观察和实验的各种材料。除教师准备好教学中所需的实验器材,如铝勺、铜钥匙、铁钉、烧杯、电池、导线、灯泡等外,还应指导学生自己收集并准备一些易于获得的材料,如稍粗一些的铁丝、铝丝、铜丝,香烟盒里的铝箔,可用于捶打的卵石等。教学时,应有顺序地组织好学生分组实验,引导他们去探究金属的共同性质。1.组织学生观察三种金属时,要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并给予必要的提示,让他们用砂纸把金属表面打磨一下后寻找出这些金属外表的相同点。这样做既可达到观察的目的,也能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2.教材中的三个实验和“试一试”实验要让学生人人动手操作,以增强他们对金属的感性认识。对学生不便准备的传热实验,教师也应该在演示该实验时尽可能让学生摸一摸没有浸在热水里的物体的一端,使他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铜、铁、铝都能传热。3.最好把教材中的“试一试”分散在一个观察和三个实验中去分别完成,形成对比实验。这样有利于突出铜、铁、铝的共同性质,加深学生对这些金属的感性认识。4.学生实验时,要提示他们注意观察实验现象,以便于告诉老师“看到了什么,通过实验或观察,知道了什么?”
二、精心组织研讨,引导学生思维,逐步培养他们的抽象概括能力。
在完成观察和实验探究活动之后,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开展研讨,即引导他们把在探究活动中所获得的感性认识和想要说出来的话通过课堂讨论、互相交流等形式起到相互启发的作用,从而找出被研究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的属性并加以概括,使感性认识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一定层次上的科学概念。由此可见,组织学生研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展学生思维,培养他们的抽象概括能力的过程。
如《金属》一课:1.抽象金属的共性。在每一组观察或实验结束后,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讨论前教师必须向学生提出讨论题,以引导他们进行抽象思维,鼓励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尽量交流自己的观察所得和想说的话。讨论题是:你在观察铜、铁、铝等物质的外表中看到了什么?铜、铁、铝的外表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木棍、玻璃棒、粉笔呢?通过传热、导电实验,你看到了什么?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从金属延展性实验发现,把铜丝、铁丝、铝丝弯折或捶打后有什么变化?把木棍、玻璃棒、粉笔弯折或捶打后会怎样?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课堂讨论可采取小组形式,即前后相邻4个学生为一组互相交流、讨论,然后引导学生在全班范围内作交流发言,讲明他们对三种金属的共同特性的认识。通过讨论,教师在肯定学生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填写本课中的前四处空白。2.概括金属的共同性质。通过上面的研讨活动,再对金属的共性进行概括。概括时仍应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加以完成。具体过程是:(1)讨论:根据上面的观察和实验,我们可以知道铜、铁、铝有哪些共同的性质?引导学生对铜、铁、铝的共性进行概括。(2)教师告诉学生:由于铜、铁、铝有共同的性质,它们是同一类物体,叫做金属。金属表面所特有的光泽称为“金属光泽”。金属的种类很多,如金戒指(金)、焊锡、干电池的金属壳(锌),电灯泡里面的钨丝等与铜、铁、铝一样,都是金属。(3)引导学生进一步讨论:根据铜、铁、铝的相同性质,可以推想出金属的共同性质是什么?进而完成更高层次的概括。(4)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是金属”,并强调只有同时具有以上四个性质的材料才是金属。这样作好进一步抽象,建立金属初步的科学概念。
篇6
>> 机器人领域的“愚公” 日本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反思 机器人替代对中国制造的意义 对中国机器人发展走向的认识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分析 机器人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对跳跃机器人研发的分析 对矿难救援机器人的研究及应用现状 对工业机器人抓取技术的研究 对机器人教学导入策略的研究 机器人避障的原理及分析 救灾机器人的研究现状、应用及发展 工业机器人的研究状况及趋势 城轨站内导盲机器人的研究分析 并联机器人研究领域的先行者 人工智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中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飞跃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博弈” 机器人投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智能控制及其在机器人领域的应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15-05-08.
[5] 孟浩, 周立, 何建坤.自然科学基金投入与科技论文产出的协整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07, 25(6):1147-1150.
[6] 郭红, 潘云涛, 马峥,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产出论文计量分析[J]. 科技导报, 2011,29(27):61-66.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结题项目统计――按成果类型[EB/OL]. http:///default.htm, 2016-09-01.
[8] 王伟.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J].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2005(6):44-45.
[9] 姜春林, 王续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产出管理学论文的计量分析[J]. 情报科学, 2005,23(9):1345-1348.
[10]王冬梅. 科学基金制度对基础科研合作的引导效用分析[J]. 科研管理, 2010, 31(4):98-101.
[11]张宜平.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基金资助研究[J]. 现代情报, 2005, 25(3):34-36.
[12]张诗乐, 盖双双, 刘雪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效果――基于论文产出的文献计量学评价[J].科学学研究,2015, 33(4):507-515.
[13]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14]Hirsch J E. 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5, 102(46):16569-16572.
[15]w基明, 邱均平, 黄凯,等. 一种新的科学计量指标――h指数及其应用述评[J]. 中国科学基金, 2008, 22(1):23-32.
Analysis on Basic Research on Robot Projects Fun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Funding Effect
CHEN Yue,WANG Zhiqi,TAN Jiangu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nstration and Law, WISE Lab,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Liaoning, China)
篇7
西部地区科技期刊办刊存在的问题
西部地区科技期刊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短板,受到约稿难、关注度小等问题的困扰.西部地区科技期刊的发展离不开期刊主管部门的支持,新疆师范类高校科技期刊的发展也是刚刚起步,高校教师大多以学校科研激励为目标,对西部地区科技期刊投稿热情不大,针对全国科技知名专家的约稿更是困难,而自然科学论文科研时间长,编辑约稿往往需要更长时间[11~13].西部地区大部分科技期刊办刊思路就是简单地编辑加工稿件[14~15],等稿发表.科技期刊栏目设置以高校学科为基础,来稿以本校教师为主,编辑人员主动约稿意识不够.随着西部地区高校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科技期刊应转变办刊理念,借鉴内地高校科技期刊成功办刊经验,主动策划,科学设置栏目,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与专家学者交往,通过他们约高质量高水平的稿件.高校科技期刊的栏目设置多以高校自然科学学科为基础设置,如新疆师范大学科技期刊(自然科学版学报)系综合性刊物,自然科学学科包括数学、物理、计算机、生物、化学、地理、旅游、环境、体育等学科,发展不平衡,科技期刊刊发文章反映出学校优势学科为数学、地理、体育三个学科,但其他学科稿件少.科技期刊应该立足学校优势学科设立重点栏目,打造品牌栏目[16].西部地区高校科技期刊编辑人员较少,如新疆师范大学、伊犁师范学院等院校的科技期刊专职编辑较少,且编辑人员岗位流动性大,而科技期刊编辑的培养需要较长的时间,尤其是科技期刊编辑大多需要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才能较好地胜任工作.因此,科技期刊需要不断培训工作人员,为科技期刊提高质量奠定基础.科技期刊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因子,办刊通过特色栏目来提高知名度,通过栏目主持人扩大约稿范围.西部地区科技期刊应注重与各大期刊数据库保持联系,加强西部地区科技期刊的推荐,使内地学者了解我们西部地区科技期刊的办刊思路,栏目特色,逐步提高科技期刊的知名度[17].
西部地区科技期刊办刊策略
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依据《新疆师范大学2011~2015年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精神[18],栏目设置要服务于新疆师范大学“十二五”战略重点,主要刊发新能源新材料研究、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网络信息安全与信息技术应用等方向的学术论文;另外,还要大力支持干旱区湖泊环境演变实验室、新疆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学实验室、新疆多民族体质健康与评价实验室等的发展.西部地区科技期刊调整自身办刊定位,转变编辑办刊理念,向内地科技期刊学习,发动本校各学科知名专家加强对西部科技期刊的支持,与他们多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多约稿,通过学校专家向外辐射,将约稿范围扩大到疆内外其他高校,争取更多的优质稿件能在西部科技期刊上发表.对重点栏目实行约稿,力争每期都有1~2篇约稿,稿件要结合新疆自治区党委提出的现代文化引领,科技、教育支撑,工业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战略,解决新疆大发展理论及实践问题.根据“十二五”战略重点、重点实验室和优先发展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不定期组成专题研究,如:环境与资源研究、新疆多民族体质健康研究和理论物理研究等栏目.及时报道相关重点实验室和优先发展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动态,其他学科根据每期栏目稿件具体数量,对不同栏目进行一定的调整或合并[19].加强西部地区科技期刊管理,规范稿件审稿制度,实行匿名审稿,严把稿件质量关.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每年出版四期,每期约25篇论文,论文约稿和基金稿件数量占40%以上,刊物页码压缩至108页,封面重新设计,内页重新设计要美观大方,保证刊物出版质量,切实作好编辑各项工作.积极发挥编委会力量,通过编委与校内知名专家多联系,通过校内专家向校外辐射约稿范围,加强与内地科技期刊的联系,促进期刊影响因子的提高,切实提高办刊质量.西部地区科技期刊还应多借鉴内地高校的办刊经验,积极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与专家学者交往,通过他们约高质量的稿件.
本文作者:刘会强周春丽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篇8
一、科学性论文的这一特点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的。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揭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探求客观真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文明的阶段发展。因此,学术论文是以科学性为前提的,这一精神贯穿着论文写作的始终。首先,论文的论点和结论必须科学。它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论点绝对不能主观臆造,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和偏见。其次,论文的论证和论据必须科学。学术论文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观察、调查、实验等,并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对立论进行严密而富有逻辑性的科学论证。所引用的论据无论是实地调查来的,还是实验中来的,或是文献中摘引来的,都要求真实、典型,真正成为论点的支柱。再次,论文的论述必须科学。措辞严谨,概念准确,条理清楚,结构完整,才能体现正确的认识过程,令人信服地传达科学的学术见解。论文的科学性要求写作者从探求科学真理的目标出发,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形诸文字,加以科学的表述。
二、学术性论文反映的是某专业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起一定的推动作用。论文的价值即体现在学术性上,而论文的学术性又突出地体现在专业性上。学术是有系统、较专门的学问,它往往以学科的形式表现出来。学科门类繁多,各学科之间虽然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但差别是主要的,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有自己专业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术语,形成了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比如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需要研究和解释的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和现象,那就必须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而管理学方面的问题,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工具、表述方式则必须符合管理学的学科要求。人们通常将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两类之下又可逐层划分下去。分工越细,学问也就越专门化。论文要研究和阐述的就是这些专业知识中的某一个问题。因此,只有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本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基本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从而进行学术研究。论文所论述的内容,使用的语言都必须与所论述的学科密切相关,这是论文的显著特点。
三、独创性论文不仅要进行专业化的学术研究,而且还要报告自己独到的研究成果。创造是科学的本质,独创性是论文的生命。是否有创见,是衡量学术论文价值高低的标准。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它不能重复已有的知识,甚至也不同于一些学术专著。有些学术专著主要用于专业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因而比较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常规性,但论文绝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创造性地解决某一专业领域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创造能力可以有大小,创造水平可以有高低。大到能够开创一门新学科、创立一个新学派,小到发现一条有价值的资料,但无论对于哪个层次的研究者而言,独创性这一点都必须是研究者从发现问题开始,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到撰写论文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不懈的追求。具体说来,独创性可以体现在研究和探索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可以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观点;可以综合前人的研究,揭示今后研究的方向;可以为前人的立论提供新的事实材料或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等等,不一而足。
四、理论性学术论文不能停留于事实、现象的罗列,必须探究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写论文必须运用理论思维,通过对事实的抽象、概括、说理、辨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将一般现象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论文的基本框架是逻辑的,是以中心论点为核心,以分论点为支柱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其中充满了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主要与次要、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等事理关系。很多作者的论文水平不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论文缺乏理论性。没有理论支持的论文,只能囿于事实材料的堆积,不能从一般的现象中看到问题的本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论文的理论性是作者的学识水平、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综合反映。
篇9
一、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又称科研性论文,是表述科学研究成果、论证科学观点、探讨学术价值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是学术交流的工具。在系统地研究问题时,人们必须把思考的进展和结论记录下来,以便进一步深入推敲。使思考更为准确、缜密,更切合客观地深入推敲。所以,学术论文始终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获得研究成果以后,需要进行交流和推广,这就更必须用论文的形式将它完整地描述出来,使成果变成定型的文字系统,即使成果借助语言文字载体成为他人可以实际领会、可以做到准确把握的信息。所以说,“写学术论文”是传递成果必不可少的工具。随着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向前发展,学术领域的研究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的成果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学术论文可分为两大类:社会科学论文类和自然科学论文类。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
二、毕业论文写作概述
1.毕业论文的含义。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在毕业时,运用在学校学到的本专业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在教师的指导下试着独立地去进行某一项专业问题的科学研究而写出的论文。
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情况的综合性考察,而且是重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研究能力,是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必须完成的独立作业,是大学生学习阶段学习成果的总结,也是高等院校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暂行实施办法》等文件的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予以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性工作的初步能力,授予学士学位。事实上,大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已成为大学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一定要认真地完成。 大学生毕业后要求能写“文从字顺”的学术论文,有本科生撰写学士论文、硕士研究生撰写硕士论文、博士研究生撰写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生撰写专业性的毕业专著。
2.毕业论文的特点。①科学性。毕业论文必须对所研究的选题提供本质性、规律性的发现,通过充实有力的科研材料,周密严谨的论证过程,揭示事物的本质特点,展示出选题的价值和见解。对研究的学科应从理论高度的领域中对某一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观察、考证、分析、研究、演绎、归纳,从而提出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获得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并对自己的见解与成果作理论性的阐述和剖析,最终达到实用的目的。②创见性。创见性是科学研究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显著的标志。没有创见性的“研究”,不能算作科学研究,甚至不能称作研究。因此,选题是否有创造和独到的见解,是衡量研究成果价值高低的重要尺度。大学毕业生的论文基本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达到解决某一选题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创造和见解,大学生毕业文选题的创见性主要表现为不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模仿抄袭、老调重弹,应该表现在力求言别人未言的独到性,退而求其次,至少应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冲击力,自身对问题的认识与见解,看法与主张,与众不同,显示出论文的新颖性。③平易性。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应写得深入浅出,让人爱读,让大多数人都看得懂、读得懂,发挥选题科研的作用。因此,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应该追求“平易性”,显示出毕业论文的“平易性”风格。毕业论文切忌装腔作势;新名词大轰炸,故弄玄虚,这是论文的致命伤,这是玩弄论文的学术性的把戏。这里必须说明,在任何文体的写作中,必须讲究文风,毕业论文尤其应该防止想当然,平易不等于粗糙或不准确,也不是说必须使用的术语都不可使用,但使用的这些术语,应该是必要的,能为表现论文的选题服务。可以这样说:“平易性能够使科学性与创见性获得最大面积的公认和普及,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篇10
关键词:图书馆 下载频次 被引次数 论文质量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4-0100-004
Considering the Library Service in Another Point of View: Evaluating the Paper's Value and User's Interests from Number of Its Internet Downloads
Yang ChunhuaWang GuizhiMa Hongyue(The Medical Libra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Beijing,100039)
Abstract:We have analyzed the top papers by download and citations published between 2000 and 2009 by librarians. It was found that library academic-oriented papers got much more citations and user service- oriented papers got high number of their Internet download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Download and citations. Analysis of this comparison suggests that download frequency can reveal not only the paper's application value- its contributions to users, but also information of which papers are most interesting to the readers. So it should be an alternative metrics of paper quality and impact. User service- oriented study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the library.
Key words:library; download frequency; citations; paper quality and impact
CLC number:G25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4-0100-004
1 论文下载频次的意义
长期以来,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都以引文索引(SSCI,SCI)作为研究论文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评价依据,[1]然而单纯基于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并不能完整地评价一项研究的价值。[2]随着学术资源的数字化,电子版期刊成为科学论文传播的越来越重要的途径,下载次数监测有望成为一个新的基于利用的考量科学论文传播和影响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和指标。[3][4]
世界最大出版集团之一的ScienceDirect,从2004年7月起,每个季度都免费提供其数据库中下载量最高的25篇科学论文排名(TOP 25 Hottest Articles),作为读者论文使用行为的一种反映;当前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认为,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具有显著的相关性,[5][6 ]一定时期内下载量大的论文,较长时期内可以获得更多的引用,因而可从internet下载量预测研究论文的未来的被引频次。[7][8]
对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杂志2007年25篇下载量最高的论文和25篇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比较结果发现,用户阅读行为和最新论文引用之间的标准非常不同,对目前用文献被引次数作为决定或影响论文质量的评价标准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9]因为作者引用的文献往往仅占其在研究工作中所阅读过的文献的一部分,而对其中未被引用的文献的实质使用行为没有反映,从而造成被引次数对阅读但未引用文献学术价值反映的缺失。而文献下载次数在直观上能够与该文献的被阅读次数相对应,不失为一种反映文献价值的途径。[10 ][11][12]
我们发现,与其他学科相比,图书馆工作者的论文具有其特殊性:除与同行的学术探讨外,还有基于服务职能、面向广大服务对象的指导性论文,其论文读者不单单是同行。
那么,图书馆论文的价值如何客观评价?下载量分析能否作为评价图书馆论文的一个指标?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用户需求?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2 图书馆学专业论文下载与引用间的关系
因为网络数据库中的数据变化很快,我们的检索截止至2009年11月。CNKI2000~2009年收录的图书馆作者发表的论文,对第一作者单位为图书馆的论文分析他引次数(排除自引,以下同)居前的23篇论文。结果见表1。2.1 对2000~2009年图书馆学高被引论文的分析
这组论文篇均被引用146次,篇均下载221次,下载次数是被引次数的1.5倍。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都是面向同行的学术探讨,读者对象基本相同,其中91.3%发表于专业核心期刊。
2.2 2000~2009年图书馆学高下载量论文排名
获得高下载量的这组论文,篇均被引11.2次,平均下载1025次,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论文仅占5/23=21.7%。面向服务对象的论文占了绝大部分(15/23=65.2%)。
篇均下载1025次,远高于表1中高被引论文的篇下载量(1025:221),篇均被引11.2次,远低于高被引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11.2:146),这组论文中,下载量最高、达到2017次的文章,是“如何在网上进行课题检索”,而该文被引次数为0。我们认为,在2001年网络信息检索刚刚开始普及时,该文的实用性和指导性以及庞大的潜在读者群,是其获得高下载次数的主要原因。
从论文内容看,获得高下载量的23篇论文中,综述7篇,数据库检索应用或技术指导类论文12篇,二者占到了全部文献的19/23=82.6%,其他论文4篇,占17.4%。
从长期看,这组论文也不会获得高的被引次数。这些论文多是对服务对象的信息检索与应用指导,体现了图书馆最基本的服务宗旨,而不是面向本专业同行的学术探讨,应用价值远高于学术价值。
两组数据间没有重叠,且均显示了与国外文献计量学研究不同的结论,即下载量与被引频次间并无相关性,被引频次高的论文并未获得高的下载量,下载量高的论文没有获得高的被引次数(见图1)。
(三)同年发表的论文被引与下载趋势分析
为证实上述结论,我们还对2001年、2005年图书馆工作者发表的论文进行了同年文献的被引与下载量分析(结果见图2、图3)。
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占10/23=43.5%。
对同年发表的高下载量论文的分析,亦未见被引次数与下载次数间具有相关性。
3 结论
(1)我们发现,图书馆学论文的被引次数与下载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一些被引次数高的论文,并没有获得高的下载量;而下载量高的论文,被引频次往往很低。
(2)科研人员下载文献,首先要判断文献是否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关,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然后才会下载。因此,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下载量高的论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满足读者需求,揭示了服务方向,发挥了其社会影响力,应该作为评价论文应用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3)图书馆工作者的论文,因为要面向两类读者:相对少量的同行和广大的用户,面向同行的论文注重学术性,因而容易获得引用,而面向图书馆用户的论文,更注重实用性,容易获得高的下载量。因此,对图书馆论文而言,不能根据下载量预测今后的引文数量。
4 结语
1975年国际图联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图书馆职能科学讨论会上所确认的图书馆社会职能就包括了:①开展社会教育,即成为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基地,担负更多的教育职能;②传递科学情报;③开发智力资源,即图书馆承担有人才培养的职能。[13 ]分析表明,那些被下载次数多而引用极少的文献,恰恰很好地满足了用户的这些实际需求,履行了上述职能。图书馆论文被引频次与下载量的偏离也就不足为怪。
4.1 下载或被引与不同的读者群有关
图书馆工作者发表的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图书馆的业务探讨,优秀的论文获得了较高的被引次数,但图书馆专业读者基数很小,所以那些被引次数相对较高的学术论文,获得的下载量却不高;二是面向用户读者群,围绕提高用户信息素养,如检索技能、方法的介绍、指南,旨在帮助用户提高技能,获得更为深入的专业文献,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因而获得了较高的用户关注和下载频次,但这类论文与读者的专业基本不相关,所以极少被引用。
4.2 论文下载量揭示用户需求,体现论文的应用价值
研究认为,下载排名反映了读者的选择偏好。[14]一般而言,读者决定下载是在阅读全文之前,只是通过题目、文摘、作者和关键词来判断的,因此阅读决定无关论文全文的质量,但下载排序却是读者兴趣的一个标识。下载次数高的论文内容,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用户的需求,图书馆科研与服务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论文下载次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论文对于用户的贡献大小,[15]这些下载量很高的图书馆论文,虽很少会被读者引用,但发挥了它的影响,体现了它的价值,对用户参考价值高,因此应该得到认可。高质量满足用户的这种需求应成为图书馆服务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4.3 下载量分析应该受到重视
本研究统计表明,我国被引次数居前的图书馆学论文,90%以上都发表于核心期刊;而下载量居前的面向服务对象(即用户)的图书馆学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不足50%,甚至更低,可见体现图书馆服务理念、满足用户需求的这些下载量高的论文并未被专业主流期刊认同。
Web 2.0时代,专业图书馆的工作中心和导向,应该时刻以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以新的标准考量论文价值,认可那些为用户所需,具有很高应用价值但不一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应顺应读者需求,鼓励这些服务导向的研究,拓展服务范围和水准,提升图书馆的价值。
参考文献:
[1][5]Dan O'Lea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ations and appearances on “top 25” download li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2008,(9):61-75.
[2][6]Johan Bollen , Herbert Van de Sompel, Joan A. Smith et al.Toward alternative metrics of journal impact: A comparison of download and citation data[J].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2005,(6):1419-1440.
[3]Daniel E. O'Lear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ations and number of downloads i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8,45(4):972-980
[4][14]Editorial. Which papers are most interesting to the readers of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J] .Information from download monitoring.Cardiovascular Research,2005,65(1):5.
[7] Jahandideh S, Abdolmaleki P, Asadabadi EB. Prediction of future citations of a research paper from number of its internet downloads[J]. Med Hypotheses, 2007,(69):458-459.
[8]Christos Zavos, Jannis Kountouras, Nikolaos Zavos, et al.Predicting future citations of a research paper from number of its Internet downloads: The Medical Hypotheses case[J].Medical Hypotheses, 2008,70(2):460-461.
[9][10]Andrew J.S. Coats. The top papers by download and cit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in 2007[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2008,(1):1-3.
[11] CoatsAJ. Top of the charts: download versus cit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J]. Int J Cardiol,2005,105(2):123-125.
[12]郭强等.科技论文下载次数的统计性质研究[J].情报科学,2009,27(5):690-694.
[13][EB/OL].[2009-12-27]./zhinan/tsgzy.php.
免责声明
公务员之家所有资料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写作和网友上传,仅供会员学习和参考。本站非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