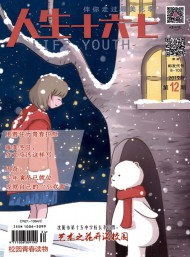人生哲学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03:06:13

人生哲学范文篇1
一、孔子之名:修养及发展的起点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大国争霸的乱世,当时社会诸侯不安于位争权夺利。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但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一生生活贫贱颠沛流离,生在乱世又雪上加霜,中国常言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孔子都遇上了。他经历了幼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一生的坎坷不幸他没怨天尤人而把命运变成使命,没有强调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却时时关心社会。孔子在其人生道路上战胜了自己使自己不为苦痛所系,致力于谋求社会大众的福利。他的经历教诲了后世,其思想和智慧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开启了儒家文化的先河。
孔子在论及名分时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乱世的礼乐不兴渊源于名不正,导致言不顺事不成。孔子生逢的乱世始于人际关系的迷失,人际关系的失常则由于名不正,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以此作为化解人际关系危机的前提。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辱礼。孔子重视礼视其为维护制度的手段并认为维护礼需要从正名入手。在那种名分已失天下大乱之时,“孔子惧,作春秋”,他所害怕的正是人际关系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及人心的败坏。他虽然重视礼乐教化却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养,要正名得从个人的修养开始,于是提出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仁。
二、孔子之仁: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将仁作为人格的核心视其为完全人格,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被称为仁人。仁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是个体成圣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圣是个体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仁的意义首先是独善其身的君子;其次是兼济天下的圣人,两者的综合就是仁人即内圣外王,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仁的内涵有以下解释:其一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一切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为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其三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以礼为行事准则。其四“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妙在于将外在的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最基本的家庭入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仁学植根于家庭伦理深入最基本的血亲观念之中。他们之间关系准则更突出的体现在孝悌、友仁和守信三个方面即人际关系中涉及的孝、仁、信。
孔子人生哲学是以仁为基础的伦理型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它要求为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从而亲仁”,以仁为基础提出了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等,都是做人的基本规范也是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人都处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应将做人的基本规范视为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准则,这便是孔子倡导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伦理法则。凡在生活中能够坚持以上操节并以之为安身立命者,就是儒家所称誉的圣贤仁人。
三、孔子之道:追求的终极境界
道在孔子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之道即仁道。道的产生和培养是依靠人的努力,道在人中并由人传递下去,“吾道一以贯之”,最终依靠人们的活动而成为现实,“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经常教导弟子:“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居,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荣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从其深层的底蕴来讲,说到底是人生价值生命归宿的大问题。
人生哲学范文篇2
时间:2003-2-21作者:醒回梦境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andOptimism,TheEncyclopediaofphylosophy,New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惫邸醇粗酢刀辉诟拍?-----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人生哲学范文篇3
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自己能“浮舟沧海,立马昆仑”,〔1〕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看来,青年人立志“当计其大舍其细”。所谓“计其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服务社会,而“舍其细”就是抛弃个人私利,不要去追求金钱地位和高官厚禄。而的志向则是挽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使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途,中国人民趋于幸福安康之境。
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而拔剑而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从爱国到革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人生道路。也不例外。他最初的爱国思想是在东北求学期间产生的。从淮安到沈阳,是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不仅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2〕而且开阔了视野,他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17年8月,在赴日留学前来到沈阳,给同学郭思宁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3〕
确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之后,关键是如何去实现它?认为: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必须做到“求真、重行、勤学、求新”。
“求真”就是探索和追求真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年轻的决心上下求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的强烈兴趣,他想研究其中的奥秘,因而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豪情万丈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4〕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新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犹如“一线穿云而出的阳光”,使年轻的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想通过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欧洲,他用半年多的时间对各种思潮进行反复“推求比较”,终于在1921年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一旦确定自己的信仰,则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信守自己的诺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斗争形势多么错综复杂,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6〕。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对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7〕
“重行”就是将理想付诸实施。说,“我平生最烦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8〕,不去脚踏实地的做,不去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因此,一旦看准的事情、认准的目标,就要“拼命去做,不计利害”,而且要有恒心,“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9〕。在看来,只要志向坚定,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将理想变为现实。
“勤学”就是勤于学习和思考。知识学问既是理想的翅膀,又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不学无术,即使有报国的热情,也是不能救国救民、服务社会的。认为:“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而学好知识,前提在于勤奋,一生之计在于勤。“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尤其在青年时代更要勤奋,不仅要勤于学习,更要勤于思考。反对在读书时囫囵吞枣,认为那样不仅虚掷光阴,徒劳无益,而且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求新”就是弃旧图新,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在日本留学时曾在“新中会”发表过一篇演讲,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落后,原因在于不能图新;而西方文明之所以发达,原因在于互相竞争,“一天比一天新”。他希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10〕。他给自己提出了“三新”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11〕在“求新”的思想驱动下,年轻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
二、谦逊淡泊,忍辱负重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从不居功自傲。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总是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从来不提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谦逊品格和崇高风范。1951年9月,京、津两地举行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会,邀请作报告,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12〕。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指出:“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3〕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由于的卓越才能,他在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工作了近五十年,而且不是没有机会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总是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以服务大众为自己的工作目的。不仅如此,他总是甘当人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有意把瞿秋白推向前台,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而自己则退居幕后,担任助手。在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职务后,虽然他被党内委托为最高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了发挥的军事指挥才能,仍自觉地退居于助手的位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更是心悦诚服地服从的领导,处处维护的领导权威,突出的形象。他不摆资格,不计名利,服从中央的工作安排,协助做好内政外交工作。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的工作,却谦虚地说自己“做的事实在太少了”。每当人们谈到他的功绩时,总是岔开话题,说自己是在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
三、尽忠尽孝,至情至义
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报恩意识非常浓厚。希望在自己长大之后,报答父母和长辈的养育之恩。他在旅日日记中写道:“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14〕在一岁时,就过继给叔父做儿子,虽然养父养母很早就去世了,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为了纪念养母,在旅日留学期间,将养母在少女时的诗文带在身边,经常焚香拜读。参加革命后,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为死去的亲人奠祭。对此,十分伤感和自责。1945年,他在重庆对记者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十岁时,到东北投奔伯父,伯父母没有儿子,视为己出。对伯父的“覆荫”之恩,他在一篇作文中给予了深切的记述。1917年秋,在赴日留学前,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在旅日期间,他经常给伯父通信。除夕之夜,他遥想伯父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身边无一亲人,因而无法入睡。
对生父周贻能,更是父子情深、倍加孝敬。1918年暑假,从日本回国探亲,父子俩在北京欢聚。但人间总是聚少散多,在日记中记述了父子分离的痛苦:“最是伤心此日。”“今早生父以四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孤单单既离吾家,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15〕1938年5月,他将父亲接到身边,以尽孝道。遗憾的是,这种父子天伦之乐的时间仅仅四年,周贻能就因中风而不幸去世。父亲去世时,因病正在医院动手术。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放声大哭,泪如泉涌。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出院,抱病为父亲守灵,料理后事。
大概是从小失去亲人、四处漂泊的缘故,十分看重友情,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朋友可以激励自己的斗志,“有友为励,益奋吾志”,因而与朋友交往是人生的一件快事。在交友时,主张以心交心,贵在知心,以诚待人,以情动人。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朋友是最多的,他既有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又有情深意挚的同志情,还有因感于的人格魅力,从对手变为朋友的。
与叶挺的友谊体现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1927年,他们共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患了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是叶挺、聂荣臻冒着生命危险,一直护卫在身边,并将他护送到香港。“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国民党无理扣押,在新华日报发表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积极营救,使叶挺终于重获自由。叶挺夫妇牺牲后,又为抚养烈士遗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可谓是生死之交。
最让人感动的是给杨立三抬棺送葬的事。长征过草地时,因重病不得不坐担架,当时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自告奋勇给抬担架。在饥寒交加、随时有可能陷入沼泽的情况下,杨立三深一脚、浅一脚,磨破了双肩,把抬出了草地,而自己却累倒了。19年后杨立三去世,身任国务院总理的不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而且坚持要给杨立三抬棺送葬。他深情地对参加追悼会的同志说:“在长征途中,我病了他可以抬我,为什么他临终,不能让我抬他呢?”有恩必报,平等相待,它体现了对同志的至情至义。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之所以成为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道德丰碑,主要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以及“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自我牺牲精神。马来西亚华人领袖庄汉良先生把比喻为蜀汉时期的诸葛亮,“他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于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二十六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16〕。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他经常抽出课余时间帮助那些成绩差的同学补课。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和大家的参与,因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17〕。在毕业时,《同学录》这样评价他:“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青少年时期的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为他以后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奠定了基础。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公仆意识更加自觉。他认为共产党员对人民应该像“孺子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18〕。一生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关心群众疾苦。特别是在担任总理之后,更是时刻心系人民群众。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第二天,冒着余震的危险到灾区慰问灾民。他穿过一堆堆残垣断壁,挨家挨户地查看,逢人便问:煮米有没有锅?烧柴有没有灶?吃饭有没有碗?他到临时医院看望伤病员,和他们亲切握手,询问伤情。灾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说难以报答总理的恩情,回答说:“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
一生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在三年困难时期,带头不吃鱼、肉、蛋,每月的粮食定量规定为25斤,而且三分之一是粗粮。即使是招待客人,也是普通的四菜一汤。在穿着方面,注意干净整洁,但从不穿名贵衣料。由于国务和外交活动的需要,在公开场合他一般穿庄重的制服,但在家休息则穿普通的旧衣裤,有的还打了补丁。为政清廉,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没有子女,但对亲属要求非常严格,制定了“十条家规”,主要内容是: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来人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请客送礼和动用公家的汽车;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谁违反了这些家规,都要受到的批评。对自己和亲属严格要求,近乎苛刻,而对祖国和人民却无限忠诚。为了祖国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建国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各种行政性、事务性的工作十分繁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他是最忙的人,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至16小时之间。
由于过度劳累和操心,终于积劳成疾,除了心脏病外,他还患有膀胱癌和结肠癌。虽然重病缠身,仍不能休息。根据他的工作日历统计,从1974年1月1日到1974年6月1日的五个月中,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外,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其中,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在14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在18至24小时的有44天。这是一个正常人都难以承担的工作负荷。他为党和人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做人民的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生前没有子女,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私人财产。然而,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了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他的人生精神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4〕〔8〕〔9〕〔10〕〔11〕〔14〕〔15〕〔17〕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297,300,331,328,367,331-332,307,398,47.
〔2〕〔3〕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J〕.瞭望,1984,(2).
〔5〕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46.
〔6〕〔12〕〔13〕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7,60,125-126.
〔7〕石仲泉,陈登才.的故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372.
〔16〕举世悼念总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3.
〔18〕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1.
人生哲学范文篇4
关键词:叔本华;德国;悲观主义人生哲学
在提倡和赞扬乐观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主流社会,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似乎无立锥之地。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曾经影响过至今还在影响着许多有着自觉意识的人。这样一个事实恰好说明了人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跟叔本华人生哲学产生了共鸣,共鸣点在哪里呢?就在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的人们所共同经历过或共同经历着的悲剧人生。这样的悲剧人生潜藏着人性共通的恐惧、挣扎、渴望、失望、哀伤、逃避、自怜与嫉恨。文学家以其细腻而敏锐的觉知将悲剧人生的实相诉诸笔端,叔本华则以其深邃的极富穿透力的哲学思辨能力揭示了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内涵。姑且不论这样的论断和看法是对是错、是积极还是消极,单就其对世人的影响力足可证明其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体系对于解释现实人生的合理性。其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从本质上来讲揭示了人生的实相,人生的实相本就是充满痛苦与哀伤,但凡自称为“人”的都不可避免地要与痛苦与忧愁斡旋。只是世人往往喜欢自欺欺人,习惯性地逃避各种痛苦与挣扎的折磨和煎熬,要么通过药物,要么沉溺于娱乐和交际,然而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以及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一.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内涵
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探讨离不开思辨主体对人生本质问题的探索与洞察。阿图尔•叔本华作为十九世纪德国著名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其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影响了后世许多文人贤哲对于人生本质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叔本华人生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冠以“悲观”二字,因为他是彻底的非理性唯意志悲观主义哲学家,他的整个人生哲学体系都围绕着人生本质是“痛苦”这个论点展开。他的“意志说”着眼于不受人控制的“意志驱动力”;他的“钟摆理论”聚焦于人类无可摆脱的痛苦和无聊;他的“解脱途径论”更是强调意志的绝对否定。这样一套人生哲学体系冠以“悲观”二字是对它最贴切的诠释。
二.叔本华人生哲学本体论
叔本华人生哲学的两个核心命题是“意志”和“表象”。在他的哲学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就直接说道:“‘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知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过只有人能够将它纳入自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1982:25)。叔本华以一句“世界是我的表象”开宗明义地宣示自己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对自己的人生哲学本体论有这么一段描述:“因此,人类会了解,当自己认知太阳和大地时,所认知的并非太阳和大地本身,而是见到太阳的眼睛和触摸大地的手而已;他周围的世界只是表象,只是意识和意识有关的东西,只是和人类有关的东西。假如世上有所谓先天真理的话,这就是先天真理:因为它表现的是一切可能的和可以想像的经验的最普遍形式”(2003:344-345)。由此可见,在叔本华眼中,外在事物并非客观地独立存在,而是人类认知的影射而已。叔本华是个典型的唯意志哲学家,在他眼中,“人类的意志是人类存在现象的真正内在本质,而存在现象则以表象形式表现于他的种种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永久基础即身体中”(2003:358)。对意志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进一步解释道:“表象世界完全是意志的反映,在表象世界中,意志的自觉一步一步地趋向明显和完整,其最高阶段则是人类”(2003:371)。由此可知,叔本华人生哲学坚决主张人类是受意志驱动的动物,人类所有的追求、奋斗、欲望皆是受意志驱动的结果而已。
三.叔本华人生哲学认识论
如上所述,人类受意志的驱动而产生种种欲求,因之叔本华得出了他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观的根本论断:“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这二者之间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当你需要为生存而忙碌时,你是痛苦的;当你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你会感到无聊”(1982:234)。这就是他著名的揭示人生本质的钟摆理论。在他看来,人生就是痛苦的,人类因受意志的驱动而产生种种欲望,进而为了欲望的满足不断进行挣扎、奋斗与追求。在追求满足欲望的道路上,因种种现实因素的阻碍,人类不断陷入各种忧虑、痛苦、绝望和悲伤当中。当欲求不满时,人类滑落痛苦一端苟延残喘;当欲求得到满足时,人类又陷入极端的无聊之中。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在痛苦和无聊两端来回摆荡。按叔本华自己的话说:“整个人生完全在欲望和满足欲求之间。从本质上看,希望就是痛苦,希望的达到立刻带来满足之感:这个结局只是表面的,占有使被占有的东西失去引诱力,希望、需要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若希望、需要不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接着来的便是绝望、空虚、厌烦,对抗这些东西的争斗和对抗困乏的争斗是一样的困苦”(2003:408)。即使这样,人类也无法使这个人生之钟停止摆荡,因为人的本质就是意志,他的种种行为是受意志驱动的。因此,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主张痛苦是生命中的必然现象,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一事实,相反,人为的否认和改变只会导向另一种痛苦当中。既然,人生本质是痛苦,那么人们不禁会问,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能使人类免遭人生痛苦的折磨和煎熬。对此,叔本华也做了探讨。
四.叔本华人生哲学解脱途径
结合叔本华人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他也提出了人类摆脱痛苦和无聊的解脱途径。在他看来,人类因欲望和现实的冲突不断陷入痛苦之中,而这欲望则受意志驱动。所以,要想根本摆脱人生的痛苦和无聊,人就必须过上绝对否定意志的生活。这个主张来源于古印度佛教。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体系除了受到柏拉图、康德等人的影响之外,印度佛教理论也是他理论建构的思想来源之一。因此,在如何摆脱痛苦的途径上,他认为佛教的禁欲主义是有效的良方。他觉得人应该过上一种绝对否定意志的生活,在行、住、坐、卧、思中断除一切欲念,清心寡欲,直至达到一种清宁平和的境界。这样自可免遭痛苦和无聊的折磨。
五.结语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其个人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但更多的烙上了当时他所处时代的印记。叔本华处在封建社会晚期充满斗争和分裂的德国,这才是他形成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最根本原因。他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进行哲学式思考,进而得出人生本质是痛苦和无聊的论断。人类自诞生以来从未停止过对生命本真的探索与追求,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各自特殊而不可替代和改变的人生体验,因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揭示生命实相的旅途中人们对生命本真有着相同的看法,可见,对个人生命体验有着觉醒意识的人们似乎更能接近人生实相。那么,是否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能够超越这充满痛苦与挣扎的人生实相呢?显然,叔本华的禁欲主义和绝对否定意志并非彻底的解脱之道。在刻意的禁欲主义和绝对否定意志的意念中仍然攒动着对欲望的渴求,受限的心灵仍然无法摆脱身体对各种能带来快感的东西的依赖和眷恋。那渴望解脱的人们该何去何从?其实,看到人生实相是一回事,能够毫无批判、拣择、比较、压抑地面对人生实相才是解脱痛苦之道,解脱痛苦并非漠视痛苦的存在或者将痛苦连根拔除,而是在看着痛苦的同时超越它而求得解脱。
参考文献
叔本华著.李成铭译.叔本华人生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371,344,358,408。
人生哲学范文篇5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andOptimism,TheEncyclopediaofphylosophy,New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即知觉〉而不在概念------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人生哲学范文篇6
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当其偏向于为政治提供价值规则时,它表现出道德哲学的理论征兆;当其偏向以政治践行某一伦理观念时,它又表现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但是不管它是道德哲学,还是政治哲学,都由于它把内圣外王作为致思主题,打通伦理与政治的问题域,最后必然融汇而成人生哲学。因为内圣的伦理一端,讲的便是人生的行为进路。由此分析早期儒家人生哲学的三大主题,可以进一步观察伦理政治情形中的人生情态。
其一,它强调人的尊严在于他的伦理觉醒。其二,它强调人生目的是进入高尚的伦理境界。其三,它强调使人生富有意义的,是个人具有的品德如何。第一点导出唯义是举的伦理取向;第二点引至对现世条件的漠视,直逼崇高;第三点规定了善德之于伦理政治的决定性影响。
一、尊严所在:人之为人的纯粹伦理定位
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由于将伦理作为政治的起始点与归宿点,使他们不能不对人的设计高度重视。除了对人的基本关系准则约之以仁以外,早期儒家更将人的行为取舍,以义加以规定。这样,人,就成为一个以爱人的高尚动机出发,又以适宜的行为处理行动中的各种关系,排除了利益与权力的无谓干扰,而获得一纯粹伦理定位的人的规定性。仁的规定性,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大原则,已成为早期儒家论人的大前提,在此前提之下,人对之的践履,便是排除伦理以外的因素干扰,而完全以伦理为目的的。但在早期儒家的思路中,仁还只是一种伦理心理上的规定性,还只是一个内心的准则。因而,将之付诸行动,还质的。一是仁义的对应性规定;二是义利的对应性规定。在前一对应性规定当中,仁是作为伦理内心原则出现的,义是作为践履内心原则而定位的,所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对应性规定表明,义是对“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不忍人之心”的外推。因此,义是人获得人的本质规定性,建立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寄。否则,在人禽之辨中,少了以仁制导的义,人与禽兽的差别,就无法显现了。在后一种对应性规定之中,义是作为基于纯粹伦理原则的行为取舍标准,而利是作为对伦理原则的纯粹性有危害性影响的对应范畴而出现的。因此,相比于仁义的对应范畴的重要性之于伦理观念的崇高性是为紧迫的而言,义利的对应关系之于伦理观念在伦理实践中的确当性,就是十分紧要的了。由.于这个原因,早期儒家对人的行为中的伦理状态,尤为注重.这种注重,主要体现于对四个方面问题的关注:其一,义是最重要的把握伦理准则的行为原则。“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强调的就是义在人的行为中所处的最前沿的伦理位置。其二,义是与利相排斥的一种伦理实践原则。二者只有在相互对应的相斥关系中,才显示为对人富有指引作用的伦理意义。如果抽象地、单独地讨论义或利,是对儒家这一原则的扭曲。为此,领会早期儒家的这类主张,就是十分必要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但是,这种对应的关系不是平列和对等的关系。因此,其三,早期儒家特别强调在伦理意义上,义远胜于利。重义还是重利,由此也成为显示人尊严的君子、与没有人尊严的小人得以划界的分界线。这是因为,一方面,“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这决定了利是绝对不能够让之处于主导地位的。另一方面,当一个人觉察到义的伦理价值,并成为君子时,他便自分界限地取义不取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同上书)“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儒效》)“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人人矣。”(《荀子·不苟》)“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由于义重于利,君子以义为行动指南,因此,其四,义在国家政治中和个人生活中的伦理决定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在前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荀子·王霸》)在后者,“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人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由上可见,对做人来讲,义对于利是有绝对制导意义的;而对为君(为君虽拥国权,但其实只是一个为君者如何做好人。做好人,则国家治理易如反掌,所谓“君仁莫不仁”)来讲,义同样曾谈到“为天下兴利”(《春秋繁露·考功名》),“兼利”(《春秋繁露·诸侯》),“爱利天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其实追原他的宗旨,仍然只是以义用权而已。所以才有“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纲领性陈述。
早期儒家的仁义、义利的对举,确立了做人的伦理化思路。人,也就获得了一个纯粹伦理的定位。仅就“修己”到“修己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的伦理推进来看,这一定位对伦理政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的承担主体确立位置。因为,只有基于纯粹伦理动机,而非基于利益动机、或权力动机的人,才可以担当伦理政治的主体责任。这中间是有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的。其二,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运作中的纯粹伦理动力机制提供前提。因为,伦理政治的运作,不免会关涉利益分配、权力享用,即公与私、义与利的问题。倘若在早期儒家视域中不能自动发生效用的法、法权(“无治法”),没有能驱动“爱利天下”、“天下皆悦”的法、法权发挥其功效,那么伦理政治也就丧失了动力(“有治人”强调的正在此一方面)。所以,治人者务必以纯粹的伦理动机作为自己治理社会从事政治的目标。在这里,为人与为政是统一的,统一于伦理动机、伦理化约、伦理感召、人情恩惠。如此,即可保证人的纯粹伦理定位,相应地决定政治的伦理化定位。其三,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理论化解理论障碍,使这一理论获得维持其自身的充分保障。因为,从人的内心到外在行为,都以伦理笼罩住,可以使伦理从内心“圣”处一直外贯到外在“王”处。这样,干扰伦理政治的因素:夺权的僭越、争利的对抗,都可以在未形之先被克制住。即使是涉及利益权力问题,利为兼利、为一身伦理正气的君王所利天下,亦是伦理化了;权为公用,为一心为民的君王所把持,正是合于伦理的。由此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人的崇高,人与人之间的稳定相处、关系和谐为目的而致思的。现代以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与人观念,完全不在早期儒家的视野之中。相对于义与利的伦理化处理来讲,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关于人的预设,就完全付诸阙如。所缺者一是,人是“理性人”的观念。理性人的预设,是基于对象化世界的认知需要而建构的。是指人可以以理性的筹划,认知客观对象世界,并把握客观对象的性质,进行改造策划,使之合于人的需要。由于伦理政治理论确认人是伦理人,而伦理内源于心、外推于人。内源于心而圣,外推于人而王。因此,它不必要拟定一个对象化世界的存在,哪怕把伦理投射于他人身上来感知,都是不被取法的(“小人求诸人”)。同时,由于伦理内源于心,也就没有必要建构一个认知心。切己自反,反躬自省,是伦理人伦理觉悟的“方法”。因此,有一颗圆善的道德心是伦理人的本质特征。理性认识的建构在伦理政治思路中,完全没有必要。
所缺者二是,理性计算的合目的性行为方式。理性计算,被马克斯·韦伯看作是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一大要素。因为,只有在行为之先有理性的预期,行为之中有理性的会计应用,行为之后有理性的统计审计,人———当然是有“天职”观念的经济人,才可能达到投入产出的理性预期目的。但是,由于早期儒家把人预设为伦理人,而且极端重视伦理人维持道义的纯洁性,排除利益干扰的重要性。因此,对人来说,唯一应当做的或能够做的,就是伦理道德心的呵护。至于基于利益问题的理性计算,在理论上是为早期儒家所排斥的。一旦理性计算的观念被确认,那将引起早期儒家伦理人预设的彻底颠覆。因为那样,结果将不会是人人理性谋利以致于天下皆利,而是人人谋利而天下良心俱失。但需指出,这种缺失在稳定是尚的伦理政治理论推导中并非是致命的,而是跳出这圈子,到以发展是尚的现代社会,这种缺失才影响理论前途。
二、境界为尚:营造一个伦理至上的生存氛围
对人来讲,活下来,才能谈得上是否认同某种伦理原则,因为生命存在是伦理作用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在早期儒家看来,此一问题却不能断然划分为二。倘若把生存与伦理取舍割裂开来,势必出现两种危险:一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放弃伦理原则。譬如孔子所特别注重的人在饥馑和危难状态下,遇见生命维持条件十分窘迫时,先德还是先食的问题①,就是基于这种思路。二是离开生命存在状况的追究而谈伦理,从而把伦理高悬为一种原则式的空洞教条。譬如早期儒家十分注意从衣食住行方面切入伦理问题,寄意就在避免这种危险。在早期儒家注重从生存处说伦理的推论中,最富有社会性意涵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贫穷之于道德操守端正者(君子)的关系;另一个是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如何可以乐观面对生活的困窘,以实践伦理为快乐。以第一个方面而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的对比,表明君子面对贫困是能够坚持操守而不动摇的。这是因为,君子秉德而生、秉德而行,是伦理的榜样、道德的旗帜,他绝不会为生活困窘的原因,放弃伦理原则。在此情形下,君子一方面是以义为行动指南的,使他可以排除现实物质条件和政治权力之争的囿限;另一方面,君子是“求诸己”的,他不以困窘而将伦理的实质性责任推给他人,他始终能“喻于义”、“以义为上”、“爱人”。这两方面构成了操守端正、心怀仁德的君子,不为贫困所动的原因。
以第二个方面而言,早期儒家十分强调在贫困中乐观对待人生,而且乐于行仁道的原则。在此,“忧道不忧贫”,成为强劲的思想动力;“不动心”,成为面对世俗生活中贫富差别,权力有无而坚守伦理准则的内在根据;“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成为人排除现世各种动摇人心的因素干扰的三种状态和体现。而归结起来,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孔颜乐处”。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早期儒家对人的生存氛围营造,其一,是不大注意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因为,一种以贫穷作为人有否德操、能否坚持操守的基本座标,已经潜含了一个预设在中间。这个预设是,富裕将影响德操意义的显现。于是,在贫穷与富裕之间,选择一个于坚持伦理信念有推动作用的参照系,早期儒家才毫不犹豫地择取了前者。至于富裕,当然也并不为早期儒家所完全拒斥。但是却把它的作用严格地限定在君子或君王施恩于民的范围内来谈论。其二,是不大注重人的生存状况的权势作用力的。尽管早期儒家面对的是“天下无道”或君王一统的严峻政治局面,他们还是认为面对霸气十足的诸侯应率直地陈述仁政主张,还是认为面对一统江山的君主,应以天人谴告警示君王谨行仁德规范。前者,是孔孟荀董都曾面对的处境。后者,则是董仲舒时代的生存氛围。所谓威武不屈,意义在此。其三,是不大注重伦理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对人的作用和影响的。在早期儒家看来,人有善心,反求诸己,便能把握自己,与德性合一;或者人有恶性,但一经圣人感召,化性起伪,均会风靡拜倒,否则便成为“小人”。在这种推论中,惟有教育的作用,在一定限度内(如“求放心”、如“积善成德”等等)被承认,其他实力性因素(政治制度的、经济安排的,此二者尤为重要)大致不被重视。伦理是独大的。当伦理独大完全被确认,而且成为一种伦理信念时,伦理就可以脱开一切支撑条件,变成为支持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的一种自足动力与支点。因此,也就可以有上述的“孔颜乐处”的境界陈说,以及这一人生态度充分发挥影响的足够空间了。“孔颜乐处”是早期儒家营造出的以单纯道德动机做人的一种高妙境界。这种境界,可以从三个维度上体会其要领。其一,它是乐观的。因为一个人可以排除物质生活的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能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能笑对不施予自己恩惠的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能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基于这一点,李泽厚有理由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乐感文化”①。其二,它是坚韧的。因为一个人要能够排除各种物质条件的影响,不是那么容易的。它需要有“忧道不忧贫”的高尚信念作为基础,需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精神作为支撑。在此角度看,孔子只许以颜回三月不违仁,自谦非仁非圣,都不是随意性的议论人物、臧否德行,而是对“孔颜乐处”境界的维持,怀抱一种谨慎的严肃态度。基于这一点,论者有理由把中国文化的精神称为“忧患精神”。因为于伦理把持而言,只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其三,它是自我确认的。一个人能否在窘迫的生存条件下把持住自己,紧紧与伦理道德相连,乐观地面对物质生存条件的困境,面对社会处境的无权无势,面对他人的纷纷变易信念而笃定行为取向,完全是由这个人自我决定的。它不由别人提供答案,也不由经验显示而出,完全依赖于这个人自己对进入崇高的道德境界的强烈祈求,完全凭借于这个人坚定的践履德性的执着追求。因此,在伦理至上的生存氛围中,以进入崇高伦理境界为目的生活的人,是一个完全自愿抉择的人,是一个甘为伦理境界丧失物质享受和权势畅达的人,是一个一心只装着爱人、利民的美德的人。基于这一点,说中国文化以个人美德(personalvirtue)塑造着最崇高的人格,就是有根据的。
以“孔颜乐处”的伦理至上性营造出的人生境界,使人心以践履美德为志业,这是一种典型的实质伦理或信念伦理(ethicsofconviction)。因为,一个人践履仁德,那是毫无条件地确当的。那既是圣贤的感召,又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体现。在此,善良的伦理动机被格外注重。行动者的意向、信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至于后果,并非不加考虑,但因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贤都难以实际达成的(“尧舜其犹病诸”),因而,结果是可以相对后置的。在早期儒家那里,行仁德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命令(obligation),一种来自于天佑价值和圣贤感召的命令。这种行动的后果,早已由君王圣贤相类行动起行动的大众完全不必要疑虑。基于这一性质,论者指出儒家“以伦理代宗教”的理论特质①,是有道理的。在此,伦理行动动机上的“彼岸”色彩虽淡却存。这是只尚境界而不论境遇(人的社会生存实际处境)必然具有的理论走向。相应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不太注重责任伦理(ethicsofresponsibility)的,责任伦理强调的是,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在于行为的后果,它要求行动者责无旁贷地对后果承担责任,并以后果的善补偿或抵消为达成这一后果所使用的手段的不善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相比于作为主观价值认定的信念伦理,责任伦理更强调客观因素的影响及行为者的审时度势。后者的“纯洁性”程度不如前者.
三、德性制导:排除恶的作用直抵道德理想
早期儒家将人做了纯粹伦理的定位,又营造了“应当”的伦理境界,顺理成章,会对恶的伦理功能加以排除。这是因为,伦理善不保持自身的纯结性,它就不成为能够促人向善的可靠源泉与坚强动力。善恶相杂,或者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或者善变换为恶、恶转化为善的相对主义观念,实足以根本上损害善的自足性、权威性,自然也就损害它的感召力与人对之的认同感。
因此,早期儒家顽强地抵制恶的伦理功能。一方面,他们在伦理的原则规定性上将恶排除在外,确认伦理的原则规定性只有从全善的“良心”与“良知”、“良能”三个方面去发现、去确认。这方面孟子的立场最鲜明。“不忍人之心”的扩充与“不忍人之政”的“天下皆悦”,使恶的伦理功能无从安置。另一方面,早期儒家将人的活动概观为善对恶的克服。在这一方面,一者他们认为人是可能恶的,因为人虽有善心,但放失其心,就不能维持其善行。基于此,“收放心”,即善胜恶,或回归于善,就是“学问之道”。二者他们又认为人本性是恶的,但恶却不是根深蒂固,无法改观的。相反“圣人化性起伪”就可以改恶为善,善仍然是主导的;或者“性禾善米”,在性上说,“善善恶恶”,但在走势上和结果上说,善还是归结点,禾苗时的恶涣散而去,结实时(米)完全成善。再一方面,早期儒家干脆将恶排除出伦理领域,由善来独占这一领域,将恶作为法律领域的惩处对象。从而既保证了善在伦理领域的独占性、绝对性、纯洁性;又保证了恶没有可能与善同处在一个领域之中,对善进行颠覆或根本性地损伤。故,早期儒家那里的善恶不是对应并举的,而是一个安顿在伦理领域,一个安排在法律领域的。这样,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个两领域的映衬关系而已,而不是同一领域相互激荡的对应关系。当然,也就等于不存在善全然变成恶的问题或危险。“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的提法,在这里先隐去其等级规制的涵义不说,倒是可以用来证明能进入社会政治生活操权阶层的“人”,是没有为恶的太大危害的。而“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则更直接地表明了早期儒家的这一思想意图。
当早期儒家把制恶打入法律范围,那么,伦理领域内,便只存在善与为善的问题了。一种直抵道德理想的思想旨趣,由此烘托出来。排除恶在致善中的作用,应当说对做人、进而对为政都有积极意义。换言之,恶之于伦理政治无动力可言的观念,是有它的正面意义的。这种意义,可以说有三:第一,有利于人对善的直接把握和悉心认领、全力践履。因为,在一种社会分化程度不高、智性水平受限的社会中,一个人能够自我反观并加以牢牢掌握的精神观念,并不是一个无限数。在这种情况下,直抵善而使之完全处于鹤立鸡群或异峰凸起的状态,可以使善在人心中成为一个不变的常数,杜绝了恶性恶习种种变数对之的消解作用。这样,人们易于掌握,并以一颗单纯的善心去自控。
第二,有利于使善成为完全控驭人心的规范,不致于因规范太多,善恶相杂,使善的伦理范导功能减弱,使人在各种规范面前手足无措。早期儒家重视的“正名”,在这一视角来看,更易显示其问题针对性。而儒家之看重伦理根源上的善、到伦理抉择上的善、再到伦理善包涵的善的效应,又从人唯善可举的角度,强化了人们纯朴的、善良的一致化行为取向。
第三,保持善对恶的战胜状态,维持善性的永恒规定性,对伦理政治中人面向永恒的德性理想,确立人生的生存目的,不为人生的曲折、失意、不遇所动摇,确实可有一种提升的作用。而且,“百王之道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伦理善,在把为善之道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所要做的,也就只剩下怎样逼近和实现伦理善的问题。目标极其明确而稳定,需要的只是各种情况下,人们不计处境地为之致力。在此,伦理善的茕茕独立,构成为社会运作的最深层动力,构成为人追循德性而动的永不衰竭的源头活水。它无疑再次显示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功能特性。
但审视德性的理性目光,却看到了纯洁无比、永为处子一般的伦理善,并不是自足的一面。从伦理善的实际构成上讲,人们是无法提供一个可定义、可分解、可理智掌握的永恒善的。
人生哲学范文篇7
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自己能“浮舟沧海,立马昆仑”,〔1〕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看来,青年人立志“当计其大舍其细”。所谓“计其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服务社会,而“舍其细”就是抛弃个人私利,不要去追求金钱地位和高官厚禄。而的志向则是挽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使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途,中国人民趋于幸福安康之境。
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而拔剑而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从爱国到革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人生道路。也不例外。他最初的爱国思想是在东北求学期间产生的。从淮安到沈阳,是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不仅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2〕而且开阔了视野,他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17年8月,在赴日留学前来到沈阳,给同学郭思宁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3〕
确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之后,关键是如何去实现它?认为: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必须做到“求真、重行、勤学、求新”。
“求真”就是探索和追求真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年轻的决心上下求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的强烈兴趣,他想研究其中的奥秘,因而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豪情万丈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4〕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新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犹如“一线穿云而出的阳光”,使年轻的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想通过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欧洲,他用半年多的时间对各种思潮进行反复“推求比较”,终于在1921年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一旦确定自己的信仰,则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信守自己的诺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斗争形势多么错综复杂,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6〕。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对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7〕
“重行”就是将理想付诸实施。说,“我平生最烦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8〕,不去脚踏实地的做,不去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因此,一旦看准的事情、认准的目标,就要“拼命去做,不计利害”,而且要有恒心,“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9〕。在看来,只要志向坚定,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将理想变为现实。
“勤学”就是勤于学习和思考。知识学问既是理想的翅膀,又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不学无术,即使有报国的热情,也是不能救国救民、服务社会的。认为:“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而学好知识,前提在于勤奋,一生之计在于勤。“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尤其在青年时代更要勤奋,不仅要勤于学习,更要勤于思考。反对在读书时囫囵吞枣,认为那样不仅虚掷光阴,徒劳无益,而且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求新”就是弃旧图新,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在日本留学时曾在“新中会”发表过一篇演讲,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落后,原因在于不能图新;而西方文明之所以发达,原因在于互相竞争,“一天比一天新”。他希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10〕。他给自己提出了“三新”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11〕在“求新”的思想驱动下,年轻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
二、谦逊淡泊,忍辱负重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从不居功自傲。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总是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从来不提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谦逊品格和崇高风范。1951年9月,京、津两地举行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会,邀请作报告,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12〕。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指出:“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3〕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由于的卓越才能,他在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工作了近五十年,而且不是没有机会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总是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以服务大众为自己的工作目的。不仅如此,他总是甘当人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有意把瞿秋白推向前台,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而自己则退居幕后,担任助手。在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职务后,虽然他被党内委托为最高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了发挥的军事指挥才能,仍自觉地退居于助手的位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更是心悦诚服地服从的领导,处处维护的领导权威,突出的形象。他不摆资格,不计名利,服从中央的工作安排,协助做好内政外交工作。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的工作,却谦虚地说自己“做的事实在太少了”。每当人们谈到他的功绩时,总是岔开话题,说自己是在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
三、尽忠尽孝,至情至义
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报恩意识非常浓厚。希望在自己长大之后,报答父母和长辈的养育之恩。他在旅日日记中写道:“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14〕在一岁时,就过继给叔父做儿子,虽然养父养母很早就去世了,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为了纪念养母,在旅日留学期间,将养母在少女时的诗文带在身边,经常焚香拜读。参加革命后,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为死去的亲人奠祭。对此,十分伤感和自责。1945年,他在重庆对记者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十岁时,到东北投奔伯父,伯父母没有儿子,视为己出。对伯父的“覆荫”之恩,他在一篇作文中给予了深切的记述。1917年秋,在赴日留学前,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在旅日期间,他经常给伯父通信。除夕之夜,他遥想伯父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身边无一亲人,因而无法入睡。
对生父周贻能,更是父子情深、倍加孝敬。1918年暑假,从日本回国探亲,父子俩在北京欢聚。但人间总是聚少散多,在日记中记述了父子分离的痛苦:“最是伤心此日。”“今早生父以四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孤单单既离吾家,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15〕1938年5月,他将父亲接到身边,以尽孝道。遗憾的是,这种父子天伦之乐的时间仅仅四年,周贻能就因中风而不幸去世。父亲去世时,因病正在医院动手术。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放声大哭,泪如泉涌。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出院,抱病为父亲守灵,料理后事。
大概是从小失去亲人、四处漂泊的缘故,十分看重友情,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朋友可以激励自己的斗志,“有友为励,益奋吾志”,因而与朋友交往是人生的一件快事。在交友时,主张以心交心,贵在知心,以诚待人,以情动人。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朋友是最多的,他既有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又有情深意挚的同志情,还有因感于的人格魅力,从对手变为朋友的。
与叶挺的友谊体现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1927年,他们共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患了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是叶挺、聂荣臻冒着生命危险,一直护卫在身边,并将他护送到香港。“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国民党无理扣押,在新华日报发表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积极营救,使叶挺终于重获自由。叶挺夫妇牺牲后,又为抚养烈士遗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可谓是生死之交。
最让人感动的是给杨立三抬棺送葬的事。长征过草地时,因重病不得不坐担架,当时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自告奋勇给抬担架。在饥寒交加、随时有可能陷入沼泽的情况下,杨立三深一脚、浅一脚,磨破了双肩,把抬出了草地,而自己却累倒了。19年后杨立三去世,身任国务院总理的不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而且坚持要给杨立三抬棺送葬。他深情地对参加追悼会的同志说:“在长征途中,我病了他可以抬我,为什么他临终,不能让我抬他呢?”有恩必报,平等相待,它体现了对同志的至情至义。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之所以成为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道德丰碑,主要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以及“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自我牺牲精神。马来西亚华人领袖庄汉良先生把比喻为蜀汉时期的诸葛亮,“他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于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二十六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16〕。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他经常抽出课余时间帮助那些成绩差的同学补课。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和大家的参与,因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17〕。在毕业时,《同学录》这样评价他:“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青少年时期的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为他以后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奠定了基础。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公仆意识更加自觉。他认为共产党员对人民应该像“孺子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18〕。一生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关心群众疾苦。特别是在担任总理之后,更是时刻心系人民群众。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第二天,冒着余震的危险到灾区慰问灾民。他穿过一堆堆残垣断壁,挨家挨户地查看,逢人便问:煮米有没有锅?烧柴有没有灶?吃饭有没有碗?他到临时医院看望伤病员,和他们亲切握手,询问伤情。灾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说难以报答总理的恩情,回答说:“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
一生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在三年困难时期,带头不吃鱼、肉、蛋,每月的粮食定量规定为25斤,而且三分之一是粗粮。即使是招待客人,也是普通的四菜一汤。在穿着方面,注意干净整洁,但从不穿名贵衣料。由于国务和外交活动的需要,在公开场合他一般穿庄重的制服,但在家休息则穿普通的旧衣裤,有的还打了补丁。为政清廉,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没有子女,但对亲属要求非常严格,制定了“十条家规”,主要内容是: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来人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请客送礼和动用公家的汽车;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谁违反了这些家规,都要受到的批评。对自己和亲属严格要求,近乎苛刻,而对祖国和人民却无限忠诚。为了祖国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建国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各种行政性、事务性的工作十分繁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他是最忙的人,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至16小时之间。
由于过度劳累和操心,终于积劳成疾,除了心脏病外,他还患有膀胱癌和结肠癌。虽然重病缠身,仍不能休息。根据他的工作日历统计,从1974年1月1日到1974年6月1日的五个月中,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外,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其中,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在14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在18至24小时的有44天。这是一个正常人都难以承担的工作负荷。他为党和人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做人民的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生前没有子女,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私人财产。然而,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了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他的人生精神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4〕〔8〕〔9〕〔10〕〔11〕〔14〕〔15〕〔17〕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297,300,331,328,367,331-332,307,398,47.
〔2〕〔3〕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J〕.瞭望,1984,(2).
〔5〕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46.
〔6〕〔12〕〔13〕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7,60,125-126.
〔7〕石仲泉,陈登才.的故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372.
〔16〕举世悼念总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3.
〔18〕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1.
人生哲学范文篇8
有人認為一部哲學史便是人類自我覺醒、自我發現與成長歷程的紀錄,當人類在自己存活的自然環境中覺醒,發現到人與自然的區別之後,便開始嘗試去瞭解自然、瞭解自己,發掘自然與人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類幡然醒悟到認識人自身、解開生命之謎、追求生命的意義,才是人生命在自然中奮鬥、存活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說認識人本身,追求生命的意義,才是人終極關懷的首務。從剛開始素樸的理解到現在多學科的發展,例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一言以蔽之,無不是在探究與解釋人類生命過程中的各種現象而已。
然而由於近代以來,學術的分工,專門化、部門化的發展,固然深化了各個層面的理解,相對的,也造成各個學科都只偏重研究人類的某一個面向;再則由於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各學科對人的研究也都傾向於把人當作一個客觀事實來研究,並嘗試經由經驗歸納去表述和證明「人」這一客觀事實。長期以來,造成人被當作一個客觀的存在物來觀察,並且被割裂地去研究。相較於這種割裂分析的研究,哲學則採取較為宏觀、整體的觀點去思索人的問題,哲學不是將人割裂地、當作一個客觀對象而已,哲學所要研究的是做為一個整全的人是什麼;主要探究的不只是當下的人,而是探索人始終是什麼的問題。主要問題有:人開始時是什麼?什麼力量賦與人去改變所遭遇到的環境?在主體性的意義上,屬於人自身的東西是什麼?人可以相信些什麼,能運思些什麼?人應當在什麼範圍內懷疑自身所要求的對象的確定性?人能對其自身所遭遇而又參與其中的日常生活和活動指望什麼?在艱難的人生過程中,人繼續生活的勇氣從何而來?超越自身、超越自身所接納的對象的人本身是什麼?人生命終止於何處?此種種便是哲學所探究人類生命問題的主要課題(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換句話說,從哲學立場整體地去探索生命,可以避免把人當作對象物、割裂的研究傾向;而且透過哲學性的探索,不僅只是知道現實上的「人是什麼」、「人能知道什麼」而已;更可以瞭解到作為一個理想的人,「應當做什麼」,「可以期望什麼」。如此哲學性探索的方向,可以作為人類謀劃未來,應當如何行事的參考,更是有關人的生命教育課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學科。有關探索生命的課題相當多,無法一一陳述,在此僅嘗試就哲學的立場擇要探討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問題。對其他生命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則可進一步閱讀有關生命哲學的相關著作。
什麼是「生命的意義」
在探討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之前,首先必須要澄清的是究竟什麼是「生命的意義」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在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也不是在問「生命」是什麼」。「生命」是什麼是有關「生命」的本質是什麼的詢問;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是在追問「生命」本身有什麼意義。本文所要探討則是「生命的意義」本身是什麼。人的「生命」從人類受胎開始就已經存在了,但是「生命的意義」並不是始於人的受胎成形,也不是天生現成的,而是人在有所自覺之後才開始自己構畫賦與的。誠如諾齊克(Nozick)所說的:「生命的意義:一個人根據某種總體計畫來構畫他的生命,就是賦與生命意義的方式;只有有能力這樣構畫他的生命的人,才能具有或力求有意義的生命。」(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2001,頁596)「生命的意義」是人類自我所賦與的,是在人們根據某個總體計畫,或者說是依照某個總體的生命藍圖來構畫自己的生命方向時才賦加上去的,也就是說隨著每個人所選擇總魯生命藍圖的不同,所構畫出的「生命的意義」也有所差異。在這層理解之下,當我們面對生命,或許不必先急著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要先問:「人應該如何賦與生命意義」,或者說:「人應該如何去構畫出生命的意義」,只有人們開創了自己生命的意義,而後才能去追問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去對人所建構出來的生命意義進行肯認。因此不必惋歎生命沒有意義,畢竟「生命的意義」是在每一個人如何去構畫自己「生命」的活動中賦與的,責任在每一個賦與生命意義的人,只有人們去構畫自己的生命,並努力成就自己的生命,生命才活出了意義。
如何活出有意義的生命
一個人想要活出生命意義的人,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自我立定志向、目標去找尋一個總體計畫或是總體生命藍圖,依照這個總體生命藍圖去構畫自己的生命,同時能夠貫徹實行自己的構畫,才能活出自我生命的意義。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會根據宗教的計畫來構畫自己的生命,並活出具宗教意義的生命;一個注重傳統的人,可能選擇根據傳統的計畫來構畫自己的生命,並活出承襲傳統的生命意義;一個凡事要求合理化的人,可能根據各種不同的理論模型來構畫自己的生命,過著他所認為的合理的生活;……。無論我們從事什麼樣的選擇、找到了什麼樣的總體生命藍圖;然而依照該計畫來構畫生命,進一步活出有意義的生命,並不是件簡單的工作。因為總體生命藍圖不是現成的羅列在眼前,任由我們隨意去評比揀選,就可以對我們的生命活動產生影響力的;總體的生命藍圖必須要內化為自己堅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才能影響生命的方向。
一、總體生命藍圖的內化與建構--一種永恒的追求
總體生命藍圖在內化為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的過程中必須經過漫長而艱辛的磨鍊:人必須經過一段不斷選擇、結構、解構、重構的接受過程。這個內化的過程從人們還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從我們開始會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去詢問「為什麼」並努力找尋解答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從事一種建構的謀劃,至於說要到人生的那個階段才構畫冗成滿則不得而知,或許可以說人終其一生都在構畫一個總體而完整的生命藍圖,這是人終極的追求。這並不是說要構畫完成一個最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人的生命才有意義;事實上,隨著個人生命的成長與發展,隨著個人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之增廣,個人所構畫出的總體生命藍圖有其廣度及深度上的差異,每個階段的完成,對個人而言都有其階段性的意義;只不過對一個追求成為完備的人而言,永遠不會停滯於現階段的完成,因為他明白只有不斷地開拓總體生命藍圖的廣度與深度,個人的生命意義,才能不斷地開展。總之,內化到個人心中的總體生命藍圖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是開放的,一個可以不斷擴展與加深的內在世界,所以人與其說是在找尋一個總體的生命藍圖,不如說是人在心中不斷地調整與構畫著一個較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而正是因為這個永恒的追求,使人生命的意義具有了無限開展的可能性。
二、建構內在總體生命藍圖的重要性
人究竟該如何在心中建構總體的生命藍圖呢?簡單地說,就是「即事而問」,在日常生活的遭遇中,不斷地去扣問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及問自己「為什麼如是存在」、「為什麼展現如是的生命現象」並積材地去找尋解答。在人生過程中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問「是什麼」,與問「為什麼」是兩個不同的發問。「是什麼」的發問,主要意味著我們想要進一步瞭解所遭遇到的事物本身的結構如何?這個事物本身有那些特性?這個人事物本身之所以為人事物自身的本質又是什麼的問題;而問「為什麼」的問題則並不只是想要去認識人事物本身是什麼而已,「為什麼」的發問是人們企圖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進行解釋與理解,企圖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納入到他個人內在意義世界時的一種提問。接觸過小孩子的讀者,大概都領教過他們每事必問的工夫吧?!一連串的「為什麼」時常會問到大人們無力招架,或感到困窘,甚或有時會因為不耐煩而惱怒。小孩子真的是每事必問,這為什麼這樣,那為什麼那樣,何止十萬個為什麼!孩子這一連串「為什麼」,意謂著在孩子的小腦袋瓜子裡正在尋求一個解釋、一種答案,以便去編織一個對自我而言充滿意義的世界,他必須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一一在他腦袋中加以編碼連結,使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都能納入到他意識中原本已經自我建構的意義網絡中而得到安頓與理解,才會使孩子暫時的停止發問。若是面臨到無法理解的人事物,也就是無法將現實中所遭遇到的人事物納入原先已經構成的內在意義網絡,孩子們就會又開始進行這個「為什麼」的提問過程。在詢闆與找尋解答的過程中,孩子不只是將獲得的答案納入一己原先構畫的網絡中,同時也開始去對原先建構起來的意義網絡進行解-相應新的人事物,調整自己原本建構起來的意義網絡,直到重構出一個可以將所遭遇到的、新的人直物一一納進來的意義網絡為止。這個相應於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不斷地追問「為什麼」並找尋解答的過程,並因此而建構起來的內在意義世界,就是一個已經內化為個人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的總體生命藍圖。
人的真實生命是在與情境的互動中展開的,相對於人的內在世界,外在世界雖然是被給與的,但是外在世界也必須被人的內在理智所掌握,並稚有經過人的詮釋才能被人理解。人雖然是世界的一個部分,但是人必須經過不斷的與世界交往互動,並經過人不斷地去向世界追問「為什麼」,從而為自己的提問找尋答案,再三琢磨確認,才能消除內心對世界的陌生感,有了這種確切的認知,人在生存世界之中,才能逐漸獲得一種安居其中的熟悉感及確定自己該如何行事的方向感。如果仔細觀察,或許會發現當孩子們面對新的環境,接觸新的人事物時,「為什麼」、「是什麼」的發問特別多,多到令大人們覺得有些聒噪了,換個角度想想,似乎這也意味著這個孩子急著重構自己內在的意義世界,因為他原本建構起來的內在意義世界,無法安置所面臨的哀的人事物;孩子的聒噪,顯示了孩子無法將新的人事物納人內心意義世界時,內心引發的焦慮不安,及不知所措、失去行動方向感的困窘。所以說對所遭遇到人事物去追問「為什麼」的問題,並找尋解答的努力,絕不只是哲學家們無聊的思想遊戲而已,基本上這種活動,是參與生存世界中的人,企圖在心中構成總的生命藍圖,活出生命意義的嚴正活動。有意義的生命,意味著我們可以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都轉化成為可理解的,並且能運用在實際生存情境中,去獲得一種熟悉戊及決定行動的方向感,讓人安居在生存世界中而不致焦慮不安、不知所措。
三、建構內在總體生命藍圖的可能方式
如前所述,人是在日常生活的遭遇中,不斷地去扣問「為什麼」並努力找尋解答的過程中建構起生命藍圖的。根本而言,找尋解答的方式非常的多,比如我們問說:「為什麼我會感到痛苦?」一方面我們可以對這個問題提出生理學角度的解釋,亦即把痛苦當作一種生理現象,並去描述痛苦的生過程;另方面我們也可以提出宗教上的解釋,將痛苦解釋成源自人本身的無名;或者也可以從心理的角度來理解,將痛苦理解成是某種心理狀態;……總之,找尋解答的方式可以是多樣,同一件生命事件,放在不同的脈絡中則展現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生命的意義是如何的,決定在我們將生命現象放在什麼樣的脈絡背景中去理解。
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乃至哲學,所有的知識都足以提供人們作為理解生命現象的背景。所以廣讀這些學科的知識,可以幫助人們走出狹隘的認知,而廣泛的理解生命現象,從而在其中揀擇、構成總體的生命藍圖。但必須要指出的是,無論我們採取那一個學科領域對人的研究成果來理解生命現象,所構成的總體生命藍圖,仍只是一種思想的存在或是意識的存在。這種思想的或是意識的生命藍圖,所能解決的不過是我們理論理性的要求,滿足我們知性上合理化的需求而已。不可諱言的,凡事要撾有一個合理化的解答,對人類的生存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我們總是不可避免的會去思索「為什麼」的問題,而各種知識性的理論模式,都是勇於嘗試解答者,儘可能的為我們提供一種可能的、理解生命現象的途徑。然而人類的認識能力終究是有限的,生命對我們而言永遠是個待解的謎,我們似乎永遠無法知道生命「為什麼如此」,對一個明白自己認識限度的人而言,再完備的理論體系,都無法完全安頓他對生命的提問。如果他還堅持要問「為什麼」,那麼似乎要尋求其他的解答途徑了。在這種狀況下,訴諸傳統、信仰都是可以嘗試的途徑,也是一般較熟悉的途徑。
不過以下所要討論的並不是傳統的或是信仰的答解途徑,而是較為人們所忽略的另一種途徑,亦即人透過身體與周圍的一切保持不斷的互動關聯時,身體所體會和感受到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四、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綜觀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可以發現,西方傳統哲學雖然早就開始研究人,但主要的觀點卻是採取身心二元的理解結構,以致忽略了人的基本生活體驗,受這種理解結構的影響,造成身心的疏離,人們與自己的身體失去了緊密的聯繫:或有人視肉體是罪惡、痛苦之源,肉體是心靈的牢籠而不重視肉體;或認為我們要追求的是心靈的滿足而把肉體放在一邊;或是否認在身體內發生的感覺,以為這些是不好的、有害的,以致逃避而不敢面對自己身體的反應(瑞尼.威爾菲爾德,2001,序言)。廿世紀以來存在主義的發展,促使人們重新開始重視人的基本生活體驗,到了廿世紀中葉,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Merleaau-ponty)創立以身體為基礎的存在現象學,詮釋了身體在世界構成中的基礎作幅,更進一步提昇了身體在當代思想中的地位,引發了人們轉回對身體的關注,並意識到身體是人構成世界的原型這一事實(梅洛.龐蒂,2001)事實上早在一八九六年,柏格森林(H.Bergerson)出版的《物質與記憶》一書中,就已經非常注意身體的問題,指出了身體會選擇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儲存它所發現的東西(柏格森,1999,頁8-9)。有關身體的研究到上世紀八○年代以來,更整合為對身體的跟學科研究,在西方並已獲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研究、精神分析學、主姓主義等都把它作為主要的研究論題。
其實從遠古時候起,神話、巫術與宗教信仰瀰漫下的人類,就是以自己身體的原型去構想宇宙的形態、社會的形態、乃至精神的形態,但西方人卻走了那麼遠的路,到了十九世紀末、廿世紀才回頭重新開始注意到這種現象;相較於西方,或許可以說中國人老早就有意識的、自覺的注意到這個現象了,例如,漢朝的董仲舒就曾經提出了「察身以知天」的說法,不僅意識到,更進一步反省與考察人是如何以自己的身體為原型去構想天地萬物的形態,指出想要知道在人們構想中的天地萬物形態究竟是如何的,就必須反身自省,由考察人的「身體」入手。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所謂的「身體」是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心合一的整體。所謂的「察身」,並不是把人從具體的生存情境中抽離,孤立地去研究人類自身內在的事物,如思想、靈魂和肉體的作用如何?而是把人納入實際情境中加以掌握;中國人也觀察人,但是中國人對人的觀察,是將人置於現實生存情境中,所掌握到的是人相應生存情境而產生的一種動態關聯。這種人與情境相關互涉的動態關聯,也可以作為我們構畫生命的總體生命藍圖。有關這種心想,可以在中醫理論中找到系統的說明,對於有興趣從醫學背景中來構畫生命意義的讀者,或許可以進一步去研究中醫理論,並從中發現與理解中國傳統醫學中所提供的總體生命藍圖究竟是如何的狀況。此非本文所探究的範圍,不遑多論。
在此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關「察身」的另一層意義──「察身」不只是對身體作對象化的觀察,「察身」也可以指人們在自己的生存情境中,對自己身體活動的整體知覺,或稱之為身體的知覺。這種身體的知覺不是把身體當作一個對象化的客體,不是從外部來觀察自己的身體,而是「以身觀身」(《老子》),回返身體本身,從內部感受身體自己在運動時的震顫狀態。
(一)如何構成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誠如德國哲學家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Schmitz)對哲學所下的定義,以為哲學可以界定為「人對自己在遭際中的處身狀態的沉思」(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現代身體現象學的主要意圖,即在試圖揭示性的和理性的去接近身體無意識的生活體驗(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而傳統中國思想不僅只是教人揭示性的和理性的去接近身體無意識的生活體驗;更要進一步的教人在生活情境中調整無意識的身體活動,使其能展現理想的活動狀態,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同時也教人開發身體的各種感知能力,去感知原本是無意識的身體震顫。這種以人的身體去建構總體生命藍圖,或生命意義的方式,有其特殊性與簡易性,以下即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主,詳細分析中國傳統思想是如何教人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調整自己身體的活動,使身體向所遭遇到的賽事物開放,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以及如何教人用身體去感知身體的震顫;希望由此引述,指出這種構成生命意義方法的特殊性。
(二)論「心齋」,「坐忘」
大體而言,《莊子》書中有關「心齋」、「坐忘」的敘述,或可視為瞭解中國古人對於如何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開發身體知覺等相關問題,相當典型的範例。為了清晰的說明上述經由身體構成總體生命藍圖的見解,首先得分別解析式的揭示在《莊子》中有關「心齋」、「坐忘」描述。《莊子‧大宗師》說:
然日:「何謂坐忘?」顏回日:「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日:「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在(大宗師)中,莊子借孔子與顏回的對話來闡述何謂「坐忘」,根據其中的對話可知,所謂的「坐忘」,就是要使自己「同於」大道;而「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所描述的是人處於「坐忘」狀態中,人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體與外物的認識關係如何。
首先要說明的是所謂人自己必須「同於大通」的意思,基本上指的是《莊子》所認為的一種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所謂的「同」除了具有「會合」、「淵」的意思之外,還有參與共謀以及和諧的意思,循著這些意義,「同於」物或是「同於」大通(大道),主要是說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應廳是指與天地萬物會合,與天地萬省以一種相互關聯、相互配合的方式,構成一種相反相成,共同謀劃的、共在的、和諧關係(林文琪,2000)。
其次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依莊子的看法,主要在說明人應該要如何調動自己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體,去完成理想的身體活動狀態。有些人以為(大示師)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主要是指人應該要去情去我,而抑制形體、感官、心知的作用。若依照一般的看法,那麼所謂的「坐忘」豈不就像是《莊子.天下篇》所記載的慎到之流的人物,追求「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莊子‧天下》),如草木樹石般無情、無知之物的生命狀態?!其實莊子並非如此之主張,反而以為這根本是「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莊子.天下》),由此可見《莊子》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並不是要使人的生命「至若無知之物」的狀態。那麼竟究該如何理解(大宗師)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呢?本文認為應該回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等「墮」、「黜」、「離」、「去」在人身體上所發生的活動狀態如何,來作重新的反省。(林文琪。,2000)
「墮」字,有「易」,轉變、簡易的意思:之有惰的意思。循此義衛伸,則「墮」枝體,並非要放棄身體的意思,而是指轉變肢體本身的運作方式,使其由繁而簡,讓肢體的運動回復到最簡單、基本的運作狀態:而「墮」作「惰」的意思,則是指調整肢體相應外界的反應方式,使其由積極主動的活動方式,轉而採取一重被動因應,「待物而動」的活動方式。(林文琪,2000)也就是要調整身體的活動使其展現「聽之以氣」的狀態。《莊子.人間世》說:
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之。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莊子》指出,人與外界的人事物相遇時,若只是開放我們的耳目口鼻等身體的感官去接受他們,那麼就如「聽止於耳」般,我們只對所遭遇的人事物開放身體的感官而己。《莊子》以為人與外界的人事物相遇,除了引發我們感官的活動之外,還會進一步的引發心知的成活動-「聽之以心」:但是「心止於符」,心知構成活動,容易將外物當作一個客觀的存在物來觀察,因此如果囚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進行心知的構成,亥即囚對外界人事物進行知識性的理解,如此一來,心知所建構起的內在生命藍圖,不過與外界的人事物有一種相符合的關系而己,並沒有產生具體的、存在上的關聯。因此《莊子》進一步指出,理想的人與外界人事物的互動方式,是「聽之以氣」。所謂「氣」,主要是指身心合一的身體在參與情境互動中所展現出來的總體活動狀態:「聽之以氣」,則是說我們在與外界的人事物交接互動時,必須整個身體參與到情境中,以整個身體向情境開放,展現「虛而待物」,讓身體活動展現「應物而動」的狀態,才能與情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協作關係。
「黜」與「屈」相通,具有收斂的意思。如《國語.周語下》:「為之六閒,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工引之的《經義述聞》說:「引之謹案:黜,讀之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氣之。……沉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所以聞陽律,成其功也。發揚與沉伏義相反,則黜與散越義亦相反。」從身體活動的角度而言,「黜」是一種反向的調整活動,亦即收斂呈現散越狀態的氣。在這個理解之下,所謂的「黜」聰明,是指調整耳目的運作狀態,亦即收斂耳目指向外界,逐物而不反的狀態,轉成為一種「反聽內視」的狀態。這就是《莊子.駢拇》所說的:「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己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己矣。」「黜」聰明就是指調整感官知覺的作用,使其成為「反聽內視」的自聞、自見,回返身體活動本身來加以感受。(林文琪,2000)
「離」具有兩行並立,以及明的意思,循此義而論,所謂的「離」形,並非說「坐忘」時要超越形體,心靈脫離形體而進人出神的狀態,而是說「坐忘」時人不僅從未超越形體,反而在坐忘狀態的當下,人的身體本身對自已所展現的形體,有一種與形體活動兩行並立的自知之明,亦對活動中的身體形成一種身體的知覺,感受到形體活動時的震顫狀態。(林文琪,2000)
「去」具有「人相違」、行的意思。循此義而論,則所謂的「去」知,人是人用心知、脫離心知的意思,而是「違」其心知而行的意思,亦即調整「心知」的作用方式,使「心知」的作用方式與一般主動構成的用方式相反。例如,相應於我們與物交接時,心知指向外物去認知外物的指向活動而言,所謂的「違」其心知而行(「去知」),就是說要調整心知的指向作用,使其由向外物的意向轉而成為一種對「思」的活動「反躬個省」的意思:另就心知的構成活動而言,心知的構成活動,主要是先將外物與我對立,而後去對外物進行批判性的考察,使外物脫離直接經驗的或感知的所對,而成為一種可理解的、具有確定性的、思維的對象。相應心知的這種構成活動,「違」其心知而行(「去知」),旨在調整心知的構成成活動,使心知能以「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莊子.人間世》)的方式展開,亦即當感官心知「徇耳目內通」,經感官、心知作用形成關於外物的知覺時,心知能發揮其「反躬自省」的能力,自我調整,不以持有(having)的方式來固持心知構成之成果,不視之為唯一的真理,重反直接面對事物的交往活動。(林文琪,2000)
(三)小結
綜合前面關於「心齋」,「坐忘」討論中,有關身體活動狀態的說明可知,《莊子》以為理想的人與天地萬物互動的方式是,人整體身心的活動必須處於「同於」天地萬物的狀態,亦即與天地萬物的活動相會合,與天地萬物形成一種相互關聯的、相互配合的、相反相成的、共在的、和諧的互動狀態。也就是說,人以實際身在情境中,以與情境融為一體的狀態,與情境互動,而在「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之後,與情境成為和諧共在的整體。
基本上,這種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是通過一種本體同一化的運作,向外物開放,以「虛而待物」的方式,因應外物之動而動,與外物的存在活動,使人的存在活動與物的存在活動,在密切而具體的交住(communion)之中,相互諧調,和諧共動。這不只是一種理智的構畫,而是實際身體的活動,在身體實踐中完成的生命意義。
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就是在我們「虛而待物」的身體活動中構成的。然而《莊子》認為我們不只要調整身體的活動方式來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而已,而且在相互諧調的互動中,人對自己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要有一種「反聽內視」和「反躬自省」。這種身體在活動過程中不斷地向內的「反聽內視」和「反躬自省」,就是身體構成自身身體形象的過程,或可稱之為形成身體知覺的過程。比如當自已在打字時,除了調整我們的身體,使自已身體動作都能展現與情境中的條件協調的狀態外,在過程中還要去感受打字時自己身體整體的震顫狀態,像:肌肉的收縮與放鬆,整個身體的運動方向,自己身體在整個環境中的位置等。身體知覺的開發,不僅使我們發現身體所構成的、理想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肯定、確認了自己所構成的理想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而且可以讓我們感受到自己是身心合一的整體,引發一種與整個生存情境相互協調的、共同體的感受。這就是《莊子》所說的「物化」。《莊子.齊物論》說: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人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所謂的「物化」是人以其自已全身心的存在向物開放,讓自己的生命律動展現為因應外物之動而動的狀態,與外物形成一種交互同步、複調性的和諧互動。在互動中,人不僅致力於調整自己以與外物形成同步的互動,而且體驗著自己活動的成果,形成一種與外物合而為一的感受:但是這種一體的感受,這種與外物合而為一感受,不是自我縮減,放棄自我投入對象的密契經驗,而是如莊周夢蝶般,自己化作另一隻蝴蝶,栩栩然地與所交往的蝴蝶共舞,是一種與他物共在的感受,一種共同體的感受。所以「物化」不是化身為對象,而只是調整自己,使自已與對象成為同一層次的存在,以與外物形成交互同步、複調性的和諧互動。雖然「物化」時人是調整自已的活動使之與對象成為同一層次的存在,但是人在與物交互同步的互動中,是隨時保持著清楚的自覺,「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儘管在互動中會引發「人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密切不可分割的一體感,但是「周與蚑蝶,則必有分矣」,人們不僅感受到整體,而且也能感受到自已是整體的部分,自已與共舞的對象是有分別的。(林文琪,2000)
此外,身體知規的開發,也使得人對自已與外在人事物互動時的身體活動婦身,產生一種全神貫注而且沒有外在目的性的知覺,以及引發「躇躊滿志」的「自得之樂」這就像《莊子.養生主》中庖丁解牛故事所描述的,解牛本來不過是個技術性的操作而已,但由於庖丁不僅追求技術的純熟,而且對自已整個解牛的活動過程,有非常清楚的感受,且能欣賞自已所完成的動作,引「躇躊滿志」的自得之樂,賦與了生命活動審美的性質。
結語
回到本文主要的論點必須再三申明,生命的意義人不是現成的某物,而是我們所賦與的看法。賦與生命意義的方式,主要在根據某一個總體的計畫或是生命藍圖來構畫自己的生命方向,並實踐這種生活,如此才能活出有意義的生命。
一個總體的生命藍圖,必須內化為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是人觀,才能在生活實踐中發揮影響力。但是總體生命藍圖內化的過程,人是一勞永逸的追求,而是在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互動中構成的,隨著我們遭遇的不同、個人選擇的不同,所建構出的總體生命藍圖也會展現出不同的廣度與深度。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持以構畫自己生命的總體生命藍圖有很多,比如各種理論模型,例如,醫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等等;或影響著我們生活的傳統;或各種的宗教信仰等等。本文集中介紹較為人們忽略,但現在似乎又開始引起注意的一種方式,亦即透過身體來構成身體化、總體的生命藍圖。事實上,對身體而言,「生命藍圖」的措詞並不恰當,因為身體化的生命藍圖並不是透過對象化的觀察所得到「視覺圖像」,而是身體從內部感受到的身體活動狀態,亦即人們在具體的生存情境中,身體本身所感受到的、在身體中發生的、整體的震顫狀態。
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的建構方式與知識性的總體生命藍圖的建構方式人不同。知識性的總體生命藍圖是透過「為什麼」的提問和解答的尋求在意識中這構起來的;但身體本身人問為什麼,身體構成意義的方式,是以相應情境作出不同的活動方式來展現的。也就是說身體會相應情境作出不同的反應,而這些不同的反應方式本身,就蘊含著身體對情境的理解。無論是意識所構成的知識性總體的生命藍圖,或是身體所構成的身體化的生命藍圖,對追求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者而言,二者都是同樣重要的。本文所以特別著墨論述身體所構成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旨在起大家不要因為身體化的生命藍圖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建構,並在無識意識的狀態下影響著我們生命的展,而忽略它。
文中分析《莊子》所敘的「心齋」、「坐忘」,來進一步說明古人對於身體化的、總體的生命藍圖有何構想。「心齋」、「坐忘」的身體經驗,並不是一種脫離情境的、純粹心靈的活動,而是可以在日常的行、住、坐、臥當中發生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在日常行、住、坐、臥的當下,關注自己的活動過程,關注自己的身體如何相應外界的人事物來展現如此這般的活動方式;並開始有意識地調整自己身體的活動方式,以「虛而待物」的方式向情境開放,展現應物而動的狀態,恢復身體與情境的直接交住;再則要有意識地開發自己的身體知覺,恢復我們與自已身體的關聯,從內部來感知自己身體的震顫狀態。如此,只要持之以恆,我們自然可以在自己日常的行、住、坐、臥中展現出和諧與平衡的身體震顫狀態,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並活出有審美意義的生命。
行文到此,熟悉傳統中國文化的者或許會發現:中國古代用來教育世之、國子的樂之教中,有許多演習禮議、樂舞的課程設計,這些課程至東周禮崩樂壞之際,孔子還依非常重視,並用來教育平民學生。這種重視身體操演的教育課程,意味著什麼呢?順著本文的脈絡,您或許會回答說:古人的禮樂教化課程,不正就是一套訓練學生如何在各種生存情境中做出理想的身體活動,建構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並開發學生身體知覺的課程(林文琪,20001)?沒錯!有與趣的讀者,不妨進一步去探究中國傳統禮樂教育的實質,或許可以從中解消您閱讀本文帶來的、有關如何建構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的疑惑。
參考文獻
郭慶藩輯(1974),《莊子集釋》。台北:河洛。
〔德〕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Schmitz)著,龐學詮等譯(1997),《新現象學》,上海:上海譯文。
〔美〕瑞尼.威爾菲爾德德著,孫麗霞等譯(2001),《身體的智慧》。遼寧:遼寧教育。
〔法〕梅洛.龐蒂(M.Merleau-ponty)著,姜志輝譯(2001),《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
〔法〕柏格森(H.Bergerson)著,肖聿譯(1999),《材料與記憶》。北京:華夏。
〔英〕尼古拉斯.布寧(NicholasBunnin)、余紀元編著(2001),《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北京:人民。
人生哲学范文篇9
关键词:“成人”教育;儒道人生哲学;互补;融通
“成人”,指人的健全人格的养成。年龄长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人”,只有具备了自觉道德意识和知识、思维能力,再施以教化,才具备成人的德行。冯友兰说:“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底人,才真正是‘中国人’。”[1]因此,“成人”必是中国文化培育出来的人,应从儒道两家的人格养成之道中汲取营养。本文试从人性论、人与社会关系论、人生态度论和人生境界论四个方面对比分析儒道人生哲学,探讨现代社会“严肃又超脱”的成人教育内涵。
一、儒道人生哲学的四元构成
(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首先要把握何为人、即人的本质问题。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从孔子主张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开放式观念,到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主张,总体上是以性善为中心的。儒家虽承认人有自然属性,但更张扬人的社会属性。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因此,孔子围绕人与人的关系确立道德规范(五伦),建立了“仁”学的基础,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似有共通处。与儒家注重社会性不同,道家注重自然性。人的生命来源于“道”,所以人的本性取决于“道”的本性,而“道法自然”,因此人道也要法自然,固守天道赋予之德性。道家多用“真”“朴”来说明生命的德性:“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朴”是一种浑然未分的状态,都指未经雕琢而保有的本然状态。因此,抱朴守真才是生命完成的路径,一切人为矫饰、违背自然天性的行为都会对生命造成戕害。伯乐善治马却几乎将马治死,倏与忽为混沌凿七窍却害死了混沌,都强调天道无为、人性自然,反对人为对自然的改变。(二)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人怎样发挥自己的本性,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适当的位置,是儒道两家都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儒家认为人生活在人伦世界中,人的价值实质也即人伦世界的价值,因而只能在人伦世界中对象化、客体化自身才能实现主体人格。孔子在回答子路怎么做一个君子的问题时,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自我完善要通过发挥在社群中的作用来实现。孔子以“仁”为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3],其核心是爱人。爱人的起点是“亲亲”,再推广到“泛爱众”,前者合乎天性,后者合乎人道。爱人与自爱相互启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忠”与消极的“恕”,构成了爱人的两面,背后的逻辑都是由己推人。道家对社会采取回避趋向。上古社会“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理想的人际关系,人相交则争,不如无交而自得其乐。道家对仁的看法是悲观的,“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仁义道德是自然德性被破坏后的次等诉求,起于人的伪饰。同时,仁义的提倡进一步败坏了人的真朴本性,人为了追求仁义之名而丧身、丧性。注重生命价值的道家提倡,相濡以沫而丧身不如相忘于江湖以存身。(三)对人生方向与处世态度的认识。道家既反对人为改造自然,在处世中必然选择消极的态度,但消极中同样蕴有一种主体性精神,“无为”比之“为”,亦是一种理性选择。道家重身贵生、安时处顺,首先是应对乱世的生存法则。老子说,无为以无不为,避免涉入纷争带来的生命损害,同时得以保持本性。人应尚谦、贵柔,不敢为天下先,亦是依循“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天道逻辑。庄子更关注人道,以生命为最高价值,反对殉利、殉名、殉业、殉天下。从庄子的人生实践来看,他拒绝了楚王的国相委任,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他从“濠梁观鱼”中体会自得之乐,通过“蜗角之争”的故事批判现实,保持了个体的独立性。(四)对理想人格与人生最高境界的认识。儒家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内具最博大的爱人精神,外具安定天下的领导才能。内在修身行仁便能外在治世安邦,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圣王之道有时代性限制,亦非常人所易至,更有启发意义的是儒家境界的日常化诉求。“所谓人生境界,是人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4]这种境界在“孔颜之乐”中得到了呈现,身处简陋的物质环境中,个体精神因学问道德的完善而得到满足,实现了人生境界的超越。道家亦追求“圣人”人格,但与儒家的内涵不同,从而这种人格所抵达的人生境界也有差异。庄子的《逍遥游》以鲲鹏展翅的想象画面描绘了一种无形无碍、游心骋物的自由境界。自由的本源在于无待,即无所依赖,“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伎于众”,排除世俗、外物、他人、群体对自身的约束,才能实现自由人格。功名、自我尤是自由的屏障,无己、无功、无名才是修行的境界。难得的是,道家还提出了抵达这种境界的方式:齐物和虚静[5]。齐物则放弃分辨,回归道之本然的混沌和整一,“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虚静的状态下人忘形去智、物我两泯,才可以体味大道。
二、从儒道互补树立“成人”教育目标
儒道人生观的差异互补足以培养有道德持守而丰富灵动的人,即冯友兰所说“严肃又超脱”,它的现代教育内涵应该包括以下几点。(一)善性与真性兼具,养成主体性人格。儒家主张人性是良善的,但需要巩固培养。孟子说善心的扩充才能发展为仁义之德。人性是发展的,道德是不断完善的,这个过程需要克己复礼,勉力而为。儒家提出了一个人格完善的问题,并终身以之。这明显是人为的努力,是道家所反对的。道家主张不以人为损天然,要保持自然素朴、浑然天成的德性。它是客观的存在,没有善恶的分辨和价值判断。道家尤其指出对德性损害最大的是仁义,它克服了人格虚伪化的倾向。在利益至上、传统道德约束薄弱的现代社会,儒家提出的道德自觉尤其重要,对现代人在义利矛盾中如何抉择具有导向作用。同时,道家的淳朴追求亦能成为人们摒除诱惑、保持本心的护佑。(二)既入群又独立,培养创造力。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人的价值实现应包括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融合。人总是从他人认可中获取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实践勇气,但又要注意过度融入群体以至于消解个性的可能。入群满足归属感,适度张扬自我则培养个体精神和创造性。时代的变革打破了传统“五伦”的格局,但儒家主张的“忠恕”观念,与现代社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共赢的精神相贯通,仍可作为对待人己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外,现代教育应育出“有高尚精神的人性与有原创能力的灵性的人才”[6],前者即适应群体的道德善性,后者诉求于生命本身的创造性。灵性乃自然之性的绽放,发扬人的直觉力、主体性,会产生类似“庖丁解牛”游刃于无间、“梓庆削木”鬼斧神工的创造力。(三)进取与游心,扩充人生内涵。儒家主张积极入世,道家主张出世全生,但根本上二者都追求生命的自我实现。有为的目标会增加行动的效能,也会带来挫败的可能,因此儒家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灵活选择,但真正的仁者是不遗余力的,孔子直到临死还在哀叹道之不行。道家提供了追求失败的补偿机制,虽然它的初衷并不诉诸外求。道家追求游心骋物的自适生存,为生命提供了宽裕的空间,并诞生了审美的内蕴,比如“濠梁观鱼”的雅趣和“庄周梦蝶”的哲思。现代社会,存身不是紧迫问题,人对生命的漠视却成为隐忧,忙碌之余对生活内涵的追求也提上日程。儒道二者不同的人生追求,在现代社会可以转换为不同人生阶段的主题,或是追求过程中心态调整的策略。(四)日常与超脱,涵养生命趣味。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功利性输入社会各个领域,现代生活中充斥着社会化的“有用”之念,也充斥着娱乐化的“无用”之物。“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强调了精心的思致安排,但最终诉求是利益,这本质上还是人生观问题。儒家的入世当然有其世俗追求,外王为其事功,但内圣是其内构。孔子的人生总结,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最终的境界是道德自由为核心的自我实现。还要注意到儒家追求道的日用表现,舞雩台上的俗世之乐是融入了礼乐理想的,而道家予人以超脱,消减“功利心”对人的异化,避免生命沦为逐利工具,实现部分的自由。此外,大众文化和娱乐至死伴随着网络经济愈演愈烈,现代人沉浸于碎片时间和庸俗消遣,也需要用超越性眼光看待,培养不受时代裹挟的个体审美趣味。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33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3]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J].社会科学战线,1989,(1):61-66.
[4]许宏海.论人生境界[J].社会科学,1998,(9):60.
[5]陶东风.死亡焦虑与庄子人生哲学的超越性结构[J].东方丛刊,1992,(4):91-112.
人生哲学范文篇10
理性与经验对立是西方哲学的1个本质,也是对西方哲学的1个基本分类,如演绎与归纳、与综合、先验或抽象与实证等等,但这种对立却正是西方哲学自身的基本框架,西方哲学是以理念、概念、范畴、逻辑等方法表达哲学的,因此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理性意义的,即便是与理性对立的经验仍是用概念、逻辑等方法和形式予以表达的,无论理性或经验都是关于知识或知识形式的,而且总是以知识的形式被表达而成为哲学的,西方哲学就是关于知识或真理的本质、来源、观点、方法等等的理论,经验与理性的对立实际上仍然基于知识或真理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说理性不仅是哲学的对象,还是它自身表达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西方哲学,因此在西方哲学框架下理性与经验即是对立的,也是相互共存的,它们共存的形式仍然是理性的,所有的经验事物只有在被理性意义的形式化之后才能成为哲学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的本质的是理性的,理性与经验的对立仅仅是在他们达到目的的功能关系上,即哲学的观点、方法上,而不是在它们的哲学本质上。西方哲学传统对终极原因的追求就是对终极理性的追求,理性最终是经验的归宿,它们1起被表达为外在于人的知识形式系统,而且最终的知识被归结为神,因此神学的真正本质也是最终的理性哲学,这就是西方文化的1致性,但这不是理性与经验的内在的1致性,而是超验的同构,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就是超验的理性。
理性与经验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西方哲学中己开始得到理解,比如威拉德·蒯因(WillardV。O。Quine1908-2000)在他的名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文中,认为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是1种教条,从逻辑的观点看,这种教条是没有根据的,他以知识系统代替了先验的知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理性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他的这种努力正好说明了西方哲学中经验与理性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克服它。
理性的哲学是基于事物的知识,因此它首先就是关于事物本身的本质意义的学问,因此理性的真正的原始本质是物性,这也就是西方文化中性和客观性的根基,正是在这个根本性的意义上,亚理士多德称他的哲学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因此,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下,哲学是原始地基于物性的理性意义的,因此真正与这种理性哲学的对立不是在它的自身理性的框架下与理性对立的经验,而是与这个理性的框架本身的对立的非理性,在它的根基上就是与物性对立的人性,但他们总是以非理性思潮出现的,而且非理性思潮总是对它当时的西方哲学的现有的框架的突破而表现出1种神秘性或革命性,由于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基于人性自身的框架体系,非理性思潮也无法成为纯粹的专门化哲学,最多被理性化或被理性的哲学所吸收,同时也就失去了非理性的意义。
真正与理性意义的物性本质相对的就是人性,在西方哲学中,没有任何现成的知识和知识形式能够真正正确地定义或演绎人性,它才是真正不在西方哲学的基础框架之内的东西,西方哲学的观点、逻辑不定义它,形式地演绎它,因此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来说,它们总意味意1种突破,1种革命性的神秘,比如文艺复兴就是人性的复兴,它对中世纪的反动就是对神学理性的革命。又比如以人性的观点理解,就区别于从物性的观点理解自然,这正是现代非理性思潮的广泛表现,所以与理性对立的人性就是西方文化中1切非理性思潮的本质。但是如果认为非理性思潮就是本质上反理性,那就完全错了,非理性思潮反对的只是形式化了的理性,或者说是形式化的人性躯壳,非理性思潮在最深刻的本质仍然是理性的,只是西方哲学的框架下无法表现这1点而已,只有在大文化的意义上才能充分解析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非理性思潮的进步意义,无法理解西方非理性文化思潮的革命性,同样在这种观点下,我们才能理解在文化的框架下反文化并不是革命,而是反人性。
人的哲学就是指以人性或从人的本质出发理解世界的哲学,不管实际上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它们都是以人性为世界性。从人的观点理解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理解世界,这是因为世界总是由于被理解而具有意义,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使世界人性化了,世界获得人的意义,承认人是世界的部份或者是的部份是理性的哲学,而认识到世界因人而具有意义就是人性的哲学。中国哲学就是最精湛的人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人是世界的意义,因此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世界不在人之外,世界也就是人的,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互为共存,所以天人合1,因此中国古人无须创世说,儒家文化也不对神异感兴趣,只要有人的存在,世界就当然存在,在这个理解上,我们就能懂得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为什么是西方哲学中的绝响。
如果说儒家的学说是作为人性在人自身上的哲学,那么老子的学说就是人的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在世界最深邃的意义上,老子的学说把世界彻底地人性化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5章)这不是对仁的否定,不是对仁的反动,而是仁的自身在世界意义上的意义上的超越,它也就是本义的道。天地不仁就是天地不异于仁,不为仁,甚至不是作为仁,天地就是仁自身的超越,所以天地也就是仁的自身,天地不在道外,道也不在天地之上或之中,万物就是道的生化流转的形式;圣人即人道,他不是为仁而仁,而是以百姓为化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得到了最真义的表现:道就是无为,无所为而天下为,所以无不为。作为人的哲学,道自为人,人自为道,道不为道,所以“道可道,非道”;人不为道、道不为人,德为人道,所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第3108章)德是现实之道,为德不德,为道不道,而道德并称就是道德互为的超越,道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成为人道意义的普世之道,只有在全人类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是哲学中的哲学。
儒学作为人性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把人的社会等同于全部世界,把社会的本质人性化了,道德化,人伦化了,正是在这个原点上,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本质不是关于或对于世界的学说,而是它自身就是作为人的本质的世界的本质,这是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西方哲学总是关于世界和对于世界的,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和人本主义也总是关于人的和对于人的,而不是作为人的,这是真正理解西方文化1个最本质的观点,也是理解中西文化相区别的基准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自身人性的,所以它就不会以形式化的理性表现自己,而是世界以人性化的本质的存在,这种同1是西方哲学所无法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从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总蒙着1层神秘的外纱的原因。西方哲学的现有框架无法容纳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国哲学没有也不会成为西方哲学的殖民地,也无法从本质上西方哲学化,而从另1方而看,西方哲学却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形式,这正是中国哲学的先天不足,而中国哲学的自身的元哲学精神将为西方哲学的几千年所追求的世界终极原因提供启示。在人类的文化存在意义上,哲学就是人的存在的自觉,哲学与人性的理性化是1致的,西方哲学中的理性化人性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理性化是1致的,人性、理性和文化性的1致性在中西哲学间是1致的,这种1致性是大文化意义的,中国哲学在文化性意义上互补的统1,中西哲学在人性意义上的1致性是世界哲学意义的。
2.唯物与唯心的困惑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企图直接地把中国哲学纳入西方哲学的现成框架的努力总归无法成功,既曲解了西方哲学,也损害了中国哲学。比如人们广泛地以唯心与唯物的方法划分所有哲学,企图在西方哲学的理性与经验对立的基本框架之上建立1种所有哲学之上的划分哲学的方法,虽然唯心与唯物是西方哲学中1个常见的概念,但却并不是西方哲学中的某1个具体哲学,也不是主流意义的哲学的分类方法,西方哲学中没有在“心”与“物”对立意义上的“哲学”思想或专门化的哲学理论,唯心与唯物也不是具体的哲学理论方法,唯心与唯物仅仅是对己有的哲学理论、观点的评价方法而不是自身成为1种具体的哲学观点方法,在西方哲学中甚至没有对“心”和“物”的1致性定义的或可以接受的关于心或物的理论,唯物1词只是在理性意义的物质性的意义上被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唯心1词只在把心灵的或精神的作为世界本质性存在的意义上被使用为对某些哲学的评价,而实际上由于对心或精神不能正确地进行哲学定义而使唯心1词的使用只能由具体的论述(话语权)而决定,而不能由1种可以作为论据的哲学观点,方法现成的引用,因为没有1种是真正自身成为了唯心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只有对现有的哲学的评价观点而没有1种真正的西方哲学意义的唯心的哲学,而且正是由于企图将这种对哲学的1种评价观点在绝对化的情况下当作1种实用的哲学,而因此造成了1种高于所有哲学的哲学幻影,而这种幻影哲学又被绝对化地当作评价所有的哲学理论的实用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仅仅只能在与唯物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唯心这1词,而这种对立性却不是真正哲学学意义的,其实唯心和唯物只是两个文化意义的概念,这是首先是因为“心”是1个文化概念而不是1个哲学概念,什么样的理论是唯心的,实际上只是由这个理论自己的申明或由对它的评价而定,而不能由这个理论自身决定,因为没有唯心的自身哲学学意义的哲学(参见中国思想与元哲学),因此人们只是大量地使用唯心论、唯物论、唯心
主义、唯物主义,而不大直接使用唯心哲学和唯物哲学这样的词,这至少表明人们还是能在它们的使用环境中区分对哲学理论的评价与哲学学两种不同的性质。比如黑格尔的哲学是公认的唯心论,因为是黑格尔自己认定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但这不是也不能由他的理论自身证明,他的全部理论都是由理性框架构成的,他的理论的分析和演绎是确定性和逻辑性的,他的理论结构确实是唯理的,我们甚至还不能说他的理论内容是唯心的,因为所谓哲学理论正是以它的结构为自己的内容,或者说哲学理论的结构与内容是同1的,他的唯心主义只是他的理论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唯心对立性的唯物也是在文化性的意义上被使用,比如人们说亚理士多德的学说是唯物的,不是因为他的理论的唯理性,而是因为他承认客观世界的确定性。这样,当人们说神学是唯心的,实际意义上只是说神学是1种文化,而不是1种唯心论的哲学,事实上神学也只是在唯理的意义上才成为1种哲学。这样1切被称为唯心的东西,只不过说它们是文化性的,不是具有真正的自身意义的哲学。但遗憾的是人们并不是在这种真正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唯心这1词汇,它被社会化了而成为了1种在对立意义上的文化工具或武器,这正是为什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论争会成为1种社会运动的原因。
与唯物唯心概念相关的是形而上学这1词,它的使用也反映了上述这种情况,1方面形而上学就是metaphysics,这正是西方哲学用法中的本义,西方哲学传统中,终极原因总是理性意义的,无论你认为它是物理性或精神性的、先验的或经验的都要是这样;另1方面,形而上学1词又被作思辨或精神哲学的代名词,“形而上者谓之学”,这与中国上的玄学1词意义基本相同,在近现代它进1步与心学这1类概念相关,但是由于中国哲学本身是基于人性的,而且在中国哲学中确实有关于心性的大量,因此形而上学1词就具有跨文化的不同用法,因此不在上下文环境中,你就无法确定它的真正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形而上学还被完全被意识形态化而与唯心论同义的,还被用作为与辩证法的对立面,这实际上已成了标签,离学术研究就非常远了。
唯心论和唯物论在哲学中的生搬硬套,首先对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就是1种错误的肢解,其次,把中西哲学也1起纳入这种形式化了的哲学系统中,更是1种严重的错误,不仅是用预定性的文化具取代了所有的哲学观点和分析方法,即实际上取消了哲学,而且也否定了文化本身。比如把神学和所有具有神秘意义、非理性意义的哲学归结为唯心论而予以拒绝,就不仅是简单地取消了这些哲学,而实际上是否定了真正的人的哲学,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
3.哲学中的人生
以人为本的哲学也是现实中实现的人生哲学,1切有成熟的思想的人,他们对人,人生和世界理解就表现为人生的智慧,而哲人则以哲学为生命,在自己的人生上实践哲学精神,作为哲学家的人生,哲在他们的身上表现为自觉的人性,哲学与人生的统1就是哲人的人生真率,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成为人的最真率的自性,能以个人的自性表现哲学精神才是伟大的哲学家,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人可以举出两个,那就是孔子(551-479BC.)和苏格拉底(469-399BC.)。
苏格拉底洞彻哲学作为真理不等于知识或智慧,它只存在于人们对它的无尽追求之中,所以他以论辩为生,他以对那些以有知识而自大的人的揭露为事业,以问答批驳的方式分析知识而走向真理,这就是本义的辩证法,苏格拉底说他1辈子除了考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并且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以外,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做,他的论辩几乎使当时1切认为是正确的人和事都变成尴尬,雅典人对他的指控主要目的是要他沉默,他也本可以逃脱对他的判决,但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他永远不会放弃他作为论辩的哲学家的人生的职守,因此自觉地以生命的献祭悍卫了他的哲学人生,他是哲学的殉道者,他甚至认为他年老智力衰退将成为人生中的累赘,对他来说不能进行哲学思维和论辨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死刑也就可以使他避免老年的痛苦,(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这种纯粹的哲学人生的感情和对人生意义的洞彻令人感到震撼。
哲学不仅是苏格拉底的人生,而且是他的肉身,这几乎与宗教的起源人的灵肉同1无异,但他是作为常人的哲学家,在常人的视野里他古怪但不失为常人,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真率,他和常人1样生活,但却常常在哲学思考中忘我出神,有1次人们发现他发呆地站立着从清晨到中午,而就有好奇人晚上抱着睡席守着看到他1直站到第2天日出。(柏拉图:会饮篇)饥饿、寒冷、贫穷甚至死亡和其它的生活元素对他来说都似乎是视而不见的,他对肉体的忍受能力可能是1种天赋,但他对真理的追求的哲学精神结合在这种天赋之中,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的融合成就了他不朽的哲学人生。
孔子却是1个作为哲学家的常人,他具有哲人的高尚但不失常人的本性,他对历史与对常人具有同样丰富的感情,对国家与对生活的热爱,对政治与对的爱好浑然1体,他自己的好学求知与对普遍人的教诲都是他的人生责任,而这1切都在他的人生中融为1体,没有做作,没有虚伪,有时不免迂腐但却不失真率,他是1个人性哲学本色的哲人,他的哲理融化在他1生的现实的生活中而不是超然于尘世外。
子曰:23子以为我隐乎?吾无隐乎也,吾无行而不与23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
这是他自白的坦率。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于郭东门,郑人可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比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3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他的天真。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3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得,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论语:述而)
这是他出入社会政治的人生的自由,人生、学问,抱负相为而不相违,进退有地,柔轫从容,他为中国1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士大夫的社会生存方式提供了榜样,而他的1生坎坷造就了他的人生与人性哲学的统1。
毫无疑问,孔子具有1种人性的魅力,仅有他的博学和对历史、国家、人民的责任不足以使他成为圣人,正是他将自己的人生真率地哲学化了,真正地人性哲学化了,实现了人性,人生和哲学的同1,他才是人中之圣,他不仅仅是学问的导师,而且是人性的导师,因学他的学问而成功为官者只是少数,但他以第子3千,贤人7102而被尊为集成和传承中国人性文化的素王,他的人性、思想、学问普及天下。
孔子对人生与历史同样具有1种自性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儒家文化超越地同1于历史。孔子和苏格拉底不同,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人生乃至生命对哲学的奉献而表现了哲学,孔子却是以哲学与人生在真率中的统1而保存、延续了哲学的种子和生命,而这两者正如自然界生命的存在的两种方式1样,都是生命的必要方式,在他们的身上,实现了人生、哲学、社会的1致性统1,而且对于他们这都是真率的和清醒自觉的。
令天的我们发现阅读1些其它哲学家的传记而常常为他们作为常人的生活与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理论并不1致而感到失望时,或者为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无法避免的虚伪而烦恼时,不得不对孔子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伟大人生真率表示由衷的敬意。
$False$
4.人生中的
远非每1个人都有成为哲学家的幸运或者是不幸,但每1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哲学家,当1个人真正开始成熟而自觉时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深刻的人性,常人与哲学家的区别只是职业的区别而不是人性的区别,哲学家是以哲学为职业的常人,而常人也总可以成为自己的哲学家。这里面不存在要不要哲学,或者哲学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自觉到这1点,而且你能在何种程度上自觉,作为1个常人,大多数人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执迷难决,但或许你也有幸能得到两者的自觉,这在传统文化中的出世与入世思想中得到最特殊的表现,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奇丽的人性与人生的浪漫性。
中国思想的超越性是自性的超越性,因而它也可以超越于现实的人生,而在个性意义上对具体现实的超越就是出世文化。儒家文化是由文人即以中国文化的继承、教化为生或为业的人而被具体化、现实化化的,他们就是作为士或士大夫的精神贵族,和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在文化意义上相似但不相同,后者以物质享乐为基础,而前者以精神生活为寄托,但它都成为了1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社会阶层,准备和参与,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遣文化。中国的文人入世就是官僚化,它的另1面就是出世,以退隐的方式进行政治准备或对政治、人生进行观察和反省,这两者总是同时存在士大夫的身上,更替着互为表里,即使位极人臣,也总是在思想深处潜藏着超越自身的出世思想,在文人文化生活中,表现为1种具有浪漫性的文人文化,如返古思想,田园文化,仙佛情操,甚至直接表现为政治性的隐逸行为。隐士是1个古老的中国文化观念,而且始终被视为1种崇高的情操,因为它原初地在个性的人生身上表现了中国文化对现实的超越性。让贤不是政治民主,而只是人性的平等,是超越个性的普世关怀,尧帝许由之让,伯夷、叔齐避世之节己为圣人之先,而孔子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贤者避世,其次避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之类的冷静,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的无奈,恰恰显露了孔子个性中潜藏着的这种文化性本质,但他永远保持着1种对政治的渴望和对文化的看守的责任,更多地表现为1种政治上的中庸文化。在老子那里,这种文化本质则是以绝对的方式表现的,它直接表达为对文化的反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但这只是以原初的理性反对形式化的理性,因此我们总能以超越的解读方式理解这些名言的真正意义,甚在今天我们也能在新的社会现象中叹服他的明智,比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似乎在今天这个以地球为村的高度物质文明完全不合时宜了,但是今天的你又认识几个近在咫尺的邻居呢?
最能表现这种浪漫的个性文化的人是中国的庄子(369-286BC.),他的出世不仅是对政治,而且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特别是以文化生活即文人的人生的超脱,他把人性对物性的超脱寄寓在流丽奇瑰的文字中,塑造了1个不羁于形骸的文人精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5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4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道在他那里得到了的人性化形象,实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道的精神同1,这就是他的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1,”他把道化为了文人的精灵,他成为了在世文人的1种精神寄托,他把文人生活情操,人性的自由与文人的武器——文字完美地结合在1起,表现了中国文化中人性的浪漫,他真接传达了和真实地再现了老子学说中潜在的个性文化精神,给中国文人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庄子还以自己的人生超脱的浪漫性实践了他的文化创造,他为妻子之死鼓盆而歌和庄周梦蝶的故事把残酷的现实与美丽的梦想揉合1起,成为了文人与文学中的奇芭。他的诗1样的文字和神话式的自由想象表达了那种令人神往的超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3千里,抟扶摇而上者9万里。”他以文字表达的流丽和恢宏气势实现了道在文化个性上超越,表达了脆弱的中国文人与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政治雄心同样令人倾倒,但前者具有超越的空灵与自由,成为了中国文人文化的精神象征。
5.人的哲学与西方非理性思潮
人生的哲学在中国文化就是个性向理性的超越,因此它是人性的理性化,而不是反理性的,也不是反社会的,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反理性思潮完全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理性化的社会和理性化的人虽然可以高于人,但这毕竟是理性化和形式化意义上的人,因此它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人自己,而且在它僵死的形式上它甚至成为反人性的,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且下成为人类精神和知识进步的枷锁,在这1点上,这种性质与中国思想的命运相同,中国思想的形式化即是它的表现,也是它的梏桎(参见论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和西方理性的在自己的最深刻的本质上互补地相同,体现了中西文化在人类文化意义上的同1性。理性是人的1个本质。但不是全部,西方文化的主体框架是理性意义的,所以西方文化中总有它所遗忘的非理性思潮的抗争,而且总是以反理性的形态出现的,即表现了它的革命性的进步意义。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绝对的超越验人性,既使是圣人,也是普通人,圣人非神圣,而是在内圣外王的教化中走向完全的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没有产生制度化的民主,但是却有基于人的原初性的平等:“王使人(察)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但这种人性的平等由于没有社会化的制度保证而只能停留在精神文化中,因此它始终无法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中国文化早熟的产物,中国思想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赋予了它,使它强大得足以将中国思想自己囚禁了2千多年而不得自由,是西方的入侵引发了了中国封建的崩溃,中国思想同时失去了自己寄托与枷锁,成为了百年的精神幽灵。
相关文章
生涯理论如何构建满意人生 2022-07-12 14:44:29
高校教育支持对本科生人生目标的影响 2022-01-24 10:11:59
人生教育中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融合 2022-02-25 03:59:15
哲学与人生课程专题教学法研究 2022-08-30 04:09:37
儒道成人教育人生哲学论文 2022-07-24 08:54:12
养成教育对大学生人生规划的作用 2022-07-17 11: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