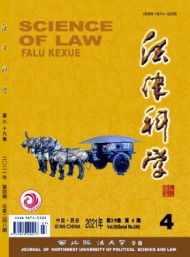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十篇
时间:2023-06-13 17:15:15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1
我国传统的事实观是“客观真实观”,即认为这一事实应当理解为司法应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法律原则所蕴含的“事实”即为“客观真实”的传统法律理念引起的司法困扰已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旨在弱化法院职权、树立法律权威等一系列审判方式改革举措纷纷涌现,理论上的落后成为司法改革的阻碍,确立新的理论的需求已引起众多法律人士的深思。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法律真实的司法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论争最早是在刑事证明标准中被论及的,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上,有论者坚持刑事证明应当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要求裁判者只有在正确反映犯罪事实真相时,才能裁判被告人有罪,即通常所说的客观真实论。有论者则主张以法律所确立的标准作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要达到了法定的裁判尺度,即视为真实并可以据此做出有罪裁判。该种主张通常被称之为法律真实论。[1]由于法律真实理论蕴含了多重客观事实标准所不具备的合理因素,法律真实范围逐渐突破刑事领域,扩展到民事、行政等领域之中,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司法人士的认同。
法律真实概念提出后,即引起了客观真实论者的猛烈抨击和质疑,并进而引起了法律真实论者与客观真实论者的论争。持客观真实论者反对法律真实理论的理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真实是否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础。
从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立法指导思想来看,内含于“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应当是指“客观真实”的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可知论、反映论和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是客观见之于主观,是客观实在在人脑中的反应;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实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是可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对案件争议事实的全面认识是完全可能的、绝对真理最终是能够全面实现的。据此,在案件事实的认识上,应该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法律真实无法代替客观真实标准,因为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真实说都不能成立。”[2]。
主张法律真实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不矛盾。传统的客观真实说所依据的认识论是一种片面化的、甚至被曲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由三个理论要素组成,即反映论、可知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我国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片面强调了认识论的反映论和可知论,却忽视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曲解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这里所说的人的思维,不是指某个单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从人类在整体上、在无止境的时代更迭中所具有的对客观世界的无限认识能力或所能实现的终极认识目标上来说的,并不等于说世界上的事物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完全可知的,并不等于说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客观真理。人的认识符合客观的程度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的。具体到诉讼领域,“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都属于认识的‘个别实现’,都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都是不可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个具体案件来说,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不是‘绝对真实’,都只能是‘相对真理’”[3]。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认识,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对诉讼中案件事实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可能是彻底的、全面的。(1)认识主体的限制性: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法官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出的一种主观判断,这种判断的过程是认识形成的过程。法官作为认识主体,其认识达到的程度与其知识水平、能力素质都是相关的,具有不定性:“诉讼的证明活动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认识的过程,更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的活动。舍弃、抛开法官这一判断主体的主观活动,强调证明活动的纯粹客观性,必然导致认识论上的纯粹客观主义,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4](2)认识对象的限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事实认定,是对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既往性,即诉讼过程中的事实大部分是过去形成的事实,属于的范畴。案件中的事实认定,是从现在确认过去。法官无法亲眼目睹或亲自感知发生在过去的当事人的争议事实,只能由现在出发去发现过去,这种时间上的逆向性,决定了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只能达到有限真实的程度。(3)认识依据的限定性。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依据遗留的证据痕迹来进行。而证据中存储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并不等于客观存在,证据外表真实之外,还有一个证据表达的是否真实的问题,即在证据中也可能包含与客观不符的内容。法律真实是建立在这种证据基础上的真实,因而也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真实。(4)认识时间的限定性。案件的审理过程,对裁判者而言是属于认识上的“个别实现”,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是不可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个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来说,不可能象考古学家那样,花费几十年甚到几百年的时间去寻求事实真相。案件的审理必须在特定的期间内终结,也就是说对事实的认识过程不可能无限延长。对案件事实认定所达到的真理实现程度也必然受到限制,只能是相对真理,而达不到绝对真理的地步。
二、法律真实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
持客观真实说的学者认为:法律真实说并不是一种完善的学说,而且在当前的背景下,这一学说还存在着误导的可能。[5]很多关于法律真实的表述给人的印象是,诉讼过程只是一个将证据材料过滤、整合为法律真实的过程,客观真实不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有的文章甚至认为法律真实并不具有客观性。[6];面对这种倾向,一个严肃的论者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认识论,那么应当如何面对裁判基础事实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说,在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理论中,是否还有客观真实的位置?[7]张志铭在《何谓法律真实》一文中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认为法律真实理论会引起偏离事实真相。“在案件事实认定及其真实性的评价上,法律因素的介入会不会导致对‘案件真实情况’的扭曲、甚至歪曲呢?考虑到非法证据的排除、证人适格性要求、举证时限规定以及审限要求等情况,我们无法不提这样的问题”。[8]认为确立法律真实理论就会导致对裁判认定的事实的客观性的否定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法律真实的理念从本质上说仍属于客观的范畴。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观标准。(1)法律为“法律真实”设定的真实标准是客观的。法律真实承认裁判主体对案件争议事实的认定受主观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案件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接近客观真实的程度与具体的认识主体的知识、能力、经验等主观因素紧密相关;但同时,法律真实并不等同于主观真实,其具有“真实”的属性不在于其是由裁判主体形成的这一主体条件的具备,而是以这一事实认定符合法律设定的可视为真实的标准。有学者认为,“法律真实就是法律规定的真实,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亦即主观的真实”[9]。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法律规定的真实”究竟是一个主观真实还是客观真实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着重于法律规定是客观还是主观的问题。如果说法律是人定的,因此符合人定的法律作为标准所形成的认识就是主观真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人类的任何认识活动都应该说是主观的,因为任何标准的认识或确定都是人类认识的结果。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是既存的,是客观的,不以承担该案裁判职责的法官的意志或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律真实的标准是客观的。(2)法律真实形成所依据的证据是客观的。法律真实的形成是认识主体通过对案件中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的综合判断形成的,不是凭空臆测的。法律真实的形成必须具备相应的证据材料,并以其所基于建立的证据材料的质与量达到法定的条件为必备要素。这些证据材料的内容有些是真实的、符合客观的,有些可能是虚假的、与客观真实不符的,无论这些材料的内容是否客观,证据的存在是客观的,因此,法律真实形成的证据基础是客观存在的。(3)法律真实并不排斥客观真实的实现。认为确立法律真实理论就没有客观真实存在的空间是没有依据的。法律真实本身不是作为客观真实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与客观真实的关系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应该说在很多方面它们都具有相似的或共同的特征。法律真实理论承认在诉讼活动中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法律真实说的学者指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如果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或者说,再没有任何一种主张比这种主张更完美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如何发现客观真实,不知道倾注了多少热情和精力。”[10]只是由于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客观真实的实现不具备现实性,才确立了以“法律真实”作为裁判认定的事实标准。因此,法律真实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真实是否符合公正的理念。
不同意法律真实的学者提出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认为,确立法律真实的事实标准,不符合我国传统的公正理念,因而很难为老百姓所接受。龙宗智在谈及这一时提出:在做理论选择的时候还必须考虑一个实际因素,即特定的文化和要求。刑事案件发生后,人们尤其看重的,是正义在实质上的实现-不让不法之徒逃脱法网,不让善良百姓无辜蒙冤,因此必然要求刑事诉讼不懈地追求实体的真实,而不能将“形式真实”、“法律真实”这类东西拿来搪塞老百姓(这就是中国刑事诉讼难以实现真正的对抗制,法官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超越诉讼双方去发现事实真相的基本社会原因)。[11]主张坚持客观真实说回避了法律真实说那种冷冰冰的法律家逻辑,上述解释显然更容易为普通百姓理解和接受。[12]客观真实论者认为:如果只讲法律真实,不讲客观真实,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司法效应。……如果诉讼中不设定一个较高标准,不设置一个明确的目标(即使有一定的理想化),那么,大而化之、马虎草率的诉讼行为将更容易凑合过关。[13]不可否认,法律真实的事实标准与客观真实相比,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衡量标准存在质和量的差异,法律真实达不到客观真实标准所要求的真实程度,但这是否就可以认为法律真实就会导致司法不公呢、就会偏离法治呢?笔者认为,在前面提出的认为“以法律真实搪塞老百姓”或者“法律真实的冷冰冰的法律家逻辑,群众无法接受”的理由,都是建立在群众所要求的公正即指案件实体处理公正这一基础之上的。我国传统的公正观念对公正的理解认为“公正就是指实体公正”。而通过考察,司法的公正不仅仅包括实体处理的公正,还应当包括程序公正等等,它们与实体处理公正一起构成了司法公正的原则标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传统的公正观念与法治的理念是相冲突的,也不利于法治目标的实现。我国的现实是人们对个案公正的要求远远大于对严格适用游戏规则的要求。对被告的处罚,是合乎法律的,在这一点上公众也达成了共识;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却认为不公正,不讲情理。法官在此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迎合公众对“公正”的期望,法律在这里势必要开一个大口子;如果坚持依法处理,就会被公众认为是不公正的。在此存在着对司法公正认识的普遍误区。(1)司法公正的衡量标准是多方面的,真实不应当是评价公正的唯一标准。对公正的衡量标准不应当仅仅是真实的实现程度,还包括实现这种公正的规则本身。(2)司法公正是一种相对的公正,它的实现有时意味对某些个案公正的牺牲。当案件的事实认定与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不相符,而法院据此作为裁判的依据做出判决时,法律真实达不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对个案的处理来说,对于某一方当事人在实体结果上也许是不公平的,只要它是在坚持司法原则、符合了法定的程序的基础上做出的,对于法的整体效果及社会公众来说,应当被认为是公正的司法,是实现了法律正义的。我们说法律真实的制度是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并不是说它就是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有限性的一面,法律真实本身也不例外。与这种对某个个案实质公正牺牲相对应的是获得了社会整体公正观念的树立和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合理的设置法律真实的实现标准,它将有助于法治和社会公正的实现。(3)正确对待群众是否接受问题。公正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的产生和内容是由法治程度所决定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司法的实践对这种公正信念具有导向作用,重塑公众的公正信念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司法理论还是实践都不应拘泥于传统的或流行的习惯标准,我国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从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不能以传统的人治观念作为否定法治观念树立的理由。(4)裁判的事实认定与客观真实之间差距的实际存在,并不因否认“法律真实”提法、强调“客观真实”的概念就可以抹杀或填平。以弹性的文字游戏来回答这种差距的原因,只能让人对法律的客观性和诚实产生怀疑。与此相对应,“冷冰冰的法律家逻辑”对于群众和社会公正而言更具有说服力和理性。
认定事实的标准的设置和实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标准的设置必须切合实际并且有实现的可能才是现实的,脱离实际的理论只是一种空想的理论;以脱离实际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将失去理论的先导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训。我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的现实是:我国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法律体系正在逐步的建立与完备,社会总体的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的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立足于这个基本上的我国法治建设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不是说我们树立了客观真实的目标,就表明我们的司法工作能够切实实现这一目标。客观真实的理念的建立与我国建国初期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超前定位是相一致的。我国的法治建设应立足于现实,重新选择适合我国法治现状的切合实际的指导理论。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规则和程序,决定了司法证明所认定的事实只能是一种推定意义上的事实,而不必然等于一种客观物质性的事实。“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它给诉讼证明过程提供了一种不的理论解释,而这种解释反过来又对诉讼证明的实践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它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极其微弱。”[14]因此,“客观事实观在实践中不但无法实现而且会带给我们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任意司法、蔑视法律和法治等”。[15]“那种‘必须’达到或‘一定’达到‘客观真实’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实务上是有害的,更是无法实现的。”[16]四、法律真实是否具有可操作性问题。
客观真实论者认为:法律真实是个不能成立的伪概念,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否真实,其标准必须是、也只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法律或任何其它外在的东西,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应该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17]江伟教授提出:“学者对法律真实说的倡导,其意义……不象某些学者说的那样,是提供‘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从操作性的角度,法律真实说等于什么都没说。客观真实起码还对诉讼证明提出了一些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法律真实说认为法官据以裁判的事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即可,这其实是放弃了要求,把一切都推给了‘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这样说并非否定法律真实说的意义,而是为了说明这一学说的意义并不具有操作性。”[18]那么法律真实究竟有没有现实操作性呢?即法律真实能否在具体的案件中得到运用的问题。法律真实论者承认,诉讼认识本身是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标的,但在具体裁判时,只能以客观真实理念指导下的更合乎情理的结论作为提起指控的裁判有罪的标准。法律真实观并不否定裁判者认定的事实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可能。客观真实观更强调诉讼认识结论的绝对正确性,而法律真实观则包含了对此种认识结果可错性的承认。
法律真实对事实认定结果可错性的承认是有现实理由的: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通过证据实现的,证据的完备与否直接决定了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与客观事实吻合的程度,也就决定了认识是否达到客观真实的标准。当案件的证据不能达到完全证明的程度时,法官的职守及裁判规则确认法官“不得借口无从发现证据而拒绝裁判”、“由于涉案证据证明力不足导致案件事实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不得久拖不决,而应径直确定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19]此时,法官无论是否驳回举证方的主张,这种判断都无法证明是绝对符合实际情况的、是达到客观真实的地步的。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2
关键词:法律原则效力标准系谱内容
作者马驰,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天津300134)
自罗纳德・德沃金以法律原则为肇端向哈特式的法律实证主义发动攻击以来,由这一论题引发的讨论几乎构成了半个世纪以来法律理论或法理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围绕着法律原则,已有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相互联系却又具备各自的独立性。第一类研究主要涉及法律的概念,即区别法律规则的法律原则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对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法律概念问题产生何种影响,尤其是,现有的法律实证主义能不能在坚持自己基本立场的情况下,回应与法律原则密切关联的各种责难。第二类研究是有关法律原则的方法论,这类研究基本上已经肯认了法律原则的存在,重点在于,区别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之后,无论它们的区别是何种意义上的,原则究竟在个案判决中充当了何种作用,对于法官来说,它的适用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和特征。不难发现,无论上述哪类研究,在逻辑上必然要以“法律原则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的妥当回答为前提。法律原则的本体论问题是本文讨论的基本范围。我将以法律原则已经存在为前提,检讨其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即其效力标准(criterion of validity)是什么。我力图证明,原则与规则无论在适用方法论上存在多大的差异,也不能简单地说,相对于法律规则系谱的或形式的效力规则,法律原则的效力准则就是基于内容的;此种二元划分简化甚至遮蔽了法律原则效力标准的复杂性,造成了规则与原则之间某些不必要的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在本体论上的差异不应该被夸大。
一、效力标准的含义
在法律理论的研究中,如同很多名词术语一样,效力一词含义并不总是十分清楚。在我看来,人们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使用法律效力这一术语,并以此产生了多种相互区别却又相互联系的效力标准的含义:
其一,效力是法律的约束力(binding force)。汉斯・凯尔森曾提到,效力是法律规范针对其所调整的对象所具有的约束力,一个有约束力的法律也就是一个有效力的规范。①我国现行的某些法理学教科书也采取了此种用法②,“法的效力是对其所指向的人们的强制力或约束力,是法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此意义上,效力标准实际上是法律之所以有约束力的标准或原因。法律效力的此种定义实际上与法律的规范性或权威性如出一辙;尤其是,由于法律的约束力必定是针对人们行动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在实践中表现为人们的行动理由,故当引入行动理由这一重要概念之后,对法律约束力问题的研究已经被有关法律权威性讨论所取代。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必要再使用效力一词来与法律的权威性相以混淆。
其二,在语义学的意义上理解效力④,将效力视为法律规范为真的标志,进而将效力标准视为法律规范的真值(truth value)条件。法律规范要以命题的方式加以表达,作为命题,它或许可真可假,这样一来,一个真的法律命题就是有效的法律,相反则是无效的。命题的真假通常受制于某种条件,这种条件便是其真值条件。例如,“火星上存在生命”这一命题的真值条件是,仅当火星上存在生命,该命题为真。然而,对于一个法律命题来说,称其为真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或许可以借助所谓真理符合论来判断一个事实命题的真假,但法律命题作为规范命题或价值命题的真值条件却似乎难有定论,甚至无所谓真假。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就主张,价值命题无法证实,没有真假可言,当然也就没有真值条件。⑤实际上,命题的真值概念是用来处理命题演算的工具⑥,将之引入法律理论有关效力标准的讨论,对问题的化解并无直接的助益,反而徒增了不必要的争议。
其三,效力是法律规范存在的标志,因此效力标准就是法律规范的存在条件或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效力是法律的存在方式,因为没有效力,法律就不存在了,无效的法律等于没有法律⑦;当我们确定某个法律是有效力的时候,我们的意思首先是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法律。如果法律效力是法律存在的标志,那么效力标准的含义则在于,由于我们不总是任意地判断某一规范是不是法律规范,而是会使用一个或多个标准来对相关规范进行鉴别,这里的标准决定了相关规范是否是法律,这便是法律的效力标准。H.L.A哈特创造性地使用了承认规则(the rule of recognition)这一术语来指称法律的效力标准,在一个社会中,总会存在这样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样的规范能够算在这个社会的法律,即便这一标准的内容在不同社会中会有所差异,不同学者对这一标准性质的认定也有所差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承认规则实际上是法律规范的存在条件或前提。这便是本文所采纳的效力与效力标准的概念。当然,这里提到了承认规则,并不暗示效力标准规则一定是单一的一般性规则。实际上,本文的目标恰是要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具有复杂性。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马驰: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基于系谱抑或内容?
效力标准的这一含义需要与认知标准加以区分。在将承认规则视为效力标准的情况下,承认规则可能被当作法律的认知(epistemic)⑧标准或手段,是获得法律规范这一思维过程的工具。至少在《法律的概念》正文中⑨,哈特将承认规则视为一个单一的一般性规则,例如英国的承认规则是,女王议会制定的就是英国的法律。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一个对英国法律一无所知的人或英国法律的初学者想要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是什么,那么“女王议会制定的就是英国的法律”的确是他们认识英国法律的快捷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规则当然具有认识功能。然而即便如此,也必须区分作为效力标准的承认规则与作为认知标准的承认规则。实际上,法律的效力标准是判断法律本身的合法性(legality)准则,是法律存在的前提与条件,它所具有的认知功能是偶然的。对此,朱尔斯・科尔曼曾举过一个极为有趣的例证⑩:想象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律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法律的效力规则是,“凡德沃金说的即是法律。”这无疑是该社会的承认规则,但对于识别或认知法律来说,最可靠的规则却是,“听拉兹的”,他知道这个社会的法律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效力标准与认知标准是可分离的。不仅如此,当法官进行个案裁判时,判断何为法律,与法律如何适用至个案事实,也可能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活动。在我看来,区分认知标准和效力标准意义重大,很多有关法律原则效力标准的争议其实是对法律原则认知标准的争议,申言之,是将法律原则如何有效这一问题,与如何认知法律原则这一问题加以混淆。也即是将法律原则在适用方法上的争议,看作法律原则效力标准的本体论争议。对此,下文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二、德沃金论法律原则及其效力标准
德沃金对法律原则的界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主导着人们对法律原则的认识。在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中,德沃金认定法官最终使用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而不是法律规则,得出了正确的判决结果。在德沃金看来,法律并不仅仅由规则构成,它还包括原则。而原则与规则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来适用的,如果规则规定了既定的事实,那么当案件出现此种事实时,它就必须被适用;而在没有这种事实出现的情况下,规则对判决不起任何作用。其次,原则具有分量(weight)和重要性的维度,而规则不具有这一维度。在特定案件中,可能适用的法律原则或许存在多个,对于哪个原则应该被使用也常常是有争议的,法官需要对各个原则就个案而言进行其分量的平衡或衡量,才可能得出其正确的判决。原则和规则是否具有分量和重要性维度的这一区别还引发了它们之间的第三种差异,即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当两项法律规则相互冲突时,除非存在调整这种冲突的规则,否则其中一条必定无效――法律的规则体系不能容忍规则之间的冲突。但若冲突发生在两项原则之间,则不会导致原则的无效,无非是,法官此时只需断定相互冲突的原则中的哪一项要更为重要一些。
德沃金之所以要在法律体系中区分出不同于法律规则的法律原则,是为了攻击以哈特理论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其要义在于,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使得法律难以容留法律原则的存在,而法律原则的存在又是难以否认的,因此哈特的理论必须被抛弃。德沃金认为,按照哈特的看法,法律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由某个权威机构颁布,例如由立法机构制定,或是由法官创制的;就此而论,作为法律规则的效力标准,承认规则是一个系谱(pedigree)的检验标准,它只能按照规则的形式或来源来确定或识别法律。如果承认规则是一个系谱规则,那么法律原则就无法通过这种规则进入到法律中。原因是,法律原则并不来源于立法机构或法院的特定决议,而在于法律专业领域与公众当中长时间所形成的妥当感(sense of appropriateness),只有在此种妥当感的支持之下,法律原则才可能作为法律而持续下去。在此种论证之下,德沃金试图将法律原则的效力与道德论证或原则的内容联系起来――法律原则之所以能够作为法律而存在,不是因为它的谱系或来源,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公平正义的,符合某种道德层面的要求或标准。
借助此种论证,德沃金显然向我们提供了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这一标准首先不同于法律规则的效力标准,法律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的系谱或来源,即它是由权威机构颁布的。但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却不在于此,法官在认定诸如“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是法律时,并不会去考虑这一原则系谱或来源,他并不关心究竟是谁或制定了这一原则,他的问题在于,这一原则在特定的案件中是否公平正义,是否能够被某个道德准则所容纳,是否被法律专业人士和公众的妥当感所支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法官就可以认定该原则属于法律。因此,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主张说,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是基于内容的,或者说是基于道德论证的。
仔细考察德沃金法律原则的概念,不难认定,德沃金工作的重心在于司法裁判活动,他主要借助法律原则在适用的意义上与法律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来推断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存在“逻辑上的差异。”然而,如果仅仅依据德沃金的上述论证就得出结论说,判断一个原则是否属于法律原则,确定其内容是否符合特定的道德标准是唯一的方法,以至于主张法律原则唯一的效力标准就是基于内容的非系谱标准,并以此区别于法律规则系谱的效力标准,则是将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简单化和一般化了。实际上,法律原则效力标准需要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三、基于系谱的法律原则
或许是因为竭力将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效力标准归结为系谱规则,以便展开攻击,德沃金似乎没有注意到,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有时也可以是系谱的。即是说,我们可以因为某个原则的系谱或来源,断定其可以作为法律原则而存在。而这种基于系谱的法律原则当然依旧可以满足德沃金的原则概念。对此,至少存在两种情况。
其一,立法机构或其他权威机构的法律文件中确立了某个原则,该原则因为这种确立而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因为出现在有约束力的判例中,因而具有法律效力。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第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平等原则当属于德沃金意义上的原则而非规则,然而,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已经盛行了千年之久,除非能够证明,这种观念在1950年前后突然被社会成员集体放弃,代之以男女平等的观念,否则就难以主张说,该原则是因为法律专业领域和民众中长时间形成的“妥当感”,或是经由道德论证,才成为法律原则的。不仅如此,在成文法系国家,由于人们通常将立法是否有规定视为法律效力的条件或标准,便出现了这种情况:同一法律原则可能既出现在权威立法中,又获得了某种道德论证的支持,此时,主张该法律原则是仅仅基于内容而不是因为权威立法的规定这一观点可能难以得到捍卫。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几乎所有对这一原则的引证或研究都会提到《民法通则》这一权威法律文件原文;至少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中,很难想象,在缺乏该权威法律文件支持情况下,人们能够主张公序良俗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可见其效力标准在于该原则的谱系或来源。
其二,法律原则的效力因社会民众或法律专业人士的共识而获得,但这种共识与道德伦理无关。德沃金主张法律原则的效力必须因为社会民众和法律专业人士的长期形成的妥当感才能被确认并存续,他认为此种共识一定与道德论证存在必然的关系,亦即共识形成的原因在于法律原则内容的道德性,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是基于内容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当然可以基于道德的理由形成共识,并因此产生妥当感。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种共识有时与道德判断没有关联。其实,正是考虑到这种与道德无关的共识,哈特提出了基于惯习(convention)的承认规则理论,认定法律的效力可以与法律内容的道德性无关,而只需依靠法官群体的共识。那么,如果法官或社会民众对某一原则存有此种共识,该共识是否可以作为该原则成为法律原则而存在的充分条件呢?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在诉讼程序中,法官的活动必定要受到法律约束,英美法中的法官在法庭上常常沉默不语,只是居中主持双方律师的法庭辩论或交叉询问;而在大陆法系中,法官要活跃得多,会通过言语等各种方式引导当事人和律师,控制法庭。如果法官在法庭上的活动不符合各自的原则,则被认为是怪异或不妥当的,然而,这种制约法官活动的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在于特定社会中法律群体的共识或惯习,对此并无明显的道德依据,也无需经过道德论证;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人们通常不在这一问题上主张英美法系的法官要比大陆法系的法官更为高明或拙劣。
四、基于道德论证的法律原则
前文已经说明,某些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与规则类似,都是基于系谱或来源的;这并不会否认的确有些法律原则难以按照系谱或来源来决定其效力。对于这类法律原则,德沃金和柔性实证主义的共识是,它们是因为其道德性才构成法律原则的。但这种道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此,我们仍然做更为细致的区分。
首先需要马上澄清的是,道德性至多是此类法律原则效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如果所有道德上正确的原则都是法律,那么所有的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法律原则,这种将道德与法律完全划等号的看法自然是谬见。对此,德沃金认识到,如同法律规则一样,法律原则必定要获得某种制度上的支持,法律原则所获得的制度支持越多,它的分量就越重。然而德沃金马上指出,这种制度支持不应也无法等同于哈特所说的承认规则,原因依然在于,原则的确定需要原则在一系列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交错的标准,这些标准难以被归纳为一条简单而绝对的单一指示或承认规则。无论德沃金对承认规则的上述限制是否成立,都不会影响到这一结论:在单纯的道德正确性之外,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包含了法律制度本身提供的标准。在许多疑难案件中,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案件所涉的法律原则看起来好像只是因为其道德性并借由法官的法律推理而出现的,其中并不涉及制度支持。以帕尔默案为例,从表面上看,适用“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而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好像更加符合某种道德观,于是该原则便是一条法律原则。但这至多表明,由于该案在事实上的特殊性,该原则因此具有道德性,却不能说明该原则仅仅因为此种道德性就能够成为法律规则。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官所做的判决就完全是个道德裁定,他根本无需用法律原则这一说法掩盖自己的道德推理。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在帕尔默中的法律推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抉择,而是对已经存在法律原则进行适用和取舍的过程。
当然,在德沃金对法律原则的认识框架中,毕竟要容纳道德上的正确性作为原则的效力条件;换句话说,至少存在一些原则,对于这些原则来说,其道德性是其作为法律原则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道德论证实际上起到了支持法律原则效力的作用,是其效力标准的一部分。问题在于,此种道德论证是在何种意义上进行的呢?这里争议在于,法律原则究竟是在个案事实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还是说它仅仅是在个案中因为特定的案件事实而获得了道德论证的支持。按照德沃金的看法,这种道德论证似乎是发生在个案裁判的法律推理过程中。这是说,就特定的个案事实而论,适用某项原则要比适用规则或另一项原则更具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因此成为该原则作为法律原则的效力条件。德沃金所反复引证的帕尔默案极易给人留下这种影响。由于原则具有分量或重要性的维度,在帕尔默案中,相对于其他可能适用的原则(例如意志自由原则),“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更具分量,借助这种论证,便可以判断该原则所具有的效力。然而,如果能联系法律体系的观念,德沃金的看法似乎有些太狭隘了。按照凯尔森的经典理论,法律规范的存在前提是另一个更高层级的法律规范。在这一解释框架中,某项法律原则的效力受制于更高层次的另一法律规范。无非是,由于这里讨论的法律原则必须通过特定的道德论证,于是作为效力标准的高层次法律规范内容将出现类似的表达方式:“凡符合公平正义的规范是法律”。无论如何,一旦我们承认法律原则与体现这一原则的个案判决或个别规范之间存在区别,那么就其效力而论,法律原则只要经过了高层规范所规定的道德论证,就已经存在了,无需等到该原则适用至个案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之所以能够认定法律原则的效力,不在于其在某个案件中符合某种道德论证,或是能够产生公正的判决结果,而在于,一个在先的效力标准支持了这些原则。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必须区分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和适用标准或认知标准。在类似帕尔默案这样的疑难案件中,法官的难题是如何适用法律,适用哪一法律的认识论难题,不是判断何为有效法律的本体论难题;在这种适用或认知过程发生之前,相关的法律原则便成立了,而这些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与其是否应该被适用这一问题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否则,我们就难以主张一个法律体系中存在某项法律原则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判断。
如果能够断定,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独立于适用法律原则的个案裁判,以至于法律原则效力在逻辑上先于对该原则的适用,那么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将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当法官判断一项规则是否能够作为法律规则而存在时,其标准在于看它是否符合另一个特定的规则,例如系谱的承认规则;当法官判断一项原则是否能够作为法律原则而存在时,其标准在于看它是否具有道德性,由于这种道德性能够脱离一个具体的个案而存在,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论证一项一般性的原则具有道德性,这其实也就是要证成一项原则作为道德的效力。例如,对于“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来说,效力标准实际上要求法官作出论证,证明在道德上是成立,可以作为一项道德原则而存在,进而成为法律原则。问题在于,这种道德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所谓基于原则内容的,或是实质的,并以此区别于规则的效力标准?这里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伦理学或道德推理意义的上的问题,即一个伦理命题的效力标准或条件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必也难以展开详考,但须重视此种情况:伦理命题有时也可以是基于系谱或来源的。就此,至少存在两种情况。
其一,人们之所以认定某个伦理命题是正确的,理由只在于它是全人类或特定社会普遍看法或实践。在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中,哈特曾通过区别实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和批判道德(critical morality)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而德沃金区分一致性道德(concurrent morality)与惯习性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本身实际上也是作为惯习而存在的。当法官判断一项原则是否属于法律原则时,表面看来,其效力标准在于它是否具有道德性;但此种道德性的标准又在于它是否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或是形成了普遍的实践。
其二,伦理命题的效力标准有时可以因为该道德标准是由某个权威所的。此种情况在宗教气氛比较浓重的社会中比较常见。在这些社会中,无论对于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还是宗教教义,其效力有无的标准都在于它是否来自于宗教权威,例如诸神的意志及其表达,宗教组织所的戒律等。当然,这种情况如果夸张到此种程度,即社会所有行为规范的效力标准都是同一个标准,那么也就很难主张这个社会还存在什么道德、法律或宗教之分了,本文所谓基于道德论证的法律原则效力标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要判断一个道德命题是否有效,须考虑其是否是普遍共识或实践,或是考虑该命题是否是由某个权威所的。仅就伦理命题而论,其效力标准也是基于系谱或来源,而无需对伦理命题的内容加以实质的论证。于是,虽然作为此种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本身要求原则必须经过某种道德论证,但这里的道德论证过程所考虑的仍然是道德命题的系谱或来源,而非其内容。换句话说,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经由一个基于内容的标准,最终指向一个基于系谱或来源的标准。此时,这种基于道德论证的法律原则与基于来源的法律原则,乃至法律规则三者的效力标准,即便在性质上有所差异,但在形式或结构的意义上却极为相似,最终都将诉诸于原则的系谱或来源;无非是,确定此种法律原则效力的方式需要经过一个容纳道德论证的效力标准的允许。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坚持,所有伦理命题的效力标准都是系谱或来源。在上述列明的情形之外,人们当然可以主张说,一项伦理命题成立与否,要对其内容进行实质的道德论证或道德推理。例如,我们可以论证说,“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是因为它符合功利主义这一基本道德原理而成为有效道德原则的。在这个范围内,德沃金本人对于法律原则效力标准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因而区别于法律规则的说法依然是可以成立的。
五、结语
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是多样且复杂的,既不能简单说它与法律规则效力标准一样是系谱的,又不能主张它完全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与原则本身的系谱和来源毫无关联。实际上,某些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也是基于系谱的,而对于另外一些基于道德论证的法律规则来说,除了相应的制度支持之外,道德论证本身有时会指向系谱规则,并以此确定原则的道德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规则与原则的效力标准简单地归纳为系谱与内容的对立,其实质是加大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本体论意义不必要的差异,将是难以成立的。
注释:
①〔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原理》,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②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第105页。
③④⑦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30、128页。
⑤〔德〕石里克:《伦理学问题》,张国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9页及以下。
⑥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⑩Jules Coleman, Authority and Reason,in The Autonomy of Law, edited by R. P. George, 1996,Clarendon Press, P291,293,287.
⑨H.L.A. 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磬、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237页。
Ronald Dworkin, “Models of Rules I”, 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p. 39,22,22,53.
〔奥〕汉斯・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3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纳的是一元制证明标准,即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这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对我国民事诉讼采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学者们在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提出质疑的同时,[①]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应当采取与英美法国家相同的证明标准。英国民事诉讼采取“或然性权衡(proof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的证明标准,或者称“概然性占优”的标准。美国民事诉讼采取的“优势证据(Preponderence of evidence)”的证明标准。但两种标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有在民事诉讼中不实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确立‘盖然性占优势’或更灵活的证明标准,才能真正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及崭新的庭审方式。”[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应当建立一个由多个证明标准构成的证明标准体系,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持此观点的学者比较多。如李浩教授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民事诉讼应当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当能够从证据中获得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其他可能性在缺乏证据支持时可以忽略不计),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在例外情形下,民事诉讼可以实行较高程度的盖然性证明标准。较高程度的盖然性标准,是指证明已达到了待证事实可能如此的程度,如果法官从证据中获得的心证为待证事实有可能存在,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该心证就满足了较高程度盖然性的要求。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适用于民事诉讼中的一般情形,当事人作为诉讼请求依据或反驳诉讼请求依据的实体法事实成为证明对象时,一般都应当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有少数例外情形,才能够适当降低证明要求,适用较高程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少数例外情形,是指那些举证特别困难的案件,实践中一般是侵权诉讼中关于因果关系的证明、关于过失的证明。对举证特别困难的案件,当事人难以提出确切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为缓和证明的负担,才不得不满足较高程度的盖然性证明。[③]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应当继续采纳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批评吸取‘内心确信’、‘盖然性’的合理因素。……在民事、行政案件中,应坚持排除重大合理怀疑,排除其他现实的重大的可能性,对案件事实认定符合客观实际,具有较大的把握度。其中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或根据推定与举证责任规则,尽其调查证据之责,而据此作出判定。”[④]
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应当采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应以‘法律真实’或‘法定真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⑤]“应将法律真实作为民、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定为真实的程度。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对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判断,最终的价值目标,都要实现民、刑事实体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才算完成了证明任务。”[⑥]“民事诉讼必须重新确认一个既能保障民使诉讼任务的实现,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事诉讼证明要求。对此,用法律真实来界定民事诉讼证明要求,用法律真实来说明法院认定的事实”。[⑦]“鉴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本身存在的严重缺陷,笔者认为,应以‘法律真实’或‘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⑧]
第五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采纳实质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实质真实证据制度,即以实质真实的证明结果作为事实已查清的证明标准,才能兼顾司法行为的”效率“与”公正“两大价值目标,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⑨]“所谓实质真实,是指事实本身的真实和由事实求得的真实。在司法证明和诉讼证明中,由于客观真实无法全面达到,因此,实质真实就是能够全面达到的真实中的最高真实。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司法证明和诉讼证明中的最高标准只能是实质真实。”[⑩]
二、对上述建议的评析
上述五种建议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第二种观点和第五种观点。尤其是第五种观点,争议比较大,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笔者认为第五种观点根本不成立,因为法律真实根本就不是一种证明标准。第二种观点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要知道法律真实能不能作为证明标准,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法律真实的含义。关于法律真实的含义虽然学者们的具体表述并不完全相同,但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在阐述时有的不考虑具体的诉讼类型,而有的结合具体诉讼类型罢了。前者如所谓“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定为真实的程度”。[11] “所谓法律真实,是说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完全符合法律所规定或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达到法律标准的真实。”[12]后者如:“法律真实是指,法院在民事诉讼裁判中对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应当达到法律上的形式真实。”[13]“所谓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证明的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真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14]
民诉法学者认为应当将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主要理由是:1,法官的主观判断对案件事实形成的最终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诉讼过程中所呈现的冲突事实,实际上不过是法官凭籍相关证据材料所形成的主体性认识。再现案件事实的真正程度,取决于法官这种主体性认识与证据本身的感触和理解上的准确性、合理性。案件事实的最终确定是法官源自于证据而形成的法律真实。2,通过审查判断证据借以发现案件真实的真相是一个程序的过程,程序的正当性对诉讼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依照程序公正要求,诉讼中所再现的冲突事实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所认定的法律上“真实”的事实,才是程序公正所依赖的冲突事实。3,诉讼中案件事实的形成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在此场景下,再现于法庭上的只是那些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冲突过程中的部分事实,而绝非一切客观事实。4,由于民事权利属于私权性质,国家不加任意干预,由此而导致在证据法中包括举证责任在内的功能运作决定取决于当事人私立救济的能力。在实际中,当事人的证明能力受制于多种客观条件和因素的限制,一旦发生其证明能力与法律上应负的证明责任之间的失落,即便为其主张的事实确属客观存在,但不为法官所认可 。可见,程序上的正当无法保证事实上的绝对公正。[15]
也有学者反对将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其主要理由是:第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法律真实说不能成立。虽然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难以达到与客观事实绝对一致,但绝不能因此就否定客观事实对人们认识的判定作用。因为不是客观事实不能与人的认识完全相符,而是人的认识不能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符。难道认为人的认识不能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另外由人重新制定一个标准就能使人的认识与案件事实完全相符合吗?因此,判断证据事实是否真实的标准依然是客观事实本身,依然是客观真实标准。第二,从法律规范的基本功能来看,法律真实说也不能成立。法律规范的实质就是对一定类型的法律事实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没有真假,其只能是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好是坏,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的标准。而证据事实则是对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基本情况的反映,是典型的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才有真假值。价值判断属于价值论范畴,事实判断属于认识论范畴,两者的认识对象不同,判断标准也就必然不同。我们绝不能将用来判定行为是好是坏,是合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的标准当作判断证据是真是假的标准,反之亦然。既然法律规定或法律构成要件根本就不具备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功能,因此,“法律”和“真实”这两个概念就根本不能搭配。[16]
法律真实到底能不能作为证明标准呢?笔者也持否定意见。但笔者认为,法律真实说不能作为证明标准的原因并不是前述反对者提出的那些理由。前述反对者对法律真实标准的批评没有击中要害,并不能彻底驳倒法律真实说。原因是该学者的两个反对理由均不成立。该学者在第一个反对理由中企图通过树立一个判断真假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信念、命题、判断、语句真假的标准只能是实在、事实、事物、对象,即客观真实-来否定法律真实不能作为证明标准,并且以列宁关于图画与模特的关系的论述作为例证。但该学者却忘记了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任何一个证明标准,其首先必须能够为评判者所把握,具有可操作性。很明显,模特之所以能够判定图画是否与其相象,是因为模特这个客观事实能够为评判者观察到。如果模特不能为评判者观察到,也就失去了作为标准的意义。此时,就只能通过客观真实之外的其他标准来评判了。也就说,判定标准并不具有唯一性。该学者实际上是承认这一点的。因为该学者也承认没有被人为地伪装或修改的模特照片也可以作为评判标准。也就是说,论者自己也承认除客观事实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证明标准。因为,模特的照片与模特本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同理,“实在、事实、事物、对象”等客观真实有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之分。现在的和将来的“实在、事实、事物、对象”因其可以为评判者所把握,当然可以作为一种标准供评判者对“认识、信念、命题、判断、语句”的真假进行评判。但过去的“实在、事实、事物、对象”虽然曾经客观存在过,但却难以为评判者把握。既然评判者连评判标准都无法掌握,如何叫他评判“认识、信念、命题、判断、语句”。打个比方说,用过去的“实在、事实、事物、对象”作为标准对“认识、信念、命题、判断、语句”进行评判就象用一把无形的米尺去丈量土地,叫评判者如何得出具体结论呢?因此,该学者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批评因其大前提不成立,自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那该学者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第二个批评站得住脚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该学者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完全割裂,认为证据事实是典型的事实判断并不正确。实际上诉讼中的证据判断既是事实判断又是价值判断。众所周知,证据具有三性: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其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客观性确实属于事实判断,但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就属于价值判断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说是对证据进行价值判断的典型范例。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68条的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证据能够反映案件客观真实,但因其不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因而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此时对该证据事实的评判明显不是事实判断的问题,而是价值判断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辨明法律真实是不是一个具体的证明标准,首先必须厘清具体证明标准应当具备的两个特征:第一,任何一个具体的证明标准都是对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的具体揭示。因为证明标准是指当事人为说服裁判者相信其主张,对其主张形成心证而必须达到的最低证明程度。具体的证明标准的任务当然就是指出这种程度具体是什么。如当事人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还是应达到“证据优势”的程度还是其他。第二,作为衡量当事人证明行为的具体的证明标准,必须与当事人的证明行为相分离。也就是说,评价的标准与评价对象应当相分离,就象长度需要丈量的木棍和用来丈量该木棍长度的米尺一样。
法律真实有没有具体揭示证明应当达到什么程度呢?没有。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定为真实的程度。很明显,法律真实并没有明言这种程度具体是什么,而是转而求助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那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没有规定应当案件事实的证明到什么程度呢?考察一下就可发现,实体法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应当将案件事实证明到什么程度,只是通过构成要件规定了具体的证明对象。比如,根据一般侵权归责原则,有四个构成要件: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以及违法行为。当事人在一般侵权诉讼中只需证明这四个事实即可,无须证明其他的事实。很明显,实体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只能是证明对象而不是证明标准。
那程序法对此有没有作规定呢?对此需要作详细分析。程序法对证明的规定应当说非常全面,对证明主体、证明手段、证明方式、证明标准等一般都有明确规定。其中证明主体、证明手段、证明方式等都是法官认定事实的前提条件,证明标准则是法官认定事实的标尺。在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具体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也没错,但这与根据具体证明标准认定案件事实并无实质区别。假如,程序法规定的具体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替换一下的话,法律真实的定义就变成了“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定为真实的程度”。法律真实既然自己就是一具体的证明标准,其内涵的揭示又怎能再借助另一个具体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呢?因此,法律真实定义的荒谬性非常明显。如果程序法中没有规定具体证明标准的话,根据程序法的规定来确定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就更无从说起。
如果进一步考察对法律真实说的论述,就可以发现法律真实说的支持者们对法律真实的理解并不相同。法律真实或(1)被理解为待证对象、或(2)被理解为法官最终认定的裁判事实、或(3)被理解为有别于证明标准的证明要求,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评判当事人证明行为的标准。第一种情况如,某法律真实说支持者认为实现法律真实,诉讼证明活动只须紧紧围绕实体法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所谓实体法事实指对于定罪、量刑有决定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包括:(1)犯罪事实是否发生;(2)犯罪行为是否是嫌疑人、被告人所为;(3)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4)行为的动机、目的;(5)影响量刑轻重的情节(包括从重情节、加重情节、从轻情节、减轻情节和免除刑罚情况);(6)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包括身份事项、责任年龄和有无前科。如果为了解决程序问题,其法律真实实现只须紧紧围绕程序法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所谓程序法事实是指对于解决诉讼程序问题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例如,关于回避的事实,关于耽误诉讼期间的事实;关于影响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程序违法的事实;执行的事实;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等等。[17]
我们知道,证明标准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实现问题。只存在确立问题和适用问题。即立法者应当确立怎样的证明标准以及证明标准确立后,法官如何根据证明标准确认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成立。当事人在进行诉讼证明时确实无需对全部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只须对实体法和程序法所规定事实的有无进行证明即可,但这并不属于证明标准问题,而是证明对象问题。因为围绕什么进行证明和证明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法律真实真是证明标准的话,则无论当事人证明 的是实体法事实还是程序法事实,都应当达到法律真实所要求的程度。
第二种情况如某些法律真实说的支持者明确将法律真实看作是证明的结果,而不是证明标准,并且这一结果是根据其他证明标准判定的。“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诉讼中发现的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真实’,但是,对于这种法律真实如何认定,‘排他性’标准并没要彻底解决问题,‘排除合理怀疑’才应当是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18]换一句话说,该学者的意思就是根据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认定的事实不是客观真实,而是法律真实。另外有些学者也是一方面大谈特谈“应以‘法律真实’或‘法定真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另一方面在论及应当确立何种证明标准时,又主张确立盖然性证明标准。[19]很明显,他们所谓的法律真实是指符合证明标准后为法官所认定的事实,其本身并不是证明标准。
第三种情况如有学者主张,“在确立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后,我们还应该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对此,我同意多数学者的意见,应该建立高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20]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将法律真实作为一种证明要求而已,而不是将其作为证明标准,证明标准须另行制定。
退一步讲,如果承认法律真实是一种证明标准的话,将会引起新的混乱,将会重新出现一元制证明标准的局面。因为民诉法的学者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采此证明标准,刑诉法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也应当采此标准,行政诉讼法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也应采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那么,法律真实除了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还可以作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于是,证明标准只能又回到一元制证明标准的局面。但打破证明标准的一元制,是很多民诉学者的主张,也基本上获得了共识。既然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有别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毫无疑问,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实现不了证明标准多元化的目标。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一个由多个证明标准构成的体系。笔者完全赞同。但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具体应当包括几个证明标准,对这些个证明标准应当如何命名,这些证明标准具体应当适用于那些证明对象,学者之间显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李浩教授认为包括两个: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和较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有学者认为包括三个: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特殊侵权案件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家事案件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21]与英国的“灵活性证明标准”、美国的“清楚的、可信赖的证据标准”相类似的中等证明标准;较盖然性权衡程度稍高一些的证明标准和高度盖然性标准。[22]
三、笔者的观点
由于裁判者不能绝对地认识清楚案件事实,因此不能以客观真实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同时为了保证裁判的公正,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不能太低,即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相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没有形成优势时,不能认定该方当事人的主张。还一句话说就是,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盖然性的下限不能低于50.因此,从盖然性的角度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处于50(不包括50)与100(不包括100)之间。
在确定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盖然性的区间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一个还是多个。笔者首先认为民事诉讼应当建构多个证明标准,而不是一个。这是因为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包括多个: 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证据事实、外国法和地方性法规、经验法则。这些证明对象有些制约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能太高,即存在一个最高的证明标准;有些着制约着它不能太低,即存在一个最低的证明标准。最高的证明标准与最低的证明标准之间存在一个幅度。这个幅度内还存在一个中等程度的证明标准。因此,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肯定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正是这多个证明标准构成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具体是多少个呢?笔者认为应当是三个。最高程度的证明标准、中等程度的证明标准和最低程度的证明标准。之所以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确定为三个,一方面是因为证明标准不能太多,太多不便于裁判者适用;另一方面是因为证明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程序法事实与证据法事实、一般的实体法事实、特别重要的实体法事实以及外国法规、地方性法规。由于证明标准受制于证明对象,既然证明对象有三大类,无疑,应当有三大类证明标准与这些证明对象相对应。
那应当怎样称呼这些证明标准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三个证明标准都是以盖然性为基础,区别仅在于所要求的盖然性程度不同。因此,在命名时,所采概念一方面应当能够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另一方面还应当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故笔者建议将它们分别称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最高程度的证明标准);较高程度的盖然性证明标准(中等程度的证明标准):盖然性占优证明标准(最低程度的证明标准)。
这三个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通过下图加以形象化:
其中,A:最低程度的证明标准
B:中等程度的证明标准
C: 最高程度的证明标准
注释:
[①] 对一元制证明标准的质疑,可以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以下。杜闻:《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②] 王圣扬:《论诉讼证明标准的二元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第142页。
[③] 参见李浩:《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0页。
[④] 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22页。
[⑤] 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⑥] 韩象乾:《民、刑事诉讼比较论》,《政法论坛》1996年第2期,第49页。
[⑦] 刘道华:《应确认法律真实的民事诉讼证明要求》,《法律适用》,1997年第4期,第11页。
[⑧] 彭晓冬:《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118页。
[⑨] 陈珺:《实质真实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中国律师》2002年第10期。
[⑩] 裴苍龄:《制度证据法典刻不容缓》,《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4页。
[11] 韩象乾:《民、刑事诉讼比较论》,《政法论坛》1996年第2期,第49页。
[12] 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页。
[13] 刘道华:《应确认法律真实的民事诉讼证明要求》,《法律适用》,1997年第4期,第11页。
[14] 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第117页。
[15] 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8页。
[16] 参见张继成、杨宗辉:《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9页以下。
[17] 参见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中国 法学》2000年第1期,第118页。
[18] 锁镇杰、吴宏耀、陈永生(《刑事证据前沿问题研究》,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卷,第189页。
[19] 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第128页。
[20] 苗加佳:《论法官判案以“事实为根据”—兼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资料来源:.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4
关键词:刑事证明;刑事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层次化建构
一、证明标准之内涵的反思
关于证明标准涵义众说纷纭,现择其一二分析如下。有说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的要求”;[1]有说其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了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程度”;[2]还有说其是指“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须达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3]上述关于证明标准的说法分别从不同侧面强调了证明标准的部分本质内容,但也有其亟待完善之处。第一种说法没有指明证明主体和证明达不到标准时应否承担责任;第二种说法没有指出证明主体和证明标准的法定性;第三说法将诉讼主体视为证明主体,有引人误解之嫌。其实,证明标准既非程度,也非要求,它是刑诉证明必须达到的标尺和准则,是衡量证明结果的参照物,是卸除证明主体的证明责任的分界线。
笔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所须达到的程度上的具体标尺和准则。如上所述,证明标准是尺度、参照物和分界线,然而其是否至善至美而没有必要去探讨呢?笔者认为不然,正因为其处在衡量证明结果、卸除证明责任等关键的尺度和分界线之位,更有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探析的必要。故笔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量互变规律”,即质、量和度三个维度进一步探析证明标准。
二、证明标准的“质”:标准性——法律真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使它区别于他事物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即为质。即质和事物的存在是直接的同一。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质,丧失了自己的质,它就不再是自身而变成他物。”而刑诉证明标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是因为刑诉证明标准也有其自身存在的“质”。刑诉证明标准的“质”是什么呢?这需对其进行的定性的探析,实际上,就是笔者所提出的证明标准的标准性,即一切刑事案件所要达到和遵循的原则和定性的标准。
正如田口守一所言:“随着近代合理主义的兴起,开始通过人的理性发现事实真相。因此,形成了一项原则: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依据。”[4]在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有“证据材料——证据事实——待证事实——法律事实”之说。其关系详述如下:案件事实均不同程度地留下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便是司法机关获取案件信息和查明案件真相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在证明过程中通常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整合,符合通说“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便被整合为“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系统,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各要件或情节,并能排除各种合理解释的差异和矛盾,同时能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即证据事实通常在法庭辩论阶段,在刑诉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整合下,证明待证事实达到在法律上的意义,从而成为在法律上得以认定的事实,即法律上的事实或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正是“诉讼中所呈现的并最终为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乃是经过证据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调整过的、重塑了的新事实”。[5]“案件判决只能以法律事实为依据,客观事实具备唯一性,而法律事实则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证据及主审法官判断的变化而变化”。[6]“法律事实实际上是强调了法律的作用,在一定程序上说,是法律程序自主产生的,即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将公民的各项诉讼权利落到实处,通过公民的参与所发现的事实”。[7]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事实层面上具有基本内容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在刑诉中,不存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客观事实,所有的事实必须在进入刑事程序之中的证据的基础上,并且依照法定程序推论出来,即在法律规定的机制和标准上得出关于事实的结论,也就是法律事实,而其应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8]“如果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观念的表达的话,那就是让价值在事实的认定中发挥作用,而这里的法律事实也就具有了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9]故在法律上衡量待证事实查明与否,论证主张成立与否和证明责任卸除与否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证明标准的“质”即证明标准的标
准性,就是证明待证对象是否达到在法律上具有意义——法律真实。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标准性,是一种原则性标准、定性标准和从各具体证明标准中抽象出来的标准。
法律真实是指“在发现和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必须尊重体现一定价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在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时,即可定罪量刑,否则,应当宣布被追诉人无罪”。[10]所以,法律上的真实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其可接受性“包含了和客观事实相一致的极大可能性,也包含了通过程序而获得的正当性,还包含了国家为平纷止争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并不是单纯地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性情况”。[11]它也有别于“实质性的、客观存在的、本原性的、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和被法律剪裁,框定下来的范围较为狭窄的真实”。[12]法律真实不同于事实真实,前者强调真实的本原性和法律性,后者强调的只是真实的本原性;法律真实不同于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法律真实是真实的实质性和形式性的有机统一;法律真实也不同于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法律真实强调真实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有机统一;法律真实也不同于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以上正是笔者从法律真实的起源和本质上对之进行的论证。
笔者从不同时代的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特征出发,将法律真实分为原始的法律真实、传统的法律真实和现代的法律真实,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传统的法律真实和现代的法律真实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依据封建制国家的法律,该法律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体现,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和保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广大劳动人民成为诉讼客体;后者依据民主制国家法律,该法律是广大劳动人民意志体现,维护其利益并使其成为诉讼主体。第二,性质不同。前者只追求证据事实反映的形式合法,以形式上的真实代替了实质上的真实;而后者是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的完善地有机统一,并统一于法律事实。第三,适用的目的和方法不同。前者从有罪推定出发,并把被告人的口供视为“证据之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者的意志和利益;后者从无罪推定出发,重证据轻口供,是为了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尤其是保障无辜。第四,前者强调形式真实,忽视甚至排斥法官对认定案件事实与审查判断以及运用证据方面的主观能动性;而后者则不同,其吸取了传统法律真实尤其是证明标准法定的形式上的法治精神的合理内核,舍弃了法官不得依法自由评断和取舍的机械操作,同时,它给这一合理内核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现代法律真实将证明主体由法官扩展到公安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将法官的职权由机械地操作扩展到依法主观能动地居中裁判;将证据由形式规定扩展到形式规定和内容规定的有机统一。一言以敝之,它强调了证明主体的结构合理性、法官职业的独立性和法定内容的完备性和科学性。
三、证明标准的“量”:标准化——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及其层次性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量是事物的规模、发展速度和程度以及它的构成成份在空间上的排列结合等可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量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直接同一的,相同质的事物可以有量的区别。认识事物的量是认识的深化,是把相同事物区别开来的依据。证明标准的“量”即标准化是认识证明标准的深化,是把证明标准的“质”即标准性——法律真实可用“量”即标准化加以区别建构,即证明标准的“质”即标准性——法律真实的构成成份一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在空间上的排列结合方面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此处标准化是一个相对量化和宏观上量化,而不是一个绝对量化和微观量化,否则,充满活力的法律真实便退为形式真实,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证明主体便成为机械识别法条形式的机器,似有回到传统法律真实之嫌。
如前所述,证明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证明过程是主观思维活动和具体法律行为的有机统一的过程,证明标准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所要达到的标尺和准则,则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证明标准的“质”即标准性——法律真实也有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之分。主观法律真实是指发现和决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证明主体在尊重体现一定价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时,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世界具有法律规定的意义,即法定的真实性,其能保证有关的人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将主观任意性降到最低限度。客观法律真实是指在发现和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必须尊重体现一定价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时,认定案件事实的客观依据具有法律规定的意义。
首先,主观法律真实是人的意识、观念外在化和法律化,即人的头脑反映案件事实的精神活动以及心
理活动的总和,包括意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达到对案件事实真实性认定的法定标准。刑诉证明过程是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过程,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3]即若思维或认识能够用来改变世界,则就具有真理性。其次,主观思维活动结果是否具有真理性,看其在程序正义基础上能否根据零碎的证据材料和系统的证据事实,将待证案件事实和诉讼主张整合为“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等等而构设出来的”法律事实。使待证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主观思维必须达到法律上有意义。最后,主观思维活动具有规律性和价值性。对认识过程来说,存在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并统一于社会实践。主观思维活动过程和抽象的、普遍的、分散的法律规范合成为一个具体的、有机的、系统的法律规范,由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法律意识上的主观思维活动过程统一于符合程序公正的刑诉证明实践,因此主观思维活动过程也就具备了主观法律真实的价值意义。主观真实往往“以主观上认为其为真实为满足,尽管人在确认实质真实的时候,其主观状态也表现为主观上相信其为真实,但主观真实往往不是指这种情况,而是认为世界乃人的感觉的组合,人只能就自己的感觉依据经验进行判断,当自己相信其为真实则确认其真实,至于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则因不可获知而不必考虑”。[14]综观主观真实与客观法律真实的实质性、真理性、规律性和价值性可知,它们完全不同。
关于证明标准层次化建构的总体设想,一方面是主观法律真实层次化建构。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国家和国际性组织的法律文件对主观法律真实标准具体落实到对“疑”作出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关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的法律文件就有如此规定。1984年批准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规定:“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15]其“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是要求证明主体在主观思维上达到绝对确信,或者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在英国法上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初期。开始要求如对被告定罪量刑,须有明白的根据。以后曾用各种不同的术语,用来表信念的程度。最后仍有疑字作标准,即所谓‘合理怀疑’,亦即须信其有罪至无合理之怀疑。到19世纪初期,流行一种典型的说法,就是由于良知的确信,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16]但根据“疑”的程度不同即有‘量’,上的区别,故笔者认为,主观法律真实应建构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有确实证据的推定和证据不足而存疑”[17]四个层次。其中证据不足而存疑有其自身的丰富内容和确立的必要性。有罪与无罪之间的“疑罪”,在司法实践中,确属疑难杂症,是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感到棘手的问题,对“疑罪”的处理,法律已有明文规定,但现实中对法律明文规定也有作变通处理的。更有甚者以此为借口,徇私枉法,而法律上未有为主观法律真实在“疑罪”上作出判断而规定其参照标准,这在客观上也为少数人枉法裁判打开绿灯。基于此,确有建立“证据不足而存疑”标准之必要。
另一方面是客观法律真实层次化建构。与上述主观法律真实层次化建构相适应,笔者认为,客观法律真实应建构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主要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有确实证据推定事实清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个层次。关于层次化建构的具体内容及每一层次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刑事证明的“度”(即现代化)的论证,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再详细论述。笔者试图强调,不论从哪一视角来建构层次化的证明标准,均不能采用纯主观或客观标准,而要将二者结合考虑,否则难免给人以主观定罪或客观定罪之嫌,也难免给人以人文主义或物文主义之感,只有在主观法律真实和客观法律真实有机结合达到对应的标准,才真正达到法律真实之标准,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刑诉法的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目的。
【注释】
[1]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3]卞建林:《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4](日)田口守一着:《刑事诉讼法》(中文版),法律出版社2000年
版,第217页。
[5]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6][7][8][9][10][11]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第214页,第206页,第208—209页,第214页。
[12]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8期,第14页。
[13]姚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4]转引自齐树洁、吴旭莉:《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证据制度的完善》,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二卷,第590页。
[15]陈光中、郭志嫒:《量刑公正与刑事诉讼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6]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2年版,第665页。转引自樊崇义:《落观真实管见》,《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5
内容提要: 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价值评判和利益衡量以及要件事实与行为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决定着立法者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摄取和规定。“法律真实论”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以此指导司法实践也是有害的,因此,应当坚持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由于诉讼证明标准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即追求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诉讼证明标准应为一元制。
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诉讼证据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具有高度的理论性与抽象性,学术界一直对此存有较大的学术分歧⑴,由于问题的紧要和分歧的重大,因此,探讨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至今仍然不失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实体法律规范下的要件事实
(一)为什么是要件事实
在探讨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诉讼证明标准是针对什么而言的,也即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问题。于此,诉讼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一样具有共同的终极指向对象,因为,证明责任的适用前提是证明对象尚未达到证明标准而出现真伪不明的情况(从这一个角度来讲,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是针对同一终极指向对象而对立适用的两个概念)。
大陆法系国家的裁判采逻辑的三段论推理,其意旨是,法律规范采取“行为模式十法律后果”的基本逻辑结构,将法律适用看作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的运用。其中,作为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的构成要件是大前提,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相符合的特定案件事实是小前提。根据确定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通过三段论的逻辑方法,推导出裁判结论[1]。即:TR(具备T的要件时,即适用R的法律效果),S=T(特定的案件事实该当于T的要件);SR(关于该特定的案件事实,适用R的法律效果)[2]。大前提中的“T”,在法理学中又被称为“行为模式”,一般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并不是实际行为本身,它并没有实际行为中的具体细节。”[3]具体的、特定的案件事实“S”是否符合“T”的要求,取决于法官的价值评判。
由于理论具有高度抽象性,为便于理解笔者试举一例以图说明得直观明了,如“夫妻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则应判决离婚”这一法律规范,“夫妻感情破裂”为T,“判决离婚”为R,但作为S的特定案件事实比如“夫妻分居两年以上”是否符合“夫妻感情破裂”的T,则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
在诉讼中,作为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应为具体的案件事实(主要事实),即三段论推理中的S。在日本,法学界对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并未加以区别,而是作为同样的概念适用[4]。“证明责任的负担只需限于主要事实,因为只要对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确定,法院就能够决定是否适用实体法规,进而作出裁判。”[5]间接事实与辅助事实不是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因为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并不是法律规范三段论推理中的小前提(即上述的S),仅有间接事实或辅助事实的存在并不足以认定主要事实即要件事实的存在,因而也不能适用SR的逻辑推断。
因此,这些刑事实体法律规范和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要件事实是否存在是确定刑事被告罪行是否成立和民事被告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本依据,因而是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
(二)影响要件事实立法的因素
立法者何以对此法律要件事实和彼法律要件事实进行规范,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立法者对人们行为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以及立法者对人们某种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认识。
首先,立法者对人们行为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决定立法者对法律要件事实的摄取。“立法者总是将能满足统治阶级需要或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行为规定为具有正价值,通过其确立的法律规范予以保护;将不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阻碍社会发展的行为规定为负价值,通过其确立的法律规范予以惩罚。”[6]例如,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律要件事实为被告人不能举证说明其巨额财产的具体合法来源,其立法价值在于国家的廉政制度不允许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又如,在司法判例中逐步确立的《民法》中的共同危险,法律之所以规定实施共同危险的当事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主要目的在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即在不清楚具体侵害人的情况下,宁由共同危险人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至于使受害人得不到救济,以求得双方利益之平衡。在这些情况下,立法者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共同危险”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加以摄取(类似的还有在刑法中被废除的“投机倒把罪”等等)。
其次,对人们某种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认识也影响立法者对法律要件事实的摄取。如《尚书·梓材》中记载:“奸宄杀人,历人宥。”这表明在此之前,歹徒杀人,过往的行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过路的行人与歹徒杀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因果联系。又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旦出现重大的天灾或瘟疫,离群索居和行为怪诞之人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再如,在古代社会,以“针扎面人”之类的咒人方法致人生病或死亡也被视为犯罪,这是由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针扎面人”之类的咒人方法与被咒之人的生病或死亡具有因果关系[7]。在当时的情形下,“行人的过往”、“离群索居、行为怪诞”和“咒人方法”成为当时立法者所摄取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
二、诉讼证明标准:要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还是实然结果
(一)应然要求和实然结果的区分意义
研究诉讼证明标准问题,其次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作为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标准,这种标准到底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还是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实然结果。因为,有学者曾对诉讼证明进行应然和实然的区分,指出诉讼证明的应然要求即诉讼证明的目的为客观真实,而诉讼证明的实然结果即诉讼证明的标准为法律真实,目的为应然,标准为实然。⑵
明确诉讼证明标准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还是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实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理由在于,应然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并不会因为存在反例而丧失其正当性,因此,司法裁判中的个案不符合这种应然要求并不能否定这种应然性要求本身的正确性和正当性[8]。于是,在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上,不能从司法裁判中个案认识的实然结果对应然要求的背离而获得舍弃这种应然性要求的正当性依据。
(二)诉讼证明标准为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
在1990年代之前,学者们一般将证明标准称为证明任务或证明要求,“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或称证明要求,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标准。……我国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9]
依照一般的术语界定,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10]尽管有学者对证明标准和证明任务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指出证明标准是具体的裁判尺度,而证明任务是抽象的诉讼理想,认为证明标准作为衡量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尺度,是证明任务是否完成、证明要求是否达到的参照物,但任务和要求并不等于标准本身,证明标准与证明任务、证明要求是不能混用的概念[11]。笔者认为,即使有区分证明标准与证明任务或证明要求的必要,但是有一点是应当承认的,即证明标准是证明任务或证明要求的具体外化,证明任务或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设置导向,其追求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
可见,从词义和逻辑内涵来理解,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对司法者认识案件事实的一种应然的要求。
三、“法律真实”的观点及批判
(一)“法律真实”观点的由来考证
“法律真实”学说正式出台的重要标志是樊崇义教授在2000年第1期《中国法学》发表《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文(该文正式引致客观真实学说与法律真实学说的交锋)。比之稍早的文献可见于毕玉谦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一书[12]。在此之前,则可见于李浩教授的《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一书[13]。
在笔者的有限阅读范围之内,祖国大陆最早主张法律真实观点的学者当为顾培东教授,他在论述“冲突事实的真实回复”时指出,“在诉讼中所回复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况的实际事实。后者如果不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加以体现就不产生法律上的后果;而前者则是事实因素与法律机理共同结合的产物。诉讼中所回复的冲突事实必须符合于法律和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所认定,在法律上‘真实’的事实就是程序公正所仰赖的冲突事实。”[14]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可谓后来“法律真实”观点的雏形。
(二)“法律真实”观点的内核概括
所谓“法律真实”,就是“裁判中对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为是真实的程度”[13]。从“法律真实”观点提出的初衷考察,其精神内核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诉讼程序对原始事实(或自在事实)的评价,原始事实应当符合于法律和形式的规定。其逻辑结构为:原始事实(或自在事实)符合法律的规定、经过法律的评价法律真实。其精神内核首先在于,这种自在事实应当受制于法律和诉讼程序的评价。
其二,在诉讼中所回复的事实只是法律意义上真实的事实,而非原始状况的实际事实。“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法律上视为真实的事实。”[15](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其认识论的基础是哲学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
其三,法律真实观点认为“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法律上视为真实的事实”(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其本质是从案件事实认识的实然结果出发,而不是从案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出发,即认为裁判中所认定的事实在实然结果上是法律上视为真实的事实。
(三)对“法律真实”观点的批判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由于“法律真实”观点的本质是从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实然结果出发,那么,这种认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实然结果是法律真实的观点是否能够成立呢?笔者认为即使如此也是同样不能成立的。
1.在法律规范的逻辑功能上不能成立
法律规范的功能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价值上的指引,引导人们实施具有正价值的行为,同时对人们所实施的具有负价值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和处罚,法律规范本身并不具有评判某种行为是否真实的功能。
就法律规范而言,其本身仅具有价值判断即所谓好坏的问题,而并不具备事实真假的判断功能。“价值判断只能是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好是坏、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的标准。而证据事实则是对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基本情况的反映,是典型的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才有真假值。价值判断属于价值论范畴,事实判断属于认识论范畴,两者的认识对象不同,判定标准也就必然不同。我们绝对不能将用来判定行为是好是坏,是合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的标准当作判定证据是真是假的标准,反之亦然。”[6]判定某种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存在与否,应依赖于证据材料,而非法律规范。
2.夸大了法律规范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许可性
如上所述,“法律真实”学说遵循这样的逻辑思路:原始事实(或自然事实)符合法律的规定、经过法律的评价法律真实。
“既然作为判决根据的事实是在诉讼程序中形成的,事实形成的过程自始至终受法律的支配,那么,与其说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诉讼前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毋宁说是法律上认为真实的事实。”[13]法律真实论认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从自在状态到获得法律上的许可和评价,即上升为法律上的真实,笔者认为,这夸大了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法律许可性。
3.认识论的基础为不可知论
“法律真实”观点的认识论基础是对可知论提出质疑,“作为认识活动,要受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支配。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尽管就人类总体而言,其认识能力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但就处于特定时期的某些或某个人而言,却只有相对的,非至上的认识能力。”[15]对于此,我国著名诉讼法学者陈光中教授对“法律真实”学说的认识论基础有着精辟的概括:“法律真实论认为客观真实不可能实现,因而是不科学的,应当以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我们认为不承认客观真实,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不可知论。”[16]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那段经典论述,并对之作科学的理解。恩格斯说:“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讲,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他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17]我们仔细分析品味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人们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矛盾是从人们认识的宏观和整体方面而言的,但并不是说人们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确定性和绝对性[16]。我们认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也就是说原始和自在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如果这一点被否认,必将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很大的混乱。
在西文中有“absolute fact”一说,意为“确凿事实”[18]。《布莱克法律词典》对“absolute”一词的界定是“conclusive and not liable to revision”[19]。意为“不容置疑和不可推翻”,此处所指的也是人们对事实认定的确定性和绝对性。可见,作为“法律真实”学说重要立论基础之一的不可知论是难于成立的。
4.在本质上是形式真实理念
法律真实论者主张,“只要司法证明活动遵循了正当合理的程序,就是说在证明形式上满足了真实性的要求,那么其在实质上也就具有了真实性。在诉讼活动中,程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其自在的独立价值,而且这种价值的实现和保障比实质真实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司法证明只要保证形式或程序的真实就可以了。”[20]对此,有学者总结,“法律真实就其主流与程序真实要求一致,因而其本质属性是程序真实。”[21]
我们认为,这种涵盖在法律真实思想中的“形式真实”理念是可怕的,上述法律真实论者以“形式真实”代替“实质真实”的论调可以说是对传统重实体轻程序弊病的一种矫枉过纵。古今中外,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或许存在着一些事实认识手段的谬误,但是追求实质真实的诉讼价值目标应当是一以贯之的。
5.不利于“疑罪从无”观念的树立
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裁判者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作出肯定性评判的认识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对诉讼证明中作出肯定结论的要求。具体地说,即刑事诉讼中作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民事诉讼中作出某一诉讼请求成立的结论,……,这些结论所根据的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必须确实、充分。”[9]“在证明标准的概念中,需要强调的是,刑事证明标准是作出有罪认定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至于作出无罪处理本身是不需要达到什么证明标准的。”[16]
但在这个问题上,持“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观的学者曾经列举一个案例。某城市巡警在午夜拦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并且在其后架上的麻袋里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该男子解释说,他在一个垃圾堆上见到这个麻袋,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想驮回家看看。而关于女尸,他一无所知。警察不相信他的“鬼话”,便带回公安局讯问。经过一番“较量”,该男子“供认”了自己强奸杀人的“事实”。但是后来在法庭上,被告人翻供,声称受到了刑讯逼供。法官经过对看守所有关人员的调查,认定被告人确实曾经受到过刑讯逼供。在本案中,公诉方除了被告人口供笔录和证明被告人曾经在深更半夜骑车驮着一具女尸的证据之外,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被告人强奸杀人的证据。对于这一案例的分析,该学者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法官判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都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基础,而这些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显然不能等于案件中的客观事实,显然不能达到客观真实的标准。换言之,法官判被告人有罪,不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法官判被告人无罪,也不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因此,本案判决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律事实,本案判决所达到的证明程度或水平只能是法律真实。”[20]其实,在这个案例中,诉讼证明标准应该是对被告人强奸杀人作出有罪认定的标准,而不是作出无罪的标准问题。正是由于尚未达到对被告人有罪指控的证明标准,所以只能无罪释放。
诉讼证明标准指的是裁判者对待证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存在作出肯定性认定的证明程度要求,而不是裁判者对待证的案件事实作出否定性认定的证明程度要求。因此,通过以上的分析还可以肯定,法律真实论者把这些未达到证明标准的事实不清的案件也称为是“法律真实”,这不利于司法实践中树立刑事被告人“疑罪从无”的观念。试想,假设某人由于杀人罪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这仅仅意味着他的无罪只是一种法律上视为的“真实”,而这某种程度上又是不是“疑罪从有”和“有罪推定”思想的复苏呢?!
6.消解司法者追求案件事实真相的内在动力
由于法律真实论者以某种程度的不可知论为基础,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持消极态度,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思想很容易消解司法者追求案件事实真相的内在动力。一些经过司法者的努力原本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案件,容易在“法律真实”理论外衣的包装下被放弃,成为司法者拒绝作出进一步努力的理论工具,以“程序真实”为由掩盖原本可以查明的案件事实真相,造成司法不公⑶。“现在,司法部门的某些人很赞赏‘法律真实论’及‘程序真实论’,因为这不仅可以为其降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提供根据,而且,由于‘法律真实论’及‘程序真实论’倡导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真实’,甚至可以为完全不讲理的司法裁断提供根据。”[22]
四、坚持与发展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
从考察历史上各种不同证据制度时代的诉讼证明标准以及客观真实现实性实现的可能性出发,可以认为,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是科学的,应当予以坚持。
(一)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在历史上是一以贯之的
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理解为是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的具体化,那么,在历史上的不同证据制度时代,司法者追求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一以贯之的。
在远古的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科技比较落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水平有限,因此诉讼存在着一些神灵裁判特征。但是,在古代,无论是占卜还是宣誓,都有其适用的前提和条件,即只有当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之时方求助于“神”,神灵裁判只是在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的一种补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仍然要讲究证据。如王充《论衡·是应篇》:“觟(同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适用的条件为“其罪疑者”)“诉讼制度中虽存在神判残迹,但仅适用于极少数无法找到证据的案件。……法官对证据不足的疑案无法判处时,便让位于‘神’来作出判决。”[10]“并不是神判主宰诉讼,在诉讼中还是要讲究证据的。公民之间发生了难辨是非的争端,需要找了解情况的邻居出庭作证;发生了土地纠纷则取出官家保存的地图证明;因财贷涉讼应以双方所订契约为证。”[23]
我国著名的诉讼法学者徐朝阳先生认为,我国封建社会证据判断以审判官的自由心证为主,“古代采自由心证主义,可无疑义。”[24]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下,证据的证明力交由法官自由判断,在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况下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应当注意,这种自由的判断仍然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一是要求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原则时必须站在客观立场并遵循逻辑和经验上的一般法则,二是法官必须叙明根据和理由,三是通过一些证据和判断的规则影响法官对证据效力的判断,进一步保证法官判断的客观性。“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⑷
西学东渐,随着立法制度的正规化,要求司法官追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法上得到了明确的规定。1907年12月4日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39条规定:“公判时,遇有下列原因可即时判决:……二、因被告人无故不到案者,原告人申请结案,经审判官查明原告之证据确凿可信者。”此处的“即时判决”即指对民事诉讼中原告权利的认定。1911年《钦定大清新律》中的《刑事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被告如无自认供词而众证明确凿无疑即将被告律定拟。”此处规定了对刑事被告人定罪的“确凿无疑”要求。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明确宣告:“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1914年4月5日教令《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第32条规定:“遇有下列情形,得为缺席判决:……二、民事被告人票传二次,无故不到案,原告人申请结案,经县知事或承审员查明原告人之证据确凿,可信其请求系属正当者;……”1914年4月4日司法部令《地方审判厅简易庭暂行规则》第2条规定:“简易庭所管案件,应具备下列条件:一、犯罪事实,据现存之证据已属明确者;……”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司法官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诉讼证据制度理念是一致的,均追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真实。
(二)证据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关联性使客观真实成为可能
英国著名证据法学者斯蒂芬(Stephen)指出,“有关联性是指两个事实之间的联系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按照事件的正常趋势,其中的一个,自身或与其他事实结合在一起,能证明另一个事实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存在或不存在或者使另一个事实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存在或不存在成为很有可能。”[25]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之间存在关联性的证据能够印证过去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发生与否。例如,作案的工具、所得的赃款赃物、犯罪嫌疑人的供认等证据能够环环相扣地印证犯罪嫌疑人曾经实施的犯罪行为;借贷的契据、资金的来龙去脉等证据能够环环相扣地印证当事人之间曾经发生的借贷法律关系。凡此等等。谚语“官凭印信、民凭契约”是证据能够印证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朴实表达。
笔者承认,由于特定历史时期证据手段的局限,判断或认定证据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错误。例如,在亲子鉴定的案件中,古代是利用“滴血认亲”的证据方法加以认定,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则采用更为科学的DNA鉴定方法。当然,应当承认的是,这种证据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之间关联性认识上的错误应当是不占主流的。
因此,可以这样概括:诉讼证明的应然要求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诉讼证明的实然结果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在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和极少数证据手段错误的情况下除外)。
(三)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出路
只有在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得到查明的情况下,才能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或者对民事权利主张者的权利主张作出认定,然而并不是所有案件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都能够得到查明,在实然结果上达到客观真实。在这种情况下,刑事诉讼的疑罪从无和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已经能够解决这种困境。
在审理已尽而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仍然不明之时,刑事诉讼要求从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对这样的疑罪作出从无的判决。至于真伪不明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在哲学本体论上是个什么状态已无法确定,同时亦非所问。长期以来,传统极端的客观真实理论在个案的认识上机械地套用了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人类整体认识的至上性和无限性一面,这就很理所当然地在理论上否认了真伪不明情况的发生。
民事诉讼领域中,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也解决了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在审理已尽而仍然真伪不明的困境。应当指出的是,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利裁判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是相辅相成的,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利裁判只能被理解为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例外和补充。自主张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来,有学者片面地强调了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把法官调查证据的职权与证明责任对立起来,认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证明责任的本质,法官不必依照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就承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证明责任制度的本质从裁判方法论意义完全演变成当事人的风险负担,证明责任成为漠视正义的理论工具。”[26]
(四)法律推定没有违背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
在民事法律中,存在着一些法律推定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法院对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或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2年而根据利害关系人申请可作出的宣告公民死亡判决;又如,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所规定的关于有相互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时间先后顺序推定,等等。
如何看待这些法律推定的性质,这些法律推定是否违背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在于:首先,这些法律推定是立法者处理一些特殊情况的特殊方法,其立法指导思想往往是遵循特事特办(ad hoc)的原则;其次,这些法律推定的规定是以事实发生的高度概率为其立法基础,某些情况下法律甚至允许这些法律推定为实际发生的事实所推翻;最后,应当正确地对待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有一般和特殊,过分地强调特殊而否定一般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在司法审判中,查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当为一般状态,而运用法律推定并不是常态。可见,法律推定并不构成对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的背离。
五、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元制
学术界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另一个重大分歧还在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为一元制,反之,如果不相同则为二元制。
现阶段,持二元制的观点在学术界几乎有“一边倒”的趋势。⑸其主要依据在于:首先,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纠纷性质不同,前者往往涉及人的生命、自由等等,而后者则通常只涉及财产问题,财产问题的重要性与人的生命、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其次,市场经济讲求效率,民事纠纷往往要求快捷地解决,在这种要求下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刑事案件。
笔者不赞同这种二元制的观点。理由在于:第一,诉讼证明标准为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而非实然的结果。第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纠纷性质不同,以及民事纠纷解决的效率要求,这些方面不能得出民事诉讼中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认识从“应然”上有所差别。从应然上而言,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要求司法者查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真相,即追求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这是对司法制度公正性要求的本质使然,“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观是司法价值观中的第一要素,这是不容置疑的。”[27]而查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真相无疑是实现司法制度公正性的重要前提之一。
当然,笔者承认,在进行实然处理的时候,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有所差别。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民事纠纷存在着处分权,实然上是否一定要查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可以听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司法者也可以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但这种状况在刑事诉讼中一般是不被允许的。
总之,由于诉讼证明标准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因此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在实然的处理上,民事案件可以与刑事案件有所区别,但这并不是由于作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应然要求的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本身所致,这一点是应当明确的。
否定法律真实并坚持客观真实理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之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司法裁判应不应该认识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存在、能不能够认识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着实紧要。如果笔者的上述论述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尚能够成立,那么这实在是法律真实和二元制论者的千虑一失以及笔者的千虑一得的结果。
注释:
⑴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之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否一致,即一元制抑或二元制之争。
⑵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准确地讲,在作者的语境中,诉讼证明标准是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实然结果,即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实然认识结果为法律真实。但遗憾的是,学术界似乎尚未对诉讼证明标准到底是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还是实然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
⑶在《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一书中,肖建华教授开篇即以“回归真实:民事诉讼法的真谛”为题,对当前民事司法实践中淡化发现真实的审判权缺位与失范进行了反思。(参见肖建华.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5.)
⑷在我国封建时期,为了保证审判官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最大限度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如规定审判官违背据证定罪的责任、审判官违背直接审理原则的责任和审判官断狱“出”“入”的责任。(参见刘春梅.自由心证制度研究——以民事诉讼为中心[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93.)
⑸代表性的文献参见:前引[14],毕玉谦书,第125-128页;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223-230;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90;王圣扬.论诉讼证明标准的二元制[J].中国法学,1999(3).等等。
[1]章恒筑.《要件事实原论——一种民事诉讼思维的展开》,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页。
[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01.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3.
[4]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50.
[5]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425.
[6]张继成,杨宗辉.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J].法学研究,2002(4):27.
[7]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1999(5):55.
[8]吴宏耀.诉讼认识论纲——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9.
[9]陈一云.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14.
[10]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96.
[11]徐静村.我的“证明标准”观[C]//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12.
[12]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6—78.
[13]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38—240.
[14]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93.
[15]李浩.论法律中的真实——以民事诉讼为例[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3):17.
[16]陈光中.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J].中国法学,2001(1):23.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6.
[18]宋雷.英汉法律用语大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
[19]Bryan A.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Seventh Edition,ST.PAUL,MINN.,1999.7.
[20]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J].法学研究,2001,(6):36.
[21]宋世杰.证据学新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38.
[22]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J].法学研究,2004,(6):18.
[23]田平安.民事诉讼证据初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40.
[24]徐朝阳.中国古代诉讼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32.
[25]沈达明.英美证据法[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6:20.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6
这种评价标准是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对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的特点是利用外来的参照物来评价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工具主义程序理论认为,法律程序不是作为独立的和自治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它只有在对于实现上述目的有用或有效时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外在的目的和手段主要是指实体法的目的,例如,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和抑制犯罪这一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减少人类的痛苦;而刑事审判程序的惟一正确目的就在于确保上述刑法目的的实现。就工具性程序价值理论的评价标准而言,它始终无法回避法律程序的道德性问题。第一,如果法律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在追求实体真实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各种工具和手段?如果这个标准成立,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利用刑讯逼供等非人道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第二,认为法律程序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工具反过来会损害实体法目的的实现。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做法得到支持,那么用不人道方式取证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由于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基于各种原因而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所有的公民都可能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待遇。对某个具体的案件而言,这似乎达到了实体法的目的,但从整体而言,结果却是相反的。
二、根据法律程序进行判断
这种评价标准认为,评价法律程序的惟一价值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好的品质,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有用性。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的形式是否公正,二是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尊重。
程序的形式公正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一套具体的行为规则来约束程序主体的行为第二,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所有的程序参与人都知道程序的运行过程,程序以外的其他公众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了解程序的运行情况;第三,程序的主持人中立;第四,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具有排它性。
程序参与人的人格尊严标准由如下几个方面组成:第一,当事人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行为对程序运行的结果能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二,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地位上的平等;第三,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当成手段;第四,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就这种评价标准而言,它存在着无先天不足。首先,人们参加法律程序的目的一般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至少是不想受到损失),人们不可能不追求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因此,仅仅靠法律程序本身来证明其合理性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其次。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要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法律程序本身是无法充分保证其运行结果的公正性的。例如,如果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是不公平的,那么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就很难保证是公正的。人们不可能长期容忍一项总是产生不公正的裁判结果的法律制度。
三、以程序正义为标准进行判断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教授认为程序正义就是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标准口](。根据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论述,程序正义可以分为三类: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存在一个判断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第二,有实现这种正确结果的途径,比如说,几个人为了平分一个苹果,让负责分苹果的人最后一个拿苹果就是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例子“平分”是评价的独立标准,“分苹果的人最后一个拿苹果”是实现平分的正确途径,但是,现实生活远比分苹果复杂,因此,完善的程序正义是相当罕见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存在一个判断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第二,不存在或是无法找到实现这种正确结果的途径。例如,刑事审判过程中,有评价审判结果公平与否的客观标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犯罪人得到应有的处罚),但很难找到能完全实现这个结果的有效途径,因为时光不可能倒流,我们不可能回到案发当时的现场,所有的证据都只能帮助人们尽可能地模拟案发现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因为实现正义与公平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整体的道德诉求,但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的途径是很难找到的。此外,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还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它有可能掉人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的深渊。因此,上述两种程序正义不可能成为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标准。
纯粹的程序正义也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不存在判断结果是否正确与否的独立的标准;第二,存在某种程序,只要按照这个程序运行,不管出现什么结果,这种结果都是正义的。例如,人们在购买体育时,只要摇奖的过程中不存在舞弊的情况,不管结果如何,它都是正义的。
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巨大实践优点就在于: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中任何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4](由于不考虑各种其他的特殊因素,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问题,因此,应用于司法领域,它就表现为法治。因此,谷口安平教授所说的程序正义应该是指纯粹的程序正义。
以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判断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前提下,所有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正义与公平的原则,所有的法律都体现了正义与公平的原则。程序法所规定的法律程序当然也符合正义与公平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以“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标准,事实上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设。
四、根据法律程序的要素进行判断
法律程序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产物,它确实存在一个由谁制定,为谁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律程序确实存在与一般的社会道德水平是否相符的问题到底符合什么要求的法律程序才是正当的呢?笔者认为,必须在法治建设的大环境中,通过对法律程序的各个要素的具体分析来进行判断。
1.正当的法律程序主体
程序主体是指在法律程序的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而所谓的“正当”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程序主体的设置必须符合权力分化理论的要求。在法律程序中,各个程序参与者都必须在程序中发挥作用,都只能享有部分的权力,即任何程序主体都不能享有独断的权力。第二,在程序参与者中,必须存在对立面的设置。从一般意义而言,人们总是因为某种利益冲突或利害关系而参与到程序中去,因此,在程序中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应该是互相对立的。第三,必须存在独立的程序裁判者或程序的主持人,由他来判断和评价当事人的行为,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结论。
2.正当的主体行为
主体行为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程序的主体能够依法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能够依法独立地行使权利或职权既是程序主体行为正当性的体现,同时也是追究不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或权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第二,程序主体的行为除合法外还必须合理。这首先要求程序主体的行为有法律的依据;其次,程序主体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最后,程序主体的行为必须合理,即符合一般的社会道德要求。第三,主体的行为必须产生法律上的后果,包括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在法律程序的运行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的程序行为都具有法律上的意义,都必须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合法行为必须得到保护,合法行为产生的结果必须被法律所承认;二是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惩处。这种违法行为既包括双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也包括程序主持人或程序裁判者的违法行为。
3.正确的行为时序
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定结合是法律程序的显著特征之一。正确的行为时序主要有如下几个要求。第一,行为的时序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例如在有些法律程序中,听证是一种前置程序,如果把这种听证程序后置或根本不举行听证,就违反了正确的时序。这种行为不但不会产生积极的法律效果,行为人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如果美国的警察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如果没有遵循“米兰达规则”,那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一般就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5]。第二,行为的时序必须符合人们的直观正义的要求。例如,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对案件的审理必须按照“先审后判”的时序进行,既不能“不审而判”也不能“先判后审”。第三,程序运行的各个环节之间必须有合理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主要是给程序主体在每一个环节开始前都有一个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合理时间。
4.正当的程序运行规则
合理合法的运行规则是体现正当法律程序的正当性的主要指标之一,它也是产生正当的程序结果的必要条件。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正当的程序运行规则包括合理合法的回避规则、公开规则,等等。回避规则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任何与法律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人都不能成为其中的裁判者或执行者。公开规则要求法律程序主体的行为必须公开透明(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例外),杜绝暗箱操作。比如在诉讼程序中,对案件的审理必须公开地在法庭进行(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除外);任何有可能影响法律程序的最终运行结果的有关证据都必须要经过当事人的公开质证;允许其他社会公众旁听,等等。
5.正当的程序结果
一般而言,人们参加法律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公正、公平地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因此,法律程序的运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这里的“正当的结果”有特殊的意义。第一,这个结果是严格地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得到的结果,具有合法性。第二,这个结果是经过严格并且严密的逻辑论证所得到的结果,具有合理性。第三,如果这个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那也是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例如,在刑事诉讼中,虽然程序被严格地遵守,据以定案的法律事实已经证据确凿,法官也在严谨地执行法律,但是判决的结果仍然有可能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法官定案的根据是由有合法证据支撑的法律事实和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人们不可能回复到过去的时空现场,因此,所有的科学实验与论证都只是对过去事实的一种模仿与猜测,都有可能出现错误。
与其他判断标准相比,通过法律程序的组成要素来判断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正当的程序主体是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前提。我们只能在一个法治比较健全的民主社会里来讨论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只有在法治社会中,才会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主体。其次,正当的主体行为是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关键。正当的主体行为还必须有正当的行为,否则法律程序也会失去正当性。再次,正当的时序与正当的运行规则是实现正当的法律程序的制度保障。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必须要被公众所认可,这既是法律程序符合一般社会道德水平的直接体现,也是充分发挥正当的法律程序的社会作用的关键。最后,正当的程序运行结果是正当的法律程序运行下来的必然的结果。这个结果也许和公众的期望值不符,甚至相反,但是由于整个运行过程所具有的合法性、合理性,它也会被公众所接受和认可。
参考文献:
[1]徐亚文.程序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美)罗尔斯.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5]樊崇义.正当法律程序文献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7
一、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与认识
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公民可以对法院、法官的任何裁判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是公民权利对司法权力的一种制约。而在现实社会的审判中,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人们是如何评价司法公正?我们讨论的既然是司法公正,公正与司法有关,就离不开的尺度和标准,同时公正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又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的一般认识。因此,认识和评价司法是否公正,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一是法律标准,二是社会标准。
法律标准是指人民法院的裁判,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违法的裁判一定是司法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裁判适用的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自然派生出的实体法律标准与程序法律标准是两个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可分,具有各自独立判断价值尺度的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必须并只能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人民法院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裁判也就是公正的。适用程序法律是否公正,则只能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
社会标准是指舆论、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在社会群体对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进行的评议中,往往采用的是这一标准。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必然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
有鉴于此,应当如何正确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我们认为,要正确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首先应当正确认识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法院的审判权特点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作一些探讨,对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加以了解,进而理解,很可能对裁判结果的公正问题就有了另外的看法。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国诉讼法的审判程序,凡较重大案件,法官审判时依法都要组成合议庭,由3至7名法官组成,他们始终在一起共同审理案件,一样了解案情,适用同一部法律作出裁判,但在合议庭评议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如何具体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合议庭组成人员——每名法官的意见却常常是不同的,一如裁判结果公开后,社会、公民对它或赞成或批评一样。因此法律规定: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裁判。哪怕“多数人”中有的是对相关法律还不熟悉的人民陪审员。这表明,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正确与否、公正与否,无论从实体法的原则规定看,还是从程序法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的规定看,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只能如此、唯一和绝对的;再如在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中,有的被告客观上确实偿还了原告债务却没能索回欠条,而原告据此欠条起诉被告索要欠款,在此情况下,法官应当如何认定案件事实是一个关键问题,是追求上的事实真相还是依据欠条进行法律上的事实认定?毋庸置疑,法官只能依据后者判令被告偿还债务,这看起来是法官没有追求案件的事实真相,判了‘错案’,似乎不那么公正。但依据证据规则和法律,法官唯有如此判决,才能维护整个法律制度不被破坏,以牺牲个案利益来维护整个法律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事实上,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完全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由于司法活动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诉讼规则的确定性,法院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予以判断并认定案件事实,通过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它与客观事实有所不同,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既可能存在重合的一面,也可能存在冲突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正也是相对的。再如在美国辛普森谋杀案的审判中,控方向法庭提供了辛普森在作案时所戴、遗留在现场的带血迹手套,而法庭因警方在没有被告人在场的情况下,翻墙进入被告人家中调取证据,违背了证据的合法性,对该证据没有采纳,从而判决辛普森无罪。而在该案以后的民事赔偿诉讼中,因民事赔偿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证据证明标准,被害人家属获得了巨额赔偿。能够理解的理由是,如果判决辛普森有罪,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警察的非法取证将得到法庭的认可,从而带来美国整个法律制度的混乱。从以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只能是相对的,任何法院所作出的裁判,其实体的公正性也是相对的。我国虽实行成文法制度,但法官也同样享有无可争议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机关虽有依法办案的严格要求,但是任何法律,不论其规定的多明确、具体,都要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刑法为例,绝大多数条文所规定的均是一个或数个量刑幅度,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节及各种因素确定适用某一个量刑幅度或在某个幅度内确定相应的刑罚都是合法的。因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要追求案件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往往是不可能的,如在民事审判中,即使是胜诉的一方,也有可能认为法院在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赔偿的份额、财产的分割等问题上存在不公。而事实上,法院判决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确,我们有时无法求得实体判决上的绝对公正。基于此,学者们早已理性地把司法的绝对公正概括为司法程序的公开与公正。程序合法正当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作为看得见的公正,这应当成为我们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
通过对人民法院实体裁判公正相对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正确评价司法公正确立了理性的基准。那么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应当采取何种标准?让我们首先一下评价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必然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譬如“广大人民群众”有多广大?一县一市中的大多数?即使有最的民意测验,获知的结果也只能接近客观;其次,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每起案件都是社会的一个矛盾对立面,对于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可能有公正和不公正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司法公正的评价,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上关心裁判结果的公民、组织可能基于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因素而对裁判结果的评价不一致;而在社会主体对司法公正的评价过程中,因其法律素质、法律水平的差异亦往往对同一案件评价各异,在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视法制栏目中,律师和现场热心观众往往对同一判决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常常是律师认为判的公正,而观众认为判的不公,究其原因,律师采用的是法律标准,而观众因受自身法律素质的局限,评价出于普通的生活逻辑;在以上情况下,社会主体对司法公正评价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听到社会上对一项裁判结果有不同意见,提出批评甚至指责为司法不公,我们至少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但以此作为评价司法公正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
那么,应如何认识和把握上述两个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笔者认为,在法治,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标准是基本的也是根本的标准,应当成为评价司法公正社会标准的基准。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别无其它任何可以行使审判权的机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这就表明,人民法院裁判的正确与否,最终认定的标准只有法律。但事实上,对于权威的、作为人民意志根本体现的法律,社会有时甚至常常并不把它作为一个评价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因此,法院司法必须依法,社会评价司法活动也应当以法律作为依据。否则,同一案件,同一裁判结果,由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标准衡量,就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公正也就失去了“公正”的标准。我们应当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作出的任何判决,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做出的裁判,且程序正当,就是合法的,以法律标准来判断,裁判也就是公正的。
二、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社会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是对司法权力的一种制约。然而近年来,对司法的程序外监督不断升级。程序外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现象。但是,由于程序外的监督大多是从普通的生活逻辑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结果的合乎正当性,而司法的过程却是严谨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审判过程的合乎正当性,这就使得司法人员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法律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督司法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和对立,损害了司法权威。所以说对此我们应当冷静下来,深入地思考不负责任地谈论、评价司法公正所必然涉及和负面到的审判权威、法律权威、法治秩序。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司法公正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可能产生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威;人民法院的审判没有权威,必然就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也会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 如若没有这种尊重,法律,这一正常情况下引导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有效力的手段,就将失去它对这一发展的影响”,而这个失去了法律影响、规范和引导的社会,怎么可能是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因此,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在任何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执法体制。
毋须回避,我们的制度环境还不足以使法官做到完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我们的法官还没有完成职业化过程,我们的学术也没有完全能为法官司法提供智识上和技术上的支持,等等。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法官们承受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官们更多的困难(包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可以想见,没有任何一个本身需要公正(帮助)的人会(帮助)做好处理公正事务的工作。而现行管理体制也难以落实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不能保证公正司法,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司法公正的实现。伴随着法官的职业化和良好执法体制的建立,必将对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推动作用。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8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自由心证;客观真实;法律真实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整个诉讼的过程围绕证据来进行。刑事证据是认识刑事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对于刑事证据所达到程度的要求,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影响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及其处理方式和结果。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证明活动的指导和准则,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要求限度,是法官进行判断的标尺。因此,证明标准在证据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学理界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和评议,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也存有困惑。故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进行探究。
一、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探析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采用“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即案件事实能否证明的标准是裁判者是否形成对待证事实的内心确信。“自由心证”,是指证明的取舍和证明力,法律不预先加以机械规定,由法官、陪审团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兰西刑事诉讼法》第342条对“自由心证”作了典型的规定:“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法官)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里所发生的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事实认定为真实的。’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是真诚的确信么?”法国将“自由心证”分为四等。“自由心证”是资产阶级平等原则和保护人权的观念在法律中的应用,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革新发展。它克服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刻板、滞后,强调充分发挥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运用其理性和智慧去发现案件事实。它以理性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认为人的认知能力不能完全发现客观事实,只能尽可能对事实的发现达到高度概然性。概然性理论表明:证明者无法确凿无疑地对已发生事实进行充分性证明,只能在一定概然性的水平上证明事实的存在。“自由心证”理论求助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对有高度责任感、业务娴熟、智识甚高的法官,能达到正确认定事实、实现公正的结果;而对其他法官则难免发生错误认识,导致误判。因此“自由心证”只是一个概括性规定,对法官主观认识能力的发挥有利,但对证据证明所达到的符合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不足。
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证明采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并把这种证明标准分为九等。这个证明标准有两项基本准则:一是要求陪审团和法官要站在一个公正和诚实的立场上,基于自己的良心、道德来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二是合理怀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种妄想、猜测和怀疑,都属于不合理的怀疑。它的特点在于否定了刑事证明达到绝对确定的可能性,只承认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概然性,并认为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的认识范围内的最高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合理性在于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发生的事物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即使人们以智慧对其全力揭示,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本来面目,人们只能对其达到大致的基本符合事实真相的认识。所以当人理性地对案件事实进行认识时,只要对证据全面细致地了解分析,符合思维逻辑,排除矛盾,不存在使人们根据经验产生怀疑的地方,则能保证最大程度地接近事实真相。“排除合理怀疑”是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的法律表述,是对“自由心证”的进一步发展,它对证明标准的司法判断提出更高要求,使对于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但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这不是一个明确而又难以界定的概念,因而对怎样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英美等国不论在法律还是法理上均无统一具体的说法。英美学者自己也认为“合理怀疑”一词不可能被精确地定义,完全可以说它是“存在于那种根据普遍接受的人类常识和经验而被认为是合理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之中的怀疑”。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侧重对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应达到的程度的要求,对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不足,这一证明标准没有达到主客观一致,在司法实践上导致很高的误判率。
“自由心证”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实质是一致的。二者都以概然性认识论为基础,对刑事证明标准都未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都侧重发挥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因素对案件事实进行认识;二者表述虽不同,但内心确信,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则必然使内心确信,因而具有同一性。这两个证明标准是人们理性认识在刑事证据制度上的体现,缺陷就在于没有强调事实的客观确定性,因证明标准是必须达到揭示案件事实、发现真相。
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弊端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每个证据都必须确定、客观、实在,有充分的证明力,足以认定犯罪事实。证据确实是证明标准质上的要求,证据充分是证明标准量上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只对证明标准作原则性规定。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以达到以下为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它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性,追求客观真实,有学者称之为“实事求是的客观验证”。应当说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比“自由心证”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有优越之处。首先表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重视与追求,这必然要求司法人员尽全力查明案件事实,包括他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内心确信”,并“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其次具有广泛性,要求查清一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这有利司法公正,是我国追求实体公正的体现。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以辩证唯物认识论为指导。辩证唯物认识论坚持可知论,认为人类有认识世界的能力,可以认识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这里所说的“人的思维”并非指单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尽管有学者反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以辩证唯物认识论为指导,尽管还有待完善之处,笔者认为它的指导理论和规定基本是正确、完整的。
毋庸置疑,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也存在一定弊端。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它有追求绝对事实的倾向。绝对事实或称为“客观真实”,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完全认识清楚的,辩证唯物认识论也不否认这一点,它只是强调理论生存在着可能和事实的客观存在性,这与概然性理论也不矛盾。既然“客观真实”发现的不完全可能,所以证据只能证明“法律真实”,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而“法律真实”也是人类认识论在法律上的体现,它尽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真实”,所以二者是一致的,我们不可能也不能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其次,它的规定过于宽泛。所谓“案件事实清楚”,是一个概括性规定,在实践中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繁多,有与定罪量刑密切相关的,也有关联不大的。如对案件事实全部收集、查明,必然导致诉讼效率低下,浪费司法资源;如只查明主要案件事实,则不易公正处理案件。不同的案件、不同的诉讼阶段所要求的证明标准的宽严不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实践运用中难以把握它的尺度。最后,它没有体现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分工,且易诱发司法人员违法现象。侦查、提起公诉、审判阶段要求同一证明标准,固然能保证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但也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公、检、法三机关工作都有其特点和不同要求,因此它们对于刑事证明标准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调查取证,律师掌握的证据,公安、检察机关不一定掌握,不一定做到证据确实、充分。为了达到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公安、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能会采取诱供甚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对于难以收集的证据,则又导致案件拖延,对犯罪嫌疑人实行超期羁押,不利于保障人权。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建议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采取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在理论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坚持真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与“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的各自优点充分结合,既坚持对客观事实的目标的追求,又坚持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去实现目标;既坚持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又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立法上对二者的结合点予以规制,以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制度。另外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制度应当从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转向“法律事实”。绝对的“客观真实”是不可能的,事实真相不会完全复现,因此只能用证据证明诉讼法意义上的事实,即“法律真实”。因为“一切刑事案件都是过去发生的,办案人员只能在案发后通过诉讼活动再现案件事实;认识案件事实的手段只能是刑事证据;诉讼证明要受到与司法公正直接有关的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的制约;诉讼效率的追求影响证明目标的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只能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法律所要求的事实,对与之无关的事实没有必要去证明,因为那不仅不可能,而且降低诉讼效率。“法律真实”是对“客观真实”的高度概然性的概括和总结,是一种相对真理,与人们认知能力是相符的。对“法律真实”的追求能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转向“法律真实”,且应对“法律真实”作出合理、完整的规定,使之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9
关键词:法律论证的合理性;逻辑层;论辩层;程序层;
在法学研究中,现实主义法学将法律时常表现出来的苍白无力推到了极致,法律的严谨之于鲜活的司法实践,从条文到判决的过程不具有逻辑真值的属性。为使人们信服这个并不唯一真的过程和结论,而非恣意擅断:法律论证理论应运而生。
法律论证具有合理性。它是人们在对法律认识理性化的过程中,引发的关于法律的确定性、正当性和可预期性的问题。法律活动从法律规范出发来商谈和论辩各自行为的理由,有着共同的前提和基础,使得论辩各方更容易理解和接纳对方的主张;论证中法律主体依据逻辑规则和法律规则进行的说理及证明,具有逻辑上的说服力和法律上的正当性;法律论证的基本形式推理,排除了主观臆断及猜测的成份,使法律论证的结果具有较高的预期性。
法律论证是一种作为过程的论证,对这种过程的论证合理性评价是多层次的。根据普拉肯等法律论证学者的观点,这种多层次构造可以分为:逻辑层、论辩层、程序层。
一、逻辑层
葛洪义认为法律论证主要涉及的是如何通过合乎逻辑、事实或理性的方式来证明立法意见、司法决定、法律陈述等有关法律主张的正确性和正当性。【1】一个法律论证总是以逻辑论证为基础的,合乎逻辑是法律论证的基础,也就是说,基于论证的论述可以被重构为一个逻辑有效的论述。“只有通过有效论述,裁决(结论) 才能从法律规则和事实(前提) 中导出。因而逻辑有效性是法律论证可接受性或合理性的必要条件。”【2】这可使论证立足于一个坚实的基石。
“我们在对案件的探讨中离不开三段论,但不能把它绝对化。其他方法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不能代替三段论的基础作用。这是我们对法律逻辑的基本态度。”【3】很多学者也都认识到了法律推理的过程并不是那种纯粹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严格证明,而是内含价值判断的过程。比如麦考密克就认为,像司法三段论这种“演绎证明并不做详细阐释,它只是一个由各种价值构成的框架中的作用,正是这些价值,使得演绎证明作为终局性方式有了坚实根据"。【4】
二、论辩层
法律论证在司法判断的过程中尤为重要。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的交互对话和商谈的过程。对法官来说,法律论证使其所做的司法裁判不仅具有了法律上的根据,而且也获得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保障,从而能够为当事人双方和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对诉讼当事人而言,在相互论辩的过程中,他们得以通过法律论证这一过程为自己的主张、为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明,以说服法官或者反驳对方当事人,即使没能达到最初目的,因为法律论证过程已经给双方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当事人一般也会服从法官最终的裁判。
麦考密克在分析合理性的限度时曾论及:“一项合理的法律程序要求旨在支配一群人的行为的规范,从给这种行为提供严格的评价标准的意义上是规范。为了保证把这些规范经常和持久的适用于个别的情况,就必须在有关的社会内任命一些人担任司法职务。”【5】同质性较高的法律职业群体,特别是法官群体,在司法过程中日渐形成了一套自己职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并趋于统一。“在这个共同体内,存在着一些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标准(虽然这些标准是随时间和社会变迁而移动的),这些标准告诉共同体的成员,哪种法律论据是有说服力的,哪种论据处理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哪种思维方法是可以在同僚中取得共鸣的。而律师和法官便在这些专业性、社会性的规范中进行他们的工作——一种修辞学的、以在这个解释性共同体内发挥说服力和赢取支持为目标的论辩性、对话性的实践。"【6】
三、程序层
在法律论证中,适用法律者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或者关于法律同题的判断,都必须从现行有效法规范为出发点,而不能运用法律以外的任何理由。阿列克西所说,“法律论证的合理性在其为制定法所确定这个程度上,总是与立法的合理性相关联。司法判决的绝对合理性似乎也将以立法的合理性为前提条件。”【7】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自始至终是根据法律进行的论证,都是在现行的有效法秩序内进行的,现行有效的法为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场域。在法律论证中,论证者论述自己观点、主张或者关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时,不能运用法律以外的任何理由,政治的或者道德的根据在法律的论辩当中对于法律规范正当性的说明不符合法治基本精神,只能以现行法律为根据,寻找恰当的法律规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既要求能对客观事实的审查要满足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也要求法律的适用符合现行法律的规范主张。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是对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所确认的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所作的说明。“由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法律自身的因素等的存在,法律论证只能实现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实现绝对的合理性。”【8】法律论证的相对合理性最终得到的结果是许多人所共识的看法,即在法律问题上没有正确答案,更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有的是一个可以为法律职业群体所接受的答案,而且这种答案必须经得起法律职业群体的反复追问。所以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是司法裁判正确性形成的理性缘由。
参考文献:
[1] 葛洪义.试论法律论证的源流与旨趣[j].法律科学,2004 (5) .
[2] [荷]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m].张其山,焦宝乾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5.
[3] 陈金钊:探究法治实现的理论——法律方法论的学科群建构.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总第121期).
[4] [英]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5] [英]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3页.
[6] 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载于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7]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第352页.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篇10
关键词:证明责任;功能
引 子
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法、证据法乃至民事实体法中极具实践性的课题,也是近年来引起学界强烈关注的课题。所谓证明责任,即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依法承担的败诉风险负担〔1〕,它是“先于具体的诉讼而规定在实体法中的规范,从诉讼开始到结束一直由固定的一方当事人在观念上承担,只是当诉讼的结果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时才真正实现”〔2〕。虽然“证明责任”与民事诉讼相伴而生或者说“证明责任”一直是民事诉讼中的客观存在,但事实上与真伪不明直接联系的“证明责任”的本质被阐明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3〕。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古罗马时期就已经确立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两条一般性原则,即“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原告不尽证明义务时,应为被告胜诉的裁判”和“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但在古罗马及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没有意识到“证明责任”的本质所在,他们在“证明必要”而非“证明负担”的意义上使用“证明责任”,使“证明责任”基本停留在提供证据责任的意义上。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认识能力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框架等的限制而使“证明责任”作为一种裁判机制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并不具有“语境的合理性”。因为对于事实真伪不明的状况,先辈们有自己的解决方式,即使某些解决方式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是落后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本文后有详述)。
证明责任既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又是一个新生的概念。作为证明负担的证明责任虽然已经在19世纪几乎同时得到大陆法和英美法的极大关注并取得重大理论进展,但对于已经是20世纪后半期的我国来说证明责任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所熟悉的所谓“证明责任”、“举证责任”仅仅被我们局限于提供证据责任的意义上),虽然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于证明责任(未必使用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极力倡导并为观念普及和制度设计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证明责任在中国真正的独立化(观念上的和立法上的)仍然任重道远,证明责任的制度价值尚待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充分挖掘。
本文写作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分析证明责任的独特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揭示证明责任的本质、规范性质以及所蕴涵的多重理念与价值,论证证明责任独立化的必要性和事实上的可能性。作者相信,证明责任穿行于诉讼法、实体法、证据法之间的事实,决定了证明责任是一个多重价值和多重功能的结合体;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本质与规范功能的差异决定了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分离不仅有助于理论上的明晰也有助于实践中的操作。这种功能视角研究的意义在于,证明责任的本质和独立化决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重新界定问题,更是一个对于民事证据制度部分重构、对某种民事诉讼理念进行审视以及对民事实体立法解释和反思的过程,这对我国的民事实体立法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事证据立法都不无意义。
一、证明责任的裁判功能
——解决事实真伪不明的法律方法和技术
(一)“事实真伪不明”与证明责任——“构造性”现实与制度化解决
1.“构造性”现实
“确定事实并适用法律就是裁判所呈现的构造”〔4〕,事实与法律构成了法官裁判的两大基础。对于法律问题,“法官知法”是一个基本的预设,但对于事实问题却无法作出这样的预设。事实问题作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往往更会成为问题的关键和争议的焦点所在。由于案件的事过境迁、司法证明的历史证明性质、事实探知成本以及法官的有限理性〔5〕等因素的制约,司法过程中对于事实的认定并不必然会达到一个确定的二分状态——“真”或“假”,而是可能会在真与假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状态即“事实真伪不明”的灰色状态。哈耶克在谈到人的有限理性时指出,人的有限理性是一个“构造性”现实,所谓构造性即不能在假设中将其排除〔6〕。而事实真伪不明由
于司法证明性质和人类的种种局限也可以认为是司法裁判中的一个“构造性现实”。所不同的是人类有限理性的构造性现实既是就人类整体而言,也完全适用于任何具体的个人;事实真伪不明作为一种构造性现实是就作为整体的司法裁判而言,而不是就个案或部分而言,虽然事实真伪不明只能具体的出现在某些个案中。虽然就绝对意义而言,任何案件的事实都无法确定真与假,但即使是奉行证伪主义的波普尔也让步说,人类的经验还可以获得概率最大的、比较确定的知识〔7〕。
2.民事诉讼目的与司法机关的裁判义务
事实真伪不明是对司法裁判的一个挑战,因为一般来说,“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在法理上意味着由该事实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否发生也应当处于不明的状态。其结果是使法官陷入既不应该判决适用该条法律,也不应该判决不适用该条法律这样左右为难的境地”〔8〕。但法官是否可以因左右为难而不作出裁判呢?答案是否定的。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并通过这种纠纷的解决使当事人由冲突走向和平,从而达成法律和社会生活的秩序目标。纠纷的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无条件的,即有纠纷就必须予以解决,否则法律与社会的秩序无以达成。正如埃尔曼所指出的:“任何法律秩序都不能容忍有责任的审判员拒绝审判,因为这种拒绝将使未解决的冲突变成公开的对抗。”〔9〕司法救济作为私权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作为正义的底线和最后的守护者,也决定了司法机关不得以法律之外的理由拒绝作出裁判。事实真伪不明这种事实层面的不可能不会对法官的裁判义务产生丝毫影响,正如罗森贝克所指出的:“法官因对事实问题怀有疑问而使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予裁决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只要判决的诉讼条件基本具备,法官总是要么对被请求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予以肯定,要么对该效果未发生予以否定,因此,在民事诉讼中,要么对被告作出判决,要么驳回诉讼。法官的判决不可能包含其他的内容”〔10〕。而古罗马的法官遇到不能克服的事实问题的疑点时通过宣誓真伪不明结束程序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既然司法机关不能因事实真伪不明而拒绝裁判,就必须有某种法律机制能够化解事实真伪不明状态。当然这里的化解不是说使事实由“不明”变为“明”,而是说通过某种机制使判决超越事实真伪不明,即通过某种机制使判决的作出虽然仍是在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做出,但通过这种社会认可的机制或法律装置,能够获得当事人以及社会民众的信赖。在我们无法保证可靠性的情形下,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使这种判决尽可能的获得某种意义的可信赖性。
3.事实真伪不明解决途径的历史演变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作为法官在裁判中的认知对象,根据被法官认知的最终结果,在逻辑上可分为“真”、“假”和“真伪不明”三种状态。与真和假不同,真伪不明在法律发展特别是裁判机制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极为不同的意义(当然,在裁判被正当化这一点上意义大致相同),它经历了由被吸收且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附属变为具有独立法律意义和地位的法律裁判机制重要部分的历史演进。
(1)神明裁判与真伪不明
神明裁判实质上是依神意确定事实,让伪证者遭受天罚,是一种“超凡的发现真实”〔11〕机制。通常是置嫌疑者于一种危险(或生命危险或肉体痛苦的危险)的境地,看他是否能够安然无恙。如果单从纯客观的角度看,无论在任何时代真伪不明是必然会存在的,但在神明裁判时代,这种真伪不明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和法律意义。因为神示裁判的这种发现真实的机制是一种“是非”机制或者说是一种二者必居其一的机制。比如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曾存在过的“水判”,将涉嫌犯罪者或被认为主张虚假事实者放入水中,若其没入水中,说明其有罪或不诚实;若其不没入水中,则说明其无罪或诚实。由于把人放入水中只有两种结果:沉没和不沉没,因而这种裁判机制不存在中间可能。因此,神明裁判机制实际上是在法律上通过“程序形式主义”〔12〕绕过了真伪不明或者说神明裁判机制排除了真伪不明具有独立法律意义的可能,这种神判机制在不受人类理性支配的意义上,是一种“非合理的决定”〔13〕。
(2)法官任意裁判与真伪不明
法官任意裁判即法官凭其主观意志强行认定事实以决定裁判的后果。与神明裁判相比,法官任意裁判作为一种依法官内心判断进行裁量的法律机制,更有可能使真伪不明取得独立的法律意义和地位。因为与神明裁判相比,法官任意裁判毕竟是一种理性的人取代假定的神的裁判机制,其科学性和准确性是后者
所无法比拟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在法律领域的表现。但这种比较而言的科学性无法掩盖其致命的弱点,即法官的任意性〔14〕。这种“一人司法”〔15〕(忽视甚至否定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必要的程序约束)中的任意性使法官任意裁判与神明裁判一样在法律上绕过了真伪不明,因为在法官任意裁判的情形下,即使在某一案件中客观上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由于法官可以任意将这种真伪不明强行认定为真或假,因而,这种情形下的真伪不明也没有在法律上独立存在的余地。
(3)法定证据制度与真伪不明
所谓法定证据制度,是指法律事先规定出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评断标准,法官在审判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则,没有自由裁量权。从神明裁判到形式化的证明力规则,对事实的认定从“超凡”回到“平凡”,只是这种事实认定的决定权力不在法官,而在于各种类型的立法者手中。在这种证据制度下,法官成为了一个法律的奴仆或一台计算器。虽然法定证据制度由于过分形式化因而缺少灵活性并且由于对某些证据形式的极端化倚重造成了相当的负效应(如由于过分倚重口供而导致的刑讯逼供的泛滥),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定证据制度提高了司法裁决的可预见性和权威性,与决斗和神明裁判等息纷止讼方式相比“对司法程序产生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影响,并向审判程序转向对事实进行理性调查迈进了一大步”〔16〕。但这种事实认定上的理性调查由于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而排除了事实真伪不明在法律上的可能性。因为真伪不明“既不是认识客体的固有属性,也不是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量对比关系的描述,这里表述的是裁判者对系争事实的存在与否无从把握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17〕。作为法律奴仆和计算器的法官没有判断真伪不明的职权(他们没有自由心证的权力),他们的工作只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中各种证据的证明力进行数学的运算,从而机械的得到事实“为真”或“为假”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作出裁判。
(4)自由心证与真伪不明——证明责任作用的前提条件
虚幻的全知全能的神、缺乏规则制约的人以及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都通过某种方式或机制使事实真伪不明无法走向法律的前台。但是在现代自由心证裁判中,事实真伪不明终于得到上场的机会,因为自由心证的本质在于法官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在法律规则范围内自由的判断证据,它在实质上同时承认了人的理性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神判排除了人的理性的作用,而任意裁判则否认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而这两者正是事实真伪不明独立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自由心证裁判使事实真伪不明在法律的台前得以存在,事实真伪不明意味着不确定性,而诉讼的最终目标是要消除争议或纠纷所造成的不确定状态。自由心证无法独立承担起消除事实真伪不明的不确定性这一任务,如果法官在自由判断证据之后仍然无法形成心证,则单纯的自由心证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强行使自由心证负担这一使命即超越其本来意义和宗旨强行解决事实真伪不明的不确定性,将会使自由心证负担“不能承受之重”,事实上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否定自由心证本身。罗森贝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果人们想强制法官,让他将真实性没有得到确认的主张作为不真实来对待,这恰恰是对自由心证的扼杀。”〔18〕这就需要另外的法律机制对这种事实真伪不明状态进行制度上的克服,证明责任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于是事实真伪不明成为证明责任作用的条件和前提,证明责任成为克服这种真伪不明的手段。在依证明责任进行裁判的情形下,真伪不明有了与神明裁判、法官任意裁判和形式化证据裁判情形下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此时由法官作出事实真伪不明的判断具有了独立的法律意义和地位,在法律上已经不能被随意绕过,而是通过某种机制(证明责任)对这种真伪不明进行某种“法律的解决”。当然这里所谓的“法律的解决”是指依据特定的法律规则进行的解决,而不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解决。因为虽然在神明裁判和法官任意裁判情形下,真伪不明没有取得独立的法律地位甚至没有表现出来,但其毕竟在事实上通过当时法律认可的机制予以解决。象神明裁判“这些看似古怪荒谬的证验与裁判手段,曾经都是相对合理的”〔19〕。在当时的社会和心理因素下它们都是被普遍相信的、因而也被认为是实现了法律正义的方式。事实上“在法律诞生的早期,在人类的智慧还没有发展到运用足够(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的手段来调查案情的时候,诉诸不可知的神灵力量是很正常的选择”〔20〕。
4.作为制度化、理性化机制的证明责任
现代证明责任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于事实真伪不明进行的是一种法律的普遍性拟制,而不是一种
个案的拟制(如任意裁判的情形,虽然这种拟制是在当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是一种理性的拟制(这种拟制是法律综合衡量各种因素并进行价值排序而做出的决断),而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拟制(如古代社会的神明裁判,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拟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并不是非理性的)。既然事实真相无法查明,那么最明智的做法是以人们能够普遍接受或认同的规则作出判决(虽然它并不能总是保证实质的正确),证明责任规则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证明责任“意味着从方法和过程上已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确定实体时,假定某个结果合乎正义是一种不得已的必要妥协”〔21〕。这种妥协的正当性还在于作为裁判机制的证明责任通过“由程序本身产生的正当性具有超越个人意思和具体案件的处理,在制度层次上得到结构化、一般化的性质”〔22〕。
司法的目标是要使判决具有对于社会而言的可理解性和意义性,司法就其本质而言只能保证裁判的终局性而不能保证其绝对正确性。法律问题不是一个真与假的事实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问题。正如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所指出的:“对事实问题真假不明并不意味着对法律问题也真假不明。”〔23〕证明责任的存在是人类在不断完善认知手段和提高工具质量仍无法发现事实的情形下所采取的一种克服有限理性的制度性保障措施,是一种无奈的法律技术或方法。正如波斯纳所指出的:“法律制度常常对它必须解决的法律纠纷的是非曲直没有任何线索,但是,通过运用举证责任,以它来作为缺乏这种知识的代位者,法律制度就避开了这种耻辱。”〔24〕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依据证明责任进行裁判,实质是通过进行某种拟制——将要件事实拟制为“真” 或“假”——进而依据法律规范作出裁判。或者也可以说,证明责任的本质意义是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为法官提供将不利益的诉讼后果判决给某一当事人承担的法律依据,从而显示在真伪不明情况下法官并不是任意的将不利后果分配给一方当事人。与历史上的神明裁判、法官任意裁判相比,证明责任的这一本质反映了现代法治国家极力强调的法的安定性、法的可预测性及司法信赖性原则〔25〕,证明责任与法治的这种天然联系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证明责任直到近代才被人们所认识并开始取得独立的地位。
“证明责任规则赋予了人民法院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作出裁判的权力,并使得这种裁判在法律上成为合法的和正确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裁判毕竟是建立在事实并未查清基础之上的,这与民事诉讼的理想状态——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相距甚远。”〔26〕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证明责任判决的本质其实就是与事实状况完全分离的风险判决”〔27,它确实包藏着实际上有理的当事人反而输掉诉讼的危险。但这丝毫不会有损证明责任的正面功能,因为依证明责任的裁判本身就是一个对于依形成的心证裁判的补充,一个无奈的选择。依据证明责任进行裁判所存在的事实认定错误的风险是我们为使司法裁判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仍为可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必须看到,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依据证明责任作出的判决在大体上是与案件事实的真相相符的。因为从理论上说,“如果一种民事诉讼制度不能保证大部分案件中认定的事实实际上就是客观真实本身的话,则该制度恐怕很难长久的存立下去”〔28〕。同时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看,法律在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时决不是任意的,而是充分考虑了诸如实体法要件、证据距离、事实性质等多种要素,从而使主张了真实(从原始真相上看)的事实的当事人通常可以容易的加以证明〔29〕。在法律诉讼中作为公正裁判第三人形象出现并给予争议当事人以较大可预见性的确定判决,是司法机关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在社会中的持久作用的基础,而对争议当事人而言,“对结果较高的可预见性可能使依赖于法院较依赖其他程序更为可取”〔30〕。证明责任非但没有因为其具有一定的或然性甚至是错判(相对案件真实情形而言)而降低判决的预见性和确定性,相反它通过制度化的克服事实真伪不明这一不确定状态作出判决而尽可能保证了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证明责任在诉讼之前被预置而且具有确定性,即不会在当事人之间转移)。
(二)证明责任作为裁判机制正当性的证成——风险分配与裁判正义
1.作为核心与难点的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作为一种为进行裁判而设置的法律装置,必然有一个正当性的问题,这种正当性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整体(裁判机制)的正当性;二是具体案件(指某一类型案件)中的正当性。对于前者,正如笔者已经论述的,证明责任作为裁判机制产生的历史必要性和可能
性已经证成了证明责任作为整体的正当性。但证明责任作为整体的正当性的证成,并不意味着在具体案件中正当性一并获得证成。证明责任作为一种无奈的法律技术或方法仅是为法官提供将不利益的诉讼后果判决给某一当事人承担的法律依据,从而显示在真伪不明情况下法官并不是任意的将不利后果分配给一方当事人。而这种法律依据本身是否合理(即是否“法官并不是任意的将不利后果分配给一方当事人”就必然意味着这种风险负担分配的合理)却仍存在疑问,因此证明责任在具体案件中的正当性证成在于证明责任分配的合理与否。
证明责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败诉风险负担,证明责任作为裁判机制就是使经由法律公
正分配而承担败诉风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于事实的真相无法查明,即不能够揭开案件事实真实的面纱,就只能以某种人们普遍接受的公正性规则作出判决”〔31〕,而这种作出判决的规则是否符合程序和实体的正义性要求,正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使命之所在。如果说证明责任作为整体的正当性证成,仅仅是迈过了第一道门槛,那么具体案件中的正当性证成即证明责任的分配将是最后一道更具决定性的门槛。如果证明责任分配是合理的,那么根据证明责任作出的裁判就能证成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是一种合理的“拟制”;反之,根据证明责任作出的裁判就等于是法律未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剥夺了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承担了不合理的败诉风险),而另一方当事人却获得了不当利益(因为他没有承担本来应当由其承担的败诉风险),这种裁判就是一种法律的“武断”。证明责任的作用机制是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下,假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的判断(即判决)。在上述任何一种假定中,都隐含着一种错误判定的危险,因为假定毕竟是假定,而不是事实。要使假定与事实相符合,必须依赖证明责任的科学划分标准〔3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证明责任分配是证明责任问题的核心。事实上,证明责任问题之所以极富争议却又使众多能人学者不断投身其中,也正是因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合理化并不容易,而这正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必须能够向当事人表明根据什么合理的逻辑或价值准则,法律将证明责任分配给一方而不是另一方,因为证明责任之所在乃败诉之所在。
笔者认为,证明责任分配成为证明责任的难点,并具有引得众多能人学者投身其中的魅力,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证明责任分配是一个法律逻辑推理和价值排序的过程,逻辑推理与法律价值有可能出现冲突,因为推理本质而言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与价值不是一个范畴内的问题。同时要在多种法律价值之间进行排序是一个艰难的衡平过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价值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既具有高度概括和广泛适用的特征,又是一个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范畴。
其次,证明责任本身的性质也导致了分配的困难。因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依法承担的败诉风险。风险的分配不是一个奖励或惩罚的问题,换句话说不是一个责任的承担问题〔33〕。正如普维庭教授所指出的,证明责任是“对事实状况的不可解释性的风险所进行的分配”〔34〕。法律是一种逻辑技术与价值伦理的结合,将损失分配给具有过错的一方或双方,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是可行的,即容易证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与人们的一般朴素观念也容易达成自然的直观的相符;相反,将风险分配给并无过错的任何一方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是困难的,即很难证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至少与将损失分配给具有过错的一方或双方相比要困难得多,而且与人们的一般朴素观念也并不总能达成一种自然的直观的相符。
再次,评价的前提是标准的制定,但法律关系的不同性质、当事人的实际提供证据能力以及证据搜寻成本的差异等因素决定了这种标准不可能是一个绝对单一的标准,而只能是一个多元的标准体系;但由于证明责任在具体诉讼中的适用要求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这又决定了这一多元标准体系必须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标准。没有主导的多元标准容易造成适用中的无谓的冲突有时甚至是错误,因为法官在审判中适用何种标准是一个主观心证的问题,没有主导性的标准会导致实践中的同类案件因法官的不同而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不仅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安定性,而且会损害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性。
2.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学说理论与立法选择
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形成了众多的学说理论,这些学说理论在被批判、修正或淘汰的过程中将证明责
任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极其复杂和具有挑战性,学者们都试图高度抽象出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但这种极度的抽象必然会将一些影响分配的因素舍弃,而且实践中千差万别的案件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出现的新型案件对这种极度抽象的标准不能公正的一一对应也在所难免,这些都为众说纷纭的学说理论留下了被批判的伏笔。但这丝毫不会有损于这些学说理论的价值,因为理论本身是相对的,或者说相对是理论的一个构造性因素,它是一种“合理的相对”,同时,在大陆法系确定一些抽象的标准要比在每一个案件中具体分配要实用也要现实得多。二是学说理论的发展史证明了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只能是一个标准体系而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标准。德国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的“规范说”〔35〕的命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规范说“着眼于事实与实体法的关系,以事实在实体法上引起的不同效果作为分配证明负担的依据”〔36〕,以其强有力的逻辑分析,以精细的法律规范作依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而在提出后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它不仅在理论上开创了新的视角与方向,也为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而那种以符合抽象的公平正义要求的实质利益的考量为分配依据的做法,忽视了抽象的概括标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较低的可预测性,对法官素质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它体现了吸引人的表象,在制度上却并不具有足够的可操作性。当然,规范说也决不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学说理论,它在提出后也招致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相当切中要害,如规范说具有某种形式化和教条化倾向影响实质公平的达成等等。虽然批评者们都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新的更合理的标准取代规范说,这些批评实质上只是对规范说设置了一些重要的例外,以弥补规范说的缺陷和不足,但规范说的缺陷与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并不妨碍规范说仍然是目前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主导学说,在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规范说一直在实务界具有支配地位。对规范说的批评仍在继续,但规范说的统治性地位也仍在继续(虽然它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唯一标准,但它无疑是一个主导性的标准)。“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性规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其自身结构对某种价值要求的偏向而导致其制度的不足或缺陷。由于该制度结构的基本合理性,又使人们不可能因这种局部的不足或缺陷而否定该制度本身,只能以其他的方法来加以弥补。”〔37〕因此,确定一个占主导标准而辅之以其它标准从而形成一个以主导标准为核心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体系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国正在进行这样的标准体系的实践,这种实践一方面体现为在我国证明责任的理论研究与民事证据立法中,对罗森贝克的规范说表现了特别的青睐,将其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一个主导性的标准。由江伟教授主持的《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就明确采纳了规范说,建议稿第73条规定:“主张请求权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就发生该请求权所需的事实承担证明负担。主张他方的请求权消灭或者主张该请求权的效力受制的当事人,应当就权利障碍的规定、权利消灭的规定、权利排除的规定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负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国证据立法草案明确采纳规范说被认为主要基于如下的理由:(1)规范说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被司法实务证明是行之有效的;(2)我国属于大陆法传统国家,民事实体法与大陆法国家民事实体法的规范结构基本相同,法学教育中采用的也是法律要件的分析方法;(3)我国早有一些学者和法官主张依该学说分配证明责任,司法实务中也有不少法官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该学说分配证明责任;(4)规范说的分配标准比较明确,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不大,就我国法官目前的总体素质和社会对法官的信任程度而言,选择自由裁量权小的规范说是适当的〔38〕 .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是成立的,事实上,规范说被我国采纳根本理由有两点:一是规范说自身相较于其它分配标准不可比拟的优势(正如笔者前文已经论述的);二是规范说运作的背景环境与我国相合(如民法规范结构)。正是这两点决定了规范说在我国落地生根是水到渠成的。
这种实践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于规范说的不足也给予客观的承认并对其进行弥补,即在将规范说作为分配一般原则的前提下设置一些例外,以确保某些特殊类型案件的证明责任的公正分配。如江伟教授主持的《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第86条规定:“因医疗纠纷引起的诉讼,提出抗辩的医疗机关,应当就医疗行为的及时性、科学性、适当性、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法定免责事由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负担。”该草案建议稿甚至对例外情形证明负担分配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草案第90条规定:“在本法没有规定的依据其他实体法的规定,适用
严格责任的案件中,提出抗辩的当事人,应当就实体法所规定的免责事由存在的事实,承担证明负担。” 〔39〕对于《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撇开具体条文规定的合理与否不谈,单就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结构体系而言是合理的,相对于以往不尽科学、不尽完善的证明责任分配的立法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二、证明责任的效益功能
——成本与激励的视角
现代社会对于效益给予了广泛关注,人们几乎可以在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都进行一番平等与效率、公正与效率的辩论,法律制度更是不能例外。简单的说效益问题主要是一个成本的问题,而法律从其制定到其实施无不贯穿着成本问题。面对不断发展的和日趋复杂的社会,如何节约制度实施成本应当也确实成为我们法律视野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制度的成本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实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外在的成本,在经济学上称为“显性成本”,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激励机制本来能够预防的支出(损失),这相当于经济学上的“隐性成本”,是一种制度规范本身的成本(因为这种对于损失或成本的预防决定于制度规范本身的质量)。对于制度实施的显性成本,由于其显性而一直受到关注,而这种隐性成本由于其隐性的特征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种状况在现代法治社会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在于因资源的有限和人口的增长,对于损失的预防比补救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现代法律不再像专制时代的法律那样强调硬性的惩罚,而是更强调软性的激励。证明责任的效益功能不仅体现在节约显性成本上,更深刻的体现在对于隐性成本的节约上。
(一)证明责任裁判与效益
证明责任作为解决事实真伪不明的法律方法和技术,它向法官表明了在现有的证据基础上仍无法通过自由心证发现案件真实的情形下可以依据某种法律的规则作出判决,即发现一种假定的真实,从而避免了幽暗的事实(事实真伪不明)面前法官的尴尬(无法裁判)。而证明责任的这种裁判功能本身又有助于司法效益的实现。首先,它使法官可以在“自由心证用尽”仍然真伪不明时直接作出裁判,从而避免了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仍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现案件真相,为了排除或防止事实真伪不明而陷入对于客观真实的不切实际的盲目追求,这不仅可能导致在浪费了大量司法资源(一个社会中的司法资源又总是有限的)后仍无法查明事实的情形,而且即使能够查明真实,在耗费了过多的司法资源以及当事人的人力、物力、精力等的情形下,这种真实的意义却未必是当事人所追求的,甚至是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在民事诉讼中,这种“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也许是我们盲目追求客观真实的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证明责任裁判的效益功能就在于通过与“法律真实”的自然关联使盲目的“客观真实”追求止步,“以防止法院和当事人在漫无目的和不着边际的举证、认证活动中浪费诉讼资源”〔40〕,从而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这不仅限制了法官对于权力行使的任意和对于司法资源浪费的漠视,而且防止了过高的诉讼成本妨碍诉讼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其次,事实真伪不明时,“证明责任之所在乃败诉之所在”的现实使当事人双方积极提供证据参与诉讼。当事人之所以积极提供证据,对于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是为了使法官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心证(否则只有败诉),对于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是为了使法官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心证或者至少是防止形成有利于对方的心证(因为对于此方当事人而言形成事实真伪不明足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结果)。当事人双方积极提供证据参与诉讼,一方面实践了当事人的主体性,使这种诉讼程序得到了相当的正当性证成,正如罗尔斯的程序正义观念所蕴涵的基础性思想:利益主体参与程序并自主行使权利足以确立程序结果在道德上的可接受性〔41〕。另一方面“法律为了诉讼目的而有意识地利用由确认风险所生的对当事人证明行为的压力”〔42〕而使诉讼证据提供显示出一种竞争的特性,诉讼当事人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竞相提供证据大大促进了诉讼真实的发现(在很多案件中尤其是民事案件中,没有这种激励机制,案件真实决不会被发现,因为有些事实的证据只可能存在于当事人手里,法院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而真实的发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效益。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公正与效益的完美结合,虽然这种结合并不总能够达成。
(二)法律指引与效益
指引功能是证明责任的一个重要但却受到忽视的功能。言其重要在于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事后的救济和惩罚,还在于提供事前的指
引和对于预防的激励。言其受到忽视在于对于证明责任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入和具体,对于证明责任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其裁判功能,对其它功能缺乏应有的关注,虽然证明责任的裁判功能是其首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功能。因此证明责任的指引功能在于“通过确立合理的举证责任规则去塑造人们未来的行为”〔43〕,引导人们树立和增强证据意识和观念(行为时充分考虑出现纠纷的可能性及其后果,而不是一味单纯的寄希望于法院在出现纠纷后给予救济,事后的救济有时候是不可能的),从而有可能有意保留一些行为的必要证据,这样不仅使自己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诉讼中保持有利的地位,而且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因此这种观念与意识对于当事人(救济)、对于案件本身(真实)对于法官(信赖)乃至对于法律(权威)都不无意义。这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实际意义尤为重大,这种证据观念和意识的确立有利于纠正传统熟人社会那种过强的“面孔意识”、“面子意识”〔44〕,而树立现代抽象社会的“程式意识”、“非人格化意识”(对一个陌生人的范畴性理解或类型化知识)。因为前者是一种单纯的日常生活理性,它由于不稳定、不透明的特性而不能直接进入法律话语;而后者却因为其稳定性、格式化因而是透明的意义体系而进入法律话语。
(三)主体预测与效益
通常来说,“诉讼开始前每方当事人都要对诉讼上的机会加以考虑并采取相应行动”〔45〕。而证明责任的预测功能就表现在它使人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自己的诉讼成败进行预测(如我们站在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视角,此方当事人通过衡量自己掌握的证据的分量形成某种确信:能否使法官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心证。如果能够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心证,则会作出自己胜诉的判决。如果不能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心证,则意味着:或者法官形成了有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心证,从而作出对方当事人胜诉而自己败诉的判决;或者法官未能形成心证即事实真伪不明,此时法官依据证明责任机制作出自己败诉的判决),从而决定是否进行诉讼,这种预测作用减少了行动的盲目性,提高了行动的实际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一些“无谓的诉讼” 〔46〕。证明责任的预测功能使人们能够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形成合理的预期,而这种可预期性本身即意味着自由(通过这种预期自由选择是否进行诉讼)与效率(不进行无谓诉讼从而避免诉讼成本的浪费)。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能够证成其正当性的标准之一在于其可预测(预期)性,法律的不可预测一方面意味着一些人能够以法律的名义对另一部分人进行专制,另一方面意味着主体因无法作出某种合理的预期而在实质上没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行的普法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和权利意识,还在于对于法律正当性的证成。
(四)证明责任倒置与效益
证明责任倒置集中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效益功能——达到了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首先,证明责任倒置通过某种例外(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证明责任分配设置了一种激励机制,即法律将风险分配给了能以最低成本避免风险的一方(这种公正标准已为法律经济学所证明和推崇,它是一种极为稳定的标准)。这种激励主要是一种对于损失预防的激励,正是这种激励机制激励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或者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损失和损害的发生。这种将法律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进行考虑的视角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思考前提的稳定性和现实性(经济人假设和博弈论的互动关系),更在于它隐含着一种深层的民法理念:虽然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但这种损害若能通过风险的预先合理分配而避免则应尽量避免。因为,一方面,从损失发生到受害人得到补偿要耗费大量成本(包括当事人的成本和法院的成本),而且即使如此,由于证据等其它因素也未必能完全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即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完全补偿也仍未达到一种理想的补偿,因为虽然通过损害赔偿能使个人的损失得到填补,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损失仍是存在的。其次,证明责任倒置实质是“对当事人收集与提供证据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部分补偿”〔47〕,是相对于证明责任的“正置”设置的例外情形,在这些情形中,“一方当事人被认为具有一种获取信息的特别条件。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48〕。它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由于形式化平等造成的利益极端失衡状态的矫正的努力和对形式与实质平等兼筹并顾的理想状态的追求。
(五)证明责任规范的实体性与效益
证明责任是预置在实体法中实现和发挥作用于程序中的“隐形”(陈刚教授语)的实体法规范,
或者说证明责任规范的性质具有“实体性”,这对于实体法和程序法学者而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实践中的司法者而言更是一种应当树立的观念。在司法过程中,强调证明责任的实体法预置性有利于促进司法的效率,因为既然证明责任是预置在实体法之中的,那么民事诉讼中依据证明责任进行裁判时只要考察实体法的规定即可(当然我们不排除某些主要依赖于自由裁量的非规范性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适用,但其仅具有补充的性质),而不必在实体法之外寻求所谓的标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裁判者在寻找标准上的大量成本耗费。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领域占主导地位,就在于其强有力的逻辑分析,以精细的法律规范作依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并因而节省了审判中的成本。证明责任规范的实体法性质在一定意义上隐含了这样的观念,即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裁判者发现法律的过程,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一个自由裁量的过程。当然这种发现法律的过程决不意味着效益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事实上这里的发现法律仍然需要裁判者优良的素质,它需要裁判者对于实体法规定的逻辑性和精神实质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否则即使有规范说这样操作性较强的分配标准,也无法保证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依据证明责任正确的作出裁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效益。
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领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但由于证明责任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典型性,同时也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在文中主要在民事诉讼意义上论述证明责任。但其中的许多结论对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也是适用的。
注释
〔1〕概念的界定是讨论的前提和起点,否则极易导致缺乏对话平台的各说各话。对于证明责任,目前国内外学界通说是包含客观的证明责任(结果责任)和主观的证明责任(行为责任),而笔者在文中使用的证明责任概念特指客观的证明责任,即风险负担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为了论述的明晰,笔者在文中将表示双重含义的证明责任加以引号写作“证明责任”,同时将本文所要论述的证明责任直接写作证明责任。
〔2〕 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21.〔3〕 德国学者glaser和美国学者thayer几乎同时(1883年和1890年)在各自的著作中(《刑事诉讼导论》和《证明责任论》)阐述了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证明责任的本质意义开始被真正揭示。
〔4〕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页419.
〔5〕法官是拥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而不是全知万能的神。顾培东教授指出:“从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看,与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主体一样,法官一方面作为社会统治秩序的特定维护者,另一方面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前者决定了法官的社会组织本质,后者决定了法官的个性自然本质。法官的社会组织本质与个性本质共同构成了法官这一特定社会角色。”参见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页114.
〔6〕[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60.
〔7〕 杨荣馨(主编):《民事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页49.
〔8〕 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6.
〔9〕 [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139.
〔10〕 [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页2.
相关文章
互联网保险法律监管探讨 2023-01-05 09:03:53
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浅议 2022-12-30 08:29:57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探讨 2022-12-28 09:00:02
数字货币的法律和金融风险应对态度 2022-10-11 10:06:39
法律顾问在企业合同法律风险的作用 2022-10-08 15:34:18
高校管理 法律风险 防范 2022-09-30 14: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