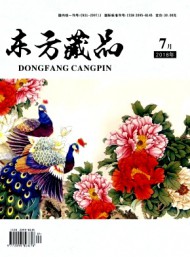关于年的传说范文
时间:2023-03-14 21:34:2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年的传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热血滚烫尘埃的战士是传说。
轻纱曼舞扬颜天下的西施是传说。
盒口的胭脂是传说。
折落在地面的玉簪是传说。
凉雨煮酒、弹琴尝醉的白翁是传说。
柳卷城郭、童打陀螺的盛世是传说。
飞鸽拔离、夕阳温柔碎的校园是传说。
过去是传说。
你,是传说。
一切原本的、刻意的、浸情的、清晰的、珍贵的、置在书籍纸面泛出陈旧味道的、卷向画幅的心脏又慢慢发黄的过去,在漫长的岁月压榨下,在变迁的潮流驱逐里,简缩成一段段可以不在乎结局的传说。
他们存在过,又销匿得极快。
他们被后世提起、铭记,又很快得被遗忘、抛弃。
他们把故事按部就班地写给曾经,他们,又是不遥远的我们。
关于高中打马而过的三年时光,关于贴满悲喜的整座校园,关于不知青春匆匆驶过却已经把它大半耗尽的我们,统统得也都会像销匿的他们,成为巨大的钢筋世界下,一段渺小而孤独的存在。
无限次对过去三年的感怀声,在星光周而复始地碰撞里觥筹交错到一起,源源不断地轰击着我们骄傲的青春,支离破碎,却又很少听到刺痛耳膜的声音。 我们全部的努力、荣耀,我们所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还有那段散发微茫的挥霍年华,都在一次又一次的强力轰击下粉碎开来。
操场上奋力奔跑的我们不见了。
三三两两聚焦韩星并且极力地争辩是谁最帅的我们不见了。
身穿的白色校服上烫映“2011”的我们不见了。
紧紧地辇着梦想在旋转的风扇下不断被汗水打湿额头的我们不见了。
把厚重的书本挡在课桌前然后偷偷看小说的我们不见了。
篇2
每年的农历的七月初七,就是七夕节,又称乞巧节,而现在则被认为是中国的情人节。
关于七夕,还有一个神话传说,那就是关于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传说,仙女织女下凡和牛郎成了亲。本来,两个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岂料,被王母娘娘知道了。她就把织女抓回去了。牛郎想要带回织女。于是,王母娘娘就用银河把两个人给阻拦了。牛郎就用勺子一瓢一瓢地舀,可是,怎么舀也舀不干。而银河那头的织女也是整天以泪洗面。王母娘娘因此被感动,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初七让他们相见一回。在那一天,喜鹊就会飞过来,搭成一座天桥,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以解相思之情。
这就是七夕的由来,现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了。
篇3
除夕传说1、除夕的介绍
除夕是春节的前夜,又叫年三十。有一种传说:是古时候有个凶恶的怪兽叫夕,每到岁末便出来害人,后来,人们知道夕最怕红色和声响,于是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贴红春联,燃放爆竹,来驱除夕兽。以求新的一年安宁。这种习俗从此流传下来,年三十晚上便称为除夕了。
2、除夕的由来的传说
关于年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在远古时候,我们的祖先曾遭受一种最凶猛的野兽的威胁。这种猛兽叫“年”,它捕百兽为食,到了冬天,山中食物缺乏时,还会闯入村庄,猎食人和牲畜,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人和“年”斗争了很多年,人们发现,年怕三种东西,红颜色、火光、响声。于是在冬天人们在自家门上挂上红颜色的桃木板,门口烧火堆,夜里通宵不睡,敲敲打打。这天夜里,“年”闯进村庄,见到家家有红色和火光,听见震天的响声,吓得跑回深山,再也不敢出来。夜过去了,人们互相祝贺道喜,大家张灯结彩,饮酒摆宴,庆祝胜利。
3、守岁的传说
传说远古时代有一个被称为“祟”的小妖怪,它长着黑黑的身子,但手却是雪白的。每年春节除夕夜,它都要到人间害人,专门摸熟睡的小孩子的脑门。凡是被“祟”的雪白小手摸过的小孩就会生病,莫名其妙地发高烧,整夜说胡话,等到十几天高烧退去后,小孩就会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所以,每年到了除夕这一天,家长们都怕“祟”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就整夜亮着灯,陪孩子一起玩,不让他们睡觉。这在当时叫做“守祟”。
除夕的食物1、饺子
招财进宝。在中华民俗中的,除夕守岁吃“饺子”,是任何山珍海味所无法替代的重头大宴。“饺子”又名“交子”或者“娇耳”,是新旧交替之意,也是秉承上苍之意,是必须要吃的一道大宴美食。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
2、鱼
意为年年有余。因为中国传统有年年有余(鱼)的说法,所以鱼是年夜饭必备的一道菜。除夕夜吃鲤鱼,鲤同”礼“谐音,过年吃鲤鱼大吉大利。除夕夜吃鲫鱼,鲫同”吉“谐音,过年鲤鱼和鲫鱼一起吃就是大吉大利。除夕夜吃鲢鱼,鲢同”连“谐音,过年吃鲢鱼连年有余。为了吃出连年有余的好意头,您可以除夕两条鱼,年夜饭吃一条,大年初一吃一条,就是连年有余。如果制作一条的话,年夜饭吃终端,大年初一吃头尾,这样就是连年有余,有头鱼尾。
3、猪手
发财就手。猪手,可以焖猪手,也可以发菜猪手,也可以花生猪手等等,吃法很多,因为猪手寓意着发财就手,做什么都会顺顺利利,就手发财,干什么也都会发财就手。所以这道菜式也是广州街坊最喜欢的一道吉祥菜!
除夕的来历除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重大的节日之一。指农历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即春节前一天晚,因常在夏历腊月三十或二十九,故又称该日为年三十。一年的最后一天叫“岁除”,那天晚上叫“除夕”。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叫守岁。苏轼有《守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除夕这一天,家里家外不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挂门笼,人们则换上带喜庆色彩和带图案的新衣。
篇4
[关键词]卫辉比干庙;地方风物传说;分类;研究
天下第一忠臣庙乃是河南新乡市卫辉比干庙,卫辉比干庙与周围的风物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干庙建立于北魏孝文帝期间大约是公元494年,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清中期修订的《汲县志》记录:“魏孝文帝南迁至此,因墓立庙,此庙之所由也。”[1]唐太宗率军东征,带领百官来比干庙祭祀比干,追封比干为“太师”,谥号为“忠烈公”,为了表彰比干的功绩,派人大修其庙。此后历朝历代的君王对比干庙都加以封赏和维修,历代的文人如孔仲尼、陶潜、李太白、孟东野、高达夫、王摩诘、黄鲁直等在此都怀念过一代殷商忠诚比干,且留下许多文学作品,让比干庙成为文化重地。因此这里流传有大量地方风物传说,有民俗传说,有关于比干庙建筑的传说,有与名人相关的传说,有特定山川万物的传说。下面对其进行分类研究:
一、卫辉比干庙地方风物类传说篇目
地方风物传说是指关于特指一定地区山川、风物等的说明性传说。其基本特性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指定自然风物或建筑物的来源、特征、起名原因等,给予阐释。从目前收集卫辉比干庙的风物类传说有:《影壁墙的传说》、《天葬墓》、《墓中出现瓷器的传说》、《金马驹的传说》、《比干墓周围为啥有砖墙》、《借土生根》、《柏树为啥空心》、《比干墓旁边的柏树为什么没有顶》、《聚宝盆的传说I》、《柏树为什么没有皮》《夜明珠的传说》、《夜明珠被盗的传说》、《夜明珠生光发财的传说》、《别断筋服输》、《文财神庙会》、《老八家看庙传说》、《比干为什么是文财神》等。(程玉艳硕士论文《卫辉比干风物庙风物传说研究》中收集整理的)
二、浅谈建筑类地方风物传说
比干庙中有关建筑风物类传说《影壁墙的传说》、《天葬墓》、《比干塑像》、《金马驹的传说》、《借土生根》、《夜明珠的传说》、《夜明珠被盗的传说》、《夜明珠生光发财的传说》等。这些传说为庙宇内建筑物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例如《天葬墓》讲述了比干被商纣王剖心之后,在元始天尊的指引下去往从新复活地方,元始天尊嘱咐他不能说话。比干碰见了妲己变成的老婆婆在叫卖:“空心菜。”比干情不自禁问:“空心菜没有菜心能活吗?人没有心能活吗?”老婆婆说:“草木空心可以活,但是人没有心不能活。”比干呕血而死,此时天崩地裂,飞沙走石,把比干的尸体包裹住,形成了比干墓。
这些传说是劳动人民奇思妙想的结果。通过塑造超自然的形象,运用神奇的幻化的手法,让比干成为解救于危难的大神,成为人们心中心灵的寄托。同时在这些传说里歌颂了比干的忠君爱国、忠勇直谏、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也是汉民族传统文化里不可或缺的精粹。
三、浅谈民俗类地方风物传说
比干庙中有关民俗风物类传说有《比干为什么是文财神》、《老八家看庙传说》、《文财神庙会》、《别断筋服输》等。这些传说里最有代表性比干是文财神的传说,代表有《文财神庙会》和《比干为什么是文财神》。
财神分类有正财神和偏财神。正财神里有文财神和武财神,武财神里有赵公明和关公,文财神是范蠡和比干。例如《比干为什么是文财神》传说故事里描述到比干挖心没死升仙了,玉皇大帝怜惜他为国捐躯,认为比干没有心,不会再有贪财之念,他生前又是做的文官,被封为文财神。比干当文财神后对下属公平,对待做生意的人一视同仁,办事公平,深受民间老百姓爱戴。
这些传说反映出财神信仰在民间深深扎根,表现了人民对财富追求,对待金钱渴望。希望有这样一位公正无私大神来职掌民间金钱关系,保佑自己全家升官发财。同时也体现出当地百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朴素的金钱观念。
四、自然地方风物类传说
比干庙里自然地方风物类传说有《柏树为啥是空心》、《比干墓旁边的柏树为什么没有顶》、《柏树为啥没有皮》、《聚宝盆的传说I》、等。这些通过庙宇内寻常的植物加以想象,结合比干的故事,来解释比如柏树没有皮,或者平冠柏为什么是空心的。体现出神话时代的人民无法对自然万物做出科学性的解释,用地方风物类传说来赋予庙内一草一木神话性色彩,更体现出比干庙神奇的所在。《柏树为啥是空心》比干庙的大殿前有一颗百年老柏树,它的躯干裂开,裂开处有碗口大小的洞,好像没有树心一样。传说当年比后,老树有灵性,情愿把自己的树心奉献给比干,玉皇大帝得知此事后,颇为感动,让比干复活返回阳间,继续主持正义。
五、卫辉比干庙地方风物传说体现出民俗底蕴
卫辉比干庙地方风物传说体现当地老百姓对历史、对伦理道德、对生活的追求,反映出神话时代老百姓对自然万物思维方式,一种朴实价值观念,具有丰富的民俗底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那一片热土的厚爱,乡民对卫辉比干庙地方风物类传说大大的美化,幻想化故乡比干庙的一切风物。
2.反映民众朴实道德意识,卫辉比干庙中地方风物类传说是按照当地伦理道德标准,其中核心就是大力宣扬比干爱国思想,同时宣扬比干直谏精神、刚直不阿,这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错宣传素材。
篇5
通往青海湖的路上,沿途的景色引的我们在车内,发出阵阵惊奇的欢呼声。青藏高原的山没有多少植被,远远望去是一些浅褐浅紫色的草,洁净蔚蓝的蓝天下白云朵朵,绵延的山坡上到处可见飘扬着的五彩经幡,和有着浓郁的宗教气氛的建筑,牧草上静静的羊群、牦牛在悠闲的吃草,这里的山不像我们陕南的山峰俊秀,郁郁葱葱绿得醉人。如果说我们陕南的山像清扬婉约的女子,那么青藏高原的山像心胸宽广、伟岸、粗犷、豪迈的汉子。
因为是秋天,偶尔在山上也可见层林尽染的浅黄色树林。在静静的、洁净的蓝天白云下,山坡上浅黄的树林,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洁白的羊群悠然自得,像一幅天然的油画,醉人心扉。整个途中给我的印象是“静”、“洁”、“蓝”。
途径日月山、倒淌河,有文成公主塑像和行宫。传说当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时经过此地,远离京城的繁华,来到这荒凉的地方,心中甚是忧伤,可肩负着唐蕃世代友好的重任,无奈的流下思念故土的泪水,河水为之动情,倒头向西流去,带着公主的无限相思流向故里。
过了倒淌河往前行,感觉离天空越来越近,巍峨的山顶上有白茫茫的雪,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射着耀眼的光芒,白的闪亮,白的圣洁,我们激动的直呼“雪、雪......”。虽然正值中午,阳光明媚,却能看见天上的月亮,正可谓有”日月同辉"的感觉。
在快要到达青海湖时,远远看去,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天湖一色,一片蔚蓝。美丽辽阔的牧草上,一片黄色的油菜花海里,飘扬的五彩经幡,还有白色藏族风格的建筑,房子的周围有风能、太阳能作为能源,看上去像一幅大的经典画卷,美轮美奂。
走近青海湖,湖水湛蓝,清澈,辽阔,在风的吹佛下,湖水泛起朵朵浪花,海鸥展翅飞翔,让人感觉到心胸豁然开朗,有天高任飞翔,地阔任驰骋的豪放。在这祥和、宁静、圣洁、宽广的地方,尽情的释放内心深处的自我,使我们的灵魂在这里得到了净化与洗礼。
关于青海湖的传说,有“汉族传说”、有“藏族传说”、有“蒙古族传说”,最让人不能平静的是有关于仓央嘉措的故事。当年在拉萨八角街的一个酒馆里,微醺的仓央嘉措邂逅相遇给阿爸打酒的玛吉阿米,一个气宇不凡,一个双瞳剪水,清丽脱俗,只一眼,便觉仿佛前生就擦肩遇见过,今生便要与子偕臧。他们的相遇犹如烟花般,却留下了几世传唱。一个叛逆的,在臧佛教伦理与禁忌中穿越荒芜的行者,怎能做到“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呢!
我漫步在湖边,凝视着宽广宁静的湖面浮想联翩,当年仓央嘉措是否也从这里走过?!今天我是否还能嗅得他当年的气息?!当年的他是否也和我一样暂时忘记了尘世情缘?!是否还在思念他心爱的姑娘玛吉阿米?!在他们的故事里是否还有漫长等待与无尽的守候?!
1683年,在西藏纳拉活域松的地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诞生了一名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后来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一位在西藏历史上生平迷离,又极具才华,又备受争议的一届达赖喇嘛。1706年清康熙年间,23岁的仓央嘉措,在解送京城的途中,行至到青海湖湖畔染病圆寂,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成为政治牺牲品。他信马由缰、桀骜的性格,天生就是个多情的诗人,而不是受比丘戒的活佛。正如在他的诗词里所说:和有情人,做快乐的事,别问是劫是缘。
我挥毫为他们蘸一世的痴情,用千年的青词阙歌,为他们唱一曲含血的痴念。铺一纸素笺,在平平仄仄的笺行里,深情的书写他们遥远的忧伤。我听一夜的梵歌,不为禅悟,只为寻找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丝气息,我转动经筒,不为修来世,只为他们在来生,都能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篇6
这“兔儿”,就是民间传说中广寒宫里给嫦娥捣药的玉兔,“爷”是旧时北京人对有身份地位的人的尊称,所以“兔仙”被老北京人昵称为“兔儿爷”。兔儿爷与北京人又有何渊源呢?
这其中还有个流传比较广的传说。相传,北京地区有一年发生了瘟疫,疫情蔓延开来,几乎每家都有人得病,情况十分危急。月宫中的广寒仙子嫦娥见此情景,十分忧虑,便派身边捣药的玉兔带了药材来到北京,挨家挨户给人治病。经过治疗,人们的病都好了,便想酬谢玉兔。可谁知,不管人们拿了什么金银珠宝给她,她都坚决不收,而是向人们借了衣服穿,每到一处便换一身衣服。玉兔骑着马、鹿、狮子、老虎等坐骑,走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她帮人们治好了瘟疫之后,才返回月宫。人们为了感念玉兔的恩德,便用泥塑造了玉兔的形象,为其“穿”上了各种各样的盔甲和衣服,还为其选择了各种不同的坐骑。在每年的中秋节祭月的时候,北京人都要供奉她,将兔儿爷视为祛病救灾之神。除了“兔儿爷”的昵称外,人们有时也亲切地称她为“兔儿奶奶”。
传说毕竟只是传说,但民间八月十五祭月的风俗确实是有的。为了避开男女之嫌,古时有“男不祭月,女不祭灶”的风俗,因为月神嫦娥是女子,所以祭月活动都由家里主妇一手准备和进行。家里的小孩子时常跟随在母亲左右,他们喜欢模仿大人的动作,久而久之,就有了专门供儿童祭月用的神像―兔儿爷。清朝诗人张朝墉在诗中写道:“蟾宫桂殿净无尘,剪纸团如月满轮。别有无知小儿女,烧香罗拜兔儿神。”就描写了小孩子们在中秋之夜祭拜兔儿爷的可爱之状。兔儿爷的造型憨态可掬,尺寸又小,是儿童十分喜爱的岁时玩具。
兔儿爷大约产生于明末,旧时每到中秋节前,街巷上到处都是兔儿爷摊子。特别是清代之后,兔儿爷已经由祭月用的神像逐渐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制作也日趋精致,除了威风凛凛的将军,还有扮成兔首人身的商贩、剃头师傅,也有缝鞋的、卖馄饨的、卖茶汤的等造型,贴近生活,十分有趣。
北京因为兔儿爷文化,还诞生了不少有关于兔儿爷的俗语和歇后语。如“窝了犄角”说的就是兔儿爷的耳朵折了,比喻人遭遇了不顺心的事;“兔儿爷拍心口―没心没肺”说的是兔儿爷是中空的,没有心也没有肺,形容人没有心计,不会应付,大大咧咧;“兔儿爷的靠旗―单挑”,说的是兔儿爷的靠旗只有一边;还有“隔年的兔儿爷―老陈人儿”,因为兔儿爷是泥制的,很少能保存到第二年,所以,见到隔年的兔儿爷,也就是老兔儿爷、“老陈人”了。
篇7
便瞥见那一簇四叶草
我不禁心一惊
想起了那一个关于四叶草的传说
拾到四叶草的人便可以得到幸运
一片是希望
一片是真爱
一片是信心
得到的那一片是幸运
我想寻找我的幸运
为何找不到呢
呵,四叶草的幸运就体现在珍贵二字
十万株四叶草只有一株是的,十万分之一的几率
心形的叶形
被人们说为是爱情的象征
传说找到四叶草的人类便能得到真爱
四片的心形叶子
被人们认为是信心
因为有了幸运草就有了希望
那么找到四叶草就找到了幸运
那么许愿给自己心爱的人,会实现吗
小小的四叶草载着人们多少美好的愿望,不实现又何妨,只要快乐就行
曾听说:用右手的两只手指握着四叶草,慢慢的转动四叶草,许下你的愿望
就会实现,那么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
拥有了四叶草,就拥有了幸福,我愿幸福伴我永久
我曾今好奇,去尝过 味道是酸甜的
哦,寻找四叶草的过程是酸酸的
而得到四叶草的日子是甜甜的
我努力寻找着属于我的幸运
可是却是一无所归
心中不免有些失望
也许幸运还没来吧
来年的春天,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幸运
篇8
老宅多传说
这个地方现在被人称为“16号公馆”,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文化街16号。这是一座建筑面积约1550平方米的大院,该建筑坐东朝西,大部分一楼一底,局部三层,建筑形式中西结合。
这栋楼的旧址为四重门进深的近现代豪宅,主要以砖、石、木建造。建筑大致由东西两部分组成。西侧为碉楼似石砖混合砌筑建成。底层由石材堆砌。上层为砖墙承重,木构楼板。大门处门楣上有时刻匾额,细节考究。院落建筑主体为木穿斗结构,石砌勒脚,木构楼板,兼以夹壁墙围护隔断,东侧尽端为砖构封火山墙。入口及正厅还保留着仿罗马柱式及柱头花饰,朴素中透着几分雅致。建筑屋顶为悬山顶,板瓦铺设。
特别是采用了这种主义建筑中西方多立克、科林斯柱式和柱顶花式,其门式、窗式也反映了近代建筑的风格。16号公馆遗存建筑为近现代建造,后来又分别经历了解放前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其去留兴衰丰富的反映了我过一段重要的历史,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屋顶高低错落,层次生动丰富。16号公馆是重庆市区不多见的深宅大院,不光呈现出一种较好的建筑价值,同时在艺术感上也是很有味道的。
这个三进三出的院落看似独立,装饰风格呈现出前后不同时代的痕迹。两道石门依旧显示出昔日的气派。最外的大门上镶嵌着用石头雕刻的匾额,但是上面却看不出什么字迹。尽管这座深宅大院显示了不同时期修复的痕迹,但这座院落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
尽管外面不起眼,但里面的空间还不小,是个三进三出的院落,随着拆迁,显得十分凌乱。因为拆迁,这里的居民已经搬走了。不断有人到这里来拍照、探访。来这里的人,总能听到附近的老太婆说这里是监狱。
位于渝中区下半场的文化街太平门一代,著名的巴县衙门坐落于此。所以这里被传说是巴县衙门的男监狱。据说这里还有处决犯人的断头台、关押囚犯的监狱等。这些传闻一点点被扩散,曾经还因为这个监狱的传说,还被电视台的人拍成了纪录片,最终澄清了并非监狱之事。
再次路过家门
多年后,当这个宅院的主人肖能铸兄妹三人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显得非常激动:“这后面一通都是我们住”,“八嬢结婚就是在这里”,“那里是九舅的书房”,“我在这个坎上还摔过一次”……一瞬间,仿佛那个年代的记忆又回来了。关于童年,关于那段在这里居住的日子,再一次被唤醒的时候,肖家兄妹的头上已经显露出斑白。
这栋房子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肖家兄妹的外公买下了的。说起肖能铸姐弟几个的外公肖俊晨,那可是解放前重庆城一个有名的人物。他以盐业起家。后涉足于烟草、电力银行等诸多行业,资产丰厚,如今文化街16号的宅院是他在重庆的多处房产之一。当年肖能铸的父母一大家人都生活在这套大宅院中,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家人才搬了出去。
肖能铸的哥哥姐姐分别生于1943年和1941年,“我妈妈过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我们都是在这里生的”。其实在肖能铸姐弟出生之前,他们家人已经在这里居住多年了。对于今年已经六十多岁的肖能铸及其哥哥姐姐来说,这里记载了他们三个孩童时代的快乐时光。“小时候骑自行车都能在屋里骑”。
对于肖家兄妹来说,原来自家院子大门的匾额上有几个字是他们认字时最便捷的的教材。即雕刻的“巴山小尹”四字,肖能铸告诉我们,关于这处老宅的很多信息都隐藏在这个匾额上的四个字中“巴山小尹”,在他看来,这里更老的主人可能是一个曾经的官员。
在房子的地底下,还有防空洞,大概有三米深,这里是当年日机轰炸时,还是自家长辈为躲避轰炸而修的。“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还下去乘凉,里面大概有一寸多厚的木板做的门。”在宅院里还有一口很深的老井,“当年我们经常在里面冰西瓜,有一次还发现了一条蜈蚣。”听长辈们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在自家的厨房里藏了好几个囚犯。“我妈妈到厨房去的时候发现了他们,我妈妈给了点钱,又给了点吃的,他们就走了”。时而的一个片断的记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这个老房子最动人的地方。
那些模糊的味道
对于在这个宅院只住了四年的肖能铸来说,对这处宅院的记忆很特别,一种孩童的视觉在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小时候,我家的客厅很大,沙发都是一大圈。前厅还停着一个玩具吉普车”。
那时候,一大家子三十几口人住在这栋大院子里,家里还有很多带小孩的保姆、专门做饭的。“我的兄弟姐妹各有一个保姆带着,大多数的时候,我记得父母都在忙着他们的事情,一般不让我出院,我只能在院里玩我的玩具,模型玩具车,那时候的玩具都是上发条的。包括脚踏三轮车。印象中,家里经常都很热闹”。
而出了大门,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茶馆,远远地可以看见那些在梁板上躺着喝茶的人,里面非常热闹,人很多。而冠生园就在我家对面,过个马路就到了。夏天,家里的大人会带着我们去冠生园里面吃冰淇淋之类的甜点,坐的凳子就像现在酒吧的高凳子。能走出
老房子很闭塞,似乎跟外边的空气都不一样,那时候的院墙差不多有两层楼高,似乎把街上的空气都隔绝了。到了门外,总能闻到餐馆里的香味。对于孩童的肖能铸来说,能够跨出自家的院墙,呼吸墙外的新鲜空气,就是那个时候最期盼的事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有公交车了,夏天,肖家兄妹总会被送到保姆家去过暑假。“那时候我的保姆基本都来自农村,我会跟着他们到石桥铺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一两个月。他们种地的时候我们跟着去‘种地’,挑水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甚至还跟着保姆一起去卖菜。不管是吃还是住,都是一样的待遇。和乡下的孩子也一起玩,到堰塘游泳,捉黄鳝,当然小孩子之间甚至还要打架”。
“我们家都是把保姆当自家的人,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保姆去世,我们都还有着联系,至于他们的儿女,我们都是以哥哥姐姐相称,大家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
篇9
城中的人造仙岛
在布达拉宫背后的山脚下有一水清潭名日龙王潭,潭中央的仙岛上筑有一座小小的庙,这座庙便是龙女宫——宗角禄康。莫看这庙小,它的来头可是不小。
17世纪时,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修复和扩建,建筑所用的土就从红山脚下的平地里取,久而久之,平地渐渐变成了水洼最终形成了小湖,湖中的小岛因为有修行洞而被保留了下来没被挖走。为了祈雨,修行洞被改建成了龙女宫。第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又将它按照佛教仪轨中坛城的楼式扩建成了现在三层楼高,四面各一门的楼阁。
龙女宫主要供奉以龙女墨竹色青为主的八龙塑像,墨竹色青背后盘绕的九蛇明白地告诉来访者龙女的身份。龙女旁边供奉着白度母和千手千眼观音,除此以外,龙女宫里还有龙王鲁旺杰波的塑像以及达赖喇嘛的卧室,墙上的壁画多以藏戏剧本、气脉修炼、各类神佛像为主。
相传第六世和第八世达赖喇嘛都曾在这里献宝瓶求雨,此后,布达拉宫的朗杰札仓负责派驻一名僧人于此。地方噶厦政府的四位噶伦也曾在这潭水中乘着牛皮船,向湖水中抛撒用来祭祀的宝瓶和糌粑。每年的藏历四月十五日萨嘎达瓦节时,除了耍纪念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得道和圆寂,拉萨城中的百姓还要聚集到龙王潭来祭祀、泛舟,整个龙王潭显得热闹非凡,甚至吸引了一些民间的藏戏表演团体前来助兴演出。
自龙女宫被修建的300年以来,墨竹色青受了凡人的祭礼,保佑着这片土地的风调雨顺。
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
墨竹色青到拉萨缘于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
墨竹色青的家乡在拉萨河上游墨竹工卡县的司普峡谷,她用七彩宝石在色青朗错雪山湖底建造了座水晶宫殿,作为苯教古老神灵的她拥有这片峡谷中广衰的森林。年轻的藏王赤松德赞为了获得建造第一寺院桑耶寺的木材,而亲自进入司普峡谷,向森林的主人求取资源。
善良的墨竹色青与年轻英俊的藏王在色青朗错湖畔第一次相遇,开始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爱情。突如其来的爱情的结局,在传说的末尾提到莲花生大师知道此事以后便出面干涉,人与神的恋爱最后不得而终。经过此事之后,墨竹色青皈依了佛法,由苯教的神变成了佛教的神,成为了藏传佛教宁玛派地位很高的护法神。龙女宫里供奉的龙王鲁旺杰波据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以苯教神灵之躯调伏龙女,再回归佛教。
皈依佛教的龙女捐献了大量的木材,桑耶寺的建筑材料也就有了保障。为了表示感谢,每年藏历五月十五日,桑耶寺都要派人来到墨竹色青的老家,色青湖旁祭祀。
关于这场爱情,并没有更多的细节的描述,但是从结局来看,可以想象因为人与神的身份,他们的爱情注定会过得有些艰辛。即使;中破障碍走到了一起,也避免不了人之生命的短暂,龙女最终还是得独自去面对百年、千年的孤寂。
数百年后,受到宗喀巴大师的感召,墨竹色青再次踏上拉萨城的土地,供奉酥油赠予风雨。此后,每年,墨竹色青定时从墨竹工卡赶来,在布达拉宫旁的拉鲁湿地住上一些日子,她带来的供养和雨水滋润了拉萨城。
大约又过了两百多年,五世达赖喇嘛重建起红山上的布达拉宫,山脚下的平地被挖出了一个大坑形成水潭。墨竹色青托梦告诉五世达赖喇嘛要回到墨竹山谷的老家去,五世达赖喇嘛感念墨竹色青为佛教所做的巨大贡献,招第悉·桑结嘉措主持修建了精美的龙女宫。
其实众所周知,龙女宫实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时修建,并深得仓央嘉措的喜欢。传说听起来很美,却与实际有些出入,想必应该是人们心中真诚愿望的写照吧。
传说缘于自然崇拜
不管这个传说的真假与结局如何,传说中也透露出了一些有趣的信息——藏族由来已久的对大自然的崇拜。
藏族的传统观念中,万物皆有灵。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几乎每
篇10
仙茗之传说
龙井茶之所以名为“龙井”,是源自泉名,此泉古称龙泓,位于一千七百多年前老龙井寺左侧。相传当年掘井时,从井底掘出一块大石头,形如游龙,故名龙井。而关于“龙”,关于龙井为何历久弥鲜,又在坊间有着诸种美丽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那十八棵老茶树与一个破石臼的故事。
相传王母娘娘在天庭举行盛大的蟠桃会,粗心的地仙捧着茶盘送茶时,一不留神,茶盘一歪,一只茶杯滚落到凡间去了。这个茶杯到了人间,就成了个石臼的样子,落在一位老大娘住的茅屋和十八棵老茶树旁边。石臼里面的茶像是苍翠碧绿的青草。而偷食仙茗的蜘蛛精为了不让地仙找到石臼,把它打入地下。被打入地宫的“茶杯”就成了一口井,吸引了龙来吸吮仙茗,龙去了,留下一井水。这就是传说中的龙井。
沧海桑田,历史变迁,原来大娘居住的茅屋改建成了老龙井寺,后又改名为现在留存的龙井村胡公庙。庙前的十八棵茶树经过仙露的滋润,越发出落得盎然茁壮,品质超群。据说乾隆下江南时,曾于狮峰山下的胡公庙品饮龙井,饮后赞不绝口,于是将庙前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
现实与仙境
不过传说归传说,回到现实中,今人大可不必为那十八棵御茶树的真实性费脑筋。想一探龙井的究竟,不如亲自到产地走一走,转一转。西湖龙井有“狮龙云虎梅”这几个一级产区,其中“狮”,以狮子峰为中心,包括胡公庙、棋盘山、上天竺等地;“龙”,指的是龙井村、翁家山、杨梅岭、满觉陇、白鹤峰一带;“云”,包括云栖、五云山、琅铛岭以西地区;“虎”包括虎跑、四眼井、赤山埠、三台山;“梅”指的是梅家坞一带,它从“云”字号独立出来,现在成为西湖龙井的最大产区。
作为著名的西湖龙井茶生产基地,梅家坞有龙井茶生长得天独厚的条件――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16°C,年降水量1500毫米左右。可以说,这里拥有“不雨山长涧,无云山自阴”的自然山水风光。在春茶期间,这里常细雨蒙蒙,漫山遍野云雾缭绕,为茶树生长营造出“天时地利”之美境。深入村中,成片的茶田让人激动不已。当地茶农都把竹制桌椅摆在家门前,供游人参观制茶工艺,亲手采茶,尝试炒青,再品一品这杯中清绿……经历过这些,才不算白来这“十里梅坞蕴茶香”的神仙之境了。
TIPS
交通:梅家坞位于云栖西二公里的琅砀岭北麓,是开放式景区,杭州市内可以乘坐24路、游5线、游4线、游5线(区间)到达。
相关期刊
精品范文
10关于梅花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