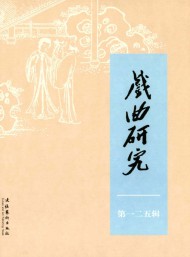苏格拉底名言范文
时间:2023-04-09 15:10:2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苏格拉底名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唯有神知道。
2、我与世界相遇,我自与世界相蚀,我自不辱使命,使我与众生相聚。
3、暗恋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爱情。
篇2
“明白。”那位助手赶忙说,“您的思想光辉是得很好地传承下去……”
“可是,”苏格拉底慢悠悠地说,“我需要一位最优秀的传承者,他不但要有相当的智慧,还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这样的人选直到目前我还未见到,你帮我寻找和发掘一位好吗?”
“好的、好的。”助手很温顺很尊重地说,“我一定竭尽全力地去寻找,以不辜负您的栽培和信任。”
苏格拉底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那位忠诚而勤奋的助手,不辞辛苦地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四处寻找了。可他领来一位又一位,总被苏格拉底――婉言谢绝了。当那位助手再次无功而返地回到苏格拉底病床前时,病入膏肓的苏格拉底硬撑着坐起来,抚着那位助手的肩膀说:“真是辛苦你了,不过,你找来的那些人,其实还不如你……”
“我一定加倍努力,”助手言辞恳切地说,“找遍城乡各地、找遍五湖四海,我也要把最优秀的人选挖掘出来,举荐给您。”
苏格拉底笑笑,不再说话。
半年之后。苏格拉底眼看就要告别人世,最优秀的人选还是没有眉目。助手非常惭愧,泪流满面地坐在病床边,语气沉重地说:“我真对不起您,令您失望了!”
“失望的是我,对不起的却是你自己。”苏格拉底说到这里,很失意地闭上眼睛,停顿了许久才又不无哀怨地说,“本来,最优秀的就是你自己,只是你不敢相信自己,才把自己给忽略、给耽误、给丢失了……其实,每个人都是最优秀的,差别就在于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发掘和重用自己……”话没说完,一代哲人就永远离开了他曾经深切关注着的这个世界。
那位助手非常后悔,甚至后悔、自责了整个后半生。
为了不重蹈那位助手的覆辙,每个向往成功、不甘沉沦者,都应该牢记先哲的这句至理名言:“最优秀的就是你自己!”
篇3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有始有终,定能成功”。古希腊着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在中学当教师,有一天他对班里同学说,我们来做个甩手游戏吧。游戏很简单,就是把手使劲往前甩三百下,再往后甩三百下,但要求每天都这样做。同学们纷纷说这个游戏容易,保证能做好。一个星期以后,苏格拉底问同学们游戏完成得怎么样?同学们全都举起了手。一个月以后,当苏格拉底再做统计时,全班仍有百分之九十的同学在坚持做。一年以后,当苏格拉底在课堂上再次向大家了解情况时,只有一位同学举起手,他就是后来成为大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凭着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自觉锻炼自己的意志,终于在哲学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哲学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
同学们,这个甩手游戏从动作上看很简单,但每天坚持,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有始有终,绝不能半途而废,如果我们能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人们常说,在科学之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敢于在崎岖的小路上不断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希望的顶点。让我们认准自己的努力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地鼓励自己,这样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和收获的快乐。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句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名言:“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惟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篇4
关键词:主体性意识 萌芽发展 困境
主体性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与主体性问题也是了解西方哲学的一条主要逻辑线索。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看,主体性的自觉经历了原始人类社会对自己认识混淆不清的状态到希腊哲学本体论阶段,近代认识理论的发展又使得主体性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主体性的变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改造世界和改造社会实践里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所激发出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一、主体性意识的兴起
人类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才真正提出了对认识自己的质疑,在西方文明开始的希腊时代,辉煌的物质、精神文明以及人对世界、对自己的思考开始了。
(一)认识自我
人是主客体的统一,主体又可以决定客体。在一定程度上原始人类与自然仍未明确区分开来,与自然、世界交互渗透,主体与客体处与一种混沌不分的状态。马克思曾论述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就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群体主体意识的出现和原始社会的宗教及祖先崇拜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这一切促成了主体意识的萌芽。随着主客体的分开,主体意识随着实践的脚步日益明显。
(二)认识自我意识
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认识自己的历史,尊重人的地位真正是从进入人类文明开始的,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开源,其辉煌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西方哲学思想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时代,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范畴,是对生活的智慧的总结与思考。因此,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一开始就致力于对万物本原、始基的哲学思考。所以,代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起点应该是泰利士的“水是万物的本原”,它是指千变万化的世界,归根到底应该归于单一的具体物质。这时候的哲学思想主导就是追求物质的本源,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程度和如何看待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其哲学意义就在于强调认知的作用、强调知识的作用,从而肯定人的地位,拥有了知识从而拥有了道德,知识和道德的完美结合就成了真正意义的人。从智者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启了对于自己认识的开端。但是,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出发点并不是关注人,而是更多的看重物,他们认为“物”是万物构成的基础,是哲学家追求的真理,关注的重点并没有放在对于人的关注上。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本身的问题上,由此开始古希腊哲学注重对自然本身的研究转到对社会伦理和对自我的研究上,追求的是千变万化的自然真理,从感觉而来的知识更是变化莫测的一种永恒不变、确定的真理,苏格拉底在自然界中找不到,所以更多的是研究自我而已。自然与我不再是一体的,而是逐渐分开的,人不是成为主体的一部分,而成为有自己特点的独立的实体。人由自然中走出来,体现了哲学由自然到注重人的过程。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识到这一点也是人的尺度,这需要更透彻和深入。
因此,一方面他认为通过反思精神才能来认识和理清自己;另一方面,苏格拉底认为灵魂应该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自然界的产生和灭亡也不过是如此,不过是某个东西的聚合和分散。虽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定还不明确,但确让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对立起来,这种区分让苏格拉底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奠基人。不研究自然界,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从伦理上来探讨普遍真理,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和了解认识自己,这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在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想要将伦理道德来靠理智主宰。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对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主体性思想的萌芽发展。但是把自我当成认识的对象,在追求知识的同时并没有脱离朴素性和直观性,并没有把知识、理性当作把握事物的主要手段,因此,苏格拉底只是注意自我意识的灵光,而并没有意识到主体性问题掌握主体性原则。
可见,主体性思想还只是处在萌芽中,并没有脱离开这个阶段。古希腊哲学主要是本体论哲学,比如,“认识自己”、“人是万物的尺寸”等问题虽然涉及到了一些诸如认识论问题等,但并没有脱离本体论的传统。在本体论下的人的主体问题,是以本体论问题基础来展开的,和现在的认识论哲学探讨主体性原则是有所不同的。古希腊哲学毕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没有真正达到把主体与客体自觉对立起来的水平,没有把主体性原则当成哲学的真正原则,也无法真正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的哲学理论中看到,在终极本体论思维下,希腊时期的主体概念还不是很清楚,还没有和人有着必然的联系。总而言之,虽然有一定的萌芽出现,但是主体意识在希腊没有形成确定下来的主体概念和原则。真正的得到关注和重视是在近代以后,科学在不断发展、哲学理论也在不断完善,对于认识论的问题就成为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关乎着人们精神层面的发展,关系着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拓展和发掘。
二、主体性思想的快速发展
哲学发展时期,人和主体的统一成为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这样的哲学环境使得人这个个体有了成为主体的内涵:拥有主体能动的创造性内涵的特点人们从自然存在的世界中游弋回到了此在的世界里,从对自然的崇拜到对人自我意识的研究,人们开始关注知识领域、追求个性解放,展现了人们的时代精神、人文精神。
篇5
关键词:本体性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2(c)-0221-01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本性是哲学在任何一个历史维度下都不可或缺的一个本质要素,而其内在的核心或本质则在于对主体性超越的本体追求和终极关怀的理性至高追求,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萌芽于古希腊时期;彰显于近代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提出;绽放于德国古典时期,它孜孜不倦地推动着西方哲学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其理论的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使其陷入了困境,现代西方哲学家竭尽全力挽救或给其寻找安身立命的稳固的基础使其摆脱困境,那么我们就需要从源头来反思主体性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
古希腊哲学是建立在自然哲学的基石之上探究万物产生的本原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裂变为真理的“逻各斯”和意见的“自然”,巴门尼德的真理与意见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他总结了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各种理论形态,从中提取一个抽象的概念来界定世界的本质,这就是‘存在’概念。在他看来‘存在’的存在是‘真理’之路,‘非存在’是意见之路”至此形而上学的本体论(Ontology,其中on便是存在)雏形得以展现,经验世界产生了“意见”,“真理”是依据抽象思维而形成的,这样强调理性思维的唯理主义认识路线清晰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沿着此路线前进,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走向了形而上学,主要体现在对逻各斯的深层分析之后,问题研究的重心已经转向了“逻各斯”背后的人和神,人的伦理生活和社会生活纳入了哲学的研究视野。巴门尼德用逻辑的思维方式给予原始质朴哲学以前进的内部动力,但是这时的哲学仍然在“自然”的范围,后来的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等也涉及到人的问题,但是均未从根本上发现人的主体性。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曾认为苏格拉底第一次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他的意思是说,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开始将眼光从自然界转向了人的道德世界。然而实际上普罗泰戈拉在苏格拉底之前就这样做了。[1]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在这里尺度、逻各斯通过人来建立,这对于追求本体的古希腊哲学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崭新的思维向度-主体纳入到了哲学研究的视野中来,万物依据人的逻各斯而存在或非存在,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同时它也是古希腊历史发展的主动性和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的崭新形态。虽然人的主体意识有了一定的觉醒但是这仍然不是主体能动性的觉醒,而是感性方面的理解,人仍然是形而下的存在。
苏格拉底的“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孕育了人的主体性思想,他把人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标准,苏格拉底引用镌刻在德尔菲神庙门前的名言来号召人们:“人啊,要认识你自己”,使哲学的研究视角转向了人,苏格拉底将人看作是理性的思维主体,承认了人的力量的存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认识的途径、认识的可靠性的条件等问题的研究。因此,主体性思想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获得萌芽状态。亚里士多德在对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之后将哲学理解为一切科学的汇总,并将其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以及艺术三部分,形而上学则存在于理论科学的体系之内,他认为人的认识是经过经验(一般知识)、技术(普遍知识)、理论最终到达知道的智慧(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并建立了以实体为核心的关于“存在的存在”本体论哲学,他的形而上学研究对象是存在本身即“存在的存在”,这种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得以高纯度的发展,他试图建立一个远离尘嚣的“本体”世界。但深入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行剖析,我们会发现其内部结构中对主体性的关注。亚里士多德提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前两个命题表现出亚里士多德力图通过人的形而上追求来建立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的鸿沟,同时也为知识论提供了根基。第三个命题“人是政治动物”则将至高无上的形而上追求给予了现实的根基,“人是政治的动物”强调了人对社会整体的依存性。这一点也为实践哲学的研究找到了本源性的证据。“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的特征,即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具有使用人类自己制造的工具改造自然的活动,亦即生产劳动,更广泛一点讲,即人的实践活动。”
古希腊时期的形而上学发展路线是在理性提纯至最高点的本体论或存在论哲学,其中主体性思维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主体性蕴含在实体和属性的关系之中,主体性思想在古希腊时期仍处于潜在和萌芽阶段。而到了近现代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形而上学的发展脉络发生了颠覆性的翻转,意识论的形而上学登上了历史舞台,主体性思维开始走进了形而上学研究的视野中来。
篇6
认识自我
[黎巴嫩]纪伯伦
一个雨夜,赛艾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支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对话引起了赛艾姆的注意……赛艾姆掩卷深思,心中油然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
“认识你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对!我必须要认识自我,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这样我就抛脱了一切疑惧和不安,从我物质的人中找出我精神的人,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找出我的抽象实质,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赛艾姆像害了场热病,眼中闪烁着酷爱“认识自我”的狂热光芒。
他踱到邻屋,像座塑像一样伫立在穿衣镜前,凝视着镜子里鬼一般可怕的自我,并默默地估量着自己的头形、面庞、躯干和四肢。
赛艾姆的这种塑像神态持续了半小时,空灵缥缈的“认识自我”,仿佛给他灌注了一套足以揭示自我灵魂秘密的奇异、升华了的思想,并使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他平静地启动双唇,自言自语地说:“嗯!从身材上看,我是矮小的,但拿破仑、维克多・雨果两位不也是这般吗?我的前额不宽,天庭欠圆,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秃顶,这并不寒碜,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我的鹰鼻弯长,如同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我的双眼凹陷,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亦是这般;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媲美,而我那粗胖的脖子堪与汉尼拔和马克・安东尼齐肩。
“不错,我的身体是有缺陷,但要注意,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更奇怪的是,我与巴尔扎克一样,阅读写作时,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我同托尔斯泰一样,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脸,贝多芬、惠特曼亦有这一习惯;我的嗜酒如命,足令马娄和诺亚自愧弗如;我的饕餮般暴食暴饮使巴夏酋长和亚力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
又沉默了片刻,赛艾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继续发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在。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是一定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
“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伟人们把宇宙的这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从诺亚到苏格拉底,从薄伽丘到雪莱,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幻梦中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人,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是的,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而神灵也已洞鉴了我。啊!我的灵魂万岁! 自我万岁!愿天长地久,诸事如愿!”
赛艾姆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那丑陋的脸上荡漾着欢乐的光泽,嘴里不时发出一阵像猫啃骨头时的欢快叫声。他反复吟哦着阿比・阿拉的一段诗文:尽管我是这个时代的晚辈,创业祖先的未竟之业,总会历史地压在我的肩背。
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这位赛艾姆穿着他那肮脏的衣服倒卧在乱七八糟的床上,进入了鼾声如雷的梦乡。
篇7
阿基米德是被困的7个小矮人中的一员。一晚,他在梦中遇见了雅典娜,雅典娜告诉他:在这座城堡里,除了他们所在的那个房间外,其他的25个房间里,一个房间里有一些蜂蜜和水,够他们维持一段时间,而在另外的24个房间里有石头,其中有240块玫瑰红色的灵石。收集到这240块灵石,并把它们排成一个圈的形状,可怕的咒语就会解除,他们就能重回自己的家园。
第二天,阿基米德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梦告诉了其他6个伙伴。有4个人不相信,但是艾丽丝和苏格拉底愿意和他一起努力。一开始,艾丽丝想先去找些木材生火,这样既能取暖又能让房间明亮些;苏格拉底想先去找那个有食物的房间;阿基米德想先把240块灵石找齐,好快点儿解除咒语。3个人无法统一意见,于是决定各找各的,但两天下来,3个人不仅没有成果,反而累得筋疲力尽。这让其他的4个人嘲笑不已。
但是,他们仨没有放弃,失败让他们意识到应该合作。他们决定:大家一起先找火种,再找吃的,最后找灵石。这是个有效的方法,3个人很快找到了火种以及蜂蜜和水。
在他们3个人的感召下,其他人也参与到合作的队伍中来。大家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终于搜集到所有的灵石,成功解除了身上的咒语。
美好的愿景是团队组建的前提;明确的目标是团队运行的基础;默契的合作则是团队成功的关键。
大道 理
在现实生活中,孤立的人是无法生存的,每个人都要与别人进行合作,在合作中学习、工作和生活。即使你是一枝娇艳、美丽的牡丹,也要知道:一枝独放不是春,春天应是万紫千红的世界。
:听到这儿,你知道合作的重要性了吗?
:我有点感触。平时在学习中,当遇到难题的时候,如果我和同学一起讨论解答,效果可能会事半功倍的。
:没错,聪明的“小雨点”。你真是一点就通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些谚语和名言警句,看看合作究竟有多重要!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谚语
人心齐,泰山移。
――谚语
篇8
1、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诸葛亮
2、自尊心是一个人灵魂中的伟大杠杆。——别林斯基
3、没有比认为自己是有用之才的自尊自信对人更有益的东西。——卡内基
4、假如你认为能够,你便能够;假如你认为不能够;你便不能够。——戴维斯
5、应该相信自己是生活的强者。——雨果
6、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罢!——但丁
7、无论是别人在跟前或者自己单独的时候,都不要做一点卑劣的事情:最要紧的是自尊。——毕达哥拉斯
8、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
9、自尊自爱,作为一种力求完善的动力,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屠格涅夫
10、没有自尊心的人,即近于自卑。()——莎士比亚
12、最野蛮的是轻蔑自己。——蒙田
13、自尊心是一个人品德的基础。若失去了自尊心,一个人的品德就会瓦解。——斯特那夫人
14、楚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穷困而变节。——子路
篇9
这时,托尔斯泰34岁,度过了他放荡的青年期。索妮亚18岁,聪明热情,对爱情充满美妙的狂想。然而,结婚前夕,她受到了当头一击――托尔斯泰出于一种“诚实”与“忏悔”的道德动机,把他的全部日记拿给她过目:说谎、、妓、酗酒,婚前与农妇阿克辛雅疯狂情爱并生下私生子……一个男人对其放荡史的坦白,带来的是一个女人对爱情的绝望幻灭!
每个伟大的男人,在女人那里,似乎部有一块“软肋”。
苏格拉底再雄辩,一切言语在她妻子那里,也有理说不清。还好,苏格拉底足够豁朗,他把悍妻当头泼下的一桶凉水,诙谐喻之为“我早知道打雷之后一定要跟着下雨”。
林肯再英明,也终生遭受悍妻玛丽的暴烈及动辄咖啡浇头的“待遇”。当然,林肯足够幽默,他向世人证明有一个怕老婆的总统的国家会是更民主的国度。
也可以这么说,大师与丈夫,压根是两回事。
托尔斯泰与索妮亚呢?如果不是晚年的索妮亚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症,在精神上自酿悲剧,她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妻子。
从19岁开始,索妮亚一共为托尔斯泰生育了13个孩子,还有过3次流产。托尔斯泰一生沉溺于男女之欢,即使中年皈依后,依然在禁欲与欲望之间挣扎。
索妮亚的前半生充满牺牲精神,她出色地完成了人妇与人母的角色。她才干出众,打理雅斯纳亚庄园,使其财产收入较原先增加4倍。更重要的一点是,她每夜挑灯抄写托尔斯泰的文稿,在她不厌其烦、无比繁冗的誊写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巨著浩浩荡荡地诞生了。
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托翁的这句名言,赫然写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上。信徒多如山的大师,在这场婚姻纠葛中到底充当了一个怎样的不幸角色?终其一生,他多情而软弱,自负而彷徨,无私而自相矛盾。索妮亚则始终精力旺盛,强悍异常。愈到晚年,她随更年期而来的支配欲、狂躁症,愈发强烈。
两人的家庭矛盾,在于对生活等级的选择与对待财产的价值观的分歧上。托尔斯泰在写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鸿篇巨制后,突然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一种“羞于提起”的否定与厌恶感。更有甚者,他对靠作品赢得版权以及对私有财产、贵族生活产生了罪恶感。他宣布,1881年后的所有作品版权公有,并想把自己的庄园分给贫困的农民。
在庄园里,他与妻子就著作版权与私有财产问题进行了一场“至死方休的争吵”。孤独!隔阂!叛离!晚年的托尔斯泰,陷入了一种终极的孤独与众叛亲离之中。索妮亚成为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生活中充满争吵与自杀,妒忌与发作,家庭似乎成了地狱。大师托尔斯泰日渐在家庭纠葛中耗尽精力,疲惫绝望。出走的愿望,一次次在脑中酝酿:“像一个印度信徒那样出走!”
1910年9月24日,托尔斯泰和索妮亚结婚48周年纪念日。信徒布尔加科夫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索妮亚紧攥着托尔斯泰的手,如同攥紧她余生里的爱与财产,她身材健壮,精力充沛,脸部透着神经质的乖戾痕迹;再看托尔斯泰,白须,白发,驼背,衰老,两眼直勾勾盯着镜头,除了冷漠,孤独,他的眼光已不投向眼前人。他对女人的恨意,从安排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开始,到晚年更甚。
1910年10月28日,莫斯科寒冬。托翁82岁,他在拂晓前离家出走了!“亲爱的索妮亚,像每个老教徒那样,我想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奉献给上帝。感谢你,并怀念你给予我的一切。”
篇10
哲学在古代称为“玄学”,被人为的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有人说:哲学如同夜空中的星星,美丽但又遥不可及。对于初接触哲学的高中生来说,刚开始对哲学充满了好奇,可是由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能力较弱,面对哲学抽象的概念、深邃的原理、理性化的观点,很多学生学习中慢慢地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哲学课产生了恐惧心理而望而却步。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教学中我不断学习别人经验,总结课堂教学,反思自身不足。经过多年的探索,结合学生实际,结合教材特点,结合个人教学风格,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俗语、诗句、名言名句、日常生活的现象、时政热点、生活热点等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打造了趣味性、生活性、思辨性、历史性的“四性”哲学课堂。“四性”课堂化抽象为具体,课堂洋溢思辨的氛围,闪耀智慧的光芒,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达到了“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和哲学“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效果,让很多学生受益匪浅。
一、讲叙故事,引趣激思,打造趣味性哲学课堂
趣味故事孕育哲理,通俗易懂,回味无穷。心理学研究表明:爱听故事的高中生占85%以上。教师可以将学生爱听故事的心理倾向引向课堂,结合《生活与哲学》教材内容精选一些趣味故事进行教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兴趣,开拓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来创造教学佳境。
例如,在教学“矛盾的对立统一”时,可采取故事式设疑:传说孔子曾带领一班学生找老子请教,老子很老了,正在闭目养神,大概听到了响动,抬起眼皮看了看,孔子赶快请安说:“弟子孔丘特来候教。”过了很长时间,老子才张开嘴,用手指着自己的嘴问:“你看到我的牙怎么样?”孔子说:“已经全掉了”,又问:“我的舌头怎么样?”孔子说:“还好。”老子又合上眼皮,静养去了。孔子带领众弟子退了出来。在故事中,老子教了孔子及弟子们什么道理?刚开始学生会认为什么也没有教,让学生再思考讨论。待学生回答后,教师补充总结,老子的意思是牙齿是刚强的,却是柔弱的,舌头是柔弱的,却是刚强的,看起来刚强的牙齿,敌不过柔弱的舌头。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看问题要用矛盾的观点。
又比如在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个难点知识时,可以用古代的“白马非马”的故事导课,讲完之后,不忙着分析,可以再讲个幽默笑话:“黑马向白马求婚,说:如果咱俩结婚,一定能生出一个黑白相间的什么活也不用干的斑马。”学生一听肯定哄堂大笑,紧接着提问:“白马是马么?”“黑马和白马结婚后能生出一匹斑马来吗?”继续启发“为什么”,学生讨论回答后,由此得出,马是白马、黑马的共性,白马、黑马是马的个性。一个很难的知识点就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中解开了,而且学生的印象会很深。
总之,以寓言、笑话、典型故事、历史故事、哲理趣文等的讲述和分析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道理。这类材料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还可以逐步地吸引学生参与到材料的分析中来,使学生慢慢地改变学哲学难的认识,从而提高学习参与的积极性。
二、结合热点,联系实际,打造生活性哲学课堂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一切知识是从感官开始的”。学生需要生活化的哲学课,需要让学生用感官感触社会生活,通过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最终习得《生活与哲学》课的观点、技能、方法、
转贴于
态度、价值观。教师要努力创设情境,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引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生活的实境中感悟。
例如在教学第一课第一框“生活处处有哲学”时,可以这样导入。电视剧《武林外传》热播以来,男女老少都爱看,影响面很广。播放视频《武林外传》第29回“吕圣人智斗姬无命”中那段吕秀才说死姬无命共3分钟的视频。学生看完了很兴奋,教师借机分析:为什么一个书生能把一个武林高手说死,用的是哲学思维,靠的是知识力量。视频中的经典名句“谁杀死了我”,“我杀死了我”,用到的哲学思维是人的个体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学生一听,太有意思了,从而很想了解哲学这门学科。哲学到底是什么?把学生引进来,让他们在兴趣中自己找答案。
哲学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哲学教学中,我们可以选择现实的时事素材作为背景,设置一定的情景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自主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利于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例如在教学“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时,播放10分钟视频呈现我国的探月进程,让学生自己结合理论来分析讨论,从而真正领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三、循序诱思、展开辩论,打造思辨性哲学课堂
哲学问题也需要在思辨、争鸣、对话和交流中加深理解。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个接生婆,他努力追随母亲的足迹,做一个精神助产士,帮助别人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苏格拉底通过盘问的方式向别人提出问题,诱导别人思考、回答,使被问者不断否定错误,从而不断接近真理,这个方法被称作“苏格拉底接生术”。如果我们能在哲学教学中学习苏格拉底的接生术,善于循序诱思,必将会为哲学课堂增色。
在“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中,播放《林黛玉进贾府》片段设置了三个问题:(1)唯物主义认为是存在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存在?(2)但是林黛玉、贾宝玉从未谋面,却为何在他(她)们的心灵深入处先有了对方的影子?(3)那么倒底是先有我的观念,还是先有我看到的那个心灵之外的真实世界呢?这三个看似矛盾的三个问题,却非常好地引发了学生的讨论、争鸣,达到了教学目的。
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教学中,可以运用教材p67中的漫画《悬挂在山崖上的两个人》设置以下问题:(1)他敢烧断绳子吗?为什么?(2)他真的不敢烧断吗?在什么情况下他就敢烧断,而且非烧断不可?(3)这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这种循序诱思打破传统,善于进行逆向思维,不仅启发了学生的思维,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体现了哲学的魅力。
四、追寻历史,理清轨迹,打造历史性哲学课堂
学习哲学历史,就是要知道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是如何看宇宙,如何看人生,如何思考自己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并给出解答方案的。不学哲学历史,就很难真正讲授好哲学,也就谈不上课堂教学的实效性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认真学习哲学历史,去追随哲学大师的思维轨迹,去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真正所想。在《生活与哲学》教学中适当穿插一些哲学家的介绍,让学生慢慢理清哲学发展的线索,唯如此,我们高中哲学课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哲学课。
例如在教学第三课“时代精神的精华”时,我通常先用2个课时给学生简单介绍西方哲学发展线索及代
转贴于
表性的哲学家。西方哲学发展史中,从古希腊哲学说起,早期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我寻找我自己)、毕达哥拉斯(世界上最有趣而又最难理解的人),到中期的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柏拉图(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哲学被神学所奴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代表人物但丁、哥白尼、伽利略、马丁路德等。近代西方哲学包括:17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代表人物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休谟等;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代表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康德、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然后到哲学的产生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代表人物叔本华、尼采、罗素等。通过这种简单的介绍,能让学生明白哲学的产生绝不是偶然,它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推动时代的步伐,指导社会变革。
免责声明
公务员之家所有资料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写作和网友上传,仅供会员学习和参考。本站非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