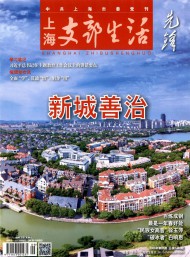世说新语的故事十篇
时间:2023-03-17 16:11:43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1
谢仁祖八岁的时候,父亲谢豫章带着他送客。此时谢仁祖已经是聪明颖悟、应答敏捷的上流人才。大家都在赞扬他,说道:“少年是坐中的颜回呀。”谢仁祖答道:“坐上没有孔子,怎么能区别出颜回呢?”陶公病重,对身后谁可以替代的话一点也没有讲,朝中官员都很遗憾。谢仁祖听说此事后,说道:“现在没有竖刁这样的宦官,自然不会将陶公的话留下来。”当时的贤达认为这是有德之言。谢太傅对王右军说:“人到中年,很容易感伤。我和亲友告别,就会难受好几天。”王右军说:“快到晚年,自然要这样,只好靠音乐来陶冶性情了,还总怕儿女伤害这种快乐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2
在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作家中,江苏作家黄孝阳算得上是一个有抱负、有才情、“喜新厌旧”的作家,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能带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制或文学形态,从《遗失在光阴之外》到《阿槑历险记》,从《人间世》到《旅人书》再到眼下这部《乱世》,作品风格的迥异,作品系谱线条的起伏,即使熟悉他的人都会备感讶异,同时更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这股持续的探索和热情的“折腾”。作家不满足传统和前辈,甚至不愿重复自我,从而不断颠覆既往写作路数和向度,诉诸更新的写作方式和目标,这种“折腾”无疑具有可喜的探索精神,是作家对自我风格化的警惕。《乱世》无疑是孝阳“文学折腾史”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作品。
《乱世》最初名为《一个人的战争》,后改名《民国》,出版时改成《乱世》,小说几易其名,三易其稿。它讲述的是民国故事,以国军营长、抗日功臣刘无果1946年回乡追查大哥刘无因的死因作为中心线索,以此勾勒出民国社会的政治图景:多种政治力量、帮派之间扎根南坪县,各色人物和势力竞相渗透,彼此之间钩心斗角,相互攻讦。从而以刘无因一案作为主轴再现了复杂交错的案中案、谜中谜,以及纷乱、血腥的民国乱世。这是一部很好看、很耐看的小说。熟悉《旅人书》的人都知道,《旅人书》是一部充满理趣和思想,交织着文化隐喻和现实症候的巨型文本。相对于《旅人书》的“加法”叙述,《乱世》则是做的“减法”,这种“减法”意味着作者有意识的“后撤”。尽管《乱世》仍然葆有孝阳对权力、生死、宗教等范畴的热情的言说,以及语言上的精致和结构上的俄罗斯套娃式的繁复,但《乱世》回归了有趣跌宕的故事,形象鲜明的人物,错综复杂但盎然有趣的情节线索。如果从写作目的来看,《乱世》究竟意在何为?作家本人给出的解释是:“我再回想撰写《乱世》的动机,视角会更加多元。比如,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我想证明这一点。所以它显得很奇怪;比如我渴望得到智性与德性双方面的奖励。智性方面,我试图邀请读者与我对弈,我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的草蛇灰线;而在德性这块,我通过某几个人的价值判断,给出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在复制成灾、文学面孔趋同的当下,孝阳拒绝加入众声“合唱”的写作,选择了一种有难度充满智慧的小说叙事。《乱世》是一次艰苦而复杂的写作,显示了孝阳对现代性叙事的苦心经营,显示了他开放式的文学理想以及小说的智性。
从小说的叙事来看,《乱世》无疑有着现代性向度的诉求。阅读《乱世》,首先遭遇的是开篇长达四页纸的“楔子”。“楔子”是古已有之的一个叙事手法,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放在两折之间衔接剧情,在明清小说中,常常放在篇首交代剧情。那么,《乱世》中,在这个民国故事的整体叙事之前,小说设置了一个关于这个故事的前史和诞生由来,其作用有交代剧情之用,但似乎不仅仅是交代剧情,因为女作者之死,小说是残稿等这些内容与剧情并没有直接关联。那么,如何理解楔子,如何理解楔子中这个身份不明、死因不详的女作家,如何理解小说的结尾,成为我们首先应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女作者很可能就是作家的一种自比和另一重人格。作为写作者,这个只在小说的楔子中飘忽而至,而又倏忽走向死亡的女作家,她的身世和背景我们知道不多,但她是一个敏感的人,是一个也许遭遇了挫折、经历了荣光的人,在创作了这部残本小说后,她选择了自杀。这种肉体清零和告别生命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并不惊心动魄,在世俗中并不会激起多少波澜,然而,对于敏感的写作者,一定是在内心经历了暗流涌动、波涛汹涌般的挣扎,对于女作者和孝阳,大概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对于像孝阳这样一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让一个《乱世》的文本层面的写作者,瞬间逝去,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随意的叙事行为。我认为,女作者是作家的一个影子,是作家隐喻化的自我。女作家遭遇的生的无力感和肉体清零的选择,是孝阳关于生死命题的一种文学延伸。熟悉孝阳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具有哲学家气质和关乎哲学命题的作家,他的文论,他的访谈,他的自述性文字,以及很多小说都在专注地思考着生死,思考着作家如何用文字安置生死,如何抚慰生的迷茫和死的痛楚。女作家没有完成自己的小说而卧轨自杀,这种决绝和大时代下人的无力渺小,是孝阳对作家个人甚至作家群体命运的一种悲观或夸张的叙事。简言之,女作家的命运有孝阳身为作家的夫子自道,女作家的残稿以及被编辑所忽视的现实,与当下社会中作家处于普遍的边缘化和有意识的遗忘的处境,具有一种隐秘的对应关系。
孝阳非常看重叙事维度的多样性和事态走向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创作的诉求甚至表现在他对小说的楔子、尾声、跋这些细小环节的经营上。他自己说:“序与跋无非是一个供众人辨认我脸庞的标签,除了满足一些廉价的好奇心,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又有什么意义呢?”《乱世》如果跳过几千字的楔子、跋,直接进入故事,这个民国司法黑幕的故事照样会熠熠生辉。但孝阳选择了复杂,写了一个不知身世的女作者的死,并且不厌其烦地在尾声和跋中告诉读者自己对这种现代性叙事向度的理解。小说是在第二十章,即七顶山土匪联合城中袍哥会攻打南坪县政府的纷乱战火中结束的,第二十一章是编辑朋友(当然是小说虚拟的另一个人物)自己续写的。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原有叙事结构上,呈现了某种断裂——这种断裂当然是孝阳自己的有意为之,这种断裂用孝阳的话说是为了让读者“从一个大家都听起茧的套路中跃出,跃至一个广阔丰饶处”,女作家的“残稿”中断了小说的自由逻辑,使小说叙事逻辑不再理所当然或理应如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编辑朋友”参与了第二十一章的书写,其实,每个读者何尝不可以继续书写二十二、二十三章,直至无穷呢?因而,序、结尾和跋对于《乱世》,对于孝阳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面,蕴含了孝阳对现代性叙事的一种渴望和实践,这种努力针对的恰恰是要反叛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逻辑和传统的叙事结构。因而,打破传统的封闭式、起承转合、有始有终的叙事结构,呈现叙事的多种可能性,甚至吸引读 者参与残稿之中,对没有完成的叙事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进行个人化的阐释,这是这篇小说借助于楔子、结尾和跋所要达到的另一叙事诉求。
二
解读《乱世》,“故事”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在《旅人书》中孝阳对于故事已经开始启用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了,因而,《旅人书》中的故事要么是抽去了逻辑关系的事象呈现,要么是因果中断的断片,或者是高度哲理化、象征化的抒情议论的载体。而《乱世》中的故事则呈现出明朗、具体、生动的特点。故事在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区别在于呈现的方式不一样。“传统故事的元素,如事件、情节、人物、环境都很集中,有场景感,活动方式,有连续和冲突,有发展过程与结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简单说,故事有可讲述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小说不是没有故事而是故事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他们不再相信故事整体的力量,不再相信时间的连续和逻辑的力量,简单说,现代人不再相信一个由故事组成的封闭空间。”因而,可以说,在信息爆炸与图像化、视觉化的当下,读者并不排斥故事,相反一个好的故事往往是文学或影视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按传统的因果、顺序等范畴讲述故事,还是用现代主义的反逻辑、碎片化的方式讲解?显然现代主义的讲述方式对读者更具吸引力。孝阳对一般读者的“故事”情结及其弊端有着相当深刻的体认,他说,“当下的文本读者需要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事的完整性,这种‘有头有尾’在碎片化生存的今天弥足珍贵,它帮助读者想象自己的悲欢离合。但这种经验的传递与情感的分享,是在追求一个更大的公约数,不可避免沦为陈词滥调的命运,无法提供真正的原创性与现代性。”因而,在《乱世》中,故事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和面貌出现的,而是高度现代性意义上的。
《乱世》的故事主干是国军军官刘无果回到四川偏远的南坪故乡探亲,获悉感情甚笃的大哥无因已离人世,于是他和助手蒋白开始追踪案件的由来。随着他们的走访和对案情信息的积累,无因的死不是变得明朗和豁然,而是更为迷蒙和复杂。无因之死如同一个罗生门一样的事件,不同人的叙述更形成了关于所谓真相的罗生门式的复调声音。回乡伊始,刘无因的死因是经由无果的发小狗子建构的,狗子代表的是一般民众对这件事的理解:无因刚娶之妻周氏加害于丈夫,后与袍哥会老大罗秦明勾搭成奸。证据是周氏在丈夫死后藏身于罗秦明家中,数日后又去法院自首。随后,警察的解释是无因病重吐血而死。接着,刘府的管家五叔成为怀疑的对象,因为五叔很可能因贪念刘府的家业而动杀机。接着,少年杨二作为另一个“见证者”道出了刘无因是南坪县种植大烟的始作俑者,同时强抢民女周氏做妻。但在说书人的口中,刘无因是一个体恤民情,奉公守纪的抗日英雄。这样,随着无果对案情的了解越多,疑窦也逐渐增多。案情趋向复杂化的同时,大哥刘无因这个南坪县家喻户晓的“英雄”,其身份也变得可疑。刘无因究竟是一个英雄、功臣,还是一个种植鸦片、强抢民女的恶人?当然,事实与真相远非这么简单。随着李鸿远、王培伟、周怜花的依次叙述,人物的真实身份,各种势力和帮派的真实动机,以及刘无因的死亡原因逐渐清晰。收缴南坪县的藏匿烟土、大量钱财,以及寻找汪伪潜伏名单,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和众多人物丧命的原因。《乱世》中布满了太多的迷局,太多的机关,太多的悬念,当读者跟随着小说步入民国那段波云诡谲的历史深处时,备感云山雾海、惊心动魄而又妙趣横生。结尾处,《乱世》的内部真相和关系谱系无疑超出了很多读者的预期:王培伟和罗秦明是同一人;五叔和王培伟是父子;周怜花由于军统身份不得不杀了丈夫刘无因;刘无因因为游说土匪被施腐刑……在对历史之谜抽丝剥茧的阐释中,读者也似乎完成了一次思维的体操和心智的锤炼。
对于《乱世》来讲,呈现这样一个趣味、缠绕、智性的故事固然是一个方面,但通过这样一个其实是“不确定”的故事来表达一种多维度的叙事理想,是这部小说更为重要的一个诉求。《乱世》中的人的选择和结局,事情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是多样化而非单一的。比如,小说的第十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分别借助于梦境、幻觉、月光下的事实(全知视角呈现的一种现实可能)来叙述纷乱的案情和复杂的现实可能具有的发展向度,这种虚拟的现实一种构成了事物真相的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小说让众多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各自独立又共同汇聚到刘无果这里。每个声音都从自己的角度参与解释谜底。因而,形成了对一个人、一件事的不同立场和见解。比如对于李鸿远的认识,周怜花认为李是一个对上舐痔捧臀之人,对下心狠如狼之辈。而五叔则认为他是勤勉用心的父母官。刘无果认为他是一个深谋远略、爱国恤民的人。再如,围绕刘无因的死形成了病死、精神错乱自杀、妇人所杀等多种见解。《乱世》在讲述故事时并非以某种先验的结局或真相作为故事的终点,《乱世》试图达到的实际上是提供一种开放的空间和叙事逻辑,让读者参与其中,完成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想象或填充。《乱世》的尾声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她好像是试图让文本从‘人之命运’的维度(而不是蒙太奇、拼贴、元叙事等现写作作技巧),摆脱单纯的线性,形成复杂的旋涡。而要理解这个旋涡的异乎寻常,就需要读者摆脱过去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去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能调动更多的智力与耐心,更深地进入到旋涡中,去重新连接,乃至于想象人物关系、因果变化,对现有这个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再做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呈现与阐释。”因而,从呈现故事的方式来看,《乱世》是用“反故事”的方式讲述故事。“反故事”质疑的是传统叙事逻辑,以及先验的因果预设和可预期的情节发展。“如果说经典叙事是核心的网络(或链条),它提供的选择途径中只有一种是可能的,那么反故事(antistory),就可以定义为是对这一惯例的攻击,它把所有的选择视为同等有效的。”“反故事”是典型的现代叙事策略,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小说打破了预设的 故事结局,使小说具有了多种可能性。这种手法,孝阳在《旅人书》中已经反复运用,其作用无疑是极大地解放了文学叙事,使小说文本空间大大拓展。
《乱世》的语言是充满生机和智性的现代汉语。有人曾问苏珊·桑塔格,什么是一个作家最应当做的。她回答说:“爱文字,为句子搜肠刮肚。还有注意这世界。”桑塔格所说的正是优秀作家对待文学语言必须具备的一种姿态和追求。当代汉语写作的危机其中之一是文学语言的危机。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开端,五四文化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出于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的需要,采取激进主义的立场,对古典文学和文言文采取的是整体否定的态度。这样中国新文学的语言实际上是从零度海拔起步,开始自己的语言现代化之路。“五四”的这场白话文运动对于后世文学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现代语言在俗与白的起点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充满动荡和意识形态的语境里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戴望舒、卞之琳、胡风以及后来的九月诗派对丰富现代汉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20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毛文体和苏联的政论式语言对建国后的文学语言形成巨大影响。五四时期语言的文白之争演变成语言的偏执化发展,到了“文革”,现代汉语已经发展成一种充满暴力和火药味的汉语系统。新时期之后,现代汉语迎来了解冻和变革。自艨胧诗人开始,中国的很多作家对现代汉语的解放和丰富做出了很多贡献。
当下文学中,语言的俗化、粗鄙化严重,很多作家放弃了语言的雅化、智性的追求。孝阳的《乱世》让我们读到了一种精致、雅化的智性语言,言白互渗而又清新脱俗。《乱世》的语言是非常考究的典雅语言,小说中的人物如县长李鸿远、法院推事王培伟、罗圈腿郎中,操持的都是具有文言气息的古典语言,即使是国军营长刘无果与其莽汉式随从蒋白,使用的也是极为典雅的半文半白的语言,除此,管家五叔,七顶山土匪刘富贵等人的语言,都是极有智慧的语言。比如描写幽静而又森严的李鸿远的处所,先写极其粗大的合抱之木给人以青黑之感和暑杀之意,然后细写人的触觉感知以及处所情形:
“人像是一下子浸入清水,连皮肤上的毛孔都立刻惬意地做起深呼吸。进侧门,眼前骤然一宽,飞檐翘脊,壁染朱红。大成殿丹墀左右,立有一对青石狮子。石狮头部略有破损,脊背处裂缝中野草生出,挑出几许荒凉之意。”
再如说理,极有理趣和对人生世态、宇宙万物的了然与参悟:
“世间事,大抵是笙歌鼎沸,然后曲终人散。”李鸿远一叹,“散是必然,聚是偶然。聚散之间便生出万千姻缘,托起红尘滚滚。彼地,你是叱咤风云的主角;此时,你或许就是一个死跑龙套的。又或者说,前一秒钟,你还被众生瞩目,后一秒钟已然横尸街头。”
描摹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和交锋,比如“五叔与狗子住了嘴,互相注视的目光里就有了十八般兵器。”三言两语将不学无术的狗子与管家五叔在对簿公堂时相互间的仇视勾勒出来,用语细腻而犀利,极具动作性。
《乱世》的语言有明清小说的谨严工整、精致典雅,尽管稍显繁复但充满了理趣和智性。用语谨严雅致的同时,小说时有幽默谐趣之语,比如:“已近正午,阳光跟牛皮拧成的鞭子一样,抽得人鬓角发汗,胸口处阵阵发烫。刘无果心中燥热,牙缝里溅出几字‘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枣红马似觉得‘禽兽’两字是对自己的侮辱,咴溜溜一声长嘶提出抗议,扬鬃跃蹄,倒让守门团练士兵差点惊落了手中步枪。”
可以说,孝阳是用心经营《乱世》的语言表达的,他让这个民国故事拥有了民国文化语境和政治氛围,更让卷入了这场民国司法黑幕中的人都拥有了民国式语言。尽管我们已难以准确说出民国语言是怎样一种形态,但《乱世》中的人物语言以及叙述语言与小说构建的民国“知识地理”和文化历史版图已然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何谓民国知识地理和民国文化历史版图?阅读《乱世》,我时时诧异于小说对民国政治风云、文化历史、风俗传统的精细呈现,民国的历史旧闻、掌故轶事、风俗民情被作家信手拈来,分析民国基本时局、江湖帮派则鞭辟入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语录、以及蒋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四维”、章士钊为戴笠所题挽联等历史知识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民国风范和文化政治气息。尽管《乱世》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小说建构的民国知识地理和民国历史坐标构成的民国历史语境是坚实而丰富的。阅读小说时我就不断在想,关于民国的这些细部知识的考古式征用一定耗费了孝阳不少精力,写这篇小说需要作家有相当的民国历史储备,一定需要阅读大量的民国史料,并收集相关素材,而这种钻故纸堆的事孝阳竟然做得那样认真,那样煞有介事——这是《乱世》非常扎实和迷人的方面,也是孝阳令当下很多以简单和浮泛态度从事写作的人感到羞愧的地方。
《乱世》是孝阳民国情结的一次演绎和释放,可以说,语言是他进入民国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乱世》孝阳试图在探索一种智性的现代汉语表达方式。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语言不是纯粹的文笔,更不是所谓的堆积词藻。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要理解世界的意志及其表象,语言是渡江之筏。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语言被暴力与金钱渗透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探索一种白话的书面之美。”我想,在如今当代文学格局中,孝阳的这种语言自觉和《乱世》的智性而雅致的语言实践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当下很多小说语言乏味、无趣,有的是缺乏这方面的语言天赋和语言能力,有的是没有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而疏于对语言的经营和探索。优秀的作家应该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同时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不断去丰富本民族的文学语言。为了版税和畅销书,为了迎合某种风潮而进行的某种语言实践和文学写作,无疑是值得警惕的写作立场。孝阳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作家,在这样众声喧哗、作家居于时代边缘的时代,他弃易就繁,选择了一种有难度、有挑战的写作方式,努力让小说文本融合巨大的时代信息,尽量让文学语言具有诗意,让小说从简单、朴素回归到复 杂、典雅,孝阳的这种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孝阳无疑是这个喧哗时代真正为纯文学守灵的人。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3
关键词:文学;亡灵书写;《第七天》;《灵魂摆渡》
当代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种类繁多,从题材到形式,都带给人们极富差异的阅读体验。在当代作品中,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相关性。从几年前古墓系列小说备受青睐开始,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亡灵书写的前沿话题。近期小说《第七天》、影视文学作品《灵魂摆渡》倍受关注。抛开外在声色科技手段,单就作品脚本主旨而言,二者都是亡灵叙事的相同主题。探讨两部作品的写作主题和叙述手段,可对这一时期出现对亡灵叙事的热衷现象略窥一二。
一、亡灵叙述与作品主旨
亡灵在中国的古语中俗称为“鬼”,自有人类传说始,鬼故事也随之绵延不绝,中国古典精粹小说《聊斋》被奉为古代鬼故事的集大成者。一个时代对死亡后的世界很感兴趣,要么是寻找精神依托,要么是逃避或针砭现世。
余华《第七天》是以一个死去七天的人的所见所为记录成文,主人公杨飞是一个鬼魂,本在死后对现世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和价值,这一点他延续了文学作品中的先锋精神。作品中亡灵的身份和普通人差别不大,没有中国传说中的“鬼面獠牙”,同时,亡灵经历的事情也和世间人的日常生活相差无几,所以,这本小说,是典型的“托鬼世写人事”。
首先,主人公杨飞七天的所见所闻基本勾勒了一个问题时代的全貌。光怪陆离的生活,活人的思维延续至死亡是要有墓地,那么没有墓地的灵魂去处呢?“死无葬身之地”。余华把死无葬身之地塑造成了一个亡灵完美的归宿,没有恩怨、没有阶层差别,没有生活之累,是众生平等的和平的理想伊甸园。余华用一个亡灵写了所有亡灵,用一个死人写了一世界的活人。余华借助了一个亡灵视角,将现世的典型社会事件加以汇集引人深思;用社会不公、爱恨情仇反思现实世界活人的切身利益。现世的荒诞让人死后仍不得安宁完满,这就让人对现世的社会加以警醒。
其次,余华选择亡灵叙述的写作方式从形式与效果来看,都是在渲染“荒诞”色彩。死人的世界本就是未知的,所以以死人做主人公是极其荒诞的,因为内延范围太广,写不好非常容易成为失败的作品。对此,余华设置了灵魂“寻找”父亲的情节为作品主线。和亡灵相关的每个小故事都反映一个现实问题,通过夸张与戏谑的笔法反映出来,问题得以扩大化与典型化,突出社会的荒诞。所以,从亡灵叙述的主题的意义上看,余华的这部作品不仅仅是通过亡灵写现实,而是其先锋精神的延续写作,凸显社会与世界的荒诞性。
网络电视热剧《灵魂摆渡》又名《见鬼之灵魂摆渡》,在主题上较符合中国传统的亡灵书写。其核心主旨是在“道”的轮回的法则下颂扬真情、鞭笞丑恶。因为该剧情节紧扣,每集都有深意能给人以启迪警醒,受到观众热捧。
首先,作为影视作品,它除了借助视觉和听觉的手段,加强故事的感染力外,还在人物对话、情景旁白等方面运用传统文学作品表达手段,使主题夸张化和警醒化。其次,这部网络剧由20集串联而成,每集的故事大多无关联,陈述了近二十个鬼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有中国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也有和西方传说契合的“灵”的存在。除了作品的三个“显性”主人公:有“阴阳眼”的便利店的店员冬青及女友王小亚、店长赵吏外,还有很多“隐性”主角:每集故事的主人翁。其亡灵叙事将亡灵分为很多类型,每集选其一展开故事。就单纯的“亡灵”主题的“鬼”特性来说,《灵魂摆渡》显然囊括更广,内涵更丰富。
再次,与《第七天》中通过亡灵映射现世不同,《灵魂摆渡》更看重人的“意念”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正如俗话常说:“鬼本不存在,它只存在于人的心里。”尽管在作品之中鬼被设定为客观存在,但其产生的最终源头皆因“执念”:现世生活中强烈的欲望或心愿,主角或走火入魔或鬼迷心窍或自取灭亡。作品将心理意念的力量放到了无限大,既有中国传统的“黑白无常、地府、燃犀、字灵、冥王、杨贵妃、画中仙、饕餮等”传统志怪典故,还涉及“好色、暴食、贪婪、懒惰、愤怒、妒忌和傲慢”的西方“七宗罪”概念,将人性作为终极审视目标。所以,这部作品借助剧情中出现的一个个亡灵故事或警醒人的贪婪、自私、欲望、诱惑等劣根现象,或叹惋天地间存在的爱情、真情、善良等美好感情。这里的亡灵叙事更多的是提醒读者和观众警醒人性缺点,追求灵魂的真善美。
二、亡灵质量与现实参照
小说《第七天》和网络热剧《灵魂摆渡》虽然都是在讲亡灵故事,但是因为写作角度写作目的不同,造成了很大的相异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故事中的亡灵的数量有多寡之分,亡灵质量的描述侧重点也有差别,叙述目的效果迥异。通过亡灵书写达到现实目的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但是在关照现实的程度和内涵上,一部重在反讽现世社会,一部重在解剖警醒现实人性。
杨飞作为《第七天》的主人公,围绕他寻找死亡的父亲的旅程中,囊括叙述了多个故事来映射社会现实。作品的写作线索十分集中,《第七天》是集中一个中心展开的亡灵书写。这样的写作方法可以使主题更凸显,符合长篇小说的常规写作策略。但是在叙述效果上就会面临挑战,通过一个故事涵盖所有小故事要求作品有极强的衔接性,且逻辑严密,结构合理。作品正是在杨飞的大故事背景下,附属了医疗废品婴儿事件、强拆事件、卖肾事件等众多社会事件,会使部分初读的读者产生散乱拼凑之感。所幸,余华非常巧妙的用了“第七天”作为文章题目和结构,依托了西方文化的“上帝造世说”,又暗含了中国的语境中死者“头七”还魂说。他将七天内发生的所有故事放在大结构下设的七个小结构中,才使附属小故事发挥其丰富的内涵效果。总体来说,第七天用一个亡灵做叙事主角和线索,以“反讽”和“夸张”的形式构建了荒诞的社会“镜像”,死人是活人的倒影。通过这一个亡灵主线将社会的荒诞全貌展露无遗,较完美地达到了写作效果。
毋庸置疑的是,《灵魂摆渡》中的亡灵角色特别多。每一集都有真正的鬼魅主角出现。亡灵的数量之多带给读者以新奇感,是受篇幅所限,能将一个新鬼的故事讲述完整并达到感动人心的效果是有难度的。恰好电视剧脚本的“短篇单元剧”写作模式强化了各故事之间的独立性,降低了全剧结构的要求,同时“阴阳眼”的情节设置加强了大线索与小故事之间的逻辑联系,使多个亡灵的出现合情合理。故《灵魂摆渡》中的亡灵虽多,但是相互不冲突,在写作方法上类似于《聊斋》的结构形式,每单个故事拆离成独立的个体,进行针对性的叙述,强化感染效果。观众通过深度与宏观思考之后能把握全剧整体的主题。比如第九集通过讲述“字灵”的故事,将作家创作的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幻化为真。这一“字灵”内涵可上升至所有的“物灵”,只有人类用心对待,爱意形成的强大意念足以使所有的有形无形的作品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宝贵遗产,用心就会有收获。又例如剧中用一个平凡女子为求得年轻美貌膜拜被邪灵附身;人类贪图美食沉溺阴谋不自知等故事,来表达贪欲对人性的侵蚀对灵魂的伤害。单个的独立故事结构和变化多样的主人公角色正有利于强化亡灵书写对人性的警醒目的。
三、亡灵语调与语言特色
两部作品都用到了死人身份,相貌有异,语言也各不相同。巧妙的是,每部作品都找到了适合自己人物身份的语言并加以烘托主题,成为它们独特的“亡灵书写”语言特色。
余华曾坦承《第七天》后期的修改集中在语言部分,可见作家对言语表达的重视。他为了追求行文逻辑上的合理性,模拟、想象死人是怎样开口说话的。所以,他设置了一个死人腐烂至骷髅的外貌,临死的变形模样也被保留,塑造父子相见不相认的情节合理性。其次,他将亡灵的说话声音加以陌生化,死人嗓音改变,切断亡灵和前世的直接联系,故事的发展空间就扩大了。再次,在具体的语言内容表达上,风格接近于灵魂的虚无缥缈的状态,叙述变得平稳、直白、冷冰冰的,没有感彩。没有“温度”的语言切近死亡给人的感觉,死人的世界注定和现实世界有所区别,那么交流上的语言表达就成为最大的“区别”方法。有些读者说余华的语言退步,以往温情语言变换成没有色彩的修饰缺陷的句子,缺失了文学语言特有的感染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余华特意强调“亡灵书写”的现实,将语言进行了意向调整,为的是更有逻辑感、更符合亡灵主题。
《灵魂摆渡》是影视作品,它的文学脚本只需要将故事的来龙去脉陈述清楚、将情节发展展示清晰即可。但是这部作品的语言是值得玩味的,它融入了很多文学性词语的修饰,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带给读者观众以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不但借用张爱玲的名句、融入旁白意境,还有时代感极浓的台词,使作品语言十分有感染力。文学性语言和辞藻具备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如若在影视作品中放置的不够恰当就会流于煽情性和通俗性,运用的合理巧妙就会给整个剧集增色添彩,使作品不仅以故事情节取胜,更以语言细节动人。比如,第四集的剧情讲述了一个女子怀疑老公豢养鬼妾,后愕然发现她自己才是鬼,且早已身亡。老公不舍她离去,用灵犀续鬼魂之命,使人鬼得续前缘。故事除了情节设置巧妙之外,语言的力量对夫妻二人的温婉爱情的烘托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旁白:“忘川之畔,与君长相憩,烂泥之中,与君发相缠,存心无可表,唯有魂一缕,燃起灵犀一炉,枯骨生出曼陀罗!”传说点燃灵犀,便可人鬼相通,表白性的表达方式感慨着爱情的伟大,让读者观众更加感动唏嘘不已。
四、结语
作为当前网络和小说这两个潮流的综合体,《第七天》和《灵魂摆渡》对亡灵的关注,用鬼魂来表达主旨,可谓颇有深意。虽然两部作品的体裁式样有别,但是就其文学性而言,它们的亡灵叙述主题是一致的,都在用“鬼事”表达“人事”。通过写作主旨、作品细节、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分析探讨,两者在相同的“亡灵叙事”主题下,依托鬼世反省人世,将主旨归依到社会现实、善恶人性的深层意蕴中,一部重在讽刺社会荒诞,一部重在警示人性灵魂。这一写作手段的热用在现时代频现,反映出作家编剧以创新性手法、先锋性卖点引导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1]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2]《见鬼之灵魂摆渡》.网络电视剧,2014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4
一、童话开路,用想象作翅膀引导学生探究
童话,之所以让学生喜爱,主要是童话采用幻想、夸张、拟人一些表现手法,呈现离奇的故事。毕竟在童话世界里,一切动物、植物都能够像人类一样,可以说话,可以思考、还能够像人类一样生活。在童话里,所有善良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良好的结局。而童话中的这些东西,最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积极的想象思维活动。故而,我们在童话教学中,对学生的想象应该给予积极引导,让其在想象中进入童话世界的美妙意境之中。激发小学生在想象中探究知识。例如,我在执教《蒲公英的梦》这篇童话的时候,为了引导小学生的想象,向学生提问:“蒲公英在经历了一段遭遇后,她做了一个梦,如果你是蒲公英,你会做这样的美梦吗?”通过这样一问,学生的想象一下子激活了,就不由自主地随着教师的进一步引导而展开学习。
二、童话开路,用诵读走进童话的情感世界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是就是对作品的读,只有多读才能够深入到作品的个内容中去,以及深入到作品的情感世界去。在应用童话开路进行创新教学的时候,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性让学生去诵读,有感情地诵读,让学生充分体验童话故事中人物的情感。由于童话故事具有很强烈的爱憎分明思想,故事也充满了无数的情趣性,学生对童话故事中的人物有极浓的模仿兴趣。故而在语文教学中,多让学生诵读,可以很好地通过这种诵读方式,让他们的心灵走进童话的情感世界。比如教学《四季童话》,这篇文章通过对春夏秋冬四季劲舞的描写,展示了大自然的美好。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积极地让学生多诵读,在优美的文字中,让其走进童话世界的情感中去。当然,诵读的形式尽量多样化,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诵读的热情。
三、童话开路,用表演形式积极感受童话的形象之美
教师通过对学生进行实时的想象引导,以及让他们有感情地对童话故事的诵读后,学生对童话故事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掌握。这时候,在学生的内心深处,强烈地萌生出一种要表现的欲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用童话引路,主要就是借助童话故事的形象性、语言的生动性跟学生的强烈表现欲望充分地结合,进而让他们在表现中感受童话的形象美。当然,这里的表现形式,多以表演形式出现,可以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表演之中去。通过表演,让他们更好地领略童话故事的思想情感,让他们学得快乐,受到美好人物形象的熏陶。例如在教学《狼和小羊》这篇课文的时候,在引导学生对童话故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将童话故事改编成课本剧。让一学生扮演狼,让另一学生扮演羊,教室就是当时的环境。通过绘声绘色的表演,在活泼有趣的故事中,进而不自觉地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其学习效果自然就提高了。
四、童话开路,用品读来感受童话的精彩
童话故事在语言上,有着明快的节奏,有着简洁的特性。故而,童话中人物的语言、性格、思想就很具特色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运用童话开路,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对童话故事的语言进行有效的品味。对童话故事中的语言品味,有效地增强学生的语言素养。例如教学《四季童话》的时候,可以对“春姑娘爱笑,笑出一个暖暖的太阳。春姑娘爱哭,一撇嘴就细雨沙沙……”多加品读,品味这里的“笑”“哭”两个字就很好地体现了春天天气的特色,让学生从这些词、这些句子中充分体会春天的美。
五、童话开路,用练习去强化学习效果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5
如此结构,层层深入,恰与“授之以鱼一授之以渔一悟其渔识”的育人三境界暗合。这正是该书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文学研究者、高校文学相关专业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所受用之处。
古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今之眼光看来,存在明显疏漏。首先,“鱼”是目的,“渔”是工具,二者不能割裂。其次,“鱼”和“渔”都有着丰富的种类,不能奢望掌握了一种工具就能捕获所有的鱼,如何针对要捕之“鱼”选择合适的“渔”才是关键。对此,《小说艺术十二章》以实现小说艺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融合为基本理念,采取因“鱼”而异的策略,将“渔”落到实处,同时实现了“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
对于文学爱好者、评论者、研究者,“鱼”和“渔”分别对应其关注的对象和方法。对此,《小说艺术十二章》在经典小说作品文本分析的实践中,合理诠释了文本与方法、个案与理论的完美结合。首先,逐层选择有代表性的经典小说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使得原本复杂的文学理论变得层次鲜明,也使理论中原本易混淆的概念变得明晰。比如,第三章的“虚构话语世界的文学语言”一节,分别选取《穷人的专利权》和《菜园》为个案,区分说明“语气”和“语感”两个语言要素的文学韵味异同。其次,分析具体的作品文本,使得原本抽象的分析方法变得具体可感,也使经典小说作品的意义潜质得到立体呈现。比如,第八章的“故事嵌套”一节,选取了“有两个故事和两套叙事话语”的《我的叔叔于勒》、“有三个故事和三套叙事话语”的《象棋的故事》和“一个大故事嵌套六个并列的小故事,以两套话语讲述”的《周秦行记》进行分析,向读者演示了分析方法的具体操作。而且,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还同时出现在第八章后两节“场面与小说艺术”和“心理与小说艺术”中,多面彰显该文本在“功能层”上的价值。
对于中学语文教师,“鱼”和“渔”分别对应其教学的两个侧重点:知识和意义。知识需要记忆,意义需要创造。二者密不可分,又有所区别。对此,《小说艺术十二章》提出了以知识介绍为前提,以文学经典为依托,引导学生体悟意义世界,提升审美能力的教学任务。具体到经典小说的教学,路径如下:首先,有关小说家的创作背景、作品风格等背景知识,以及小说艺术的基本要素、基本类型、发展历史等基本知识,属于现象界规律,属于涵义世界,应予以详细介绍。其次,是否需要意义,是人区分于动物的根本所在,而叙事是小说的第一要义,是人类处理经验的方式之一,体现人类对意义的追求。教师以文学研究者身份关注小说作品,解读小说作品艺术价值的形成,便自然提升到对叙事理念的探讨,由此引导学生思考意义之形成。最后,意义绝非白行生成,而是读者借助于作品的创造,经典小说作品是一个凝聚意义的宝库,教师立足于经典,在掌握艺术规律的同时,启发学生南理解到阐释再到创造意义。
“悟其渔识”是“鱼”和“渔”融合的最高境界,即,在收获“鱼”和“渔”的基础上,有所参悟,形成创新。对于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悟其渔识”意味着将小说艺术本体论和方法论融会贯通,同时洞察小说艺术背后的深层理念,以挖掘新的理论增长点。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悟其渔识”意味着在熟知叙事理念和小说艺术价值之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悟出自己的意义世界。对此,《小说艺术十二章》提取出“故事”概念,作为小说艺术的核心要义,以引导读者达到“悟其渔识”的境界。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6
[关键词]吉本芭娜娜;后现代主义;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I3/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135-03
文学创作和批评方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经历各种流派的思辨和撞击发展至今。文本间性又称为“互文性”、“间文本性”和“文本互涉”,最早是由法国符号学家、解构主义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权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1966年提出来。文本间性是指文本的意义与其他的文本相关联。克里斯蒂娃所描述的“文本间性”,是索绪尔的构造主义符号学(符号在文本结构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的研究)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各文本[特别是小说]和话语中存在的多义或异质、异形的研究)统合而尝试出的新概念。克里斯蒂娃认为,如果并不是作家向读者直接传达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由其他文本被传达的“符号”互相参杂、渗透、过滤,从而文本间性的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例如,我们在读詹姆斯·乔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时,我们作为近代人的文学性实验,或者作为对庞大传统的反应,或者作为对他人对话的一部分,亦或者作为对自我谈话的一部分来共时性解读文本。这种文本间性的文学见解,正是对罗兰·巴特“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作者,而在于品鉴其的读者”观点的补充。
美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伊哈布·哈桑通过后现代主义对抗现代主义的角度,罗列了一系列与现代主义相比较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中一项就是现代主义的“体裁/疆界分明”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互涉文本”的比较,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基本特征之一即包含了“互涉文本”。罗兰·巴特和德里达、利奥塔等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要求消解元话语和同一性,主张文本间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大力推崇文本间性的概念并加以发展,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中与“超文本”性相互联系研究。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日本,随后逐渐形成为一种时堪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吉本芭娜娜出身于日本东京,在日本是与村上春树和村上龙齐名的大众小说家,其父亲是日本著名评论家、诗人的吉本隆明,姐姐是漫画家宵子,母亲和子是出版了句集《寒冷前线》等的日本俳句诗人。在这样的书香世家里成长起来的吉本芭娜娜,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在1987年由小说《厨房》获得海燕新人文学奖而出道以来,已经出版了独著43部小说,随笔27部,合著10部著作,成为较多产的作家,其中四部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其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是颇具国际知名度的日本作家。
《N·P》是芭娜娜早期小说中较长篇的一部,1990年刊行,1993年芭娜娜凭借该小说获得了意大利SCANO文学奖,曾被改编为日本同名电影。《N·P》是以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事,主人公风美的男友庄司因翻译一个住在美国的日本人作家高濑皿男的小说而自杀,由此展开了故事情节,机缘巧合下风美遇到了高濑的两个与自己同龄的孩子,在逐步产生友情互相了解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高濑在自己的小说集《N·P》里收录的第九十八篇小说中所描述的人和事即是高濑本人和自己未曾谋面的私生女“萃”相遇的一段不伦之恋;而在这第九十八篇小说之外作家高濑自杀后,“萃”又巧遇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已彦”并坠入爱河,两个纠缠在亲情、血缘和爱情痛苦中的年轻人最终选择分离迈入新人生的结局。
一、语篇内互文
小说最精彩之处,即在于其语篇内的互文互动,也具备了元叙事风格。元叙事是后现代小说叙事手法中的一项重要技巧,即是作品中套作品,文本中套文本。虚构世界的虚构行为已经构成故事,而且充当了小说的结构功能,从而使得故事本身具有了不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内在独立性。《N·P》中小说内情节设置了一个三层同心圆,最内层是自杀了的小说人物《N·P》的作家高濑的第九十八篇小说故事情节;中间层则是相对于第九十八篇小说而在芭娜娜小说中相对现实中作家高濑由于某种缘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遇到了自己的私生女并与之相恋的故事;最外层则是高濑所著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其自己的女儿“萃”在他自杀后又无意中遇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并与其相恋的哀伤故事。最内层与中间层形成了共时关系,而最外层则与中间层形成了历时关系,使得小说充满了动态、三维立体感,故事情节扑朔迷离,让人回味无穷。
语篇内互文互动,其意义在于如下两点:(1)作者自我评价和审视。元叙事本身也渗透着文内评价的含义,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在互相评述小说中的同名小说,从而再现其创作小说时的想法和思维。在芭娜娜小说《N·P》中,主人公风美与乙彦再次相聚时的场景,作者借风美之口述说,“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本应是存在于故事中的属于过去的人物”,“好像在一个三维空间里再次重逢”,此时,作者芭娜娜也如风美一般置身于小说之外,把创作的灵感溶入到了小说当中,也让读者感受到动态的层层叠加的思维。(2)与读者对话。文学话语不仅与外部世界相关联,也和它自身内部的参考文字相互渗透。因此,互文性往往呈现出混合的形态,这也是它的特色。它将若干的言语、语境以及声音罗列在一起,也为读者提供了多层次的阅读,使得读者可以从组成文本的素材中读出不同的话语。《N·P》小说中套小说,相对于高濑的第九十八篇小说,主人公风美、乙彦、姐姐关和妹妹萃之间发生的事确实相对现实的,也即是究竟是现实还是小说,似乎很难分辨了,这就产生了隐喻,隐喻着即使在人类社会的现实中,也往往如同小说故事里一般充满了变数,充满了扑朔迷离的因缘,充满了真挚而令人向往的感情,值得人们去追求,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勇于自我救赎。读者的任务就是与这一他者对话,或是与这种超文本形成新的互文性关系:作者交给读者的这种互文性阅读任务。
二、与传统、习俗、现实的互文
《N·P》在整个小说情节编排的过程中,不断融入作者自身的思想,在小说的第一页,即写道:“讲完怪谈百物语的第一百个故事时总会发生什么,而在那个夏天,我的体验就恰如那第一百个故事,仿佛真切地经历了那种事情。”在此,作者似乎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源泉:怪谈百物语。“怪谈百物语”是日本传统的以鬼怪故事为题材的民间游戏,晚上友人们聚在一起点上100盏灯开始轮流说荒诞鬼怪的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就掐灭一盏灯,相传第100个故事讲完所有的灯都掐灭漆黑一片的时候,鬼怪的真身就会出现。日本历史上也出现了收集这些鬼怪故事编辑而成的书籍,日本延宝五年(1677年)的《诸国百物语》等就是代表作。从室町时代开始进一步发展成为怪诞文学,江湖时代成了一种风潮。日本现当代除森鸥外著有同名小说之外,手冢治虫、杉浦日向子也出版了同名漫画。值得一提的是,吉本芭娜娜自小就读藤子不二雄的《怪物小弟》和《怪物Q太郎》漫画长大,她曾戏说自己的初恋就是Q太郎。日本新生代的小说家、漫画家由传统色彩的传奇故事而引发了新的创作灵感。
三、与作者所著其他小说之间的互文
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从其处女作《厨房》开始,几乎都具有如下特点:(1)以年轻女性为主角,女主角都会遭遇童年的不幸。《厨房》和《满月》的女主角美影“父母双双早逝,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上中学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几天前,奶奶竟也离我而去”。《甘露》的女主角“在母亲生下我和妹妹真由以后,父亲因脑溢血遽然死去。六年前母亲第二次结婚,生下弟弟,一年前离了婚”。《雏菊人生》里的雏菊的母亲是个未婚妈妈,“那个身为我父亲的人好象并不知道我存在”,但在雏菊小学的时候,妈妈却因车祸去世了,从小由姨妈和姨夫抚养。《N·P》也不例外,风美九岁时父母因父亲喜欢上别的女人而离婚,在十九岁之前一家三口:母亲、姐姐和我住在一起的单亲家庭。(2)因某种因缘与无血缘的人相遇,重组新型家庭。《厨房》的美影在自己最后的亲人奶奶也去世之后,在葬礼上遇到了以前在奶奶的花店打工的可爱男孩田边雄一,雄一把美影接到自己家寄宿,由此和雄一变性的爸爸(由此成为了妈妈)一起生活,组成无血缘关系的新家庭。《N·P》中风美偶遇自杀了的恋人庄司翻译的小说作者高濑的一对儿女以及私生女“萃”,得知作者高濑及这些儿女间破碎了的家庭和父女、兄妹近亲关系发展经过,以及最后在“萃”选择牺牲自己而退出后,风美和乙彦能重新走人生活的正常轨道。“归根结底,无一不是继续深化着在处女作《厨房》中所探讨的关于家庭的破碎和家庭的再生,以及现代人寻找自我居所的主题。”(3)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在不健全的环境下成长、患上了某些心理障碍的角色。《哀伤的预感》中的弥生由于亲眼目睹了父母亲车祸去世现场而丧失了童年的记忆;《白河夜船》中寺子经常穿梭在梦境和现实当中;《月影》中女主角的亲密爱人阿等和他的弟弟阿同的恋人由美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阿栋太思念由美子而穿着她的女式校服出入在校园和街上;《N·P》的风美小时候由于父母离异而患上了失语症。(4)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磨难后,在与他人的共处中逐渐找到新的生活重心,实现自我治愈、自我成长的某些经历,因而芭娜娜的小说被称为“治愈系”小说。
四、结语
小说的互文性是作者基于自己对历史、风俗、见闻以及自己对知识的吸收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创作从而产生的特性。吉本芭娜娜的作品《N·P》中的互文性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者采用了互文性的叙事写作手法,使得作品语篇内产生互文,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立体感和鉴赏性;另一方面,小说中体现的与民俗故事、漫画的互文,以及与芭娜娜所著其他小说之间的互文,则是文学评论中后现代主义互文性评价依据的体现。而同一作家的作品间存在太多的互文特性,也被指创作缺乏新意、套路单一。这就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有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对知识的吸收、学习和升华,才能产生新的互文甚至超文,创作出更多内容丰富题材风格新颖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吉本ぱをを,N·P[M],角川文库,1992,(11)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7
关键词: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释
中图分类号:G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89-02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下简称刘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及李善《〈文选〉注》并称“四大古注”,声誉颇隆,是注家的楷模。刘注为世人所重,原因有二:一为引文丰富,内容浩博;二为体例严谨。前者早有学者论及,并且成果颇丰。本文着重探讨后者。汪耀楠先生在他的《注释学纲要》中将刘注的体例分为补阙、纠缪、备异、论辩、存疑、释典、梳理、别见八端,现就此八种体例对《德行》第四则、第三十则,《政事》第十六则,《文学》第一则、第九十七则,《赏誉》第九十五则,《品藻》第五十一则,《纰漏》第三则进行分析。
一、补阙
即凡《世说新语》所不载的或语焉不详的事与人等,刘注都援引他书予以补充,以增见闻。如《德行》第三十则:“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刘注介绍竺道潜其人曰:“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誉播山东。为中州刘公弟子。值永嘉乱,投迹扬土,居止京邑。内持法纲,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师也。以业慈清净,而不耐风尘,考室剡县东二百里峁山中,同游十余人,高栖浩然。支道林宗其风范,与高丽道人书,称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终于山中也。”叙其生平甚详,所谓“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者也。又如《政事》第十六则首句:“陶公性检厉,勤于事。”刘注于其下引《晋阳秋》所记一事注曰:“侃练核庶事,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嫁,家给人足。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营种柳,都尉夏施盗拔武昌郡西门所种。侃后自出,驻车施门,问:“此是武昌西门柳,何以盗之?”施惶怖首状,三军称其明察。又援引《中兴书》上所载一事注云:“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谈者无以易也。”此二事注陶侃“性检厉,勤于事”的特征,生动具体。此所谓“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者也。
二、纠谬
凡《世说新语》所载,刘注认为明显有悖于事理,有乖于事实者,皆予以指出、纠正,这是最能体现刘孝标的学学识和治学态度之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于史法绳甚严,对《世说新语》也颇有微词,但对刘注的纠谬却给予肯定,誉之为“正说”。《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刘注“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刘注纠谬之处,俯拾即是。如《文学》第一则“郑玄在马融门下”条载马融因嫉妒郑玄而欲害之得事情。刘注驳之曰:“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3年不得见老师,马融只让高足弟子教他,郑玄学成归家时,马融慨叹礼乐东去,此《后汉书》本传亦载:“然马融怕郑玄盛名超过自己,心生妒忌,进而加以追杀之事。”《后汉书》未见记载。刘注谓马融身为大儒,服膺仁义,不可能因猜忌而下毒手,并指出这仅是里巷之传言而已,此说极为合理。从郑玄辞别归家,马融慨叹“礼乐皆东”之语,可知马融对郑玄,只有赞许之意,而无猜忌之心。这就是刘注以情理揆之,驳有悖于事理人情者。
三、备异
凡其他材料有与《世说新语》所载不合者,刘注即将其附于文下,以广异闻,供后人判断取舍。如《文学》第九十七则“袁宏始作《东征赋》”条下,刘注云:《续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问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二说不同,故详载焉。此文写陶范责问袁宏为何在《东征赋》中没有提及自己的父亲。刘注引《续晋阳秋》则谓桓温责问袁宏为何不提其父桓彝之功,并谓“二说不同,故详载焉”。《晋书》本传则将此二事同时载入传中,先叙桓彝事,后写陶侃事,二说并存。其实二事并不矛盾,可能确有其事,二文中人物不同,文辞各异,即同事异人。
四、论辩
凡《世说新语》所载,刘孝标认为不尽妥当或意犹未尽者,皆申以己说,有所论辩。如《品藻》第五十一则曰,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比羊叔子。”刘注曰:“羊祜德高一世,才经夷险。渊源蒸烛之曜,岂喻日月之明也。”刘注发挥己意,指出殷浩之于羊祜犹如蜡烛之于日月,无法类比,世人之喻,颇为不当。
五、存疑
凡《世说新语》所载,刘孝标对有所怀疑但不能确定,或欲注其事却不知所以者,以“疑”或“未详”存之,以俟后人考证,这充分体现了刘孝标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如《赏誉》第九十五则“许玄度送母”条,刘孝标注云:“《许氏谱》曰:‘玄度母,华轶女也。’按《询集》‘询出都迎姊,于路赋诗’。《续晋阳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缪矣。
六、释典
凡《世说新语》所引故事典实,刘注皆尽可能地原其本事,释其来源,以使后人知其始末,增加了解。如《德行》第四则“李元礼风格秀整”条曰:“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刘注曰:“(1)薛莹《后汉书》曰:‘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俊才。迁司隶校尉,为党事自杀。’(2)《三秦记》曰:‘龙门一名河津,去长安九百里,水悬绝,龟鱼之属莫能上,上则化为龙矣。’”
刘注引薛莹《后汉书》谓李膺“抗志清妙,有文武俊才”。他任青州刺史时,守令惧其威名,“多望风弃官”(《后汉书・李膺传》)。为司隶校尉时,宦官无不畏惧,“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出宫”(同上)。为乌桓校尉时,他亲冒矢石,“虏甚惮慑”。为度辽将军时,羌人攻掠边境,“自膺到边,皆望风惧服……声震远域”。他曾教授生徒千人,但当樊陵求为门徒时,却坚决不受,后陵果然以阿附宦官而位至太尉。荀爽十二岁即通《春秋》、《论语》,被杜乔誉为“可为人师”(《后汉书・荀爽传》),却为能替李膺驾车而感到荣幸。《后汉书・李膺传》:“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袁山松《后汉书》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违也。有难李君之言者,则乡党非之。李君与人同舆载,则名闻天下。”(《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五)因党锢之祸朝廷要收捕党人时,乡人劝其逃匿,而膺以节义为重,“诣诏狱”,毅然赴死。故薛莹《后汉书》谓其:“为党事自杀。”当时有门徒景顾尚未录入名册,故未受牵连,其父侍御史景毅慨然承认其子与膺为师生,“自表免归,时人义之”(《后汉书・李膺传》)。如此等等,都可见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并非虚语,无怪后进之士都以登其堂为身登龙门,声望倍增,荣幸无比。
七、梳理
凡《世说新语》所载之文,难以理解者,刘注辄予以疏通条理,使行文及文义得以畅通无碍。如《纰漏》第三则曰:“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两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这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但是,谢仁祖的话却不易理解。刘孝标于其下注之曰:“《大戴礼记・劝学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鳝之穴,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故蔡邕为《劝学章》,取义焉。《尔雅》曰:‘小者o’,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于蟹,而大于彭,即《尔雅》所谓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状甚相类。蔡谟不精其大小,食而致弊,故谓读《尔雅》不熟也。”
八、别见
凡《世说新语》某则所提之人或事,在其他地方(包括《世说新语》正文和刘注)有较详细的介绍,即注以“别见”或“已见”以省文,前者为在其后将出现的,后者为在其前已出现的。如《文学》第九十七则“袁宏始作《东征赋》”条,刘孝标注“胡奴”时曰:“胡奴,陶范,别见。”在《方正》第五十二则中,刘注曰:“胡奴,陶范小字也。《陶侃别传》曰:‘范字道则,侃第十子也,侃诸子中最知名。历尚书秘书监。’何法盛以为第九子。”此即刘注中所言“别见”之处。
刘注基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基础而又有所超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高似孙《纬略》有云:“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汪耀楠先生将其归结为补阙、纠谬、备异、论辩、存疑、释典、梳理、别见等八端,对后人的研究亦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中华书局,2006.
〔3〕朱碧莲.世说新语详解[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8
我们现在面对的小说或文学的危机,不是技艺问题,而是存亡问题,如今所谓的雅或俗的文学势不两立,我仔细想小说并没有雅俗之分,畅销的不见得就不经典,经典的大多也都是畅销的。面对网络这种新载体,影视这种新形式,娱乐那么多新花样,这些问题更加纷繁复杂。这时我们就要追寻小说的本意,小说在汉代本指“街谈巷语”,后来发展出“传奇”,英文的Novel追溯到拉丁语也是“新鲜故事”,短篇小说直译就是“短的故事”。那么今天文学为什么面临危机?就是因为我们忘记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追求小说的意义也好,小说的文本也好,不过小说的根本在故事,这一切都要在自足的故事中体现。
小说这种文体何以划分?文学因为有韵律与否划出诗歌,因为有行动与否划出戏剧,因为有虚构与否划出小说,小说在英文中总的名称就是Fiction,就是虚构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对纪实的材料完美虚构。虽然有诗化小说,戏剧化情节,我们要切记在小说中滥用抒情和满篇巧合,小说家应该保持冷静叙述,什么元素都要恰到好处,就像在娓娓动听地讲故事,既不能冷场尴尬,也要调足胃口,既要惊心动魄,又要含义隽永。
优秀的小说家就是擅长讲故事的人,莫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就是《讲故事的人》,当时许多人一片哗然,他们原本要听多么高深的理论,结果大失所望,进而有人弱弱地提出:难道小说只是讲故事?事实上小说就是故事。其实许多人没有领悟到这篇演讲的精妙,整个演讲也都是由故事组成,在这些故事中他面对各国的读者就讲完他可以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全部幽微观点。比如他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八个人在破庙中避雨,有人说他们中有人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才会下暴雨,就提议八个人扔草帽,草帽被吹走的人就是做过坏事的人,其中一个人因此被赶出庙外,结果那个人一出去庙就坍塌,这个人成为唯一得救的人。这个故事有多层次的象征,最基本的可以说莫言就是那个从众人中走出的人,当然还有更深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批判精神,譬如我们对于体制的思考。所以小说可以去追求意义,可以去追求文本,不过这些都要在故事中。
在世界化的今天,文学负有文化的责任,我一直在主张大诗主义:合一天人、合璧东西、融合古今,在小说中同样是大小说主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让神秘的和通俗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今天的故事艺术在深层次上融汇为一体。文学早已分化为多种体裁和形式,不能是过去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是从来都是文化的核心,从世界大势来看,当前不过是中国“战国时代”或者希腊“城邦时代”的重现,大一统的世界就要到来,只有融合了这些文化,才能说是世界的文学,融合了世界的故事,才能说是世界的小说。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9
范克(Funk)在《词源》一书中说:“词汇常常隐藏着传奇故事,它往往把我们引入神话和历史,使我们了解伟大的人物和重要事件”。的确如此,《圣经》中许许多多的习语背后就隐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在英语学习中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些源自《圣经》的习语,尤其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本文从《圣经》对英语文学、英语语言及修辞的影响等几方面加以阐述。
二、《圣经》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整个西方文化有着深远影响。法国作家雨果说过:“英格兰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莎士比亚,是英格兰造就了莎士比亚,但造就英格兰的却是《圣经》。”可以说《圣经》孕育了西方文化,抽去了《圣经》,西方世界就要倾斜,以至今天,人们还用基督教文明一词来指西方文明。《圣经》是英美文学家创作的重要源泉,许多著名的英美文学作品都直接取材于《圣经》。从古英语时期开始,由于教会对文化的垄断,文学作品就与《圣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以诗歌为代表,作品的情节也大多取自《圣经》或有关《圣经》的故事。早在公元七世纪末拉丁文《圣经》传入英国不久,就陆续出现了西德蒙谱写的诗歌《创世记》、辛纽武甫创作的《基督》、《使徒的命运》、约翰・ 曼德尔爵士创作的《曼德维尔爵士》等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这以后的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均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圣经》地影响,其中不乏大家比较熟悉地文学作品,如: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就常引用《圣经》中的典故。有人做过统计,莎翁在每一出戏剧中引用《圣经》的平均次数多达142次。比如大家熟悉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最后一场,罗兰佐感谢鲍西亚尼莉莎:“你们像是散播吗哪的天使,救济着饥饿的人们”。“吗哪”(Manna)的典故就出自《旧约・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The people called the bread manna. It was white like coriander seed and tasted like wafers made with honey(七天七夜被困在沙漠中的饥饿的以色列人,不知道周围地面上出现的白色圆物状的东西为何物,摩西就告诉他们说:“这是主给你们吃的食物,叫“吗哪”,“吗哪”指“天降的美食”)。《圣经》中的《创世记》,上帝开天辟地,但这个故事就被众多作家所引用,如拜伦的神秘剧《该隐》、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等。其中最经典的还要数十七世纪英国清教革命时期的另一著名作家约翰・弥尔顿的传世佳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作者在这些作品中,以长诗的形式阐释了人类不幸的根源是因为意志薄弱,经不起引诱而丧失了乐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二十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的名著《太阳照常升起》,整个作品的基调都是受《圣经》的启发而来,尤其是作品的题目更能体现《圣经》的影响:“Generations come and generations go, but the earth remains forever. The sun rises and the sun sets, and hurries back to where it rises. The wind blows to the south and turns to the north; round and round it goes, ever returning on its course. All streams flow into the sea, yet the sea is never full. To the place the streams come from, there they return again. All things are wearisome, more than one can say”(《旧约・传道书》,第一章)。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特・ 勃朗蒂的《简・爱》,主要故事情节的构思也都包含了《圣经》故事的隐喻,尤其是小说结尾部分的大火颇有《圣经》中施洗约翰所预言的,耶稣将用圣灵与“火”给世人施洗的意味。这些例子都有力地证明了《圣经》对西方文化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
三、《圣经》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除了在文学方面的显著影响外,《圣经》中的习语还融进了英美的日常用语,极大地丰富了英语语言,如:“At the eleventh hour”(尚来得及的最后时刻)、“The day of judgment”(末日审判)、“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 、“Noah's ark”(诺亚方舟)、“Scapegoat”(替罪羊)等等。《圣经》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也被直接用来代表某一特定类型的人或事,如:“Wise as Solomon” (像所罗门一样的智慧过人);“Greedy as Ahab”(像亚哈一样的贪婪);“Devout as Abraham”(像亚伯拉罕一样地虔诚);“Eloquent as Aaron”(像亚伦一样地能言善辩)等等。有些习语甚至成为人们处世的准则,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地信念和言行,如《圣经》告诫人们:“Therefore do not worry about tomorrow, for tomorrow will worry about itself. Each day has enough trouble of its own”( 一天的难处一天忍受就够了,不要无端担忧明天,《新约・ 马太福音》,第六章);“Listen to advice and accept instruction, and in the end you will be wise”(听劝教,受训悔,使你终究有智慧,《旧约・ 箴言》,第十九章);“Make a tree good and its fruit will be good, or make a tree bad and its fruit will be bad, for a tree is recognized by its fruit”(判断一个人,看其所作所为就知道,《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等等。
四、《圣经》中的修辞
《圣经》中用得更多的是一些比喻和象征,如:“To put new wine into old wineskins”(《新约・马太福音》, 第九章, 把新酒放在旧皮囊里,指两种事物格格不入);“Ask for bread and be given a stone ”(《新约・ 马太福音》,第九章,想要面包,反而给石头,比喻得非所求);“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新约・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心有余而力不足);“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旧约・ 出埃及计》, 做无草之砖, 指根本做不到的事);“I am nothing but skin and bones; I have escaped with only the skin of my teeth"(《旧约・约伯记》, 第十九章,上帝使约伯倾家荡产, 疾病缠身, 以考验他是否坚信上帝。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抛弃了他,但他忍受着, 他对朋友说:“我的皮肉紧贴骨头, 我只剩牙皮逃脱了”,这里指除生命外全部丧失)等等。林肯也曾借用《圣经》,在他仅有272个字以简短而著称的Gettysburg Address中将全人类视为上帝所造,且不分贫富贵贱:“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在论及《圣经》这部文化典籍时,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说:“《圣经》是知识与德行的无价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圣经》的语言简练、朴实,自然、优美;其文学修辞手法除了比喻、象征,还有夸张、双关、委婉、矛盾等;其文体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圣经》以当时流行的隐喻和象征述说人生和历史的哲理,后世读者能被它所吸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五、结束语
于冠西说:“人类文化从整体上说, 是各国、各民族文化汇聚、交流的产物”(1985)。“任何国家的文明, 来自外来影响的产物总是多于本国的发明创造。如果有人要把英国文化中任何受外国影响或源于外国的东西剔除掉,那么,英国的文化就所剩无几了”(赖肖尔, 1981)。英语民族文化是多民族长期磨合、交融的结果,《圣经》的影响尤其深远。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和欣赏英语《圣经》必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英语, 增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世说新语的故事篇10
[关键词]电影《铁皮鼓》;叙事;改编
一、《铁皮鼓》及同名电影的概述
君特・格拉斯所著的多部小说之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这部小说――《铁皮鼓》,作者本人也表示过对这部小说有特殊的情感。《铁皮鼓》出版于1959年,格拉斯用其生动的文字语言描绘了一个侏儒奥斯卡,奥斯卡出生就具备了成人的智商,因其目睹了妈妈与表舅的而拒绝生长,从他眼中看到的人和世界变成一个荒诞的状况,他不断用鼓声和尖叫来表现出其对现实世界的反抗。奥斯卡的鼓声和尖叫声记录下了他的成长经历,记录在那个动荡年代的真实面目,用极其现实的笔墨和黑色幽默的言语向读者描绘出德国的真实历史。《铁皮鼓》在出版之后,许多导演一直想将其拍成电影,直到1978年施隆多夫将其搬上银幕,并获得了多项大奖,如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电影奖,电影能够如此成功不仅是由于小说原著的精彩内容,还包括导演等人以小说为基础对其创造和改编。20世纪开始电影快速发展,电影从黑白转变为彩色,从无声转变为有声,其也有了自身独特的叙事手法。而电影一直都以改编小说原著为其重要的叙事手法,将小说改编为电影,不是简单将一个故事变为不同的版本,而是成为两部参差交错却又珠联璧合的佳作,《铁皮鼓》就是这样一个相对成功的改编电影
二、电影《铁皮鼓》叙事内容的删改
电影的叙事主要以人物、故事情节和故事背景环境为主要线索,因此本文将从叙事的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小说与电影的不同,进而阐述出电影《铁皮鼓》叙事文本内容对小说做了何种删改。
(一)电影《铁皮鼓》故事情节的删改
电影故事情节是指对叙事作品的素材进行艺术加工,电影创造者按照因果关系对情节重新安排。小说《铁皮鼓》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一部时间跨度相当大的、文本篇幅较长、故事性较强的小说。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由于其篇幅的局限性,导演不能完全将小说原封不动搬上银幕,而是以小说框架为基础重新塑造了其内容,这个创作过程中既会有对原著的保留,又会具有其创造性的部分。小说《铁皮鼓》主要叙述了1899年~1954年所发生的故事,通过一个在精神病院疗养的侏儒奥斯卡用第一人称讲述了故事,小说中奥斯卡时常会在其中穿插一下疗养院的情况,但电影仅是截取了其长高之前的主要内容,没有对战后经历进行描述,比如他当过石匠学徒和人体模特等种种经历,电影之中都没有展现出来。电影主要叙述了奥斯卡的成长经历,主人公出现之前,电影利用画外音让观者了解了其家庭成员,之后延伸到他本人,镜头之中也自然地出现了他。电影中的奥斯卡与小说中所出现的那个30岁的中年男子不同,其给观者的印象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种电影与小说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电影具有一次性的特征,使得电影对小说有所改变,更趋于简单化,让观者能够在这90分钟内明白故事情节内容。导演最终只是选取了小说原著中的前两个篇章来作为电影的主线,并在这两篇中导演删除了大量情节,奥斯卡引诱别人犯罪,奥斯卡上学等情节。另外,电影还删除了一些相关的故事人物。比如,电影将小说中玛利亚的母亲特鲁钦斯基大娘一家从故事情节中剔除出去了。这是由于电影的叙述空间相对有限,无法将每一个人物及其特性都展现出来,那样也会显得电影结构拥挤。
(二)电影《铁皮鼓》人物形象的删改
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是通过细腻笔墨来渲染人物内心世界的,使得读者的想象力丰富起来,但电影则是用不同的镜头来展现出人物的形象,将人物形象直观地展现于观者面前,比小说更具有表现力。但其人物的个性和思想等方面还是与小说大体上是一致的。
电影与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奥斯卡是作为整个故事的叙述核心,其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还是一个故事的参与者,奥斯卡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以往的观念,人类文学史上之前出现的侏儒形象都是源自于民间故事,其是作为辅的角色出现,而奥斯卡是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个外表丑陋而内心也极其丑陋的畸形人。小说中首先塑造了一个丑陋的外形给奥斯卡,其本身的形象就已经带给人们一种冲击,而且还是一个有鸡胸、驼背和大脑袋的人,小说使得其畸形到底。同时,奥斯卡内心世界也是丑陋的,奥斯卡丑陋的内心是对现实世界的一切背叛,奥斯卡拥有成人的智商,他能够洞悉整个世界,心中却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超级利己主义者。电影中将奥斯卡形象塑造成为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但仍然保留其内心丑陋的一面,并将这种丑陋的姿态以一种无辜的状态呈现出来。奥斯卡3岁生日时候,他发现了母亲与舅舅的,觉得周围许多事情不能够接受,因此让自己停止生长。导演在电影中运用了几个特写镜头对准奥斯卡的面部表情,来展现出内心的丑陋。比如,从地窖楼梯摔下去之前,电影中镜头对向了奥斯卡脸部特写,其眼神中带有报复、痛恨之情。又如,学校里的女教师命令奥斯卡不要敲鼓,而他却发出尖叫震碎了教师的眼镜,这时镜头转向了奥斯卡的眼睛,看起来是多么天真无邪的孩子,但这是表面的现象。
(三)电影《铁皮鼓》场景的删改
小说和电影在叙事上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对于时空的处理,叙事对象的动作肯定是在特定时空中发生。从本质上来看,小说是时间的艺术,电影是空间的艺术,电影是运用空间来构建时间的链条,其能够将叙事内容展现得更加丰富生动、直观。《铁皮鼓》中涉及许多场景,本文将从两个场景进行有效的分析。首先是小说和电影中所涉及的葬礼场景,奥斯卡面对死亡的时候,小说和电影之中其表现也是有所不同的。小说中的奥斯卡是一个冷漠的“局外人”,而在银幕上奥斯卡则是一个带有感情的人。比如在奥斯卡母亲的葬礼上,小说文本用大量笔墨来描述了奥斯卡母亲的灵柩,他对母亲灵柩的观察行为完全掩盖了他的悲伤之情,他的冷漠无情跃然于纸上。电影中在奥斯卡母亲葬礼场景上,奥斯卡没有去观察母亲的灵柩,而是站在墓穴旁,放慢速度去敲打他的铁皮鼓。导演运用了多个特写镜头来展现出奥斯卡因失去母亲而伤心。同时,小说与电影中战争场面较少,小说中的战斗场面是指波兰邮局保卫战,奥斯卡积极参与了这场战争,从他的眼中看到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与扬・布朗斯基的胆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由于这些人都懦弱,而使得纳粹德国闪电般地攻克波兰。电影中,纳粹刚刚开始之时,但泽的市民遇到游行队伍会向他们扔东西,这一镜头,能够看出来人们对纳粹的反感。后来,但泽沦陷为德军的地盘,人们却表现出了对纳粹领袖的热烈欢迎,甚至连奥斯卡都敲起铁皮鼓来表示欢迎。这一阶段的人们已经处于一种盲从的状态中,完全失去了理智。
三、电影《铁皮鼓》叙事策略的借鉴与超越
电影文本和小说文本的符合系统和话语样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小说作为语言艺术,大量使用了语言符号,而电影作为影像艺术,则使用较多的符号,包括画面还有声音等要素。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其叙事策略都包括叙述时间、叙述者等要素。本文也是从这两方面来分析电影叙事策略对原著小说的借鉴和超越之处。
(一)电影《铁皮鼓》叙述时间的改编
电影《铁皮鼓》是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来对故事进行描述的,其逻辑顺序与时间顺序是相互一致的。电影是以奥斯卡的成长经历作为叙事线索,而没有战后及精神疗养院中所发生的故事情节。这部电影的叙述时间十分清晰,从19世纪末开始到一战,而后又到二战,逐步地将奥斯卡的人生历程全部展现出来。电影的基本事件发生也有一定的逻辑性,开始部分是奥斯卡出生之前,他的外祖父母及他父亲、母亲和表舅的故事,而后是奥斯卡母亲去世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第三部分则是母亲去世后到波兰邮局保卫战,剩下的内容为最后一部分。电影的叙述时间顺序是呈一条直线的发展趋势,没有任何镜头上的回闪,故事自然而然地逐渐呈现于观者面前。但小说《铁皮鼓》的叙述时间并不是如此清晰,其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不是完全一致的。小说故事开头是30岁的奥斯卡在精神疗养院的自述,以宣判奥斯卡无罪,自己却对未来生活感到渺茫而告终。小说文本的叙事时间整体上还是以顺序时间为基础,但其中穿插了大量的倒叙内容,顺时间和逆时间的交替使用,使得读者通过奥斯卡的自述来想象其成长的过程,又使得读者不忘其已经是一个成年人。
(二)电影《铁皮鼓》叙述者的改编
小说《铁皮鼓》中叙述者就是主人公奥斯卡本人,其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故事的外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内叙述者。小说中故事外叙事者是指在精神疗养院中回忆往事的奥斯卡,小说文本采用了许多文学创作叙事方式,比如白漆床和洁白的纸等具有象征性的手法,逐渐谈到他自己,娓娓道来他的身世,其成为后续故事的主人公。这一阶段,他自然转换成了故事的内叙述者。小说文本中,奥斯卡的叙述者身份不断地在内叙述者和外叙述者之间相互转换。比如,奥斯卡描述了其外祖父的故事之后,他又转换为叙述者,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之后他的朋友来看望他,自然地与照相衔接到一起,从照相又联系到照相簿,现实世界又转换到往事之中,奥斯卡的身份再次变为了内叙述者。小说文本中包含大量的如此转换,每一个新故事的开始,奥斯卡都讲述在疗养院的当前处境,而接着又进入了故事叙述之中。电影由于时间局限性,仅仅截取了小说部分内容,没有其在疗养院的故事,因此奥斯卡没有双重叙述者的身份。电影是以奥斯卡成长经历为主线的叙述结构,奥斯卡在影片中是惟一的叙述者,导演将其设定为第二叙述者,整部影片是以奥斯卡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向观众展现出他的人生经历。导演将奥斯卡设定为第二叙述者,主要是通过他的声音、镜头的变换及场面的调度来完成。导演巧妙地运用了画外音和画面叙述来完成了奥斯卡出生之前的故事。导演考虑到奥斯卡是一个侏儒,为了使得电影画面更加逼真,运用了许多仰拍镜头来代表奥斯卡的主观视角。
[参考文献]
[1] 李昌坷.提示历史,警示现实――评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J].国外文学,2001(04).
[2] 冯亚琳.批判、继承与能指游戏――论君特・格拉斯作品中基督教题材的表现手法及意义[J].外国文学评论,2003(02).
[3] 李万钧.格拉斯的《铁皮鼓》与20世纪小说叙事学[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02).
相关文章
世说新语叙事构造及艺术手法 2022-07-04 08:27:42
读世说新语体会感言 2022-04-13 10:37:00
读世说新语后有感 2022-05-04 04:17:00
语文世说新语管理论文 2022-08-15 04:19:00
初中语文教案:《世说新语》(新课标) 2022-09-27 03:10:00
初中语文教案:《世说新语》 2022-09-27 11:5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