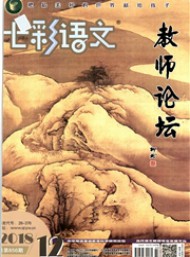逻辑真理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17:29:42

逻辑真理范文篇1
(一)前提或者命题真。这种真是指命题的思想内容是真的。任何一个命题的内容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在这里真或假不是用以描述事物状态的,而是评价命题或陈述的内容的。它的核心是针对其所表达的知识或信念的,例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命题的内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是个真命题。
(二)推理真。这是指推理中前提真和结论真之间的关系。演绎推理前提真结论必然真,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前提真而结论是或然性真。因此推理真就是推理中的结论相对于前提是必然的真或者是或然的真。这里“真”指的是否再现逻辑推断关系而不是对命题内容的评价。
(三)指派真和赋值真。在逻辑学中(特别是在现代逻辑中)把命题形式当作真值形式,而且只从真假的角度研究每一种命题形式的逻辑特征,真和假是命题的唯一属性。逻辑真在这里指这些真值形式和其中的变项与公式的真假,这时的真假和具体命题内容的真假无关,而只是一种假定的真假和根据这种假定而推论出的真假。
(四)形式真。这是指永真式(重言式)或普遍有效式的真。逻辑学中有一类公式,对其中的变项可以代以任何命题、谓词、个体词总能得到真命题。这类公式的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的真,例如:P或者非P中不管变项P赋真值或是假值,这个公式都是真的。
(五)系统真。现代逻辑建立了形式系统,如果它的定理都是形式真,即都是永真公式或是普遍有效式,那么整个系统便是可靠的和一致的,这种可靠性和一致性就是一种系统的真。
在以上这五种“真”的情况下,逻辑学不考虑第一种意义的“真”,而只关注后四种“真”。后四种“真”在逻辑学中有各种表现,在其他科学中也有这些意义上的真的表现,就被称为逻辑真理。
所谓逻辑真理是一种特殊的真理,是一种因逻辑关系或逻辑原因而成为真的一种真理。逻辑真理不能凭经验而得知其为真,它需要我们借助逻辑分析、语义分析、关系分析确定它们是真的。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真理是有区别的。
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或者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问题。从逻辑哲学的角度来看,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任何逻辑学家都要回答:逻辑真理是否与客观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理论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形而上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述了逻辑基本规律(矛盾律与排中律)。在谈到矛盾律时认为,事物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矛盾律首先是存在的规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因为它符合“事理”。亚里士多德肯定了逻辑规律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其根据就是真理符合现实的理论,即所谓真理符合论。它在解释真与假这对概念时说,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按照真理符合论,一切真理必需与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也不能例外。可见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这个真理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只强调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却忽视了逻辑真理的特殊性。莱布尼兹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了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学中的推理问题,对亚里士多德的真理一元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两种真理:即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推理的真理不像事实真理那样依赖于经验,它们的证明只能来自所谓的天赋的内在原则。因此莱布尼兹的这种观点,就成为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先验论的一个起源。
基于莱布尼兹的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对立,在康德的哲学中就演变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分歧。康德认为一切来源于经验的判断都是综合判断;分析判断是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即先天知识。例如:“白人是人”就是分析判断,在康德看来表示逻辑规律的判断就属于分析判断。
数理逻辑问世之后,逻辑哲学领域中出现了维特根斯坦学派,即以维也纳小组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工作就是利用数理逻辑的成果,发展从莱布尼兹到康德的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的先验论,使之获得科学化的外观和现代化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真理称为重言式。他认为重言式的命题是无条件的真,由此他断言,重言式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同样的也不能为经验所否定,也就是说与现实没有任何描述关系。逻辑实证主义者进一步把康德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推向极端。在他们看来,凡是先天的都是分析的;反之,凡分析的都是先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信条: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某些陈述的真理是逻辑的、必然的、根据意义而定的,另一些陈述的真理是经验的、偶然的、取决于世界上的事实的。前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分析推理,后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综合推理。逻辑真理被看作是分析真理的一个特殊的真子集。
1933年塔尔斯基以形式化的方法给出了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他用非形式化方法对其语义学的成果作出概述。他认为逻辑真理同其他真理一样,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或者相一致,在形式语言中,一个语句是不是逻辑真理,取决于它是不是在每一种解释下都成为真语句;同时一个语句在某一解释下是否为真,取决于它在这一解释下,是否与它所“谈论的对象”相一致。可见逻辑真理的概念直接依赖于形式语言中的语句,与它们所描述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符合关系,这说明它的逻辑真理或者分析真理并非先验的真或者先天的真,它们为真同样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相符合。塔尔斯基重新建立了真理符合论,表明一切真理包括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真理符合论,肯定了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但是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莱布尼兹、康德、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真理和现实绝对无关,与事实真理根本不同。塔尔斯基主张真理必需以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符合论为基础,而且只能以形式语言来构造,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思维中的正确反映。同样逻辑真理也是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反映。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而最普遍的逻辑格,就是事物被描述的很幼稚的……最普遍的关系。列宁认为逻辑的公理、正确的推理形式是事物最普遍的关系,是由人们实践中千百万次的重复而反映和巩固在意识中。列宁说的最普遍的逻辑格是指三段论推理的正确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逻辑真和事实真是相容的,事实真是基础,逻辑真是建立在事实真基础之上的,二者是一致的,但是逻辑真理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第一,逻辑系统的公理和定理的真是逻辑系统设定,其为真的根据是某种初始的逻辑关系。第二,逻辑公理和定理经过解释的真命题,其为真不取决于解释中的内容,而取决于这些公理、定理所显示的逻辑关系。第三,逻辑推断关系这种推论的结论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真。第四,根据逻辑联系词的性质,由逻辑真得到逻辑真。如:A、B是逻辑真命题,那么A并且B、如果A那么B都是逻辑真命题。第五,数学中的逻辑真命题,是建立在公理演绎基础之上。以上这些逻辑真由于逻辑的原因或者逻辑关系而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在局部意义上,相对于特定的逻辑系统而言,逻辑真理可以说是分析的,是以逻辑意义为根据的,而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关系是:事物之间的关系显示一定的逻辑关系,也是逻辑真的基础。逻辑真理在某些方面与事实真理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逻辑真理又与事实真理不是一致的,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逻辑真理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有些逻辑关系是绝对的真,但是另一些逻辑真理是相对的真。逻辑真理之所以为逻辑真理,不是由于它们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事物或事物的普遍性,而只是涉及到逻辑自身,只根据逻辑自身而成立。逻辑真理的必然性需要在逻辑自身中去寻找,而不能在现实中寻找。
综上所述可见,逻辑真理来源于经验,但又不同于事实真理。由于逻辑思维的作用,它越远离事实,其真理性越强;当它与具体事实相符合时,即成为事实真理的必要条件。当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一致时,逻辑思维就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规律,因此逻辑真理在认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当我们认识世界时,会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作出许多推测和猜想,也会试图把这些思想与已经获得的关于被研究对象的材料联系起来。为了搞好各项工作,我们要正确的调整各种思想关系,从中抛弃不适当的思想,选取可以促进我们前进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在思维过程中严格遵守逻辑规律和规则。只有认识逻辑真理才能更好地认识事实真理,随着人类的经验积累,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交叉容量必然会不断增大,为了探求真理我们必须保证思维的逻辑性。
逻辑真理范文篇2
论文摘要:逻辑学是研究推理的一门学问,而推理是由概念、命题组成的,不懂得命题就不懂得推理。普通逻辑学在研究命题时,主要是从二值逻辑的角度研究命题逻辑形式的逻辑值与命题形式之间的真假关系。本文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逻辑真理的内涵,同时详细论述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为了探求真理必须保证思维的逻辑性。
逻辑学离不开“真”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人们是从下述意义上使用“真”这个概念的:
(一)前提或者命题真。这种真是指命题的思想内容是真的。任何一个命题的内容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在这里真或假不是用以描述事物状态的,而是评价命题或陈述的内容的。它的核心是针对其所表达的知识或信念的,例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命题的内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是个真命题。
(二)推理真。这是指推理中前提真和结论真之间的关系。演绎推理前提真结论必然真,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前提真而结论是或然性真。因此推理真就是推理中的结论相对于前提是必然的真或者是或然的真。这里“真”指的是否再现逻辑推断关系而不是对命题内容的评价。
(三)指派真和赋值真。在逻辑学中(特别是在现代逻辑中)把命题形式当作真值形式,而且只从真假的角度研究每一种命题形式的逻辑特征,真和假是命题的唯一属性。逻辑真在这里指这些真值形式和其中的变项与公式的真假,这时的真假和具体命题内容的真假无关,而只是一种假定的真假和根据这种假定而推论出的真假。
(四)形式真。这是指永真式(重言式)或普遍有效式的真。逻辑学中有一类公式,对其中的变项可以代以任何命题、谓词、个体词总能得到真命题。这类公式的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的真,例如:P或者非P中不管变项P赋真值或是假值,这个公式都是真的。
(五)系统真。现代逻辑建立了形式系统,如果它的定理都是形式真,即都是永真公式或是普遍有效式,那么整个系统便是可靠的和一致的,这种可靠性和一致性就是一种系统的真。
在以上这五种“真”的情况下,逻辑学不考虑第一种意义的“真”,而只关注后四种“真”。后四种“真”在逻辑学中有各种表现,在其他科学中也有这些意义上的真的表现,就被称为逻辑真理。
所谓逻辑真理是一种特殊的真理,是一种因逻辑关系或逻辑原因而成为真的一种真理。逻辑真理不能凭经验而得知其为真,它需要我们借助逻辑分析、语义分析、关系分析确定它们是真的。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真理是有区别的。
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或者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问题。从逻辑哲学的角度来看,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任何逻辑学家都要回答:逻辑真理是否与客观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理论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形而上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述了逻辑基本规律(矛盾律与排中律)。在谈到矛盾律时认为,事物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矛盾律首先是存在的规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因为它符合“事理”。亚里士多德肯定了逻辑规律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其根据就是真理符合现实的理论,即所谓真理符合论。它在解释真与假这对概念时说,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按照真理符合论,一切真理必需与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也不能例外。可见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这个真理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只强调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却忽视了逻辑真理的特殊性。
莱布尼兹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了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学中的推理问题,对亚里士多德的真理一元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两种真理:即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推理的真理不像事实真理那样依赖于经验,它们的证明只能来自所谓的天赋的内在原则。因此莱布尼兹的这种观点,就成为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先验论的一个起源。
基于莱布尼兹的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对立,在康德的哲学中就演变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分歧。康德认为一切来源于经验的判断都是综合判断;分析判断是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即先天知识。例如:“白人是人”就是分析判断,在康德看来表示逻辑规律的判断就属于分析判断。
数理逻辑问世之后,逻辑哲学领域中出现了维特根斯坦学派,即以维也纳小组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工作就是利用数理逻辑的成果,发展从莱布尼兹到康德的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的先验论,使之获得科学化的外观和现代化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真理称为重言式。他认为重言式的命题是无条件的真,由此他断言,重言式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同样的也不能为经验所否定,也就是说与现实没有任何描述关系。逻辑实证主义者进一步把康德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推向极端。在他们看来,凡是先天的都是分析的;反之,凡分析的都是先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信条: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某些陈述的真理是逻辑的、必然的、根据意义而定的,另一些陈述的真理是经验的、偶然的、取决于世界上的事实的。前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分析推理,后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综合推理。逻辑真理被看作是分析真理的一个特殊的真子集。
1933年塔尔斯基以形式化的方法给出了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他用非形式化方法对其语义学的成果作出概述。他认为逻辑真理同其他真理一样,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或者相一致,在形式语言中,一个语句是不是逻辑真理,取决于它是不是在每一种解释下都成为真语句;同时一个语句在某一解释下是否为真,取决于它在这一解释下,是否与它所“谈论的对象”相一致。可见逻辑真理的概念直接依赖于形式语言中的语句,与它们所描述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符合关系,这说明它的逻辑真理或者分析真理并非先验的真或者先天的真,它们为真同样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相符合。塔尔斯基重新建立了真理符合论,表明一切真理包括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真理符合论,肯定了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但是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莱布尼兹、康德、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真理和现实绝对无关,与事实真理根本不同。塔尔斯基主张真理必需以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符合论为基础,而且只能以形式语言来构造,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思维中的正确反映。同样逻辑真理也是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反映。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而最普遍的逻辑格,就是事物被描述的很幼稚的……最普遍的关系。列宁认为逻辑的公理、正确的推理形式是事物最普遍的关系,是由人们实践中千百万次的重复而反映和巩固在意识中。列宁说的最普遍的逻辑格是指三段论推理的正确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逻辑真和事实真是相容的,事实真是基础,逻辑真是建立在事实真基础之上的,二者是一致的,但是逻辑真理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第一,逻辑系统的公理和定理的真是逻辑系统设定,其为真的根据是某种初始的逻辑关系。第二,逻辑公理和定理经过解释的真命题,其为真不取决于解释中的内容,而取决于这些公理、定理所显示的逻辑关系。第三,逻辑推断关系这种推论的结论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真。第四,根据逻辑联系词的性质,由逻辑真得到逻辑真。如:A、B是逻辑真命题,那么A并且B、如果A那么B都是逻辑真命题。第五,数学中的逻辑真命题,是建立在公理演绎基础之上。以上这些逻辑真由于逻辑的原因或者逻辑关系而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在局部意义上,相对于特定的逻辑系统而言,逻辑真理可以说是分析的,是以逻辑意义为根据的,而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逻辑真理范文篇3
关键词:思维三律;强化的排中律和强化的矛盾律;“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不矛盾律
一、重新把握“思维三律”的基础地位
“思维三律”(ThreelawsofThought)即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的研究,是金岳霖长期关注的课题,在他思想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金岳霖是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三律”问题研究得最系统、最深入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1]。在金岳霖看来,从“穷尽可能”角度来理解“思维三律”能更好地体现“思维三律”的基本性,同时对“思维三律”的阐述又反过来促使我们对“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金岳霖先生对“思维三律”的阐述是对“穷尽可能”逻辑真理观的一种深化。然而许多现代逻辑学者认为“三律”只不过是现代逻辑演算系统中的重言式或普遍有效式,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例如,罗素不重视“三律”的研究论文。在罗素看来,命题演算中逻辑定理都具有重言式的形式结构,而“三律”“也是这一演算中的定理,也是有重言式的形式结构的,它们和别的定理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把这三条定理特别挑选出来作为基本的思维规律”[2]。艾耶尔认为“三律”是“任意选择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律’”[3]。
但是在元逻辑已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构造和研究逻辑演算系统,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内定理和元定理以及内定理和元规则区别开来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意义上,“思维三律”是用元语言表述的元公理或元规则,“它们是一个逻辑演算系统所赖以奠基和出发的基础,是构造或检验一个逻辑演算系统的根本指导原则”[4]。因此,否认“三律”有特殊地位是因为反对者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层次,“把一个逻辑演算系统所赖以奠基和出发的元规则等同于该系统所肯定和接受的一个内定理”[4]。金岳霖关于“三律”的见解,与他关于“逻辑系统的工具”和“逻辑系统的实质”的区分是相关联的。而这两者的区分与上述语言层次的区分也是关联的。金岳霖正是在现代逻辑这个大背景下来阐述“三律”的。
金岳霖指出,对于“三律”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逻辑系统的实质,一种是逻辑系统的工具。习于传统逻辑的人以‘思想律’为无上的‘根本’思想,而从事于符号逻辑的人又以为‘思想律’与其他思想两相比较孰为‘根本’的问题,完全为系统问题。这两说似乎都有道理。前一说法似乎是界说方面的说法,后一说法似乎是工具方面的说法”[5]。金岳霖所说“逻辑系统的工具”的立场,就是把“三律”视为某一特殊系统之内的构成要素,“是一系统所利用以为那一系统演进与推论的工具”[5]。因此,“三律”作为逻辑定理,在不同的逻辑系统中具有不同的地位,而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完全由该系统本身决定,而“逻辑系统的实质”的立场,则是从系统的逻辑本质,或者说从一系统之成为逻辑系统方面来考察“三律”。金岳霖认为,从这个立场考虑,“即使面对现代逻辑系统,‘三律’非但不失其‘基本性’,反而能更清楚地显示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只有从前者分析,才可考虑“三律”是否系统内的定理;而从后者分析,“三律”乃是最基本的逻辑法则。作为逻辑基本法则的“三律”,应该是构造任何逻辑系统的元理论法则。
由此,从逻辑系统的实质或者说从其界说方面着眼,“三律”是逻辑的基本法则,它们不仅是经典逻辑系统的基本法则,而且也是表示“必然”的任何其他逻辑系统的基本法则。金岳霖认为,对于不同的逻辑系统,“界说方面的‘同一’、‘排中’与‘矛盾’均为各系统之原则,不过表示的形式不同而已”[5]。因而,“三律”也最直接地体现出“逻辑的功用”:“它是思想的剪刀,一方面它排除与它的标准相反的思维,另一方面因为它供给能取与否的标准,它又是其他任何系统的工具。”[5]因此,“就规律说,它们的确是最基本的规律,它们是规律的规律”[6]。
金岳霖所说的同一、排中、矛盾是逻辑系统之所以为逻辑系统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原则,就是说,作为系统,它不能违背同一、排中和矛盾原则,一系统也只有遵循了这三个原则,它才可能成其为一个系统。因此只有从“逻辑”而不是从“逻辑系统”着眼,才可说清“三律”之异于其他逻辑命题的基本性,反过来又可以用“三律”最直接地说明“逻辑”的本性。金岳霖对“三律”的分析源于他的逻辑观。金岳霖认为逻辑学是研究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必然关系的,这里的必然是“穷尽可能的必然”,也即逻辑的必然。金岳霖认为在表达“必然”命题这一点上,“三律”与其他逻辑命题没有什么差别:“任何逻辑命题都是别的逻辑命题的必要条件无论我们否认三思想律也好,或三段论原则也好,结果一样,它总是取消思议。从这一点着想,任何逻辑命题都是思想律。”[6]但是,与其他逻辑命题相比,“三律”无疑是“最简单而又最显而易见的必然命题”[5],它们最直接地体现出“穷尽可能的必然”的本性。因此,对“思维三律”的阐述是对“穷尽可能”逻辑真理的一种深化。那么这种本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金岳霖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了说明。
首先,关于同一律,金岳霖认为同一律是“可能的可能,意义的条件”,是思议的最基本的条件。但这不是说承认同一律,话就有意义,而是说如果不承认同一律,话就没有或不会有意义。而意义又有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分别,“一句话可以没有系统外的意义,不能没有系统内的意义。无论系统外的意义也好,系统内的意义也好,只要我们所说的话有意义,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同一律”[7]。
从命题角度讲,如果说逻辑命题都表示“穷尽可能的必然”,那么“就有可能的可能问题。可能的可能或者有别的条件,但无论可能分为多少,每一个可能总要是那一个可能才行。如果一个可能可以不是那一个可能,至少说话无意义,而可能就不成其为可能。意义的条件不少,但至少有一条件为大家所承认的,此即普通所称为同一律中的‘同一’思想”[5]。其次,排中律是一最简单而又最显而易见的必然命题。金岳霖说:“逻辑系统所要保留的都是,或都要是必然命题,而必然命题都表示‘排中’原则。既然如此,每一必然命题的证明都间接的是‘排中’原则的证明。所以整个逻辑系统的演进可以视为‘排中’原则的证明。”[5]排中律的证明和“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是相互作用的,对排中律的证明是对“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的一种深化。
金岳霖所说的排中原则实质上是排外原则。他说:“排中原则的可能就是彼此穷尽的可能。如把可能分为两类,则此两可能以外没有第三可能;排中原则所排的是第三可能。如把可能分为三类,则三可能之外没有第四可能,排中原则所排的是第四可能。如把可能分为n类,则n类可能之外没有n+1可能,排中原则所排的是n+1可能。所以说‘排中’实即‘排外’。这个原则不过表示可能之拒绝遗漏而已。必然的命题从正面说是承认所有可能的命题,从反面说是拒绝遗漏的命题。”[5]
金岳霖并不把排中律等同于二值原则,在他看来,二值原则不过是对命题的值引用二分法的结果,即使对命题的值引用多分法,排中原则的“实质”依旧。排中律最直接体现逻辑所要“保留必然”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金岳霖所说的排中原则称作排n+1值律,排n+1值律是强化的排中律的一种在有穷领域的展开形式,排n+1值律与强化的排中律实质上是一致的。
我们把形如“本语句或是真的或是不真的”称为强化的排中律[8]。“强化的排中律对于任何合理的多值逻辑系统均是成立的。”多值逻辑的确立“否定的只是二值排中律即二值法则的普适性,而二值法则只是强化的排中律在二值逻辑世界内的一种表现形式”。“强化的排中律因其适用范围更广而比二值排中律为‘弱’。”“强化的排中律在排中律的所有表述中居于最深的层次,其他表述都是它在各种规定和限制条件下(相对于其适用范围)的表现形式。因而它是排中律最基本的或曰‘本真’的形式。”[8]强化的排中律居于比二值法则更为基本的层次,它容许将“假”与“不真”的其他种类区别开来,因而能够适用于多值化思维,面向多值逻辑时,仍可保持其普适性。因此,在有穷领域内,当排n+1值律运用于多值逻辑时,也可保持普适性。因此,作为逻辑思维基本法则的应该是排中律的强化形式而不是其二值形式。强化的排中律是属于元语言层次的逻辑系统的指导原则,它具有普适性这一点是肯定的。
因此金岳霖的“排中律”是“一种思议上的剪刀,它一剪两断,它是思议上最根本的推论”[6],它穷尽了一切可能,揭示了“逻辑的必然”。
从对排中原则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金岳霖的排中思想适用范围非常宽广。对于多值逻辑的欢迎和接纳,是金岳霖关于“三律”特别是排中律思想的当然推论[1]。针对“排中原则相对于多值逻辑失效”的说法,金岳霖指出,决不能把排中律与二值原则及其在二值逻辑系统中的表现形式混为一谈。二值原则相对于多值系统的失效理所当然,但金岳霖意义上的排中律决不会失效。只是在多值逻辑系统中要采取与二值逻辑系统不同的表现形式。
学界通常认为“直觉主义逻辑是拒斥排中律的”,奎因也认为,最广为人知的对排中律的反对还不是出于量子力学方面的考虑,而是数学家L.布劳威尔在直觉主义名称下所进行的[9]。而事实又是什么样的?直觉主义逻辑从构造性立场出发,认为“真”是“构造真”,“假”是“构造假”,因此在有穷领域内,“任一陈述是构造真的或是构造假的”显然是不成立的,经典二值排中律失效。但强化的排中律却不会失效。因为我们说“任一陈述或是构造真的或是非构造真的”时,我们穷尽了所有可能的情况。因此“强化的排中律”对直觉主义逻辑也具有普适性。
最后,关于矛盾律,金岳霖认为“严格地说它是两命题能否同时成立的问题”[7]。矛盾律最直接体现“逻辑之所舍”。“保留必然”的另一方面必定是要“淘汰矛盾”,因为“逻辑方面的可能不仅彼此穷尽,而且彼此不相容”。金岳霖对矛盾的认识同样也不限于真假二分。“如把可能分为两类,则此两可能不能同时承认之。如把可能分为三类,则此三可能不能同时承认之。矛盾原则可以说是表示可能之拒绝兼容。”[5]若承认可能之兼容而产生矛盾,则“思议根本不可能”,因而金岳霖又把矛盾律视为“最基本的排除原则”[5],是逻辑“取舍”的唯一的标准。
金岳霖认为“思议的限制,就是矛盾,是矛盾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是矛盾的意念,当然也是不能以之为接受方式的意念”[6]。因此,矛盾原则是“排除原则”,它排除思议中的矛盾。矛盾不排除,思议根本就不可能。虽然它并不能保证思议过程中不出现矛盾,但它排除、“淘汰”思议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从而使思维具有一致性。和排中原则一样,矛盾原则也有其强化形式。强化的矛盾律比经典的二值矛盾律更为根本。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矛盾律是“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有效的”,它是思维和存在的普遍原则。然而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出现了否定矛盾律的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又译“亚相容逻辑”、“弗协调逻辑”),次协调逻辑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认为“矛盾律不是普遍有效的”,这显然触及了经典逻辑的支柱。但如果从发展科学理论的角度考虑,将逻辑矛盾圈禁起来,不承认逻辑矛盾是真的,在这点上也不会与金岳霖的观点相左。因此,一个次协调理论系统是否违反金岳霖的逻辑真理观,实际上取决于其在元理论上是否承认强化的排中律和矛盾律,也就是是否承认有“真矛盾”存在。金岳霖的这个观点在理解非经典逻辑和经典逻辑的关系上,在理解各种非经典逻辑的“非经典性”上,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必然为逻辑之所取,矛盾为逻辑之所舍。逻辑系统之所取为逻辑上之所不能不取,逻辑系统之所舍为逻辑上之所不能不舍,而取舍标准不在逻辑范围之内,但有矛盾的命题无论在什么系统范围之内都是要被淘汰的命题。由此可知,金岳霖的逻辑只是预设了无矛盾,因此,我们说金岳霖的逻辑观是非常宽泛的。二、在逻辑真理研究中的比较优势金岳霖关于“穷尽可能”必然的阐述与他的逻辑观是分不开的。金岳霖认为逻辑与逻辑系统是不同的,逻辑系统可以有很多,但“逻辑”只有一个。不同的逻辑系统都部分地表达了“逻辑”,但不能完全达到逻辑。“逻辑”超越于任何逻辑系统,但不能脱离所有逻辑系统[10]。因此金岳霖所说的“逻辑”,就是“穷尽可能”,是唯一的“逻辑”实质,而不是各种逻辑系统。他认为逻辑系统是“没有特殊的原子,它的独有情形不在原子而在它的系统所要保留的‘东西’(此处用“东西”二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更便当的名词)”[5]。他指出了逻辑系统的特点:保留必然,淘汰矛盾。淘汰矛盾是从反面来保留必然,因此按照金岳霖对逻辑系统的解释,逻辑系统的特点就是表现必然。将逻辑与逻辑系统明确分开来能够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
金岳霖的这一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狭隘的一元论。学界关于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讨论,其实是关于逻辑系统之间的竞争性问题的讨论。一元论只承认有一个正确的逻辑系统,而多元论认为正确的逻辑系统不止一个,而是有好多个。而金岳霖的“一元”决不是学界通常所说的一元,金岳霖的“一元”是独特的一元,这个“一元”指的是逻辑真理的实质上的“一元”。金岳霖在这点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逻辑真理的实质只有一个———“穷尽可能”,但逻辑系统可以有很多。因此,金岳霖是在一个“逻辑”的基础上,承认逻辑系统的多样化,这与通常所说的“多元论”并不矛盾。
金岳霖对逻辑与逻辑系统的区分和现代逻辑发展中的系统内与系统外的区分本质上是相通的。逻辑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的学科,有效性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系统内的有效性,又称相对于系统的有效性;一种是系统外的有效性,又称直观有效性。系统内的有效性还可分为语法有效和语义有效而我们在进行日常的非形式论证时,显然也能分清什么样的论证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论证是错误的,这里所依据的显然不是上述的形式标准,而是某种直观的非形式的标准,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非形式论证不可能前提真而结论假,那么它就可被看做是有效的。这种直观的有效性标准就是所谓系统外的有效性。因此系统内的有效性是指在一个形式系统中的有效,它涉及系统;系统外的有效性是非形式的,它的论证得自它的前提,即它不可能前提真并且结论是假的,系统外的有效性是不涉及系统的[11]。逻辑“一元论”(通常意义上的)者认为,一个逻辑系统是正确的,如果在该系统内有效的形式论证相应于在系统外意义上有效的非形式论证,并且系统内逻辑真的公式与系统外意义上逻辑真的语句也存在对应关系:只有系统外有效,系统内才会有效。我们构造系统的目的就是要把握系统外的有效性。这种观点在金岳霖的思想里体现为:逻辑属于系统外有效,而逻辑系统则属于系统内有效,因为在没有逻辑系统之前,逻辑就一直在起作用。因此,金岳霖的观点能适用各种逻辑系统。金岳霖承认有一个“自在”的逻辑,他所讲的“逻辑”与“逻辑系统”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符合反映论的观点。
相比较而言,奎因认为标准逻辑系统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各种标准逻辑系统“是同一个逻辑的不同表述,是同一个逻辑配置以不同的计算机或证明程序”[9]。但这仅限于“标准逻辑”即经典逻辑系统。关于模态逻辑系统,奎因认为:“必然地”、“可能地”这些词会使语句成为非真值函项及量化构造的成分,为了容纳它们,可以接受一种必然性的构造,它通过在一语句前置连接词“必然地”而得出一语句。而“可能地”则可直接看做表示三个逐次一元构造的连接词的连接:“并非必然地并非。”然而模态词的用法是不清楚的。如果用两个相等的真陈述中的一个去替换另一个,就可能会出问题。例如,他说语句“汤姆认为图利写《伟大的艺术》”可能为真,而当以“西塞罗”去替换“图利”后,它可能会变成假的,尽管“西塞罗”=“图利”。于是,对模态逻辑的解释便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因反对模态逻辑,而这与奎因所处时代逻辑发展是有关的。因为在模态逻辑中,语形学是先发展起来的,语义学很晚以后才被提出来。因此在奎因时期,许多东西得不到解释。但是,在同样的背景下,金岳霖却并不反对模态逻辑作为一种新的模态逻辑的资格,由此在现代模态逻辑兴起并且长足发展的今天,我们可看出金岳霖的逻辑真理观和逻辑观的优势地位。
除必然性外,以往关于逻辑真理观的探讨中,“先验性”和“分析性”概念也起着重要作用。维特根斯坦将先验和分析都归于逻辑,主张逻辑之外都是偶然的。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命题是先天命题。“逻辑之为先天的,就在于非逻辑的思维是不可能的”,“一切演绎都是先天造成的”。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命题是先天真的,但却认为“先天的真的图像是没有的”。同时维特根斯坦又说:“逻辑是先验的。”而金岳霖区分了“先天”和“先验”两个概念,他的这一思想是非常独特而弥足珍贵的。
金岳霖认为“逻辑命题是先天的命题”,是可以“思议”的无矛盾的逻辑命题,是穷尽一切可能的必然命题和原则。“先天的原则无论在什么样的世界总是真的。”[12]逻辑命题从积极方面说,既不能假又不能不真;从消极方面说,逻辑命题没有肯定任何事实为事实,也没有供给我们任何事实方面的信息。“逻辑命题对于这世界是如何的世界,完全是消极的。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表示。”“对于事实毫无表示,逻辑命题才能无往而不真。”“它完全消极,它才能是先天的命题。”[6]虽然它们对一件一件的事实毫无表示,但却是任何可以思议的世界所不能违背的,也是不能不遵守的命题和原则。逻辑命题无往而不真。
金岳霖提出“逻辑既是可能的必然的关联,当然也就是任何事实的最高(或最低)限度”,提出“逻辑独立于共相的关联”的目的,就是要说明,逻辑是与事实无关的,逻辑对事实无所肯定,所以无论事实如何,逻辑总是必然的,逻辑是先天的必然的。
“先验原则(先验命题),在经验老在继续这一条件之下总是真的。可是,假如时间停留,经验打住,先验命题也许是假的。”[12]“先验命题”里的“先验”并不是我们对于它的知识是先验就有的,而只是说“只要有可以经验的世界,我们就得承认有这样的、本然的、轮转现实的、新陈代谢的世界”。先验属于接受方式,强调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对于以往为真,对于将来,只要有经验,总有相应于它的经验,所以不会不真;这一部分就是这里所说的先验的知识,即令将来的世界不是现在这样的世界,只要有经验,这一部分知识总是正确。”[12]显然,金岳霖关于先天与先验的区分,对于他未使用维特根斯坦关于“基本事实”的形而上学预设,起了重要作用。维特根斯坦把所有命题都分析成基本命题,然后运用基本命题真值函项的思想,说明维特根斯坦已经懂得用“穷尽可能”来定义“逻辑必然”,并且知道这种定义并不会导致恶性循环。金岳霖吸取了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从“穷尽可能”的角度,给出了逻辑真理的全新刻画。“穷尽可能”的逻辑真理观只预设了不矛盾法则,这样的预设是最少的,这也是他较之其他哲学家的优越之处。即使在金岳霖致力于自我批判的后期思想中,他也没有放弃其对演绎逻辑真理的认识,仍然认为用“穷尽可能”来界说逻辑“必然”最能体现逻辑真理的性质。这也是对其逻辑真理观优势与威力的一种独特说明。
参考文献:
[1]张建军.论金岳霖先生关于“思维三律”的思想[A].矛盾与悖论新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金岳霖.罗素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金岳霖.逻辑[A].金岳霖文集(第1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6]金岳霖.知识论[A].金岳霖文集(第3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7]金岳霖.思想律与自相矛盾[A].金岳霖文集(第1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8]张建军.强化的排中律与多值逻辑[A].矛盾与悖论新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奎因.逻辑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1.
[10]金岳霖.不相融的逻辑系统[A].金岳霖文集(第1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逻辑真理范文篇4
没有真理。这差不多是后现代主义的唯一共识。这共识的经典表述则是,怎么都行。从怀疑,到相对,到虚无,逻辑上顺理成章。反过来,从独断,到绝对,到决定论,结果依旧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最偷懒的思想,因为事情弄到这个份上,就什么事情都用不着干了,就这样了,一切结束了,玩完了。只有我们的共识是“怎样才行”的时候,哲学以及人类,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可惜,哲学式的经验一直是,用怀疑来驳斥独断,又以独断来抵制怀疑。问题在于,怀疑驳不倒独断,独断也抵挡不了怀疑。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问:哲学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老是纠缠独断和怀疑的两端?我们能不能到“问题的现场”去看看?这是个关键。很明显,哲学并不在随便什么地方都独断或者怀疑——这样的独断或者怀疑肯定得不到哲学的关照。哲学最大的特点是讲理。什么都怀疑或者什么都独断,那就是什么都不讲理,所以算不上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在什么地方都讲理。因为一个逻辑上的根本困难在于,理由需要进一步的理由,进一步的理由继续需要更进一步的理由,依次类推,以至无穷。我们总要在某个地方不再给出逻辑理由,也给不出理由。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只能给出那么几个层次的理由,理由很快就被我们用完了,于是就碰到了那个“坚硬的石头”,这时候我们就只能说,“事情就这样了,再没有别的理由了”。康德也是谨慎的,于是说自在之物不可知。这个自在之物差不多就是康德式的“坚硬的石头”;说“不可知”,大概的意思也是说,我们不可能在那个“坚硬的石头”(自在之物)上再给出理由。于是,康德早就想说,对于不可想的,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则公开表态,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
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象康德、维特根斯坦那么诚实谨慎。哲学家喜欢喋喋不休,所以很不愿意沉默,哪怕前面是块“坚硬的石头”,并没有办法给出进一步的理由。这样,问题出现了。在理性的尽头,哲学家要么会给出一个或者几个所谓“自明”的公理——这是独断论;要么因此而怀疑一切理由,声称一切都是虚妄——这是怀疑论。于是,我们可以说,在理性逻辑的尽头,在那块坚硬的石头面前,最能够看出一位哲学家的本来面目了。大致就这么三种,独断的,怀疑的,以及沉默的。能够在逻辑/语言的尽头沉默的哲学家,已经相当的高明了。但是,其实也很常识。因为大家都很明白,我们不可能一直没完没了地喋喋不休下去,话总得有个头。关键的问题是,哲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头”?哲学的出“头”之日在什么地方?
问题的现场在逻辑和语言的尽头。
于是,我们先要问:在逻辑和语言的尽头,在人性和神性的边界,理性和启示存在着什么样的两难?这个时候,我们究竟是继续相信力不从心的理性,还是相信神秘兮兮的启示?这当然很难抉择,也从来没有清晰的抉择。哲学家在这里倒是很狡猾,打着理性的幌子去求助于神性的启示,同时,借着神性的权威来保证理性的牢靠。这种事情实在太便当了。却一直能够互相保持默契,一本正经地把买来的便宜当作真理。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况是哲学家的谎言?
2、事情的真相
以往哲学的根本性的问题现场发生在逻辑/语言的尽头。我在怀疑,这是不是一个虚假的现场?一个虚假问题的虚设的现场?就是说,哲学的真正的根本问题并不发生在理性和启示的边界上,就好象我们人的问题并不能依靠纠缠于天堂和地狱来解决。我想说,其实我们中了逻辑的圈套,中了语言的埋伏。
按照通常的说法,哲学就是反思的,就是前提批判。这当然不错。但是过于夸张。思想的大敌是过于张扬,过于任性。哲学出于对普遍性的特殊偏好,总喜欢把某种大致的普遍原则放纵为绝对的思想体系。举例来说,当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的确说出了很大的真理,但是,他得意洋洋地从这个东西开始来建设他的哲学体系的时候,他就弄出了更大的谬误。对于所谓反思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炮制类似的东西,比如,我坚持说,哲学就是“元-”思(meta-thinking);或者,哲学就是“后-”思(post-thinking);诸如此类。只要足够固执,这些说法就会显得很伟大。所以,当你说哲学是反思的时候,说出了很大的真理;但是当你说,哲学“就是”反思(没有其他的思了),那就犯了更大的错误。偏执一端是小孩子的天性,但不应该是哲学家的嗜好。
哲学的问题就是在反思这个问题上过火了。正是这个地方过火了,才制造了虚假的问题和虚设的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反思总会先天地逻辑地要求进一步反思,于是进进一步反思,结果就遇到了逻辑和语言的尽头。这样给人的错觉就是,那些逻辑尽头上的问题就是基本最重要最根源最关键的问题了。这实在是个假象。因为我们中了逻辑反思的圈套。我们不幸中计了,还浑然不知,一相情愿地把它当作个宝。我现在想说,其实哲学一直在纠缠的那些问题一直是些逻辑或者语言的问题,而不是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逻辑反思的尽头所出现的问题,那些看上去朔大无比的问题,其实不过是些逻辑的/语言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还说,语言是思想的界限。其实逻辑也是这样。逻辑和语言一起规定了想/说的边界。但是也仅仅是界限的问题。界限是个事实,不是我们管得了的。逻辑/语言的尽头所出现的问题是不能逻辑地/语言地解决的。逻辑/语言上的最后困难只能哲学地解决。但是,哲学根本性问题和困难并不能轻易逻辑/语言地解决。莱布尼茨曾经设想一种人工数理逻辑语言,目的是,如果出现什么哲学的争执,那就用不着争论,“让我们来算一算吧”。莱布尼茨就是想把哲学问题逻辑地解决。后来的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也表述了一个相似的方案,他们说,哲学就是澄清语言的意义。他们的理想就是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到现在,他们的努力除了还有点技术/方法上的意义之外,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我想再强调一遍,哲学的困难不能语言/逻辑地解决,相反,逻辑/语言的困难到是必须哲学地解决。
现代哲学过于迷信语言了,就好象近代哲学迷恋逻辑一样。很多哲学家都不愿意把语言作为工具来看待。海德格尔就夸张地说,语言是存在的家。甚至有人说,不是我们是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诸如此类。这些说法的确足够惊世骇俗。但是我要说,真理往往是朴素平实的。当然没有低估语言的重要性的意思。把语言当作工具丝毫没有低估语言的意义。因为没有工具人就没法活。但是,语言却并不具有那么重要的存在论意义。我们生活在生活/世界中,而不是语言/逻辑世界中。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人生活在语言/逻辑世界中,但也仅仅是在如下意义上:人仅仅是生活在生活/世界的语言逻辑中。语言/逻辑是个无限开放的可能世界,它们通过某种方式,可以“说出”任何多种可能世界。但是,很明显,我们并不对所有语言的可能世界都在乎。这里的一个存在论根据是什么?不是别的,而是生活/世界。人们为什么老说,“说得到好听”、“说得比唱得好听”、“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等等。这就很说明了人们并不是对任何语言意义上的可能世界都很在意。也很说明了,人们真正在意的是生活/世界——对语言的可能世界的评判根据就是生活/世界。
现在我要指出,当我说哲学的很多问题是假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些问题过于形而上,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其实哲学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取消那些问题,就必须全盘取消哲学。我说哲学的很多问题是假问题,意思是说,哲学过于把逻辑的/语言的问题当做哲学的问题,并且过于相信哲学的问题可以逻辑地/语言地解决。也就是说,哲学所关注的某些朔大无比的问题,其实仅仅是逻辑/语言上的问题,而哲学的解决方案也是逻辑/语言地解决。再直白点说就是,哲学研究是不是哲学,而是逻辑/语言。哲学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真相。
3、哲学的问题
我们刚刚说,以往哲学的错误在于,它研究的其实不是哲学,而是逻辑/语言。那么,哲学本身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他现在没有写哲学论文的欲望了。因为很多问题想啊想啊,最后都是一个结论——我应该沉默!因为问题弄到最后,都是不可说的。这是很有维特根斯坦色彩的思想体验。胡塞尔也曾经比喻说,他搞哲学就象是在磨一把刀子,磨啊磨啊,不知不觉,结果竟然磨没了。他们真是诚实得可爱。其实,如果谁想要坚持传统哲学的问题和思路,把那些逻辑/语言问题很当真,那就必然是这样的宿命。因为你最后碰到的问题都不过是逻辑的悖论和语言的悖论。要么是逻辑上的无穷第推和循环论证,要么是语言上的语义悖论和语法反复。而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逻辑地/语言地解决的。根据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任何理论系统都不可能获得自足的圆满性。所以,问题弄到这个份上,就只能沉默了。
前边说到了,逻辑/语言的问题只能哲学地解决,而哲学的问题却不能逻辑/语言地解决——除非是假的哲学问题。所以问题并不象维特根斯坦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哲学把那些胡说变成明显的胡说就可以告老还乡了。假设大家都规矩了,不胡说了,仍然还有问题,这时候出现的就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我先要说,并不存在确定的哲学问题。也并不存在哲学这样一门专业的哲学学科。如果谁要专业地学哲学,那就肯定学不到真正的哲学,而仅仅是些哲学史(死)的知识。哲学的问题在哲学之外,在理论之前。任何专业领域都不会出现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哲学问题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那些所谓基础性和根本性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想象。解决逻辑的前提性之后,我们依然会遇到巨大的思想困难,这时候就暗示着哲学问题的出现。当然,哲学问题也不是某些人文理想特别发达的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哲学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就是人的存在意义的问题。因为,1)、人的存在意义问题并不是可以哲学地解决的,不可能因为哲学家论证了人存在的意义人的活着就有了意义——这不就等于说,在哲学家有效地论证这个问题之前,大家不是白活了?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在这里也是值得怀疑的——先不说这个命题本身的逻辑问题。应该说,我做故我在。我做事,我存在。哲学家的故作深沉真让人觉得可笑,好象人活着的主要工作就是成天顾影自怜自怨自艾似的。当然,那样的说法对传统的哲学的确非常有利的——这恐怕是问题真正的原因之所在。2)、这个世界肯定不单单存在着人,对于人的任何思考都必须同时思考和人相关的所有事物。过于沉迷于私自的“存在与虚无”无助于人的存在意义这个问题的解决。人文主义有着过火的文学式抒情。哲学当然不能变成数学,但是也不能变成文学。德里达等后现代哲学家已经赤裸裸地这样鼓吹了。
到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哲学的问题就是那些生活世界中的两难,那些冲突着的观念、思想、习俗以及趣味。因为不管这世界如何美好,都会出现说不尽的两难。举例来说吧。假设我的哥哥犯罪了,甚至杀人了,警察在外面追他,现在他跑到我家来躲避警察的追捕。这时候,我怎么办?这里我不打算说该怎么处理这个具体问题,仅仅想说,这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两难,是哲学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实际上,生活/世界中有太多类似的两难和困境了,这种困境又不是理性就可以解决的。诸如,情与理、忠与孝、仁与义、家与国、亲与友,等等等等。我相信,这就是直接面对了问题本身,哲学就要在这里发现思想的困难以及生活本身的困境,发现一些宝贵的思想素质。而且,我们在这里会发现,理性或者逻辑的力量其实非常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给出所谓的规律和规范——给出了也不会有效,不可能有效地教导人们说,大家应该应该怎么样。当然法律总会给出严格的规则。可惜哲学不是法律。
在这个时候,哲学也就面对了真正的问题,面对了真正永恒的困难。与那些逻辑的和语言的问题相比,这些问题显得那么真实有力,直逼人心。
4、从事实开始
人们通常都对哲学望而生畏,感觉它好象是高深莫测。更多的人倾向与于嘲笑哲学家。比如,人们曾经嘲笑分析哲学家说,哲学家不过是用他自己也觉得稀里糊涂的语言来分析蠢人说的傻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有点刻薄,但是并没有错怪哲学家。
哲学家过于看重逻辑的眼色了,喜欢跟着逻辑走。如果说艺术家是跟感觉走,那么哲学家大概是跟逻辑走。逻辑需要什么,哲学家就献上什么。有两种想象,一种是文学的想象,一种是逻辑的想象。文学的想象当然是感觉体验的随心飞扬。逻辑的想象则是因为逻辑的需要而给出的蹩脚假设。我们很容易看到,哲学有太多的蹩脚假设了。其实那都是哲学和逻辑的勾当。哲学史上有太多的第一原理了,但是可惜很少有后来人把这些原理当真。如果谁对逻辑百依百顺,那么肯定会挖空心思给出几条第一原理。无论如何,这些第一原理都不过是逻辑的想象。也正由于我们有过多的第一原理,当怀疑主义很兴奋的时候,人们会毫不客气地戳穿假象,说“一切都不过是些说法”。面对这样的指责,哲学家通常会故作镇定,然后一本正经地给出进一步的第一原理。其实,在这里没有办法判明谁对谁错。因为那些出于逻辑需要而给出的普遍性的逻辑假定,都是不可证实也是不可证伪的。或者说,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说的。
但是,哲学喜欢体系,喜欢自圆其说,并且大致认为能够自圆其说就是真理体系了。说实话,预先假设几条原则,然后据此推证出几个体系并不是什么难事。哲学厌恶矛盾,就象自然界厌恶真空。于是一心打磨逻辑上的圆润,一心避免逻辑上的漏洞。但是,很遗憾,避免了漏洞却同时陷入了空洞。从给出的逻辑假定开始,然后小心翼翼地推论,当然不会出现太大的逻辑漏洞。但是,如果假定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得到的也不过是个自圆其说逻辑完美的谬论。有不合逻辑的错误,也有自圆其说的谬论。当然,哲学家给出的逻辑假定大体不会错得很离谱(一个人活那么几十年总会明白几条大致不错的所谓规律),再加上在推论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经验性修正——哲学并不会象数学那么干净,哲学家在建设体系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参考经验生活中的事实,并据此作出即时修正——这样,最后的哲学体系也很难全盘皆错。但是,在这里我想指出,哲学家的逻辑想象至少给定的是不真实的假设,于是就必然推论出不真实的理论。不存在一劳永逸并且全面正确的第一原理。一个虚假的开端必然得不到一个真实的结论。
举例来说,哲学家在伦理问题上喜欢假设人性,要么说人性善,要么说人性恶,或者虚张声势地含糊其词,说人性不善不恶。然后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给出一打或者几打伦理规范,好象人类的问题就这样得到圆满解决。追问“本”性,是一种逻辑的嗜好。或者是受了语言的表面假象的诱惑。以为搞定一个“本”,对那些枝节的“末”的解决也就势如破竹了。其实这仅仅上一种逻辑的和语义的想象罢了。问题是,不管人的“本性”是什么,一个无法否认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我们这个世界永远都有好人和坏人。伦理的思考要从“好人和坏人同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开始,而不是从假设人有没有良心开始。
从事实开始,直面问题本身。为什么要追问那么多的所谓“本源”?哪里有那么多的所谓“本源”?哲学由于职业的习惯,喜欢宣称诸如“我思故我在”、“思想是人的唯一尊严”、“诗意地栖居”等等,这样一些对自己明显有利的话。但是,我们何不把眼光转向生活事实?人类生活那么精彩多样,那么多美丽与伟大,丑陋与渺小,怎么到哲学家这里进单单看到“思想”这东西了?怪不得人们很容易把哲学家当作疯子。哲学家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疯子。以至于哲学团伙的内部都有叛徒出卖他们,说那些话不过是些胡说。
迷信逻辑,迷信语言,迷信罗各斯,都远离了事实,远离了生活现场,远离了问题本身。通过逻辑的手法偷换了的问题,当然也是问题,但是肯定不是真实的问题。哲学应该回归一种生活的感觉,哲学应该重新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能跟着冰冷的逻辑或者热烈的人文想象走得太远,最后变成一种谁学了谁糊涂的专业。
5、事实和逻辑
事实和逻辑,究竟谁更强大?当事实和逻辑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站在哪一边?人们当然毫不由于地站在事实一边。但是哲学家通常会站在逻辑一边。哲学家有个很好的说法,有了这个说法,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逻辑一边。是这样的,哲学家通常喜欢区分现象与本质,区分假象与实在。于是,他们宣称那些所谓事实不过是些现象,看问题得看本质,得用逻辑理性来把握本质。事实总是个体的、特殊的,不可能存在某种“普遍的事实”。但是,在那些特殊的、个体的事实背后,究竟有个什么样的本质?
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本质是一种逻辑纵深所给予的一个逻辑设定。逻辑主义思维喜欢挖掘“背后的东西”,以为沿着逻辑的康庄大道一直挖下去,就可以抵达那个本质。但是,就象剥苹果一样,哲学家剥啊剥,剥到最后剩下个苹果核,于是说,看啊诸位,这才是真正的苹果。他们假装不知道那个苹果早就被剥得面目全非。这可能也不能过分地指责哲学家,因为他们总是有过火的野心和热情,总想一劳永逸地全盘解决或者根本解决。
其实,事实可能就是在生活/世界中立体而整体地给予我们的。我们说看到了某个事实,并不是单纯地在一种横向的、平面的层面上看到一个现象或者假象,当然也不是在一种逻辑的、纵深的意义上的所谓本质。而应该说,是在生活/世界中立体而整体地理解了一个饱满而真实的存在现场。任何事情都是整体而立体地发生在存在现场的,我们也都是整体而立体地身处生活现场。我们都在现场,于是我们“目击”了一切。事情的发生,不仅仅通过眼睛而给予我们,还通过心灵,通过理智以及情感等等,饱满地给予我们的。当然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是不会老是看到假象。人们并不会愚蠢到只是单纯地相信眼睛,但是哲学家却常常精明到只是“深刻地”相信逻辑。
逻辑不能代替事实,只能用来分析事实。事实是思想的起点,逻辑是思想的界限。事实是思想的根据,逻辑则仅仅是思想的工具。逻辑形而上学过于夸张了逻辑的力量。以为只有逻辑理性把握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本质的。逻辑凭借某种形而上学的任性才有横行霸道的可能。事实才是真正的力量。真实而有力,这就是事实。当然,事实的力量不在逻辑意义上,而在存在论意义上。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就不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逻辑可以建设很多可能世界,但是并不是所有可能世界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回避逻辑,但是没有办法回避事实。逻辑的对错仅仅是推理上的对错,但是事实的对错却是价值上的好坏。我想说,价值上的对错是最要命的。
当然你可以追问说,什么是事实?这个问题我仅仅能够回答说,事实就是事实,并且就此了事。因为这样的问题仍然是个逻辑主义的圈套。它蛊惑着我们去给出本质化的定义。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大家(哲学家是个例外)不可能竟然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意思,要麻烦哲学家来解释。对于那些基本的概念,哲学是不需要给出定义的。你给出定义反倒把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东西弄糊涂了。比如,哲学家怎么定义“好”?如果硬是要定义,那可能只能说:所谓好,就是有用的;或者,好就是美好的;或者,好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诸如此类。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定义其实都乱七八糟,越说我们越糊涂。对于怎么分辨这样一类不可定义的基本概念,我想,至少可以给出这么两个标准:1)、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地使用,离开它我们就说不了话的那些词语。比如,好、坏、善、恶、美、丑、真、假,等等。这些基本概念绝对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那些逻辑意义的基本,不象那些所谓本质、本体、现象、先天直观、绝对理念,诸如此类。尽管它们看起来大得吓人,好象基本得很。2)、规定着我们的思想结构和世界形式的那些词语,离开它们我们的思想和世界图景就得散架,就不知道怎么思想。比如,我们的经常说的好/坏、美/丑,我们当然可以对这样的二分和二元语言表示不满,但是没有这样的二分,我们就没有办法思想——那不等于好坏不分、美丑不顾一团混沌吗?
最后我得补充说,这里没有要全盘打倒逻辑的意思,而仅仅想反对逻辑形而上学,仅仅想反对逻辑主义、逻辑本体。我很乐意把逻辑当作思想工具——其实,亚里士多德以及培根也都把他们的逻辑学体系叫做《工具论》、《新工具》。
6、真理与价值
后现代已经宣布了唯一一条真理:没有真理。当下哲学的任何思考,都不可能回避了后现代责难还能取得进展。我们现在来面对这个最大的诘难。
通常认为后现代是现性主义的内部后果。理性没有办法保证绝对真理,于是没有办法根除怀疑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主体性,等等理性主义思路在现代哲学发展中出现了巨大的根本性困难。这些说法当然没错。但是可能还有一个相对外在的因素,一个社会学因素。我的意思是,后现代主义其实更多的是个现代社会的一个综合病症,或者可以叫做“现代社会综合症”。因此后现代更多的是个社会学事件,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有那么严重的思想根源。因为后现代的思想根源都是先天的,一开始就是那样,一开始就没有绝对真理。哲学家老喜欢夸张思想的作用,这其实是虚假而过分的。哲学思考应该跳出哲学学科的专业眼光来观察、思考问题。
法国的奈仁在分析法国1968红色五月风暴的后现代因素时,曾经用“心智剩余”这个词来描述现代社会——注意,不是“后现代社会”,其实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情绪,大家矫情地抱怨一切,却什么也舍不得放弃。所以,后现代差不多就是,一边兴高采烈地大鱼大肉,一边埋怨吃肉不够绿色环保。说得难听的,那叫吃饱了给撑的。我对后现代也有一个和奈仁相似的描述,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泡沫”。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在物质剩余、经济泡沫的同时,也有着大量的“心智剩余”和“精神泡沫”。这个社会学因素可能比哲学家所想象的思想因素更具有决定性。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个技术的时代。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很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点。好象人们的理性(所谓理性人)就是成天用来盘算一些蝇头小利。这个假设其实大体上揭示出了现性的技术性和工具性。因为现代哲学也差不多是个经济人,老是在技术上、细节上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相反,在价值问题上却一直低头沉默。分析哲学尤其是这样,技术上到是一丝不苟滴水不漏。而以解释学问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由于过分发挥了主体性(尽管他们自称是反主体的,然而却陷入了更深的主体性)和个体存在的体验价值,也不可能在价值问题上给出有力的表述。于是,总体上说,现性或者说是现代哲学是个悬隔了价值的哲学。要么避而不论,宣称价值问题不可说;要么本身无力给出有效有力的表述。因此,现代哲学的那些话语,都是些“缺德的”话语。现代社会是“缺德的”社会,人们成天在盘算自己的那些蝇头小利。相应的,现代哲学则是“缺德的”哲学,在逻辑语言的细枝末节上喋喋不休,或者在个体的存在意义体验上自怨自艾。
一方面,是话语/知识/真理与价值/德性脱钩,价值缺席;另一方面,则是话语/知识/真理和权力/利益勾结,真理失贞。知识悬隔了价值,真理失去了贞操,这时候,后现代主义出来挑明说,“没有真理”,这又有什么奇怪呢?于是鼓吹“怎么都行”,又有什么不行呢?
当初现代哲学仅仅是想谨慎,没有大的抱负,以为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盘算一下就一切OK了。在技术细节上可以“不择手段”(费耶阿本德说的“怎么都行”其实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个方法论口号),但是没想到,最后竟然堕落为“不择价值”。于是怀疑主义顺理成章地兑变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本身是个技术性的东西,虚无主义才是价值性、存在论意义上的东西。
到这里,我想说,我们应该鼓吹一种“德性的话语”,把价值和真理给重新糅合起来。真理和价值的分离就是现代哲学的一个后果,也是哲学传统的一个逻辑结局。事实上,我们很难把真理与价值上有效地剥离。价值和真理本身是统合着的。这一点在伦理学上表现的尤其明显。伦理的真理总是和价值直接关联的。可惜现代伦理学也几乎要把伦理价值从伦理真理中剥离。于是规范伦理学横行,德性伦理学凋尽。人们喜欢谈论规范意义上的公正(规范的第一原则是公正),却不愿意论证价值意义上的善。
我想强调,没有价值,哪里来的真理?因为至少真理本身是有价值的,不然我们就真用不着那么麻烦,干脆一劳永逸地怎么都行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不存在价值问题,而是哲学过于软弱无力,回避了价值问题——确实,价值问题是最难说的,但是并非不可说。
7、饱满的真理
哲学史上至少存在着三种经典的真理观,是这样的:a、认识论哲学中的符合论;b、现代人文主义的无蔽论;c、实用主义的效用论。这些真理论都存在着这样的根本困难:一)、就认识/逻辑本身而言,真理缺乏理性自身所要求的确定性,简单说,就是真理往往显得不够真,因此哲学史上怀疑论源源流长;二)、就实践/行为自觉而言,真理缺乏对生活/世界的指导权——如果真的有,那也是很微弱的。我们通常并不老按照所谓真理办事,通常的说法叫做:“我知道XX是真确的,但是……”。也就是说,你说的很对,但是我却不想或者不能那么做。这无疑让哲学很是尴尬。这种尴尬的根源在于,“真理之路”仅仅是在逻辑图式中寻找“单边主义的”逻辑合理性。就是说,这远远不是饱满的真理观念。首先,它存在于一种不真实的假设的逻辑图式中;其次,它依附于“单边主义的”逻辑合理性。简单说,它们都是一种片面的真理观,总是透过一个门缝——逻辑的、人文的或者功利的门缝,把真理给看扁了。
真理不幸被看扁了。我们需要一种饱满的真理。
所以我在上面说,要把真理和价值重新糅合起来——它们本来就不是分离的。传统的真理尤其强调的是逻辑意义上的真,差不多等于说,真理就是符合逻辑。我想说,符合逻辑仅仅是真理的一个起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哲学的真理和数学的真理是不一样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区分数学与哲学。哲学直面生活中的困境和两难,所以也必定要是生活/世界中的真理。生活/世界有情有义,有声有色,有真有假,那么,哲学首先就必须把这些事实考虑进去,而不能仅仅搭了逻辑的便车,仅仅考虑逻辑意义上的真。哲学不能不顾生活事实,而只顾勾结了逻辑一起投机取巧。因为你不顾生活的声色情义,那就不可能发现真实而有力的真理,只能给出一些自以为是而势单力薄的说法/意见——人们仅仅是姑且听之而已,并不当真。
把生活/世界中司空见惯的真假虚实、声色情义都考虑进去,那么,就必须是一种蕴涵了逻辑的真、行为的善和情趣的美的饱满真理。生活/世界也必须配套这样的饱满真理。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真理、价值和事实是统合着的。简单点说,当我们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逻辑意义上的合理性,单纯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不具有真理的完全合法性。现在,任何作为一个真理是否合法,至少需要参考这样两个标准:1、合理性,也就是逻辑意义上合乎逻辑规定,合乎生活事实的规范;2、合情性,即符合生活直观——大感性(赵汀阳发现了这样一种感性的存在,他在设想伦理学理论的时候,明确把“合理性”和“合情性”两个概念并列,并且指出“合情性”“意味着在理性理由之外的、但是与理性理由同样有力的感性理由”,“是具有普遍性力量的‘大感性’”,“它和理性理由是同水平的无可置疑的人性理由”。《论可能生活》,页1。)和生活情趣。我曾经在我的一篇论文《从逻辑图式到生活世界》中说,一方面,真理受生活直观(大感性)和逻辑理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它受生活情态(活理性)和辨证理性的调节。简单说,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这是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
我们下面就来谈中国的智慧。
8、中国的智慧
现在中国哲学界还在一本正经地争论一个虚假的问题: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我都怀疑学者们是否就是以研究这类问题来混饭吃。那是个假问题,至少不是哲学问题。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肯定还离哲学很远。如果谁要是逼着我回答——不回答就不给饭吃,我会迫不得已地说,我想指出关键的三点:1、知识和权力的勾结。中国知识因为处于弱势,所以话语权明显短缺,搞得连自己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当年赵家老爷就硬是不准阿Q姓赵。2、中国自然有着自己的独特智慧,至于这智慧叫不叫哲学或者其他什么名字,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中国智慧给思想提供了什么样可能方向和思路?3、中国的学者在思想上一直压着“现代化”这块历史巨痒,如果中国思想要想有新的进展,那就必须超越这个历史巨痒。
在真理问题上,中国智慧是很值得关注的。我们前面说到的“饱满真理”,其实就来自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国有所谓“天人合一”(真的最高境界)、“知行合一”(善的最高境界)和“情景合一”(美的最高境界),讲的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饱满的智慧理念。生活/世界中的真正智慧也就是这样“三合一”的饱满智慧。遗憾的是,中国传统中的这种饱满智慧一直在西方的知识权威(权力)下的不到应有的合法性。还有人在论证中国哲学的时候,喜欢夸大“天人合一”的一面,把中国哲学解释成了宇宙啊人生啊之类的玄学。其实中国哲学一点都不玄。她就是生活现场的思想/践行/审美的活生生赤裸裸的思想素质。孔子老是讲仁啊义啊,忠啊孝啊,可见他是直面生活的两难的。而且他很少给出一成不变的原则,一直在忠孝仁义的困难中挣扎。因为孔子很清楚生活/世界是个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存在现场,只能饱满地理解了这个现场之后,才能对与其中的困难给出有效有力的解决。所以中国人喜欢讲权衡,讲中庸平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就是,谁也不愿意得罪。比如,《论语-学而》中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差不多是面面俱到。中国思想总是考虑得很周到,所以有时候显得有点狡猾。但是,对于生活和智慧的饱满理解却是相当高明的。
如果把中西哲学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务求高深——所以老是喜欢在逻辑上望深里挖,搞单向的直线的逻辑纵深;中国智慧则贵在高明,习惯照顾到四面八方,总是愿意直接地面对问题和困难本身。西方过于迷信逻辑和语言,算得上是逻辑/语言本体论和逻辑/语言独断论,中国则对此相当谨慎,因为中国哲总是把生活看做最牢靠的东西,于是,在语言/逻辑问题上,可以说是语言/逻辑怀疑论和语言/逻辑工具论。比如,《老子》里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辩若纳”、“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论语》“巧言乱德”、“敏于事,慎于言”、“天何言哉”;《孟子》“予岂好辩哉”;《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如此类。
中国智慧是很讲人“情”的,但是并非不讲道“理”。只是中国智慧中的道理更具有人情味,更符合人们的生活直观,符合生活/世界中的“大感性”。中国人的“道理”就是生活智慧,而不是死板的、冰凉的逻辑真理。中国智慧讲原则,也讲人情,讲合理性,也讲合情性。因此我们很讲究“方中有圆”、“外圆内方”。——这一点让无疑西方哲学忍无可忍,因为在逻辑主义思维方式中,“方的圆”或“圆的方”都是不可理喻的。所以现代语言学的哲学家(如梅农、罗素等)老是喜欢拿“方的圆”做反例来说事。
逻辑真理范文篇5
然则凭着这个本质之问,我们难道没有遁入那窒息一切思想的普遍性之空洞中去么?此种追问的浮夸性难道不是彰明了所有哲学的无根么?而一种有根的、转向现实的思想,必须首先并且开门见山地坚决要求去建立那种在今天给予我们以尺度和标准的现实真理,以防止意见和评判的混淆。面对现实的需要,这个无视于一切现实的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抽象的”)问题又有何用呢?这种本质之问难道不是我们所能问的最不着边际、最干巴巴的问题么?
无人能逃避上述顾虑的明显的确凿性。无人能轻易忽视这一顾虑的逼人的严肃性。但谁在这一顾虑中说话呢?是“健全的”人类理智。它固执于显而易见的利益需求而竭力反对关于存在者之本质的知识,即长期以来被称为“哲学”的那种根本知识。
普通的人类理智自有其必然性;它以其特有的武器来维护它的权利。这就是诉诸于它的要求和思虑的“不言自明性”。而哲学从来就不能驳倒普通理智,因为后者对于哲学的语言置若罔闻。哲学甚至不能奢望去驳倒普通理智,因为后者对于那种被哲学置于本质洞察面前的东西熟视无睹。
再者,只消我们以为自己对那些生活经验、行为、研究、造型和信仰的林林总总的“真理”感到确信,则我们本身就还持留在普通理智的明白可解性中。我们自己就助长了那种以“不言自明性”反对任何置疑要求的拒斥态度。
因此,即便我们必得追问真理,我们也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立身于何处?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形如何。我们要寻求那个应当在人的历史中并且为这种历史而为人设立起来的目标。我们要现实的“真理”。可见,还是真理!
但在寻求现实的“真理”之际,我们当也已经知道真理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只是“凭感受”并且“大体上”知道真理?不过,这种约莫含糊的“知道”和对之漠不关心的态度,难道不是比那种对真理之本质的纯粹无知更加苍白么?
一、流俗的真理概念
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呢?“真理”,这是一个崇高的、同时却已经被用滥了的、几近晦暗不明的字眼,它意指那个使真实成其为真实的东西。什么是真实(Wahres)呢?例如,我们说:“我们一起完成这项任务,是真实的快乐”。我们意思是说:这是一种纯粹的、现实的快乐。真实就是现实(dasWirkliche)。据此,我们也谈论不同于假金的真金。假金其实并非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它只是一种“假象”(Schein),因而是非现实的。非现实被看作现实的反面。但假金其实也是某个现实的东西。因此,我们更明白地说:现实的金是真正的金。但两者又都是“现实的”,真正的金并不亚于流通的非真正的金。可见,真金之真实并不能由它的现实性来保证。于是,我们又要重提这样一个问题:这里何谓真正的和真实的?真正的金是那种现实的东西,其现实性符合于我们“本来”就事先并且总是以金所意指的东西。相反地,当我们以为是假金时,我们就说:“这是某种不相符的东西”。而对于“适得其所”的东西,我们就说:这是名符其实的。事情是相符的。
然而,我们不仅把现实的快乐、真正的金和所有此类存在者称为真实的,而且首先也把我们关于存在者的陈述称为真实的或者虚假的,而存在者本身按其方式可以是真正的或者非真正的,在其现实性中可以是这样或者那样。当一个陈述所指所说与它所陈述的事情相符合时,该陈述便是真实的。甚至在这里,我们也说:这是名符其实的。但现在相符的不是事情(Sache),而是命题(Satz)。
真实的东西,无论是真实的事情还是真实的命题,就是相符、一致的东西。在这里,真实和真理就意味着符合(Stimmen),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一方面是事情与关于事情的先行意谓的符合;另一方面则是陈述的意思与事情的符合。
传统的真理定义表明了符合的这一双重特性:veritasestadaequatioreietintellectus。这个定义的意思可以是:真理是物(事情)对知的适合。但它也可以表示:真理是知对物(事情)的适合。诚然,人们往往喜欢把上述本质界定仅仅表达为如下公式:veritasestadaequatiointellectusadrem[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不过,这样被理解的真理,即命题真理,却只有在事情真理(Sachwahrheit)的基础上,亦即在adequatioreiadintellectum[物与知的符合]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真理的两个本质概念始终就意指一种“以……为取向”,因此它们所思的就是作为正确性(Richtigkeit)的真理。
尽管如此,前者却并非对后者的单纯颠倒。而毋宁说,在两种情况下,intellectus[知]与res[物]是被作了不同的思考。为了认清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溯通常的真理概念的流俗公式的最切近的(中世纪的)起源。作为adaequatioreiadintellectum[物与知的符合]的veritas[真理]并不就是指后来的、唯基于人的主体性才有可能的康德的先验思想,也即“对象符合于我们的知识”,而是指基督教神学的信仰,即认为:从物的所是和物是否存在看,物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们作为受造物(enscreatum)符合于在intellectusdivinus即上帝之精神中预先设定的理念,因而是适合理念的(idee-gerecht)(即正确的),并且在此意义上看来是“真实的”。就连intellectushumanus[人类理智]也是一种enscreatum[受造物]。作为上帝赋予人的一种能力,它必须满足上帝的idea[理念]。但是,理智之所以是适合理念的,乃是由于它在其命题中实现所思与那个必然相应于idea[理念]的物的适合。如果一切存在者都是“受造的”,那么,人类知识之真理的可能性就基于这样一回事情:物与命题同样是适合理念的,因而根据上帝创世计划的统一性而彼此吻合。作为adaequatiorei(creandae)adintellecctum(divinum)[物(受造物)与知(上帝)的符合]的veritas[真理],保证了作为adaequatiointellectus(humani)adrem(creatam)[知(人类的)与物(创造的)的符合]的veritas[真理]。在本质上,真理无非是指convenientia[协同],也即作为受造物的存在者在自身中间与创造主的符合一致,一种根据创世秩序之规定的“符合”。
但是,在摆脱了创世观念之后,这种秩序同样也能一般地和不确定地作为世界秩序而被表象出来。神学上所构想的创世秩序为世界理性(Weltvernunft)对一切对象的可计划性所取代。世界理性为自身立法,从而也要求其程序(这被看作是“合逻辑的”)具有直接的明白可解性。命题真理的本质在于陈述的正确性,这一点用不着特别的论证。即便是在人们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徒劳努力去解释这种正确性如何发生时,人们也是把这种正确性先行设定为真理的本质了。同样,事情真理也总是意味着现成事物与其“合理性的”本质概念的符合。这就形成一种假象:仿佛这一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是无赖于对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的阐释的——这种阐释总是包含着对作为intellectus[知识]的承担者和实行者的人的本质的阐释。于是,有关真理之本质的公式(veritasestadaequatiointellectusetrei[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就获得了它的任何人都可以立即洞明的普遍有效性。这一真理概念的不言自明性的本质根据几乎未曾得到过关注;而在这种自明性的支配下,人们也就承认下面这回事情是同样不言自明的:真理有一个反面,并且有非真理(Unwahrheit)。命题的非真理(不正确性)就是陈述与事情的不一致。事情的非真理(非真正性)就是存在者与其本质的不符合。无论如何,非真理总是被把握为不符合。此种不符合落在真理之本质之外。因此,在把捉真理的纯粹本质之际,就可以把作为真理的这样一个反面的非真理撇在一边了。
然而,归根到底,我们还需要对真理之本质作一种特殊的揭示么?真理的纯粹本质不是已经在那个不为任何理论所扰乱并且由其自明性所确保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中得到充分体现了吗?再者,如果我们把那种将命题真理归结为事情真理的做法看作它最初所显示出来的东西,看作一种神学的解释,如果我们此外还纯粹地保持哲学上的本质界定,以防止神学的混杂,并且把真理概念局限于命题真理,那么,我们立即就遇到了一种古老的——尽管不是最古老的——思想传统,依这个传统来看,真理就是陈述(λογοζ)与事情(πραγμα)的符合一致(ομοιωσιζ)。假如我们知道陈述与事情的符合一致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有关陈述还有什么值得我们追问的呢?我们知道这种符合一致的意思吗?
二、符合的内在可能性
我们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符合。例如,看到桌子上的两个五分硬币,我们便说:它们彼此是符合一致的。两者由于外观上的一致而相符合。因此,它们有着这种共同的外观,而且就此而言,它们是相同的。进一步,譬如当我们就其中的一枚硬币说:这枚硬币是圆的,这时侯,我们也谈到了符合。这里,是陈述与物相符合。其中的关系并不是物与物之间的,而是陈述与物之间的。但物与陈述又在何处符合一致呢?从外观上看,这两个相关的东西明显是不同的嘛!硬币是由金属做成的,而陈述根本就不是质料性的。硬币是圆形的,而陈述根本就没有空间特性。人们可以用硬币购买东西,而一个关于硬币的陈述从来就不是货币。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上述陈述作为一个真实的陈述却与硬币相符合。而且,根据流俗的真理概念,这种符合乃是一种适合。完全不同的陈述如何可能与硬币适合呢?或许它必得成为硬币并且以此完全取消自己。这是陈述决不可能做到的。一旦做到这一点,则陈述也就不可能成为与物相一致的陈述了。在适合中,陈述必须保持其所是,甚至首先要成其所是。那么,陈述的全然不同于任何一物的本质何在呢?陈述如何能够通过守住其本质而与一个它者——物——适合呢?
这里,适合的意思不可能是不同物之间的一种物性上的同化。毋宁说,适合的本质取决于在陈述与物之间起着作用的那种关系的特性。只消这种“关系”还是不确定的,在其本质上还是未曾得到论究的,那么,所有关于此种适合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争执,关于此种相称的特性和程度的争执,就都会沦于空洞。但是,关于硬币的陈述把“自身”系于这一物,因为它把这一物表象(vor-stellen)出来,并且来言说这个被表象的东西,说它在其主要方面处于何种情况中。有所表象的陈述就像对一个如其所是的被表象之物那样来说其所说。这个“像……那样”(so-wie)涉及到表象及其所表象的东西。这里,在不考虑所有那些“心理学的”和“意识理论的”先入之见的情况下,表象(Vor-stellen)意味着让物对立而为对象。作为如此这般被摆置者,对立者必须横贯一个敞开的对立领域(offenesEntgegen),而同时自身又必须保持为一物并且自行显示为一个持留的东西。横贯对立领域的物的这一显现实行于一个敞开域(Offenes)中,此敞开域的敞开状态(Offenheit)首先并不是由表象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向只作为一个关联领域而为后者所关涉和接受。表象性陈述与物的关系乃是那种关系(Verhaltnis)的实行,此种关系源始地并且向来作为一种行为(Verhalten)表现出来。但一切行为的特征在于,它持留于敞开域而总是系于一个可敞开者(Offenbares)之为可敞开者。如此这般的可敞开者,而且只有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可敞开者,在早先的西方思想中被经验为“在场者”(dasAnwesende),并且长期以来就被称为“存在者”。
行为向存在者保持开放。所有开放的关联都是行为。依照存在者的种类和行为的方式,人的开放状态各各不同。任何作业和动作,所有行动和筹谋,都处于一个敞开领域之中,在其中,存在者作为所是和如何是的存在者,才能够适得其所并且成为可言说的(sagbar)。而只有当存在者本身向表象性陈述呈现自身,以至于后者服从于指令而如其所是地言说存在者之际,上述情形才会发生。由于陈述遵从这样一个指令,它才指向存在者。如此这般指引着的言说便是正确的(即真实的)。如此这般被言说的东西便是正确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了。
行为的开放状态(Offenstandigkeit)赋予陈述以正确性;因为只有通过行为的开放状态,可敞开者才能成为表象性适合的标准。开放的行为本身必须让自己来充当这种尺度。这意味着:它必须担当起对一切表象之标准的先行确定。这归于行为的开放状态。但如果只有通过行为的这种开放状态,陈述的正确性(真理)才是可能的,那么,首先使正确性得以成为可能的那个东西就必然具有更为源始的权利而被看作真理的本质了。
由此,习惯上独一地把真理当作陈述的唯一本质位置而指派给它的做法,也就失效了。真理源始地并非寓居于命题之中。不过,与此同时也生发出一个问题,即开放的和先行确定标准的行为的内在可能性的根据问题,唯这种可能性才赋予命题之正确性以那种根本上实现了真理之本质的外观。
三、正确性之可能性的根据
表象性陈述从哪里获得指令,去指向对象并且依照正确性与对象符合一致?何以这种符合一致也一并决定着真理的本质?而先行确定一种定向,指示一种符合一致,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只有这样来发生,即:这种先行确定已经自行开放而入于敞开域,已经为一个由敞开域而来运作着的结合当下各种表象的可敞开者自行开放出来了。这种为结合着的定向的自行开放,只有作为向敞开域的可敞开者的自由存在(Freisein)才是可能的。此种自由存在指示着迄今未曾得到把捉的自由之本质。作为正确性之内在可能性,行为的开放状态植根于自由。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DasWesenderWahrheitistdieFreiheit)。
然而,这个关于正确性之本质的命题不是以一种不言自明替换了另一种不言自明么?为了能够完成一个行为,由此也能够完成表象性陈述的行为,乃至与“真理”符合或不符合的行为,行为者当然必须是自由的。不过,前面那个命题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作出陈述,通报和接受陈述,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行为;相反,这个命题倒是说:自由乃是真理之本质本身。在此,“本质”(Wesen)被理解为那种首先并且一般地被当作已知的东西的内在可能性的根据。但在自由这个概念中,我们所思的却并不是真理,更不是真理的本质。所以,“真理(陈述之正确性)的本质是自由”这个命题就必然是令人诧异的。
把真理之本质设定在自由中——这难道不就是把真理委诸于人的随心所欲吗?人们把真理交付给人这个“摇摆不定的芦苇”的任意性——难道还能有比这更为彻底的对真理的葬送吗?在前面的探讨中总是一再硬充健全判断的东西,现在只是更清晰了些:真理在此被压制到人类主体的主体性那里。尽管这个主体也能获得一种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也还与主体性一起,是人性的并且受人的支配。
错误和伪装,谎言和欺骗,幻觉和假象,简言之,形形色色的非真理,人们当然把它们归咎于人。而非真理确实也是真理的反面,因此,非真理作为真理的非本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真理的纯粹本质的问题范围之外了。非真理的这种人性起源,确实只是根据对立去证明那种“超出”人而起支配作用的“自在的”真理之本质。形而上学把这种真理看作不朽的和永恒的,是决不能建立在人之本质的易逝性和脆弱性之上的。那么,真理之本质如何还能在人的自由中找到其持存和根据呢?
对上面这个“真理的本质是自由”的命题的拒斥态度依靠的是一些先入之见,其中最为顽冥不化的是:自由是人的一个特性。自由的本质毋需进一步的置疑,也不容进一步的置疑。人是什么,尽人皆知的嘛!
四、自由的本质
然而,对作为正确性的真理与自由的本质联系的说明却动摇着上面所说的先入之见;当然,前提是我们准备好作一种思想的转变。关于真理与自由的本质联系的思索趋使我们去探讨人之本质的问题,着眼点是保证让我们获得对人(即此在)的被遮蔽的本质根据的经验的那个方面,并且是这样,即这种经验事先把我们置于源始地本质现身着的真理领域之中。但由此而来也显示出:自由之所以是正确性之内在可能性的根据,只是因为它是从独一无二的根本性的真理之源始本质那里获得其本己本质的。自由首先已经被规定为对于敞开域的可敞开者来说的自由了。应当如何来思自由的这一本质呢?一个正确的表象性陈述与之相称的那个可敞开者,乃是始终在开放行为中敞开的存在者。向着敞开域的可敞开者的自由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于是,自由便自行揭示为让存在者存在(dasSeinlassenvonSeiendem)。
通常地,譬如当我们放弃一件已经安排好的事情时,我们就会说到这种让存在(Seinlassen)。“我们听其自然吧”,意思就是:我们不再碰它,不再干预它。在这里,让某物存在含有放任、放弃、冷漠、乃至疏忽等消极意义。
但在此必不可少的“让存在者存在”一词却并没有疏忽和冷漠的意思,而倒是相反。让存在乃是让参与到存在者那里。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对当下照面的或者寻找到的存在者的单纯推动、保管、照料和安排。让存在——即让存在者成其所是——意味着:参与到敞开域及其敞开状态中,每个仿佛与之俱来的存在者就置身于这种敞开状态中。西方思想开端时就把这一敞开域把握为τααληθεα,即无蔽者。如果我们把αληθεια译成“无蔽”,而不是译成“真理”,那么,这种翻译不仅更加“合乎字面”,而且包含着一种指示,即要重新思考通常的正确性意义上的真理概念,并予以追思,深入到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和解蔽过程的那个尚未被把握的东西那里。参与到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中,这并不是丧失于这一状态中,而是自行展开而成为一种在存在者面前的引退,以便使这个存在者以其所是和如何是的方式公开自身,并且使表象性适合从中取得标准。作为这种让存在,它向存在者本身展开自身,并把一切行为置入敞开域中。让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开着的(aus-setzend),是绽出的(ek-sistent)。着眼于真理的本质,自由的本质显示自身为进入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的展开。
自由并不是通常理智喜欢任其借此名义四处流传的东西,即那种偶而出现的在选择中或偏向于此或偏向于彼的任意。自由并不是对行为的可为和不可为不加约束。但自由也并不只是对某个必需之物和必然之物(以及如此这般无论何种存在者)的准备。先于这一切(“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自由乃是参与到存在者本身的解蔽过程中去。被解蔽状态本身被保存于绽出的参与(dasek-sistenteSich-einlassen)之中,由于这种参与,敞开域的敞开状态,即这个“此”(Da),才是其所是。
在此之在(Da-sein)中,人才具有他由之得以绽出地生存的本质根据,而这个本质根据长期以来未曾被探究过。在这里,“生存”(Existenz)并不意味着一个存在者的出现和“定在”(Dasein)(现成存在)意义上的existentia[实存]。但“生存”在此也不是“在生存状态上”意指人在身-心机制的基础上构造出来的为其自身的道德努力。绽出之生存(Ek-sistenz)植根于作为自由的真理,乃是那种进入存在者本身的被解蔽状态之中的展开。历史性的人的绽出之生存还没有得到把握,甚至还需要一种本质建基;历史性的人的绽出之生存唯开端于那样一个时刻,那时侯,最初的思想家追问着,凭着“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而投身到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中。在这个问题中,无蔽状态才首次得到了经验。存在者整体自行揭示为φυσιζ,即“自然”;但“自然”在此还不是意指存在者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是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而且是在涌现着的在场(dasaufgehendeAnwesen)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唯当存在者本身被合乎本己地推入其无蔽状态并且被保存于其中,唯当人们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追问出发把握了这种保存,这时侯,历史才得开始。对存在者整体的原初解蔽,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追问,和西方历史的发端,这三者乃是一回事;它们同时在一个“时代”里出现,这个“时代”本身才无可度量地为一切尺度开启了敞开域。
然而,如果绽出的此之在——作为让存在者存在——解放了人而让人获得其“自由”,因为它才为人提供出选择的可能性(存在者),向人托出必然之物(存在者),那么,人的任性愿望就并不占有自由。人并不把自由“占有”为特性,情形恰恰相反:是自由,即绽出的、解蔽着的此之在占有人,如此源始地占有着人,以至于唯有自由才允诺给人类那种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整体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才首先创建并标志着一切历史。唯有绽出的人才是历史性的人。“自然”是无历史的。
如此这般来理解的作为让存在者存在的自由,是存在者之解蔽意义上的真理之本质的实现和实行。“真理”并不是正确命题的标志,并不是由某个人类“主体”对一个“客体”所说出的、并且在某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在哪个领域中——“有效”的命题的标志;不如说,“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成其本质。一切人类行为和姿态都在它的敞开域中展开。因此,人乃以绽出之生存的方式存在。
由于每一种人类行为各各以其方式保持开放,并且与它所对待的东西相协调,所以,让存在之行为状态,即自由,必然已经赋予它以一种内在指引的禀赋,即指引表象去符合于当下存在者。于是,所谓人绽出地生存(ek-sistieren)就意味着:一个历史性人类的本质可能性的历史对人来说被保存于存在者整体之解蔽中了。历史的罕见而质朴的决断就源出于真理之源始本质的现身方式中。
但另一方面,由于真理在本质上乃是自由,所以历史性的人在让存在者存在中也可能让存在者不成其为它所是和如何是的存在者。这样,存在者便被遮盖和伪装了。假象(Schein)占了上风。于此,真理的非本质(Unwesen)突现出来了。不过,因为绽出的自由作为真理的本质并不是人固有的特性,倒是人只有作为这种自由的所有物才绽出地生存出来,并因而才能有历史,所以,即便真理的非本质也并不是事后来源于人的纯然无能和疏忽。而毋宁说,非真理必然源出于真理的本质。只是因为真理和非真理在本质上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共属一体的,一个真实的命题才能够成为一个相应地非真实的命题的对立面。于是乎,真理之本质的问题才达到了问之所问的源始领域之中,其时,基于对真理的全部本质的先行洞识,这个问题也已经把对于非真理之沉思摄入本质揭示中了。对真理之非本质的探讨并非事后补遗,而是充分地发动对真理之本质的追问的关键一步。但我们应如何来把捉真理之本质中的非本质呢?如果说陈述的正确性并没有囊括真理的本质,那么,非真理也是不能与判断的不正确性相等同的五、真理的本质
真理的本质揭示自身为自由。自由乃是绽出的、解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任何一种开放行为皆游弋于“让存在者存在”之中,并且每每对此一或彼一存在者有所作为。作为参与到存在者整体本身的解蔽中去这样一回事情,自由乃已经使一切行为协调于存在者整体。然而,我们却不能把这种协调状态(即调谐)把捉为“体验”和“情感”,因为这样做,我们只不过是使之丧失了本质,并且从那种东西(“生命”和“灵魂”)出发对之作出解释而已——这种东西确实只能维持自己的本质权利的假象,只要它本身包含着对协调状态的伪装和误解。协调状态,也即一种入于存在者整体的绽出的展开状态(Ausgesetztheit),之所以是能够被“体验”和“感受”的,只是因为“体验的人”一向已经被嵌入一种揭示着存在者整体的协调状态中了,而并没有去猜测调谐之本质为何。历史性的人的每一种行为,无论它是否被强调,无论它是否被理解,都是被调谐了的,并且通过这种调谐而被推入存在者整体之中了。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并不就是我们恰好熟悉的存在者之总和。情形倒是相反:存在者不为人所熟悉的地方,存在者没有或者还只是粗略地被科学所认识的地方,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能够更为本质地运作;而比较而言,在熟知的和随时可知的东西成为大量的,并且由于技术无限度地推进对物的统治地位而使存在者不再能够抵抗人们的卖力的认识活动的地方,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倒是少见运作的。正是在这种无所不知和唯知独尊的平庸无奇中,存在者之敞开状态被敉平为表面的虚无,那种甚至不止于无关紧要而只还被遗忘的东西的虚无。
调谐着的让存在者存在贯通一切于存在者中游弋的开放行为,并且先行于存在者。人的行为乃是完全由存在者整体之可敞开状态来调谐的。但在日常计算和动作的视野里来看,这一“整体”似乎是不可计算、不可把捉的。从当下可敞开的存在者那里——无论这种存在者是自然中的存在者还是历史中的存在者——我们是把捉不到这个“整体”的。尽管不断地调谐一切,但它却依然是未曾确定的东西、不可确定的东西,从而,它大抵也是最流行的东西、最不假思索的东西。不过,这个调谐者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让存在总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者存在,对存在者有所动作,并因之解蔽着存在者;正是因为这样,让存在才遮蔽着存在者整体。让存在自身本也是一种遮蔽。在此之在的绽出的自由中,发生着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存在着(ist)遮蔽状态。
六、作为遮蔽的非真理
遮蔽状态拒绝给αληθεια[无蔽]以解蔽,并且还不允许无蔽成为δτερησιζ(剥夺),而是为无蔽保持着它的固有的最本己的东西。于是,从作为解蔽状态的真理方面来看,遮蔽状态就是非解蔽状态(Un-entborgenheit),从而就是对真理之本质来说最本己的和根本性的非真理(Un-wahrheit)。存在者整体的遮蔽状态决不是事后才出现的,并不是由于我们对存在者始终只有零碎的知识的缘故。存在者整体之遮蔽状态,即根本性的非真理,比此一存在者或彼一存在者的任何一种可敞开状态更为古老。它也比“让存在”本身更为古老,这种“让存在”在解蔽之际已然保持遮蔽了,并且向遮蔽过程有所动作了。是什么把让存在保存于这种与遮蔽过程的关联中的呢?无非是对被遮蔽者整体的遮蔽,对存在者本身的遮蔽而已——也就是神秘(dasGeheimnis)罢。并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东西的个别的神秘,而只是这一个,即归根到底统摄着人的此之在的这种神秘本身(被遮蔽者之遮蔽)。
“让存在”——即让存在者整体存在——是解蔽着又遮蔽着的,其中发生着这样一回事情:遮蔽显现为首先被遮蔽者。绽出的此之在保存着最初的和最广大的非解蔽状态,即根本性的非真理。真理的根本性的非本质乃是神秘。这里,非本质还并不意味着是低于在一般之物(κοινον[共性]、γενοζ[种])及其可能性和根据这种意义上的本质的。这里所说的非本质乃是先行成其本质的本质。但“非本质”首先大抵是指那种已经脱落了的本质的畸变。不过,在上述任何一种意义上,非本质一向以其方式保持为本质性的,从来不会成为毫不相干意义上的非本质性的东西。而如此这般来谈论非本质和非真理,已经远远违背了常识之见,看起来好像是在搬弄煞费苦心地构想出来的“佯谬”(Paradoxa)。这种印象是难以消除的,所以,我们似乎应当放弃这种矛盾的谈论;不过,它只是对于通常的意见(Doxa)来说是矛盾的。而对有识之士来说,真理的原初的非本质(即非真理)中的“非”(Un-),却指示着那尚未被经验的存在之真理(而不只是存在者之真理)的领域。
作为“让存在者存在”,自由在自身中就是断然下了决心的姿态,即没有自行锁闭起来的姿态。一切行为都植根于此种姿态中,并且从中获得指引而去向存在者及其解蔽。但这一对于遮蔽的姿态却同时自行遮蔽,因为它一任神秘之被遗忘状态占了上风,并且消隐于这种被遗忘状态中了。尽管人不断地在其行为中对存在者有所作为,但他也往往总是对待了此一或彼一存在者及其当下可敞开状态而已。就是在最极端的情形中,他也还是固执于方便可达的和可控制的东西。而且,当他着手拓宽、改变、重新获得和确保在其所作所为的各各不同领域中的存在者之可敞开状态时,他也还是从方便可达的意图和需要范围内取得其行为的指令的。
然而,滞留于方便可达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不让那种对被遮蔽者的遮蔽运作起来。诚然,在通行的东西中也有令人困惑的、未曾解释的、未曾确定的、大可置疑的东西。但这些自身确实的问题只不过是通行之物的通行的过渡和中转站,因而不是本质性的。当存在者整体的遮蔽状态仅仅被附带地看作一个偶尔呈报出来的界限时,作为基本事件的遮蔽便沦于被遗忘状态中了。
不过,此在的被遗忘了的神秘并没有为被遗忘状态所消除;而毋宁说,这种被遗忘状态倒是赋予被遗忘者的表面上的消隐以一种本己的现身当前。神秘在被遗忘状态中并且为这种被遗忘状态而自行拒绝,由此,它便让在其通行之物中的历史性的人寓于他所作成的东西。这样一来,人类就得以根据总是最新的需要和意图来充实他的“世界”,以他的打算和计划来充满他的“世界”。于是,在遗忘存在者整体之际,人便从上述他的打算和计划中取得其尺度。他固守着这种尺度,并且不断地为自己配备以新的尺度,却还没有考虑尺度之采纳(Maβ-nahme)的根据和尺度之给出(Maβgabe)的本质。尽管向一些全新的尺度和目标前进了,但在其尺度的本质之真正性(Wesens-Echtheit)这回事情上,人却茫然出了差错。他愈是独一地把自己当作主体,当作一切存在者的尺度,他就愈加弄错了。人类猖獗的忘性固执于用那种对他而言总是方便可得的通行之物来确保他自己。这种固执在那种姿态中有它所不得而知的依靠;作为这种姿态,此在不仅绽出地生存(ek-sistiert),而且也固执地持存(in-sistiert),即顽固地守住那仿佛从自身而来自在地敞开的存在者所提供出来的东西。
绽出的此在是固执的。即便在固执的生存中,也有神秘在运作;只不过,此时神秘是作为被遗忘的、从而成为“非本质性的”真理的本质来运作的。
七、作为迷误的非真理
人固执地孜孜于一向最切近可达的存在者。但另一方面,只有作为已经绽出的人,人才能固执,因为他确实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当作标准了。而在他采纳标准时,人类却背离了神秘。固执地朝向(insistenteZuwendung)方便可达之物,与绽出地背离(ek-sistenteWegwendung)神秘,这两者是共属一体的。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而这种朝向和背离却又与此在中的来回往复的固有转向亦步亦趋。人离开神秘而奔向方便可达的东西,匆匆地离开一个通行之物,赶向最切近的通行之物而与神秘失之交臂——这一番折腾就是误入歧途(dasIrren)。
人彷徨歧途。人并不是才刚刚误入歧途。人总是在迷误中彷徨歧途,因为他在绽出之际也固执,从而已经在迷误中了。人误入其中的迷误决不是仿佛只在人身边伸展的东西,犹如一条人偶尔失足于其中的小沟;毋宁说,迷误属于历史性的人被纳入其中的此之在的内在机制。迷误乃是那种转向的运作领域,在这种转向中,固执的绽出之生存(diein-sistenteEk-sistenz)总是随机应变地重新遗忘自己,重新出了差错。对被遮蔽的存在者整体的遮蔽支配着当下存在者的解蔽过程,此种解蔽过程作为遮蔽之遗忘状态而成为迷误。
迷误是原初的真理之本质的本质性的反本质(Gegenwesen)。迷误公开自身为本质性真理的每一个对立面的敞开域。迷误(Irre)乃是错误(Irrtum)的敞开之所和根据。所谓错误,并非一个个别的差错,而是那种其中错综交织了所有迷误方式的历史的领地(即统治地位)。
按其开放状态以及它与存在者整体的关联,每一种行为都各各是迷误的方式。错误的范围很广,从日常的做错、看错、算错,到本质性态度和决断中的迷失和迷路,都是错误。但通常地,甚至依照哲学的学说,人们所认为的错误,乃是判断的不正确性和知识的虚假性,它只不过是迷误的一种,而且是最为肤浅的一种迷误而已。一个历史性的人类必然误入迷误之中,从而其行程是有迷误的;这种迷误本质上是与此在的敞开状态相适合的。迷误通过使人迷失道路而彻底支配着人。但使人迷失道路的迷误同时也一道提供出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人能够从绽出之生存中获得的可能性,那就是:人通过经验迷误本身,并且在此之在的神秘那里不出差错,人就可能不让自己误入歧途。
由于人的固执的绽出之生存行于迷误之中,由于引人误入歧途的迷误总是以某种方式咄咄逼人并且由于这种逼迫控制了神秘——而且是一种被遗忘的神秘,所以,人在其此在的绽出之生存中就尤其屈服于神秘的支配和迷误的逼迫了。他便处在受统一者和它者的强制的困境中了。完整的、包含着其最本己的非本质的真理之本质,凭这种不断的来回往复的转向,就把此在保持在困境之中了。此在就是入于困境的转向。从人的此之在而来,并且唯从人的此之在而来,才出现了对必然性的解蔽,相应地也就出现了那种入于不可回避之物中的可能的移置(Versetzung)。
对存在者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解蔽同时也就是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在这种解蔽与遮蔽的同时中,就有迷误在运作。对被遮蔽者之遮蔽与迷误一道归属于真理的原初本质。从此在的固执的绽出之生存来理解,自由乃是(在表象之正确性意义上的)真理的本质,而这仅仅是因为自由本身源起于真理的源始本质,源起于在迷误中的神秘之运作。“让存在者存在”实行于保持开放的行为。但让作为如此这般的整体的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却只有当它在其原初的本质中偶而被接纳时才会合乎本质地发生。于是,朝向神秘的有决心的展开(Ent-schlossenheitzumGeheimnis)便在进入迷误本身之途中了。于是,真理之本质的问题便得到了更为源始的追问。于是,真理之本质与本质之真理的交织关系的根据便显露出来了。观入那从迷误而来的神秘,这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追问,即追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什么。这种追问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该问题根本上是令人误入歧途的,因而在其多义性方面是尚未得到掌握的。源起于这样一种追问的存在之思,自柏拉图以来就被理解为“哲学”,后又被冠以“形而上学”之名。
八、真理问题与哲学
把人向着绽出之生存解放出来,这对于历史具有奠基作用。这种解放在存在之思中达乎词语;不过,词语并不只是意见的“表达”,不如说,它一向已经是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得到完好保存的构造。至于有多少人能听到这词语,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正是那些能听者决定了人在历史中的位置。但在哲学发端的同一个世界瞬间里,也就开始了普通理智的鲜明突出的统治地位(智者学派)。
普通理智要求可敞开的存在者的无可置疑性,并且把任何一种运思的追问说成是对健全的人类理智的攻击,是健全的人类理智的不幸迷惑。
然而,健全的、在它自身的区域内十分正当的理智对于哲学的评判却并没有切中哲学的本质,后者唯有根据与作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者的源始真理的关联才能得到规定。但由于真理的完全本质包含着非本质,并且是首先作为遮蔽而运作的,所以,探究这种真理的哲学本身就是分裂性的。哲学之思想乃是柔和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derMilde),它并不拒绝存在者整体的遮蔽状态。哲学之思想尤其是严格性的展开状态(EntschlossenheitderStrenge),它并不冲破遮蔽,而是把它的完好无损的本质逼入把握活动的敞开域中,从而把它逼入其本己的真理之中。
在其“让存在”——让存在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整体而存在——的柔和的严格性和严格的柔和性中,哲学遂成为一种追问;这种追问并不唯一地持守于存在者,但也不允许任何外部强加的命令。这种最内在的思想困境已经为康德所猜度;因为康德在谈到哲学时说:“这里,我们看到哲学实际上被置于一个糟糕的立足点上了,它应该是牢固的,虽然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都没有它赖以立足的地方。在此,哲学应当证明它的纯正性,作为它的法则的自我维持者,而不是作为那个向哲学诉说某种移植过来的意义或者谁也不知道的监护本性的人的代言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康德文集》,学院版,第四卷,第425页)。
康德的著作引发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一次转向。在他上述对哲学之本质的解说中,康德洞察到一个领域,按照他的形而上学立场,他是在主体性中,而且唯有从这个主体性而来,才能把握这个领域,并且必定要把它理解为它自身的法则的自我维护者。尽管如此,这一对哲学之规定性的本质洞见已经足以推翻任何对哲学之思想的贬损,其中最无助的一种贬损是声称:作为一种“文化”的“表达”(斯宾格勒)和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类的装饰品,哲学也还是有其价值的。
然而,哲学是否实现了它原初的决定性的本质而成为“其法则的自我维护者”,或者,哲学是否由其法则一向所属的那个东西的真理来维护本身并获得支撑,这取决于那种开端性,在这种开端性中,真理的源始本质对运思之追问来说成为本质性的。
我们眼下所阐述的尝试使真理之本质的问题超越了流俗的本质概念中习惯界定的范囿,并且有助于我们去思索,真理之本质(dasWesenderWahrheit)的问题是否同时而且首先必定是本质之真理(dieWahrheitdesWesens)的问题。但在“本质”这个概念中,哲学思考的是存在。我们把陈述之正确性的内在可能性追溯到作为其“根据”的“让存在”的绽出的自由,同时我们先行指出这个根据的本质开端就在于遮蔽和迷误之中。这一番工作意在表明,真理之本质并非某种“抽象”普遍性的空洞的“一般之物”,而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历史所具有的自行遮蔽着的唯一东西;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乃是我们所谓的存在的“意义”的解蔽的历史——而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仅仅把所谓存在当作存在者整体来思考。
九、注解
真理之本质的问题起于本质之真理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中,我们首先是在“所是”(quidditas)或实在(realitas)的意义上来理解本质的,又把真理理解为知识的一个特性。而在本质之真理的问题中,“本质”一词作动词解;在这个还停留在形而上学之表象范围内的词语中,我们思的是存有(Seyn)——作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运作着的差异的那个存有。真理意味着作为存有之基本特征的有所澄明的庇护(lichtendesBergen)。真理之本质问题的答案在于下面这个命题:真理的本质是本质的真理。依照我们的解释,人们不难看出,这个命题不只是颠倒了一下词序而已,并不是要唤起某种背谬的假象。本质之真理是这个命题的主语——倘若我们毕竟还可以使用一下主语这个糟糕的语法范畴的话。有所澄明的庇护乃是知识与存在者的符合,其中的这个“是”(ist)也就是“让……成其本质”(laβtwesen)。这个命题并不是辨证的。它根本就不是陈述意义上的命题。对真理之本质问题的回答是对存有之历史范围内的一个转向的道说(dieSageeinerKehre)。因为存有包含着有所澄明的庇护,所以存有原初地显现于遮蔽着的隐匿之光亮中。这种澄明的名称就是希腊的αληθεια[无蔽]。
逻辑真理范文篇6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真/涵义/使用
中图分类号:B516.5293文献标识码:A
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给出了一种关于真的符合论。这种符合论与逻辑图像论联系在一起,例如2.222节这样说,“图像的真或假在于它的涵义与实在是否一致”①。但这就立即面临弗雷格在《思想》这篇著名文章中对于符合论的批评,按照这个批评,不仅符合论是不可能的,而且真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可定义的。这就自然产生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关于真的符合论,是否因为这个批评就垮掉了呢?本文就以这个问题为起点,整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给出的真理概念。
弗雷格的批评大意是这样的:如果用与事实符合来定义某个命题是真的,那么要使用这个定义来判定命题p是否真,就要先考虑p是否符合事实,也就是说,先考虑“p符合事实”是否为真,而这就预设了真,从而使对这个定义进入了无穷后退;同样的思路适用于所有关于真的定义,因此真是不可定义的。②
沃克尔③认为这个批评适合于融贯论,但不适合于符合论。他区分了关于真的理论和关于事实的理论。如果符合论是一种关于真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事实的理论,那么它就可以避开弗雷格的批评。为看到这一点,考虑“p符合事实”这个命题,要使其为真,所要求就是“p符合事实”这个命题符合事实。如果视事实这个概念为初始概念,那么由p符合事实,就可以得到“p符合事实”这个命题符合事实,这一点就相当于说由p得到p为真,由p为真得到“p为真”为真,这个过程可以无穷继续下去,但不是恶性循环。
但是,沃克尔的策略不适合于维特根斯坦。这个策略仅仅考虑了真,而没有涉及语义。维特根斯坦似乎持一种真值条件语义学,他说:“要理解一个命题,就是要知道如果它是真的话,情况是怎样的”(4.024节)。如果可以通过真值条件来确定语义,那么即使事先不知道命题的语义,只要知道与之对应的真值条件,我们也可以确定命题的语义。沃克尔策略的核心在于,承认有一个独立于真的事实概念。但是,如果事实独立于真,那么与一个命题相符合的是什么事实,就并不取决于这里的命题是什么。联系到真值条件语义学,这就相当于说这里有真值条件,但不知道是哪个命题的真值条件,从而也就不知道要为哪个命题确定语义。真值条件语义学意味着事实能够成为命题的个体化条件,但对于独立给定的事实来说,符合关系并不足以挑出任何命题,从而不能得到个体化的命题。
沃克尔策略必须承认,事实概念是一种外延化的概念。按照这种事实概念,金星升起来了,即使这个事实与启明星升起来了这个事实是用不同命题表述的,它们仍然是同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同一性不依赖于表述它的命题。显然,这样的事实不足以确定它是“金星升起来了”这个命题还是“启明星升起来了”这个命题的真值条件,而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真值条件语义学要求给出足以区分这两个命题的事实,而这意味着作为真值条件的是内涵性的事实概念,按这种事实概念,金星升起来了与启明星升起来了,是两个不同的事实。
弗雷格批评的关键在于,如果真是以命题为主目的谓词,那么关于它的任何定义都必定采取了如下形式:
D)对任一命题p,T(p),当且仅当,F(p)。
其中“T”表示谓词真,T(p)即命题p为真,而“F”则表示用来定义真的任何性质。这种定义形式本身就预设了真这个概念,因为双条件句所使用的连接词(“当且仅当”)意味着两边的子句真值相同。为了避免这个批评,可以采取的对策有两个。其一,把“当且仅当”这个连接词看作是一个过渡,它仅仅表示两边同时为真这一事实,关键是得到定义项,即双条件句的右边为真的情况。此时只需表明可以不用真这个谓词来实现这种情况就行了。沃克尔的策略就是如此。其二,则是表明这里的双条件句不是用来定义真的命题,真这个概念已经先于这个定义而被把握了,类似于D)的命题仅仅是对我们已经把握到的真这个概念的一种阐明,这个命题本身并不表明我们理解真这个概念的基础。如果情况是这样,要断定命题p真所需要的“F(p)”为真,就不是恶性的无穷后退。我将表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引入的真,就以第二种方式避免了弗雷格的批评。当然,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维特根斯坦就没有一种真正的符合论,也不会遇到弗雷格的批评。
《逻辑哲学论》集中讨论真的段落是在4.06节至4.0641节。4.06节说,“只有作为实在的图像,命题才能是真的或假的”。这是在说真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考虑到真这个概念在什么情况下有效,这种情况中就包含着对于这个概念来说具有本质性的东西,这一节的说明就是极为重要的。按照文本的编号排序原则④,4.06节覆盖了整个关于真的讨论,这就很说明问题。显然,一个命题如果不作为实在的图像,我们就说这里有记号串而没有命题。当记号串被用来表征实在时,它就是命题,由此直接就可以看出,只有在记号串的表征性使用中,我们才会触及真这个概念。这一点在哲学上的后果一时还不明显,需要继续分析。
4.061节通过讨论命题的涵义(Sinn/sense)来讨论真:
如果没有看到命题具有一个独立于事实的涵义,就会很容易以为真和假是记号和记号表示的事物间具有同等权利的关系。
人们就会说,例如“p”以真的方式表示“┐p”以假的方式表示的东西,等等。
命题涵义与事实间的关系是通过真建立起来的。按照4.024节的提示,如果知道命题为真时事实是怎样的,也就知道了命题的涵义。由这个提示很容易这样推论,命题的涵义是什么,这一点依赖于命题为真时,事实是怎样的。进一步的推论是,命题的涵义是什么,同时也依赖于当命题为假时,事实不是怎样的,因此,只需要把不是这样的事实反过来理解,就得到了事实是怎样的。这一点就体现为,“p”以真的方式表示“┐p”以假的方式表示的东西。但是,上述引文表明的恰恰是,这个推论是不可接受的。
接下来的4.062节对何以如此做出了解释:
我们能否就像理解真命题那样理解假命题,只要知道它是假的就行了?不行!因为如果我们用命题来断定的是确实如此的情况,那么它就是真的;如果我们用“p”来说┐p,而情况确实是我们所说的,那么在新概念中“p”是真的而不是假的。
这一节的意思并不如文字表明得那么平易。在把握维特根斯坦的想法前,对照一下研究者的理解是有益的。戴尔蒙德⑤按照吉奇⑥的提示假想了一种与英语有完全相同的词汇及语法的语言“Unglish”,它与英语的唯一区别在于,Unglish的一个句子与英语中的同形句子涵义正好相反,例如其中的句子“Roverisspotted.”与英语中的“Roverisnotspotted.”具有同样的涵义。有趣的地方在于,这种假想的语言与英语都可以按4.062节的说明,与关于真的符合论表述相容,但就每个句子而言,它与英语句子的真值恰好相反。造成这个区别的,是句子与真值条件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种对应关系来改变句子的涵义,而这一点是使用句子的行为所决定的。因此戴尔蒙德说:“……命题的表达能力本质上涉及方向性,通过某种使用,某种按规则的约束与实在相对照的方式,这种方向性本身属于命题,并且是可以颠倒的”。⑦引文中提到的前一个“方向性(directionality)”显然是指具有方向这一事实,后一个“方向性”则是指具有某一特定方向。
在戴尔蒙德看来,这说明了命题与名称间有范畴区别,前者具有方向性,而后者没有,前者的颠倒构成了另一个命题,后者如果能颠倒的话,颠倒以后仍然是同一个名称(Unglish与英语有完全一样的名称)。这种范畴区别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就表述为,命题是事实,而名称则不是,进而,名称可以代表关系项,而命题不能。在这种意义上,说真表明了命题与实在间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消解的表述。戴尔蒙德进而把这种自我消解的特征当成整个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基本特征。
对戴尔蒙德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整体解读方案这里不予置评,我同意她关于命题涵义具有方向性的理解,但关于这种方向性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证思路中起什么作用,她的理解在我看来是错的。
戴尔蒙德正确地看到,关于真的概念允许对涵义进行颠倒,这种可颠倒性使得记号“p”与“┐p”能够说同样的东西。确实,4.0621节直接表述了这一点。戴尔蒙德的思路接着这一点继续下去。在她看来,这就使得吉奇所假想的Unglish成为可能。它与英语的区别是,句子与实在间的对照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使用插了进来,说的是英语还是Unglish,这一点取决于使用。使用的作用仅仅在于,在命题涵义的两个方向中任意选择一个。不过,无论选择哪个方向,命题涵义都是可以颠倒的。这种方向性本质上就属于命题涵义,命题的真假二值性表明了这种可颠倒的涵义具有方向。关于方向性和可颠倒性的这种理解被戴尔蒙德认为是关于真的早期(inchoate)理解的一种发展形式,它试图从分析真入手来表明命题在何种程度上有所说(informative)。
回到《逻辑哲学论》的文本,就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与戴尔蒙德的理解间存在错位。4.061节确实提到了类似于Unglish的语言。在Unglish中的句子“Roverisnotspotted.”是句子“Roverisspotted.”的否定,在说英语的人看来,这正是用“┐p”以假的方式说“p”以真的方式说的东西。但是,这种可能性正是4.061节所要否定的。戴尔蒙德提到的方向性出现于4.0621,这里维特根斯坦似乎赞同涵义具有方向性。但她没有注意到这一节是4.062节的一个转折性的继续。4.062节对涵义的可颠倒性给与了否定的回答。
细读之下就会看到,4.0621节对于4.062节来说是一种发展:在命题记号与真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谈论涵义的这种颠倒。而在4.061节中这种颠倒不被允许,这应当是由于,涵义是通过命题记号与真的联系确定的,在这样确定涵义时,涵义的颠倒意味着涵义是不确定的。4.061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否定Unglsh的可能性,在涵义没有确定之前,存在Unglish这种可能性意味着我们甚至不会有英语;戴尔蒙德之所以能够设想这种语言,这仅仅是由于我们已经有确定的英语,我们把Unglish当成另一种语言,以此来保证这种确定性。
之所以说戴尔蒙德的理解错位,是因为在她看来维特根斯坦试图揭示的语言的内在逻辑只进入了涵义的层次,关于真的二值性理解表明了涵义的方向性,但维特根斯坦实际进入的层次则是涵义如何建立起来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使用真这个概念的方式通过涵义的方向性表现出来。
找到了切入点,就可以入手分析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处理真这个概念的。
4.061节包含一个论证,它的目的是表明,我们必须认为命题的涵义独立于事实,否则就得不到确定的涵义。如果认为涵义依赖于事实,那么对于命题p,我们可以说与之对应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赋予命题以涵义。这就是说,在事先不知道命题涵义的情况下,只要确定了与之对应的事实,就能够确定命题的涵义。但是,在不知道命题所说的是什么的情况下,同样是这个事实,既可能使命题为真也可能使其为假,因此我们必须认为,无论事实使命题为真还是为假,都将赋予命题以涵义。这就是说,真和假是记号和记号表示的事物间具有同等权利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真与假的平权性的理解,4.061节第二段说,“人们就会说,例如‘p’以真的方式表示‘┐p’以假的方式表示的东西,等等”。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平权理解的辩护。既然同一个事实可以使一个它将要赋予其涵义的命题为真,也可以使其为假,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情况分别以“p”和“┐p”的形式标出来,分别确定涵义以后把任意一个赋予原来的那个命题就行了。维特根斯坦在紧接下来的4.062节直接否定了这一点,而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理由。这里可以给出理由:如果不预设命题涵义已经以某种方式确定了,我们无法确定“p”和“┐p”标出的情况是什么。这就好像我们说,左和右这两个方向是相对的,因此我们可以随意规定左右。但是能够说左和右相对,这就已经预设了左作为左和右作为右是确定的,这两个确定的方向本身不是通过两者的相对关系规定出来的。
这样,在接下来的4.062节否定以知其假的方式,理解假命题的可能性就顺理成章了。这里的关键不是对假命题的理解和对真命题的理解互为前提,而是缺乏真假之别。前一种情况不是循环,而是真命题与假命题是一同被理解的。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真命题与假命题中理解任何一个就理解了另外一个,因而以知其假的方式理解假命题就没有问题,为此只需理解了真命题就行了。这里的问题显然是,就我们能够通过知道命题的真值条件来理解命题而言,命题本身应当已经以某种方式提供了真假之别,进而使涵义得以确定。
建立真假之别的方式,就是戴尔蒙德认为需要在涵义的两个相反的方向中任意选择一个的方式,也就是说,使用。4.062节接着说:“如果我们用命题来断定的是确实如此的情况,那么它就是真的;如果我们用‘p’来说┐p,而情况确实是我们所说的,那么在新概念中‘p’是真的而不是假的。”这里把“┐p”换成任何其他东西并不构成影响,也就是说,命题记号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不起作用的。这是在确定涵义之前确定什么是真。这里的要点是,用“p”来说时情况确实是我们所说的则“p”为真,这并不要求事先确定一个事实(否则我们需要先确定涵义),然后来判定“p”是否确实为真,而是一个关于“p”这个命题记号与真这个概念的用法的说明。这里,是使用的活动本身建立了真的概念,而不是通过使用在已经给定的涵义的可颠倒的方向中选择一个。因此,是命题的二值性决定了涵义的方向性,而不是涵义原来已经有某种方向性,真这个概念的使用确定了某个方向。免费论文网
二值性属于使用,并通过使用被赋予命题。这一点体现在4.0621节所说的否定记号不代表任何东西中。如果涵义已经有方向性,只不过在使用真这个概念前没有得到明确,那么不管怎样,使用否定记号就意味着我们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如果不明确涵义具有方向这一事实本身依赖于使用,那么按照理解涵义就知道其所说的事实这一基本原则就可以认为,涵义在方向上的区别对应于一种事实上的区别,因而否定记号最终就有所代表了。戴尔蒙德把方向性归于命题或者说命题的涵义,仍然无法解释何以否定并不代表什么。
真与涵义间的这种关系在4.063节得到进一步肯定,在这一节维特根斯坦批评了弗雷格的判断理论。我们且不管他是否错误地理解或表述了弗雷格的理论,而只关心维特根斯坦在这种批评中透露的正面的观点。在他看来,弗雷格把真和假看做是思想(弗雷格意义上的涵义)的谓词,在确定真值之前,命题涵义已经确定了,判断(judgment)就是断定这个涵义是真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认定,我们可以有一个与真理理论分开的意义理论,因而给出涵义就相当于在平面上标出一个点,确定其真值就相当于在这个点上涂黑色或白色,我们可以在不知道什么是黑与白的情况下标出一个点。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要能够说‘p’是真的(或假的),我必须断定在何种情况下称‘p’为真,从而确定命题的涵义”(4.063节),而这就相当于说,如果不知道何时称“p”为真,就不知道“p”是什么命题。这样一来,要能够把真归于命题,真就必须已经以某种方式被归于命题了。这时真通过确定命题真值条件,而不是作为真值起作用,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真这一概念。在真这一概念下看待命题,命题才能具有真值。命题的真值条件依赖于真这个概念,并赋予命题以涵义,进而使命题得到个体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在4.063节中说:“命题的动词并不是像弗雷格所想的那样‘是真的’或‘是假的’,而是,‘是真的’东西已经包含了动词”。包含了动词表达式的是命题而不是名称。
至此,维特根斯坦在涵义与真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顺序:真先于涵义。这个顺序正是4.0621节断定否定不代表实在中的任何东西的前提。如上所述,如果真后于涵义,那么否定就构成了涵义上的区别,进而对应于实在中的区别。
但是,先于涵义的真不是赋予命题的特定真值,要赋予真值,就必须已经确定了涵义;先于涵义的真包含于这样一个事实中:我们使用命题来描述实在,就是把命题当成图像,来从中看到实在。真这个概念就包含在使用命题的方式中,如果命题是真的,那么实在就被命题所描述,从而达到了使用的目的。维特根斯坦关于真的理解在图像论的框架中进行,这就是4.06节所提示的:“只有作为实在的图像,命题才能是真的或假的”。
按照这个框架,当我们通过一个事实确定命题涵义后,能够脱离这个事实设想命题取其他真值的情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命题具有独立于事实的涵义。事实上,客体的独立性就是以类似的方式建立的。事态被分解为客体,因而客体具有构成事态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客体在本质上就要与其他客体结合构成事态,就它们能在一切可能的结合中出现而言,仍然是独立的。同样,按照我在别处给出的解读《逻辑哲学论》的分解—合并法这一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我们把某个命题描述了实在这一事实分解,就能够得到某个命题,并且该命题能够描述实在(具有构成该事实的可能性,就像客体具有构成事态的可能性一样),这一点我们表述为,该命题具有它自己的涵义。这个命题可以在其他的描述活动中使用,就这一点而言,其涵义或者说用于描述的可能性,是独立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命题具有独立于事实的涵义。
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命题具有二值性。使用一个命题,要么成功地描述了世界,要么没有,这一点对使用命题的人来说就是,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这种二值性并没有被归于涵义,因而没有被理解为实在中的区别;相反,它被归于使用命题的行为。因此,否定就属于使用,而不属于使用命题所描述的东西。“p”和“┐p”之间的区别在于,如果其中一个描述了实在,另一个就未能描述。对于使用者来说,否定就意味着命题具有两个可能性,即正确地或错误地描述的可能性,进而表现为涵义上的方向性。
不过仍然会有一个问题:以这种分解命题被使用这一事实的方式不能确定命题的涵义是什么,因为这就要求事先确定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是什么,而既然事实是内涵性的,那么要确定事实,就等于说要先确定命题的涵义,以便挑出被描述的事实,这样就进入了一个循环。这个问题只对使用行为的旁观者来说才存在,对他来说,命题涵义与事实是分别给与的;对于使用命题的人来说没有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命题涵义与事实一同确定下来。这正是命题作为图像的题中之义。一个东西是图像,仅当从它就能看到它所描绘的东西,无论它是以何种方式描绘的。一个图像描绘了事实,如果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那么图像实际描绘的东西,即图像的涵义,和被图像描绘的事实,这两者是一同给出的。图像使用者处于这样一个角度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从图像中看到其所描述的东西;相反,旁观的角度则能把图像看做是其他东西,例如一块布,或者一串墨迹。对于命题的使用者来说,正如命题显示其涵义,它所显示的就是,如果它是真的话,事实是怎样的(4.022节)——他不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不知道命题涵义的情况下,你用这个命题描述的是什么。
最后,我们来看按这种方式理解的真这一概念如何应对弗雷格的批评。
真这个概念就内在于使用命题来描述实在的行为中,如果一个命题描述了实在,它就是真的。真内在于使用,这等于说,只有在使用者角度上我们才能说,描述了实在的命题是真命题,从而才会有符合论表述。如果撇开这个角度,符合论与真值条件语义学是不相容的。只要承认能够通过真值条件来确定命题的涵义,那么在这样做的时候就相当于说要先确定使命题为真的事实是什么,而这又反过来要求命题涵义已经确定,从而进入循环。但我们不能舍弃真值条件语义学。即使我们不准备把它作为一种探究语义的系统方法,用命题来描述实在这一使用命题的目的,也要求能够按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方式处理命题的涵义,因为,既然使用命题的目的是要正确地刻画事实,而我们依据命题的涵义做到这一点,那么命题具有何种涵义,必须依赖于它能够刻画什么事实。
真内在于使用,此时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理解真这个概念,而不是真本身是什么。这本身就在排斥任何对真的定义。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符合论表述,不过是对作为命题使用者的我们是如何使用真这个概念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表明了,作为使用者,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从而按相应方式约束我们使用命题的行为。
注释:
①参见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5),本注及以下凡引自《逻辑哲学论》处,均只注明文内编号。译文参照德文略有改动。
②G.Frege,CollectedPapersonMathematics,Logic,andPhilosophy,BrianMcGuinnessed.,Blackwell.1984,p.353.
③R.C.S.Walker,"TheoriesofTruth"(inACompaniontothePhilosophyofLanguage,BobHale&C.Wrighted.,Blackwell,1997,pp.309-330),pp.318-319.
④L.Wittgenstein,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Trans.C.K.Ogden,withanintro.byBertrandRussell,Routledge&KeganPaulLtd,1955,p.31注。
⑤CoraDiamond,"TruthbeforeTarski:AfterSluga,afterRicketts,afterGeach,afterGoldfarb,Hylton,Floyd,andVanHeijenoort",FromFregetoWittgenstein:PerspectivesonEarlyAnalyticPhilosophy,editedbyErichH.Reck,Oxford,2002,pp.252-282,p.263.
逻辑真理范文篇7
关于人的精神,既然它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没有长宽厚的广延性、没有一点物体性的东西,那么我的这个观念当然比任何物体性的东西的观念都要无比地清楚。而且当我考虑到我怀疑,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依存于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在我心里就十分清楚明白地出现一个完全的、不依存于别人的存在体的观念,也就是上帝的观念;单就这个观念之存在于我心里,或者具有这个观念的我是存在的,我就得出上帝是存在的而我的存在在我的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完全依存于他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如此地明显,以致我不认为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明确、更可靠地为人的精神所认识的了。因此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我们就能从深思真实的上帝(在上帝里边包含着科学和智慧的全部宝藏)走到认识宇宙间的其他事物。
因为,首先,我看出他绝对不能骗我,因为凡是欺骗都含有某种不完满性;而且即使能够骗人好像标志着什么机智和能力,不过,想要骗人却无疑地证明是一种缺陷或恶意。因此在上帝里边不可能有欺骗。
其次,我体验到在我自己的心里有某一种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和我所具有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无疑是我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而且,因为他不想骗我,所以他肯定没有给我那样的一种判断能力,让我在正当使用它的时候总是弄错①。因此我认为假如不是从这里得出我永远不会弄错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么对这个真理②就再没有可怀疑的了;因为,如果凡是我所有的都是来自上帝的,如果他没有给我弄错的能力③,那么就应该说,我决不应该弄错。真地,当我单单想到上帝时④,我在心里并没发现什么错或假的原因;可是,后来⑤,当我回到我自己身上来的时候,经验告诉我,我还是会犯无数错误的,而在仔细⑥追寻这些错误的原因时,我注意到在我的思维中不仅出现一个实在的、肯定的上帝观念,或者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的观念,同时,姑且这样说,也出现一个否定的、“无”的观念,也就是说,与各种类型的完满性完全相反的观念;而我好像就是介乎上帝与无之间的,也就是说,我被放在至上存在体和非有在体之间,这使得我,就我是由一个至上存在体产生的而言,在我心里实在说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导我到错误上去;但是,如果我把我看成是以某种方式分享了无或非存在体,也就是说,由于我自己并不是至上存在体⑦,我处于一种无限缺陷的状态中,因此我不必奇怪我是会弄错的。
--------
①法文第二版:“其次,我从我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在我心里有某一种判断的功能,或分辨真、假的功能,这种功能我无疑地是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和在我心里的以及凡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一样;而且因为他不可能想要骗我,那么肯定他没有把那样的功能给我,让我在正当使用它的时候总是弄错。”——译者
②“这个真理”,法文第二版是:“关于这一点”。
③“能力”,法文第二版是“任何功能”。
④法文第二版:“当我把我单单看做是来自上帝,当我完全转向他”。
⑤“后来”,法文第二版是“紧接着”。
⑥“仔细”,法文第二版缺。
⑦法文第二版里下面还有一句:“并且我缺少很多东西”。
这样一来,我认识到,错误,就其作为错误而言,并不取决于上帝的什么实在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种缺陷,从而对于犯错误来说,我不需要有上帝专门为这个目的而给我什么能力①,而是我所以有时弄错是由于上帝给了我去分辨真和假的能力对我来说并不是无限的。
--------
①“能力”,法文第二版是“功能”。
虽然如此,我还不完全满足;因为,错误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否定,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缺陷或者缺少我不应该有的什么完满性,而是缺少我似乎应该具有的什么认识。而且,在考虑上帝的性质时,我认为,如果说他给了我某种不完满的,也就是说,缺少什么必不可少的完满性的功能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匠越是精巧熟练,从他的手里做出来的活计就越是完满无缺的这件事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想像由一切事物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所产生的东西,有哪一种在其各个部分上不是完满、完全精巧的呢?①当然,毫无疑问,上帝没有能把我创造得永远不能弄错;同时的确他也总是愿意要最好的东西。那么弄错比不弄错对于我更有好处吗?②--------
①法文第二版:“那么由宇宙的这个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所创造的东西有什么在其名个部分上不是完满、完全精巧的呢?”
②法文第二版:“那么我能够弄错比我不能够弄错是一件更好的事吗?”
仔细考虑一下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智慧理解不了①为什么上帝做了他所做的事,这我倒也不必奇怪;同样,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存在,因为我通过经验也许看到其他许多东西而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以及怎样产生了它们②。因为,既然已经知道了我的本性是极其软弱,极其有限的,而相反,上帝的本性是广大无垠、深不可测、无限的,我再也用不着费事就看出他的潜能里有无穷无尽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原因超出了我精神的认识能力。光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相信:人们习惯于从目的里追溯出来的所有这一类原因都不能用于物理的或自然的东西上去;因为,去探求和打算发现上帝的那些深不可测的目的,我觉得那简直是狂妄已极的事。
--------
①法文第二版:“我理解不了”。
②法文第二版:“而且也不应该因此而怀疑他的存在,因为我通过经验也许看到其他许多东西存在,虽然我不能够理解上帝为什么以及怎样做成了它们。”
再说,我还想到,当人们探求上帝的作品是否完满时,不应该单独拿一个造物①孤立起来看,而应该总地把所有的造物都合起来看。因为,如果它是独一无二的②,它也许能有什么理由好像是十分不完满的;可是,如果把它看成是这个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它在它的本性上就是非常完满的③。而且,自从我故意怀疑一切事物以来,虽然我仅仅肯定地认识了我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可是自从我认出了上帝的无限潜能以来,我就不能否认他也产生了其他很多东西,或者至少它能够产生那些东西,因而我也不能否认我存在并且被放在世界里,作为一切存在的东西的整体的一个部分。在这以后,更进一步看看我,并且考虑一下哪些是我的错误(只有这些错误才证明我不完满),我发现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即由于我心里的认识能力④和选择能力②或由于我的自由意志⑤,也就是说,由于我的理智,同时也由于我的意志。因为单由理智,我对任何东西都既不加以肯定,也不加以否定,我仅仅是领会我所能领会的东西的观念,这些观念是我能够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可是在把理智这样地加以严格观察之后,可以说,在它里边决找不到什么错误,只按照“错误”这个词的本身意义来说。而且,虽然在世界上也许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在我的理智里边我没有任何观念,却不能因此就说它缺少这些观念,好像欠了它的本性什么东西似的,而仅仅是它没有那些观念;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上帝本来应该给我比他已经给我的那些认识功能更大、更广一些的认识功能;并且不管我把它想成是多么精巧熟练的工匠,我也不应该因此就认为他本来应该把他可以放到几个作品里的完满性全部放到每一个作品里。我也不能埋怨上帝没有给我一个相当广泛、相当完满的自由意志或意志,因为事实上我体验出这个自由意志或意志是非常大、非常广的,什么界限都限制不住它。而且我觉得在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心里的其他一切东西里,没有一个能再比它更大、更完满的了。因为,举例来说,如果我考虑在我心里的领会功能,我认为它是很狭小,很有限的,而同时,我给我提供另外一个功能的观念,这个观念要广阔得多,甚至是无限的;仅仅从我能给我提供其观念这一事实,我就毫无困难地认识到这个观念是属于上帝本性的。如果我用同样方式检查记忆,或者想象,或者别的什么功能⑥,我找不出任何一种能力在我之内⑦不是非常小,不是有限的,而在上帝之内不是广大无垠,不是无限的。我体验到,在我之内只有意志⑦是大到我领会不到会有什么别的东西比它更大,比它更广的了。这使我认识到,我之所以带有上帝的形象和上帝的相似性的,主要是意志。因为,虽然意志在上帝之内比在我之内要大得无法比拟,不论是在认识和能力方面(因为认识和能力在意志里结合到一起使意志⑧更有力量,更有实效),或者是在事物方面(因为意志无限地扩展到更多的东西上),如果我把意志形式地、恰如其份地对它本身加以考虑的话,那么我就觉得它就不是更大。因为它仅仅在于我们对同一件事能做或不能做(也就是说,肯定它或否定它,追从它或逃避它),或者不如说,它仅仅在于为了确认或否认、追从或逃避理智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我们做得就好象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外在的力量驱使我们似的。因为,为了能够自由,我没有必要在相反的两个东西之间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上抱无所谓的态度;而是,我越是倾向于这一个(无论是由于我明显地认识在那里有善和真,或者由于上帝是这样地支配了我的思想内部),我选择得就越自由,并且采取了这一个;而且,上帝的恩宠和自然的知识当然不是减少我的自由,而是增加和加强了我的自由。因此,当我由于没有任何理由迫使我倾向于这一边而不倾向于那一边时,我所感觉到的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不过是最低程度的自由。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与其说是在意志里表现出一种完满性,不如说是在知识里表现出一种缺陷;因为,如果我总是清清楚楚地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我就决不会费事去掂算我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判断和什么样的选择了,这样我就会完全自由,决不会抱无所谓的态度。
--------
①即“东西”。基督教把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认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也叫“造物”。
②法文第二版:“如果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③法文第二版:“它们仍然是非常完满的。”
④“能力”,法文第二版是“功能”。——译者⑤“自由意志”法文是“自由裁决”(librearbirre,或francarbitre)。
⑥法文第二版:“或者在我之内别的什么功能,我找不出任何一种”。
⑦法文第二版:“只有意志或者只有自由意志的自由”。
⑧法文第二版:“认识和能力同意志结合起来,并且使意志”。
从所有这些,我认识到,我错误的原因既不是意志的能力本身(它是我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因为它本性是非常广泛、非常完满的;也不是理解的能力或领会的能力,因为,既然我用上帝所给我的这个能力来领会,那么毫无疑问,凡是我所领会的,我都是实事求是地去领会,我不可能由于这个原故弄错。那么我的错误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这里产生的,即,既然意志比理智大得多、广得多,而我却没有把意志加以同样的限制,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理解不到的东西上去,意志对这些东西既然是无所谓的,于是我就很容易陷于迷惘,并且把恶的当成善的,或者把假的当成真的来选取了。①这就使我弄错并且犯了罪。
--------
①法文第二版:“并且把假的当成真的、把恶的当成善的来选取了。”
举例来说,过去这几天我检查了是否有什么东西在世界上存在①,并且认识到仅仅由于我检查了这一问题,因而显然我自己是存在的,于是我就不得不做这样的判断,即我领会得如此清楚的一件事是真的,不是由于什么外部的原因强迫我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在我的理智里边的一个巨大的清楚性,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我的意志里边有一个强烈的倾向性;并且我越是觉得不那么无所谓,我就越是自由地去相信。相反,目前我不仅知道由于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什么东西因而我存在,而且在我心里出现某一种关于物体性的本性的观念,这使我怀疑在我之内的这个在思维着的本性,或者不如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②是否与这个物体性的本性不同,或者是否二者是一个东西。我现在假定我还不认识有任何理由使我相信后一种而不相信前一种。因此对于否认它或肯定它,或者甚至不去加以任何判断,我都完全无所谓。
--------
①法文第二版:“真地存在”。
②法文第二版:“我是我自己”。
而且这种无所谓不仅扩展到理智绝对认识不到的东西上去,而且一般也扩展到(当意志考虑到这些东西时)理智不能完全清楚地发现所有这些东西的程度。因为,不管使我倾向于当我判断什么事情时我所采取的猜测的可能性有多大,单是这一认识的理由(即这些不过是一些猜测,而不是可靠的、无可置疑的),就足以给我机会去做出相反的判断。这几天我充份体验到,当我把我以前当作非常真确的一切事物都假定是假的,光是从这里我就看出了我们所以对这些事物采取某种怀疑的态度。
可是,如果我对我没有领会得足够清楚、明白的事情不去判断,那么显然是我把这一点使用得很好①,而且我没有弄错。可是如果我决定去否定它或肯定它,那么我就不再②是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去使用我的自由意志了;如果我肯定了不是真的东西,那么显然我是弄错了。即使我判断对了,这也不过是碰巧罢了,我仍然难免弄错,难免不正确地使用我的自由意志。因为,自然的光明告诉我们,理智的认识永远必须先于意志的决定。构成错误的形式就在于不正确地使用自由意志上的这种缺陷上。我说,缺陷在于运用(因为运用是我来运用),而不在于我从上帝接受过来的能力③,也不在于从上帝来的运用。因为,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埋怨上帝没有给我一个比我从他那里得来的那个智慧更有才能的④智慧,或比那个自然的光明更大⑤的自然的光明,因为事实上⑥不理解无穷无尽的⑦事物,这是有限的理智的本性,是一个天生就是有限的本性。但是我有一切理由感谢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欠过我什么,却在我之中给了我少量的完满性,我决没抱不正确的情绪,设想他不该把他所没有给我的其他完满性取消了或不给我。我也没有理由埋怨他给了我一个比理智更广大的意志,因为意志只在于一件事,并且它的主体就像是不可分似的⑧,它的本性看来是这样的,不管从它身上拿掉了什么都会把它毁灭。而且,当然,它扩展得越广,我就越要感谢把它给了我的那个人的好心。最后,我也不应该埋怨上帝助长我做成这个意志的行为,也就是说我弄错了的那些判断,因为这些行为既然是取决于上帝的,所以就是完全真实的、绝对善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能够做成这些行为比我不能做成这些行为,在我的本性上有着更多的完满性。至于缺陷(错误和犯罪的形式的理由就在于缺陷),它不需要上帝方面的什么助长,因为它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存在体,而且因为假如把它连系到上帝上去,把上帝当做它的原因,那么它就不能叫做缺陷,而应该叫做否定,按照学院所给的这两个词的意义来说。--------
①“显然是我把这一点使用得很好”,法文第二版是:“显然我是做对了”。
②“再”,法文第二版缺。
③“能力”,法文第二版是“功能”。
④“更有才能的”,法文第二版是“更广泛的”。
⑤“更大”,法文第二版是:“更完满”。
⑥“事实上”,法文第二版缺。
⑦“无穷无尽的”,法文第二版是“许多”。
⑧法文第二版:“并且就像在于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一样”。
因为事实上,假如说上帝并没有给我自由让我对于在他没有在我的理智里放进一种清楚、明白的认识的某些事物上去下判断或者不去下判断,这也不是在上帝方面的一种不完满,而无疑地是在我方面的不完满,是我没有使用好这个自由,因为是我在我领会得不清楚和糊里糊涂的一些事物上卤莽地下了判断。
可是,我看得出,虽然我一直是自由的,并且具有少量的认识,也就是说,上帝在把一种清楚、明白的智慧给了我的理智,使我对于一切事物用不着我加以丝毫考虑时,或者他仅仅把我在领会得不清楚、不明白时永远不去对任何事物下判断这样的一个决心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永远忘不了它,那么他本来是很容易使我决不弄错的。而且我看出来,只要我把我自己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就好像世界上只有我自己似的,如果上帝把我造成为永远不弄错,那么我就会比我现在完满得多。可是我不能因此就否认在某种意义上,宇宙的某几个部分难免错误比一切部分都错误①,会有更大的完满性。而且上帝在把我投入世界中时,如果②没有想把我放在最高贵、最完满的东西的行列里去,我也没有任何权利去埋怨。甚至我有理由满意:如果他没有给我由于我前面说过的第一个办法而不犯错误的能力(这种能力③取决于我对于我所能够考虑的一切事物的一种清楚、明白的认识),他至少在我的能力里边留下了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下定决心在我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以前无论如何不去下判断。因为,虽然我看到在我的本性中④的这种缺陷,即我不能不断地把我的精神连到一个同一的思想上,可是我仍然由于一种专心一致的并且时常是反复的沉思,能够把它强烈地印到我的记忆中,使我每次在需要它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它,并且由于这种办法能够得到不致犯错误的习惯。而且,由于人的最大的、主要的完满性就在于此,我认为⑤我从这个“沉思”里获益不浅,因为我发现了虚假和错误⑥的原因。
--------
①法文第二版:“比其他部分犯错误,比如果它们都犯错误”。
②“如果”,法文第二版缺。
③“能力”,法文第二版是“完满性”。
④“看到在我的本性中”,法文第二版是“体验到在我之中”。
⑤“我认为”,法文第二版是“我认为今天”。
⑥法文第二版“错误和虚假”。
而且当然,除了我所解释①的那个原因以外不能还有其他原因了。因为每当我把我的意志限制在我的认识的范围之内,让它除了理智给它清楚、明白地提供出来的那些事物之外,不对任何事物下判断,这样我就不致于弄错;因为凡是我领会得清楚、明白的,都毫无疑问地是实在的、肯定的东西②,从而它不能是从无中生出来的,而是必然有上帝作为它的作者。上帝,我说,他既然是至上完满的,就决不能是错误的原因;因此一定要断言:像这样一种领会或者像这样一个判断是真实的。
--------
①“我所解释的”,法文第二版是“我刚才所解释的”。
②“实在的、肯定的东西”,法文第二版是“什么东西”。
逻辑真理范文篇8
1912年到1916年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在其中他探讨了盛行的主要逻辑理论,并涉及到逻辑在一些学说——新经院主义、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主义”(先验逻辑或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奥·屈尔佩(O.Külpe)的“批判实在论”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形而上学基础。[1]在所有这些观点中,范畴理论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受亚里士多德或者是康德的激发,逻辑理论试图说明使得经验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概念,以及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基础。于是,逻辑学并非仅仅研究论证的形式特征,作为先验逻辑学或“真理的逻辑学”,它包纳了知识论和科学的所有基本问题。即便是新经院主义者(他们将逻辑学从属于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通过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一先验问题而展开的,虽然他们想重新赋予“先验的”这一术语以中世纪的超越性(transcendentia)所包含的前康德主义内涵,以恢复作为规定存在者的范畴的本体论意义。[2]海德格尔对这一讨论的最为原创性的贡献,即他1915年的《教职论文》及1916年关于它的“结论”(“即范畴问题”——译者注),显示了他在新康德主义的和新经院主义的逻辑学之间寻求一条独立道路的紧张努力。
这个主要文本,[即《教职论文》或《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译者注]重新审视了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中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粗略说来,即确定逻辑和语法的关系。海德格尔已提出过这样的论点:“逻辑学的真正准备性的工作并非是凭借对表象的起源和组成的心理学研究,而是凭借对词语意义的毫无歧义的界定和澄清而赢得的。”(《全集》1卷186页)[3]但是何谓意义呢?这一准备性工作同哲学的结合要求从范畴上将意义与口头的、书面的或思维的符号区分开来,这转而要求一种普遍的范畴理论。海德格尔受到“现代[逻辑]研究的视角”(《全集》1卷202页)的明确引导,在《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中进行的重构,其目的就在于阐明这两个问题。[4]司各脱的范畴理论使得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意义(significations,Bedeutungen)研究的首要意旨是……作为有效意义的真理”(《全集》1卷307页)。由于转向真理“不可避免地要求确定意义领域和对象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全集》1卷307页),所以海德格尔就设法保留了司各脱的范畴的本体论特征。但是海德格尔在这个主要文本中所进行的重构与其说是受了存在论观点的引导,毋宁说是受了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唯心论的指引。因为(正如海德格尔在1912年所指出的)逻辑学是“理论的理论”(《全集》1卷23页),它有(正如他在1915年所说的)“超出可认知的或被认识的对象世界的绝对优先性”(《全集》1卷279页)。逻辑学是第一哲学。
但是在《范畴问题》中出现了另一条注释,这是海德格尔在1916年发表关于邓·司各脱的书时附的一条简短结论。在此海德格尔对“范畴问题的系统结构”进行了一次有限的、“准备性的审查”,它又引出了“这个问题及其背景的基本潜力”(《全集》1卷300页)。这个主要文本中的论述已经是“严格概念式的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片面的”,它“有意识地排除了一系列更为纵深的形而上学问题”(《全集》1卷400页),有“对知识问题进行形而上学解决”的要求(《全集》1卷403页)。“如果从长计议的话”,哲学,包括逻辑学,不能“缺少它的真正眼力(optic)——形而上学”(《全集》1卷406页)。这样,由于对“形而上学”解决办法的需求,逻辑学的“绝对优先性”似乎被打了折扣。先验逻辑必须在“超逻辑的背景”中被审视(《全集》1卷405页)。因此,《范畴问题》确认了预示着一种形而上学的三个问题域,根据这种形而上学,已经抛弃了心理主义和语法主义的海德格尔相信能够恢复逻辑学的哲学意义,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
让逻辑学重获哲学意义的筹划并非仅限于海德格尔的学生时代。在他的1912年关于逻辑理论的评论中,海德格尔问道:“何谓逻辑?”,并回答道:“在此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问题面前,这问题的解决留待将来”(《全集》1卷18页)。十五年后,在他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课程中,海德格尔依然吁求一种“逻辑自身问题的彻底概念”(《全集》24卷252页)。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无论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拉斯克的范畴理论,都没能公平地对待在“事情本身”的压迫下,在对逻辑的哲学探究中出现的“本体论问题”(《全集》24卷253页)(这也暗示了他的早期作品所受的两个主要影响)。如果毕竟要“使逻辑再次进入哲学”的话,人们必须首先克服黑格尔的“本体论向逻辑学的还原”,并且审问何谓逻辑,何谓逻各斯的存在(《全集》24卷254页)。
两年前,当海德格尔开设他的题为《逻辑学——真理之追问》的讲座课程,通过批判当代“学院逻辑”将“所有的哲学,即所有的发问和探究”(《全集》21卷12页)都置诸脑后的做法,就已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了。作为一门在哲学专业内安逸的学科,逻辑“科学”实际上是无根基的,它自身的对象、它的科学领域一片混乱。把它界定为关于逻各斯的科学,也就是关于论证、言说、句子和命题的科学,并没有将它与其它研究这些东西的科学区分开来,除非人们补充说逻辑学特别地与“关于真理”的逻各斯有关。其它科学通过在方法论上探讨它们的对象来寻求“真的东西”;严格说来,只有逻辑学才是真正的关于“真理”本身的科学(《全集》21卷7页)。因此,如果逻辑学“想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形式,一种哲学化的逻辑学”,那么它“最为应当关注的”不是进一步发展技巧,而是“真理的源初存在”,即成为真的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全集》21卷12页)。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就是通过确定真理的存在,重新在逻辑和存在问题之间建立起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由康德予以革新的关联。
当海德格尔在1916年确认范畴问题的潜力时,真理概念就已经支配着他的观点了。但是他对一种“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全集》1卷402页)的吁求仅仅是点明了《教职论文》和它的“结论”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诉求表明了它向新经院主义的靠近,但主要文本中的论证却排除了一种新经院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将形而上学聚焦于真理问题,就保持了主要文本中“作为逻辑上有效的意义的”真理之优先性,这是一种批判主张,但却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那种将形而上学完全从属于逻辑学的企图。[5]这样,先验逻辑真理论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有计划的迈进设定了条件,但是他所主张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牵强妥协却不能保留了。要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最终还是要诉求于形而上学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对于如何看待范畴问题,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些论点:本文就试图说明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这就要求,首先以通向真理的先验逻辑方式揭露出它们的起源。
2.真理问题
康德已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做了区分,他指出:形式逻辑为真理提供了一个“否定性的条件”(没有它我们的思维就不能同自身相一致),而先验逻辑则提供了没有它们我们的思想就不会“与任何对象相关联”的条件,所以它是“真理的逻辑”。[6]如果说前者涉及的是思维的先天句法,那么后者则与其先天语义学有关。承认了“关于真理的名义上的定义,即真理是认知与其对象的符合”7,康德的范畴就成了作为一致或符合的真理的可能性的条件。在这一框架内,新康德主义者和新经院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呈现为下面的问题:是否真理的逻辑学需要在“本体论的真理”(enstanquamverum),也即在作为判断的尺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之中奠基。能对一致性给出一种纯逻辑的解释吗?双方都承认仅仅分析真理的结构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揭示对真理的认知性把握,对被认知者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但是如果去认识就是去把握思想和事物、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在1914年对森特罗尔(Sentroul)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引用此书中“真理问题的二律背反”(antimonyintheproblemoftruth)(《全集》1卷51页)的说法来说明这个问题:“或者人们拥有为真理所必需的比较的两要素,即思想和事物,但却没有比较它们的可能性;要不就是人们可以进行实际的比较,但却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全集》1卷51页)。在第一种情况下,判断和思想被视为一种实在的现存者(realexistent)、某种主体的行为,而对象则被视为是独立于认知过程的同样实在的现存者。但是,由于比较自身恰恰是另外一种主体行为,因此即使作为一致性的真理被赢得了,要知道(know)是否确实如此也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情况设定,一种在判断和被给予知觉的事物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但是由于被给予的东西不能先天地被确证为真实的事物,因此比较不是在“所需要的两要素之间”进行的。
由森特罗尔倡导的新经院主义的解决办法求助于本体论真理的观念,即“‘所是的东西’与‘所是者’之间的一致性的”形而上学“关联”(《全集》1卷52页)。在此,判断被认为与一种“客观的对应物”相一致,而这种对应物“以某种方式必定是事物本身”。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不是什么解决办法,他问道:“何为客观的对应物?它的客观性何在?”(《全集》1卷52页)。于是海德格尔提出了经典的新康德主义问题。虽然他也想走向一种存在论真理的理论,但他发现前批判哲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在认识论上是不充分的。它的“认知对象”的概念“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赘疣”(《全集》1卷50页),它也没能公正地对待实际科学:“甚至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主义哲学也没有导向科学的理论。”(《全集》1卷53页)。海德格尔不想借助于返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
这样还剩两种可能性:怀疑主义,否则就是对一致性的纯“逻辑的”解释,这种解释在揭示了对象是如何可能被认知的同时保持了它的真正先验性。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判断的]有意义的内容可以有效地决定判断的对象的话,那么判断是真的或是假的。如果存在(res)被理解为对象,而认知(intellectus)被理解为决定性的有意义的内容的话,那么古老的真理概念——认知与存在的符合(adaequatioreietintellectus)——就能以一种纯逻辑的方式被解释(《全集》1卷176页)。这又如何能够避免二律背反呢?显然,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对象”。如果它被形而上学地理解,那么结果是教条主义;如果将其理解为主体的表象,那么结果就是怀疑主义。要让知识是可能的,逻辑的对象就必定是事物本身;不过,这事物本身与认知有一种本质的(先天的)关联。
在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中,对象的逻辑特征成了一个主导性的问题。范畴理论是一种关于对象的对象性的理论(《全集》1卷216页)。在真理问题的范围内,它必须提供那些让人理解何为(are)对象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它们能作为衡量知识的尺度。由于此问题预示了下文的探讨,这里就先行指出海德格尔的观点的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解决这个二律背反部分地涉及到这样一个见解,即以现象学的“充实”(Erfüllung)观念来代替“比较”这一有误导性的隐喻。正如海德格尔在1912年指出的那样:真理是一个“‘意向性思想’是否被对象所充实”(《全集》1卷35-36页)的问题。但是,为了充实判断,对象必须是什么样呢?关于这一点,以上这个见解什么也没说。什么是认知性关联?海德格尔以如下的反心理主义的论题开始:判断是“有意义的内容”(significativecontent),它既不是心理行为也不是语法结构,而是“有效的意义”(validmeaning)(《全集》1卷31页)。有意义的内容就能够是真的或是假的。到1915年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观点:决定判断是真是假的东西,即对象,是“被给予者的有意义的内容,是被单纯直观着的事态”(theintuitedstateofaffairssimpliciter)(《全集》1卷273页)。
于是,第二方面就涉及到这被给予者的有意义的内容。对被给予性的诉求使得海德格尔的立场同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区分了开来,但是如果被给予的东西仅仅是“主观的”,那么它也会招致相反的指控,即怀疑主义。逻辑的对象不能仅仅是事物,但也不能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上的实在表象。对海德格尔来说,它是被给予之物的意义。真理的二律背反要求一种关于有意义的(meaning-full)对象的先验理论,它是形而上学的和生理的-心理主义的知识理论的前提。这样,在“结论”中被筹划的“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就将是一种意义的形而上学。但是如果形而上学已经设定了对象的先验逻辑概念,那么一种意义的形而上学如何能够解决知识(真理)的问题?这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是一个难点(aporia),它的要点在他作为范畴问题的视域而予以探讨的三个问题中得到了反思。
3.对象和对象领域
第一个问题——“范畴理论的基本要求”——是“将各种对象领域纳入到在范畴上不可还原的区域中去”(《全集》1卷400页)。一个对象领域,粗略说来就是一门科学理论依之而进行数量化的集合,是一种当代逻辑学意义上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先验逻辑的兴趣首先在于确定在这些领域之内及其之间的范畴关联,在于在其“特定的结构和构造”受“范畴”支配的“区域本体论”(胡塞尔)或“实在领域”之内安置对象(《全集》1卷210-11页)。8
范畴为每一对象都提供了“逻辑位置”。只有依据某种“秩序”,“位置”才有意义,因此“有其逻辑位置的东西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特定的关联总体相适应”(《全集》1卷212页)。任何一种“在可想见的范围之内”的现象都在逻辑空间中占有一个位置。在化学中被认知的某一特定事件,例如一个碱基反应,就通过在受自然范畴支配的逻辑空间(或实在领域)中被给予——被显示为具有——一个位置,这样它就成了化学领域的对象。9范畴属于科学的理性结构,并且提供了构造对象的原则,这些原则使得科学成了一种“对客观的东西的理论阐释”(《全集》1卷208页)。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海德格尔会认为将逻辑空间纳入不可还原的范畴领域如此重要呢?
部分说来,这是他与新康德主义内部的一场争论的关联在起作用。那托普的马堡学派关注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形成了一种大体上遵循着康德的范畴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成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就是能够被归入范畴,这与范畴和对象的种类无关而有其形式的有效性。10但是海德格尔也参与其中的里凯尔特西南德国学派,提出了一种更为多元化的研究范畴的方式。它认识到,例如,在历史中为知识奠定基础的概念并不与那些适用于物理学的概念相一致。狄尔泰对历史理性批判的吁求和胡塞尔对心理学中的非自然主义范畴的要求,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作为科学理论的逻辑学必须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而且康德的也是如此)“似乎只是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种类,而非范畴自身”(《全集》1卷211页)。范畴既不能从对被思考的那种对象进行抽象的思想中“推演出来”,也不能通过求助于一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立场而“类推地”确立起来,它们只能被现象学地揭示。在对各种科学的根基的反思中,“不可还原”的实在领域显示着自身(showthemselves),并如是地“被展示着”(《全集》1卷213页)。11
不过除了这一内部争论以外,对于划定范畴区域来说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紧迫的原因。如果逻辑学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对于对象的理论阐释”,那么逻辑学的对象属于哪一实在领域呢?真理问题需要一种对象的逻辑理论,而且如果此理论要成为真理论,那么它的原则就必定适用于它自身:“因此逻辑学自身要求它自己的范畴”(《全集》1卷288页)。如果逻辑学要澄清(包括它自己的)关于对象的认知是如何可能的,那么就“必定有一种逻辑学的逻辑学”。这一问题从总体上关系到这第一个问题的视域以及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
逻辑学的“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直接背景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宣称,揭示了将逻辑判断(在其中我们“非常容易和直接地遭遇到逻辑学的特有对象”)等同于判断的心理行为所具有的荒谬性(《全集》1卷166页)。12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论证反对将它等同于句子(“语法形式”),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认为行为和词语属于变易着的、可感觉的现成存在者的范畴领域,而判断则显示出自身还包含着“同一的”东西,它“使得它能以一种持久性和不可变易性而被体认到”,相比之下“心理实在则只能被说成是短暂的和不稳靠的”(《全集》1卷170页)。海德格尔将逻辑学的这一对象,即判断中的同一性因素,称为“意义”(Sinn)。但是,意义属于什么样的实在领域?意义的范畴是什么(《全集》1卷171页)?
意义问题“在整个哲学史上,从来就未曾以一种完全有意识和有意义的方式被给予过它的应得之地位”(《全集》1卷24页)。如果说后来海德格尔是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框架内来阐释它的话,那么他在此寻问的则不是存在的意义,而是意义的“存在”,也即它在逻辑空间中的位置。对作为逻辑学对象的意义的现象学把握,意味着对第三种实在的确认,而这种实在是在可感觉(心理-物理的)和超感觉(形而上学的)存在者之外的。对于这种实在,“洛采已在我们德国语言的宝库中找到了确切的表达”,即“除了‘它是(is)’以外,还有一种‘它有效’(gilt)”(《全集》1卷170页)。意义,逻辑学的对象,并不存在但“行得通”(hold),也就是“有效的”。它既不是可感觉的也不是超感觉的,而是“不可感觉的”。这样,在意义和任何存在着或发生的事物之间有了一种存在论差异。意义“不必存在而有效”(holdswithouthavingtobe)。
这个词来自埃米尔·拉斯克13,因为虽然有效(Geltung)概念最初是由洛采引入的(并且以某种形式几乎被所有反心理主义的逻辑学家所接受),但主要还是拉斯克对它的阐释影响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拉斯克以一种新的两个世界理论取代了传统的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可以想见的宇宙”被分为存在的和有效的。范畴理论的意义有两个:第一,它解决了逻辑范畴是形而上学实体(亚里士多德)还是心灵的思维形式(康德)这一问题。范畴两者都不是,它们属于“有效性”的领域。14第二个并且对海德格尔来说决定性的意义是,它确立起了意义超出于任何和每一对象领域的“先验的”优先性。既然范畴不是思维的形式而是意义的形式,那么逻辑的领域就是不受限制的。在范畴有效性之外,没有任何“存在者”(包括形而上学的存在者)领域是“元逻辑的”(metalogical)。如拉斯克所言,“形而上学也许可以被证明完全是一场骗局和一件荒唐之事,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的、逻辑的思考有能力说服我们相信这一点”,范畴理论“根本不能判决这一问题”(LP,125页)。这样拉斯克的逻辑学于是就消解了康德“批判的”[对形而上学的]放弃并恢复了“真理的无限领域”(LP,125页),这一观念回响在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学“超出于所有对象世界的绝对优先性”的谈论中。于是,意义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拉斯克的(和海德格尔的)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
意义(Sinn)这个词语最初是被用来标明逻辑判断的,但是真理的二律背反已经指向了这一概念的扩展,拉斯克在其《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中着手进行了这一工作。在拉斯克看来,逻辑范畴体系与对象自身的对象性有关(LP,29页),因此,“意义”这个词应当适用于后者,即先验逻辑的对象。判断的意义是一种“衍生的”、第二位的、人为的构造。“绝对意义上的”意义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或关联”(LP,34页)。这种统一不是现存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原事态(Urverh?ltnis),“在可感觉范围内获得的任何一种关联都不可与之相比拟”(LP,175)。
如果被先验逻辑学所理解的对象因此是范式的(paradigmatic)或原型的(urbildlich)意义而非再现的(nachbildlich)意义,那么范畴和质料之间的原事态这一意义概念,对于非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说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是它,而非诸如实体或主体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才是“存在者的”首要的“哲学修饰”(philosophicalepithet)(LP,123页)。但它是一种特别先验的观念,直接经验和经验科学的话语都无法理解它。它所涉及的只是拉斯克所谓的对象质料(LP,122页);人们只是“生活”于意义领域之中,却没有“认识到”它本身(LP,191页以下)。但是“如果我们作为逻辑学家把现存对象刻画为意义”,那么在对暗中使我们的一阶(first-order)认知性把握得以可能的东西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范畴形式本身(LP,123页)。依据对存在/有效性的区分的理解,我们把握了作为形式的范畴,所以在先验逻辑中我们能“认知”作为意义的对象。15
海德格尔明确地采用了拉斯克的范畴形式概念,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先验哲学中,形式概念都起着同样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它并不总是“清晰地和特别是毫无歧义地被理解”(《全集》1卷223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形式具有“作为心理的、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实在的构造原则这样的形而上学意义”,也即是说它是一种形而上学实体。但是如果形式是一种实体,而且如果它被认为是将实体构造为实体的东西,那么就会有一种无限倒退(《全集》1卷221页)。康德在逻辑的东西的领域内将形式概念抬到了权能这样的决定性位置上(《全集》1卷223页),但是他没有决定性地摆脱心理主义。16而对拉斯克来说,范畴形式只有“有效”的特征,而且由于有效总是对某物有效(Hin-gelten),所以形式在本质上就与特定的质料关联在一起。因此,说形式能够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或者通过思维能被赋予质料(康德)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如果存在着诸多的形式(有一张范畴“表”),那么区分的原则必然在于质料本身。由拉斯克的这一“对形式的质料决定”(materialdeterminationofform)原则可知,范畴的“发现”,如海德格尔所要求的那样,将是一件经验现象学的事情(LP,63页)。
质料决定原则意味着不能以黑格尔的方式将对象扬弃到(逻辑的)概念里去,即使是在黑格尔主义化的新康德主义的无限上升中也不行。但是如果形式不是对象的一个现成的组成成分,例如就像一棵树的枝杈或基因(DNA)是它的组成成分一样,那么它的“有效”如何被理解呢?拉斯克回答说,形式“只是一种与质料相关的、特定的、客观的意蕴关联(Bewandtnis)”(LP,69页),只是质料自身内所固有的某种秩序。17它是一个“澄明的契机”(momentofclarity),借助这一契机事物同质料相一致的方式被“照亮”了(LP,75页)。对象质料不能被还原为逻辑形式(“泛逻辑主义”),而是内在于逻各斯的(logos-immanent),它在形式之内就如在它的意蕴关联之内一样“被持有”(“逻各斯的泛统治”)(LP,133页)。同样,对海德格尔来说,形式既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实体的现成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澄明的契机”;范畴给对象质料“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带来了“更多的澄明”。它只是“与对象的某种意蕴关联”,只是质料自身的排列或卷入(《全集》1卷224、225页)。作为“被给予者中一个秩序的契机”,范畴使被给予者成为“可把握的、可认知的、可理解的”,也即它“有效”(《全集》1卷224页)。这样,对海德格尔和拉斯克来说,形式都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原则而是一个可理解性原则,但它属于质料本身而不是首先通过思维的构建活动才出现的。
这种关于逻辑形式及相应地关于原型意义的对象的观点,使得拉斯克的真理概念更为牢靠。严格说来,认知、判断只能说是“与真理一致”或“与真理相反”,因为它们是在经验知识的主观过程中,通过对对象的“人为的”解构而出现的。使这种相反或一致被衡量出的东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作为“超对立的”(übergengens?tzlich)意义的对象自身,它超越了真与假的对立。18对象是有效形式和质料的统一体,它可恰当地被称为“真的”:“特定的对象就是特定的理论的意义统一体,就是特定的真理。”比如,“时空对象是真理”,虽然它们不是“认知、判断、命题”,而是“原型领域内的意义统一体”(LP,41页)。因此,拉斯克的先验对象概念满足了上面开列的对一致性进行逻辑解释所需要的条件,也即是说,它显示出对象在判断中是如何能够作为真理的尺度而从原则上起作用的。这么说的理由是,如果“对象自身无非是意义”,那么由此可知“意义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判断的意义和事物本身之间怀疑论的距离)“就等于意义和意义之间的距离”(LP,43页;LU,394页)。
对拉斯克要揭示原型对象(范畴形式和质料)的要素是如何被纳入判断的结构中去的企图,我们在此不能再加审查了。19在此介绍的拉斯克的观点只是用来提示出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对象的思考的思想来源,并为确定他的解释中有何新的东西做些准备。拉斯克使得海德格尔以一种批判的、逻辑的方式形成了对存在论真理的新经院主义式的诉求,但他没能彻底地解决这个[关于真理问题的]背反。
海德格尔将司各脱的存在论的真理学说——存在(ens)和真理(verum)的可转换性——明确地表达在了一句逻辑成语中:“每一个对象都是一个真的对象”(《全集》1卷265页)。虽然怀有同新经院主义一样的诉诸存在论真理的动机(也即是说,将事物本身作为判断的尺度整合到逻辑中去),但是海德格尔的重构用基于有效性之上的逻辑思考代替了后者的形而上学“赘疣”。说每一对象都是一真实的对象并不是做了一个形而上学论断(一个形而上学论断总是与超感觉对象质料有关,而非与对象有关)。它只是意在显示范畴自身的范畴本质,意在确认与有效性自身相关的意蕴关联,也即“与认知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全集》1卷267页)。但是如果不涉及认知主体,那么这一意蕴就是不可理解的。即使作为范畴和质料的统一体的对象,作为“超出”真与假的“对立”的意义统一体是真的(《全集》1卷268页),即使“在纯粹的被给予性中意识可被导向‘真的东西’”(《全集》1卷285页),但海德格尔还是强调指出:这对象“实际上只包括”(《全集》1卷271页)那些在判断中能被明确地端呈出来,并结合到意义统一体中去的要素:“真的东西在认知中构造自身”(《全集》1卷271页)。通过“主体的取位(positiontaking)行为”,在范畴上被构造的“真的”对象,“即随其特定的实在形式一起被给予的对象质料的有意义的内容”,就被“纳入到了判断中来”(《全集》1卷270页)。
看起来对一致性进行逻辑解释的要素现在已然齐备。通过第三种“实在形式”,即有效的意义,范畴理论已在对象之中被奠基。对形式的质料决定观,无需还原主义就澄清了各门区域性科学的认知对象,而且无需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或康德怀疑论的拒弃,它就确立起了“逻辑意义的优先性”。但是这一对存在论真理的重塑是否是充分的呢?对象被纳入认知——作为“真的”对象的先验意义所依赖的那意蕴关联——如何被理解?出于“结论”中的未竟任务的第二点所暗示的原因,海德格尔发现他在此必须超越拉斯克4.逻辑与主体性
范畴问题的第一个视域是划定意义的对象领域[所属]的实在区域,但没有第二个视域,即将其“嵌入主体和判断问题”(《全集》1卷40页),它是不能被赢得的。真理的逻辑要求填补司各脱(从而当代的新经院主义)及拉斯克(从而当代的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所具有的某种空白。只要范畴理论依然像拉斯克的理论那样,将全部目光都集中于“真正的先验性”(“未被任何主体性触及的”对象),它就尚未揭示知识作为认知是如何可能的。20二律背反将依然会出现,因为“要比较判断的意义和实在的对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全集》1卷273页)。拉斯克的对象意义的要素和判断的意义的要素之间的同构(LU,394页)只是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需显示此同构是如何被给予的。
与拉斯克相对,海德格尔现象学地阐释了这一问题。认知不是比较而是充实(Erfüllung)。这也就是说,被给予的对象、“被给予的有意义的内容、被单纯直观着的事态”是“判断的意义的尺度;后者从它那里获得它的客观有效性”(《全集》1卷273页)。但是这意味着,拉斯克的逻各斯的内在领域(作为原型意义的对象的所在或“澄明”)的被给予性必须被逻辑地加以定位。如果不涉及主体,对对象的逻辑澄明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存在论真理必须奠基于早已被司各脱指出过、“被正确理解的内在性概念”之中(《全集》1卷273页);存在和真理的可转换性蕴涵着拉斯克的论题“‘逻辑的存在者’和对象的可转换性”(《全集》1卷279页)。但是对于海德格尔/司各脱来说,逻辑的存在者(从先验逻辑观点来看的对象)是一种生命中的存在(ensinanima)。这不可能是一种现成的、实在的心理实体,不可能是一种活动或表象,而只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意向对象的意义’(noematicmeaning)”(《全集》1卷277页)。
对于海德格尔对知识和对象之间的意蕴关联的理解来说,提及胡塞尔是非常关键的。意向对象,也即被给予的有意义的内容,无非就是在反思的第二意向(secundaintentio)中被把握到的事物本身,在这第二意向中意识不是(像在原初意向[primaintention]中那样)被导向“在其直接实在性中的实在对象”,而是“被导向它自己的内容”(《全集》1卷279页),也即真实的对象“的”可理解性,并从而也被导向它的范畴结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认知的对象和对对象的认知之间的区分归属于内在性的领域,这种领域是受反思的和非反思的意识之间的(现象学的)区分支配的。“实在样式间的首要区分是意识与实在之间的区分;更准确地说,是在实在性的非有效样式间的区分,而这些非有效样式转而又总是能在以有效性为特征的意义背景之内并通过它而被给予”(《全集》1卷279页)。如果说“只是因为我生活于有效性领域之中,我才能知道关于存在者的事情”(《全集》1卷280页)是正确的,那么说只是因为能反思这样的“生活”,我才能知道有效性领域的事情,这也是正确的。
有了他的现象学的内在性概念,海德格尔就能够“在主体和判断问题的范围之内”来安置拉斯克的范畴有效性理论了。如果范畴——海德格尔在此称之为“对可经验的东西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要素和资源”(《全集》1卷400页)21——并非来自对实在者的“复制”,而是“相关于”质料而安排秩序的原则,那么需要解释的,大略地说来,是它们的充实的需要(Erfüllungsbedüftigkeit)(拉斯克)或语义学的质,以及它们对某物的有效(Hin-gelten)或对质料“的”持有(holding)。在拉斯克将有效性视为一个不可还原的先验范畴的地方,海德格尔就指出它必须被奠基于意向性之中:“意向性是逻辑领域的‘规定范畴’”(《全集》1卷283页),也即“决定秩序和划定逻辑学领域的契机”(《全集》1卷281页)。如果不把逻辑的这一“主体方面”考虑进来,那么一种范畴的“客体逻辑”理论“必定依然是不完备的”(《全集》1卷404页)。
范畴是“对象的最为普遍的决定因素”,但是提及一个对象就已牵连着主体了(《全集》1卷403页)。首先,在生活的“单纯被给予性”中,意识“朝向‘真的’状态”(《全集》1卷285页);其次,人们要“意识到它是真的、有效的意义,就只有通过判断”(《全集》1卷285页)。于是,范畴理论遇上了传统的被给予性和“述谓”问题(《全集》1卷403页)。对象是如何作为有效意义(“‘真的’状态”)被给予的,以至于通过作为“取位”的判断主体的“成就”,主体就能够“意识到意义”(《全集》1卷285页)?述谓活动及其内在逻辑构造——判断的意义——如何能对超验的对象(“实在的非有效样式”)有效呢?这一问把人们从范畴理论带到了意义理论,因此必须在此对之置而不论。但是在“结论”中海德格尔总结道:只有“从判断开始”,“范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于‘思想之外’的)有效性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因为“不把‘主体逻辑’考虑进来,即使谈及内在的和先验的有效性也毫无意义”(《全集》1卷404页)。
当海德格尔引入“投射”(Projektion)一词来探讨一个对象领域是如何被范畴所构造时,他就已经触及了主体逻辑问题,虽然他并没有展开。例如,只有通过将它们投射入一个受范畴支配的“同质媒介”或“生活元素”(Lebenselement)之中,我才能计数极为特殊的对象质料,如“两棵树”(《全集》1卷255页)。当司各脱为了区分被给予性的样式(存在[essendi],意识[intelligendi],指示[significandi])而诉诸主体或“行为”分析时,他就暗示了主体逻辑,而胡塞尔则为海德格尔指明了这一点(《全集》1卷321页)。22但是在司各脱那儿也有一个空白:他缺少一个“精确的主体概念”(《全集》1卷401页),加之经院心理学处于主导地位的“客观的-意向对象的导向”(《全集》1卷205页),这意味着司各脱从没有完全地将客体逻辑(范畴理论)与判断中的被给予性,以及客观性的构造这些主体逻辑问题完整地结合起来过。23
如果说中世纪的逻辑学最终没能将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立即指出,当代逻辑理论同样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比较了两种对立的现代观点——屈尔佩的批判实在论和新康德主义的先验唯心主义——以此表明二者都没能够成功地澄清认知和对象之间的关联。
批判实在论的观点在认知的经验的(心理的)方面和理性的(范畴的)方面之间做了区分,并坚持认为后者,范畴,使我们得以从仅仅“设定”(poisiting)一个先验对象(在主体被给予性的基础之上)进展到对之进行一些如实的述谓。24这避免了心理学的唯心主义,因为[按其观点]范畴不是作用于知觉的被给予物的联想的原则。但是海德格尔指出,按照屈尔佩的观点,“被认知决定的实在世界的对象”并非如实地“呈现在知觉中,并非仅仅在意识中被给予,而是首先通过认知的过程,尤其是通过科学研究而被把握”,而且这也恰好正是马堡(形式的)唯心主义的首要观点:认知的对象不是被给予者,而是通过科学的不断探索而被赢得的有效判断,这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理念(Idea)。由于没有认识到判断问题(被纳入它自己的科学的对象-概念之中)对于“客观性的奠基”所具有的意义(《全集》1卷403页),批判实在论是不够批判的。25
但马堡唯心主义也未获成功,虽然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首先,通过把空间和时间处理为范畴,它规避了被给予性问题。随着康德的先验美学的这种逻辑化,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形式唯心主义没能“将对形式的质料决定原则与其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集》1卷404页)。如果范畴从质料那里获得它们的意义,那么除了现象学地诉诸不同类型质料的被给予性,它们就不能被理解。其次,出于对心理主义的恐惧,它将意向行为(noetic)或行为的领域贬斥到“理性心理学”中的范畴构造的地位上。但是如果质料并非首先被给予“理论的”主体,而是被给予投身于前理论的、实际的世界生活的意识,那么这种对“客观有效”思维的形式重构就会错失在其中可觅得范畴之起源的那个维度,也即处于“生活”中的可理解性或澄明。
是拉斯克最接近于克服了当代实在论和唯心主义的缺陷。以其被从质料上决定的范畴形式理论,他“毫无疑问地赢得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全集》1卷405页)。但是质料如何决定形式的问题——原事态的所在——最终开启了一个“新领域”,在其中拉斯克不能“对可感觉质料和非可感觉质料之间的区别做出充分的解释”(《全集》1卷405页)。也就是说,如果范畴自身就是先验逻辑认知的“质料”,那么拉斯克对范畴如何能被给予(就如可感觉地存在的质料在知觉中如何被给予)这一问题的忽略就是不合适的。拉斯克关于意义的“真理论的(aletheiological)实在论”从而最终依然是非批判的,因为他把所有这样的问题都看作是心理主义的。通过将有效性奠基于意向性之中,海德格尔为这一问题指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他对胡塞尔的“范畴直观”的高度关注,显示了在其后来的作品中他是多么严肃地来对待它的。26然而,在这里海德格尔只是简单地评论说,如果不首先弄清“下判断的主体”,那么人们将“永远不能将所谓的‘有效性’的意义完全端呈出来”(《全集》1卷405页)。
关于范畴问题的第二个视域,海德格尔接着指出,必须将批判实在论和先验唯心主义的动机(motives)带入“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去”(《全集》1卷404页)。屈尔佩的实在论正确地保留了认知对象的先验性,但是它的自然主义没有公正地对待意义问题。马堡唯心主义正确地坚持了有效意义的逻辑首要性,但是和拉斯克一样,没有认识到“逻辑的最基本问题自身只显示给那些将‘前科学的’知识考虑在内的逻辑探究者们”(LP,185页),在这种“前科学的”认知中可觅得在质料上被决定的形式的起源。但是,即使说拉斯克把握了对形式的质料决定的话,那么他对判断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还是依然深陷于“真正的先验性”这一准教条主义泥潭之中,这种先验性关注的是“结构问题”,它脱离了在内在性中赢得或发现结构的问题。质料决定的问题并没引导他走向对形式/质料二元分立的“价值和局限进行不可规避的有原则的探究”(《全集》1卷405页),从而它的“极富成果的”作为“超出”真与假的“对立”的对象的意义概念,驱使他来到了“他也许从没充分意识到过的形而上学问题”面前(《全集》1卷406页)。27但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又是什么样的“更高的统一体”呢?这就是范畴问题的第三个视域。
5.形而上学问题
前两个问题域属于逻辑自身,包含其客体和主体方面的协调。然而,第三个问题则要求超出逻辑的范围,从而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逻辑研究和海德格尔在此所谓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前行论述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一超出之举的成问题的特征说些什么了。
如果第一个问题(在范畴上划定意义的逻辑领域)不诉诸第二个问题(主体和判断问题)就得不到解决,那么海德格尔是通过诉诸胡塞尔的内在性观念而开始走向这一目标的。胡塞尔的《观念Ⅰ》已提供了“对‘意识’的丰富性的决定性洞见,并摧毁了关于意识一般的空洞性的通常看法”(《全集》1卷405页),但最终说来这还是不够的:“人们根本就不能如实地看到逻辑和它的问题,除非它们由之而被解释的背景成了超逻辑的”(《全集》1卷405页)。尤其是,为主观的(现象的)逻辑问题提供背景的内在性概念,不能以任何传统的或当代的唯心主义或实在论的模式来理解。显然,能澄清这种内在性自身的范畴不能通过对认知的意蕴关联,也即对逻辑的“认识论主体”的反思而被赢得。必须超越逻辑,超越“理论态度”,这种态度“只是活生生的精神(livingspirit)的诸多形成方向之一”。这样,范畴问题的第三个视域就显示为,依据“活生生的精神”观念“对意识进行一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解释这样的任务”(《全集》1卷406页)。由于这“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精神”(《全集》1卷407页),所以“历史和它的文化-哲学的、宇宙目的论的解释”就必须成为“在范畴问题范围内决定意义的因素”(《全集》1卷408页),也就是说,在一种范畴形式理论中,历史属于决定着意义的质料。
这些观念引出了诸多问题,它们对充分阐释海德格尔的早期逻辑著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虽然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吁求反映了他向新经院主义的靠近,但是他自己的话语则远非一种盖泽尔(Geyser)或者森特罗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在论;它们来自黑格尔,或者更精确地说,来自狄尔泰的后黑格尔主义的生命哲学。但在此我们将仅仅指出,海德格尔诉诸形而上学的方式与真理的逻辑有关。海德格尔说,正是“真理问题”要求一种“对意识的形而上学的-宇宙目的论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哲学离开了逻辑“结构研究”而“突入到真正的实在和真实的真理(turerealityandrealtruth)”(《全集》1卷406页)。即使逻辑意义(真理)既非心理的又非形而上学的,但海德格尔依然要求以某种方式对其所谓的“存在论”地位予以具体阐明。形式/质料的结构统一体在逻辑的范围内也许够用了,但是如果人们要为逻辑学“保证给我们真正的实在和客观性”的能力奠定根基,那么“逻辑的意义就必须被带入到与其存在的意义(onticsignificance)也有关的问题中去”(《全集》1卷406页)。
这些有所节略的评论等于宣称先验逻辑没能回答问题:何为意义?“形而上学”应当提供通达“存在的意义”的途径,但清楚的是,海德格尔在“结论”中的用法并不与那个主要文本[《教职论文》——译者注]中被发现的形而上学(一门关于超感觉实体的科学)的意义一致。何为存在的意义?当海德格尔暗示说这将是一种“对对象概念的先验的-存在的解释”时,我们可以在“存在的意义”这个词中听到他后来作为存在论而加以展开的东西,也即对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的(先验)研究,这是承继作为真理基础的原型意义的先验逻辑研究的学说。
一种源自先验逻辑学的“意义的形而上学”最终要求形而上学之外的东西,这一点昭然地显示这样一个问题之中,即如何用那个主要文本中的系统术语将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协调起来这样一个问题之中。考虑到逻辑学作为理论的理论的绝对优先性,它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作为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理论的形而上学。又考虑到对象、形式和质料是全部的逻辑原则,那么对于对象的一种存在的解释,只能是一种(对形式和质料的原事态的)“存在的”意义的把握。例如,说质料“决定”形式,或者说形式“澄明”质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形而上学是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科学,那么关于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它又能告诉我们哪些逻辑学所不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呢,既然它已经预设了逻辑?它的“超逻辑”原则从何而来?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但两则评注已指出了困难之所在。28第一,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在中世纪哲学中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是“共属一体”的,“脱离了生活,作为一种理性主义构造的哲学是无力的,而作为非理性主义体验的神秘主义则是盲目的”,因此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必须在某种更高的统一体中被审视(《全集》1卷410页)。第二,与质料决定问题相联,他承诺要揭示艾克哈特(Eckhart)的神秘主义对于“真理问题”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全集》1卷402页)。29因此,似乎决定形式的质料并不要求作为一种关于超感觉存在者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反之,对逻辑意义的“真正的实在和实在的真理”,及对它的“存在的意义”的突破,似乎蕴涵着与神秘主义的结合。然而它也将有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解释”的特征,我认为这意味着它依然关注着批判的、在现象学上被理解的“独一无二的意识关联”(《全集》1卷277页)。
因此,范畴问题的形而上学视域也要求一种对主体的先验的存在解释。主体的“真正的实在”是历史的,在其内在性中真理问题逻辑地被构建并被解决。范畴既然是质料自身的意蕴关联,那么它就不能从一种无时间性的意识一般中推演出来。因此范畴的出现——“对可经验者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资源”的出现——是一个历史问题,为了对范畴的本质进行“存在的”解释,这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如果并非首先是在科学中,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前理论的可理解性中、在其“在有效性中的生存”中,质料的意蕴关联原初地显示自身,那么把范畴理论限定于科学的可理解性原则就是人为的做作。可理解性、范畴体系并非仅仅在理论生活中才被发现。因此,逻辑学必须认识到,意义(和范畴)的根源存在于活生生精神的所有富有意义的形成方向中。只有通过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活生生精神的“基本形而上学结构”,“及其与形而上学的‘起源’的关系”,人们才能理解如何能将“行为的独一无二性和个体性与意义的普遍性和持存性本身一起融入活生生的统一体中”(《全集》1卷410页)。30
这就是意义的形而上学,也即“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的终极视域。意义(逻辑对象)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行为之间的差别被设定了,虽然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表明这种意义与一种对行为的非心理学的、逻辑的研究并非水火不容。但是,在形而上学的或“存在的”层次上,依然需要通过研究历史的活生生精神的基本形而上学结构,来理解个体性和普遍性、行为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的存在。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要求对内在性和意识的现象学领域进行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解释。认识论的内在性必须被提交到历史的活生生精神的超逻辑背景中去,这种背景是意义的原初所在(虽然显然不是根源)。海德格尔没有说人们怎样做到这一点,也没有说这种解释的逻辑地位会如何。
可以表明这一要求很快就把海德格尔引向了他的核心发现之一,也即抛弃意义与“对象”的先验逻辑的同一性,转而采用(作为“世界”的)意义的先验存在论概念。但是这将需要考虑他早期的弗莱堡讲座课程,同样也要求对他如何和为何逐渐抛弃了1916年的“哲学的更深层的、本质上的世界观特征”这一思想(《全集》1卷410页)进行充分的解释,这一思想是掩藏在他那有点神秘主义气息的形而上学背后的。我们在此只是提请人们注意:对范畴理论、对哲学化的科学的要求,继续在他那些研究缘在(Dasein)的生存状态(existentials)的文本中发挥着影响。尽管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存在与时间》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在逻辑真理问题中被摆明的挑战,也就是去说明不同的(包括它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式中真正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这种说明并不意味着为知识问题提供某种形而上学的解决方案,而是对它的一种先验存在论的再阐释[1]本文依据了海德格尔的下列早期著述,它们是与当时的逻辑学有着重要关联的:“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DasRealit?tsproblemindermodernPhilosophie”)(1912),“逻辑新探”(“NeuereForschungenüberLogic”)(1912),《对查理斯·森特罗尔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Reviewof‘CharlesSentroul’sKantundAristoteles’)(1914),《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DieLehrevomUrteilimPsychologismus)(1914)和《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1915,DieKategorien-undBedeutungslehredesDunsScotus),最后这本著作附有1916年的一个结论《范畴问题》(“DasKategorienproblem”)。在文中我是依据《早期著作》(FrüheSchriften)(《[海德格尔]全集》1卷)中的页码来引用这些作品的。所有的引文都是我翻译的,但参考了先前已有的译文。
[2]这是“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的争论系统地进行之处,而且对于新经院主义的这样一个策略,即表明“现代”思想家及其争论的问题(包括现代科学)都能被纳入经院主义的框架中去的策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策略被教皇通谕aeternipatris(1879)官方化。因此,沃尔夫-迪特尔·古道普(Wolf-DieterGudopp)在其《青年海德格尔》(Frankfurt:VerlagMarxistischeBl?tter,1983,21)中,看到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有一种关键性的新经院主义式的“反现代主义”。但是在对海德格尔早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审查后,胡戈·奥特(HugoOtt)在《马丁·海德格尔:正在形成之中的传记》(Frankfurt:CampusVerlag,1988)的第74页以下,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曾深深地被“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所吸引。
[3]由于我没有篇幅在此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所以我只是简单地指出,我将把“Bedeutung”及其同族词译作“意义”(signification),而将Sinn及其同族词译为“含义”(meaning)。海德格尔在所引段落中提及的“准备性的工作”与将自然语言转译为逻辑形式(如表征符号)的任务有密切关联。这就出现了海德格尔与符号逻辑学的产生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我在此不讨论它。在1912年的逻辑评论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了罗素和怀特海,他要争论的只是这种“逻辑斯谛”并不能通达“真正的逻辑问题”,即“[‘对逻辑问题进行数学处理’的]可能性条件何在”的问题(《全集》1卷42-43页)。
[4]海德格尔的重构部分地奠基于[《理论语法》一书中的]“意义的形态”(Demodissignificandi)这一章,后来这本书的作者被证明是埃尔富特(Erfurt)的一名司各脱主义者托马斯,而非司各脱本人。由于考虑到它的问题历史的方式(《全集》1卷196、399页),这一出入对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影响甚微,所以我将继续在文章中将它指涉为“司各脱”。
[5]于是,正如曼弗雷德·布莱拉克(ManfredBrelage)在其“先验哲学和具体的主体性”[载《先验哲学研究》(Berlin:deGruyter,1965,72-230)]中已表明的那样,海德格尔的计划可被看作他完善或超越一种形式的“客体逻辑”(这种逻辑是关于有效知识的原则的)几次努力中的一次,它们具有晚期新康德主义特征。在为批判的认识论寻求背景的这些努力中,除了海德格尔的努力以外,布莱拉克还探讨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晚期那托普的《思维心理学》、R·赫尼希斯瓦尔德(R.H?nigswald)的《单子论》和N·哈特曼的“认识形而上学/本体论”。
[6]伊曼努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KempSmith)译(London:Macmillan,1968),98(A59/B84),100(A62-63/B87)。
7同上,97(A58/B82)。
8“Wirklichkeitsbereich”(实在性领域)是海德格尔指称范畴“种类”(sort)的常用词语,不同对象和对象领域(Gegenstandsgebiete)都归属于这种范畴种类,当然他有时也使用诸如“缘在的形式”(Daseinsform)、“实在性的形式”(Wirklichkeitsform)、“实在性的方式”(wirklichkeitsweise)等相关词语来表达这个意思。考虑到这些概念和接下来的存在者的/存在论的区分之间的关联,值得指出的是,在此“存在”(being)只是意味着实在的单个领域的范畴,也就是只意味着可知觉的现成存在者。在1925-26年的冬季学期的讲稿中,海德格尔明确否认这种“来自洛采”的用法(《全集》21卷64页)。
9诸如“存在者”、“因果性”、“事件”(occurrence)等等。经验科学家不关心这样的范畴,而是关心科学的对象之中及其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海德格尔正是这样理解科学的“理性”维度的。但显然,在来自范畴维度的抽象中,正如下面将被探讨的一样,科学家通达对象的“理论”方式失却了它的意义。
10对较布莱拉克,前面所引书的第103页。
11表明如下一点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这些(无可疑义的)早期著述中,不是海德格尔的那研究方式,而是他对现象学的那种吁求是现象学的。关于狄尔泰,我也必须做出同样的防止误解的说明。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出色探讨,参见弗瑞特尤夫·罗迪(FrithjofRodi)编著的《狄尔泰年鉴》4卷(1968-87)中的文章。
12在逻辑评论中,而后又一字不差地在其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赞许胡塞尔已经“打破了心理主义的进路”,然而同时他也赞同那托普的如下论断:新康德主义者从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论证中“学不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全集》1卷19、64页)。
13埃米尔·拉斯克,《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DieLogikderPhilosophieunddieKategorienlehre),载《作品集Ⅱ》(GesammelteSchriftenⅡ),欧根·赫里格尔(EugenHerrigel)编著(Tübingen:J.C.B.Mohr,1923,6)。当下文中引用这本1911年的作品时,其出处会在文章中给出,此书名被缩写为“LP”。根据上面我对“存在论差异”一词的用法,比较一下拉斯克早已使用了的而海德格尔将会使用的明确表述(如LP21,46,117,121页)。对此的一些讨论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和逻辑学的无家可归性”(Lask,Heidegger,andtheHomelessnessofLogic),载《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JournaloftheBritishSocietyforPhenomenology),23/3(1992)卷222-39页。
14当然,新康德主义者并没有把范畴看作思维的心理形式,但是他们的确是将范畴理解成了有效知识的形式原则。然而,拉斯克拒绝承认这种关于知识的提法,对他来说“认知”蕴含着一个认知主体。被称为“有效性”的实在样式和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拉斯克试图界定的,而非定义式地设定的,虽然如下文所论,恰是在此海德格尔发现他失败了。也参见前面所引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一文。
15要对拉斯克心中所想进行充分的解释需要进入他对体验(Erleben)和认识(Erkennen)的区分,并对他的“功能形式/质料”的区分进行阐释。本文的当前目标更为有限,但可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胡塞尔、拉斯克和先验逻辑观念”,载罗伯特·苏克罗维斯基(RobertSokolowski)编著的《胡塞尔和现象学传统》(Washington,D.C.: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nPress,1988,63-85)。
16虽然早在1912年海德格尔就证明,康德哲学在本质上是心理主义的还是先验的这个问题早已被解决了,“先验的-逻辑的解释受到了偏爱”(《全集》1卷19页),但是心理主义解释的依然存在正显示了康德思想(如“综合”思想)的一种不清晰性。拉斯克无论如何也没完全解除康德的心理主义(LP,243-262页)。人们知道,大约在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海德格尔已对康德发生了一种新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一条对康德进行现象学解释的道路(《全集》25卷6页)。参见丹尼尔·达尔斯托姆(DanielDahlstrom)的“海德格尔的康德式转折:对他《纯粹理性批判》的评论的注释”,载《形而上学评论》45卷(1991)329-361页。达尔斯托姆没有涉及海德格尔在早期作品中对康德的解释,在那儿海德格尔似乎感到,像那时的胡塞尔一样对康德有所保留是合适的。
17这个词——对《存在与时间》中的“世界性”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被马克奎利(MacQuarrie)和罗宾逊(Robinson)译为involvement(“意蕴关联”),虽然如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Tugendhat)在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Berlin:deGruyter,1970,290)中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这个词所包含的“两个含义也许没有任何语言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一问题值得另行对待,但现在指出如下一点就够了:如果逻辑空间的“关联整体”(Beziehungsganzes)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关联统一体”(Bewandtnisganzheit)的先兆的话,那么海德格尔采用拉斯克的“意蕴关联”(Bewandtnis)一词来解释逻辑形式就是这一过渡中的重要一环。在我的文章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对它留而不译,以此来突出这个词的成问题的新奇之处。
18这形成了拉斯克的第二篇重要论文《判断理论》(1912)(载《作品集》,前面所引的书,尤其是413页及以下)的主题。当本文在下面引用《判断理论》时,它被缩写为“LU”。
19用拉斯克的话说,这是一个已内在于逻各斯的原型意义对主体来说“成了内在的”的过程(LU,414页)。虽然海德格尔称赞拉斯克关于判断的书“对范畴理论而言甚至比他的《哲学的逻辑》的意义更为重大。”(《全集》1卷407页),虽然在其博士论文中他使用了拉斯克的“元语法的主谓理论”(《全集》1卷177-181页;以及1912年的《全集》1卷32页以下),但是与“成为内在的”这种观念相对的“先验性”观念,使得拉斯克不可能对对象和判断之间的关联进行意向行为的探讨。而且,如下面的第4节所要讲的,正是从这里海德格尔转向了现象学。
20所引段落是拉斯克的(LU,425页),而且他是与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意义概念明显相对地引入它们的。对拉斯克的先验性概念的进一步探讨,参见克洛维尔的《胡塞尔、拉斯克》,前面所引书的第73-78页。对拉斯克来说,先验逻辑是一种关于“未被任何主体性触及过的”对象的逻辑,然而由于认知“原罪”,这种对象是一个“失乐园”(LU,426页)。
21这一短语预示着作为“形式显示”概念的范畴观念,这些概念“以一种特殊方式来解释现象”(《全集》61卷86页),它们是海德格尔在1921/22年的冬季学期引入的。在此,范畴“在生活自身中生活”,是“生活在其中通达自身的”突出方式(《全集》61卷88页)。
22对此的一些讨论,参见R·M·斯特瓦尔特(RoderickM.Stewart)的“海德格尔《教职论文》中的意义和激进的主体性”,载《人与世界》12期(1979)360-386页;及约翰·卡普托(JohnKaputo)的“现象学、神秘主义和思辩语法:海德格尔《教职论文》研究”,载《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5期(1974)101-107页。在即将出版的论文“1919年战争应急时期讲课: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突破”中,西奥多·克兹尔对斯特瓦尔特和卡普托对样式(modi)所做的处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批判性校正。也可参见西奥多·克兹尔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起源》(Berkeley/LosAngeles/London: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的第31页及第515页以下。
23这与海德格尔如下的论断有关:在对其“作为问题的问题”,及对“解决它们的方式和可能性”的“反思”这种“现代的”意义上,中世纪思想“显示出缺少方法论的自我意识”。一句话,“在现代的意义上,中世纪的人不是凭其自身的(beisichselbst)”(《全集》1卷199页)。据海德格尔说,这并非毫无益处,因为它排除了心理主义的错误,但是它也导致了上面提到的“精确的[即逻辑上充分的]主体概念”的缺乏。
24海德格尔在1912年的论实在性问题的文章中研究过这些问题(《全集》1卷1-15页,尤其是13-15页),这也是他在“结论”中所做的简短注解的背景。
25最后,海德格尔抛弃了批判的——或“科学的”——实在论,因为它摧毁了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区分。根据屈尔佩“自然主义的”观点(如在其1902年的《今日德国哲学》中),最终只有通过一种“归纳的形而上学”知识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种形而上学将关于主体的科学(心理学)和关于客体的科学(物理学)的成就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早在1912年海德格尔就发现,这种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假设的”特征是要不得的(《全集》1卷15页)。
26例如,在1925年的夏季学期,海德格尔将范畴直观视为现象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全集》20卷63页以下)。而且在1973年的查林根(Z?hrigen)研讨班上的报告表明,海德格尔把范畴直观概念看作“胡塞尔思想的闪光点”。参见《四个研讨班》,由库尔得·奥克瓦特(CurdOchwadt)译自法国研讨班的草稿(Frankfurt:Klostermann,1977,111)。
27在1921-22年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自己研究了形式/质料二元分立的“价值和局限性”,最后告诫说:“最好是把形式概念与范畴概念分开”(《全集》1卷86页)。这一结论是已蕴含在作为“质料”的意蕴关联的范畴形式这一观念之中。
28这一问题最终在海德格尔的“事实性的解释学”中得以阐明。参见西奥多·克兹尔的“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的‘实际性’概念领域的起源”,载《狄尔泰年鉴》,前面所引书的第91-120页。我只想补充说,这种解释学依然明显地被理解作先验哲学。以此观点对《存在与时间》的一种解释,可以在卡尔-弗里德里希·格特曼(Carl-FriederichGethmann)的《理解与解释》(Bonn:BouvierVerlag,1974)一书中找到。
逻辑真理范文篇9
[关键词]主谓项逻辑学泛逻辑主义定义理论命题理论
莱布尼兹是近代普遍语言计划的真正实施者,他不但用符号化的方式重新表述了形式逻辑的三大,而且提出了逻辑演算的七条公理,从而开始了逻辑数学化的工作。[1—S.205]他继亚里斯多德之后对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首次提出了二者在根本上一致的思想。他对概念、定义、命题的论述,对逻辑的有激励作用,他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成了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莱布尼兹的逻辑哲学观。
一、逻辑学对形而上学的意义
自亚里斯多德以来,逻辑学便与形而上学、认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形而上学一直被视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被视为追求世界的第一原理和最终根据的学问,而逻辑学一向被看作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学问。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折不仅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内在联系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且扩大了两者的论域和视野。在十七世纪哲学家中,莱布尼兹最为明确,最为完整地表述了逻辑哲学的基本思想。在他那里,逻辑既是理智的伟大工具,又是表达哲学真理的根本,也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因为在他看来,“通过理智创造的一切可以通过完善的逻辑规则创造出来”。[2—S.523]莱布尼兹试图通过确立逻辑理性的价值把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因为他发现哲学缺乏一种明晰性和确实性。因此,他希望对哲学进行逻辑化改造从而使哲学概念、命题和推理具有确实性。在《人类理智新论》中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哲学的功用,就是造成一些语词,以求给人确切的概念,并求其在一般命题中表达确定的真理。”[3—p375]
按莱布尼兹的分类观念,对所有学说的真理有两种主要处理方法,每种处理方法各有所重,各有其价值和意义,但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因为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两种方法分别是综合方法(也称理论方法)和分析方法(也称实践方法)。综合方法或理论方法是将真理按照证明的顺序加以排列。就像数学证明一样,把每个命题放在作为前提的命题之后。这样一来,所有表示真理的命题就会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分析方法或实践方法是从人的目的开始,从善开始,从善的最高点即人的幸福开始,然后过渡到实现善(或避免善的反面即恶)的各种特殊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分析方法是从目的过渡到手段,从抽象进入到特殊,或从一般下降到个别。莱布尼兹认为,除上述两种处理方法,我们还可以补充第三种方法,即,一种按名词来安排真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索引方法,莱布尼兹将它用于图书分类和编目。莱布尼兹说,第三种方法相当于古代的逻辑学方法,因为它是按一定的逻辑的范畴来处理知识和真理,其中既涉及对种和属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涉及对范畴的逻辑外延和内涵的界定。上述分类法与古希腊人的科学分类法是一致的。因为古希腊人将哲学或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伦理的知识三大类。理论的知识相当于莱布尼兹在这里所说的综合法,实践的知识相当于分析法,按名词来安排真理的方法则相当于逻辑学。
随着莱布尼兹的思想趋于成熟,他对逻辑学愈加重视。他说:“至于逻辑学,是教人以思想的条理和联系的技术,我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加以责备。相反,倒是缺乏逻辑才使人们弄错。”[3—p639]他不仅大大扩展了逻辑学的范围,而且力图从命题的逻辑分析入手重建形而上学。为此,他既需要重新审视并确立形而上学的逻辑前提,又需要建立一套可靠的逻辑方法以便发现和表达确定的真理。根据罗素的看法,莱布尼兹哲学的主要前提有五个:
(1)每个命题都有一个主项和谓项;
(2)一个主项可以具有若干个关于存在于不同时间的性质的谓项;
(3)凡不断言处于特定时间的存在的真命题是必然的和分析的,而那些断言处于特定时间的存在的命题则是偶然的,后者依赖于终极因;
(4)自我是一个实体;
(5)知觉产生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我自己以及我的状态之外的存在物的知识。
显而易见,这五个前提中的前三个均与逻辑学有关。第四个前提是莱布尼兹认识论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但这个前提也间接地与逻辑学相关。正如罗素所说,“实体概念如我们将会明白的,是由主项和谓项的逻辑概念派生出来的。”[4-p13]如果说实体概念是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那么,主谓项的逻辑概念对其形而上学的奠基作用也就不言自明了。正因如此,罗素断言“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是从他的主谓项逻辑学推演出来的。”[4—第二版序言]他甚至断言,“莱布尼兹的哲学差不多完全源于他的逻辑学。”[4—第二版序言]
然而,罗素的第二个断语过于夸大了逻辑学在莱布尼兹哲学中的作用,他所做的解释明显地带有从他自身哲学立场出发的泛逻辑主义色彩。我们且不说他的这一断语如何与他提到的第五个前提相矛盾,单是莱布尼兹的哲学和认识论就无法按其逻辑学来解释。况且,莱布尼兹对两重真理,即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的区分决定了他无法用纯逻辑的方式来处理偶然真理的,因为偶然真理的发现是离不开经验观察的。在此,我们暂不细究这个问题,我们仅仅研究莱布尼兹的逻辑学究竟对形而上学贡献了什么。
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在莱布尼兹看来“真正的形而上学很少不同于真正的逻辑学,即一般发明的技术。”[5—p10,12,1]要理解莱布尼兹的这一观点,就必须了解他对形而上学的规定。从渊源看,他对形而上学的规定主要受苏阿勒兹(Suarez)和魏格尔(E.Weigel)的。前者使他认识到形而上学是关于实在存在的学问,而实在存在的标志是其可理解性。实在存在既包括有限的东西,也包括无限的东西;既指物质性的东西也指非物质性的东西,既指实体性的东西也指偶性的东西。总之,形而上学是探讨上帝及其创造物的学问。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论》的结构就反映了他对形而上学的这种理解。莱布尼兹在耶拿时的老师魏格尔则让他认识到形而上学可以成为一门类似数学证明的学问,逻辑与数学的结合将使形而上学概念的定义获得一种精确性,而形而上学命题的证明也会因此获得确实性。由于这种影响,莱布尼兹终身保持着对形而上学的这种信念。
在苏阿勒兹和魏格尔的影响下莱布尼兹是怎样规定形而上学的呢?他在不同地方对形而上学进行过不同的定义。比如,他时而说形而上学是“关于可理解事物的科学”[6—p348],时而说形而上学是“以存在,因而也以存在的根源,即上帝为对象的科学”[7—S.227],时而又说形而上学是关于以理性为基础并为经验所证明的一般真理的科学。他还说形而上学是使用充足理由原则讨论事物的原因的科学。从他的《形而上学论》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上述形而上学规定本质上是一致的。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是万物的最终根源,上帝的智慧是最高智慧,上帝通过给万物赋予秩序,给宇宙赋予和谐来体现这种智慧。因此,形而上学的探讨必须从上帝开始。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寻找终极因的解释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可以从世界的一般结构中,从自然的构造中,从一般运动的规律中发现上帝的智慧,形而上学的探讨必须从上帝、从万物的终极因和充足理由过渡到有形自然的一般原理,过渡到人的理智和一般观念。莱布尼兹把这种解释方法称为寻找动力因的解释方法,并认为形而上学需要把这两种解释方法结合起来。他的《形而上学论》和《单子论》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两种解释方法。
作为探讨可以理解的事物的科学,形而上学也是关于存在及其可能性的科学,因为按莱布尼兹的理解,存在的实在性及其根据潜存于上帝的理智中。因此,诚如鲁特福德(DonaldRutherford)所说,“就形而上学是关于可理解事物的科学而言,它也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和关于神的理智的科学。在形成形而上学知识对象的可理解的概念中首要的概念是实体概念或自我持存的存在物的概念。因此,关于一般实体的真理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核心部分,最后,就形而上学指在获得有关存在物的本性的完整知识而言,它旨在获得足以解释为什么每个事物是现在这个样子的知识。所以,形而上学与充足理由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8—p71]”
实质上,充足理由原则不仅是莱布尼兹的逻辑原则而且是他的形而上学原则,他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一致性首先体现在这里。按莱布尼兹的理解,形而上学就方法而言也是一门证明的科学,而证明均离不开逻辑推理。莱布尼兹在《单子论》中给推理确定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同一原则或矛盾原则,二是充足理由原则,用莱布尼兹本人的话说:“
我们的推理是建立在两个大原则上,即(1)矛盾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我们判定包含矛盾者为假,与假的相对立或相矛盾者为真。
(2)充足理由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我们认为: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7—s.612]
不管今天的逻辑学家是否把充足理由原则作为一条逻辑原则,它被莱布尼兹作为逻辑原则使用却是无可置疑的,它对其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也是无可置疑的。没有这条原则,他在《形而上学论》中描述的两种解释方法,即寻求终极因和动力因的方法就无法得到说明,因为如前所述,形而上学探讨存在的本质及其最终根源,而存在的东西及其本质之所以被称为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恰恰在于它根植于上帝的理智的实在性。所以,莱布尼兹说,“这些本质和关于这些本质的永恒真理都不是虚构的,相反,它们存在于观念的某一领域,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它们存在于上帝本身那里,上帝则是所有本质的根源。”[7—B.Ⅶ.s305]以存在及其根据为对象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要涉及上帝,就是因为充足理由原则要求它这样做。至于矛盾原则,即便是初步接触形而上学的人也无法否认它是形而上学研究必须遵守的一条思维原则。
逻辑学对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为形而上学推理和论证提供了基本原则,而且在于它的命题理论为揭示形而上学真理提供了基本定向。莱布尼兹虽然没有建立首先由布尔开创的现代意义上的命题逻辑,但他已初步区分了命题与陈述,陈述之真与事实之真。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被称为主谓词原则。莱布尼兹对它的表述是:“真理的根据在于谓词与主词的联系,即谓词包含在主词中”[5—p11]。根据这条原则,在任何由主谓词构成的命题中,谓词表达的概念总是包含在主词包含的概念中,否则这一命题就不是一个真命题。众所周知,这样的命题在康德那里被称为分析命题并成为他的形而上学讨论的基本因素。这一原则在莱布尼兹那里虽然不一定像罗素断言的那样确保了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是从他的主—谓项逻辑学推演出来,但它的确有利于莱布尼兹把形而上学体系看作一种从少数原理演绎出来的体系,也有利于莱布尼兹说明为何寻求某个事物的理由也就意味着在逻辑形式上肯定某谓词是对特定主词有所断定。当然,由于莱布尼兹除了承认必然真理外还承认偶然真理,除承认必然命题外还承认偶然命题,在形而上学中能否将上述逻辑原则贯彻到底对莱布尼兹来说仍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逻辑学对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的定义理论方面。形而上学是用概念和范畴来表达的,但概念的内涵要通过定义来阐述。莱布尼兹继承了中世纪的做法,区分了名义定义和实在定义。当对一种定义的确切观念是否可能尚有疑问时,这种定义就是名义定义。反之,则是实在定义。对定义莱布尼兹做过许多阐述。他说:“本质归根到底不过是人们所提出的东西的可能性。被人们认为可能的东西是用定义来表示的。当这种定义不能同时表明可能性时,它就只是名义上的,因为那时人们就可以怀疑这种定义是否表明某种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可能的东西,除非那个事物在世界上现实地存在时我们借经验之助后天地认识了这种实在性。”[3—p318]
莱布尼兹将本质和定义区别开来,并认为名义定义只能触及事物的可感性质,而实在定义则要触及事物的本质和内部构造。本质只有一个,定义则可以有多个,就像同一结构或同一城市可以从不同角度或用不同景色的画面去表现一样。虽然对实体进行实在定义比较困难,但形而上学能够给真正的实体以定义,甚至在数学中,同一样式既可以有名义定义也可以有实在定义。实在定义对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在于:形而上学的概念多半是涉及存在物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某物是一个存在者,但不必断定它有现实的存在;实在定义则使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存在者的同一性,并对真正的实在性有所断定。此外,实在定义有利于我们追溯事物的根据并最终确定神的理智与人的理智的一致性。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在莱布尼兹眼里就根植于这种一致性中。
总之,在莱布尼兹那里,逻辑学为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也为形而上学预设了一些理论界限;逻辑学为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些分析的工具和手段,也为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些概念框架;逻辑学为形而上学树立了某种确定性的理想和模式,也为形而上学阐述了某些思维规则。但是,莱布尼兹并非罗素所说的那种泛逻辑主义者。他对逻辑学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即便他试图建立一个符合逻辑规则的形式化的普遍科学体系,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他的过于宏大的计划,使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他的兴趣广泛而多变,他有着发散型的思维方式,他热衷于活动并希望通过结交名流显贵来实现自己的抱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由于精力过于分散,他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学术的黄金岁月沉下心来像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那样一步一步地从一些基本前提出发合乎逻辑地推演出自己的体系。无论是他生前发表的唯一完整的著作《神正论》,还是后来出版的《形而上学论》和《人类理智新论》,就结构的严整性而言,都远远不能与斯宾诺莎的《伦》相提并论。他给后人留下了15000余封信和大量未刊手稿。但他一直没有建立一种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所以,虽然他比他的先驱和同人更加重视逻辑学并且设想依据少数公理和逻辑规则建立一套哲学体系,但他仅仅描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认他在逻辑哲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莱布尼兹的逻辑哲学思想的新颖性与超前性。
二、概念与定义理论
概念既有逻辑学的意义也有哲学的意义,因此,它既是逻辑学的对象也是哲学的对象。唯其如此,人们既可以从逻辑学的角度去分析哲学意义的概念也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去审视逻辑学意义上的概念。这一点决定了概念理论的两种向度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他在重视范畴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在《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这些逻辑学著作(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们当作哲学著作来读)中辟专章来讨论概念问题,而是在《形而上学》和其他地方偶尔提及概念的涵义和划分问题。另一方面,亚里斯多德又恰恰是在那些最有哲学味的著作中指出了概念的某些逻辑特点,如,概念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概念本身并不断定;“亚里斯多德关于种、属、实体等论述,实际是揭示概念种类的包含关系,以及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9—p24]
莱布尼兹的概念理论在继承亚里斯多德的上述特点的同时也将他未曾发挥的一些萌芽性思想充分揭示出来。他既继承了亚里斯多德有时将概念与定义混淆不分的缺点,也在中世纪唯名论的影响和他同时代人的激励下开始考虑概念的形式化问题。莱布尼兹不但对定义作了定义和分类,从而将定义的不同形式明确地区分开来,而且已经发现了概念的合取和析取,与数值的加法和乘法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之处。此外,莱布尼兹还讨论了概念的内涵、意义与同一性问题,并试图区分外延与内涵。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外延问题深入讨论,这使他没能建立外延逻辑,因而也无法完成建立逻辑演算系统的设想。但随着内涵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莱布尼兹对概念内涵的一些看法重新显示出它的启发意义。刘易斯(C.I.Lewis)对量化的模态逻辑的研究,卡尔纳普(R·Carnap)对模态逻辑的语义分析,克里普克(S.Kripke)对命名与必然性问题的探讨,辛提加(J.Hintikke)对模态性模型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莱布尼兹的概念理论。因篇幅所限,对这些问题此处不予讨论。
莱布尼兹认为,概念是组成命题的基本要素,命题则是概念的复合。因此,对命题的逻辑分析必须从概念开始。莱布尼兹在不同地方对概念有不同称呼。正如前一章谈到的那样,他将概念有时称为“观念”,有时称为“项”,有时称为名称表示的东西,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指”或“被指称者”。概念当然要用名称来表达,但概念并不等于名称,广而言之,概念可以用语言实体表达,但不同于语言实体本身。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表达式来表示,但它靠什么来保证它的同一性呢?
莱布尼兹认为概念的同一性是由概念的内涵的同一性来保证的。对许多人来说,“三角形”与“三边形”仿佛是两个不同的意义,但这两个表达式表示同一个东西,菜布尼兹用A∞B这一符号表示两者的同一性。用他自己的话讲,“A∞B意味着A与B是同一的,或者,一个可以随时替代另一个。”[6—p261]为防止误解,莱布尼兹在其他地方还特意补充说,两个项的相互代替只有在不丧失真值的情况下才是同一的。这条原则被许多人称为“概念的同一性原则”,也有人(如Hidelshiguro)把它称为“不失真值的替代性原则”①这条原则也是莱布尼兹的逻辑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对它的确切表述是:
“A与B相同意味着在任何命题中一个可以代替另一个而不失真值”。或者,“‘三角形’与‘三边形’,‘四角形’与‘四边形’这样一些概念是相同的,其中的一个可以代替另一个而不失真值。”②
“真值”概念和“概念的同一性”原则的引入对莱布尼兹的逻辑哲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直接决定了他对逻辑命题的建设性讨论。概念的真值决定着概念的恒常性、不变性。概念的同一是保持思想同一的先决条件。莱布尼兹所说的概念是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因此也不同于接下来被心理主义者归结为心理过程的那种概念。他说,“至于(notion)这个名词,许多人是把它用于所有各种观念或想法(conceptions)的,既用于根本的,也用于派生的”[3—p213]。但莱布尼兹之所以对概念与观念不加分别地使用,并不是因为他把概念等同于心灵的变动不居的印象,也不是因为他把概念等同于心灵活动。概念无疑与心灵活动相关,因为它既是思想的对象也包含一定的思想内容,但它绝不是随意的,概念是用表达式固定下来的东西,它表征事物的整体或事物的本质和性质。当一个概念能使我们认识到它所描述的事物时,这个概念就是清楚的;反之,当一个概念不能使我们认识到它所描述的事物或将此一事物与彼一事物区分开来时,这个概念就是不清楚的。
概念的意义是实在的,它本身已经包含本质的知识。比如,“三角形”的概念就包含着不同于“四边形”的本质并且包含“三内角和等于180°”的知识。当我们说“每个人都是动物”时,“动物”这个概念实际上适用于每个人,但我们不能说“每个动物皆是人”。在这里,莱布尼兹实际上已经触及概念的外延问题。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兹认为概念涉及可能性,甚至断言,“如果一个概念是可能的,它也是真的,如果这个概念包含矛盾,它就是假的”[10—s.31]。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认为命题有真假问题,概念也有真假问题,而概念真假的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包含矛盾。
如果根据有无矛盾来判断概念的真假,这种概念显然是逻辑学意义上的概念。如果我们说“所有人都有一个上帝的概念”,这里的“上帝”概念在莱布尼兹看来就是一个涉及必然真理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叫天赋观念;“如果这概念是指一种人们实际想到的观念,那它就是一个事实的命题,是有赖于人类的历史的”[3—p503~504]。从这里我们看到莱布尼兹并未把概念与命题区分清楚,而是把它们混为一谈。这一方面表明,他无法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概念与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分开,另一方面表明他隐约看到了概念的意义要通过命题来展开。后一点从他的定义理论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定义是使概念明晰的逻辑工具。对莱布尼兹来说,凡复合的概念或观念都是可以定义的(他有时将“可定义”与“可分解”当同义词使用)。“对一些单纯的观念,我们是不能给它们定义的;也有一些公理和公设,总之,有一些原始的原则,是不能够证明的,也不需要证明,这就是‘同一陈述’,其反面包含着显然的矛盾。”[11—p297]按照莱尔尼兹对定义所下的定义,“所谓定义不是别的,无非是把那些观念清楚地揭示出来。”[3—p70]因此,说一些单纯概念或观念不可定义可以避免逻辑矛盾,因为如果那些单纯的概念可下定义就意味着它不再是单纯的。另外,自然的秩序是从最单纯的东西开始的。既然自然的本性与心灵的本性一致,那么,与此相应,为了寻找知识的基础,我们可以采用分析的方法由复合的概念追溯到单纯的概念。“数学家就是这样用分析法把思辨的定理和实践的法则归结成定义、公理和公设。”[11—p297]定义的目的也就是要“得到那些同一的或直接的公理”。这一点也说明定义不是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是随意的。
莱布尼兹对定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定义的同一关系与命题的主谓式包含关系统一起来并试图加以形式化。他相信,如果有人试图用数学的方式来写形而上学或伦理学的作品,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这样做。他本人在讨论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神学问题时就常常喜欢给出一些定义。这些定义有可能是名义定义,也可能是实在定义(也叫原因定义),还可能既是名义定义又是实在定义。
区分名义定义与实在定义尽管不是莱布尼兹的首创,而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贡献,但对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学都非常重要。他在《人类理智新论》、《形而上学论》以及一些短文和通信中反复提到这两种定义的区别。1684年,莱布尼兹在题为“对知识、真理与观念的沉思”(Meditationesdecognitione,veritateetideis)的文章中对名义定义与实在定义做了最为明确的区分。他写道:“于是,我们具有将名义定义与实在定义区分开来的界限,名义定义只包含将一物与他物区别开来的标志,而根据实在定义我们可以确定事物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以某种别的方式确定被定义的东西是可能的,那么,名义定义对完满的知识来说是不够的。”[7—B.Ⅵ.s424]简单地说,名义定义不表明事物的可能性,实在定义则表明事物的可能性,简单的名词不能有名义定义,但可以有实在定义,以便说明其原因。仅根据名义定义去获取知识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它无法保证我们的知识的确定性,也无法让我们获得必然的真理。正因如此,莱布尼兹说,“将名义定义与实在定义区分开来也很不错。如果人们仍然怀疑被定义的概念是否可能,我就将它称为名义定义……只要人们仅有名义定义,他们就不能确认从中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它隐含着矛盾或不可能性,他们就会从中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真理并不取决于名称并且不像少数哲学家相信的那样是任意的。”[10—s.206~207]
莱布尼兹还提出了“因果定义”和“本质定义”的概念,以便对实在定义进行补充说明并区分实在定义的不同情形。当被定义的概念的可能性仅由经验来证实时,这种定义就只是单纯的实在定义,当我们可以先天地证明其可能性时,这个定义既是实在定义又是因果定义;当定义可以使我们揭示最原始的概念,而又不需要先天地证明其可能性时,这种定义就是本质定义,在所有定义中,这是最完满的定义。针对亚里斯多德在《论题篇》(Topica,亦译《正位篇》)中提出的“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莱布尼兹在肯定其优越性的同时也指出定义的方法应该有多种,而且“种”与“属差”不一定非得用一个词表示,而可以用多个词表示。比如,我们可以把人定义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也可以定义为“一种动物性的理性之物”。此外,“种”与“属差”是可以互换的,互换的方式取决于细分类的秩序变化。
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莱布尼兹试图突破传统逻辑学的定义框架并指出了定义的多种可能性。对名义定义与实在定义的区分及其,与其说具有逻辑学意义,还不如说更富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因为它们不但涉及概念的语词表达及其逻辑结构,而且涉及事物的可能性,涉及概念的实在性,甚至涉及经验。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定义理论与命题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很快发现,他的定义理论与命题理论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三、命题
如上所述,莱布尼兹曾将真理性归之于概念,认为概念也有真假。他接下来解释说,他实际上是把概念的真理性理解为断定概念对象的可能性的那些命题的真理性,因为概念是隐含的命题,命题是展开了的概念。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概念与命题的逻辑关联。
在命题的方面,莱布尼兹所取得的成就虽然不能与后来的德摩根、布尔、皮耳士和罗素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但他仍在某些方面做了对后人具有启迪意义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1.对命题做了比较细致的分类;2.对主谓式命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3.考察了命题的真值条件;4.初步涉猎了关系命题。
莱布尼兹根据不同的标准或者说不同的角度对命题作了区分。有些区分对逻辑学意义更大,有些区分对的重要性大于对逻辑学的重要性。
与区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相适应,莱布尼兹区分了必然命题与偶然命题,前一种命题表述必然真理,后一种命题表述偶然真理或事实真理。前者,如“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三角形有三条边”等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必然性,它们的逻辑特性是不包含矛盾。对这类命题,我们可以采用法找出它们的理由,把它们分为更简单的概念和公理,直至不能再分。所有公理都是用那些最简单的无矛盾的命题来表述的,莱布尼兹把它称为“同一性命题”。这种命题的特点是原始性、自明性、无矛盾性,且在认识上与直觉相关,它不需要逻辑证明,也不能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有点类似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原子命题。对一个演绎推理的体系而言,作为公理的同一性命题越少越好,其他的复合命题无非是根据少数同一性命题推演出来的。偶然命题也叫存在命题或事实命题。如“那个人很高”,“在有个康熙皇帝”等等。莱布尼兹认为它与感觉经验相关,它只表达了偶然真理。“所有偶然命题都有它们是这样而非那样的理由,或具有涉及其真理性的确实的先天证明,并表明某些命题中的主项与谓项的联系是基于这件事或那件事的本性。但它们没有必然的证明,因为那些理由仅依据偶然性原则,或有关事物的存在的原则。”[7—B.Ⅵ.s438]
莱布尼兹的逻辑哲学主要关注的是必然命题而不是偶然命题。他的组合术实际上是把经验的偶然命题排除在外的,因为他认为像“奥古斯都(Augustus)是罗马皇帝”,“所有欧洲人都有上帝观念”这类命题是要靠经验归纳才能证明的命题。莱布尼兹接受了“直言命题”、“模态命题”、“假言命题”、“析取命题”这样一些命题分类。1679年,他写过一篇题为“演算初阶”(ElementaCalculi)的论文。这篇论文把“直言命题”看作最基本命题,并认为所有其他类型的命题是以直言命题为基础的。他写道:“如果不另作说明,我所说的命题是指直言命题,直言命题是其他命题的基础,模态命题、假言命题和析取命题都是以直言命题为前提的。”[6—p49]就拿直言命题与假言命题的关系来说,两者具有同样的真值条件。虽然从形式上看,一个可以表述为“S是P”,另一个可以表述为“如果P,那么Q”,但它们都可以根据概念的包含关系来说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P代表的概念包含在S代表的概念中,“S是P”就是真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P代表的命题所涉及的概念包含“Q”指代的概念,那么,这个命题便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
与区分必然命题与偶然命题相联系,莱布尼兹实际上也区分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在莱布尼兹那里,分析命题是必然命题,综合命题都是偶然命题。分析命题是谓项包含在主项中的命题。凡断定存在的命题(除“上帝存在”这一命题外)都是偶然命题。正如罗素在分析莱布尼兹的哲学前提时曾经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莱布尼兹试图把一切命题还原为主谓项命题,在关于存在(不问是表示现实存在还是关于可能存在)的命题中,“存在”本身即是谓项。但每个主项可以有若干个谓项,尽管这个主项有时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别的主项的谓项。对命题的性质的考察和分类可以依据主谓来进行。罗素的下面这段话是对莱布尼兹的主谓式命题的最好不过的:“每一个命题最终都可以还原为把一个谓项归属于一个主项的命题。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命题里除非存在本身是所考察的谓项,谓项都以某种形式包含在这个主项里。这个主项是由它的谓项来界定的,如果这些谓项不同,则它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主项,对主谓项的每一个真判断都是分析的;也就是说,谓项构成了这个主项的概念的一部分,只要不是在断言现实存在,情况就必然如此。”[4—p10]
莱布尼兹非常重视命题中的概念包含关系,因为在他眼里,命题是复合的概念。如果我们说A包含B,那么,谓项B就是对A的普遍肯定。比如说,“贤人包含公正的人”这个命题也意味着说“每个贤人都是公正的”。莱布尼兹所说的谓项不仅指单一的现实的谓项,而且指一切的谓项,凡真的命题都表述了一个或多个谓项与一个主项的关系,这种关系确定了命题的真值条件。当我们面对两个命题时,如果一个命题可以替代另一个命题而又不丧失其真值,那么,这两个命题便是一致的。但命题的这种一致性或同一性归根到底是由概念的同一性来保证的。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莱布尼兹对关系命题的初步探讨。由于莱布尼兹非常强调思想与世界的一致性,命题作为思想的逻辑表达也要体现这种一致性。从形而上学的眼光看,莱布尼兹似乎认为关系是实在的,其实在性来自最高理性。关系具有某种理性的本质,它们存在于事物本身中,是主体的某种偶性(他对偶性一词的用法与十七世纪许多人对此词的用法不同)。莱布尼兹对关系的重视不下于亚里斯多德。“关系”在亚里斯多德的《范畴篇》中与“数量”、“性质”、“位置”等并列的九个次范畴之一,莱布尼兹则在《人类理智新论》中专门阐述了关系问题。由于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实在的联系,人们关于关系的观念以及体现这种观念的关系命题自然要受到应有的重视。莱布尼兹把关系分为“比较”和“协同”两种,前者涉及“相合”与“不相合两种情形(如,相等,不等,相似等),后者涉及某种联结(如,因果,秩序、处境等)。
逻辑真理范文篇10
关键词:思辨;客观思想;现实思想;自由;权利;黑格尔;哲学体系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贺麟成立“西洋哲学编译会”,准备重点翻译黑格尔哲学著作。1955年西洋哲学编译会不复存在,黑格尔哲学翻译工作却全面展开,及至1980年代,黑格尔大部分重要著作已被译成了中文。黑格尔研究在我国西方哲学学科中资料准备最早,基础最好,成果最多。奇怪的是,此后黑格尔研究没有充分和深入地发展。1980年左右,国内哲学界出现了“回到康德还是黑格尔”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未充分讨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的情绪和意见。流行的意见似乎是,黑格尔语言晦涩难懂,但思想易于掌握,无非只是“辩证法三大规律”,而康德体系思想大有深究之处,且可与现代西方哲学直接联通。这种意见有意无意地助长了“扬康抑黑”的情绪。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有讨论的必要。我的看法有四点:第一,没有必要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第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和黑格尔犹如比肩耸立的双峰;第三,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力依思潮和流派的不同而不同,并且两者在19—20世纪已成为历久弥新的两大独立传统,不能一概而论谁的影响更大或谁更重要;第四,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黑格尔哲学更值得研究。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逻辑严缜细密,可加以精简呈现。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黑格尔哲学体系,那就是“精神”。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把精神提高到自由与真理,乃是更高的逻辑事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很多词汇,如“辩证法”、“理念”、“异化”、“扬弃”、“反思”、“发展”等等,都是阐明论述精神的真理和自由的黑格尔逻辑术语,这些词汇通过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日常生活。诚如黑格尔所说,人们熟悉不一定是真知①。要获得对黑格尔哲学的真知,我们需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以及为什么是一个精神世界?真理是不是客观的,有没有绝对真理?我们所处的时代精神是不是以及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由?通过阅读黑格尔,我们今天仍能获得一些真知灼见。
一、精神
康德首先发动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让客体围绕主体转。主体是什么?康德写了三大批判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把人的能力区分为认知、意欲和情感。在认知领域,人的知性主体能动地为自然立法,但只能根据被给予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的结合去认识经验现象;在意欲领域,人的纯粹理性主体为自己立法,道德自律是理性实践的事实和目的;在情感领域,人的判断力主体或鉴赏大自然的美和崇高,或把人类自由和尊严判断为自然界的终极目的。黑格尔不满意康德条分缕析的区分,他用“精神”的概念统摄康德在各个领域规定的主体性。在西方哲学史上,阿那克萨戈拉首先把“努斯”(Nous)当作世界本原,黑格尔说,Nous表明了精神的准确意义②。但是,柏拉图把Nous当作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相分离。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把精神等同于上帝,与世俗世界相对立。黑格尔用“精神”跨越神圣与世俗的鸿沟,打破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物自体与现象界的隔离,克服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为了适应当时的流行文化,黑格尔经常把“上帝”作为绝对精神的代名词,不能因此说黑格尔企图“为神代言”。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申明,上帝的生命和活动不是“自娱自乐的爱”,而是充满着“否定性的严肃、痛苦、忍耐和劳作”;在《小逻辑》中说,“我们不可以离开精神和真理去崇拜上帝”,“精神的内容,上帝本身,只有在思维中,或作为思维时,才有其真理性”③。可以说,精神是人类把握自然和自身的曲折反复的思维活动,也是在分裂苦难中不断创造更好的社会和生活的“客观思想”。如果看不到黑格尔几乎在每本著作中都强调精神与人类思维的同一性,那么“上帝是精神”的命题或被理解为泛神论,或被理解为正统神学的理性化。这两类理解曾经造成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不足为训。一些英美哲学家把黑格尔的“精神”理解为“用上帝的观点看”,不过是在重复此类错误。当黑格尔用“纯概念”“理念”“思维纯形式”“思辨思维”等概念表述“精神”实质时,他不是在一味拔高,更不是“绝对唯心论的呓语”。如果认真聆听黑格尔,就不难理解黑格尔如是说的理由、论证和客观依据。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是把握人类知情意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说,精神“渗透了人的一切自然行为,如感觉、直观、欲望、需要、冲动等,并从而使自然行为在根本上成为人的东西,成为观念和目的,即使这仅仅是形式的”④。这里所说的“形式”指把握知情意的自然行为的方式,即思维的概念活动。如果说贯穿知情意的概念活动把人与动物分开,那么精神的最高对象是依据思维的原则来把握思想自身。黑格尔把表象、经验和思辨作为精神三个层次,说明了内在于它们之中的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一)表象
在日常生活中,人类语言的特点就是用普通概念或共相把握千差万别的感性对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凡语言所说出的,没有不是具有普遍性的”⑤。语言可谓人类的第二本能,“百姓日用而不知”。黑格尔称日常语言中的概念和概念关系是不自觉的“自然逻辑”⑥,思维“沉没在只知道自己的直观、表象以及我们的欲望和意愿之内”⑦。康德曾把拉丁文的“表象”(repraesentatio)当作一般的认识论概念,包括知觉、感觉、认识、直观、知性概念(思想)和理性概念(理念)①。黑格尔则说:“我们所意识到的情绪、直观、欲望、意志等规定,一般被称为表象(vorstellung)。”②相比而言,黑格尔既把表象限定在感性认识范围之内,又把表象扩大到情绪和意欲范围,他的理由是:“没有人的欲望和意愿是没有表象的。”③
(二)反思
被译作“反思”的黑格尔术语有两个:一是Nachdenken,意思是“后思”和“反复思索”;另一个是Reflex-ions,意思是“映射”,即《逻辑学》的“本质论”中两两相对范畴的相互映射。前者表示较为宽泛的精神。通过对沉没在表象中的普通概念的反复思索,精神提炼出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意义更加普遍、关系更加准确的概念。这类概念有两种:一是近代经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普遍概念,二是理智或知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适用于经验对象,二是可用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推导一般法则。黑格尔称赞康德在经验和普通逻辑中发现了纯概念,即知性范畴,提出了超越普通逻辑的先验逻辑。但是,无论经验科学、传统的理智主义,还是康德的知性范畴,都只能适用于经验对象,而不能说明内容是无限的理性对象。康德认识到知性范畴运用于灵魂、世界和上帝等理性对象,必然引起矛盾,这本是康德优越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高明之处,但他把辩证的矛盾当作认识理性对象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以为这些理性对象是不可知的物自体。黑格尔认为,康德正确看到了现象界之外还有更高的领域,但他错误地宣布这一领域不可知。费希特、谢林和雅可比等后来哲学家认识到、但未能克服这一错误④。
(三)思辨
思辨是以理性对象或纯粹思想为对象的思维活动。黑格尔说:“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思辨的逻辑,包含有以前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保存有同样的思想形式、规律和对象,但同时又用较深广的范畴去发挥和改造它们”⑤。“较深广的范畴”即《逻辑学》中的纯范畴。古希腊哲学家首先把思辨与表象分开,但他们的纯思辨缺乏具体性,“思维停留在理念的普遍性中”,“思维对特殊性采取漠视态度”,如爱里亚派所谓存在和赫拉克利特所谓变易,“自应被指斥为形式主义”⑥。近代经验科学与作为逻辑学的思辨哲学之间有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经验科学为哲学思辨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材料,“哲学的发展实归功于经验科学”;另一方面,思辨哲学“赋予科学内容以最主要的成分:思维的自由(思维的先天因素)”,“又能赋予科学以必然性的保证”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思辨的东西,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又说:“精神是知性的理性或理性的知性,它比知性、理性两者都高。”⑧“比两者都高的思维”的思辨综合了知性的肯定性原则和理性的否定性原则。这种思辨辩证法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改造。他说,康德正确地“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但只是从否定方面看待辩证法,因而得出“理性不能认识理性的东西”的奇怪结论。黑格尔要求“从它的肯定方面来把握”理性对象,即“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尚未经训练的、不自由的思维能力来说,也是最困难的方面”⑨。确实,理解黑格尔的思辨非常困难。“思辨”现在是一个贬义词,含有“否认感觉”、“轻视经验”、“罔顾事实”等含义,这些看法没有看到,黑格尔的思辨是精神贯穿于人类感觉和经验的运动所达到的最高形式,思辨以纯概念形式把握感性的质料和经验的内容。对黑格尔而言,无概念的事物本身没有意义,他说,逻辑思辨的对象“不是事物(dieDinge),而是事情(dieSache),是事物的概念”瑏瑠。通过事物的概念,感性对象和经验事物不但没有丧失其内容,反而在意识中显现出它们的本质和真相。黑格尔哲学根本谈不上是“泛逻辑主义或唯智主义的认识论”。他所批判的“知性思维”恰恰是理智主义(现代西文的“知性”或“领会”Verstehen,understanding,compréhension都来自拉丁文的intellec-tus,即“理智”)。而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超出认识论,涵盖了人类的知情意的内容。对待“泛逻辑主义”的批评,可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回应:“纯概念就是对象的核心和命脉……这个逻辑的本性,鼓舞精神,推动精神,并在精神中起作用,任务就在于使其自觉。”①
二、精神的真理
“真理”是一个崇高的概念,哲学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但是,古往今来也有蔑视、无视和轻视的态度。黑格尔总结了对待真理的错误态度。其一,有权势者对真理弃如敝履,当耶稣说他来是为真理作见证时,审判者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新约•约翰福音》18:38)“他的意思是说”,黑格尔解释道:“他已经看透了真理是什么东西,他已经不愿理会这名词了,并且知道天地间没有关于真理的知识。”其二,普通人以为真理无用,即使为求真理而学哲学和逻辑,“末了又复回到这无常世界的沙岸,与最初离开此沙岸时一样地毫无所谓,毫无所得”。其三,头脑简单、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相信他们一生下来现成地便具有宗教和伦理上的真理”②。最后,黑格尔最为关注的态度是真理不可知论,因为这在哲学内部拆了哲学的台。他归咎于康德知性思维的影响:“它所主张的观点是:真理建立于感性的实在之上,思想只有在感性知觉给与它以内容与实在的意义下,才是思想;而理性,只要它仍然还是自在自为的,便只会产生头脑的幻影。由于理性这样自暴自弃,真理的概念也就跟着丧失了……知识降低为意见。”③黑格尔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康德固然将知识当作主观和客观都充分的真,以区别“主观上的充分性叫作确信,客观上的充分性则叫作确定性”④,但既然他把“知识”限定在现象界,而把理性排除在客观真理之外,那么黑格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康德所说的知识很难与主观确信的意见相区别。黑格尔区分了真理与确定性,认为确定性是主观的,充其量只是“主观真理”,而没有达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关于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论”认为,“我们的表象与一个对象相符合叫做真理”。黑格尔批判说:“这说法预先假定有一个对象,我们的表象应与这对象相符合。”这对象之所以是“预先假定”的,因为它本身也是表象,被规定为一个观念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标准,判断其他表象是否与这个观念的内容相符合。比如,“真朋友”与预先假定的“友谊”观念相符合,“真艺术品”与特定的“好艺术”的观念相符合,“不好政府”与特定的“真政府”的观念相矛盾。黑格尔说,“符合”只是假定了被当作真理标准的观念内容是正确的,但并不能证明这个观念必然为真,“像这类正确的但又是不真的观念,我们脑子里面可以有很多”⑤。这种自以为正确的不真观念其实是表象中的一种思维,不过,这种“思维自诩过高,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工作”,“不但未能认识真理,反而推翻了政府和宗教”;因此,真理观不只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时代精神的现实性问题:“考察思维的本性,维护思维的权能,便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兴趣。”⑥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要求在认识对象之前考察认识能力。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他用“媒介”和“目的”的关系说明认识论哲学的偏差。认识能力的批判本来只是认识真理的手段,最终却成为回避真理的理由,“导致了目的的反面”⑦。与认识论中流行的“符合论”相对立,黑格尔说:“把真理认作自身的符合,构成逻辑学的真正兴趣。”他欣赏斯宾诺莎所说“真理是它自身的标准,又是辨别错误的标准”⑧。但是,“自身的标准”不是固定的准则,也不是演绎的规则和证明,而是内容与形式的动态关系。对黑格尔而言,形式始终是思维及其概念,而被概念把握的内容则是表象、经验和理性对象。如前所述,在不同层次的精神运动中,普通概念(共相)经由普遍的经验概念上升为知性概念和理性概念。对这四种概念,黑格尔有两种组合:一是把经验概念和知性概念合称为思想,另一是把知性范畴和理性概念合称为纯概念。第一种组合的意思是,思想改变了“感觉、直观、表象中的内容”,在意识中呈现出这些感性对象的真相①;第二种组合一方面说“纯概念”不与表象和经验的内容相混杂,另一方面说“纯概念”从表象和经验中提炼出本质和一般规律,因此比经验的普遍概念更接近于真理。黑格尔把“纯概念”的运动称为“客观思想”。他说:“客观思想一词最能够表明真理。”②客观思想以理性对象为内容,以纯粹思维为形式,理性对象与纯粹思维形式是自在自为的统一。“自在”指不依赖他物的统一,不像感性对象和形式的统一有赖于共相,经验对象和普遍概念的统一有赖于知性;“自为”的意思是为了自身的能思自觉地运动。黑格尔把客观思想的全体称作理念(DieIdee),而个别的“纯概念”和思维形式是理念的要素。他说:“理念并不是形式的思维,而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形成的全体,这些规定和规律,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决不是已经存在于外面的写成的事物。”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真相是一个整体。”④这也适用于逻辑学,既然理念是逻辑纯范畴的全体,“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无异于说“真理就是逻辑的对象”⑤。黑格尔的真理观常被指责为“武断”,“未经证明”,“缺乏确定性”,是“独断主义”,“排拒经验的检验”,是“绝对的、无所不包的,因而是封闭的体系”,等等。文本证据表明,黑格尔已经料到种种指责并预先准备好答辩。针对如何证明逻辑范畴的真理性问题,黑格尔回答说,不能从自明的定义出发来证明逻辑范畴的普遍必然性,因为“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它的发展里,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⑥。他的《精神现象学》审视了经验意识发展的全过程,结束于“绝对知识”。康德把认识形式可能性条件的证明称作“演绎”,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在《逻辑学》“导论”中说:“精神现象学不是别的,正是纯科学概念的演绎,所以本书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种概念及其演绎作为前提”,经验意识发展过程的结果即是纯范畴的证明,证明了“一切形式意识的真理”⑦,也保障了纯范畴或“客观思想”的确定性。而逻辑学要沿着精神现象学表述和证明经验意识真理的方法来表述和证明纯范畴的真理性。“我认为”,黑格尔满有信心地说:“只有沿着这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⑧不难理解,“真理符合自身”是达到“真理”与“确定性”、“客观性”与“证明”相一致的精神发展的结果。反之,历史上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对立是主观与客观、真理与确定性相分离的结果。黑格尔所反对的怀疑论不是怀疑感官可靠性的古代怀疑论,而是怀疑“知性所坚持的坚固不移的东西”,即倒退到“假定经验、感觉、直观为真”的休谟式的近代怀疑论⑨。他认为知性思维不能抵抗近代怀疑论,只有辩证思维才能“把怀疑论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内”,即,保存了对感性和知性的否定原则,又扬弃了否定,肯定理性的矛盾“有确定的内容”瑏瑠。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思辨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怀疑论,更不是独断论。黑格尔从不回避经验的检验,相反,他说:“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Wirklichkeit)。我们对这种内容的最初意识便叫做经验”,“哲学必然和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瑏瑡。黑格尔所说的“现实性”有两重优先性。一是时间次序的先在,黑格尔承认:“按照时间的次序,人的意识,对于对象总是先形成表象,后才形成概念,而且唯有通过表象,依靠表象,人的能思的心灵才进而达到对于事物的思维地认识和把握。”①这段话可以解释经验为什么是最初的现实意识以及检验真理的外在标准。其二,“现实性”的范畴相对于表象的“定在”和经验的“实存”具有逻辑的优先性。只有纯思维的现实性或“客观思想”才是真理的最终标准和全体。黑格尔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②黑格尔和康德一样,要确认经验的先验条件,不同的是,康德止于知性范畴,而黑格尔进一步走向思辨范畴的理念。他说:“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能真实如此的地步。”③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最易遭批评。首先要理解,“绝对”的意思是“最高”或“最终”,但“绝对”只是某一领域的最终和最高,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绝对”,因为精神的发展没有止境。《精神现象学》最终达到的“绝对知识”是经验意识的最高知识,而《逻辑学》最终达到的“绝对理念”是诸多逻辑范畴的最高范畴。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事实上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不仅是同一的,而又是有区别的。”④这就是说,逻辑上主客观绝对统一,不等于事实上主客观绝对统一。正因为绝对理念含有主观和客观的事实差别,“绝对理念”才会把自己“对象化”,首先异化为自然界的对象,在克服其中的主客观矛盾后又返回精神自身,相继对象化为主观精神的意识、客观精神的制度和绝对精神的思想。“绝对精神”最后阶段的哲学只能写到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但黑格尔从来没有说过哲学的发展终结于自己的体系。他在去世前一周还在修改19年前写的《逻辑学》。他在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他完全意识到研究对象本身及其阐述之困难,也完全意识到第一版的缺点,他要弥补这些缺点,但这一次修改是不够的,如果有时间,要作七十七遍修改才好⑤。如果要说黑格尔哲学有绝对性的话,那应理解为:他认识的辩证法的无限运动与他做哲学的包容精神是知行合一,他为如何建构哲学体系树立了一个典范。黑格尔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他描述了对待客观真理的种种主观态度:武断的态度是虚幻的骄傲,与此相反的漠视的态度是反对真理的鄙视,因为欲速而不达而对真理失望是“理性之恨”⑥,彻底的怀疑导致的“绝望”⑦,等等。黑格尔说,正确的哲学态度应该在真理面前保持“谦虚”,即“不附加任何特殊的特质或行动上的主观性”,同时保持“高贵态度”,即把真理所把握的事物本质当作我的精神的自由产物。哲学的谦卑和高贵应相一致,因为“高贵性即在于摆脱一切特殊的意见和揣测,而让事物的实质当权”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然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完全抛弃了客观真理。在认识论领域,回到黑格尔所批判的主观确定性,把经验检验当作真理的终极标准。更为甚者,在价值哲学和文化领域,相对主义盛行,最后导致否定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黑格尔把对真理虚幻骄傲、鄙视、“理性之恨”、“绝望”当作没有哲学修养的人的主观态度;而现在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们却为这些情绪披上高贵的外衣,排斥真理、否定哲学成为主观虚无情绪的偶像狂欢。正如黑格尔所说,把一个以普遍为原则的哲学与一个根本否认哲学的学说平列起来,“认为二者只是对哲学不同的看法,这多少有些像认为光明与黑暗只是两种不同的光一样”⑨。现代哲学的状况岂不令人悲乎?
三、精神的自由
黑格尔说,自由是“精神无限权利的范畴”瑏瑠。在逻辑学领域,他区分了精神自由的三个层次:其一,揭示经验科学一般规律的真理,即,证明“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①,而不至于像康德那样把自然规律的决定论与人的自由当作“二律背反”。其二,精神把握和创造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他说,一个伟大的精神创造出伟大的经验,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洞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比如,歌德的精神,“静观自然,透视历史,能够创造伟大的经验,能洞见理性原则,并把它抒发出来”。其三,自由是自在自为的认识真理的纯思想,“人采取纯思维方式时,也就是最为自由”②。“爱智慧”的希腊哲人第一次达到了纯思维的自由,那是“翱翔于海阔天空是自由思想,在我们上面或在我们下面,都没有东西来束缚我们,我们孤寂地独立地在那里沉思默想”③。黑格尔鼓励青年人经过长期、艰苦的逻辑思维训练,能够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同时希望“哲学能够卸下‘爱知识’这个名号,成为一种现实的知识”④。可以说,《精神现象学》是关于经验意识的现实知识,而《法哲学原理》是系统地论述自由意志的现实知识。黑格尔和康德一样相信自由的主体是人的意志。康德的自由意志首先是道德主体,而黑格尔的自由意志首先是权利主体;康德认为道德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王国,黑格尔则说:“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⑤能不能说黑格尔轻视道德,相信人性的根本恶,把自由归结为只有上帝才能实现的目标呢?我以为不能如此解释。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人的内在主观性领域,“它主要以尊严的形式表现出来。尊严的基础就在于它涉及一个为我而在的不可触动的领域”⑥。黑格尔与康德的分歧在于,黑格尔更加关心自由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他说:“法的东西是自由意志的外部定在,意志在一个外在领域赋予其自身以实存。意志使自身成为客观的;人只是作为财产所有者才是自由的。”⑦固然,康德也认为法权是自由意志的外部表现,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把法权概念当作道德概念,法权的普遍原则是先验道德律的正当性⑧。康德的法哲学属于“德治”范畴,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则丰富发展了现代“法治”思想,认为道德只是法权制度的内在环节和中介。黑格尔把人占有物的所有权作为意志自由的最初形态,物权是人类脱离自然界的自由。但是古代社会只知道物权,不承认人权,甚至有权把人当作占有物(奴隶),对冒犯物权的人的身体施加惩罚的报复。因此,最初的物权和保护物权的抽象法是对人的不可剥夺尊严感的野蛮摧残,因而需要道德的扬弃。黑格尔没有把道德看作人的善良本性,也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的道德规则。他认为个人内在道德意识与外在的法权制度有对应关系。依据“故意”来“追责”的道德意识,否定了“抽象法”人身刑罚的合法性;而“意图”与“福利”相结合的道德意识是市民社会的幸福观。康德所说的“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并不是“理性存在者”固有的“纯粹实践理性”,而是现代社会发展出的更高的道德意识。黑格尔说:“人作为良心,已不再受特殊性目的的束缚,所以这是更高的观点,是首次达到这种意识、这种在自身中深入的现代世界的观点。”⑨把“伦理”(Sittlichkeit)与“道德”(Moralitt)区别开来,是黑格尔的一大发明。古希腊文的ēthikē和拉丁文的moralis是同义词,现代语言也不区分伦理道德,哲学家把伦理学等同为道德哲学。黑格尔在哲学上首次把伦理作为高于道德的自由意志发展阶段。在伦理阶段,道德的内在意识发展为社会习俗,内在的个人尊严和独立人格得到外部法权制度的保障。Sittlichkeit没有相应的英文名词,被译作ethicallife(伦理生活)。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不只是生活方式,而是主观的伦理习俗和客观的伦理实体的结合。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三个伦理实体,三者分别有自身的习俗和法权制度。概言之,这三个伦理实体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都有连续发展关系。黑格尔把德国启蒙强调的教化看作伦理习俗的发展。他说:“教化(dieBildung)的绝对规定就是解放(dieBefreiung)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在主体中,这种解放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这种工作反对举动的纯主观性,反对情欲的直接性,同样也反对感觉的主观虚无性与偏好的任性。(……)同时,特殊性通过锻炼自己和提高自己所达到的这种普遍性的形式,即知性”,最后到达理性:“主观意志获得自身的客观性,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它才有价值或能力成为理念的现实性。”①相应地,客观的法权制度越来越全面、具体地保障人格的自由和尊严。伦理家庭的教育培养了“自由人格”,而市民社会的法权制度保障其成员的所有权和个人尊严,市民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私人,有能力拥有自己的自由财产和组成自己的家庭,具有平等权利和个人尊严。黑格尔说:“这里初次,并且也只有在这里是从这一涵义上来谈人(Mensch)。”②而现代国家实现了最高形态的自由,即具体的自由。关于具体自由的含义,黑格尔说:“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③
四、澄清几个误解
相关文章
差异化逻辑主导下土地流转影响 2023-03-30 16:23:47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逻辑及优化路径 2023-03-30 09:45:52
红色校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逻辑理路 2022-10-14 09:16:06
法定数字货币监管逻辑分析 2022-08-25 11:17:51
小学数学对学生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 2022-07-20 10:43:46
党的斗争精神内涵生成逻辑和实践路径 2022-07-13 15:1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