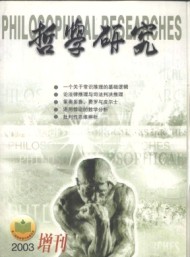逻辑学导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6:41:3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学导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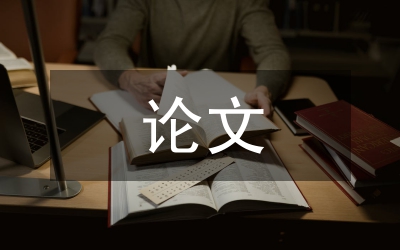
篇1
本文针对目前高中学生天真烂漫,思维活跃,思想激进,追求时尚的特点。根据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广大学生爱好上网这一特点,提出充分发挥网络的正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班级舆论。提出了“学生为主,教师引导,家长参与,网络纽带,焦点主题,展开讨论”的做法。并作了一些初步尝试探索,取得了一定效果。
[关键词]
网络 班级舆论 正导向作用 论坛 留言板
一.提出问题
1.中学生中上网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互联网对青少年影响的报道很多,一时间人们谈网络色变,许多家长根本不让学生上网。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科技是把双刃剑,对于网络,我们应发挥其正导向作用,尽量克服其负面的影响。而不能一叶障目,因噎废食。我们认为可以疏导为主,运用互联网这一手段来为教育服务。
2.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形成了正确的班级舆论。青年学生接受事物的能力强,模仿能力强,思维活跃,追求时尚。我现在带的文科班学生更是思想激进、天真浪漫,还有少数同学盲目追星。如何让学生更健康的成长呢,在自我教育中成长,方为上策。而正确的班级舆论对于学生的自我教育是非常关键的。让班级舆论制约不规范的行为,有时比教师的苦口婆心更为有效,让班级舆论弘扬正气比教师的简单表扬更具影响力。
正确班级舆论的形成,运用互联网技术将如虎添翼。因为网络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二.网络教育具有的特点
公平性。在网络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可以平等交流的。这也正是网络的迷人之处。在互联网上,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亲师之间平等交流,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开放性。互联网上是开放的,因此网络使得利用时空范围大大拓展。
共享性,网络教育资源是可以共享。在网络上,同学们的精彩论点大家可以共同分享,智慧的火花会在交流中得以碰撞。
即时性。反映快。这使得网络成为影响人们生活最大的媒体之一。
三.班级舆论对于班级建设的意义
(一)班级舆论与班风建设意义重大。如果班风不好,歪风邪气上升,学习气氛不浓,班级里没有正确的舆论,也会对好学生造成压力,使一些意志薄弱者随波逐流。所以,教师要十分重视良好班集体的建设,致力于班级优良班风和正确舆论形成。形成正确的强势舆论。正确的班级舆论对于违背纪律、不良道德行为有巨大的约束力。有道貌岸然是众怒难犯。人们都怕舆论压力,这种惧怕感是一股自我教育力量。所以教师不但要致力正确的班风建设,还要善于运用舆论力量的威慑作用。
四. 网络形式
(一)网站形式。首先确定网站主题,如召开班会讨论主题:首先确立,家园的名称:“奋发向上高一(七)”。
(二)网上论坛。选定话题,正确引导,家长交流参与讨论,老师与学生和父母心连心,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三)留言板。可以通过校友录等的留言板。充分发挥留言板的作用。
五.操作步骤
1.提出论题。一个好的论题,对于正确班级舆论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抓住时机,针对同学们关注关心的问题,确立主题。
如确立为文科班后,同学们念念不舍,确定了另一个话题,“永远的高一(七)”,大家还在网上相约,相互鼓励,不断进取。高二(文)科班,我又建了一个新的网站定为,走向成熟高二(七)。现也交由学生轮流主持。同学们也没有因制作这些耽搁时间而影响成绩,相反,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奋发向上。高三已经来临,时间紧,同学们一致确立班级主页的主题为“追星赶月高三(七)”。
2.发动组织。利用班会等作好动员工作,尤其希望代表正确舆论的一方作出自己好发言。
3.学生舆论。学生的参与程度是成功关键,只有学生的充分参与,让学生感到以理服人,让整个班级形成正确的舆论。针对文科班有部分学生追求打扮,追求时尚,我提出让同学们讨论,什么是中学生所需追求的时尚。让学生、家长、教师都参加,以理服人,形成共识:青年学生应拒绝成人化的时尚。
4.家长支持。只有争取家长的支持,让学校与家庭形成合力,让学生在更为理想的环境中成长。家长都是关心自己的孩子。
5.教师总结。每一活动最好都要有教师总结。只要认真总结,让每一活动都既开花又结果。教师通过参与学生的讨论,在思索的海洋上领航,使学生沿着正确的航向,顺利地驶向理想的彼岸。
六.注意的问题
学生为主,教师引导,家长参加,以学生为中心,以网络为纽带,以焦点为论题,展开讨论。防止“德西效应”出现。
篇2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模块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育方案的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这一模块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基本的哲学、逻辑学等思维。课程包括学校统一安排全校公共课和文科公共基础课,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训、军事理论与军事高科技、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简明微积分、体育等。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包括所在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包括专业选修课、一级学科选修课、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该模块的课程,应该在院系的指导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自由选择搭配。课程包括政治学专业英语、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城市与社区管理、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学说史、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学、政治认同导论、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台港澳政治与行政、社会实践。跨专业选修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篇3
关键词是存在逻辑陈述此在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14-08
近30年来,随着海德格尔的思想的引入和传播,特别是对其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界开始真正自觉地以哲学的态度和方法来看待西方哲学,特别是加深了对西方哲学所固有的希腊品性的认识,进而力图来以此为机理来重新审视哲学在中国古典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鉴于当前“翻译学术”的缓慢推进及可预期时间之内的相对保守和可靠,以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推动一些哲学问题的讨论不失为一种学术进路,这即是哲学本身的一种“问题化”。在中国思想遭遇海德格尔之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翻译和理解“Sein”(Being)和源于该词的“Ontology”一词,这不仅涉及到译名之争,更是哲学自身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言,Sein的意义事关西方思想的天命。当然,以哲学严格的希腊性来检视中国思想和哲学的话,Sein也事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及中国思想的天命。然而,就国内学界对Sein、Being的翻译和理解而言,现在基本上还处于一种争论之中,大体上形成了两派:一派基于分析哲学的传统,强调Sein的系词来历,主张以中文的“是”来对应翻译;另一派认为系词“是”不足以涵盖Sein的丰富涵义,主张以中文的“存在”、“有”、“在”、“存有”等来翻译,强调Sein指涉存有、反映真实存在(真理、成真、断真)的一面。这两派各有各的学理依据和论证的根据,然而都忽视了海德格尔本人对作为系词“是”的存在问题的梳理和批判,即参照逻辑史的发展进程标明了系词这个意义上的存在论问题,其中海德格尔特别谈到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穆勒和洛采的系词理论。由此,本文重点疏解海德格尔对于系词“是”和存在论基本问题之关联的清理,并结合现象学对陈述问题(与系词“是”最为紧密)的解决来观照Sein的翻译和理解问题,指出狭隘地以系词“是”来翻译Sein一词之不足。
一
依据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对于系词“是”,特别是作为主词-谓词-关系的存在之含义讨论是在其论著《解释篇》中。这本书的主题是讨论Logos,准确地说是Logos Apophantikos(展示的逻各斯、证明的逻各斯),即如其所是展示存在者的一种言谈或言谈形式。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Logos,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Logos,它是具有某种形式的言谈,包括祈祷、要求甚或抱怨。另一种就是具有展示功能的Logos Apophantikos,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陈述(Aussage)、命题(Satz)和判断(Urteil)。在亚氏看来,并不是每种Logos 、每种言谈都可以如其所是地展示存在者的功能,能够进行展示的言谈只是那种“en ho to aletheuein e pseudesthai huparchei(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言谈)”,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52页。也就是真存在(Wahrsein,成真的)与假存在(Falschsein,是假的)在其中出现的陈述。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存在是某种特定的存在,它要通过作为Logos的陈述表达出来,就必然采用S是P这个形式,必然要与系词“是”发生某种关联。一个陈述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其真假的判定与系词“是”密切相关,但现在的问题是,“真存在”如何与系词“是”相关?为什么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把真理与系词、真与“是”、真与在相提并论?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看待系词“是”的。亚氏在分析语词最初的形态,也就是动词的时候提到了系词,“动词本身便是一个词,并且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说话的人一旦停止他的思想活动,听话的人,其心灵活动也跟着停止。但是,动词既不表示肯定也不表示否定,它只有在增加某些成分后,不定式‘是’‘不是’,以及分词‘是’才表示某种事实。它们自身并不表示什么,而只是蕴涵着某种联系,离开联系的事物,我们便无法想象它们。”②海德格尔对这一段进行了解释,他把动词称之为时间词(Zeitwort),指出一旦当我们说出某些自为的动词时,比如走(Gehen)和做(Machen)时,那么这些动词就变成了名词,意指那个走、那个做的人或物。因为谁说出了这些词,他的思维就停止了,当然这种停止并不是一无所思,而是意味着他的思维发生了转移,逗留于某物了,他借此意指某个有规定的东西。同理,谁要是听到了这些词,听者的思维也逗留于凭借这些语词而领会到的某物了。所有的这些动词意指着某物,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并没有关涉这些意指的物到底存在不存在。因此,“是”(存在)或“不是”(不存在)并不意指一个事物,根本没有意指自身存在的东西。即使我们说出“存在着”这个自为的词时,存在也不意指自身存在的东西。然而这个表达还是意指了某物,毋宁说意指某种Synthesis(联系),但联系本身由被联系之物的思维所担保,只有被联系之物被思维到了,联系本身才能被思维。因此,系词“是”没有独立的意义,它只是一个联系性的概念,蕴涵或表达着某种联系,表达了联系的自身存在。据此,“是”的意指功能是附加性的,是附加在对被联系之物的意指行为和意指性思维的旁边。
海德格尔的解释到此就终止了,在他看来,我们根本无法进一步的深入《解释篇》的主题了。对于注释工作而言,这本论著显示了巨大了困难,这种困难不是文本的模糊和不清晰造成的,而是反映了问题自身的实质性深度。他只是提示我们牢记,“是”意指存在者之存在,而不是意指一个现成的物。在“黑板是黑色的”这个陈述中,主词“黑板”和谓词“黑色的”意味着某个现成的东西,无非就是黑板这个物件和或黑色的东西,但系词“是”并不意指某个现成的东西。对于这个“是”,亚里士多德说道:“这里真与假不在事物――这不像善之为真与恶之为假,存在于事物本身,而只存在于思维之中。”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4、224页。可见,系词“是”所意味的东西并不是位于诸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者,并不是厕身于诸物之间的现成存在者,而是存在于思维之中。就“S是P”这个命题结构而言,系词“是”就是综合,是S与P的某种联结和综合,就是在思维中所思者的联系。亚里士多德认为以“是”为连接词的陈述或命题具有综合和区分的功能,命题的真与假以此综合和区分为标准。“S是P”不仅意味着主词S与谓词P的联结,同时也是一种分散和拆解。由综合和区分所造成的真假不在事物之中,而是在思维之中。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命题的这种结构的分析是本质性的,而且认为我们必须继续深究这个结构。就“是”意味着一种综合而言,亚里士多德有时也把“是”称之为“依于思想的一种结合,也是思想的一种遭受。”④系词“是”所意味的东西不是外在于思维的存在者,不是厕身于诸物之列的存在者,那么这个“是”所意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这个‘是’应当意味着这样一种存在者之存在――它并不厕身于现成者之列,却是一种存在于知性之中的主观性的东西。”②④[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43、246、248页。但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搞懂知性和主体是什么,特别是主体是如何规定它与现成存在者的关系的,也就是说,要依赖于他的此在及其与真理的关系,我们才能对在主体、知性与现成者之间的规定做出决断。
二
海德格尔解读的第二种系词理论是霍布斯的极端唯名论理论背景下的系词理论。所谓极端唯名论,乃是从陈述中被表达出的思维来阐释知识,由于陈述外在形式表现为词语关联,表现为词语和名称,所以知识或思维也以词语关联为准。一切知识,包括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包括系词理论,都被引向了语词关联。系词“是”构成了“S是P”这个命题的简单部分,因而它可以从命题的概念得到更切近的规定。首先,霍布斯仿效亚里士多德,从言谈、言说所具有的可能形式出发来标识言谈,比如有祈祷(Precationes)、许诺(Promissinones)、希望(Optiones)、命令(Iussiones)、抱怨等形式,并且认为这些言谈形式都是对心之活动的指示。从这点就可以看出,霍布斯是从言谈形式所具有的语词特性来规定言谈的,认为这些语词是灵魂类东西的符号。但他并没有确切地阐释这些言谈形式所具有的结构。就对逻辑学起决定作用的言谈形式,也就是命题而言,霍布斯认为:“相反,命题是由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名词所构成的稳定的表述,它们表示了这个说话人说出的东西,他自己认为后一个名词是事物自身的名词。”②很明显,霍布斯一开始就把命题理解为两个名称的结合,并且在前的名称和名词包含于之后的谓词和名称之中,谓词和主词命名着相同的事物。以“人是一种生物”这个命题为例,“人”与“生物”所意味的东西相同,“人”的本质内涵包含于“生物”之中。纯然外在地看,这种命题就是两个名称的结合,呈现为一种词语序列,而“是”就标识着言谈者领会到两个名称与相同的事物有关,因此“是”就是一个符号和标记。
霍布斯对命题之语词序列特征的描述接近亚里士多德,亚氏曾这样开始讨论命题,“口语是灵魂状态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9页。对亚氏而言,所思、所说和所写,或者说,思想、语言和文字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对这种关联的考察必须以符号(“是”)为线索,但亚氏并没有深究这种符号关系,而霍布斯只是以更加外在的语词序列来把握这种符号关系。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胡塞尔对这种符号关系做了实质性的研究,而他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第17节“指引与符号”对胡塞尔的研究又进行了某种扩充。符号关系可以说是西方哲学一个隐秘的密码,当符号成为我们流行话语的一部分时,成为一种流行的套话时,我们需要更加详细地研究符号的多样性及其复杂结构所隐藏的困难。
命题里面的名词是在前的名称,谓词是在后的名称,“是”则是两个名称的联系。如何规定在其符号功能中的这个“是”呢?霍布斯说,联系自身无需通过“是”来表达,“因为各种名称的秩序或次序本身就足够指示它们的联系。”④主词与谓词、在前的名称与在后的名称,正是通过它们的顺序就充分地显示了它们的结合,并且通过系词和动词词性的变化,把这个联系之符号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联系本身就引出了因这些名词而产生的对该事物的思维,也就是说,联系本身或者联系之符号(“是”)导致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两个前后有别的名称何以要加到同一个事物上去,并且其根据在这种思想中被思维了。海德格尔总结道,系词“是”不仅是联系之符号,并不只是联系性概念,它还指示了被联结者植根于何处,指示了其联结的根据和原因。可见,霍布斯在极端唯名论的取向之下,把系词引向了对被联结的名称所意味的存在者之何所是(Wassein)和何所性(Quidditas)了,引向了被命名的事物中构建的区别是什么。作为对联结名称之根据进行思维的标志,系词“是”指示了我们在命题和陈述中,我们思维了何所是和何所性,而命题就是对“物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在霍布斯极端唯名论的取向下,这个问题意味着:“将两个不同的名称归给相同的事物的根据何在?在命题中说出‘是’、思维系词,这意味着相同事物上的主词与谓词之可能与必然的同一关涉之根据进行思维。在‘是’中被思维的东西,根据,正是何所是(实在性、Realitas)。因而‘是’表明了陈述中被述及的事物(Res)之本质(Essentia)或者说何所性(Quidditas)。”②③[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49、251、254页。
正是基于对命题之结构的这种分析,霍布斯区分了两种名称:具体名称(Nomina Concreta)和抽象名称(Nomina Abstracta)。具体名称是被设定为实有的、作为基底的、被思维为现成者的东西的名称,比如物体、运动和相似。抽象名称则标识在进行奠基的事物中现成的、具体名称的根据,是对具体名称之根据的说明,比如物体性、运动性和相似性。依照命题的形式结构,具体名称在前,占据主词的位置,抽象名称之后,处于谓词的位置。霍布斯认为没有系词“是”,表达物之何所是和何所性的抽象名称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抽象名称源于系词。
把不同的名称赋予相同的事物,这样做的根据是由系词指明的。系词“是”说的就是事物的主词名称与谓词名称之同一化关系是有根据的。但我们知道,一个命题有真有假,并且系词“是”必然与这种真假或者说真存在(是真的)与假存在(是假的)有关联,那么霍布斯又是如何把握命题之真假的呢?他认为“如每一陈述中主词与谓词这两个名称的结合关涉相同的事物,该陈述就是真的;如被结合的名称关涉不同的事物,该陈述就是假的。”②在一般意义上,我们用“是”来表示两个名称表达相同的事物,因而霍布斯单向度地认为陈述之真理在陈述环节就有权利确定是否指涉同一事物(最初的真理来源于对万物的命名者及其接受者),并且视作是两个名称之被联结性的统一根据。比如,“人是一种生物”这个命题之所以为真,就是因为人们把“人”与“生物”这两个名称赋予同一个事物。因此霍布斯把系词的意义界定为与真理相同,作为系词的“是”同时就表达了真性存在或真理。在霍布斯这里,真的(Wahr)、真性(Wahrheit)和真命题(Wahrer satz)说的是一回事情。真理并不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所说之中,命题之中。
当霍布斯把物之真理还原到命题之真理时,他还特意加了一个评注,“然而,形而上学家们通常习惯说,是存在者,是一个,是真的,这三者都是相同的。这种说法纯属无聊,简直是幼稚的闲扯,因为谁不知道‘人’同‘一个人’、同‘一个现实的人’所指的是相同的东西呢?”③在这里,霍布斯所说的“形而上学家们”针对的就是经院哲学家,涉及到的是经院哲学的一个著名论题,即“任何事物都是一,是真,是善”,或者说,经院哲学讨论了四个“超越者”,即“‘存在’、‘一’、‘真’、‘善’被称为最在先的东西(Prima,The firsts)。”经院哲学家利用这个命题或原则论证了“灵魂的存在”、“世界整体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认为“惟有上帝才恰当地是‘一’、‘真’和‘善’”。据埃而芩考证,这些超越者直到13世纪才与认识论结合。(参见让・埃而芩:《先验哲学的开端》,曾小平译,载《哲学评论》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49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12节对其中的“一”(单一性)、“真”(真实性)、“善”(完备性或完满性)这三个概念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三个用来述谓“任何事物”的“先验的谓词”只是反映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客观的实在性和指向性,并不能成为构成知识的要素之一,所以被排除在他的范畴表之外,以此间接地衬托出他的范畴表之充足和完备。对经院哲学家来说,任何事物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都是一个存在者(Ens),都是一个(Unum)东西,就某种方式能被上帝所思维来说,都是一个真实的东西(Verum),“存在”、“一”和“真”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的替换,共同本源地归于每个作为某物的某物。然而,霍布斯却认为这三个概念都意指了相同的事物,是一种“同一”的关系,这就是对经院哲学的一种无视。海德格尔指出,关于这一点,我们无法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只需要看到,霍布斯极端地否认任何物之真理,而把真理之规定只归于命题。关于霍布斯对于陈述、系词和真理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陈述就是语词的简单结合或语词序列,系词“是”作为语词之结合的符号,指示了对相同事物上两个名称之同一化关系之根据的思维,“是”意指了我们就之做出陈述的诸物之何所是或本质。
三
J・S・穆勒(1806~1873年),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在其代表作《逻辑体系,演绎的与归纳的》中提出了他的陈述和系词理论。通过对言谈形式的考察,穆勒界定了命题,“一个命题是言谈的一部分;在该言谈中,一个谓词对一个主词做出肯定与否定。一个主词和一个谓词,这就是要构造一个命题所需的全部;但正如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两个名称放在一起,就得出结论说,它们是主词与谓词,命题的意向是用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做出肯定或否定,同样必然地应该有某种样式或形式的指示来指明这是一种意图;有些符号把述谓和其他任何种类的言谈区别了开来。”②③[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59、262、26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穆勒区分命题的主词和谓词也是依赖于符号,正是符号把主词和谓词作为名称而并置在一起,符号承担了述谓的功能,以此体现命题的某种意图或意义。穆勒指出,符号的这种述谓化的功能就是通过系词“是”(ist)与“不是”(ist nicht)来实行的,“是”指向了肯定性的述谓,“不是”指向了否定性的述谓。当然,这种述谓功能也可以通过系词“是”的动词原形Sein的时态变化或单复数来实行。用来做述谓符号的这个词就被称为系词。然而,我们肯定不会把系词只看作是述谓的符号,它肯定包含着比符号更多的东西。穆勒以“苏格拉底是正义的”这个命题为例,指出系词“是”不仅意味着“正义的”这个述谓可以被肯定地附加到苏格拉底身上,而且表明苏格拉底存在(ist),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这个人确实实有(Existiert)。这一切都表明ist是有歧义的,它不仅实行了肯定断言中的系词功能,而且还指涉了命题所陈述的对象之实有,借此它自己才可以作为命题的谓词。当然,作为系词的ist并不必然包含对实有的肯定性判断,比如,“半人半马怪是诗人的虚构”,这个命题不可能断定“半人半马怪”的实有,因为这个命题的谓词已经断言了这个东西是没有实有性的。在穆勒看来,命题就是一个语词序列,这个序列通过系词“是”这个符号表明了这个命题述谓对象。海德格尔据此推断出,在系词“是”中有一种双重的含义:它不仅承担符号功能或联结功能,而且意指对象之实有,表达了实事(Sache)之事实性(Tatschlichkeit),意味着命题与事实(Tatsachen)有关。然而,如何消除系词“是”的这种歧义性或两义性呢?
针对上述问题,穆勒引进了一切可能命题的一般区别。他区分了本质的命题和偶然的命题,本质的命题又被称之为词语的(Wrtliche)命题,偶然的命题又被称之为现实的(Wirkliche)命题。穆勒相信自己对命题的这种划分是沿袭了康德哲学的传统,本质的、词语的命题相当于康德的分析命题,偶然的、现实的命题相当于综合命题。不过,两个人的理论动机完全不同,康德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是为了追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如何可能,而穆勒对本质命题和偶然命题的区分更多的是消除系词“是”的歧义性。对他而言,本质的命题或判断总是词语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命题的功能仅仅在于阐明词义,它不关涉事物的事实性和现实性,只关涉名称的含义。简言之,本质的、词语的命题就是定义。依照穆勒,定义就是指出词义的命题,最简单最纯粹的定义就是:“要么是它在通常接收中所承载的含义,要么是说或者作为其话语之特殊目的有意附加的东西。”②定义就是对词的说明,所有的定义都是关于名称的,但除了说明词义之外,定义还有其他的作用。在这点上,穆勒没有把自己的定义理论贯彻到底,在其后来的《逻辑体系》一书中指出:“在一些定义中,很显然除了说明词义并未意指什么东西,而在其他一些定义中,除了说明词义之外,还有蕴涵着与该词对应的某事物实有。这个在某种情况下究竟是否被蕴涵,这无法从表达的单纯形式推出。”③穆勒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半人半马怪是一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的动物”,“三角形是一种有三个边的直线图形”,如果从命题的形式结构来说,这两个命题完全相同。但前者并没有蕴涵与语词对应的事物存在或实有,后者则肯定事物的实有。为了区分具有相同特性的命题,穆勒指出,在前一种命题里,可以用“意指”来代替系词“是”,我们可以说“半人半马怪意指一种动物”。但在后一种命题中,我们却不能以“意指”来代替“是”,因为语词所意指的三角形确实存在。因此,穆勒把在不同的命题中能否以“意指”来代替“是”的可能性视作是区分作为语词说明的纯粹定义与陈述实有的命题之标准。结合他对两种命题的区分,我们可以说,在本质的命题中系词“是”可以用“意指”来代替,或者说,可以用“意指”来把握和理解系词“是”,穆勒把这种命题称之为词语性命题。相反,陈述或表达物之实有意义上的命题,陈述“实有”意义上的“是”的命题,则被称之为现实的命题。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穆勒对于词语命题和现实命题的区分是无法贯彻到底的,因为即使语词命题所表达的含义中也必然与某种事物相关涉,无法与该命题所意指的存在者相分离。一切命题都是源于事物的。正是在对现实的陈述基础之上,我们才会不断丰富和调整着我们的语词陈述,“毋宁说,一切语词命题都是枯萎干涩了的现实命题。”③④[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64、266、268页。因此,以“意指”来替换“是”的语词命题也是一种陈述存在(Seinsaussage)的命题,穆勒称之为本质命题,也就是陈述事物之本质的命题,即霍布斯称之为陈述事物之何所是的命题。系词“是”对于霍布斯来说等同于“本质”(Essentia),对穆勒而言则等同于“实有”(Existentia)。
四
鲁道夫・赫尔曼・洛采(1817~1881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其逻辑思想对海德格尔前期思想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但一直被学界所忽视和遗忘。海德格尔从1909年就开始研究洛采的思想,这种研究一直持续了30多年,早在弗赖堡神学学习期间,海德格尔就研究洛采和胡塞尔。他在1913年的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就是依据洛采的有效性(Geltung)概念对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进行了批判,显示了对洛采的特殊“偏爱”。1915的高校教职资格论文《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义学说》中也大量引用洛采的《逻辑》一书,借此批判了司各脱的真理和意义学说。关于洛采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参见张珂:《真理与有效性》,《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以及《海德格尔与其思想的开端》(靳希平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和《回答:海德格尔说话了》(陈春文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之中的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和回忆录。他的代表作是《形而上学》(1841,1879年)和《逻辑》(1843,1874年),特别是《逻辑》一书受到了黑格尔的决定性影响。海德格尔把1843年出版的第一版称之为小《逻辑》,而把1874年出版的第二版称之为大《逻辑》。正是在小《逻辑》一书中,洛采首先提出了他的系词理论。他把系词的功能看作是“既进行联结又进行分解”,这实际上再次重复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过的思想,即“陈述既是Synthesis(综合),又是Diaiesis(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洛采对系词之联结功能的强调,在否定判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S不是P”这种否定性判断是自柏拉图《智者》以来逻辑学与存在论的基本困难。因为系词有了一种否定的特征,“不是”的特征,好像有了一种否定性的系词。但洛采明确说过“否定性的系词是不可能的”③因为否定或分解不是联结方式。就“S不是P”而言,如果我们针对S而否认P,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S和P联结了起来。针对这个理解上的困难,洛采在其大《逻辑》中发展了双重判断学说:首要(第一层的)判断和次要(第二层的)判断。在否定判断中,否定就是一种次要的判断,它所判断的是那些得到肯定性思维的首要判断的真实性,次要判断是对首要判断之真实或虚假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判断都是一个双重的判断。“S是P”的意思的:是的,然也!这是正确的!!“S不是P”的意思是:〔“S是P”或“S等同于P”〕,不,这是不对的。就“S是P”这个判断而言,“S是P”是首要判断,“‘S是P’这是真的”则是次要判断;就“S不是P”这个判断而言,首要判断还是“S是P”,次要判断则为“‘S是P’这个判断是假的,不对的”。可见,“S是P”作为肯定性判断、首要判断隐含于否定性判断的判断设定中,它作为前提或根据给否定性判断、次要判断进行奠基。
洛采进一步还把双重判断或判断的双重性发展为主要思想和附加思想的双重性。“S是P”、S的“是P”就是表达了命题的内涵,它就是主要思想,“是的,这是正确的”、“是的,是这样的”则为附加思想。就“S不是P”这一判断而言,其主要思想还是“S是P”,附加思想则为“不对,这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海德格尔指出,洛采对主要思想和附加思想的区分其实可以收拢到亚里士多德表达过的思想中:系词“是”一方面意指了联结,是联结符号;另一方面又表达了真性存在。对于逻辑学中多半会作为例子的“S是P”或“S等同于P”这个范畴性陈述来说,洛采已经预见性地洞见到了其后来的思想价值,他说:“关于这一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可教的,其构造看起来完全是透明单纯的;只需表明,这个表面上的清晰性完全是一个谜,这种关于系词之意义蔓延在范畴性判断中的这种晦暗,将会在很长时间里构成对逻辑学研究工作进行改造的有力动机。”④洛采的这种预言我们可以在现代逻辑(新康德主义、新经院主义、胡塞尔的逻辑学)或分析哲学(特别是弗雷格)对逻辑学的推进中得到印证。
正是得力于洛采的逻辑思想,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和激活逻辑与存在论的关联,并且可以清晰地透视康德哲学以来系词“是”与“认识论”的复杂纠缠。“认识即是判断”这是自霍布斯以来现代逻辑学与认识论所确立的基本信条。判断就是真理的承载者,认识具有“是真的”之标志。认识所指向的东西,就是判断的客体或对象,依照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对象要符合认识,认识的真理,也就是判断的真理由此成了对象性或客体性的评判尺度。在判断中总有对象的存在被表达了,所以真性存在或真的被判断存在(Wahres Geurteilsein,被判断为真)规定了对象之对象性或客体之客体性。依照海德格尔的术语解构,对象性或客体性是从认识论方面所看待的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之存在与对象性相同一,因而对象性无非就是意味着真性存在或真的被判断存在。
海德格尔指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以上述的命题真理观来为取向,尽管他把判断区分为进行判断的行为和被判断的事态。在判断行为中这个被判断者或命题的内涵和意义就是发挥效用的东西,即有效者。[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5页。对判断和命题而言,意义就是被判断存在的东西或真的被判断存在,真的被判断存在、真的东西建构起来的就是对象性,所以对象性就是判断的意义。陈述之真就是对象性,就是意义。这个以判断为取向,以Logos为取向,以命题逻辑来引导真理与存在的取向,就成了认识之逻辑学的认识观,更是新康德主义的主要准则。一言以蔽之,认识等同于判断,真理等同于被判断存在,等同于对象性,等同于意义。
四
通过对以上四个颇具代表性的逻辑学家系词观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系词“是”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系词的特性规定有:“是”作为主谓词的联结符号;可以等同于何所是、本质;可以等同于实有;可以等同于真存在或起效用的东西(意义)。为了从总体上把握系词的各种不同理解,海德格尔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概括:第一,“是”意义上的存在没有独立的含义,只是一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是”仅仅在一种联结性思维中意指某物。第二,根据霍布斯,这个存在的意思是主词与谓词之可联结性的根据之存在。第三,这个存在的意思乃是何所是。第四,在穆勒的语词命题中,存在等同于“意指”,等同于实有,等同于现成存在。第五,存在的意思在洛采附加思想中所表达的真存在或假存在。第六,依照亚里士多德,真存在仅仅存在于思维中,而不在物中的存在者之表达。总而言之,在“是”中包含有:1. 是-某某(偶然的);2.是什么或何所是(必然的);3. 是如何或如何是;4.是真的或真存在(Wahr-sein)。对此可对照卡恩对于动词“Be”的语文学考察,即在巴门尼德时代,希腊词einai有三种用法:系词、实存和断真,可参见Ch.H.Kahn, Verb Be in Ancient Greek,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p.33.另见卡恩:《动词“To Be”与Being概念研究回顾》,韩东辉译,载于《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4页。进而存在者之存在的意思则为:何所性(Washeit)、如何性(Wieheit)和真性(Wahrheit)。[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具有这么多的解释?对“是”的不同阐释是偶然的,还是源于某种必然性?为什么不能使得这些阐释能够统一起来,并且通过一种彻底的提问方式而将它们把握为必然的呢?
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我们追问作为系词的存在是被陈述与陈述真理的问题所引导,对系词“是”的阐述以被说出的、外化的语词关联为指导,而陈述(Logos)现象本身就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和界定,所以系词“是”才会有多重的含义。当然,这种多义性并不是什么缺陷,反倒表达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多重结构及其存在领悟的多重结构。作为陈述的Logos不是声音和语词的简单集合(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陈述不只是一种发声表达与语词序列),不是语词、含义、思维、所思、存在者之关系的形式化和一般化,相反,这些都属于Logos的多重结构整体之面相。与一般的对Logos、陈述的命题界定不同,海德格尔对作为多重结构整体的陈述进行了特征性的双重含义描述:陈述意味着进行陈述和所陈述。进行陈述的是此在(Dasein)的意向行为,也就是此在之绽出着的生存着的超越(Transzendenz)。依照此在的定位,此在的基本建制和结构乃是在世之在(In-Der-Welt-Sein),此在一旦投身于世界之中时,它就与世内的存在者相关,并对之进行陈述。由于“每一种陈述都是关于某物的陈述”,[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05页。就此在“就某物进行陈述而言”,此在与其所要陈述的存在者之间就有一种特殊的关联,这就是在此在的陈述意向行为发动之前中总是包含了一种对其相关的存在者之特殊的领悟,所以在此在要陈述存在者,这种存在者作为被揭示者(Enthülltes)已经预先被给予陈述了,被给予此在了。此在作为揭示者揭示着存在者。这一切都是基于此在的基本建制,基于此在的超越性,换言之,此在的陈述意向行为必须以其超越性为前提条件和基础,此在的“意向性是超越性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上的根据),超越性是则是各种意向性的Ratio Essendi(存在上的根据)。”[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0页。因此,真正说来,陈述现象最初就不是认识,作为整体的陈述无非就是生存着的此在自身。
篇4
关键词:司法三段论 法律解释 法律论证 法律方法论
Abstract : traditional legal methodology represented by judicial syllogism has been challenged from variousaspects and is becoming less acceptable.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major theoretical trend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deep transformation is going on in contemporary ethodology , thatis , judicial syllogism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legal methodology characterized by such dimensions as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argumentation.
Key words :judicial syllogism legal interpretation legal argumentation legal methodology
一、趋向衰落的方法论
三段论演绎系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以来在科学领域获得极大成功的逻辑三段论就一直主宰着法律推理的思维。可以说, 近代法治理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严格逻辑。[1]依照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 (1) 只有,而且只能有,一种实在,即感官可以把握的个体对象。(2)因而只有感官经验为人类认识的源泉。(3) 必存在着本质上互有区别的认识方法。(4) 将非描述性陈述———在它们不是逻辑—陈述的范围内———从知识和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这种做法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价值判断被驱逐出知识的范围。[2] 司法三段论即立足于这种哲学认识论。经典的司法推理(即涵摄subsumtion) 就是在法律规范所确定的事实要件的大前提下,寻找具体的事实要件这个小前提,最后依三段论得出判决结论的过程。从学理上,一个法律规范通常被分为“要件事实”和“后果”二部分。只要一个具体事实满足这个规范所规定的所有事实要件,则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因而其突出优势在于,在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二分格局下,法律适用之操作过程极为清楚。并且由于法律推理乃直接自既定规则出发,无须触及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如正义等。[3]故如此似乎足以消除法官的恣意裁判,从而保障了判决的客观性和确定性。
实际上,这种推理模式早在二十世纪初就遭到美国霍姆斯、弗兰克等人的挑战。不过,这种批判乃出于对传统法律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本能的反叛,缺乏论证的系统性和严密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往往只“破”不“立”的一般立场往往易威胁乃至颠覆近代法治的根基。只是到了当代,西方法才不仅从理论上全面省思了司法三段论的利弊得失,而且提出若干解救其弊的理论策略,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完善了法律适用理论。当然,这跟1970年代以来西方法学界开始普遍关注法律推理问题的背景有关。在阿尔尼奥、阿列克西和佩策尼克那篇著名的《法律推理的基础》文中,他们认为,法律推理问题成为近年来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界探讨的中心课题的原因有三:第一个涉及到当今法律理论的状况;第二个原因涉及到一般的科学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状况;第三个原因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了具体分析。尤其是第二个原因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实践理性的复归;分析哲学和诠释学传统差异和对立的式微;科学哲学中社会和因素的纳入以及分析哲学和批判理论的接触。哲学思想的新发展使得法律理论易于独立地采取不同哲学背景的思想观点。[4]
针对传统的司法三段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德国法学家普维庭认为,经典的三段论推理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认为“, 这种逻辑推理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如有人认为,那种推理模式无法正确地描绘法律适用的过程,掩盖了真正的观察问题的角度。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实际上就是对大前提和生活事实进行处理和比较。甚至有些学者(如Esser) 则完全放弃了推理的过程。这种观点认为,要进行判决,首先要进行不受规范制约的纯粹的认知活动;然后进行第二步———依据法律规范和方法论对第一步的认知进行检验。[5] 考夫曼从解释学的视角认为,[6] “法律发现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复杂结构。这种结构包括着创造性的、辩证的、或许还有动议性的因素,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仅仅只有形式逻辑的因素,法官从来都不是‘仅仅依据法律’引出其裁判,而是始终以一种确定的先入之见,即由传统和情境确定的成见来形成其判断。”然而传统的形式主义却对此视而不见。针对三段论,考夫曼指出:“我们绝非能够分别独立地探求所谓法律推论的‘大前提’或‘小前提’,法律发现绝非单纯只是一种逻辑的三段论??。”拉伦茨[7]则对三段论涵摄模型的适用范围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案件事实不能划属特定法规范的构成要件,尚未必导致该法效果的否定,因为同一法效果可以另一构件为根据。” 从语言学的立场,拉伦茨认为:“如果精确的审视就会发现不是事实本身被涵摄(又如何能够呢?),被涵摄的毋宁是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不过尽管如此,拉伦茨仍然坚持认为,在法条的适用上,涵摄推论模式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相比之下,凯尔森的法律适用理论颇为独特。在他看来,司法判决既是法律的创造又是法律的适用,“法院的判决永远不能由一个既存的实体法一般规范决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法院所适用这一一般规范,仿佛只是由判决的个别规范加以仿造而已。”因此,在判决内容永远不能由既存实体法规范所完全决定意义上,法官也始终是一个立法者。不过凯尔森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即认为上述“授权”是经过一个虚构的方式———法律秩序有一个间隙(gaps Lacunae) ———给法院,结果:一方面,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余地太多,另一方面,凯尔森认为这一虚构也限制了对法官的授权,尤其是这种间隙虚构公式“只具有心理学上的而不是法学上的性质”。[8]而晚年的凯尔森侧重于对规范理论的,更是提出了令人惊异的结论:逻辑三段论(Syllogismus) 并不适用于规范。[9]荷兰法学家Hage 则认为即使在简单案件上,规则适用三段论模式也不正确。[10]其实,二十世纪的实证主义法学均承认法律的未完成性(Unfertigkeit des gesetzes) 或如哈特所言规则的“空缺结构”。在此情形下,法律实证主义以为法官应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正因如此,这遭到德沃金的批判并提出法律推论中规则和原则的区分问题。他认为规则是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并且规则表达越明确,其效力也越分明;而原则则带有较大的弹性与不确定性。原则具有规则所没有的分量和重要性的程度,因而带有“权衡”的性质。并且当规则和原则发生冲突时,原则的效力高于规则。更重要的是,当德沃金确认了原则等准则同样具有法的性质时,法官在裁判中就无须行使如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德沃金还对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法律的语义学理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其法律推理理论进行了反驳。[11]在世界,波斯纳法官主张区分三段论的有效性和它的可靠性。“其可靠性不仅取决于个别三段论的有效性,而且取决于前提的真实性。”三段论的功能只是表明某个推理过程是正确的而不是确定这一过程的结果的真理性。此外,不仅小前提的确定即发现事实不是一个逻辑过程,而且法官将规则适用于事实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种不断地对规则的重新制定。波斯纳更注重实践理性诸如轶事、内省、想象、常识、移情等的作用。总之在他看来“, 在法律推理上,科学方法几乎没什么用,故与科学相比,法学与神学和形而上学更为接近。”[12]
不过,在批判的热潮中,也应当看到某些法学家依然对涵摄三段论的肯定立场。除了上文提到的拉伦茨以外,德国法学家Koch 和Russmann 就回头转向———已经被一些人宣告死刑的———“古典的”方法论。Pawlowski也认为,在说明裁判理由时,不能弃置涵摄模式。但是对正确地做出裁判一事,其帮助不大。[13]Hage 自以为提出的“基于理性的逻辑”(RBL) 是“初级断言式逻辑”( FOPL) 的一种延伸,所有演绎性论辩皆可同样适用于基于理性的逻辑。[14]美国法学家Branting 也提出一个综合了“基于规则的推理”(Rule -based reasoning)和“个案推理”(Case - based reasoning) 的法律分析模型。[15]
从总体上可以说,传统的科学方法论正日益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法学家对传统的三段论又提出若干替代性和修补性的主张。其实,早在拉德布鲁赫就曾提出借助“事物的本质”在法的发现中架起从应然通向实然的桥梁。还有人提出一种由演绎和归纳组合而成的推理形式:类比和设证。考夫曼认为法律发现是一种使生活事实与规范相互对应,一种调适,一种同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从二方面进行: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具有规范的资格,必须与规范产生关联,必须符合规范。并且在此,“涵摄”的类推性格完全表露无遗。“涵摄”在此不能被理解为逻辑的三段论方法,而应理解为规范观点下对特定生活事实的筛选。另一方面,规范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解释”: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在此基础上考夫曼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普通的概念思维的思想形式:从“事物的本质”产生的类型式思维。[16]Hage 提出的法律推理理论也颇具启发。[17]针对传统的将规则于论辩(arguments) 所产生的诸多缺陷,hage主张最好将法律规则理解为产生于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目的。然后他拓展出一种根据原则和目的推论的模式。最后将这一模式整合进一种较传统“初级断言式逻辑”更为完善更具说服力的“基于理性的逻辑”。
二、哲学上的反思: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上述科学三段论的重大转变必须置于更深的哲学层次上予以解释和阐明。正如朱庆育博士所论:[18]不与科学分享其本体论的法学,如何能够在方法论上有效的援引科学推论方式?倘不从包括本体论在内的整个法学理论来重新检讨法律推理问题,而一味的希望科学方法论能够支撑起法学的学术品格,那么,法学家们无论表现得如何殚精竭虑,或许都不过是在追求海市蜃楼式的幻觉。实际上,当今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的巨大进步已经为法学领域将科学方法论重新置于牢固的本体论框架提供了可能。在西方哲学向现代哲学迈进中,哲学家们对于“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或理解和说明的关系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9]一种是以卡尔纳普、纽拉特、亨普尔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为代表的“统一科学派”(或科学一元论)观点,大多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他们主张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的行为等社会现象作出因果说明。另一种是以德雷、P·温奇、泰勒、冯·赖特等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派”(方法二元论)的观点强调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后者所采用的说明方法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需要采用理解的方法。所以他们主张把理解和说明区别开来。他们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观点出发,把这二种概念形成的语言游戏区别开来,一种语言游戏讨论那些严格的可以观察的事件及其原因和性。另一种语言游戏说明人的行为和那些人的行为相关联的意义、意向、理由和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则和规范等等,[20]他们致力于后一种语言游戏。而这种精神科学派的主要观点“与韦伯的看法很接近:社会行为具有一种”意义性“(Meaningfulness) ,它不是由观察者设想或设计的,而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行为本身;正是这种意义性使得其他人能够理解该行为。意义性与受法则支配有关;但是,理解支配某现象的法则并不等于是赋予该现象一个原因。”[21]而P·温奇竟然极端到主张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学科而是哲学学科。“这种‘理解性的社会学’(这是在德语中得到广泛使用的名称)。最近,它往往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名目之下得到倡导??。”[22]相对于这两种立场,美国哲学家罗蒂的观点也值得注意, [23]在基础认识论撤除后,罗蒂并非提出解释学来作为认识论的一个“继承主题”,作为一种活动来填充曾经由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填充过的那种文化真空。不过他同时也区别了哲学家发挥作用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博学的爱好者、广泛涉猎者和各种话语间的苏格拉底式调解者所起的作用;一种是起文化监督者的作用,他知晓人人共同依据的基础。前者适于解释学,后者适于认识论。解释学立场上,谈话不以统一诸说话者的约束性模式为前提,但在谈话中彼此达成一致的希望绝不消失,只要谈话继续下去。而认识论则把达成一致的希望看作共同基础存在的征象,这一共同基础也许不为说话者所知,却把他们统一在共同的合理性之中。不过罗蒂同时也反对那种认为解释学特别适用于精神或“人的科学”,而客观化的实证的科学方法则适合于自然。罗蒂从其实用主义立场认为“情况仅仅只是,解释学只在不可公度的话语中才为人需要,以及,人需要话语,事物则不需要。”于是,解释学就不是“另一种认知方式”———作为与“说明”对立的“理解”。最好把它看成是另一种对付世界的方式。总之,西方哲学上的对科学认识论的反思和讨论其实印证了哲学家鲍曼的看法,即“立法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而“阐释者”的角色的隐喻则最适于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24]相应地,在法学领域,皮尔斯(Pierce)迈出了这一大步,即“从仅仅认识特征评价的亚理士多德和康德逻辑学,发展到了关联评价必须在法哲学和法律理论中才可以理解。”[25]上述哲学争论及转向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哲学诠释学之为人文科学对抗传统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合法性地位日益牢固,同时也为法学尤其是法律推理理论摆脱传统科学认识论走向作为自身学科的存在论提供了重大契机。
另一方面,基于近代科学认识论上的法律实证主义在伦理学上通常坚持一种不可知论立场。法律和道德相分离的根本立场使之放逐对价值(善恶)的探求,而在法律适用的形式逻辑三段论思维模式下,法官只需做是非、真假的形式判断而绝不能做价值判断。否则即超出这一科学方法论的认识框架和理论初衷。可以说,本体论与方法论上的严重背离乃是基于主客体二分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到后来趋于衰落的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法律和道德是否分离,而在于人的理性如何来判断伦理价值问题的对错。其实,实证主义分离命题无非是希望正本清源,维护法律本身的体系自足,防止法官专断。达到这样的目的未必非得采取这种思维进路。肯定认知者在价值问题上能够有所作为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研究路径。在西方法学史上这就涉及“实践理性”的问题:[26]有实践理性吗?实践理性如何作用? 通过实践理性能够得到实质性的价值命题吗?亦或只能解析价值命题之逻辑关联?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法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所谓“实践哲学的复归”。法哲学家们通过对康德“实践理性”的再审思,为法与道德哲学寻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27]在英国,实践理性的再发现,推动了法学家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推理、法律和道德等问题的探讨。在德国、奥地利等国,一种新的理论趋向———法律论证理论也逐渐兴起。这种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等人的商谈理论或实践商谈理论(practical discourse theory)的。该理论旨在确证、道德和法律论辩。从这种意义上,它取代了古老的自然法理论。所不同的是,自然法关于道德和法律理论的实质内容在这里等而下之,而程序成了最基本的正当性根据。亦即,这些实质性命题或规范只有经过理性的商谈过程达致合意始为有效。[2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推理”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科学方法论上的用法,而是“成了一种说服或反驳对手,并根据一个决定的正当性与对手达成一致的讨论技术。”因此“,实践推理使人的动机、意图具有一种规范或一种价值的特征。”[29]
不过,如哈贝马斯指出,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强烈现代意义,以主体哲学为基础的概念。它在理论上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具有一定负面作用,所以建议以“沟通理性”来取代实践理性的地位。在其交往行动理论中,法律和道德就可以通过言说原则(diskursprinzip)加以联结。[30]哈贝马斯认为“真理”不是超验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类经验中的并且是由理性的、自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成员经过讨论和对话获得的知识。“其理论的目的仅仅是要保证理性探讨的前提,而不是要预知这一探讨的结果。”[31]所以,哈贝马斯批判德沃金理论乃一种出于独白的观点“,由于Hercules是一个孤胆之英雄,缺乏对话的层面的考量,因此其整体性最终仍将落入法官具有特权地位之认识。” [32]为摆脱这种理论困境,应将其理论导向一种商谈式程序性的法概念,探讨一个理性判决是如何作出的。这就需要一种法论证理论。[33]因此,从知识论上,法律论证理论已然摆脱了仅局限于逻辑和语义的层次,而延伸到语用学(pragmatics)的领域。[34]另外,法律论证理论更凸显出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因此,它不仅依赖于法律论据的品质,而且依赖于论证过程的结构。在解释规则时,在各种可能解释当中选取一种之后,法官尚需对其解释作出充分的说明即对其判决进行确证。而法律论证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近年来人们对法律论证可接受的标准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阿列克西认为,法律论证必须成为法学理论之根基。“论证理论并不仅限于法律领域,论证理论研究者试图拓展一种对论证进行分析和评价的一般模式,并且这也适于特殊领域。”[35]总之,法律论证理论是在西方法学“解释学转向”以后,学者们在实践理性、商谈理论等知识基础上拓展出的法学新的领域。同时,这一研究触角兼及当今西方逻辑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等知识领域。
三、解释学转向背景下的法律论证初探
在法律方法伦上,无论是近代自然科学还是实证主义法学都不脱离司法三段论的思维模式。“二者对法律发展或适用的过程的理解在方法上是一致的。二者均致力于客观的认识概念、实体本体论的法概念、概括的意识形态和封闭的法体系的理念。”[36]随着近年来本体论转向后的诠释学理论和语言哲学大规模的进入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话语被深刻地改变了。其中最重要者,恐怕是解释由最初作为一种简单的方法或技艺,至此上升到法概念的本体地位, 即“诠释学的法律本体论”( hermerneutische rechts- ontologie) .在此背景下,学者主张“在敞开的体系中论证”(阿列克西) .此时,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开始普遍被区分为法律发现的脉络(context of discovery) 与确证的脉络(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37]前者关涉到发现并作出判决的过程,后者涉及对判决及其评价标准的确证。一如科学哲学上区分所谓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发现的逻辑和证明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罗素所说的熟而知之者和述而知之者。英国哲学家赖尔在《心的概念》一书中,提出了区别两类知识范畴的一种有用分法:知道如何 (Knowing how) 和知道是何( Knowing that)。很好地说明了发现和辩护的关系。[38]这一区分同样对于理解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论证的作用十分关键。因为它提出了评价法律论证规格的标准。判决作出的过程固然是一个精神的心理过程,但也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它也成为另一种研究的对象。无论判决是如何作出的,为使其判决能被人接受,法官必得对其法律解释予以充分阐明,由此确证其裁判的正当性。而法律论证即关系到这种确证的标准。至此传统司法三段论模型从整体上被具体化为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推论模式。这在西方法律解释思想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近代西方法哲学传统固有的关于民主和法治、合法和正当等叙事的对立和紧张,由此至少从理论上得以缓解乃至克服。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结合能够有效地克服科学与人文、理性与经验、逻辑与修辞、[39]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此类的二元对立。解释和论证的关系可以套用考夫曼关于“诠释学”与“分析学”的公式:[40]没有解释的论证是空洞的,没有论证的解释是盲目的。
相较于传统的三段论,诠释学和法律论证在新的基础上运用更为广泛的和手段,如论题学、修辞学、逻辑哲学、符号学等。法律推理过程也摆脱了那种严格、呆板、机械的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而呈现为全方位、立体式和动态化的结构图式。法律诠释与法律论证对上述知识的运用也不尽一致。如关于修辞学方法,在法律论证理论产生中,修辞学是其重要思想来源。法律论证理论所注重的可接受性即取决于论辩本身对受众(Audience)所产生的效果。而修辞术是就每一事物觅出所有可能的说服方式的技能。“他既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Episteme ,也不是Techne ,而是技能Dynamis.”[41]而修辞学与解释学关系也颇为密切。加达默尔即力倡“解释学与修辞学同出一源说”。[42]哲学解释学在形成之际就十分关注语言,因为语言同时关系到解释学的存在论维度和实践哲学维度,而修辞学则是一种说服技能。加达默尔强调解释学与修辞学同出一源,目的就是为了将语言中这些禀赋再度结合起来。不管这一观点能否成立,解释学和修辞学确实在不少方面有共同之处。相比之下,解释学与逻辑方法就较为悬殊。魏因贝格尔批判解释学依然是个没有完全的科学分支。它虽然已经拓展出一种类型学的推理模式(typology of models of reasoning),但没有分析不同推理过程的相关性。虽然已经确定了不少规则,但对规则在逻辑和认识上的多元性未予注意。[43]为此,他提出一些矫正意见。从解释学看,所有解释都是主张某规范具有法律上效力的言说行为,而后者又是一种规则导向的行动。实际上,在法学知识共同体经过长期论述已经逐步形成一套基本的、共同的概念和规则体系,此即法学中法教义学(Rechts dogmatik)的作用。若无法教义学的指引,那么法制度运作之论述将极易陷入浪漫的修辞,而无法产生合理的说服力和共识。从这种意义上,法律解释学和修辞学虽然共同有利于致力语言之自然禀赋,但法律裁判毕竟旨在达成合理和有说服力的结果。法律解释必须遵循某种逻辑的制约。在批驳三段论形式逻辑时,切不可矫枉过正。所以解释学与逻辑学还应当携手并进。当然,法学又不能仅限于法教义学的操作,“因为规范性概念之联结主要不是透过逻辑而是透过提出理由(论据)之论证来加以支持。”[44]而在法律论证理论中是否应包含逻辑,一种看法是将法律论证跟逻辑或逻辑分析区分,因为他们担心,逻辑的严格将伤及法律的适应性,妨碍法官在个案中发现公正的解决办法。不过许多论者还是肯定逻辑在论证理论中的地位。“论证理论主要源于分析学,这仍为今天几乎所有的论证理论家们所确认。”[45]如魏因贝格尔认为,作为现代法学理论的两个标志,其一是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的法律结构理论,其二是法律理性论证理论。二者都涉及将逻辑于法律的问题。逻辑论辩部分是逻辑演绎,部分是佩雷尔曼意义上的修辞论辩。[46]季卫东认为:“虽然有一些学者站在反对决定论的立场上否认法律议论(即法律论证———引注) 也具有三段论的结构,但是一般认为,既然合乎逻辑是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合理性的法律议论很难也没有必要拒绝法律三段论的帮助。实际上,在有关法律议论的新近中,人们所看到的却是三段论的复兴。当然那是按照法律议论的要求改头换面了的三段论。”[47]
不过,论证理论和解释学并不尽一致。如考夫曼曾经谈到二者的差异,“论证理论是反诠释学的??论证理论是反本体论的??论证理论并不赞同诠释学对主体-客体图式的摒弃,而是坚持客观性”。[48]当然,考夫曼也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某些不同意见。
按照荷兰学者Feteris对当今西方法律论证研究所做的一个概览式的综括:主要涉及托尔敏的论证理论、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麦考密克的裁判确证论、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阿尔尼奥的法律解释确证论以及佩策尼克的法律转化理论(ory of t ransformation in the law) .[49]当然,其中有些学者也涉及其他领域,如托尔敏就涉及伦。七十年代,法律论证被视为法律逻辑即一种法学方法论或法律判决的制作,而不是法律论证本来的意义。自产生后,法律论证理论获得很大发展。学者研究的具体领域涉及如立法过程、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等。法律论证一词有不同说法,Neumann 认为当今日本、德国法学界使用“法律论证”这个用语时,其含义尚未确定,但可以归为三大类:逻辑证明的理论、理性言说的理论和类观点-修辞学的构想。 [50]法律论证理论研究适用于对作出理性裁判予以确证的条件问题,而对法律论证合理性之研究具体涉及对法律判决进行理确证的方法、用于法律判决进行重构或评价的方法及其适用的合理性的标准等。法律论证理论乃法学中一门独特的学问。跟其他法教义学、法学和法哲学等研究路向不同。[51]总之,法律论证理论是一种以论证为基础的法律解释理论,其主张以事实和逻辑为论据,在主张-反驳-再反驳的“主体间”的论证过程中,通过说服和共识的达成来解决法律争议问题。因此“,法学之理性在于它的论证之理性,或具体说,在于依据理性论证的标准去考察法律论证的可能性。于是,法学的科学理论遂汇入法律论证理论之河。”[52]
[1] 当代英国哲学家Hare 对实践三段论(practical syllogism) 的界定是:由一个规范性前提与非规范性前提推出的一个规范性结论之推理。芬兰哲学家冯·赖特(G. H. von Wright) 则认为实践三段论跟意图(intentions) 和行动(actions)相关。见Robert Alexy , A Theoryof Legal A rgumen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8. 荷兰法学家Hage将传统司法三段论依据的逻辑称为“初级断言式逻辑”(first order predicate logic) ,以与其主张之“基于理性的逻辑”( reason - based logic) 相区别。见Jaap C. Hage , Reasoni ng withRul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 130。
[2] 参见[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18-19 页。
[3]参见[美]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 页。
[4] Aulis Aarnio ,Robert Alexy and Aleksander Peczenik , The f oundation of Legal Reasoni ng ,该文发表于德国的《法律理论》(Rechtstheorie) 12 (1981)。
[5] [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71页。
[6] [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 - 22 页;[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5 页。
[7] [德]Larenz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8 - 174 页。
[8]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 - 168 页。
[9] 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280页。颜厥安进而评价说:“Kelson的这种规范反逻辑主义并非其独创,也并非毫无问题。但是晚年Kelson规范论的作品则为法理学研究开创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规范存有论及规范逻辑,其与法学方法论及法论证论的结合更成为当前法理论界最为重要的课题。”同书,第281页。
[10] Hage , Reasoni ng with Rul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 2。
[11]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 [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12]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55-90 页。
[13]参见[德]Larenz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7-46 页。
[14]前引Hage , Reasoni ng with Rul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158。
[15] L. Karl Branting , Reasoni ng with Rules and Precedents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16]参见[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五、六章。
[17] Hage , Reasoni ng with Rul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 130。
[18]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哲学解释学-修辞学视域中的私法推理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
[19]参见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 页;另见王巍:《 科学说明与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5期。
[20]在法学上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论”即是一典范。“必须用解释学或内在的观点来理解的东西就是与规范有关的行动的概念。”见[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 页。
[21] [法]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春、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8 - 209页。郑戈博士也曾作过这方面的理论努力。见郑戈:《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2] [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49 页。
[23] [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七章:从认识论到解释学。
[24]参见[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5 - 6页。
[25] [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 页。
[26]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227 页。
[27] 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 年第4 期。有那么一段时期,许多哲学家似乎忽略了实践理性的统一性,然而只是到了现代逻辑和逻辑哲学兴起以后,哲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道德推理和道德以外的实践推理的关系。人们对实践推理的兴趣还因人们日益意识到它在解释人类行为的特殊性。另外,许多数学和心理学在“决策”问题的研究也是其一重要原因。参见Raz, Practical Reasoni 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
[28] 跟传统自然法不同,通过程序达致正义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重大贡献。其思想在德国也颇有。1993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已经明显意识到并重视社会多元化的事实,正义原则被限缩到只适用于康德式的个人理想社会。而越来越强调政治正义是多种合理的广泛的议论的“交叠共识”。参见何怀宏: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载《读书》1996年第6 期。
[29] [法]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春、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20 - 421 页。
[30]颜厥安:《法效力与法解释》,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7 卷第1 期。
[31][美]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 页。
[32]见颜厥安:《法效力与法解释》,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7 卷第1 期。
[33]在大陆法系法学谱系中,传统的科学方法论由于涵摄模式对法律解释学的支配,从而视论证理论“没必要”;另一方面,决断论则强调法律决定的非理性主义,从而视论证理论为“不可能”。关于决断论,见颜厥安:《规则、理性与法治》,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1卷第2 期。
[34]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即立足于人文主义立场,力图修正科学主义的传统,消解形式语义分析和实践语用分析之间的隔阂并构架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为意义和真理问题提供了一种语用学的解决路径。见郭贵春:《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 哲学研究》2001年第五期。
[35] Eveline T. Feteris , 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 6.
[36]郑永流:《法哲学是什么》,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37] 这一区分最早由Reichenbach 于1938 年提出,后来被普遍接受。见Eveline T. Feteris 上引书, p. 10 ;Alexy 前引书,p. 229 ;Maccormick and Summers , Interpreti ng Stat ute : A Comparative Study ,Dartmouth ,1991 ,pp. 16 - 17 ;另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 页。
[38]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64 - 365页;关于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的区别,另参见沈铭贤、王淼洋:《科学哲学导论》,上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 - 108 页。
[39] 在波斯纳看来,“我看起来可能像是在说,只存在两种形式的说服方法:一方面是逻辑,它不能用于决定困难和重要的案子;而在另一方面是修辞的伎俩。并非如此。在逻辑说服同感情说服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取得合理真实的信念??这就是实践理性的领地。”见[美]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 页。这种实践理性相当于宽泛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修辞”。
[40]参见[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 页。
[41] [德]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8 页。
[42]张鼎国:《经典诠释与修辞》,“中国经典与诠释研讨会”(威海·2002)论文。当然,加达默尔的观点也受到哈贝马斯等人的反驳。
[43] Ota Weinberger , L aw , Instit ution and Legal Politics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p. 89. 而在西方哲学史上,“诠释学一直曾被隶属于逻辑学,成为逻辑学的一个部分。”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9 页。
[44]见颜厥安:《法效力与法解释》,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7 卷第1 期。
[45] [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 页。
[46] 见Weinberger , L aw , Instit ution and Legal Politics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p. 70 - 71。另外有学者以为,“法律推理逻辑的性格为实践话语领域中形式化限度的讨论,提供了极好的检验标准。”而“法理逻辑是义务逻辑支持者(卡里诺斯基,冯·赖特)和‘新修辞学’支持者(佩雷尔曼) 之间相互争夺的一块地盘。”见[法]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春、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19 、423 页。
[47]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5 - 106 页。
[48][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 页。
[49]见Eveline T. Feteris , Fundamentals of Legal A rgumentati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50]张钰光:《“法律论证”构造与程序之研究》,http :/ / datas. ncl. edu. tw。
篇5
关键词:知性思维,实践思维,中西哲学
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是中西方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明显的不同特征,对中西方哲学致思的方向,以及对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性思维与古希腊哲学
知性思维是古希腊哲学总体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它表现出对于纯知识的追求,对于抽象逻辑的热情。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 即爱智慧①的意思。这一本义导引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基本路向,奠定了其“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求知出发点。
据说,泰勒斯有一次走在路上,因只顾观察天象,不慎跌入泥坑中,遭到一个女奴的嘲笑,笑他只想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地上和身边发生的事。后来柏拉图认真对待了这一嘲笑,认为该女奴无意中说的话实际上对所有哲学家都适用。哲学家们经常驻足在常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凝神思考。他们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并非为了达到什么直接的实用性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本性。哲学家们排斥了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追求,使哲学成了为智慧而求智慧的纯思辨活动,“它涉及满足某种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属于实用范围”[1]。
对形上本体的探索,最能反映古希腊先哲们知性思维的特征②。为知而知的出发点将哲学家们的目光引向了遥远的天际和抽象的思维领域,产生了从伊奥尼亚派“形体质料说”到新柏拉图关键词的本源意义或者说是哲学之本性的话,那么,“本体论问题可以说最能体现哲学本性的问题了”[2]。
古希腊知性思维的特征还表现在逻辑学的成熟上:古希腊人更侧重于对思维本身、思维形式本身进行反思,其思想更能走向抽象逻辑理论的深处,从而他们经过自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不断努力,最终建立起一整套更为严密的概念、判断、推理的体系。
二、实践思维与中国先秦哲学
实践思维的主要特征在于现实性与目的性的合一:思想的出发点以现实需要为指向,并普遍接受这一目的的制约。也可以说,实践思维有着求实用、求功利的特质,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与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西方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范畴之间划上等号,它不涉及道德标准问题,而只强调一种认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它也不同于作为获得科学途径的实验主义或者审视知识之结果的实证主义,虽然它们也具有与知性思维相反对的一面,有着反形而上之空想玄谈的倾向,但这仍逃不脱在人的外围世界打转转儿,仍然是为一个解释而已。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实践思维的主要表现。言人道必言天道,言天道意在人道;行是知之依归,知是行之先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3]《论语公冶长》载:“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为什么孔子不言天道呢?孔子是很衙实际的人,也继承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不言天道,少谈鬼事,都是为重人事。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这里,荀子已明确将行动上的实践作为认识世界的直接目的。主张“贵用”的墨家,不仅在思想体系上具有实践思维的明显特征,而且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墨子及众多门徒在行动上也亲自参加生产实践。,知性思维。至于老庄之“道”与“无为”,亦无非是另辟蹊径的人生处世之道吧。,知性思维。如果说没有什么概念比“求真”二字更能把握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实质了,那么,实践思维则更在“求真”与“求善”的结合。
三、中西哲学的总体特征与差异
中西哲学发展的原点时期所具有的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的特征和差异,实际上也适用于中西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和总体差异。尽管这个整体发展模式在某个时期或个别思想家那里有过不同的偏离,但这也正如原点所具有的个别现象一样,并不影响中西哲学所带给我们的整体印象。宋明理学的高度思辨有“知性思维”的味道,让讲究实际的中国人受不了,以至于他们把宋明两代的灭亡加罪在这些“无事闲来谈心性”的学者头上,并很快就以“经世致用”之学扭转其发展的方向。反过来,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识”,号召哲学家关心人事后,哲学家无不以改善公众事物为己任,柏拉图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斯斯多亚派的“世界公民”都指向了政治实践,然而,在对待人事的方式上,他们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拿出“对待自然的一套来研究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4]。所以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在中西哲学上的差异尚不只在研究范围上,而更在研究方式和态度上。
总之,实践思维和知性思维成为中西文化中两种不同偏好的认知态度和方式。在思维起点上,实践思维以“实用”为求知的首要动因,知性思维以“求知”为求知的出发点(此即所谓追求纯知识的热情)。在思维内容上,一方面,二者关注的对象各有侧重,实践思维关注人及其与自然的合一,知性思维关注自然、关注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同一内容的思维领域里,实践思维关注于人的德性实践,知性思维则以重分析与思辨的方式表达了对道德理论方面的关注。
四、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之影响问题上的中国式反思
当中国人在近代战争中败于西方人之手后,“”、“维新变法”便成为噩梦惊醒后的直感选择,然而不过是技艺的模仿和政治的抄袭,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于是二十世纪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思想领域去寻找问题的症结,其中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没能孕育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梁漱溟、牟宗三、冯友兰等一代巨匠都曾站在肯定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思想重新审视,对此问题提出过一系列比较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在“科学”产生的问题上,正是实践思维模式让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实践思维功利性目的的影响下,“中国主要发展起来的是应用型知识体系”,即使‘理论的建立也必须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无论其针对生存意义、经济基础层面的现实需要,还是观念意义、上层建筑方面的现实需要”[5]。反之,所作所为怕思所想若不能看到直接的实用价值,则为学界所不齿。《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巧。,知性思维。,知性思维。子墨了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故所谓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知性思维。”公输之此时表现的尚是一种技艺,远非抽象的科学理论性的知识,却已不能为人所容,那就难怪在知识的旅途中,中国人与超越于实用意识、偏重思维抽象和逻辑推理的西方人最终分道扬镳:他们选择了科学,中国人选择了技术。,知性思维。
如果我们庆幸自己还有技术,那么技术这棵苗在中国实践思维的土壤里却缺少充分的营养。首先,实践思维欠缺有时甚至鄙夷知性思维中可贵的思辨精神,而理性思辨在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很多功利性目标的实现便离不开理论思辨的前提。其次,很多事物在其产生之前甚至在产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其作用及程度是很难一眼望穿的,所以,戴着效用意识的近视镜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谁能说公输子发明的“鹊”不是中国第一架飞机的雏形呢?可惜被墨子狭隘的实用思想一句话抹杀了!最后,实践思维中极端的道德、政治实践目标钝化了中国人向外、向自然界的追求,在“自然--人―社会”的结构中,“义欲之辩”、“义利之辩”让人们惭愧地弱化了物质追求的欲望。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的表面形式最终被“以天抑人”、“以善制真”的实质内容所代替。
注释:
①此并非否定中国哲人的爱智慧,只是中国人不愿将其作为学问的目的。
②用知性思维来说明西方本体论发端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被引以为证明中国先秦时期没有或缺乏本体论的证据。但中国的本体论更偏重体用一源、当下即是,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之中有着明确的“人道”实践指向。
参考文献:
[1][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求实出版社,1982.
[2]李维武.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张再林,中西哲学比较论[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5]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篇6
关键词: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方法论、发展趋势、脉络、价值
A中图分类号:G40 - 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方法学是1637年由笛卡尔提出的哲学观点,并在西方得到广泛的推崇,笔者将其基础定义理解为;一门学问采用的规则、方法与公理,一套可实现目标的做法及一种特定的做法。美国韦氏大词典[①“韦氏大词典”作为《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的习称,参考自《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1492页。]①对方法学的释义为“在某种知识领域上,对探索知识的原则和做法而作之分析。”方法学的通用概念是:在某一门学问或所要探索的知识领域上,对所使用之个别方法加以整合,比较,探讨与批判。以方法学为理论背景的各科科学学问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结构体系,譬如医学方法学、法律方法学、设计方法学等,学问的方法学包括能够支持这些方法之准确性原理。而美术教育的研究,应该也有属于其本身的方法研究体系,即美育方法学。且所涵盖了一系列已编撰好的美术教育建议方法,包括标准美育信息材料,正规教育程序、工作表与图像工具等的总和。
近年来美术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融合方法学体系的美术教育发展原理,并非单一解决美术教育问题的某一办法,它是一种具有学术方法精神的理论知识背景,是科学态度与人文背景有效结合的成果。笔者将它视为美术教育学科学术拓展的命脉。要使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规律化、妥善化,首先以统计学为基础,整合了近年来有关美育研究方法的理论信息材料与相关文献,美育研究论文及著作内容分布;
表1 20 年来中国美育研究论文和著作内容分布
以思想史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中国美育思想史、西方美育思想史和美育思想史是三大主要内容。美育思想史著作的写作范式表现为以美学思想史为蓝本,分别阐明每一位美学家的美育思想。在此类著作中凸显出古今教育的差异。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以讨论儒道两家思想为主,而近现代美育思想的论争焦点在梁启超、和王国维。西方美育思想则重点在席勒的《美育书简》上。这些著作提出;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论开启了中国美育的道路,同一时期的王国维基于西方哲学的“知、情、意”三分法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基于当时的西方教育发展成就与国情推动了美育的制度化。[[1] 王晓旭,孙文娟,郭春宁.1990年-2010年中国美育研究脉络 [J].美育学刊.2011.6(2);1-11.][1]21世纪以后对中国美术教育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几乎是90年代的3倍。学者们以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为中心,进行深入解读与现代性阐释。其中也不乏一些以南宋程朱理学为基础的论文代表,如潘立勇在《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中提出,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传统命题。
以思想史作为美育研究方法的例证不在少数,近年来逐渐攀高的中国美育思想逐渐改变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趋势,这种改变是源于以思想史为研究方向,推进了美术教育研究多元发展的应证。以思想史为切入点的资源整理方法是最普遍的美术教育学科方法论途径,有助于为美育研究提供广泛的理论知识。也概括了一部分以伦理社会发展为背景的美术教育知识体系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方向。
以原理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原理的研究方法是美术教育方法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支脉,它与美术教育的实施有着密切的联系。原理揭示了美术教育的内在属性,它将观念与动态程序连接起来,并形成一种规律。原理是模式的导论,尽管我们不断更新研究模式,但始终需要原理作为支持,另外,原理决定了可行性,使研究对象不脱离社会与自然环境,而这种无法避免的种种联系,使美术教育原理本身具有鲜明的个性。细化与规范原理的内容,深入原理的内在属性,将使美术教育方法论更实际切入美术教育研究的核心。
正确的教学方法,受多方因素制约:第一是正确的美术教学任务或目标;第二是优秀的教材教科书;第三是教学执行者―――教师的全面素质;第四是教育对象学生的心理、认识和思维全面情况。这四方面原理都从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教学方法的制定和运用。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有一些教学方法是属于静态性质的方法,有一些教学方法则是动态的方法,由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提出的“ 发现法”,意即,引导学生利用教师和教材所提供的有关材料,亲自去发现结论或规律而成为“ 发现者”;即为动态的教学方法。美术教学中要善于将这两种方法统一起来,以期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2] 王雨中.美术教育方法论.[J].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百家.2007.7(99);175-176.][2]原理的认识角度能够启发引导发现与建设方法,并促进合理改善美术教育教学体制。
美术教育原理研究方法还涉及了美育的性质与任务;内容与形式。从检索结果看,近十年不少学者在原理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一种开拓性的共识。如拉尔夫・史密斯著、滕守尧译的《艺术感觉与美育》( 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凌晓蕾主编的《艺术美育》(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爱萍主编《美育与艺术欣赏》(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7 年) 等,都认为美术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教育,它通过美开启人的心灵,以一种熏陶而非灌输的方式对人的内在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教育行为则是美术教育的实践形态,在高校中展开美育的主要途径; 美术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趣味和人文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高校的现行体制中,美术教育是必不可少和行之有效的素质教育方式。[][1]
以实践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应证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正是实践活动,同样,在推进美术教育研究的进程中,实践活动仍然是验证学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以《美国哈佛大学课程体系改革考论―――哈佛通识教育( 美育类) 实地考察报告之二》[[3] ,傅晓微.哈佛课程体系改革考论―哈佛通识教育(美育类)实地考察报告之二. [J].美育学刊:美育实践研究.2011.6 (2):51-60][3]为实例,研究高等学院美术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研究方法,为我国高等教育美育实践方法研究提供参考。美育类课程作为哈佛新课程体系的缩影,从以“学科”为分
类标准,到以“需要”为分类标准; 从重理论研究方法,到重审美对象“是什么”和“为什么”,“连接”大学院墙内外、学生现在和未来,实现了从美术教育到审美教育的跨越。
尽管美国和世界许多高校把哈佛核心课程体系( Core Curriculum System) 视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模板,但哈佛最新课程改革的首要动因,恰恰是看到这“模板”显在和潜在的弊端。哈佛大学摒弃全球众多高校趋之若鹜的核心课程体系,追求更完美的课程体系,既来自俯视全球的霸气和视野,又来自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这些哈佛精髓,完全可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找到同样的文化元素。也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积弊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积极因素。
哈佛课程体系改革是从自身多维认识到实践过程的衍化,再次宣告了它放眼世界的雄心,从研究实践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中国在1990 年先生逝世50 年之际,李祥林的《中国近代美育体系的创导者》指出,蔡先生曾言: “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FsthetischeErziehung 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真正从理论上使美育系统化,在实践中做出显著成绩并有广泛影响。[][1]而当下国内不少学院的美育体制改革也常以旧识推新学,但新学并非是由当下美术教育现状所催进的学术研究方法,实为扩充研究方法而学习、引用、采
纳的诸多办法,其结果大多是改变了学术
路径,而未改变学术研究的大格局。意识
表22009年哈佛新课程体系
寻找美术教育学科交叉点研究方法
有关于寻找学科交叉点的方法,一直是学者们推进学术的重要办法之一。现也有 “跨语境”美学的研究方式可成为美术教育学科探索研究法之参考。如比较受推崇的《高居翰中国美术史文集序》,它说明了学术研究可通过外来参照系的对比发现自身研究领域的盲区。近年来比较显著的学科交叉点是美术教育与语言语义学,美术教育与统计学、美术教育与生态学、美术教育与心理学、美术教育与图像学、美术教育与现象学,而相对传统的学术焦点是美术教育与文学、美术教育与哲学、美术教育与社会学、美术教育与逻辑学等。
以寻找学科交叉点的美术教育学术研究方式极大程度的丰富了学科内容,并为找到新的学术领域和资源提供了有效途径,从美术教育与学科交叉研究分布法的要义来说,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是学术价值的体现。在这种研究方法逐渐成型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学术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如:李欣人在《席勒美育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中指出,席勒美育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和“人性复归”理论的提出。赵伶俐《高校美育―――美的人生设计和创造》偏向于科学化、量化的研究,把美育目标所体现的观念意识和知识分解为一系列的行为、方法和技能,使学生在懂得和了解基本的美学、美育和美育心理学知识的同时,掌握运用美的规律去进行自我人生的理想设计、形象设计和生活设计的方法。[][1] 但也有弊端,如范景中教授就曾经担忧“这种研究以常识碎片的拼凑而扼杀了美术史的魅力,也淹没了智识的光芒,导致了巧取之伪问题泛滥意一时”。而在美育与学科交叉分布研究方法的观念里,可以以笛卡尔在《论方法》中提出的四条理论作为依据:1.普遍怀疑,将一切可疑的知识圈出,剩下绝对正确的内容。2.将最复杂的事物转化为最简易的事物,例如将精神实体化为思维,将物质实体化为广延。[①笛卡尔“第一哲学”特有的哲学术语。就是物质的基本属性 , 即物质的空间属性,即所谓的长宽高, 凡是物质必然占据空间 , 这就是广延 。]① 3.用综合方式从简单事物中,获得复杂事物。4.尽可能累计全面,复查周全,以确定毫无疏漏。这样的思维虽未必适用于美术创作,却可为美术教育方法学系统的形成提供参考,如,将第一条用于学科交叉点的寻找过程中,可相对减少无关知识对学术主题的干预;第二条则利于我们看清多维复杂事物,直击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本质与核心;第三条则利于美术教育与各学科知识体系相互碰撞、促进与发展;最后一条则适用于检验学术成果,为成果的实践和学术价值的体现创造可能。
2.5 美术教育部门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
近年来不少学院致力于学科探索,潜心研究美术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教法,也有的部分学者特别关注师资建设。在美育课程的目标方面,李开玲、孙景曾在《大学美育课程论略论》中从美术教育的大局观角度提出了具体的美育目标论与课程论,认为美术教育的目标有三个: 第一,现代化的忧思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教育的使命; 第三,促进生存方式重建。美育课程的功能层面,邢云提出了美育课程设置的必要性,认为美育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的目标、价值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从师资队伍建设上,特别突出的有孟繁梧从师资的自然状况、素质状况和管理状况进行分析,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提出了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包括完整的知识体系、较强的艺术教育科研能力、更强的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以及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从艺术管理的课程设置来建设美术教育的新学科。艺术管理[arts management or arts administration]是一门新兴的辅助学科,它顺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和学院制美术教育普通学科相比,它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艺术管理者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为艺术家营造富有成效的创作环境,提供最佳机会发展其艺术;另一方面,要将由此而获得的成果呈现给理想的观众,为其艺术体验准备条件。在过去2000多年里,艺术家曾自行担当这个责任,而当艺术创作及其展示成为一种生产与营销机制时,人们认识到,艺术组织的领导与管理需要专业技巧。[[6] 曹义强.艺术管理的观念与学术状况.[J].新美术.2007.3(28);4-15.][6]“艺术管理是一门将文化政策、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博物馆学和艺术史与管理学结合的操作性学问。艺术管理者需具备商学、财经、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技巧,才能胜任其工作。”这个观点是2007年由曹义强教授所提出的,以他将学科建设中的普遍方法与艺术管理学科特性结合所得出的学术观点来比较我们在以常人方法学取向的角度研究美术类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极易忽略学科的特性,我认为曹对艺术管理学科观念见解很值得我们借鉴。回顾一下常人方法学的特征有:1. 行动的权宜性( conting ency) 与规则的说明价值。2. 行动的场景组织与局部索引性。3. 行动的反身性和可说明性。4.研究方法的“独特适应性”。[[7] 周斌.教育研究中的――常人方法学取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10(21):9-13.][7]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是学术者不可忽略的要素,在美术教育研究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常人方法学,但常人方法学并非作为我们学科发展的拼图之一,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参考。且无论是以与美术教育相关的学科发展角度出发,或者依照社会功能变化的不确定性,在美术教育部门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中,仍需具有潜在随机性。
3. 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趋势
近年来,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趋势十分明显,1.逐渐脱离纯理论的研究方式向实践迈进。2.是针对院校性质的改善内容、目标、教材、方法、评估体系。3.是对美术教育与美学关系的进一步深入。5.隐性课程体系与交叉学科的开拓与探究。6.随着社会自然环境与人类意识的改变,发展数字化和实验性教学。对于美术教育研究的发展而言,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如在《高居翰中国美术史集序》里,我们发现跨语境研究为美术和美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系,这种外来的参照系往往能照亮容易处于盲区的问题与领域,高居翰善于默记大量的图像,他对视觉材料的评述,具有图文互证的效果。
从总体趋势来看,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成为一个单一途径而迅速发展,但从方法学的角度看,它们并未形成一个具有稳定性规律的方法体系,常态单一的方法无论是来自于东方的哲学观照,还是出自于西方思维的能量,都无法满足美术教育研究发展的未来格局,避免学术者尽可能不落入一种本位主义,如致力于完善美术教育方法学的研究,可综合文献与数据整理,结合社会学、统计学和哲学等探索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形成与结构、普遍特征与内化逻辑、理序与稳定数据、变化与自然反应等,以至于美术教育研究的方法本身集成一套具有学术价值的参考体系,对美术教育研究的学术方法具有创新、预测、评估等功能。
篇7
一、形式分析缘何举步维艰
1985年前后,文论界曾刮起一股“科学主义批评”旋风,不少学者直接套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模糊数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于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虽不乏亮点,但最终都归于沉寂。科学主义批评的引进-热闹-沉寂的三部曲乎为三十年来绝大多数登陆中国的文论观念定好了生存基调。如今,当我们检点当年热闹非凡的文字和论争,面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实质性成果寥若晨星的残酷现实,心态浮躁、准备不足、量化数字化不适合作为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艺术学的评判标准的反省聊可让人。于是乎,科学主义批评被认定不适合文艺理论和批评,至多算个文论史的事件而已。事实果然如此么?20世纪80年代西方最新潮科学方法在中国学界热闹后归于沉寂、落寞,往大处讲,可以归咎于我们缺乏科学理性(数学-逻辑)文化传统,朝小处说,也与学者们大多急功近利,缺乏“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实干精神脱不了干系。但我认为,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学者们普遍对于所谓科学主义批评“背后”的东西缺乏明晰深刻的认识。从表面看,科学主义批评这一来自中国学者的特定指谓无非是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取得伟大成就而兴起的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美学和文艺现象进行“自下而上”实证的、经验的研究的20世纪回响罢了,费希纳的实验美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美学都可以划入这一世纪大潮。实际上,半个世纪前朱光潜那代学人已经凭深厚的学术功力让古老的华夏诗性智慧领受了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这一壮阔宏大的文化更新创造历程至今远未画上句号。更深层次地考量,批评的科学化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崇拜。确切地说,批评的科学化不过是西方思想追求普遍必然知识传统的表征而已,在当今中国学者的著述中屡见不鲜的概念不清、思维混乱、分析淡弱、理论缺乏系统性等现象,便是这一传统匮乏的必然结果。衡之以此传统,科学主义批评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满足于实验和精确数据的收集、归纳,恰恰大成问题。因为它们根基不稳,忘记了对其理论如何可能的前提条件进行彻底的追问,如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所做的那样。就连“解构天使”德里达在其扛鼎之作《论文字学》里都一再申明自己在寻根溯源,追问整个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可能性的条件———痕迹(trace),一种先验的原始的不可还原的综合因素,可见这一传统威力之强大。衡之以此传统,穆卡诺夫斯基、雅各布森的布拉格学派、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特的结构主义、英伽登的现象学,成就斐然、影响甚巨,倒更足以代表这一传统的精神风貌,因为他们志在建立文学科学、美学科学、艺术科学,至于其客观性理想能否实现则另当别论。我曾用“科学型美学”指涉西方美学主流的根本性质,它有别于科学美学、技术美学,当然也并非仅指科学主义批评,这种哲学美学智慧具有十分鲜明的形式性、分析性、先验性、纯粹性、超越性、系统性①。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美学、文艺理论建设始终在这个异域思想传统的巨大身影下苦苦寻觅自己的话语生存、叙述空间。现在,我们不但有了本土学者撰写的为数不少的西方美学史、艺术哲学史、文学理论史论著,还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传统、现代文学批评传统。但就构建中国形式美学而言,我们仍然有十足的理由诘问,我们真得对这个以科学理性精神(我不大喜欢用“科学主义”这个在中国有过诸多误解和争执的名词,丰富深刻的科学理性精神之内涵远非有特定所指的科学主义所能涵括、表述)为支柱的哲学美学传统之精髓了如指掌了吗?我们真得对作为思想方法、知识原理、存在根基的形式分析精神这一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构成成分做到运遣自如了吗?“分析”表示何意呢?形式分析如何进行呢?“分析”这个范畴的内涵相当宽泛,与本文有关的涵义包括:(1)从前提到结论的超越经验的理智运作,即证明活动,譬如,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是借证明去认知的。(2)把事物分解成各个部分加以严格考察,从而确定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新批评对独立自足的客体“诗”或“小说”的“细读”是一种形式程序,意在详细地、精确地分析作品的基本构成成分,即语词、形象、比喻、象征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作品的中心主题就是围绕着这些语言学成分组织起来的,而作品的结构则是张力、反讽、悖论这些对立冲动之间的和谐、平衡。再如,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神话犹如一种语言,是一个自足的、自我决定的结构。这一系统可以被分解为多个基本单位,这些单位相当于语音的基本要素音位,它们之所以有意义,能够存在,取决于它们在这一系统内部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差异关系。这种对对象进行严密、客观分析的思想方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分析的目的是运用理性思维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追求确定性,倾向于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本质进行形式的把握。形式的感性内容越少,普遍性就越大。当然,抽象性和确定性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哲学思维的确定性就不如科学思维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系统在现代符号逻辑看来只是实质系统。请注意,形式分析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它还是一种知识原理。按照康德的说法,纯粹感性材料形成知觉判断,没有普遍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命题形式叫做“先天综合判断”,它是先天的形式“纯粹理智概念”包容、整理感觉材料的结果。进而言之,由于形式的、分析的精神浸润于数学的逻辑的理性文化氛围里,它还是或者说首先是存在论的。柏拉图的理念(形式、种或类概念),既是存在论的,指现象变化中的永恒存在,又是认识对象,指逻辑建构的知识形态概念。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向度是科学,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学的反思,并为之提供基础和说明。存有论为科学规定了客观性原则,逻辑和数学为之规定了以确定性和分析性为表征的知识原理。”①根据我们的考察,中国学人的三重“误解”也许造成了他们对形式分析的不喜欢甚至厌恶反感。其一,形式批评高度抽象,脱离具体的经验内容,不及中国式感悟批评灵心妙赏,一发即得。其实,这样的看法混淆了对具体作品的体验解读与对文学知识的普遍追求。形式分析通过部分的分析达到对普遍必然的关系即整体的本质的把握,目的在于达成理想的知识。譬如,英伽登现象学美学对文学的艺术品结构的分析是存在论的,即对存在-实体的观念内容的先天分析,如果它是可能的,便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很多西方大艺术家、大批评家的谈艺录,往往寥寥数语,切中要害,而又文心渊深,生动有味,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式感悟批评,它们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法朗士曾称之为“灵魂在杰作中冒险”。其二,纯粹形式不过是个理性抽象出的空架子而已,没有实际的作用和价值。由于道的本性无法诉诸语言,所谓可道非常道,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不重视语言和逻辑分析,看不到纯粹的知性概念,未能产生与质料相分离的纯粹形式。形式化建构按中国传统的眼光看,不啻于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实质上,缺少了严格的形式化建构,便难以产生符号语言,不可能进行符号之间的纯逻辑的推演,现代计算机系统就无法想象。从席勒到马尔库塞,强化审美形式的批判功能、政治潜能,说明形式有着丰富的人文因素和社会文化内涵。牟宗三先生更是指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民主政治的精神与遵守逻辑数学前进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深刻关联②。其三,形式在先,意味着内容被忽视甚至遭到否定。这是对内容即形式的现代观念不能领会的结果。形式批评、内在批评不是不考虑文学研究的外在因素,诸如作者、时代、读者等,而是强调内在的优先性,只有把作品的自身意蕴、本性搞清楚了,才能为整个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穆卡诺夫斯基把艺术本性界定为符号,又区分符号为能指和所指、物质性和意义性,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被感知者感知的是审美客体(所指),这样就用艺术品这个“自主的符号”连接起了作品、读者、社会。诚然,不能否认,分析思维肢解对象、强分畛域,事事处处以精密性、确定性、明晰性为旨归,的确显露出理性的“暴力”倾向,不但有碍于直接把握事物的整体性,而且往往破坏了对象的原始的生命样态。不过,一种特定思想文化类型之特性之长项在充分展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必然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弱项和短处。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批评中国传统思想重整体领悟缺乏分析精神吗?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明白当今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认为,反体系、反本质主义一类的时髦话语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积极作用非常微弱。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的现代化是“体”的变化,这个“体”指社会本体,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存在。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许多人仅仅想把科学作为运用的东西,而实际正是科学代表了社会本体,推动社会存在前进,在此基础上发展文化意识形态”③。这里的科学不单指自然科学,更是一种社会建制,而始终贯穿其间的则是科学理性(形式理性)精神。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技术层面的实用式的拿来,它更指向思想文化类型的更新。接纳数学-逻辑的分析精神,尊重科学的文化氛围的造和精神传统的养成,艰难曲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乃在于规则意识、形式正义等现代观念恰恰内在于中国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小而言之,形式分析精神也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学科建设的系统化科学化的迫切需要。当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批评流派和方法涌入中国,如前所述,倘若我们对这些现代批评方法的“根性”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形式分析之类的异质思想因素的摄取、消化、转换也许会成为未来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已经有一批学者,例如,李幼蒸、赵毅衡、赵、董小英等,开始了艰难的也是富于建设性的理论探索。
二、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
吴炫把中国形式文学难以真正突破的原因追溯到中西文化哲学的根本差异,是非常有眼光的①。他有关建立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学理论不能采取抛弃认识论的态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一种确定性的文化意旨建设、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通过形下走向形上的整合尝试的观点,笔者也很认同。我们认为,建立中国形式美学,如何对待西方的形式本体论同样是个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但能否就此断言形式本体论不适合中国形式美学的构建呢?看来为时尚早。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辩明两个术语,一个是本体(论),另一个是形式本体(论)。对本体论,有学者下过这样的定义:本体论就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从实质上讲,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原理系统;从方法论上讲,本体论采取的是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到了黑格尔发展为辩证逻辑的方法;从形式上讲,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含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②。从上述概括可以见出,本体论在源头上牵连着西方思想的种种根深蒂固的特质。譬如,两重世界、质料和形式的分离、概念思维、逻辑分析、体系化建构、先验形式、本质追求,这些特质构成了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从狭义上讲,中国文艺理论界所理解的形式本体论指现代西方随着“语言学转向”而兴起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布拉格学派、巴黎结构主义),他们分析文艺作品的语言构成,探寻文艺作品的内在规律即结构,试图在本质上(本体论上)揭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独特性,展示形成作品统一性的规则、秩序。这种建立文学科学的理想显然是科学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宽泛而言,本体论的基本特性是形式的,也可以说,就是形式本体论的。展现结构(理性的抽象化、理想化)、先验必然的形式(给知识内容赋予形式)、形式系统(将高度普遍的命题组成形式系统)、形式化(以数学-逻辑的形式表示符号间的推理演算)、把握本质(事物现象背后的共相、模式、秩序),本体论的理性主义(形式理性)在认识对象、思想方法、知识原理、理论形态等方面刻画着西方思想的精神面貌,当然也规约着西方形式美学的基本面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本体论(本质论)意义上的形式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公开打出形式美学旗号的学派有赫尔巴特-齐美尔曼、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在对美的本质、艺术本性、审美经验、文艺风格、艺术作品、审美形态等重大问题的探究中,到处可见毕达哥拉斯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超验理式、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形式的身影。康德更是对20世纪的美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此看来,当我们问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形式美学的构建)时,表面的意思是指中国学人能否运用现代形式主义方法于中国语境,深层次的含义却在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如何可能这一重大课题,就本小节探究的主旨而言,就是上述形式理性精神的种种内涵能否为中国思想文化所吸纳,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大课题。粗略言之,这种吸纳、转换、创造之所以可能的基础或许在于科学精神文化氛围的培育,中国学者在逻辑学、符号学等方面学养的提升,一大批学者的主动选择等。不过,我们在此把焦点集中在形式概念身,看一看中国学者在构造形式美学时,如何处理形式概念与中国思想语境的适应性问题,其种种难点既在技术性、学理性上,更在源于中西思想传统根本差异的冲突矛盾上。我们知道,形式的涵义复杂多层,使用者往往在一个形式的名义下指涉好几个涵义,且每个涵义适用于不同的问题。据我们的观察,在种类、体裁、技巧等意义上,形式的使用麻烦较少;由于中国形神合一、道显为文的传统,中国学者,譬如朱光潜、宗白华使用黑格尔以来西方近代主流形式概念感性形象或感性形式也并不觉得有多大的隔阂;语言论转向下产生的文本批评、现代形式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语境下显得不那么成就斐然,究其实质在于中国学者普遍对符号学、语言学陌生,操作起来自然底气不足。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仁学解释学》,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的问世,赵将文学文本范例分析上升到类型学的研究思路,表明中国学者不仅可以介绍得到位,更能着手富于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在我们看来,真正的难题主要在于如何对待先验形式(纯形式)。所谓先验就是先于、独立于经验而又使经验得以可能,它以普遍性、必然性为其表征。这种先验形式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与质料分离的理性-逻各斯传统,此传统的底蕴又在希腊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中发现事物的永恒秩序(不变的客观形式),为变动不居的万事万物确定最初之动力。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着重从事物的作用、功能和性质上看待其终始生化与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没有离开个别具体的事物而追求一恒常不变的形式的传统,故而对待先验形式中国学人的态度颇多分歧。冯友兰的新理学(形上学)对一切事物做形式的解释,其四个观念(理、气、道体、大全)完全是形式的观念,对实际无所肯定,也就是与事物的质料内容、具体的感性存在无关。金岳霖区别了先天命题和先验命题,认为只有逻辑的知识是先天的,先天、先验的知识都由经验而来,但正确性并不依赖于经验,可见个别与共相有区别而又不可分离(道是式和能的综合)。李泽厚在为其美、美感、艺术论奠定本体论基础时,形式的作用(度的本体性)居功至伟,但他明确表示不接受先验理性(形式),他使用的形式指人的主动造型力量,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赋形),朱光潜把“纯粹形式直觉”这个形式主义核心命题与经验心理学的“心理距离”、“移情”杂糅起来诠释审美经验,不但断然舍弃了先验形式,而且将先验认识论命题转换为经验心理学命题(古代的心物交融说)。我们绝不否认建构美学和文艺理论当然有其他进路和方法,其理论体系的本体论范畴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之外另辟蹊径,然而一旦我们决定以“形式”作为体系大厦建构的脚手架而非普通的砖瓦石料,那么,明确拒绝也好,积极建构也罢,都不能不对此先验形式有所回应,因为它不仅关乎加强逻辑分析、为传统审美智慧的现代转换添一思路,更是对美、美感、艺术、自然美、艺术史动力等重大问题如何可能的先验条件分析,是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原初的”、“先在的”根据。
三、象家族改造与新生的重点在哪里
上世纪30年代,在那篇创见迭出的力作《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里,宗白华先生权衡比勘中国思想的象和西方思想的形式,得出象即中国形而上之道、象之构成原理乃生生条理和西洋形式美的根源是逻辑、几何、数学一以贯之的概念世界、永恒超绝的范型是先验的理数的结论。耐人寻味的是,在表解中国独特的生命精神时,宗白华没有用“象”,反而用译自异域文化的术语“形式”,认为“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①。倒是吴炫提出“什么是中国式形式”的理论命题,并试图既向传统的“象象”思维里灌注追求独创的精神,又以中国式形式(象象)的整体性、通透性弥补西方文化片面彰显纯粹性、对抗性的缺陷②。吴炫的做法的确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艺学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传统如何进行创造性转换,具体而言,就是象及其家族成员的当下适应性问题:传统美学文论概念术语如“象”、“文”、“法”等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人的审美经验、艺术趣味、文学特点?以这些概念术语为基础有无可能创造出美学和文艺的新理论形态?我们认为,倘若说运用“形式”于中国思想语境尤其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时面临着是否契合———尤其在形而上层面———之难题,那么象及其家族的改造、转换主要不是针对中国古代的美学和艺术,而是现代中国的美学和艺术,一方面我们应当考量其诠解在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生成、以现代汉语表述的审美精神、艺术实践、文学世界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另一方面,这种解释之富于效力的来源在于如何回应、接纳业已在现代中国美学文艺学学科体系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形式系统及其体现的形式理性精神,质言之,本文对此问题的先验探究就是俗语所谓“旧瓶”能否“装新酒”或曰“注入新鲜血液”。据考察,象及其家族成员包括象、美、道、文、法、气、形、理、和、势、韵、体、境、格、意象、声律等①,它上通中国人的本体论、宇宙观、道德学,下达审美创造、审美理想、艺术表现、艺术法则、艺术构思、形式美等重大问题,中间横贯着道气象一体、文道(文质)合一、整体思维、以象喻意、体用不二、不离弃感性经验等象家族思想特质,其涵义包括对立面的统一、形象、规律、象征、法则、风格、节奏、声律、韵律、体裁等,若论涵义的多样性、功能的丰富性、思致的深刻性,与西方形式系统相比,丝毫不逊色②。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艺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形式论传统,尽管形式在现代中国的美学文艺学的话语系统中已经取得了几乎一统天下的实绩,但是“形式”和“象”这两个足以代表中西哲学美学精神特质的范畴在形上层次、思想方法、话语形态、言说构意而非技巧、体裁、风格、节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次次地令学人们陷入困扰尴尬的境地:形式系统的概念用到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上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不够贴切③。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形式也好,象也罢,都是文化学、社会学、哲学范畴,在其背后挺立着一个特殊文明的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不过我们在此不准备提出形式与象的形而上“融通”的可能性(探究其具体途径、哲学基础、语言根基等)这一难题,我们只尝试性地解答后一个问题,即象家族的改造与新生。这种现代改造建基于对其缺失弱项的深刻洞察与清醒认识之上,取决于我们对西方的形式与中国的象之间的巨大精神差异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我们明确表示不同意失语症论者或汉语诗学论者的部分观点。幻想径直地回归古典传统,简单地沿用古代术语命题,除了具备怀乡抒情的价值,并不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失语的困境。中国现代形式论传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一批学者,如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都是在实质上而非传统范畴术语的移植沿用上开拓形式的新疆域。我们主张,象家族的改造与新生的关键步骤,不仅在于发掘其固有的、较之形式论可以说是“独特的”现代性因素、观念、原则,更依赖于中国学人主动摄取、延揽、吸纳、融会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形式理性精神。不管你是否承认,这一硕大的思想工程乃建立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化的核心课题之一,它不自今日始,也不会在短期内画上句号。具体言之,就本节的主旨而言,除了上面提到的引入先验维度、加强形式分析外,主要有以下四端:第一,扩张构型力量。在宇宙论上,象家族的本质特点是主客不分、道不离器,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论意识欠发达,数学-逻辑理性精神不够强劲的必然反映。明末清初以来,随着西方逻辑与科学论著的译介,重逻辑理性,讲个体主体的思想因子逐渐深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肌体。理性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主客二分所缔造的理智主义和客观主义。所谓形式的构型力量实乃理性借助概念、范畴(最高的概念)建构超越的本质世界的活动,概念、范畴决定着全部客体,决定着我们的感觉经验对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即本质,形式具有给质料赋形的造型力量;用康德的讲法,人的理智给自然立法,他的范畴体系从质、量、关系及其内部诸规定和相互间的逻辑关系来建构存在者的世界。卡西尔认为,文化世界是人的精神本质固有的对象化符号化(构型)的创造,文化符号的各种形式折射出人性的不同层面。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将形式与人的自由活动,与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与建立法律、政治、经济等各种新形式联系起来,恰恰是中国哲学美学走向现代的深刻表征。第二,建立批判理性。由以上论述可见,象家族的诸种涵义几乎没有涉及社会政治功能。而在西方,批判功能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形式的活动中。柏拉图的“理式”(形式、本质)是理性建立的概念形而上学,其现实的投影就是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当代西方者更是普遍凸显形式的批判功能。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艺术的批判功能,艺术为自由而奋争所做出的奉献,存留于审美形式中”①。实质上,形式的批判源于理性的批判。批判理性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知识而知识地追求真理,它来源于人的心智解除愚昧教条禁锢后迸发出的强大的创造能量,是知识不断增长的基本动力。批判理性具有双重性,其起点是普遍怀疑,正如笛卡尔在《形而上学的沉思》里所说,“凡是我从前信以为真的东西,没有一件我不能加几分怀疑;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②。在他那里,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追求真理的绝对信念,一切都在怀疑之列。既然知识追求永无止境,那么质疑、挑战、叛逆也就不会停歇。但批判理性绝非专事破坏、否定,其另一面充满着建设性、创造性的力量。它不但致力于构建普遍性的知识原理,而且要按照理性和理想来改造社会。第三,重视语言之维。中国传统思想没有把语言纳入形上学(道论)的思考,所谓道本于心性无须假言,道体粲然莫可名也。中国薄弱的知识论传统也少有深研知与言之关系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承当,它以训诂为主体,重在字词意义的训释,不重语句分析,几乎不从形式上把握语言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是便把握不到带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和世界的形式结构。直到晚清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汉语语法问题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因而古代文论中不满足于从技巧、修辞角度看待语言,而试图将其提升到文化哲学、语言哲学、心理哲学高度的语言论几成绝响。此后,中国学人开始努力构建具有自身特点的语言论,譬如朱光潜在《诗论》里提出的颇富创见的以情感思想语言一致说替代形式与实质关系说。今天看来,这样的新见实在太少。西方极为发达的语言哲学传统源于逻辑-数学传统,逻各斯兼有言说与理性两义,逻辑-语言-形而上学连为一体的传统在17世纪前的霸主地位不可撼动,至今余威犹存。
篇8
近十年来,笔者开始进入文艺学(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领域,也连续多年给本科生讲授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与中华审美文化》,因此在易学与美学的关系上有所思考和体会。令人困惑的是,如何把易学和美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更好地解决这原本属于不同的学科在比较和整合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在设想,如果我们既能用美学的思维来阐释易学,又能用易学的思想来阐释美学,或许能对两个学科都有启发和指导作用。当然,要正确理解易学与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要的不是论述彼此历史上的联系,也不是对两种学科思想作机械的比较和联系,而是应该更客观地从大哲学、大理论的高度把握两者之间共通不悖的事实。在此,笔者只是希望能够通过对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观,来发现一些被人忽视和遗忘的东西,也借此阐述一下研究易学与美学关系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美”字的易学解释
(一)“美”字源于八经卦中的兑卦。在中国研究美学,首先难免要问及的便是“美”字的意义,也就是涉及到对所“审”之“美”字的理解。时至今日,人们对“美”字基本上已形成普遍的看法,正如百度百科对“美”词条的解释:“美měi,会意。金文字形,从羊,从大,古人以羊为主要副食品,肥壮的羊吃起来味很美。本义:味美。另外羊是象形字,象征人佩戴羊角、牛角,古人认为这样很美。”这种说法的雏形至少可以远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直到清代《康熙字典》也仍沿用《说文》的理解。古人的说法,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羊大则美,另一是美与善同意。值得注意的是,“美”与“善”在古代中国,不仅都是对审美境界极致状态的形容,而且都与“羊”字相关。可见,要理解“美”和“善”,离不开对“羊”字的全面和深入理解。这也是现当代以来,我国许多美学家都从“羊”的角度来理解“美”的原因。于是,从羊这种动物的基本现象,如“肥大”、“味甘”、“温顺”、“可爱”等,来加以解释的思路比比皆是。毋庸置疑,从文字学的角度,根据汉字的形体及其造字的法则,把“美”的意义跟“羊”有机联系在一起,是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的。但是,认真追问起来,还是感觉如此解释不够透彻。所以,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从符号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这也是符合文字发展历史和规律的。
我们知道,在汉字基本定型之前,《易经》的八卦符号已经出现。由于史阙有间,我们已经很难证明汉字的出现是奠定在《易经》卦爻符号系统之上的,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推证汉字与《易经》文化可能存在着密切联系。沿循这样的思路,笔者发现“美”和“善”的取象意义,可能都是源于《易经》八经卦中的兑卦。查考《易传》,《序卦传》有“兑者说也”、《说卦传》中依次有“兑以说之”、“说言乎兑……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说万物者莫说乎泽”、“兑,说也”、“兑为羊”、“兑为口”、“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别卦《兑》的卦辞是“兑:亨,利贞”,其《彖传》的解释是“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其《象传》的解释是“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不难发现,在《易传》中,“兑”的取义为“说”(通“悦”),即“欣悦”、“喜悦”之义。此义与《兑》卦辞“亨,利贞”的意思基本上也是相通的,这说明《易传》的说法仍然没有离开《易经》。
《易经》滥觞于“观物取象”,其象征思维离不开对自然万物的观察,然后再用虚拟的符号加以形象概括,并从中归纳出具有根本性质的意义。简言之,先取象,后取义,然后又可以“触类”取象,也可以“合意”再取象。正如东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指出:“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易经》的象征思维和类比思维,可以使同一个符号跟无数个相类相合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无限发展的意象群。在这个意象群里,彼此之间要么有相类之象,要么有相合之义,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真正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妨以兑卦为例加以分析。八经卦中的兑卦,卦象是,在《易传》中其主要象征为泽――沼泽、湖泊(上面一个阴爻象征平静的浅水,下面两个阳爻象征坚硬的土层),根据对自然的观察,凡是沼泽和湖泊之地,都是风光独特之所,让人容易引起美感而“欣悦”(从另一个角度看,泽被万物,滋润营养,万物因而得“悦”);还可象征为少女――年轻的女孩,丰润貌美,惹人“喜悦”(从卦象看,跟梳着两个辫子的小姑娘相类);还可象征为羊――温顺的动物,形声和美,也是惹人“喜悦”(从卦象上看,跟羊的形象相似,上面一个阴爻如同两个羊角,整个卦象与“羊”字也大体相同)。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美”和“善”两字中的“羊”,不止是指代“羊”这种动物,而更可能是与兑卦整个象征系统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羊”只不过是对兑卦象更进一步的具象化和形象化而已,或者说“羊”就是兑卦象的典型代表之一。
(二)一阴一阳之谓美。看到这个小标题,熟悉《周易》的人自然会联想到《系辞上传》第五章中首句“一阴一阳之谓道”。对这句的理解,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笔者只想从比较的角度尽可能简单地理解这句话。“阴”“阳”“道”三字,实际上是三个符号,“阴”和“阳”各自象征两类不同的东西,看似截然不同,事实上又都同属于一个整体――“道”;而“道”是一个可以指代万事万物的符号名称,大到整个宇宙,小到最小粒子,远到宇宙本源,近到当下世界,无论是物质性还是精神性的“东西”,都可以“道”代称。既然如此,那么能够给人审美愉悦(“欣悦”)的“美”,尽管无法准确定义,但完全可以肯定“美”无论是本质还是形式,都是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一定也是“道”;或者更直接地说,“东西”与“道”是异名同实的,都是一个符号名称而已。因此,理解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含义,也就可以理解“一阴一阳之谓美”了。
美的本质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之问”,事实上也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追求。柏拉图的思路大致可以简单理解为:“事物各不同都被称为美,后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决定他们为美。这就是美的本质。”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转换成另一表述:“事物各不同都被称为易,后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决定他们为易。这就是易的本义。”本义与本质,都是指根本性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各种事物的共相。共相,就是相关处、联系点。而联系点,有远近之别。在同一时空中的事物尽管显现为千差万别的现象,但都根植于同一时空的本体世界(即道体),最远也最为根本的可追溯到宇宙的起点,最近也最为宏观的可追溯到两种事物共同的起点。以最远而论,万物本是同一体质(即本质相同、同道),因此可证万物本来是相同相通的,当然也就可以同名同义;以最近而论,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亲有疏(如同一姓氏的同时代人,有的是同祖父,有的是三百年前同祖宗,有的是三千年前同祖宗,前所谓“联系点”即如“祖宗”),因此可证万物的演化是相通但又是相异的,那么也就会出现同名异义(有如同姓异名一样)。可见,所谓的“本质”,既可指一成不变的本体,也可指随时变异的各个联系点。那么,以不变观之,“美”的本质跟“易”的本质都一样,同是(属于)绝对不变的道体,简言之:美的本质是道(实体)。以变观之,“美”跟“易”(可推至所有字符)的本质都一样是无所不包,不一而足的,其意义跟具体的指称相联系相等同,简言之:美的本质是变(虚体)。由此联想到维特根斯坦的“用法即意义”、“美是一种家族相似”之论,我们可以发现“易”和“美”一样,都是没有固定本质,也没有固定外延的。至此,也可以更透彻地理解海德格尔“美存在,但不可言说”的观点。
绕了一圈之后,再回到《周易》经传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中“易”之意义复杂多变,说明《易传》作者并没有把“易”义定死了,而是赋以变化之美,唯一如同下定义的表达“生生之谓易”,也是运用变化的思想来加以体现。生生不息,既是现象,也是规律;既是理论,也是方法;既很简易,又很复杂;既是本质,也是差异;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既是可知,也是不可知;既是主观,也是客观,真是妙不可言!说不可说之道,就是如此而言!明于此,我们就不必再千方百计去考证“易”作为书题的含义了,因为:“易”作为书题的含义因其命题者“引而不宣”而彻底隐蔽了,但又因为“易”的意象群在史料中和生活中广泛存在而且意义“显露无疑”,尤其是《周易》经传的完整传世,使得后人可在易学思维的指引下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易”的符号与意义。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易存在,但不可言说”。
(三)“易”字源于先民的审美取向。当我们在时间长河中逆溯时,就可以对事物的本源问题有更客观的理解。人类如同星球一样,都是有一个开端的。地球出现数十亿年后,人类才诞生。人类诞生之后,愚昧无知地生活了非常漫长的时期。由于居住地环境和气候等的差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类,也都各自打上所处自然的烙印,体现出许多明显的不同。在人类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中,不同区域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进程中得以生存和延续,因此而形成的生活习性和审美取向也就存在差异性。换言之,不同种族或民族在繁衍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审美追求。自然特性和文化个性的差异,导致不同主体对客体的理解方式和思路不同,最为直接的就在于指事符号及其系统的差异。人类文化的形成看似复杂,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易学文化也必然存在一个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取决于发源地的自然生态,其次又奠基于聚居地的文化生态,而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具有独特性的审美文化倾向逐渐清晰、完整、扩大,乃至演变成具有核心理论体系的思维与思想。
在一个尚且无法用语言符号来表达思想的时代,可以推想那是多么原始和落后!翻开中国的典籍,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在传说伏羲氏“观物取象”创制八卦符号之前,华夏的先民是无法描述眼前世界景象的,也是无法表达并纪录内心所想的,但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动物应该已经具有一定的生存本能。有生存本能,是否就意味着具有审美本能呢?人类是有生命的,而生命的维持需要阳光、水分、空气、食物等等,而这些并非都能自动进入人体,必须经过人体的选择、获取和吸收等过程;这一过程看似人的天性和本能,实际上已经包含着某种审美取向,完全可以理解为审美本能。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的审美本能,大致应与人类的诞生同步,否则人类的生存就得不到应有的保证。随着漫长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本能在审美实践中逐渐由自然转向人为(各种条件和因素,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了),从量变到质变,促使人类开始进入文明发展的阶段。这种转变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也还是自然而然的!
自然的审美本能,与人为的审美本能,显著的差别无疑就在于人类智力的成熟,开始具有一定的审美思想与方法了。那么,审美本能也就脱胎换骨,演变成人类独异于低等动物的审美功能了。有了审美功能,人类就可以更主动地趋吉避凶,更好地生存和生活了。对于人类而言,不论处于何种社会阶段,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趋吉避凶。如果我们可以把趋吉避凶的本真想法及其行为,笼统地理解为人类的审美活动,那么也就可以从审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近几千年人类文明的进程。
基于以上的想法,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易经》的趋吉避凶思想乃是一种具有模式化的审美思维。任何一个汉字,包括“易”字,都是审美文化所造就的,一定是源于先民的审美取向。因此,研究《易经》,完全离不开研究造就《易经》的早期华夏先民的审美文化,也同样离不开整个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中华审美文化。进而言之,《易经》乃是远古华夏先民审美文化经验的结晶,其作者乃至后续的传承者和研究者以及运用者们都可视为这一辉煌灿烂审美文化的主体。从审美入手,关注文化,联系主体,《易经》所独具的趋吉避凶的审美功能,无疑就具有了巨大的人文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易学与美学的融通
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诞生于十八世纪的西欧德国。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许多哲学家、美学家不断对美学的内容性质与研究对象展开探讨,但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根据德文Aesthetica的原意,中译应该是感受之学,在中国称之“美学”是转译日语造成的。从研究的过程与结果来看,美学与哲学、文化、心理、艺术等都有密切联系,尤与艺术学如同一类。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学看似独立,却与不同学科都有联系,已经可以涵盖所有学科领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因此,我们很难解释清楚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解释不清,意味着用于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存在问题。长期以来,中西方的学者都惯于运用西学的逻辑思维来认识和理解世界,不但没能把根本问题解决,反而衍生了许多假问题。倘若我们能够运用易学思维来反观美学,也许就能解释得更清楚更透彻。那么,什么是易学思维呢?面对这个带有西学思维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无法运用语言加以准确表述的,只能通过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加以理解。笼统地说,易学思维是一种符号思维、形象思维、意象思维、象征思维、类比思维、感性思维、直觉思维、整体思维、太极思维等的合称,源于《易经》思想,涵盖道、理、象、数、占,贯通天、地、人,力求效法自然变化法则。以下姑且用太极思维指代易学思维,并作简单论述。
整个宇宙世界是一个太极整体(即道体),任何事物无论巨细都是一个太极整体(物物一太极);任何一个太极整体,都必须包含阴和阳两个方面(两种东西);任何一个太极整体都是无法运用语言(符号)准确描述的,只能运用语言(符号)加以准拟(象征)。当人类懂得运用语言(符号)准拟事物(太极整体)之后,时空观念才逐渐得以形成,世界才得以定位。于是,人类开始拥有描述历史的时间观念。依据长期观察和记录而形成的时间学(天文历法之学),人们开始主观地认识客观世界。在认识过程中,人们发现任何事物都有开端,有始终,有历史。依据历史时间观,人们通过追溯发现: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源(道、无极、太极、时间起点,太极本无极),伴随时间的展开,本源中的存在物自然而然地按照时间顺序(理)发生演化(造化、变化、独化、自化、物理和化学变化),如同前一世界生出后一世界直至现在世界(生生之谓易),如同一阴一阳的不断转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每一次演化的现象结果(气、象),都是自然程序密码(数)的体现;时间之流,是绵延不绝的,前后贯通的,时空混合的,一时一世界,所有的世界同属一个整体,是没有间隔距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妙不可言的;因此,面对具有同一性的世界,只要掌握其中任何一个事物(太极整体)的信息,借助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心物合一、物我两忘、与时偕行)就能彰往察来(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当我们运用太极思维来看美学时,就能很好化解美学的逻辑矛盾。美学研究至少有三大难题:一是美的本质问题。前已述之,美如同道一般,不是一个实体却又寓于一个实体之中,是一个虚体却又寓于一个具体感性的实体之中。换言之,美是亦真亦幻,无法定义。如果因此完全取消“美的本质问题”,美学就立刻失去哲学之根,与根本问题绝缘,显然不可取;反之,长期面对一个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美学家变得不知所措。这无疑是美学研究的心病!二是美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有很多人都认同美学是“美的艺术哲学”,几乎是把美与艺术等同起来。而事实上,艺术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并非美的全部。三是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为了避免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纠缠不清,西方现代哲学家开始以美感说美,更加注重主体(人)的审美心理、审美经验,甚至把一切审美现象都归结为必须跟人相关,侧重研究人与客观世界的审美关系。这样,研究人(审美主体)与世界(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了现当代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不难发现,为了解决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西方美学已经逐渐在向中国传统学术思维靠拢了。
至此,我们再进一步运用太极思维来处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更加清晰了。以太极整体而论,所有审美现象都“同一太极”,彼此联系,不可分割,都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以太极整体中的情况看,“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一“美”的整体都包含两方面的关系(阴和阳),美学要研究的就不能只是“阴”,也不能只是“阳”,而必须是“阴和阳之间的关系”。同理,“美”不只是“阴”,也不只是“阳”,必须是“有阴有阳”,是虚实相生的一种意象或意境。明于此,我们就可以使中西方美学理论对接融通:所谓“美”就是阴阳相依的太极,是意象或意境式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审美”(艺术鉴赏)就是知道、悟道(感知太极之道),阴阳合德,物我交融,人天合一,神与物游,主体与客体瞬间的有机统一;所谓“作美”(艺术创作)就是合道、体道(模拟太极之道),阴阳相须,有无相生,文质彬彬,情景交融,虚实相半,真幻相即,形神兼备,色相俱空,物我两冥,生动逼真,形成一种具有“艺术真实”的作品。
反之,我们也可以运用美学思维观易学。美学不论是指哲学美学、艺术哲学,还是指研究审美心理、审美经验、审美文化、审美历史、审美现象、审美规律、审美活动、审美范畴、审美原理等的学科,都体现出没有边界、不受局限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学科领域“无边界”的美学与易学一样,都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按照西方逻辑学的观点,一个学科沦为“无边界”的说法是危险的,会导致许多逻辑矛盾。这无疑也是把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截然分开之后,在认识和解释现实世界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矛盾问题。美学研究在西方的横空出世,提醒人们治学不能仅仅关注工具理性和道德伦理,还必须深入研究人的感性思维(审美心理、主观判断力);而西方美学研究的穷途末路,昭示人们单纯从理性思维来研究感性的心理问题是行不通的,必须运用理性与感性思维相结合的思路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这一历史经验与教训,同样可以深刻地启示我们当下的易学研究,务必要运用太极思维来看待易学本身,才不会无知地把本身有价值的东西抛弃掉,把本身圆融一体的学问用理性思维肢解成支离破碎。此外,必须着重指出的是,美学走向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与重在研究阴阳关系的易学可谓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但相比之下,以卦爻符号为主体的易学原理体系,毫无疑问在解释可知与不可知的世界时更为根本和透彻。
总之,易学与美学是有机统一的。以易学观美学,美学处处是易学;以美学观易学,易学样样是美学。倘若我们能打破学科的界限,从大哲学、大理论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历史和现实,那么就有可能找到更好地解释宇宙世界和人类现象的思想理论,使原有的知识、经验、文化、学术等融会贯通,让后来者更易于理解和运用。因此,以“审美”之心来研究易学,与以“变易”之道来研究美学,都同等重要,也同样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中国团体操;境遇;本体;再定义;思考
中图分类号:G83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10)05-0122-04
Reunderstanding on China’s Group Calisthenics under the View
of Ontology
――A Thought on Group Calisthenics Based on Its Contemporary Condition
ZHAO Haibo1,HUANG Kuanrou2
(1.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 25000, Zhejiang China; 2.Institute of sports and science of China South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redefines the concept of group calisthenics by making historical and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indicates that “collective cooperation action of spo rts” is its ontology, and “the performance effect for spectacular appearance o f significant form” is its performing form, and many kinds of “collective coop eration action of sports” through “artistic weave” is its main performing tec hnique. Furthermore, the improved taste of beauty appreciation and the demand o f culture under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time are the main impetus for the evolu tion of china’s group calisthenics. The purpose is to review the contemporary
condition of China’s Group Calisthenics. For China’s Group Calisthenics, it i s not only a kind of defense of its “selftheory” and reunderstanding to it , but an exploratory study for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it.
Key words: China group calisthenics; contemporary condition; ontology; r edefine; review
中国团体操,以其独立而严谨的表演编训体系、独具特色的大广场表演效果,在上个世 纪中后期得到社会高度认同而成为主要的广场表演形式,并依托其发展的土壤――现代运动 会开幕式,得以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而广泛包容的体育审美形式,在我国堪称广场体育艺术 。然而随着社会审美意识和人们文化诉求的提升,团体操逐渐失去了运动会开幕式表演的话 语权,而“团体操美学”的滥觞,使包括体育界在内的诸多人士发出团体操是“时代的产物 ”、“集权主义的象征”等评论,中国团体操的当代生存境遇不容乐观。基于学科的自觉性 和对中国团体操这一百年体育文化的保护,本文提出对团体操“本体”的探究,并对建国以 来以“大型团体操表演”命名的运动会开幕式进行研究,尝试对团体操独立的本质特征、表 现目的、表现形式以及表现手法等进行追寻,以此为我国团体操当代的生存危机和潜在的生 命力提供学理上的辩护和求证。
1 中国团体操的当代生存境遇
美国学者福山关于意识形态“历史的终结”似乎点明了我国团体操的当代处境。回顾我 国团体操蓬勃发展时期,恰是集体主义强势要求下的建国后时期,在各类运动会或庆典演出 中团体操以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得以利用。然而当代诸多人士(包括体育界)认为,团体操如 同具有时代特质的“红色经典”序列那样,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1.1 “团体操美学”的滥觞――危言耸听下的团体操
当视觉文化充斥现实社会时,基于对反映大型战争暴力、集会场面的影视评论中,文学 界创造了“团体操美学”这一文艺评论术语。而开启“团体操美学”评论之源的,当属德国 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拍摄的《奥林匹亚》和《意志的胜利》这两部纪录片(前者反映柏 林奥运会开幕式、后者反映纳粹党代会集会),特殊时代的奥运和特殊身份的导演使这两部 纪录片被冠以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经典之作,而其随后的文艺
投稿日期:2009-09-29
作者简介:赵海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场体育艺术(团体 操)。界便有了这一带有意识形态倾向 的评论术语,因此“团体操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美学”、“集权美学”或“暴力美学” 的 统称。我国美学评论家朱大可先生曾提出“时空的伟大性”和“意志的统一”是帝国暴力美 学或权利美学的两项基本原则,更进一步指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影视大片均是建立在团体操 基础上的,是“团体操美学”的体现,也是一种“法西斯美学”或“集权美学”的形式主体 。诸如此类的文艺评论数不胜数,尤其是针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所引发的评论中, 对“团体操美学”的引用和鞭挞更是达到了极致。于是现实中的团体操运动也就自然而然的 被贴以“千人动作整齐划一、体现集体抹杀个性”的特点,而把团体操本身所具有的实用性 价值抛开不管。
1.2 运动会开幕式上的表演――话语权转换下的团体操
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和表演形式,团体操所彰显出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毋庸置疑,然而 随着社会审美意识的提高和对文化诉求的提升,以“团体操表演”命名的开幕式越来越少, 团体操表演越来越被弱化。如果说我国前六届全运会开幕式表演是以团体操表演为主,则第 七届明显是个分水岭,七运会开幕式表演引入了商业和文化的概念,使团体操由单纯的表现 手法向更深层次的表意手法转变。从八运会开始,我国全运会开幕式表演由体育部门负责变 为文艺部门主抓,由此随后几届的全运会开幕式中,团体操便被淹没在形形的文艺汇演 中。表演主体话语权的转化,一方面是政府作用的弱化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经济主导下 的趋势。时至今日包括全运会在内的各种大型运动会开幕式表演,皆以“大型文艺表演”为 主,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征集、参与开幕式表演设计的体育界人士也越来越少,团体操表演形 式退出了历史前台而隐于幕后。
2 团体操本体的探究
针对我国团体操的当代生存境遇,基于学科的自觉性而引出“团体操是什么”的命题就 有了现实意义。相关学术研究表明:我国团体操形成于近代体操传入时期是近代徒手体操 和轻器械操与队形结合的演练形式;兵操与普通体操的盛行是其形成的客观条件;动作造型 、队形图案和艺术装饰是其构成三大要素;团体操是一种体育与艺术高度结合的表演形式 。尽管早期的理论研究促进了团体操的发展,但终究无法消解团体操的当代生存危机。而“ 团体操本体”正是基于此的探讨性解答,因为“用‘本体’表达更加简约、更加自由,它更 像是一个路标、方向标,为我们指向各种体育现象的核心”[1]。
2.1 团体操“本体”阐释
本体论源于古希腊哲学思想,也即亚氏“第一哲学”,在我国被译为“形而上学”。本 体(ontology),指事物的“始基”、“本质”,本体论就是一门研究最高哲学层次上的“ 是”与“存在”的哲学,其一开始仅局限于哲学范畴,并非指某种具体事物的存在。而随着 “哲学平民化”的趋势,本体论从“形而上”的关注开始下放到包括文学、诗歌、戏曲乃至 音乐等“形而下”的具体研究对象上。团体操的“本体”也是“哲学平民化”趋势下的一个 必然。“本体论是以追求终极实在为依托,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任务,以达到终极解释为目标 的哲学”[2]。由此探究“团体操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是”的团体操本体的提出, 就有了“ 本体论”上的哲学意味。其指向是明确的:团体操既然是人体运动的一种形式,而“运动是 物质的存在方式”(恩格斯),那么研究团体操就要考虑它初始的作为一种运动的存在方式 。
由此团体操本体的提出便有了如下意义:首先,把团体操作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自下 而上的理论思考,其研究要旨在于“寻求各种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3],这 样可为团 体操学科建构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石;其次,把团体操“发生体”当作研究对象,探究其发生 体的真实存在形式,这就势必引导人们把目光放在团体操何为“团体操”也即是团体操最本 质的界域,在认识并承认团体操的艺术本质和表现价值的同时,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团体操仅 是“集体做操”的观点;最后,根据上述的思考和研究,推导出团体操独立的艺术本质及审 美特征,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团体操“历史终结”的当代生存危机。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 对团体操本体的追寻也就是对现代团体操表演形式身份认同的一个过程。
2.2 “有意味的形式”――团体操本体的切入点
形式,“通常指事物的外部结构,是事物构成要素的排列或组织方式及表现方式”[4 ] 。英国形式主义美学代表贝尔“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的命题,为团体操本 体提供了探究的切入点,贝尔指出“有意味的形式,是那些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感动我们的排 列与组合”[5]。在他看来那些看似外在的“排列与组合”因其“有意味”,就能 为人所“ 感动”,成为审美对象。形式由构成要素组成,团体操是人体运动的一种形式,因此认识团 体操本体必须从其动作构成要素着手。通过对以“大型团体操表演”命名的运动会开幕式( 前六届全运会、第十一届亚运会、第二、五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等)的影像分析可知,团体操 动作主要有体育动作(基本体操、技巧)、舞蹈动作、模仿动作、特殊动作(组图、技巧造 型、“波浪”)等四大类典型动作,如图1所示。
图1 团体操动作示意图(各动作类型不分先后) 作为开幕式的运动场或其它场地,因其空间大而产生的视觉上的空旷感,必然会使观者 有“恢宏大气、场面壮观”的、表现“崇高”的审美情感需求。团体操按其字面意思既是“ 集体做操”,而集体做操所反映出的“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的集体运动场面,恰与上述心 理审美需求达到契合,这就为团体操作为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形式提供了现实基础。团体操 的四大典型动作表明“集体做操”仅是现代团体操表演的形式之一,或者说是其最简单的表 现形式,集体技巧翻腾、“波浪”、组图以及造型等,无论在表现团体操全场主题如“全民 同庆”、“革命赞歌”、“红旗颂”、“凌云志”、“奋飞”等,还是在表现团体操分场主 题如“红色接班人”、“火红的战旗”、“群英比武”、“祖国万岁”、“新的高度”等, 均能给人带来一种“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视觉审美上的震撼,由表及里的一种心理上 对“集体动作力量美、崇高美”的赞叹和折服,以及对团体操表现主题的深刻理解,从而凸 显出团体操深刻的人文价值。团体操不讲求戏剧性的情节展现,而是以粗线条、大画面的表 现手法做“泼墨式”的艺术构图场面,因此这种由集体动作表现出“有意味形式”的、追求 运动场面艺术编织的表演效果,才是团体操所重视的表现形式,也是其追求的目标。
2.3 集体体育配合动作――团体操本体的确证
无论是集体做操、集体技巧翻腾亦或是“波浪”和组图造型等,把体现“有意味的形式 ”的大场面表演效果作为最根本追求目标的团体操,其发生的“始基”正是大场面的集体体 育配合动作,而这也正是团体操所要探究的本体。
集体体育配合动作分显性和隐性两种类型。有肢体接触的动作似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 体配合动作,这种观点在以人体动作为表现主体的各类表演形式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波浪 ”、组图造型和“叠罗汉”等呈现给外界的是一种显性集体配合动作,这些动作语汇势必需 要表演者有肢体上的接触、按照一定的人体排列和组合、遵循一定的运动路线做出相应的动 作方能完成,其直观的表现手法呈现给外界的是一种一目了然的集体配合动作。但在明确了 团体操以追求“大场面表演效果”为根本目标时,集体配合动作有了更深层次上的理解,有 “场面”必须有配合,“场面”产生于集体动作的配合中,所以没有集体动作的配合,也就 无从谈及大场面的表演效果。因此即使最简单的“集体做操”,也是基于“集体配合做动作 ”基础上的,因为“集体做操”也是在刻意地表现一种大场面的表演效果。因此基于集体配 合动作的分类,团体操动作又可如图2所示。
图2 团体操集体配合动作示意图 毋庸置疑,包括舞蹈在内的其它形式的表演艺术,也不乏有大场面的表演效果和集体配 合动作,但艺术发展史指出,舞蹈是“以塑造出具体生动的、可感知的人物形象为表演形式 ,以表现人的情感和思想为目的的一种审美形式”[6]。因此,尽管团体操和舞蹈 都脱离不开人体动作,但团体操重场面的形式表演,舞蹈重形象的情感刻画。表现形式和表 现目标的不同,构成了区分团体操和舞蹈等表演艺术的主要标志。
3 基于“本体”对我国团体操的再定义
概念是思维形式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构成知识结构的最基本要素,团体操可持续性发 展的动力最终也要落实到其科学的概念界定上来。定义也既是“界说”,“是揭示概念所反 映对象的特点或本质的一种逻辑方法”[7],内涵和外延是概念最基本的逻辑特征 ,内涵是 概念反映对象的本质,外延是反映在概念中的一个个、一类类的事物,因此定义不仅要有明 确的内涵也需要明确的外延。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或表演艺术,团体操只有找到“本质”才能 保证其独立自主的发展,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显现其存在的价值,而对团体操“本体” 的追寻,无疑对挖掘团体操的本质提供了最直接的关联,也为其概念的界定提供了最简洁的 路径,因为“本体”即事物的“始基”或“本质”。
从上个世纪中后期,我国团体操领域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团体操定义的尝试性研究(如表 1所示),这其中包括不同时代奋战在我国团体操领域的体操、团体操专家的专著和论文中 。在这些带有实践积累和经验总结的论述中,闪现着我国老一辈团体操专家的真知灼见。不 同时期的表述既表明了人们对这一表演形式认识的不断发展,也表明了团体操随社会审美意 识而提高的发展规律。这些思索与观点组合使团体操逐渐接近其自律理论的边缘。
表1 我国团体操有代表性的定义表述
时间出处定义表述
1957《团体操表演》上海市体育运动竞赛委员会运动竞赛科主编出现在大规模的运动竞赛会上的一种集体性体育活动,具有一定的表演的艺术性。1961 《体操》人民体育出版社由几百、几千人在运动场或广场上进行的体育 表演项目。1979 《体操》人民体育出版社由几十、几百以至成千上万人参加,在运动场或广场,以及在游行队伍中所进行的一种群众 性的体操表演项目。 1980《团体操的创编与训练》人民体育出版社综合了体育、音乐、美术的,具有艺术性的集体的体育表演项目。1988《中国团体操》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一种体育与艺术高度结合的、以体操动作为主的群众性体操表演项目。1991《体操基本理论和教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通过徒手体操、轻器械体操、舞蹈和技巧动作,队列队形,各种组图和造型,再配以音乐、 服装、道具、背景等艺术装饰构成的表演主体。2000《健美操 团体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体育与艺术高度结合的综合性的集体表演项目,动作造型、队形图案和艺术装饰为三大构成 要素,堪称广场体育艺术。2007《团体操》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为运动会开幕式或国家级的庆祝活动专门设计的,在体育场中,在主题思想的引导下,借助 最新的科技手段进行的团体文体表演。
如前所述,“有意味的形式”的“大场面表演效果”是团体操追求的目标,“集体体育 配合动作”是其本体,那么通过“集体体育配合动作体现大场面表演效果”,无疑就成了团 体操表演的本质特征,而这也正是团体操概念所要表述的内涵。“集体体育配合动作”已指 明团体操属于一种人体表演,因此团体操的属概念应为“表演艺术”,而这种人体表演艺术 形式体现的是对多种“集体体育配合动作”的艺术化编织。
因此根据“被定义项=种差+属概念”的公式,团体操(广义)定义可以表述为:是一种“ 由集体体育配合动作来体现大场面表演效果的表演艺术形式”。一般采用整齐划一的体操动 作或体操化了的舞蹈动作,通过对灵活多变的队形、立体壮观的造型、富有寓意的图案等多 种表现形式的艺术编织,在音乐、道具、灯光乃至背景台等烘托下,集中体现一种大动势的 表演场面,有统一的主题思想。
4 本体论视域下对我国团体操发展的思考
4.1 自律理论――团体操发展的关键
团体操的生存归根结底要建立完整的自律理论,自律理论的缺乏导致其始终处在“他律 ”、“通律”的影响下,这也是影响我国团体操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纵观我国团体操的 发展史,其实践层面的研究远远超过了理论层面,而理论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现象”层面 (发展趋势、艺术装饰、动作造型等),对涉及团体操本质特征和审美特征,尤其是团体操 发生体方面的研究尚不深入。本体论视域下对我国团体操的研究,可以揭示影响团体操发展 的根本,从而寻找团体操发展的自律理论,因此对其自律理论的完善,就成了我国团体操未 来发展的关键。
4.2 现实实用性――团体操发展的可能
中国团体操即有“气势宏大、图案优美、形式丰富、整齐有序、技巧高超”的外观,又 具有“主题鲜明、内涵深刻、构思严紧、结构完整、层次清楚”的内相[8],鲜明 的民族特 色使中国团体操成为世界团体操花坛中的一朵奇葩。特殊时期的中国团体操,作为包括全运 会在内的各种大型运动会开幕式的“价值定义”,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备受关注,因此当团体 操表演在大型运动会开幕式中减少时,其“终结论”势必难免。然而当团体操依然作为诸多 幼儿园、大中小学乃至企事业等基层单位的运动会或庆典开幕式上的表演形式时,表明团体 操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价值依然被普遍认同,这也是团体操“草根”性最直观的体现。团 体操的“本体论”决定了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用性,而这也决定了我国团体操未来进一步发 展的可能。团体操表演不是曲高和寡的表演艺术,而是贴近大众、贴近现实的广场表演形式 ,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是其价值体现的一个平台,但不应仅仅局限于此。
4.3 广场体育艺术――团体操发展的升华
时代进步下审美和文化诉求的集体提高,是促进我国团体操变化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近 代西方体育的传入,在“健身强国”意识形态感召下,“集体做操”式团体操成为上个世纪 重要的广场表演形式。建国前后,形成了在“集体做操”式团体操的基础上,与造型图案互 相配合,同时配以简单的艺术装饰,表现一定主题的广场表演形式。六十年代后,团体操与 其他文体形式如民族舞蹈、武术和技巧动作以及符合各场特点的服装、道具等互相配合,在 丰富多彩的艺术修饰下,表现出更加强劲的大广场表演功能。时至今日团体操更是形成了以 大的空间为表演场地、以多种集体体育配合动作为表演主体、以集体运动场面的艺术编织为 表现手段、以宣传“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彰显人类追求“真、善、美”精神境 界的一种广场体育艺术。张艺谋在创编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时所承认的“太极拳和团体操 ,这是很经典的一种符号”,也为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5 结 语
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产生了认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 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随着 时展和社会审美意识的提高,团体操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当把表现“大场面表演效果” 作为团体操有意味的表现形式、把“集体体育配合动作”作为团体操本体、把对多种“集体 体育配合动作”的艺术编织作为表现手段时,不难发现团体操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所凸显的强 劲生命力;团体操(广义)是一种“由集体体育配合动作来体现大场面表演效果的人体表演形 式”。一般采用整齐划一的体操动作或体操化了的舞蹈动作,通过对灵活多变的队形、立体 壮观的造型、富有寓意的图案等多种表现形式的艺术编织,在音乐、道具、灯光乃至背景台 等烘托下,集中体现一种大动势的表演场面,有统一的主题思想;当代团体操表演被加入了 更多的人文色彩而显得更富有内涵,本体论视域下对我国团体操的再认识,其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传承我国这一有着百年发展史的体育文化,由此促进了我国这一广场体育艺术的进一步 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震昊.“体育”本体论(三):体育的本体和哲学矛盾[J].南京体育学院 学报,2006,20(4):7-15.
[2] 张岱年.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M].谢龙.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北京大学 名教授演讲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
[3] 吕艺生.舞蹈学导论[M].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 印书馆,1961:234.
[4] 吕艺生.舞蹈学导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160.
[5] 蒋孔阳.二十一世纪西方美学名著(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155.
[6] 隆荫培,徐尔充. 舞蹈艺术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