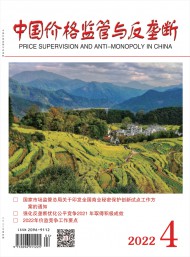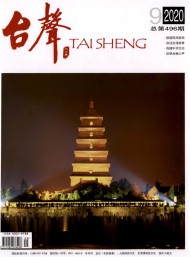正当程序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12:39:56

正当程序范文篇1
实验设计
本实验参照甘高实验基本框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计,但与甘高实验有两点基本的不同:首先,本实验除了检验正当程序的具体标准对程序正当性的影响,还将验证立法程序是否影响人们对于立法结果的接受程度———前者探讨的是“怎样的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后者探讨的则是“正当程序有用吗”。在具有悠久正当程序传统的国家,后一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国,这仍是正当程序研究的基本问题。同时,后一问题也可理解为: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正当程序的理念已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对此的实证研究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其次,本实验并不会重复“伦理性-事务性”这一议题分类———正如甘高所承认的,影响程序正当性评价的议题分类具有多样性,对此的一般性研究尚不深入。④因此,本实验选择了平等领域中“易产生差别感-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分类,并希望实验结果有助于程序正当性评价中议题分类所起作用的一般性研究。此外,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受试者的熟悉程度,本实验的测试内容集中于立法的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一)假设本实验首先意图探究的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接受立法结果,尤其是那些自己本来并不认同的立法结果。因此,基于传统的正当程序理念,本实验提出假设如下:假设1:人们越是感觉到立法程序是公正的,就越容易接受立法结果。那么,怎样的程序才是“公正的立法程序”呢?从实验的角度,需要将“正当程序”这一理念具体化为若干可以衡量与比较的因素。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有深厚积累,如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二原则”、美国学者萨莫斯提出的十项“程序价值”、贝勒斯提出的八项“程序利益”、我国学者季卫东提出的程序的四项基本原则、六项构成要素和八项判断标准等。⑤在此基础上,结合立法的特点,本实验提出体现立法程序正当性的三个要素:平等参与、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在本实验的设计中,平等参与一方面表现为利害关系各方都具有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表现为官方的中立性———因此,本实验考察影响程序正当性的四个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其中有两个都涉及到程序的平等属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无论是三个要素还是四个制度特征,都还只是较抽象的概括,在制度上仍然有不断细化的空间;在相对全面地考察正当程序各制度特征的同时,还有必要就某一特征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因此,本实验针对正当程序的平等属性,即“平等的程序”,试图进行相对更为深入的探究。参照甘高实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假设如下:假设2:具备正当程序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的立法程序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的评价。假设3:当立法程序欠缺相关的制度特征时,实体观点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评价的影响就超过相关制度特征的影响。在议题方面,本实验关注平等领域。这是由于我国目前在立法平等领域中存在着大量争议问题,这既为实验的设计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令本实验具有更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尽管本实验不会重复甘高实验中“伦理性-事务性”的分类,但这种分类是富有启发性的:它区别了人们支持某类实体结果的坚定程度,这显然会影响其对于程序的评价。因此,本实验采用“易产生差别感-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分类;这里的“差别感”指对于处在不同情况中的个人或群体的强烈感受,如厌恶、崇拜、怜悯等;而“不易产生差别感”就是指即使和对方处在不同情况中,也不会对其有特别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平等问题的背后正是差别感。经验表明,易产生差别感的议题相对而言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从而更容易令人产生“正确结果”的预期;在本实验中,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选择家庭出身,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选择生活方式。本实验的这一假设表述如下:假设4: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实体观点对立法过程正当性的影响大于正当程序制度特征的影响;涉及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则相反。本实验设计了两组虚拟新闻报道: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是关于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享有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的立法(记为“甲组”);涉及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是关于公园禁止衣衫不整者入内的立法(记为“乙组”)。(二)实验步骤本实验的基本步骤是:首先,请受试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问卷A),调查内容包括受试者的基本情况以及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然后,请受试者阅读给定的虚拟新闻报道。最后,请受试者就所阅读的内容填写第二份问卷(问卷B)。本实验以在校大学生作为受试者,⑥因此在问卷A中受试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校、专业类型、入校时间和入校前的户籍情况。调查的问题包括平等观(倾向于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平等感(对社会现状是否平等的感受)、产生不平等的因素、对虚拟新闻报道所涉议题的实体观点(即“外来工子女是否可以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入学”或“公园能否拒绝衣衫不整者入内”)、社会参与度、对立法是否公正的感受和对执法是否公正的感受。调查问题中,“产生不平等的因素”给受试者提供备选因素,其他问题的回答都用从0到1的数值标注:非常积极=1,积极=0.66,消极=0.33,非常消极=0(在对平等观的回答中,结果平等=1,倾向于结果平等=0.66,倾向于机会平等=0.33,机会平等=0)。在问卷B中,针对假设1的问题表述为“本文中,您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地方立法机关的最终决定”。针对假设2的四个制度性因素,“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与您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机会表达意见”;“官方的中立性”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是否存在官方刻意偏袒或压制某种观点的情况”;“充分交流”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的各种观点在立法讨论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交流”;“信息公开”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社会大众在本文所描述的这个立法过程中所能了解的立法信息是否充分”;而整体程序正当性则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所描述的这个立法过程是否公正”。每个问题的回答都用从0到1的数值标注:非常积极=1,积极=0.66,消极=0.33,非常消极=0。(三)议题类型及其表述在甲组和乙组的基础上,每个议题都包括两种相反的立法结果,而每种立法结果又各包含“符合正当程序”和“欠缺正当程序”两种情况———这样,虚拟新闻报道就有八种类型(参见附表一)。同时,本实验设定的四个制度因素都会通过特定的叙述方式加以对比表现(参见附表二)。
实验过程及数据
实验于2012年第一季度在广州高校中开展。共有427名学生有效完成实验。实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确保没有学生重复参加。在所有受试者中,女生占50.4%,男生占49.6%;受试者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28岁,平均年龄20岁,其中年龄介于18至22岁之间的占94.1%;理工科专业学生占50.8%,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占46.4%,艺术或体育专业学生占2.8%;入学前为城市户籍的占52.2%,入学前为农村户籍的占46.4%,还有1.4%的受试者不清楚自己入学前的户籍类型。在实验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方面,运用SPSS软件的Cronbach'sAlpha系数对问卷中14个询问态度的问题进行检验,系数值为0.702,表明了问卷较好的内在信度。这14个问题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值为0.822,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sig值远小于0.01,表明了问卷较好的效度。实验调查了受试者所认为的造成不平等的因素。问卷列举了八项社会因素,请受试者从中选择容易造成歧视的选项(可多选);这八项因素按照选中率的顺序排列如下(括号内为选中率):财富(73.1%)、家庭出身(66.5%)、职务或身份(55.5%)、个人能力(36.5%)、生活方式(15.9%)、性别(14.3%)、民族(8.4%)、机遇(5.9%)。还有3.3%的受试者填写了问卷未列举的其他容易造成歧视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出身”的选中率远高于“生活方式”。同时,在议题实体观点的调查中,甲组(即“外来工子女是否可以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入学”)有26.2%的受试者选择了不太坚定的回答(即“一般情况下可以”或“一般情况下不可以”),而乙组(即“公园是否可以拒绝衣衫不整者入内”)则有58.1%的受试者选择了不太坚定的回答———这两组数据都有力地支持了以“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进行对比实验的选择。同时,本实验试图通过虚拟报道中的不同描述,在“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四个程序的制度因素上令不同组别的受试者形成不同的感受。按照设计,甲一/甲二、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乙三/乙四这四个对照组均为实体结果相同,但前者符合正当程序要求而后者不符合。用SPSS软件的t检验分析四个对照组相关因素以及对程序公正整体感受的差异性(双侧P值)和样本均数(结果见附表三)。结果显示:四个制度因素以及对程序公正的整体感受在四个对照组都显示出明显差异(双侧P值远小于0.05);而样本均数在四个对照组中都是前者高于后者———这说明不同的虚拟新闻报道的确令受试者感受到了不同。换言之,本实验所提供的描述方式确实以预期的形式影响了受试者,从而确保了验证本实验假设的前提。
对假设的验证
(一)对假设1的验证假设1:人们越是感觉到立法程序是公正的,就越容易接受立法结果。为了验证这一假设,需要考察各组中“程序是否公正”和“能否接受立法决定”是否存在相关性(以下简称“程序与结果的相关性”)。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在各种情况下,这种相关性都应该是存在的,并且都应该是正相关关系。作为对照,还需要考察“实体观点”和“能否接受立法决定”是否存在相关性(以下简称“实体与结果的相关性”)。按照试验设计,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中对于实体的态度和对于结果的态度是相反的,即实体态度的分数越高,与立法结果就越不符合,因此这四组中实体与结果的相关性(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负相关关系,即相关系数应为负数。使用SPSS软件的偏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附表四),分析结果表明:在全部八组中,程序与结果相关性的P值都远小于0.05,即程序与结果的相关性在全部八种情况下都是存在的(相比之下,实体与结果的相关性在乙二和乙三中就不存在),并且都是正相关关系,这就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此外,附表四所包含的信息中,还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尽管程序与结果的相关性在全部八组中都存在,但乙组的相关系数整体上比甲组要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中,程序是否公正对于结果是否可接受的影响较之易产生差别感的议题更为明显。第二,在四个对照组中,程序与结果的相关系数都表现出前者小于后者。换言之,在所有符合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程序是否公正对于结果是否可接受的影响都比结果相同但欠缺正当程序的情况要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欠缺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程序是否公正更为敏感。第三,甲一、甲二中程序与结果的相关系数比实体与结果的相关系数低,而甲三、甲四中程序与结果的相关系数比实体与结果的相关系数高———乙组则不存在这一现象。这可能与甲组中实体观点的倾向性有关:在甲组问卷中,对于实体观点的问题,受试者选择“可以”或“一般情况下可以”的比率非常高(均超过90%)。这就意味着甲一与甲二的立法结果与绝大多数受试者的预期是相符的,而甲三与甲四的立法结果与绝大多数受试者的预期不符。因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在预期结果与立法结果不符的情况下,程序对于结果可接受性的影响更为明显。由于乙组的实体观点没有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倾向性,因此这一点还无法推广到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范围内。(二)对假设2、假设3和假设4的验证假设2:具备正当程序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的立法程序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的评价。假设3:当立法程序欠缺相关的制度特征时,实体观点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评价的影响就超过相关制度特征的影响。假设4: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实体观点对立法过程正当性的影响大于正当程序制度特征的影响;涉及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则相反。这三个假设存都涉及正当程序制度特征、对“程序是否公正”的评价以及实体观点这三者的关系,因此一并验证。为了验证这三个假设,需要分别考察各组中四个制度特征与对“程序是否公正”的评价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下简称“制度与程序的相关性”),以及实体观点与对“程序是否公正”的评价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下简称“实体与程序的相关性”)。如前所述,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中实体与结果的相关性(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负相关关系。而由附表四可知,程序与结果在八种情况下全部为正相关关系。因此,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中实体与程序之间如果存在相关性的话,应该为负相关关系。如果假设2成立,那么在甲一、甲三、乙一、乙三中,制度与程序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假设3成立,那么在甲二、甲四、乙二、乙四中,制度与程序的相关系数应该小于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如果假设4成立,且实体与程序的相关性存在的话,那么在甲一、甲二、甲三、甲四中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应该大于制度与程序的相关系数,而在乙一、乙二、乙三、乙四中制度与程序的相关系数应该大于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附表五的数据显示:四个制度因素与程序的相关性在所有八种情况下都存在,并且都是正相关关系。附表六的数据显示:甲三和乙三的P值大于0.05,不存在相关性;乙一、乙二存在正相关关系,乙四存在负相关关系,均与预期相反。就假设2而言,在甲一、甲三、乙一、乙三中,制度与程序的相关性都是正相关关系;相比之下,只有甲一存在实体与程序的相关性。因此假设2可以成立。就假设3而言,仅在甲二、甲四中,实体与程序才存在相关性,并且其绝对值都明显小于对照组中四个制度因素与程序的相关系数。因此假设3不能成立。就假设4而言,甲二中实体与程序的相关性不存在;甲三、甲四中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明显小于对照组中四个制度因素与程序的相关系数;甲一中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仅明显大于“信息公开”与程序的相关系数,但明显小于“官方是否中立”与程序的相关系数———因此,假设4不能成立。但乙组四种情况下实体与程序都不存在相关性,而甲组则在三种情况中实体与程序存在相关性,因此可以得出较弱的推论:涉及到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实体观点对立法过程正当性评价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大。
哪些因素与对程序的感受相关
正当程序范文篇2
一、从无意识影响到有意识运用
在“陈迎春案”中,虽然法官认定被告的收容审查“违反法定程序”,但是,事实上当时对收容审查执行程序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笔者认为,支撑法官认定的被告不向原告出示《收容审查通知书》等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可能只是朴素的程序正义观念,即被告这种不履行最基本的手续或程序就执行收容审查的行为肯定是不对的,至于被告违反何种“法定程序”,则未明示。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在该案中法官有关“在执行程序上也是违法的”的附言属于对正当程序理念的无意识适用。这是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行政法尚不发达的大背景下,法官对正当程序缺乏基本的认知,更遑论依据正当程序原则作出判决了。事实上,即便是“田永案”,从承办法官到《公报》编辑对正当程序都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更无从谈起有意识适用了。但是,到了“张成银案”,法官明确指出正当程序是作出撤销判决的主要理由。[2]也就是说,法官对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已经演变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虽然我们无法找到直接证据证实,发生“张成银案”之后的“益民公司案”、“陆廷佐案”,承办法官对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但是,在这两件案件的判决书中,法官在说理时均直言“按照正当程序”或“基于正当程序原理”。至少说明法官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已经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截了当地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和理由。这就代表了一种立场和理念,“象征着法官正当程序意识和运用正当程序原则信心的增强,也折射出正当程序理念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已经取得初步却比较广泛的共识”。[3]在《行政程序法》出台仍遥不可期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一味等待立法,而是通过判决发展法律,在行政审判中直接适用正当程序原则。
二、裁判规则/制度的构建
关于行政程序正当的基本原则在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应为程序法定、公正原则。[4]有人认为正当程序应当程序中立、程序公平、程序理性、程序经济。[5]有人认为行政正当原则可具体导出避免偏私、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三项基本内容。[6]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勾勒了正当程序的大致“面貌”,如告知、申诉与辩解、说明理由等。这些零散的内容,不仅体现了正当程序原则的价值,而且不断充实和发展了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使这一原则更为完善而具体。[7]
1.告知与信息公开。依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当事人有权阅览文书、有权获悉与其利害相关的事实与决定。在“陈迎春案”,法官指出被告执行收容审查时,没有出示相关法律文书,即未告知当事人决定的内容和依据。在“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案”中,法院重申了行政机关的告知利害关系人的义务,并认定市政府未送达行政文书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在“陆廷佐案”中,法院认为将评估报告送达利害当事人,便于当事人及时提出意见、申请复估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应有之义,违反告知义务即构成对法定程序的违反,应予撤销。至此,告知与信息公开在司法判决中被确定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之一。
2.陈述、申辩及听证。依正当程序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应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有陈述、申辩权。告知与信息公开旨在让当事人及时了解和掌握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确保当事人能够及时陈述和申辩。在“田永案”中,法官认为,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因而其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在“宋莉莉案”中,法官指出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允许利害关系人“对争议问题予以陈述和申辩,有失公正”,并据以作出撤销判决。在“张成银案”中,二审法院直接将“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作为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之一,固化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需要强调的是听证是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权利的延伸,其核心在于“给予当事人就重要事实表示意见的机会”[8]。或者说是一种较为正式的“陈述与申辩”。虽然前述案例1至案例8未涉及“听证”要求,但并不意味着其作为正当程序原则内涵的缺位。
3.说明理由。所谓说明理由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做出该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和公益等因素。”[9]在“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案”中,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市政府在行政决定中“未引出适用的具体条文”,属于说理不充分,从而违反法定程序。在“中海雅园管委会案”中,法官一连用了三个“如”,通过假设和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述了行政机关未履行说明理由义务,违反法定程序。
4.避免偏私。避免偏私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进行过程中应当在参与者各方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不得受各种利益或偏私的影响。”[10]在“益民公司案”中,法官认为被上诉人市计委在前一批文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直接《招标方案》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笔者认为,在该案中,作为决策者的行政机关未基于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地作出行政行为,违反了公正作为的义务。
如前所述,囿于《公报》案例选用标准高、涉及范围小等限制,上述案例并未全面地反映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内涵。但是,由于《公报》案例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弱强制力”,因此,正当程序原则内涵借以固定下来。当然,现阶段(至少今后一段时间内),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仍处于需要“张扬”和“推进”的阶段,仍需坚持正当程序原则中“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为‘法定程序’,在没有‘法定程序’情形时,可引入正当程序之理论辅助判断之。”同时,要考虑“是否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之因素。[11]
三、适用的方法
1.遵循前案——“典型案件”的指导作用。由于我国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裁判文书的字里行间寻找到法官对“先例”或“前案”的遵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典型案件的《公报》案例,对后续类似案件的审理不产生任何作用。最高法院通过《公报》的形式向各级法院、社会公布“典型案件”,反映了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问题的基本态度,对各级法院具有“参考和指导”作用。同时,法官也可以通过“认知确信典型案件所确立的一般规则最适合于本案的处理时所形成的一种遵从效力”[12]。在笔者看来,作为“典型案件”的《公报》案例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是有事实上的拘束力,尤其是在审理一些疑难复杂、存在法律漏洞案件时,相类似的《公报》案例往往成为法官裁判的“依据”之一,或者说《公报》案例指导法官作出裁判。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法官对“典型案件”裁判理论的继承与发扬。以正当程序为例,在“陈迎春案”中,法官只是含糊其词指出“在执行程序上也是违法的”;“田永案”的判决明确表达这样程序正义理念: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正当程序不只是一个道德约束,更是其法定义务。对这一义务的违反,即构成了行政行为的违法。由此,法官为行政机关设定了正当程序行为规则。该案对于正当程序原则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在其影响下,王纯明诉南方冶金学院不授予学士学位证书案[13]、王长斌诉武汉理工大学拒绝颁发学士学位证书案[14],因案情相似,法官作出了相似的判决。通过“平山县劳动就业管理局案”、“宋莉莉案”等一系列案件的演绎、补充和完善,最终使正当程序原则在“张成银案”中真正步入司法实践,并为“益民公司案”、“陈廷佐案”所沿用。
2.类推适用——《行政处罚法》有关正当程序规定的类推价值。《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将正当程序的内容进行了法律化。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有关正当程序规定的价值并不限于在于行政处罚类案件的直接适用,还应当包括类推适用价值,即当法官遭遇法律漏洞,且该系争案件与行政处罚正当程序规定具有类似性时,可以类推适用该规定以填补法律漏洞。类推适用主要有总体类推和个案类推两个方面。所谓总体类推是指对多数典型案件的判决理由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抽出一般的法律适用原则。但是,总体类推通常只在极少数案件中予以运用。所谓个案类推,就是法官在判断系争案件与法定案型或者说类推对象具有类似性,且符合行政处罚法正当程序规范意旨的情况下,将该法律规范类推适用于系争案件以填补法律漏洞。基于此,有人认为在“田永案”中,法院判决校方的退学处理程序违法,可以类推适用《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大可不必援用“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这一非行政法律原则作为裁判依据。[15]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在行政程序法未制定实施之前,《行政处罚法》有关正当程序的规定,完全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行政法领域以填补法律漏洞。这是因为类推适用并不局限于私法领域,建构于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类推适用同样具有公法价值,进而可以在行政法上运用。[16]
注释:
[1]虽然直接采用正当程序原则判决的案例很少,但是有的判决是附带提及,有的判决是运用了正当程序的理念,有的判决是直接援引了行政处罚法有关正当程序的条款,均被本文作为研究正当程序的行政案例。具体参见附表。
[2]有关上述案件中法官对正当程序的认知与适用的情况,请参见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4]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5]王锡锌:《程序的正义与正当程序――中国法治国家中的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大学法学院1999届博士毕业论文,第86页。
[6]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7]这里只对直接或间接适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公报》案例进行分析、归类,不包括直接援用《行政处罚法》有关正当程序规定的《公报》案例。
[8]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29页。
[9]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10]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1]章剑生:《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1985-2008)为例》,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2]章剑生:《作为行政法上非正式法源的“典型案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
[13]江西省高级法院(2000)赣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
[14]郭嘉轩、詹国强:《“考试作弊”不给学位、法院认定此举违法》,载/l/2002-05-03/23871.html/2010年7月20日访问
正当程序范文篇3
关键词:政策转换为法律/正当程序制度/听取意见制度/公开与说明理由制度/避免偏私制度
一、正当程序及其目的价值
(一)正当程序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普遍法则
正当程序是民主与法治社会应当遵循的一项普遍法则,因为它要求通过一个具有正当性的过程,实现程序的正义和理性并获得实体结果的公正。正当程序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也普遍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适用,指导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各个领域的活动。
正当程序最早可追溯到英国,称之为“自然公正”原则。英国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和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1354年英国国会首次以法令形式明确提到并解释了“正当程序”: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正当程序条款最初适用于司法程序,具体包括两项内容,即“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之后正当程序又逐步运用于行政活动领域,成为衡量行政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在英国“程序公平是一个覆盖整个行政过程的一般原则,也是法院对行政行为予以审查的基本原则”[1].自然公正原则在美国表现为正当程序原则,并得到了宪法的明确规定。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这条规定适用于联邦政府机关,它要求在剥夺私人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符合自然正义的要求,即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做法官;人们的抗辩必须公正听取。正当程序由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的规定而被扩展适用于立法程序。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这条规定适用于各州政府机关。该条要求联邦和州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和正义,政府的行为受到必要的限制。“对立法机关加以防范,因为它最有权力,最有可能被滥用,还要防止行政官员滥用职权,防止由少数人操纵的集团压迫多数人……”[2]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起源于麦迪逊起草的联邦《权利法案》。“当时的正当程序有着精确的司法技术含义,并不涉及联邦立法机构法案本身的正当性问题”,“1868年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生效后,正当法律程序逐渐具有了实质性含义”,从而使“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于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3].
当今世界,正当程序的两个要求为文明社会广泛认同,被视为文明社会的普遍法则。《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欧洲人权宪章》第6条规定:“在有关自己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决定或针对自己的刑事指控中,任何人均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从一个依法建立的、独立的、不偏不倚的法庭中得到公正和公开的审理。”
我国宪法和法律虽然没有对正当程序原则专门规定,但正当程序的要求已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中得以贯彻,在许多法律中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例如《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加立法活动。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九条分别要求提案人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进行审议时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些都体现了立法中的正当程序要求。其他类似的法律规定还有: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有关回避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有关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规定,第六条和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的规定,以及《行政许可法》第七条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的规定等等。
(二)正当程序的价值
正当程序能够成为一个普遍规则,在于正当程序的价值。关于正当程序的目的价值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两种观点。两个方面的内容指的是实体意义上的价值和程序本位价值两个方面的内容;两个观点指的是“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程序工具主义认为,程序不是作为自主和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它没有自己内在的正当性的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实体法的“功利”的工具和手段,是“附属”的法。法律程序的好坏,在于程序对实体法的意义。如果这种程序能够使实体法上的规定得以理性、公正地实现,也就是说能够实现实体法上的有效性,那它就是好的程序,“正当”的程序,否则就是不好的程序,非正当程序。程序工具主义是“将法律程序视为一种实现单一价值或目的的最大化的工具”[4];程序本位主义是指程序并不只是实现某种实体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结果有效性亦并非法律程序的唯一价值,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应当立足于程序本身是否具有某些独立于结果的“内在品质”,即过程价值有效性。换言之,法律程序的根本价值在于程序本身的正义,而不是结果的有效性。一种法律适用程序即使能够使实体法上有良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它本身在运用中出现违背道德标准的要求,那它就缺乏了“正当性”的要求,偏离了实体法的价值方向。诸如裁判员在裁判中不能保持中立,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得真实的证据,贬低人格或侵犯个人隐私等就是典型的不正当程序。在对一种至少会使一部分人的权益受到有利或者不利影响的活动或决定作出评价时,不能仅仅关注其结果的正当性,而要看这种结果的形成过程或者结果据以形成的程序本身是否符合一些客观的正当性“合理性标准”。
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即程序本位主义。程序法与实体法共同构成法治过程中的“法律”,相对于实体法而言,程序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作为手段的程序是法律目的实现所必须依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具有为实体服务的功能,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是其唯一的功能,因为程序也具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同时具有目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实体决定的正确性。程序正义是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的统一,二者统一于程序的目的价值。正当程序的目的有很多价值,在法治国家中,正当程序承载正义、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
1.实现公正、公平,体现正义。正当程序首要的价值在于实现公平、公正,体现正义。人类社会是利益博弈的社会,这是因为有限的自然资源面对的是人类无限的占有欲望。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协调冲突,反应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公正价值就被人类社会认为是最优先考虑的价值。公正是平衡和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价值,“是社会组织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23的首要价值一样”[5].公正涉及社会成员地位、权利、义务、财富、机会等最基础、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反映的是人类共同生活形式所固有的特征,是任何一个社会成立的道德基础。正当程序通过回避制度、参与制度和公开制度,使有限的资源在无限的欲望中间得到可行性的分配,实现公平、公正,实现社会正义。这是程序工具主义的表现。程序还有程序本位主义方面的意义。正当程序的关键点不仅仅在于结果公平,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平的过程是大家都能看见的,它比实体正义更能让大家直观感受,使从心理上接受和行为上认同,过程的神圣性和公正性远比一个还在期待中的结果更让人感受到“自然公正”,正当程序的反复适用远比追求一次结果正义更让“自然公正”理念深入人心,让人心服口服。获得信服的规则会使信服者主动遵循,实现相应的秩序。因此,正当程序的价值在于体现正义。
2.限制恣意、防止权力滥用并实现民主参与。正当程序通过活动过程的理性安排,能有效防范权力行为的恣意和滥用,并由此实现民主参与,保障民主权利。正当程序中的回避制度、说明理由和听取意见制度和公开制度等,都可以有效地限制权力行为的专横、滥用,而说明理由、听取意见和公开同时又保障了广大公众的了解权、参与权等民主权利,实现了民主的过程。
3.保障人权和自由。有学者在论及行政正当程序的价值时曾指出:“人的主体性以及对人的尊重和平等保护是我们把握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关键和切入点,也是正当行政程序的价值所在。”[6]当然,这种人权保障理念不仅仅是正当行政程序的价值,而且是正当司法程序、正当立法程序的价值所在。正当程序不仅能使实体上的结果对当事人是公正的,而且要求实现得到实体上的公正结果的过程同样具有尊重人权和平等保护的正当性。因此,正当程序的目的还在于人权保障。
二、政策转化为法律应当遵循正当程序
(一)正当程序与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良法追求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承载了人类美好的愿望与理想,因而其本身蕴含着一些崇高的价值。对于法治,历来都有两种理解方式,即形式法治主义和实质法治主义。以规范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为代表的法学学者主张形式法治主义,以自然法学派或新自然法学派等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实质法治主义。形式法治主义与实质法治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不具有实质正当性的法律是否承认其法律效力。前者主张恶法亦法,后者则主张恶法非法。
早在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实质法治主义,他认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7].特别是在二战以后,鉴于纳粹以法治为名肆意践踏人权的历史,世界上许多法学家又重新强调了实质法治主义。例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8].在这里,被拉德布鲁赫称为“法上之法”的即“良法”,“法下之法”的即“恶法”。在拉德布鲁赫眼里,“恶法”非法,即法治是良法之治。如果依“恶法”办事,法治将会成为持久的灾难。为此,拉德布鲁赫呼吁“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权,这是超越所有法律,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权利;自然法不赋予敌视正义的法律以任何效力”[9].在此,我们也主张实质法治主义,即认为法治是良法之治。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目标,这一治国方略和目标还被载入了我国宪法。法治从此成为我国现阶段的美好理想与期待,党和政府必须以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来约束其行为。我国立法法规定了“立法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党的十六大报告进而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目标,同时还提出了“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等目标和要求。立法体现人民意志,高质量的立法体系是现阶段我国关于“良法”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此而论,我国实行法治,就是实行良法之治,党依法执政就是依良法执政。将政策转化为法律,是党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党依良法执政决定了政策转化的目标必须是良法。
为了保障政策能够转化为良法而不是转化为恶法,要求政策本身及转化过程具备一系列条件。例如,政策本身应该具有良好的品质、转化时机已经成熟、转化过程遵守一定程序,等等。其中,遵守正当程序是实现政策转化为良法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
首先,正当程序的目的价值与良法的目的价值一致,可以保障政策转化的目标不发生价值偏离。即正当程序承载的公正、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与人权等目的价值也就是政策转化的目标即良法的目的价值。正当程序与良法的目的价值一致,可以从价值目标追求上保障政策转化为良法。
其次,正当程序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手段保障政策转化为良法目标的实现。正当程序就是程序的正当性要求,也是一种制度化的手段。正当程序的目的价值需要相应的制度来实现,如听证制度、公开制度和回避制度等实现正当程序目的价值的系列制度。在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制定立法方针听取意见制度、立法建议的公开与说明理由等一系列相关制度,这些制度为政策转化为良法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再次,正当程序的理性品质和科学精神可以从技术上保证政策转化为良法目标的实现。正当程序是民主与法治社会应当遵循的一项普遍法则,并经过了道德考证,具有理性的品质和科学的精神。它要求通过一个具有正当性的过程,实现程序的正义和理性并获得实体结果的公正。正当程序“与其说是共识,不如说是科学”[10].理性与科学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正当程序所具有的这种理性品质和科学精神,当然可以为政策转化为良法目标提供技术支持。
“正义的程序虽然并不必然导致公正的结果,但要获得公正的结果却必须存在程序的正义。”这一句英国法谚正好表达了正当程序对于追求结果公正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正当程序是政策转化为良法的程序保障。
(二)保证转化过程的正当性
政策转化为法律,是一个从政策到法律的过程。执政党提出立法建议是启动政策转化为法律的环节,在立法建议被采纳后会被纳入立法规划或计划,然后被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和表决,最后形成法律并公布,这是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大致过程。这一过程应该遵循一定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等,即政策转化为法律要符合一定的程序要求。遵守法定程序只是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法治化的最低要求,法律具有良恶之分,法定程序也会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别。法定程序不等于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是比法定程序更深层次的要求。政策转化为法律既涉及法定程序,又涉及正当程序。
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品质要求,即程序要体现一定价值,公正、公开、公平与效率等是程序的一般要求和基本价值。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作为一种程序,也应该符合程序的品质要求。其基本的品质要求是:程序能够保障相关主体的程序性权利,符合一般程序价值。而正当程序所承载的公开、平等权等一系列价值,正好符合转化过程的品质要求。
正当程序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在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中保障相关主体的程序性权利,体现一系列程序价值,从而保证转化过程的正当性。例如,在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中,贯彻正当程序的听取意见制度,可以保障派和无党派人士、公民等主体的参政议政权和平等权;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公开与说明理由制度可以保障国家机关、政党和公民等主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等等。通过贯彻正当程序的上述相关制度,可以保障派和公民等各种主体的程序性权利,使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实现公正、公开、公平、民主和自由等系列程序价值,从而使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本身具有正当性。由此,正当程序就成为保证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正当性的手段。
三、政策转化为法律的正当程序制度
如上所述,正当程序原本是司法技术上的程序,而今正当程序已经超越其原有的内涵,而成为一种法律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在于无偏私、公正、公开。作为民主与法治社会应当遵循的一项普遍法则,正当程序可以为政策转化为良法提供程序保障,并保证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具有正当性,因而,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应该遵循正当程序。为了实现正当程序的目的价值,结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应当作以下制度安排:
(一)政策转化为法律中的听取意见制度制定立法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是执政党将政策
转化为法律的两种主要方式。由于立法方针的制定与立法建议的提出一般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对国家和社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重大,为了保证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内容的合法、正当,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程序的民主、科学,保障派、社会团体及公民等各方面的参政议政权、参与权、知情权、平等权,使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体现人民意志,执政党应该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并建立相应制度。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论证制度、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民主协商制度等是执政党将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听取意见制度的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1·对立法方针、立法建议的专家论证制度
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专家论证制度是指执政党邀请有关专业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对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中的专业技术性问题进行论证的制度。这是为保证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具备科学性、合法性而设计的制度。实践中,党的大政方针,包括立法方针的确定和立法建议的形成大都坚持了专家论证的习惯做法,在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做法还没有制度化,有必要把这种实践中反映良好且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做法制度化。
我们认为,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专家论证制度主要包括论证形式、论证人员的范围和论证结果的处理等方面的内容。在论证形式上,可以采取专家论证会、专家座谈会等形式;在论证人员的范围上,参与立法建议论证人员的范围不能太宽泛,否则就是公众的一般参与;同时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论证也不能太狭窄,否则就有可能使形成的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论证缺乏全面性。在对论证结果的处理上,应当遵循正当程序的理性要求,执政党对专家论证结果应充分重视,根据科学性的要求客观做出判断与取舍,否则就会使专家论证的结果流于形式。
2·对立法方针、立法建议的民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就大政方针与派进行协商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又是中国民主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宪法就政党制度与民主协商制度只是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具体到执政党制定立法方针和提出立法建议上来,在制定立法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派进行民主协商只是实践中采取的做法。这种习惯能够体现民主,有利于执政党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充分听取派的意见,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做法制度化。有关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的民主协商制度,能够体现正当程序听取意见的要求。执政党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尊重派意见,保障派的参政、议政权和平等对待权,从而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公正、平等与自由等价值。民主协商制度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可以采取座谈会、讨论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形式与派就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进行民主协商。通过这些方式,各派代表可以就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案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供执政党参考。
(二)政策转化为法律中的公开与说明理由制度
1·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的公开制度。
公开原则在于让民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长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是正当程序的基本标准和要求。正当程序制度要求:在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中,执政党应当将立法方针、立法建议以及其他涉及有可能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内容及其依据、过程和结果向公众公开,听取公众的意见、使其知悉并有效参与。这是保障公众参与权的重要途径。媒体沟通的方法、座谈会的方法、公告评价的方法等[11],可以作为重要的公开手段和方式。公开的方式很多,其中新闻是公开的重要方式之一。“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基本自由,报纸有———也应该有———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公正意见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必须受诽谤法和蔑视法的限制”,“只要报道正确态度端正,就不能非难它们”[12].就立法建议进行公开,在我国宪法制定与修改过程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的立宪建议和历次修宪建议的形成和提交基本都坚持了将建议内容公开并征求意见的做法。这种制度不仅应该在宪法修改过程中继续贯彻下去,还应该广泛应用于一般的立法过程中,不应仅停留于惯例,还应该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因此,在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执政党应当将制定立法方针、提出立法建议形成公开的制度,使广大公众都能了解并提出建议、意见,参与到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来,同时保证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结果、内容等的公开性。
2·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是正当程序的要求之一,要求影响他人利益的决定在做出前要说明做出决定的依据和理由。体现在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由于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等涉及国家、社会和广大公民的各种利益,正当程序要求执政党在制定立法方针与提出立法建议的过程中说明依据与理由。但是,在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执政党就制定立法方针与提出立法建议等说明理由还未制度化。以中共中央提出的立宪或历次修宪建议为例,在提出建议时,中共中央一般都以不同的方式说明理由。有的是由中共中央直接受托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报告的形式说明理由,有的由中共中央建议的修改宪法委员会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报告的形式说明理由,有的是在提交修改宪法建议的同时以附件的形式说明理由。最常见的是在修改宪法建议中简要、原则地说明理由。这些做法只是出于某种政治习惯,并且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做法不太稳定,这表现在说明理由的方式多变上。政策转化为法律是否需要说明理由?怎样说明理由?有关这方面的规范目前尚缺乏。因此应该规定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
党的立法方针与立法建议是执政党提出来的,立法机关以及社会公众将极为重视和关注。但是党确定的立法方针是否正确、恰当,政策内容是否需要转化为法律,是否合宪合法,是否具备转化的时机,是否比其他组织的立法建议更妥当等问题,在公开的过程中是应当说明理由的,要阐明目的、根据、原因、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等等。说明理由的目的在于让人民群众了解、理解、信服和拥护。如果理由不充分,表明还需要调整、改进、完善甚至撤回后另行确定,以保证对人民负责。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可以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建议权、参政权,并防止随意性。
(三)政策转化为法律中的避免偏私制度
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充分表明党以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宗旨,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这种无偏私的立场,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来得以体现和落实。
政策转化为法律中的避免偏私制度包括以下要求:
1.尊重人民代表的独立表决权和立法机关的表决结果。
在法律案提出之后,立法程序将进入到立法机关内部的审议和表决阶段,它应该由人大代表们来最终完成。立法机关中的人民代表包括执政党成员的代表和其他代表。立法机关中的党员代表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既是党的成员又是人民代表。执政党可以要求自己的成员贯彻落实党的意图,努力争取使党的主张转化为法律,这是政党影响国家立法的基本方式。如在英国,议会党团中的督导员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本党议员按照党团的意愿参加活动和投票,既把本党的意向传达给本党议员,又要对可能持不同意见的议员进行开导和说服”[13].在日本,如果党员不按照要求去投票,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14].但对其他代表,执政党组织不能提出这种要求,不能以各种方式干预代表的投票自主权,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和独立选择,并通过他们的选择来检验自己的主张是否真正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不能以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取代党外民主和立法民主。同时,执政党必须尊重立法机关代表们最终的表决结果。如果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内容经立法机关表决未能以法定多数票通过,则表明政策有一定不足,尚未得到多数代表的充分理解和赞同,对此执政党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政策规定。
2.政策应适时公布。
与法律相比,政策无疑更具有前瞻性,更活跃,有着鲜明的时代感,更能及时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因为如此,它往往成为先导。法律由于其稳定性而随后跟进,在此过程中政策的精神、原则和具体内容转化为了法律,执政党的政策成为了指导法的制定、修改的灵魂。但是,执政党在制定出台政策、提出立法建议以及制定法律的顺序上有两种不同做法:
第一,先制定出台并公布推行与现行宪法、法律内容不一致的有关政策,再就政策内容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随后立法机关再制定或修改宪法、法律。如执政党在改革中关于私营经济的政策,早在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提出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93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修宪建议,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随后通过了相关的宪法修正案。
第二,先就政策基本精神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立法机关根据建议制定或修改现行宪法、法律,然后执政党再制定出台并公布推行与修改后的宪法、法律内容一致的政策。如1993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先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修宪建议,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宪法修正案,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再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这两种模式中,显然第二种是符合法治国家执政党依法执政要求,符合正当程序中的避免偏私原则的。在第一种模式中,党先制定出台与现行宪法规定不一致的政策,然后才向立法机关提出修改宪法和法律的建议,最后宪法法律得以修改。这个顺序的结果就是执政党政策超越宪法和法律,即形式上的“良性违宪”。尽管它可能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但对法治理念的冲击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这种做法往往导致了社会民众对政策的合宪、合法性产生怀疑,也会丧失对宪法、法律权威性的信仰和信任。而且会认为政策已出台并实施,宪法法律规定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党要实行依法执政,就要改变这种政策形式“违宪”、“违法”的模式。执政党应该将第二种模式制度化,变“党的政策出台———提出立法建议———修改宪法法律”的模式为“党的立法建议———宪法法律修改———出台党的政策”的模式,使党的政策与宪法法律的规定保持一致。这样,从实质上,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达到了统一而形成国家法律;从形式上,党的政策也是对宪法法律的贯彻,体现了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注释:[1CouncilforCivilServiceUnionvMinisterfortheService[1983]AC374.转引自徐亚文·程序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35·
[2][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35·
[3][10]徐亚文·程序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40,10·
[4][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2·
[5][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6]陈驰·正当行政程序之价值基础[J]·现代法学,2005,(3)·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8]徐显明·大学理念与依法治校[J]·中国大学教育,2005,(8)·
[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05·
[11]方世荣,等·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若干问题研究[A]·刘茂林·公法评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正当程序范文篇4
关键词:正当程序;高校学生管理;现状与问题;完善对策
正当程序又被称为程序正义,是一个在现代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生活领域被广泛认可的理念,基于这一理念构建的制度与程序,被视为制约与监督公权力、更好的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手段。而正当程序是否完善也是衡量特定领域是否符合法治理念、实现依法治理的重要标准。近年来高校因行使行政管理权与学生发生的法律纠纷,几乎都存在程序缺陷,因此如何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引入正当程序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一、我国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及其带来的问题与矛盾
高校在诞生之初便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论在何种政治体制和社会背景下,都一直被赋予高度的自治权。但是高校管理学生的行为方式和相关法律法规不是一成不变的,近现代随着人们自身权益保护意识的觉醒,程序正义也被从司法行政领域引入到了高校管理工作当中,成为很多国家高校行使学生管理权时必需遵循的原则。而我国高校在这一方面的相关规制尚不完善,因此虽然现行学生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有了关于正当程序的规定,但是在实践当中依然因程序问题引发诸多矛盾和冲突。(一)我国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法律依据。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法》以及《教育法》当中,都明确的赋予了高校享有学生管理权,在不违反其它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基于维护高校正常教学秩序和保障学术研究活动的有序开展,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行使管理权。因此高校的管理部门具有行政管理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一旦学生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高校的有关部门就有权对其做出处理决定,并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施加特定的处罚。(二)学生管理行为的类型及其对学生的影响。我国高校享有的学生管理权力涵盖了学生招录、学籍管理、基于维护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秩序的处分与奖励以及学位评定与证书授予颁发等方面。因此这些方方面面的管理行为,决定了学生能否顺利的完成学业,与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1]。在学生招录与学籍管理方面,我国高校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拥有一定的自主招生权,并且对所有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离校的学习成绩、奖罚记录进行管理。而奖励和处分决定是对学生影响最大的部分,高校管理部门有权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日常行为进行监督和评定,并且根据学生管理规定等法规给予处理。其中处分部分更是包含了开除学籍这一改变学生身份、剥夺其继续学业的权力的处罚。最后在学位评定和毕业证、学位证书的颁发方面,高校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学校的学位管理委员会以及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有权判定学生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三)目前高校行使管理权力时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于我国高校在学生能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并顺利拿到学位与毕业证书方面拥有决定权,这些管理权力的行使就必然触动学生的权益,公平公正与否决定了学生能否接受相关决定。而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加之学生对于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的觉醒,传统的高校管理行为模式的缺陷日益显现,导致学生屡屡感受到权益被忽视和被侵犯,而高校的管理权有被滥用的风险。首先在学生招录方面,由于程序的不公开和不透明,导致部分学生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高校没有按照正当的录取标准和程序进行招录,因而诉诸法律来要求得到公正。其次学位评定和证书颁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纠纷,学生质疑高校因个人恩怨没有在这一环节做到公平公正。而在处分权的行使方面的冲突和矛盾更是层出不穷,一些高校延续了传统的学生管理理念,忽视做出处分决定过程中学生的知情、申辩与申诉等正当权益。某些高校甚至在处罚决定做出之后,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正式通知学生本人,这些管理行为自然得不到学生的认可。而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在学校内部得不到满足,最终只能将学校被诉至司法机关。
二、正当程序的要素构成及其实践意义
正当程序理念起源于西方国家,对近现代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程序正义做为实施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基础。而随着人权保护观念的强化,为了制约和规范各个领域中的权力,保护个人的基本权益不受到权力滥用的侵害,在行政管理以及社会生活领域都相继引入了正当程序,对于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正当程序的要素构成分析。正当程序做为规范管理行为和约束权力使用的工具,其核心理念是确保当事人在受到不利于自身权益的处分之前,拥有知情、申辩和听取专业意见的权力,这些权力贯穿于整个管理行为实施的过程。即管理主体应在启动处罚程序之初告知当事人,并且经过必要的听证程序允许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和进行申诉。而经过正当程序做出的最终处分决定,才真正具有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保障。因此正当程序的要素首先应包含处分程序的公正性,即管理主体的行为应遵循公正的程序,按照相关规定保障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处分。其次正当程序应基于立场中立,即权力主体应秉持中立原则和立场,对当事人不存任何偏见,与其不存在利益冲突。最后应体现出一定的参与性,即让当事人在针对其自身的管理行为发生时全程参与其中,行使知情、申辩和申诉的权力。此外还应保证程序的公开性,让管理权所辖范围内的所有人了解相关程序,从而在发生与自身相关的事件时寻求程序正义,保障自身权益不会受到侵害。(二)正当程序理念在司法与行政领域的实践意义。正当程序之所以在现代司法和行政管理领域得到认可和应用,是由于其符合现代法治观念,能够体现法治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首先正当程序的引入有助于实现权力平等,让每一个人无论出身背景、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地位等存在多大差异,都能够在权力面前站在同一高度,依据程序正义原则得到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处置。其次正当程序是制约权力的有力手段,通过设计和构建完善的法律、行政程序,让公权力的行使得到规范和约束,避免了掌握相关权力的个人或机构权力的滥用,从而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权益不被侵犯。最后在司法行政的法律视角下,正当程序保障了实体权力的实现,使得司法和行政管理真正起到调解纷争、维护正义的作用。(三)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引入正当程序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在新世纪之初,随着一些高校学生将学校诉至法院维权案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法律研究与实务界的关注,并且针对这些案件和事件当中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正当程序缺失的普遍现象,提出了在高校行政管理领域引入正当程序理念,完善既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2]。而在一些典型案例的司法审判当中,也正式认定了高校管理行为缺乏程序正义,从而认可了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应当体现正当程序原则,为改革相关法律法规并构建正当程序奠定了基础。此外由于正当程序具有解决纠纷并保障实体权力落实的作用,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将其引入,有利于缓解学生与校方的矛盾冲突,促进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而且正当程序能够让学生接受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管理,使得高校的学生管理权力得到规范与制约,避免发生侵害学生权益的事件发生。
三、完善高校学生管理中正当程序的策略
在现行的高校学生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正当程序有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例如要求高校在处分学生之前告知当事人以及建立专门部门受理学生的申诉等。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正当程序规范,也没有针对管理行为违规的相关处罚规定,因此学生的权益被侵害、申诉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以及高校行政管理程序不透明等问题依然存在[3]。通过正当程序约束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和保证学生权益,依然需要完善现有的相关制度和法规。(一)基于现有法律法规完善申诉制度。申诉是学生在权益受到侵害后寻求正义、纠正高校管理行为不当的重要渠道。而现有的高校申诉受理机构与管理部门职能界限不明,相关人员的立场无法保持中立和公正以及权限过小等,无法确保学生的申诉得到公正的处理。因此应基于现有的法律法规完善高校的申诉制度,首先应确保校级申诉受理部门的立场中立,在处理学生的申诉时相关人员的配置应坚持回避原则,由校方、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学生代表对学生的处分决定进行复议,听取学生的申辩并允许其提供证据印证申诉内容。其次高校的申诉受理部门应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在按照正当程序进行复议并经全体人员表决之后,可以直接否决对学生的不当处分,并在必要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对存在权力滥用、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二)增加高校学生管理程序的透明性。目前高校与学生产生的各种争端的焦点在于学校的管理不够透明,尤其是在学生招录方面,甚至形成了较多的法律纠纷。因此首先要把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正当程序的部分进行完善,将原则性规定转化成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规范,才能够真正规范高校的管理行为,避免因程序不明确和不公开导致权力滥用。其次高校自身也应强化管理制度体系中的正当程序设计,尤其是针对学生处分的相关制度,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化管理程序,让学生在受到严重处分时享有知情、参与和申辩的权力,以便实现程序正义和高效的处理纠纷。(三)建立申诉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间的有效衔接。当学生对受到的处分不认可而申诉结果不理想时,应有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诉的便利渠道,寻求高校上级主管部门的帮助并保护自身权益,而主管部门也要遵循正当程序给予受理[4]。此外需要建立起申诉与行政复议和诉讼之间的衔接机制,确保当双方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时,学生可以得到事后的司法救济,根据学生的要求启动对学校学生管理行为的司法调查程序。而通过完善正当程序约束高校的学生管理,构建申诉机制和引入司法监督,对于在高校这一特殊行政单位当中实现法治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在目前的社会背景维护其正常秩序并为学生提供民主和公平的学习生活环境。
四、结束语
高校的学生管理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在构建正当程序和实现法治方面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依然存在相关程序设计不完善、执行过程不透明和申诉受理与司法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因此在学生自主与权益保护意识愈发强烈的背景下,必须尽早的完善正当程序。
参考文献:
[1]黄厚明.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合法性判决研究:基于两种法治模式的考察[J].高教探索,2018.
[2]倪宪辉.基于学生主体发展的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改革路径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7(7):458-458.
[3]许盈,李万佳,于洋.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问题调查与对策分析[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7(1):60-65.
正当程序范文篇5
【关键词】学籍管理;取消学籍;行政处罚;正当程序
武汉理工大学大四女生徐某某在毕业前夕被检举为“高考移民”,学校经过调查取证,认定徐某某户籍不符合新疆普通高考的报名资格,决定取消徐某某的学籍,不予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徐某某不服将武汉理工大学告上法庭。法庭一审认为武汉理工大学在作出取消学生徐某某学籍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告知对方校方做此决定的理由、证据等,亦没有告知该生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属于行政行为程序不当,故判决武汉理工大学败诉,应该立即撤销该项决定。武汉理工大学上诉遭到驳回,维持原判。“高考移民”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水平差异较大的结果。“高考移民”对本地考生极为不公平,是应当杜绝的社会现象。本文拟以此案为切入点,借助探讨处理此类问题的方式方法,来探讨高等教育法制与高校学生权益间的关系。此案是学校依据学校制定的《学籍管理条例》对学生做出的处罚行为。要判定此处罚是否准确、恰当,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学籍管理的概念及性质。
一、学籍管理的概念及性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高等院校有权对在校学生的学籍依法进行管理。在传统行政法领域,学籍管理关系被归类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特点在于,在其关系结构中,学校处于管理者一方,法律地位较高,而学生处于被管理者一方,法律地位较低,两者所具有的权力义务不具有对等性,因此也有理论将其称之为“高权法律关系”。因其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平等性存在显著差异,故在法律救济途径上也不一样,对于学籍管理领域产生的纠纷,我国将之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二、取消学籍行为与行政处罚行为的区别
仔细分析,两者还是存在显著区别:1.两者的权力关系性质不一样。取消学籍属于特别权力关系,学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的地位远高于学生;而行政处罚属于一般权力关系,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虽较相对人地位优越,但相对人仍可以挑战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2.两者适用的法律规范不一样。前者适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高校自己的学籍管理规定等;后者适用《行政处罚法》及相关单行法律规定,故在适用时的裁量空间和裁量因素也均有不同。3.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不一样。前者只能由承担学籍管理职责的行政主体即学校作出,只能由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接受,后者则没有这一限制。4.法律后果不同。取消学籍决定生效后,学生失去其学生身份,而行政处罚作出后,一般情况下被处罚人并不失去某种身份,而是人身自由权或财产权受到限制或减损。
三、学籍管理应当遵从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DueProcessofLaw)是英美法系的一条基本法律原则,纵观现代各国行政法,基本上都吸收了其精神,确立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享有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目前我国《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处罚类法律、法规中均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要保障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就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表现。上述案例中,学校在对徐某某作出取消学籍的决定之前,涉及的学籍管理行为是“取消学籍”。武汉理工大学接到举报后,要求新疆招生办协助调查,在收到新疆招生办的回函后,便认定学生徐某某属于“高考移民”,继而作出取消该生学籍的决定。在作此决定之前,学校并未告知学生徐某某取消其学籍决定的事实、根据及理由。若学校在作出此重大决定之前提前告知当事人,且徐某某在陈述申辩当中提出了相反的事实、依据,学校查证属实后,有可能不会继续作出取消学籍的处理决定。正是由于学校在作出取消学籍决定前未进行告知、未听取徐某某的陈述申辩,所以构成了程序不当,法院最终判决撤销其作出的《关于取消学生徐××学籍的决定》。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高校的学籍管理是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笔者认为,在以学籍管理为代表的教育管理领域,高校作为主体,应当强化法治意识和程序意识,完善各类程序性规定,特别是在作出对学生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决定过程中,应当保障管理对象的知情权和发表意见权利,确保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推动高校法治化。
参考文献:
正当程序范文篇6
一、税务行政合同的定义和种类
(一)税务行政合同的定义
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的,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机关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被管理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意思表示一致而签订的协议就是行政合同;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合同顾名思义就是带有行政性质的合同;还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合同就是以行政主体为一方当事人的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合同,是指税务机关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税务管理目标,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相互协商,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受行政强制力保护的协议。
本概念所指的税务机关包括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行使税务管理权力的国家税务机关、地方税务机关、海关以及财政机关中的农税部门。
(二)税务行政合同的类型
笔者认为根据合同内容的不同,税务行政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税务行政执行合同
这类税务行政合同通常是为了贯彻税务机关的某一决定,或实现税务管理目的,由上级税务机关与下级税务机关,或由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其他公民、组织签订的涉税行政协议。
此类合同主要分为内部合同和外部合同两部分。一是上下级税务机关之间或者税务机关与内部工作人员间就税收管理问题签订的执法责任合同、评议考核合同、廉政责任状。通过责任书的合同形式,将双方的约定转化为契约条款,明晰双方责任,明确内外监督,营造类似市场的竞争压力,从而优化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服务质量,提高其工作效率。二是税务机关为实现税务行政管理目标,与税务人、法定扣缴义务人以及担保人签订的外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和四十四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可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担保人愿意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的,应当填写纳税担保书,写明担保对象、担保范围、担保期限和担保责任以及其他有关事项。担保书须经纳税人、纳税担保人签字盖章并经税务机关同意,方为有效。纳税人或者第三人以其财产提供纳税担保的,应当填写财产清单,并写明财产价值以及其他有关事项。纳税担保财产清单须经纳税人、第三人签字盖章并经税务机关确认,方为有效”。
2、税务行政委托合同
税务行政委托合同是指税务机关根据税务管理需要,依法将自身执掌的部分职权委托给符合一定条件的组织或个人行使,并直接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一种税务行政合同。
3、税务行政协助合同
税务行政协助合同就是税务机关为共同管理某一方面的涉税事务,或合作执行特定的涉税管理任务,与地位相同、性质相似的行政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联合签订的税务行政合同。
税务行政协助合同分为联合执法合同和自愿协助合同两类。
联合执法合同中合同的双方一般是税务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其他行政机关不拥有税务行政管理职责,不承担税务管理义务,电不受税务部门行政管辖,协助税务机关完成税务管理活动只能通过合意实现。
自愿协助合同往往是税务机关与不具备行政职能的组织、个人签订的税务行政协助合同。
4、税务争议和解合同
税务行政争议中,在多数情况下,税务机关为避免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或促使当事人撤诉,通过在其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或做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不同的新的具体行政行为,积极地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寻求双方的最佳契合点,这就是税务争议和解协议。
二、税务行政合同的性质
(一)有限的合意性
税务行政合同的合意性是契约精神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体现,在税法领域,互不隶属的行政机关、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之间在法律没有限制和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调整税收法律关系,可以平等地协商一致,真正实现合意。正如有学者指出:“因双方意思一致而成立之法律关系上对等,乃系指就成立契约之特定法律关系而言,双方意思表示具有相同价值,而有别于一方命令他方服从之关系”。
(二)相对的行政性
税务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就是合同中的权力因素,是区别于私法契约、民事合同的根本特征。契约不能束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行政性具体体现为税务行政优益权,即在税法上确认的或在税务行政合同条款中规定的,作为签约一方的税务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之目的而享有的对合同单方行使公权力的强制性特权。
三、税务行政合同的功能
(一)弥补税收立法不足,替代立法调整
税务机关通过缔结税务行政合同的方式,能够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的领域与相对人通过合意形成其所预期的税收法律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实施比法律规定更加严格的政策,以达到行政调整目的,并能灵活地根据时势需要不断地调整政策,进行政策选择,从而弥补税收立法不足,达到替代立法调整的效果。这也是税务行政合同作为税务行政手段所具有的突出功能,也是其弹性和动机性所在,这种弹性和动机性对于特殊、非常态的税务行政争议尤其具有价值。
(二)扩大行政参与,实现税务行政民主化
现代税收强调追求纳税人权利、税收公正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强调纳税人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参与的过程。而税务行政合同正是顺应现代税收发展的要求,基于双方或多方主体地位平等的对话、协调和合意过程,它充分体现了服务于民的色彩。
(三)有效弥补税务机关信息不足,实现税务行政手段多样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和信息不断变化,行政机关全知全能的假设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是天方夜谭。在税务行政工作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单一的权力手段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税收的要求,势必需要新的应对手段来解决。税务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目的和法律目的,实现征纳双方的良性互动,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势要求选择适用的手段从而使税务行政工--作更加充满活力与效率。
(四)降低税务行政执法成本,提高税收效率
(五)有助于征纳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税收关系的稳定化和持续化
(六)明确税务机关权限,促进税务机关依法行政
四、税务行政合同法律调整的方式——正当程序制度
税务行政合同的法律调整重点是税务行政优益权。税务行政优益权的调整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体规则模式,它从行政行为结果着手,注重行政法实体规则的制定,行政优益权通过详细的实体规则来实现。另一种是正当程序模式。其特点是着眼于行政行为的过程,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程序来实现对行政优益权的控制。这一特点在保证行政优益权发挥功能的同时又能避免权力滥用,因而选择正当程序制度调整税务行政优益权是税务行政合同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要从立法上尽快建立以听证与协商制度为核心,以说明理由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回避制度、告知制度为组成部分的正当程序制度,调整税务行政合同的税务行政优益权,防止行政恣意。
参考文献
[1]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3]胡建森:《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余凌云:《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余凌云:《行政法上的假契约现象——以警察法上各类责任书为考察对象》。《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6]《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版。
[8]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
[9]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戚建刚、李学尧:《行政合同的特权与法律控制》,《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
[11]许宗力:《行政契约法概要》,《行政程序法之研究》1990年。
[12]崔卓兰、蔡立东:《非强制行政行为——现代行政法学的新范畴》,《行政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正当程序范文篇7
摘要: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应当遵行现代宪法原理和正当程序保障。
关键词:宪法/民事诉讼/正当性/正当程序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起诉)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起诉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起诉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起诉或申请。
就起诉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起诉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起诉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起诉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起诉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起诉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起诉(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起诉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
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宪章》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中特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
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
(二)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正当程序的审理,得到正当的诉讼结果,并能得到执行。因此,民事诉讼具有正当性则意味着当事人的民事司法救济权与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之共同实现。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领域。在此领域,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充分对话和相互说服,然后法官利用判决将对话的结果或说服的内容固定下来并表达出来。正因为法院判决是在正当程序中当事人与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其才具有正当的法律效力,即“通过程序的正当化”。[15]可见,过程与结果的一体性是民事诉讼的本性。
总之,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建立民事诉讼正当程序或者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应该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理念。
注释:
[1]王亚新:《民事诉讼与发现真实》,载《清华法律评论》,第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邵明:《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24
[3]邵明:《民事诉讼法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6-209
[4]邵明:《透析民事诉讼的正当性》,载《法制日报》,2008—06—29。
[5]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672-675
正当程序范文篇8
主题词:正当程序,尊严本位,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法
一、序论
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更为准确地说应为“正当法律过程”,1是美国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但对于什么是正当法律过程、正当法律过程在制度上应当具备哪些要件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甚明了。从法院适用正当程序条款的实际情况看,该条款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不论是法院还是学界都认为,这种“弹性”只有在确立了一种稳固的、包含价值导向的基础作为原则性要求时,才能具有合理性,才能限制恣意。缺乏某种原则的“弹性”并不是灵活性,而不过是恣意或反复无常的代名词。2因此,对正当法律过程的考察,必须将其基本原则与精神作为重点。
就正当法律过程条款适用的理论实践来看,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实质上对政府的活动施加了两方面的限制,即“程序的正当过程”(proceduraldueprocess)和“实体的正当过程”(substantivedueprocess)。实体的正当过程指当政府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证明其行为的必要性。换言之,实体性正当过程要求政府必须为其行为提供正当化的理由。实体性正当过程主要被法院运用于对立法之合宪性的审查。3关于实体性正当过程,理论上仍然存在争议。4程序性正当过程是指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在作出决定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换言之,程序的正当过程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活动施加了最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即行政过程在程序上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公平。
本文试图从行政程序角度对程序性正当程序适用中的最新发展进行考察,提出“最低限度的公正”是正当程序的核心要求。以此为背景,笔者将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价值模式问题进行探讨。
二、何时适用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问题
(1)正当程序的革命
从语义上讲,当政府采取行为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其活动必须满足程序的正当过程之要求。在这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二十世纪70年代前,最高法院一直将“权利”与“特权”予以区分,认为只有当政府采取旨在剥夺公民权利行为时,其活动过程才必须满足程序的正当过程之要求。5而“权利”(right)-与特权(privilege)相对──通常被定义为“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例如金钱、房屋、从事特定行业的执照等;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6但是自1970年以来,法院开始放弃“权利──特权”的区分,将某些原来属于“特权”的利益承认为权利,例如工作和就业,社会福利等。从1970年到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五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大大扩展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种正当程序适用范围上的扩展,被称为“正当程序的革命”。
在1970年的Goldbergv.Kelly一案中,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政府通过制定法而赋予公民的社会福利是一种“财产”,应当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7在随后的涉及政府雇员工作权的案件,即1972的Perryv.Sinderman8和BoardofRegentsv.Roth9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在某些条件下,雇员的工作权可以构成一种“财产”,应受正当程序的保护。10在1971年的Wisconsinv.Constantineau一案中,最高法院对“剥夺自由”的内涵作了很大的扩展。法院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政府采取某种“可能玷污(stigmatize)”特定个人名誉的行为,则政府的行为构成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必须适用正当法律过程。11在1972年的Morrisseyv.Brewer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因州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利益而获得“受保护的自由权”。12这种自由权可以来自于各种监狱管理规则的规定。
1970-1972年的这几个重要判例通过对“自由和财产”的拓展性解释,大大扩大了程序的正当过程的适用范围。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在“行政国”时代,“社会已经建立在政府所创造的福利这一基础之上,财富来源于并依赖于政府所提供的福利。”1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正当程序不能为这些通过政府而产生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保障,就无法有效地限制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恣意。针对行政国状态下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上述特征,耶鲁大学法学教授里奇(CharlesReich)分别于1964年和1965年发表了两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呼吁法院承认并保障个人通过政府福利而获得的利益,即“新财产权”(newproperty)。14在当时的情况下,福利政策仍然被视为通过扩大政府的职能而缓解社会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个人通过政府而获得的福利的承认和保护很容易被接受,因此,法院很快对里奇的呼吁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5
正当程序适用范围的急剧扩展在随后几年里有所回退。从1973年到1978年,最高法院作出了九个涉及正当程序的判决,在这些判决中,法院一方面对在上述五个判决中所提出的观点进行肯定,另一方面也对进一步扩大正当程序适用范围的主张和要求进行了抵制。16最高法院在主张为个人社会福利提供正当程序保障这一点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在正当程序究竟应当为个人福利提供何种程度的保障等方面有一些微妙变化,或者可以说是“回退”。17法院对正当程序适用范围的扩大已经有所节制。
(2)正当程序的“反革命”
在1979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里,扩大正当程序适用范围以及加强正当程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保障的力度作为一种态度与反对正当程序适用范围过度膨胀的态度两方面共存,并大致处在一种“艰难的平衡”之中。就行政法领域看,一些方面对正当程序的要求加强了,另一些方面则减弱了。18令人回味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1974-1985年间,关于正当程序适用范围和最低程序保障的标准,最高法院内部曾经发生过不成功的“反革命”。大法官伦奎斯特(JusticeRehnquist)在1974年的Arnettv.Kennedy一案中,提出一种新的理论,通常被称为“甜加苦理论”(bitterwiththesweet)。19这一理论认为,既然政府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给予相对一方某种福利,它自然也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福利的范围和授予或终止该福利的程序。因此,法院不应当强迫行政机关按照法院认为适当的某种程序来授予或终止福利。1985年,当时已经是首法官的伦奎斯特再次明确提出这一理论,但是另外八位大法官拒绝适用这一理论。20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正当程序革命”年代所确立的关于行政活动过程中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受到了更强有力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讲,“正当程序的反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在1995年的Sandinv.Conner一案中,联邦巡回法院认为监狱管理机关对一个有违规行为的犯人处以30天单独监禁的行为不属于“剥夺自由”,因而不受正当法律过程的保护。21这无疑是法院对正当程序适用范围问题所持态度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自1972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监狱管理规则所赋予犯人的利益都被认为是受正当程序保障的自由。而在1995年的这一判决作出之后,只有当监狱当局对服刑犯施加“与监狱中其它犯人相比较而言是典型的、明显的苦役”时,才属于对服刑犯“自由”的剥夺,应当遵循正当程序。22法院在这一案件中态度上的明显转变对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活动领域的适用范围、个人权利的程序保障等问题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到本世纪末,1970年生的正当程序革命将成为美国法律史教材中的一部分。”23
三、程序性正当过程的基本要求
如果政府的行为必须遵循正当程序,那么正当程序要求什么样的程序保障?换言之,什么样的程序才是正当的?这是正当程序在适用中的另一基本问题。
从实践中看,当行政机关应当为相对一方提供正当程序保障时,这种程序保障的基本要求或最低标准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告知相对一方有关的事实和权利;24(2)为相对一方提供有效的听证机会;25(3)主持程序活动的决定者必须是独立的。26在这三项程序要求中,相对一方的听证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甚至被认为是正当程序的最低限度要求。早在1908年,最高法院在Londonerv.Denver一案中就指出,“就其本质意义上讲,听证要求享有听证权的人有权通过论辩支持自己的主张,无论其论辩多么简单;在必要时,有权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反驳对方的观点,无论这些证据多么非正式。”271974年,最高法院大法官怀特(JusticeWhite)在Wolffv.McDonnell一案中,代表法院对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听证作出了总结性的意见。他写道:“法院一贯认为,在个人被剥夺财产或利益之前的某个时间,某种形式的听证是必须的。”28“某种形式的听证”(somekindsofhearings)被认为是程序性正当过程最基本的要求。从最高法院的以上态度看,程序性正当过程的要求与英国普通法上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要求行政机关进行某些活动之前必须告知可能受不利影响的个人有关情况,并提供听证的机会,以及由一个没有偏私的、独立的裁判者来主持程序和作出决定。29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程序的公平。
如果正当程序的核心在于“某种形式的听证”,那么在实践中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考虑:(1)行政机关在所有受正当程序调整的活动中都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听证”吗?(2)在行政机关必须提供听证机会的情况下,何种形式的听证才能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尽管法院和学界都承认听证的意义,但也有人认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都必须为相对一方提供听证的程序保障。一位法官曾经指出:“即便一种正确的感觉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定存在着某个界限,在那个界限以下无需任何形式的听证。”30但是,这一界限究竟应如何设定却是一个也许永远也不可能明确的问题,而只能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确定。实际上,最高法院也拒绝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而认为“正当程序并不是一个与时间、地点和形势不相关的技术性概念,它是灵活的,要求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提供适当的程序保障。”31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Mathewsv.Eldrige一案中提出了如何根据特定情况来判断行政机关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方法论,即权衡政府利益、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以及所适用的程序可能产生的利益。32根据这一方法,判断行政机关所适用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应平衡考虑上述三个方面因素。同样,行政机关适用正当程序作出决定时是否必须为相对一方提供听证机会,也需要平衡考虑以上三方面因素。
关于第二点,即如果行政机关必须为相对一方提供听证,什么样的听证才能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长期以来,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美国行政活动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司法程序的影响,导致行政活动过程“司法化”的情形。这种行政程序过分司法化的情形受到很多批评。早在1940年,大法官弗兰克福特就提出,“行政机关不应当全盘移植生成于法院审判活动的经验与历史中的司法程序。”33一位英国法官则评论道:“从美国行政程序的过分司法化的可怕事例中,英国人所能够学到的就是不要做类似的事情。”34美国行政程序过分司法化的趋势可能与法院对行政行为强有力的司法审查权有关。当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所采用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时,它往往倾向于以司法程序为标准对行政活动的程序提出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势从本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所缓和。最高法院在1976年提出的通过平衡考虑政府利益、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以及程序本身的有效性三个因素以确定正当程序要求什么样的程序保障这一方法,实际上表明法院已经开始从过分重视程序的形式正义这一立场退缩,并转而倾向于一种将行政过程中公平与效率进行平衡考虑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行政机关为相对一方提供的听证,既可以是正式的审判式听证,也可以是非正式听证;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既可以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也可以在作出决定之后。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进行何种形式的听证,行政机关必须对具体情况下三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平衡考虑。但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听证,听证活动本身都必须公平。一般认为,一个公平的听证应符合以下要求:(1)听证活动由一个独立的、没有偏私的机构或个人主持;(2)相对一方有权获知可能影响其利益的决定以及有关的理由;(3)相对一方有机会为自己辩护;(4)相对一方在听证活动中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5)听证必须制作记录;(6)听证必须公开。
四、程序性正当法律过程的价值:个人尊严与最低限度的公正
(1)作为正当程序基本价值的个人尊严与最低限度公正
从程序性正当程序的实践及其基本要求看,笔者认为其内蕴的基本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尊严的承认和尊重。每个人都是具有人格尊严的、平等的道德主体,因此将人作为中心的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在逻辑上必须体现对人的尊重,否则就不是“良法”。美国行政法学者JerryMashaw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正当程序的基本价值理解为“尊重个人尊严”。35这种解释与自然法精神不无关系。自然法的这一精神表达了一项程序公正的最低要求:必须将人当作人来对待。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当程序也体现了人权精神。第二,与上述观念紧密联系,正当程序蕴含了“最低限度公正”这一程序正义基本理念。从正当程序的适用看,正当程序的要求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法院并没有明确指出正当程序要求行政机关以何种程序而行使权力,但确实指出如果程序不能满足“某种标准”,就是不可接受的。36“最低限度的公正”之概念在于这样一种信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不可放弃的,否则不论该程序的其他方面如何,人们都可以感受到程序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在笔者看来,这些程序要素至少应当包括:(1)程序无偏私地对待当事人;(2)在行使权力可能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表达意见和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以及(3)说明理由。如果一个法律程序缺乏这些要素,不论通过该程序产生的结果如何,也不论该程序多么具有效率,人们仅仅根据“正义感”或一般常识就可能感觉到它的“不公正”,程序的正当性(legitimacy)也将因此而受到挑战和质疑。从这一意义上讲,效率很难作为牺牲“最低程度公正”的正当化的理由。无疑,“最低程度的公正”概念强调了程序公正的基础性意义,但它并不排斥行政程序对效率因素进行相当的考虑,这是因为:(1)“最低程度的公正”为程序及其结果提供了某种正当性,可以减少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摩擦,增强相对一方对行政机关的信任与合作意识,因而可以促进效率;(2)“最低程度的公正”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公正优先”。“最低程度的公正”概念本身蕴含着对行政程序灵活性的认可,允许程序在满足这些基本要素的前提下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对公正与效率进行平衡。
(2)“最低限度公正”概念之提倡
我们不难看出,“最低限度公正”之概念实际上暗示了处理法律程序中公正与效率关系的另一种思路。通过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行政政程序目标模式上的公平与效率之争进行另一种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也通过对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证考察、比较分析以及理论阐释等途径,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37归纳起来,关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选择,大致有三种态度:(1)效率优先,兼顾公正;(2)公正优先,兼顾效率;(3)公正与效率平衡。这些分析无疑都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因为它们都注意到了公正与效率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但是笔者以为,对行政程序立法来说,这些立场在操作层面上仍然存在着问题。例如,不论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正”,都没有具体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优先到什么程度?如何兼顾公正或效率?应该兼顾到何种程度?应当通过哪些程序制度实现“优先”或“兼顾”?而主张“公正与效率平衡”的立场面临一些基本问题,例如,这种平衡的“度”应当如何掌握?程序制度上应当如何安排?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希望法律程序避免那些可以被明显感觉到的不公平,并为权力行使的过程和结果提供某种“正当性”的话,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最低限度公正”的要求。因此笔者主张,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处理公正与效率关系时,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思路和立场:第一,在公正与效率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坚持:程序首先必须满足“最低程度的公正”。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和核心制度都应当体现“最低限度公正”之要求。第二,“最低程度公正”之概念为我们认识行政程序中公正与效率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对于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复杂关系而言,这一点虽然极为重要,但仍然是不够的。因为程序在满足了“最低程度的公正”的前提下,仍然面临着程序公正的其他要求与程序的效率发生冲突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应当对公正与效率进行适当的平衡。例如,程序中的“职能分离”对于程序公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从强调程序公正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赞成“完全的职能分离”,即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的调查、听证、决定、执行等职能应当由完全不同的行政机关来行使。但是“完全的职能分离”无疑会大大增加行政过程的成本,影响行政活动效率。因此现代行政程序法关于职能分离的制度安排,并没有采取完全的职能分离,而是采取“内部职能分离”。行政程序中的参与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参与对于程序公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制度中,对于相对一方的参与都是有限制的,而且这种参与程度在行政立法程序中和在行政决定制作程序中又有不同,其目的也在于平衡公正与效率。那么,在公正与效率平衡的制度安排和程序操作方面,我们究竟应当考虑哪些因素呢?笔者认为,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四个方面因素:38(1)行政过程所涉及到的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程序涉及到的相对一方合法权益越重大,相应的程序保障也应当更严密公正;(2)行政过程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越重要,行政过程相应的程序也应当越严密。(3)行政机关操作该程序以及相对一方参与该程序需要耗费的成本。如果成本太高,不论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一方可能都难以承受,不仅影响程序的效率,对程序公正的实现也将产生不利影响;39(4)程序可能产生错误结果的危险性。程序产生错误结果的可能性越大,程序效率就越低。正当程序的架构以及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对以上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注释:
1虽然笔者认为美国宪法上的“thedueprocessoflaw”应当被理解为“正当法律过程”而不应是“正当法律程序”──因为从法院对这一条款的理解和适用看,该条款也具有实体性内容,而不仅仅是程序性的──但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在本文中同时使用了正当法律程序、正当法律过程两个概念,其含义是相通的。
2SeeMartinH.RedishandLawrenceC.Marshall,“AdjudicatoryIndependenceandtheValuesofProceduralDueProcess”,95YaleL.J.(1986),p.455.
3410U.S.113(1973)。
4例如,哈佛大学教授JohnHartEly在其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民主与不信任》(DemocracyandDistrust)中,指出“实体性正当过程就其概念而言就是自相矛盾的,就如同‘绿色的浅红色’是自相矛盾的一样。”
5SeeRichardJ.Pierce,“TheDueProcessCounterrevolutionofthe1990s?”,in96Columbia.L.R.(1996),p.1973.
6在区分权利和特权的时期,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法学者都倾向于这样来界定权利,而“特权”(entitlement)则被认为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参见KennethC.DavisandRichardJ.Pierce,AdministrativeLawTreaties,WestPublishingCo.,(3rdedition,1994),pp.21-23.
7397U.S.at254,262(1970)。
8408U.S.at593,(1972)。
9408U.S.at564,(1972)。
10408U.S.at601-603.
11400U.S.at433(1971)。
12408U.S.at471(1972)。
13SeeCharlesA.Reich,“IndividualRightsandSocialWelfare”,74YaleL.J.(1965),pp.1255-1256.
14SeeCharlesA.Reich,“IndividualRightsandSocialWelfare”,74YaleL.J.(1965),p.1245;CharlesA.Reich,“TheNewProperty”,73YaleL.J.(1964),p.733.
15SeeRichardJ.Pierce,“TheDueProcessCounterrevolutionofthe1990s?”,in96Colum.L.R.(1996),p.1974.
16SeeRichardJ.Pierce,“TheDueProcessCounterrevolutionofthe1990?”,in96Colum.L.R.(1996),p.1977.
17424U.S.at693,708(1976)。
18SeeRichardJ.Pierce,“TheDueProcessCounterrevolutionofthe1990s?”,in96Colum.L.R.(1996),p.1991.
19416U.S.at134(1974)。大法官伦奎斯特、斯图亚特和首法官伯格一起发表了“甜加苦理论”:“实体性权利与赋予这些权利并对其作出限制的程序是不可分离的,当事人必须将‘甜’和‘苦’一起吞下。”
20470U.S.at538-541.
21115S.Ct.at2293(1995)。
22115S.Ct.at2300(1995)。
23SeeRichardJ.Pierce,“TheDueProcessCounterrevolutionofthe1990s?”,in96Colum.L.R.(1996),p.2001.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正当程序的反革命不可能成功。参见C.R.Farina,“OnMisusing‘Revolution’and‘Reform’:ProceduralDueProcessandTheNewWelfareAct”,inAdministrativeLawReview(1998),p.591.
24在1950年的Mullhanev.CentralHanoverBankandTrustCo.一案中,大法官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代表最高法院提出,告知是正当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个人有权获知针对他们的案件的相关情况并获得听证的机会。”339U.S.306(1950)。
25例如,在1970的Goldbergv.Kelly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决定终止公民的社会保险福利之前,必须为相对一方提供“有效的听证”。397U.S.254(1970)。
26在1973年的Gibsonv.Berryhill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如果程序主持者或决定制作者通过其主持的程序或作出的决定有可能获得某种利益,程序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违宪的。411U.S.564(1973)。
27210U.S.373,386(1908)。
28418U.S.539,557-558(1974)。
29SeeHenryJ.Friendly,“SomeKindofHearing”,123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R.(1975),p.1277.
30SeeHenryJ.Friendly,“SomeKindofHearing”,123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R.(1975),p1275.
31470U.S.541(1985)。
32424U.S.319(1976)。
33JusticeFrankfurtercommentedinFCC.v.PottsvilleBroadcastingCo.,309U.S.134,143(1940)。
34转引自HenryJ.Friendly,“SomeKindofHearing”,123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R.(1975),p.1269.
35参见JerryMarshaw,DueProcessinAdministrativeState,YaleUniversityPress(1986)。
36关于这一点的具体分析,可以参见MartinH.RedishandL.C.Marshall,“AdjudicatoryIndependenceandtheValueofProceduralDueProcess”,95YaleL.J.(1986),p.455.
37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姜明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年版。
正当程序范文篇9
[关键词]宪法宪政正当法律程序检验标准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它虽然是美国宪法中最难理解的部分,[1](209页)却又被认为是美国法律的本质所在;[2](19页)它虽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论争,对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①却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中有40%与正当法律程序有关,在联邦最高法院适用于各个案件的次数远远超过美国宪法其它条款的规定,[3](68页)而成为美国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宪法保障。[4](54页)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美国宪政的基石。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5](46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6](149-150页)“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6](137页)看来,正当法律程序正在超越英、美法系的传统文化藩篱,而逐渐为世界其他法律文化所认同。
壹从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
丹宁勋爵在他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中说:“我所说的‘正当程序’指的不是枯燥的诉讼案例,它在这里和国会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意思倒极其相似。它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中:‘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继承权和生命’。”“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也和麦迪逊(Madison)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它已被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7](前言)“法律的正当程序”即本文的正当法律程序,英文表达为:dueprocessoflaw。②在这里,丹宁勋爵的前一句话揭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渊源:1354年,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的法律文件中。以非正式法令形式出现的正当程序条款则可追溯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康得拉二世有“不依帝国法律以及同等地位族的审判,不得剥夺任何人的封邑”的规定,这是给封建贵族的特权或帝王赋予的权利的司法保障。[3](62页)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章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者逮捕。”这一规定反映了封建贵族与封建君主斗争的成果,即用法律程序对封建君主加以约束,而对封建贵族加以保护。[3](62页)康得拉二世及《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与后来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相去甚远,它只是一种贵族的特权,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权利(哪怕只是程序性的!)。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3](62页)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1868年第十四条修正案是美国宪法第二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然而,丹宁勋爵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并不就是后来美国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司法实践所“形成”的正当法律程序,尽管他的上述第二句话——“我所说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的第五条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都仅意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对此,丹宁勋爵作如是解释:“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7](前言)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的独特表现形式,[6](147页)是有道理的。自然公正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8](55页)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又提出两项新的自然公正原则:其一是,无论处理争议的程序是司法性质的还是非司法性质的,争议各方都有权了解作出裁决的理由。其二是,如果对负责调查的官员所提出的报告草案提出了公众质询,那么争议各方有权得到该报告的副本。[8](55-56页)自然公正的这些原则都是程序性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其基本要求是程序公正。它是“要过问政府行事的方式以及它所采用的执行机制。当政府剥夺一个人已经获得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利益时,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程序上的公正性。”[9](128页)或者说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法律赖以实施的方法或法律采用的方式。[1](209页)它是对怎样行使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它同法律的程序有关,主要限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1](211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麦迪逊将正当法律程序写入其起草的《权利法案》初稿时,他便只是把正当法律程序看作一种程序上的保障。[10](55页)在第五条修正案通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还仅指刑事诉讼程序问题,即指要保证被告一定按照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来公平受审,刑事被告人享有一定的受保护的权利,政府只有遵守这些法定程序,才可以采取对被告人不利的行动。它既不与公民的既得权利相联系,也不涉及到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的影响问题。”[3](63页)在这个时候,它要求的具体程序是:“先审讯,后宣判;根据调查起诉,只有在审问或某种听证之后才能作出判决。”[1](209页)那么,什么程序是正当的呢?在联邦法庭上,正当程序要求小心遵从第四条至第八修正案中列出的权利法案条款。“什么是正当的这一问题在另类诉讼中就是:为保证基本公平必须做什么。”这要求至少“涉及的人必须获得适当通知并有机会被听取陈述。”[1](21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但许多美国学者不加以分析和概而把联邦宪法第1-10条修正案中所适合的程序保障要求直接视为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具体标准。[8](57页)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然而,早期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建立在一种可疑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权利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规定在例外的情况下权力不应当行使或不应以某一特定的方式行使,对权力加以限制和限定。”[10](35页)权利法案特别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并不
能全部达成这一目标,这时对政府权力特别是立法机关的权力的实质性限制依赖于自然法。1909年,迪安·庞德写道:“我们必须记住,自然法是《权利法案》的理论根据,”“宪法贯穿了自然法的观念”。[11](145页)后来随着坎特著作的出版,出现了对自然法的怀疑,自然法理论随之式微。③宪法的核心从自然法的理论迅速转向包含在正当程序条款中的明示的限制。④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以致不论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的观点看,个人权利都是由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是对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立法权的一项宪法限制,即“对行使政府权力做什么加以限制”,“同法律的内容有关”,主要限制立法部门。[1](211页)它是指一项“不合理”的法律,即使是恰当地通过了,恰当地实施了,仍是违宪。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
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首先是由州法院的判决确立起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56年怀尼哈默诉人民案的判决。该案起因于一项纽约州禁止出售非医用烈性酒并禁止在住所之外的任何地方储放非用于销售的酒类的法律,纽约州法院认为,“该法的实施,消灭和破坏了这个州的公民拥有烈性酒的财产权”,这恐怕与正当程序条款的精神不符。[10](56页)这一判决的意义在于纽约州法院用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代替了自然法,对立法权进行实质性的制约。9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尼诉哈默案中首次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作为实体法条款使用。[3](64页)至此,正当法律程序开始成为一种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权不合理干涉的有力工具。1866年,国会提出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1867年该修正案被宣布生效。纽约州法院审理怀尼哈默案的推理最终为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美国法院所普遍采纳,正当法律程序成为了一项真正的宪法制度。第14条修正案是划时代条款,“代表了一场真正的宪法革命”。[10](114页)其后果之一便是实现了公民权利的联邦化,[10](105页)即使权利法案的各项基本权利“加以并入”并使之适用于各州。1968年,在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一项从权利法案中“吸收来的”保障要按它制约联邦政府的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来制约州。[9](101-102页)从单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同时兼含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演进过程,揭示了:第一,美国宪法的条文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和包容性,虽然仍是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条文,却前后包含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不同的宪法内容,在保持宪法条文不变的情况下,宪法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美国宪法发展的主流方式,它是美国宪法历200余年而能保持其稳定外观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宪法具有灵活性特征的关键。第二,随着联邦最高法院权力的扩大,需要对国家权力依制衡原则重新配置,从而使三权分立制度更趋合理、稳定、平衡。宪法内容的上述发展基本上是由法院来完成的,它是法官运用特定时期的宪法理论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的结果。这种宪法解释的权力是马歇尔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的,对宪法的解释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使美国法院获得了三权分立体制中最实在的权力。第三,人权保障得到加强。就公民而言,他不仅可以就司法和行政中程序性权利请求法院保护,而且还可以就联邦及州的立法请求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以保障其实体权利不受侵害或者在其受到侵害后能得到合理的救济。
贰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检验标准
(一)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检验标准
1、理性基础检验标准
理性基础检验标准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审查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适用于经济案件中。企业界历来在宪法中寻找依据,以便保护其财产免遭州的经济管制和干预。宪法上常被引用来支持这一保护的章节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9](103页)在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在经济案件中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判断应持尊重态度。[9](105页)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坚持一种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常常以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为由宣布“新政”立法违宪,⑤导致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2月向国会提出了改组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系统的法案。罗斯福改组法院计划虽未获成功,但联邦最高法院从1937年4月开始,法官们对每一个提交给他们的新政法令都采取支持态度,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类似于过去被宣布为无效的新政法令。[10](180页)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转变,史称1937年宪法革命。1937年以后,最高法院审慎地抛弃了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认为只要是“为了社会利益而颁布的法令,都是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⑥并且从“司法尊重很快转变成在经济管制案件中完全取消审查。”[9](106页)最高法院声称:“立法机关是否把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凯恩斯爵士或其他一些人的学说当作教科书,与我们的判决并无关系”;[10](184页)“一部宪法无意体现一种具体的经济理论,无论它是家长制理论,公民与国家的有机关系理论,还是自由放任理论”。[5](48页)虽然如此,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名义上仍然存在,法院用以审查社会经济法律时,先假设该法律合宪,而“把证明该法律与所允许的政府利益没有任何理性关系的举证责任放在提出质疑的一方的肩上”。[9](106页)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最高法院审理经济案件中的变迁,标明正当法律程序在这一领域的衰落,其实质是在相互分立的三权之间对经济领域立法权力的重新配置——最高法院采取了退让的办法以维持三方均衡。不过,“法院在经济领域退让的东西,正是它在其他领域新获得的东西,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护领域获得的东西。”[2](13页)法院在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立法采取了严格的检验标准。
2、严格检验标准
如上所述,严格检验标准针对的是联邦或州对个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立法。在理性基础检验标准的情况下,一项法律只要与所允许的政府目标之间有理性关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在严格检验标准情况下,仅有理性关系是不够的,还要求政府必须确定,该法是严格地适应紧迫或重大的政府利益的。[9](109页)但是,严格检验的标准并非始终如一,一般地讲,可以说随着对被保护权利施加的压力越大,就越强烈地要求政府申述理由。[9](110页)严格检验所针对的个人基本权利包括两部分:一是法明示的权利和从宪法文本中引伸出来的权利,二是司法上产生的权利。[9](127页)任何一项针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立法的违宪审查申请,都要证明权利是宪法明示或引伸出来的,否则,很难得到法院的同情。对于如何确定《宪法》条文中引伸出来的权利,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宪法本身的解释来找出宪法权利。一种观点认为在宪法条文之外存在着宪法原则或准则,通过这些宪法原则或准则可以发现和形成宪法外的基本权利。确定宪法外基本权利的依据包括:其一是依靠传统和习惯得来的价值观,其二是一种动态方法确定那些包含在有秩序自由的概念中的价值观。⑦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严格检验标准,体现了联邦法院对人权给予严格保护的积极态度。
3、中间层次检验标准
这一检验标准介于理性基础检验和严格检验标准之间,主要针对的是婚姻和家庭权利。对婚姻、家庭权利之所以采用中间层次检验标准,是因为在性质上,婚姻、家庭权利对于个人的意义介于经济权利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一项利益是否受正当程序的保护,取决于该项利益的性质,不取决于该项利益对个人的重要性。”[1](210页)最高法院一面声称“本法院始终认为,个人对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选择自由是受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之一。”(1974年克利夫兰教育委员会诉拉费勒案)[9](122页)最高法院同时又主张:法律必须服务于“各种重要的政治目标,并且必须与这些政府目标的实践具有实质性的联系。”[12]这说明,对婚姻、家庭权利方面的立法的司法审查中,只要该立法与政府目标具有实质性的联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不要求该立法严格地适应紧迫的、重大的政府利益。
(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标准
在美国,“宪法上的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原则上只适用于裁决性活动,而不适用于制定规则的活动。”[13]适用于裁决性活动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其基本要求是程序正当或程序公正。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认为,“程序的公正和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宁愿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厉的实体法,也不愿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8](56页)然而,什么程序是正当的呢?在美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目前,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什么程序是正当的乃是一个靠法院解释‘正当程序’含义来回答的联邦宪法问题。”[9](134页)如前所述,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坚持的理论看,在司法及行政执法中严格遵从《权利法案》的条款,保障涉及的人获得适当通知并有机会被听取陈述,是程序公正的最一般的要求。即使如此,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1976年)以后正当法律程序分析保持了极大的灵活性。在具体的案件中,如何判断所采取的程序是否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法院在早期采用一种被称为“历史判断模式的方法,将制宪者的原意作为程序正当性的判断依据。⑧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一种新的、灵活的判断标准,它判断程序正当性的依据是:“第一,受官方行动损害的私人利益;第二,通过所采用的程序造成错误地剥夺该利益的危险,以及附加的或替代的程序保护的可能价值,如果有这方面的价值要考虑的话;最后,政府的利益,包括有关的职能,以及附加的或替代的程序法规定所造成的财政和行政负担。”[9](135页))我国有人将这一新的判断标准称为“利益衡量模式”,[3](68页以下)而美国学者称之为“三部分检验法”。[9](135页)这一判断模式是目前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正当程序判断的主导模式,尽管它也招致了许多批评。根据这一标准,最高法院对程序正当性的判断可以因案而异,具有很强的主动性、灵活性。最高法院正是籍此随时根据社会的变化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从而不断获得权力,提高地位,并最终成为美国宪政制度的核心。然而,对最高法院的这一趋向并非没有限制,如,就刑事案件而言,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保障被告人至少享有如下程序性权利:(1)通知指控罪名的权利;(2)受审的权利;(3)由辩护律师辩护的权利;(4)对指控罪名答辩的权利;(5)与指控人和证人当面对质与辩论的权利;(6)拒绝自认犯罪的权利;(7)出示被告人证人的权利;(8)无罪推定的权利,即被告人被视为无罪,除非法庭在审判期间根据实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9)获得判决书的权利;(10)上诉的权利。[14](8页)又如行政法领域,在正当程序诉讼中最经常地予以审核的程序权利包括:(1)事前的通知和听证的权利;(2)获得审判形式的听证的权利;(3)律师辩护权;(4)由公正无私裁决人进行裁决的权利;(5)获得调查结果和结论的权利。[15](131-145页)对以上任何一项权利的剥夺,都将导致裁决无效。
叁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政意义
正当法律程序,在美国宪法中只有两条简单的条文,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发展出了丰富而且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特色。美国宪政中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与实践,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当今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启示:
1、对权力的程序制约,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原则和发展趋势。美国的宪政制度比较彻底地贯彻了权力分立原则,无论是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还是纵向的联邦、州、地方政权的权力分立,都是西方国家的典范。权力分立的原始意图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对权力如何制约呢?除了用宪法详细规定各种权力的范围并使各种权力行使者之间相互制约外,美国宪法还确立了以程序制约权力的原则,即不论何种权力的行使都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美国,维护这一原则的核心手段便是正当法律程序。[16](246-247页)甚至有人认为,“在对各种可能的选择谨慎地加以权衡之后精雕细刻出的程序,是保证一个文明社会认为值得保护的所有不同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的唯一方法。”[17](107页)正当法律程序是对权力的根本性制约,是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说权力分立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范围,那么正当法律程序则是权力行使的边界或底线。“现代宪法主要以程序为导向”,[18](6页)程序的稳定性被认为是立宪政体的主要特征之一,[19](201页)这意味着程序对权力的制约也应当是长期而稳定的。当今,我国上下都在谈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实,法治的关键便是治权。但仅有依法治权或依法定程序是不够的,因为,法律规定的程序并不一定合理、正当。我们必须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构建一套完整、合理的实施制度,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一个边界或底线。惟其如此,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2、程序本位是现代宪政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要求。“一个社会的立宪正体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基本规则及其实践与该地大多数人民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方式相一致的程序。”[19](201页)在美国,凡被认定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立法、行为都被宣布为无效。也就是说,评价一个法律程序的唯一标准是程序本身的内在品质即程序是否正当,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因此,程序具有价值上的独立性。在美国宪法中,除了第五、第十四条修正案外,还有大量关于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联邦高等法院大法官W·道格拉斯(Douglas)评论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6](221页)在英国宪法中,程序问题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最重要的宪法文件都与诉讼的原则、制度、规则有关,英国宪法甚至没有关于公民实体的权利和自由的具体规定。[16](221页)作为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特有表现形式的自然公正原则甚至也被认为是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20](45页)长期以来,我国存在重实体、重结果而轻程序的观念,并导致具体法律制度中程序规定零散、不科学、不合理普遍存在。在传统观念中,程序仅仅是实现某种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只有“依法定程序”的说法,而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这与现代法治社会中程序本位观念格格不入。程序本位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之一,它是现代宪政的前提。可以说,不树立程序本位观念,则不能建成法治国家。树立程序本位的关键是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全、彻底地排除违反法律程序的立法、行为的有效性。
3、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是宪法司法化的重要途径,是宪政与宪法发展的基本方式和动力。美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从两条简单的条文演绎成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并形成各种学说,是美国宪法经由法院不断地运用于具体案件即宪法司法化的结果。有学者认为,在美国,过去40年左右是司法革命的年代,而对这场革命的解释要从其宪法中寻找答案。因为,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宪法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对美国宪法的戏剧性革新,从形式上讲,主要来自对一条法条的‘诠释’。该条就是1868年植入宪法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上述变化都涉及对该项修正案中两句短语的解释,即关于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障原则的解释。”[2](16页)正当法律程序本身是宪法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宪法和其他任何法律一样,正是籍此适用于具体案件才真正具有了生命力。正如有人指出的,“司法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从书本上的法到实际生活中的法之桥梁,是从原则转化为实际规则的中介。”[21](4页)正是宪法的司法化,美国宪法获得了发展的途径,成为了一部“活的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发展,仅是美国宪法在条文不变情况下获得发展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其他许多条款也在司法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如契约自由条款、平等保护条款等都是如此。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使美国宪法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一方面它使宪法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容纳了社会的发展,这使得宪法“旧的形式依然存在,但它们已经充满了新的内容。”[5](62页)“最成功的宪法是那些允许发展而又不常改变字面意义的宪法。”[19](201页)在我国,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宪法的发展,非常有限,已有的发展多半不是来自宪法本身及宪法实践,而是来自政治及其他法律发展后的推动作用。宪法的司法化,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中的重要议题;而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必须是健全、完善的宪法实施程序,当然,其核心是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注释
①《民治政府》一书的作者认为,要准确弄清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是不可能的。(见该书第209页)
②有人认为,“法律的正当程序”与“正当法律程序”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程序的形式合法性,后者强调程序的实质正义性。(参见杨一平《司法正义论》第137页)笔者认为,这种区别其实并不存在,“法律的正当程序”与“正当法律程序”仅是dueprocessoflaw的两种不同译法——中文表达的字面差异,而dueprocessoflaw包含了上述两层含义,这反映了两种语言之间缺乏严格的对应关系。目前学界多将dueprocessoflaw译为“正当法律程序”,并同时包含上述两种含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更可取。
③在美国法学中废弃自然法的理由包括:1,当代盛行的法学既非哲理的,也不是历史的,而是社会学的;2,自然法是哲理的而不是法学的,其十分抽象的价值判断不能具体地用于审理特定的案件;3,除非每个人的道德和经济观念一致,并崇拜控制他们的单一权威,否则,自然法理论是无法运用的;4,随着宪法判决的增加,法官们现在无需援引自然法便可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判例。(参见《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第154—155页)
④有关内容参见《美国法律史》第56页的论述。另,N·卢曼进一步认为:自然法的失坠是由程序来补偿的。(见吕世伦主编《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第232页)
⑤王希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在判决中,他们(指联邦最高法院的保护派大法官—引者注)经常引用第五条修正案(保护财产权)和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和特权及豁免权条款)来向新政法律挑战。”(见该书第433页)
⑥有关内容参见《美国法律史》第183页;另见《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第469页。
⑦相关分析参见《美国宪法概论》第110-111页有关内容。
⑧关于历史判断模式,参见《宪法教学案例》第70页有关内容。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M].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朱伟一,董婉月.美国经典案例解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焦洪昌,李树忠.宪法教学案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谭君久.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5](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杨一平.司法正义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杨百揆,刘庸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8]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刘瑞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11](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M].黎建飞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曾尔恕.论美国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司法检验标准[J].比较法研究,1998,(2).
[13]杨寅.普通法律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3).
[14]刘卫政,司徒颖怡.疏漏的天网:美国刑事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5](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等.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M].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6]吕世伦.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17](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8](瑞士)莉蒂塔·r·芭斯塔.宪政民主的反思:后现代和全球化的挑战[A].刘海年等.人权与宪政[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19](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正当程序范文篇10
[摘要]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基础,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本身的理论,而且促进了宪法、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涵的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对我国宪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宪法宪政正当法律程序检验标准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它虽然是美国宪法中最难理解的部分,[1](209页)却又被认为是美国法律的本质所在;[2](19页)它虽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论争,对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①却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中有40%与正当法律程序有关,在联邦最高法院适用于各个案件的次数远远超过美国宪法其它条款的规定,[3](68页)而成为美国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宪法保障。[4](54页)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美国宪政的基石。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5](46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6](149-150页)“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6](137页)看来,正当法律程序正在超越英、美法系的传统文化藩篱,而逐渐为世界其他法律文化所认同。
壹从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
丹宁勋爵在他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中说:“我所说的‘正当程序’指的不是枯燥的诉讼案例,它在这里和国会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意思倒极其相似。它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中:‘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继承权和生命’。”“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也和麦迪逊(Madison)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它已被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7](前言)“法律的正当程序”即本文的正当法律程序,英文表达为:dueprocessoflaw。②在这里,丹宁勋爵的前一句话揭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渊源:1354年,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的法律文件中。以非正式法令形式出现的正当程序条款则可追溯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康得拉二世有“不依帝国法律以及同等地位族的审判,不得剥夺任何人的封邑”的规定,这是给封建贵族的特权或帝王赋予的权利的司法保障。[3](62页)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章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者逮捕。”这一规定反映了封建贵族与封建君主斗争的成果,即用法律程序对封建君主加以约束,而对封建贵族加以保护。[3](62页)康得拉二世及《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与后来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相去甚远,它只是一种贵族的特权,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权利(哪怕只是程序性的!)。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3](62页)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1868年第十四条修正案是美国宪法第二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然而,丹宁勋爵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并不就是后来美国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司法实践所“形成”的正当法律程序,尽管他的上述第二句话棗“我所说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棗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的第五条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都仅意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对此,丹宁勋爵作如是解释:“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捎茫稍忱厝〉茫约跋槐匾难游蟮鹊取!盵7](前言)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的独特表现形式,[6](147页)是有道理的。自然公正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8](55页)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又提出两项新的自然公正原则:其一是,无论处理争议的程序是司法性质的还是非司法性质的,争议各方都有权了解作出裁决的理由。其二是,如果对负责调查的官员所提出的报告草案提出了公众质询,那么争议各方有权得到该报告的副本。[8](55-56页)自然公正的这些原则都是程序性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其基本要求是程序公正。它是“要过问政府行事的方式以及它所采用的执行机制。当政府剥夺一个人已经获得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利益时,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程序上的公正性。”[9](128页)或者说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法律赖以实施的方法或法律采用的方式。[1](209页)它是对怎样行使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它同法律的程序有关,主要限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1](211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麦迪逊将正当法律程序写入其起草的《权利法案》初稿时,他便?皇前颜狈沙绦蚩醋饕恢殖绦蛏系谋U稀10](55页)在第五条修正案通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还仅指刑事诉讼程序问题,即指要保证被告一定按照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来公平受审,刑事被告人享有一定的受保护的权利,政府只有遵守这些法定程序,才可以采取对被告人不利的行动。它既不与公民的既得权利相联系,也不涉及到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的影响问题。”[3](63页)在这个时候,它要求的具体程序是:“先审讯,后宣判;根据调查起诉,只有在审问或某种听证之后才能作出判决。”[1](209页)那么,什么程序是正当的呢?在联邦法庭上,正当程序要求小心遵从第四条至第八修正案中列出的权利法案条款。“什么是正当的这一问题在另类诉讼中就是:为保证基本公平必须做什么。”这要求至少“涉及的人必须获得适当通知并有机会被听取陈述。”[1](21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但许多美国学者不加以分析和概而把联邦宪法第1-10条修正案中所适合的程序保障要求直接视为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具体标准。[8](57页)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然而,早期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建立在一种可疑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权利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规定在例外的情况下权力不应当行使或不应以某一特定的方式行使,对权力加以限制和限定。”[10](35页)权利法案特别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并不能全部达成这一目标,这时对政府权力特别是立法机关的权力的实质性限制依赖于自然法。1909年,迪安·庞德写道:“我们必须记住,自然法是《权利法案》的理论根据,”“宪法贯穿了自然法的观念”。[11](145页)后来随着坎特著作的出版,出现了对自然法的怀疑,自然法理论随之式微。③宪法的核心从自然法的理论迅速转向包含在正当程序条款中的明示的限制。④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以致不论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的观点看,个人权利都是由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是对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立法权的一项宪法限制,即“对行使政府权力做什么加以限制”,“同法律的内容有关”,主要限制立法部门。[1](211页)它是指一项“不合理”的法律,即使是恰当地通过了,恰当地实施了,仍是违宪。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
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首先是由州法院的判决确立起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56年怀尼哈默诉人民案的判决。该案起因于一项纽约州禁止出售非医用烈性酒并禁止在住所之外的任何地方储放非用于销售的酒类的法律,纽约州法院认为,“该法的实施,消灭和破坏了这个州的公民拥有烈性酒的财产权”,这恐怕与正当程序条款的精神不符。[10](56页)这一判决的意义在于纽约州法院用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代替了自然法,对立法权进行实质性的制约。9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尼诉哈默案中首次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作为实体法条款使用。[3](64页)至此,正当法律程序开始成为一种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权不合理干涉的有力工具。1866年,国会提出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1867年该修正案被宣布生效。纽约州法院审理怀尼哈默案的推理最终为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美国法院所普遍采纳,正当法律程序成为了一项真正的宪法制度。第14条修正案是划时代条款,“代表了一场真正的宪法革命”。[10](114页)其后果之一便是实现了公民权利的联邦化,[10](105页)即使权利法案的各项基本权利“加以并入”并使之适用于各州。1968年,在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一项从权利法案中“吸收来的”保障要按它制约联邦政府的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来制约州。[9](101-102页)从单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同时兼含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演进过程,揭示了:第一,美国宪法的条文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和包容性,虽然仍是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条文,却前后包含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不同的宪法内容,在保持宪法条文不变的情况下,宪法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美国宪法发展的主流方式,它是美国宪法历200余年而能保持其稳定外观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宪法具有灵活性特征的关键。第二,随着联邦最高法院权力的扩大,需要对国家权力依制衡原则重新配置,从而使三权分立制度更趋合理、稳定、平衡。宪法内容的上述发展基本上是由法院来完成的,它是法官运用特定时期的宪法理论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的结果。这种宪法解释的权力是马歇尔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的,对宪法的解释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使美国法院获得了三权分立体制中最实在的权力。第三,人权保障得到加强。就公民而言,他不仅可以就司法和行政中程序性权利请求法院保护,而且还可以就联邦及州的立法请求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以保障其实体权利不受侵害或者在其受到侵害后能得到合理的救济。
贰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检验标准
(一)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检验标准
1、理性基础检验标准
理性基础检验标准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审查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适用于经济案件中。企业界历来在宪法中寻找依据,以便保护其财产免遭州的经济管制和干预。宪法上常被引用来支持这一保护的章节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9](103页)在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在经济案件中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判断应持尊重态度。[9](105页)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坚持一种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常常以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为由宣布“新政”立法违宪,⑤导致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2月向国会提出了改组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系统的法案。罗斯福改组法院计划虽未获成功,但联邦最高法院从1937年4月开始,法官们对每一个提交给他们的新政法令都采取支持态度,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类似于过去被宣布为无效的新政法令。[10](180页)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转变,史称1937年宪法革命。1937年以后,最高法院审慎地抛弃了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认为只要是“为了社会利益而颁布的法令,都是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⑥并且从“司法尊重很快转变成在经济管制案件中完全取消审查。”[9](106页)最高法院声称:“立法机关是否把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凯恩斯爵士或其他一些人的学说当作教科书,与我们的判决并?薰叵怠?[10](184页)“一部宪法无意体现一种具体的经济理论,无论它是家长制理论,公民与国家的有机关系理论,还是自由放任理论”。[5](48页)虽然如此,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名义上仍然存在,法院用以审查社会经济法律时,先假设该法律合宪,而“把证明该法律与所允许的政府利益没有任何理性关系的举证责任放在提出质疑的一方的肩上”。[9](106页)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最高法院审理经济案件中的变迁,标明正当法律程序在这一领域的衰落,其实质是在相互分立的三权之间对经济领域立法权力的重新配置棗最高法院采取了退让的办法以维持三方均衡。不过,“法院在经济领域退让的东西,正是它在其他领域新获得的东西,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护领域获得的东西。”[2](13页)法院在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立法采取了严格的检验标准。
2、严格检验标准
如上所述,严格检验标准针对的是联邦或州对个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立法。在理性基础检验标准的情况下,一项法律只要与所允许的政府目标之间有理性关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在严格检验标准情况下,仅有理性关系是不够的,还要求政府必须确定,该法是严格地适应紧迫或重大的政府利益的。[9](109页)但是,严格检验的标准并非始终如一,一般地讲,可以说随着对被保护权利施加的压力越大,就越强烈地要求政府申述理由。[9](110页)严格检验所针对的个人基本权利包括两部分:一是法明示的权利和从宪法文本中引伸出来的权利,二是司法上产生的权利。[9](127页)任何一项针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立法的违宪审查申请,都要证明权利是宪法明示或引伸出来的,否则,很难得到法院的同情。对于如何确定《宪法》条文中引伸出来的权利,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宪法本身的解释来找出宪法权利。一种观点认为在宪法条文之外存在着宪法原则或准则,通过这些宪法原则或准则可以发现和形成宪法外的基本权利。确定宪法外基本权利的依据包括:其一是依靠传统和习惯得来的价值观,其二是一种动态方法确定那些包含在有秩序自由的概念中的价值观。⑦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严格检验标准,体现了联邦法院对人权给予严格保护的积极态度。
3、中间层次检验标准
这一检验标准介于理性基础检验和严格检验标准之间,主要针对的是婚姻和家庭权利。对婚姻、家庭权利之所以采用中间层次检验标准,是因为在性质上,婚姻、家庭权利对于个人的意义介于经济权利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一项利益是否受正当程序的保护,取决于该项利益的性质,不取决于该项利益对个人的重要性。”[1](210页)最高法院一面声称“本法院始终认为,个人对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选择自由是受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之一。”(1974年克利夫兰教育委员会诉拉费勒案)[9](122页)最高法院同时又主张:法律必须服务于“各种重要的政治目标,并且必须与这些政府目标的实践具有实质性的联系。”[12]这说明,对婚姻、家庭权利方面的立法的司法审查中,只要该立法与政府目标具有实质性的联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不要求该立法严格地适应紧迫的、重大的政府利益。
(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标准
在美国,“宪法上的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原则上只适用于裁决性活动,而不适用于制定规则的活动。”[13]适用于裁决性活动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其基本要求是程序正当或程序公正。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认为,“程序的公正和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宁愿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厉的实体法,也不愿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8](56页)然而,什么程序是正当的呢?在美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目前,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什么程序是正当的乃是一个靠法院解释‘正当程序’含义来回答的联邦宪法问题。”[9](134页)如前所述,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坚持的理论看,在司法及行政执法中严格遵从《权利法案》的条款,保障涉及的人获得适当通知并有机会被听取陈述,是程序公正的最一般的要求。即使如此,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1976年)以后正当法律程序分析保持了极大的灵活性。在具体的案件中,如何判断所采取的程序是否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法院在早期采用一种被称为“历史判断模式的方法,将制宪者的原意作为程序正当性的判断依据。⑧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中碌摹⒘榛畹呐卸媳曜迹卸铣绦蛘毙缘囊谰菔牵骸暗谝唬芄俜叫卸鸷Φ乃饺死妫坏诙ü捎玫某绦蛟斐纱砦蟮匕岣美娴奈O眨约案郊拥幕蛱娲某绦虮;さ目赡芗壑担绻姓夥矫娴募壑狄悸堑幕埃蛔詈螅睦妫ㄓ泄氐闹澳埽约案郊拥幕蛱娲某绦蚍ü娑ㄋ斐傻牟普托姓旱!!盵9](135页))我国有人将这一新的判断标准称为“利益衡量模式”,[3](68页以下)而美国学者称之为“三部分检验法”。[9](135页)这一判断模式是目前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正当程序判断的主导模式,尽管它也招致了许多批评。根据这一标准,最高法院对程序正当性的判断可以因案而异,具有很强的主动性、灵活性。最高法院正是籍此随时根据社会的变化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从而不断获得权力,提高地位,并最终成为美国宪政制度的核心。然而,对最高法院的这一趋向并非没有限制,如,就刑事案件而言,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保障被告人至少享有如下程序性权利:(1)通知指控罪名的权利;(2)受审的权利;(3)由辩护律师辩护的权利;(4)对指控罪名答辩的权利;(5)与指控人和证人当面对质与辩论的权利;(6)拒绝自认犯罪的权利;(7)出示被告人证人的权利;(8)无罪推定的权利,即被告人被视为无?铮欠ㄍピ谏笈衅诩涓菔抵手ぞ葜っ鞅桓嫒擞凶铮唬?)获得判决书的权利;(10)上诉的权利。[14](8页)又如行政法领域,在正当程序诉讼中最经常地予以审核的程序权利包括:(1)事前的通知和听证的权利;(2)获得审判形式的听证的权利;(3)律师辩护权;(4)由公正无私裁决人进行裁决的权利;(5)获得调查结果和结论的权利。[15](131-145页)对以上任何一项权利的剥夺,都将导致裁决无效。
叁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政意义
正当法律程序,在美国宪法中只有两条简单的条文,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发展出了丰富而且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特色。美国宪政中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与实践,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当今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启示:
1、对权力的程序制约,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原则和发展趋势。美国的宪政制度比较彻底地贯彻了权力分立原则,无论是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还是纵向的联邦、州、地方政权的权力分立,都是西方国家的典范。权力分立的原始意图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对权力如何制约呢?除了用宪法详细规定各种权力的范围并使各种权力行使者之间相互制约外,美国宪法还确立了以程序制约权力的原则,即不论何种权力的行使都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美国,维护这一原则的核心手段便是正当法律程序。[16](246-247页)甚至有人认为,“在对各种可能的选择谨慎地加以权衡之后精雕细刻出的程序,是保证一个文明社会认为值得保护的所有不同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的唯一方法。”[17](107页)正当法律程序是对权力的根本性制约,是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说权力分立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范围,那么正当法律程序则是权力行使的边界或底线。“现代宪法主要以程序为导向”,[18](6页)程序的稳定性被认为是立宪政体的主要特征之一,[19](201页)这意味着程序对权力的制约也应当是长期而稳定的。当今,我国上下都在谈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实,法?蔚墓丶闶侵稳ā5鲇幸婪ㄖ稳ɑ蛞婪ǘǔ绦蚴遣还坏模蛭晒娑ǖ某绦虿⒉灰欢ê侠怼⒄薄N颐潜匦朐谙芊ㄖ腥妨⒄狈沙绦蛟颍菇ㄒ惶淄暾⒑侠淼氖凳┲贫龋Φ男惺够ㄒ桓霰呓缁虻紫摺N┢淙绱耍芊ü娑ǖ幕救ɡ妥杂刹拍艿玫接行У谋U稀?/P>
2、程序本位是现代宪政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要求。“一个社会的立宪正体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基本规则及其实践与该地大多数人民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方式相一致的程序。”[19](201页)在美国,凡被认定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立法、行为都被宣布为无效。也就是说,评价一个法律程序的唯一标准是程序本身的内在品质即程序是否正当,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因此,程序具有价值上的独立性。在美国宪法中,除了第五、第十四条修正案外,还有大量关于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联邦高等法院大法官W·道格拉斯(Douglas)评论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6](221页)在英国宪法中,程序问题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最重要的宪法文件都与诉讼的原则、制度、规则有关,英国宪法甚至没有关于公民实体的权利和自由的具体规定。[16](221页)作为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特有表现形式的自然公正原则甚至也被认为是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20](45页)长期以来,我国存在重实体、重结果而轻程序的观念,并导致具体法律制度中程序规定零散、不科学、不合理普遍存在。在传统观念中,程序仅仅是实现某种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只有“依法定程序”的说法,而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这与现代法治社会中程序本位观念格格不入。程序本位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之一,它是现代宪政的前提。可以说,不树立程序本位观念,则不能建成法治国家。树立程序本位的关键是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全、彻底地排除违反法律程序的立法、行为的有效性。
3、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是宪法司法化的重要途径,是宪政与宪法发展的基本方式和动力。美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从两条简单的条文演绎成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并形成各种学说,是美国宪法经由法院不断地运用于具体案件即宪法司法化的结果。有学者认为,在美国,过去40年左右是司法革命的年代,而对这场革命的解释要从其宪法中寻找答案。因为,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宪法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对美国宪法的戏剧性革新,从形式上讲,主要来自对一条法条的‘诠释’。该条就是1868年植入宪法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上述变化都涉及对该项修正案中两句短语的解释,即关于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障原则的解释。”[2](16页)正当法律程序本身是宪法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宪法和其他任何法律一样,正是籍此适用于具体案件才真正具有了生命力。正如有人指出的,“司法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从书本上的法到实际生活中的法之桥梁,是从原则转化为实际规则的中介。”[21](4页)正是宪法的司法化,美国宪法获得了发展的途径,成为了一部“活的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发展,仅是美国宪法在条文不变情况下获得发展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其他许多条款也在司法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发?梗缙踉甲杂商蹩睢⑵降缺;ぬ蹩畹榷际侨绱恕U狈沙绦蛱蹩畹乃痉ㄊ视茫姑拦芊ň哂泻芮康氖视π裕环矫嫠瓜芊ū3至私锨康奈榷ㄐ裕硪环矫嫠旨蟮厝菽闪松缁岬姆⒄梗馐沟孟芊ā熬傻男问揭廊淮嬖冢且丫渎诵碌哪谌荨!盵5](62页)“最成功的宪法是那些允许发展而又不常改变字面意义的宪法。”[19](201页)在我国,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宪法的发展,非常有限,已有的发展多半不是来自宪法本身及宪法实践,而是来自政治及其他法律发展后的推动作用。宪法的司法化,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中的重要议题;而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必须是健全、完善的宪法实施程序,当然,其核心是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注释
①《民治政府》一书的作者认为,要准确弄清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是不可能的。(见该书第209页)
②有人认为,“法律的正当程序”与“正当法律程序”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程序的形式合法性,后者强调程序的实质正义性。(参见杨一平《司法正义论》第137页)笔者认为,这种区别其实并不存在,“法律的正当程序”与“正当法律程序”仅是dueprocessoflaw的两种不同译法棗中文表达的字面差异,而dueprocessoflaw包含了上述两层含义,这反映了两种语言之间缺乏严格的对应关系。目前学界多将dueprocessoflaw译为“正当法律程序”,并同时包含上述两种含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更可取。
③在美国法学中废弃自然法的理由包括:1,当代盛行的法学既非哲理的,也不是历史的,而是社会学的;2,自然法是哲理的而不是法学的,其十分抽象的价值判断不能具体地用于审理特定的案件;3,除非每个人的道德和经济观念一致,并崇拜控制他们的单一权威,否则,自然法理论是无法运用的;4,随着宪法判决的增加,法官们现在无需援引自然法便可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判例。(参见《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第154—155页)
④有关内容参见《美国法律史》第56页的论述。另,N·卢曼进一步认为:自然法的失坠是由程序来补偿的。(见吕世伦主编《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第232页)
⑤王希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在判决中,他们(指联邦最高法院的保护派大法官椧咦ⅲ┚R玫谖逄跣拚福ū;げ撇ǎ┖偷谑奶跸芊ㄐ拚福ㄕ背绦蛱蹩詈吞厝盎砻馊ㄌ蹩睿├聪蛐抡商粽健!保檬榈?/FONT>433页)
⑥有关内容参见《美国法律史》第183页;另见《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第469页。
⑦相关分析参见《美国宪法概论》第110-111页有关内容。
⑧关于历史判断模式,参见《宪法教学案例》第70页有关内容。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M].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朱伟一,董婉月.美国经典案例解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焦洪昌,李树忠.宪法教学案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谭君久.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5](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杨一平.司法正义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杨百揆,刘庸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8]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刘瑞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11](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M].黎建飞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曾尔恕.论美国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司法检验标准[J].比较法研究,1998,(2).
[13]杨寅.普通法律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3).
[14]刘卫政,司徒颖怡.疏漏的天网:美国刑事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5](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等.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M].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6]吕世伦.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17](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8](瑞士)莉蒂塔·r·芭斯塔.宪政民主的反思:后现代和全球化的挑战[A].刘海年等.人权与宪政[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19](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相关文章
正当刑法解释判断标准探讨 2022-08-11 02:46:29
后劳教时代“微罪”入刑正当性分析 2022-03-02 10:59:29
社会主义正当防卫制度的价值取向 2022-03-02 10:19:03
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边界分析 2022-11-12 04:40:37
第三人到期债权执行名义的正当性分析 2022-11-03 10:54:31
网络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与法律适用 2022-06-16 03: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