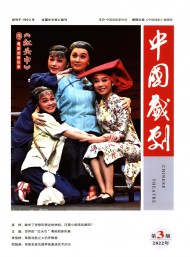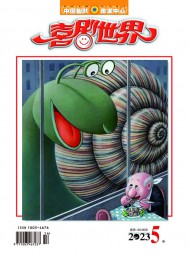剧作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1 08:58:38

剧作家范文篇1
剧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参加到电影剧本创作的队伍中来的人都会问到的,可是人们的回答却很不一样。很久以来就流行着一种观点,电影编剧的责任应该就是创作出故事情节,运用人物动作和对话来塑造出丰满立体的性格,至于蒙太奇、拍摄方法、用什么景别来表现、声音和画面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方面的事情就交给导演来处理吧!表面上看,这还真有点分工合作的道理,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所谓的“道理”阻碍了电影编剧整体水平的发展。
电影动作的意义
确实,电影剧作家应该有责任讲好故事并运用结构技巧铺排好情节,他们更应该把塑造出性格扎实可信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最最重要的责任。但是,剧作家用什么来塑造人物呢?传统的说法喜欢笼而统之道:“动作。”也许,这在过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定律,然而我们今天却不能不重新考虑它的真理性。
动作,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戏剧。对“动作”这个概念作出最全面的也是最具影响的论述者应该是贝克,他对动作所总结出的理论成为沿用至今的定理。他甚至认为动作比其它剧作元素都要重要。他说:“‘情感交流’是一切好剧本的公式。所谓情感交流,是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把感情先流到观众身上,那么,这就非靠动作不可,因为动作是激动观众感情最迅速的手段。”是他首次明确地将动作分为内部动作(也作“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两大方面的。他的失误在于没能正确地说明内心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物能够不用外部动作就可以将内心动作表现出来,例如他在舞台上一动也不动。后来者多次指出他的这一失误,因为内心动作是外部动作产生的依据,外部动作是内部动作的反映,内部动作只有通过外部动作才能得到揭示,而他所谓的“一动也不动”,其实就是人物在那一时刻的外部动作。那时,人们还把人物的形体动作(其中包括表情动作)看作是外部动作的全部内容,但到后来,人们开始觉得语言动作(对话)也是外部动作的一部分。因为在戏剧舞台上,人物可以发挥的形体动作(尤其是表情动作)实在是有限,而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更主要地依靠着对话。所以,戏剧对于对话的写作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动作性。对话只是内心动作的外部表现,并非内心动作的全部的、直接的反映,对话的“潜台词”就产生于对话与内心动作之间的差异。
总之,在戏剧的剧作理论中,“动作”这一概念便是人物塑造的全部武器。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向戏剧学会叙事的。戏剧的叙事经验曾经就是电影编剧的罗盘经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有着同样的定律,那就是动作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唯一法宝。除了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你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动作。所以我们至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导演将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全部努力都用在了演员身上,为了说明那个剧中人物此时是痛苦的,便让演员作出嚎啕大哭之类的痛苦状来。但也有很多高明的导演越来越发现电影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有着很多与戏剧不同的办法。比如,在最初,人们发现的(这也是最最容易发现的)是就人物动作中的形体动作而言,在戏剧舞台上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细微的表情和手势动作却在电影里成为揭示人物心理更重要的武器。例如弗雷里赫就曾经指出:“摄影机善于摄录极其细小的动作、极其微妙的细节、难以捉摸的语调、眼睛的闪动、睫毛的颤动;善于选取出最最重要的东西,用一个单独的场面把它突出出来——摄影机的这些能力决定了银幕上的戏剧动作的性质。”
很快,人们就发现电影与戏剧在揭示人物内心方面的差异还不仅仅是动作幅度上的问题,例如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当尼洛夫娜坐在丈夫的棺材前陷入令人窒息的悲哀的时候,导演并没有指示演员嚎啕大哭,甚至他不让演员流一滴泪,只是木然地静坐在那里。当然,前面我们说过,静静地坐着也是人物的外部动作,但仅仅靠这样的动作就很难揭示母亲此时的内心痛苦了。这时,导演聪明地在母亲的脸的镜头之后接入了一个特写镜头:水从悬壶洗手器中慢慢地滴下来,一滴又一滴。水滴的形象和节奏十分巧妙地将人物此时此刻那种绝望的、欲哭无泪的悲哀揭示了出来。现在要问:滴落的水滴是人物的动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情况纳入剧作理论呢?
电影剧作理论家们在这一方面似乎有点保守,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他们通常能够指出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的方法与戏剧的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依然不敢贸然地抛开戏剧理论已成的“动作”概念。他们依然将那些电影艺术中出现的新武器叫作“动作”,只不过有了点小小的改良。例如:劳逊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就英明地发现,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内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包括将这个动作展现给观众的方式。他以卓别林的影片《巴黎一妇人》举例说:“他(卓别林饰演的人物)的妻子因为他啫酒而离弃了他。我们看到他背对着摄影机,望着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肩膀上下抽动,好象在伤心地啜泣。之后我们却发现他正在摇动一瓶香槟酒。”在这时,揭示人物性格和引起观众笑声的不是人物的动作。如果你一开始就从正面将卓别林开香槟的动作直接表现给观众看就绝对不能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劳逊指出:“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这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应该是重要的发现。他甚至还指出:“构图决不只是动作的注解。它本身就是动作。”这同样是英明的。但是,他依然将这些发现统称为“动作”,只不过在“动作”前面加上了“电影”两个字用以区别戏剧的“动作”概念。他定义说:“电影动作就是用光和影表现出来的活动。”
弗雷里赫将劳逊的发现向前推进了,他除了前边我们提到的他关于电影在表情和手势动作方面与戏剧的不同外,还指出:“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准备让演员来表演,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把这表演拍摄下来。”显然,他认为,对于戏剧说来,动作本身就是一切,而对于电影说来,在表情达意方面摄影机表现动作的方式也许更加重要。他这样要求电影的编剧:“电影剧作家在下笔以前也应该先在自己头脑中看见所设想的动作,但他在想象中仿佛预先看到了演员的表演,以后被摄影师拍成许多镜头,又被导演剪辑成统一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电影动作’这一概念之中。”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本文一开始提到过的夏衍先生对电影编剧的要求,就不难发现,弗雷里赫对电影编剧的要求扩大了很多,他将景别、摄法(是固定拍摄?还是运用推拉摇移的运动拍摄?)甚至于蒙太奇方式都交给了电影编剧。但是,他依然将所有这些都称作“银幕上的戏剧动作”或“电影动作”。
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苏联电影剧作理论家瓦依斯菲尔德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发现,他在《电影剧作家的技巧》一书中的“动作”一节中问道:“影片中的动作跟舞台剧或小说中的动作又和区别呢?”接着他就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重点放在了电影的平行蒙太奇上。他认为在舞台上是无法充分表现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的,而电影的平行蒙太奇却很好地利用它来增强了动作的表现力了戏剧性。然而,他依然认为电影的这些武器是“动作”的范畴。
其实,我本人在最初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在我1986年完成的《你了解这门艺术吗?——电影剧作常识100问》一书中,我论述了主观镜头、摄影机的运动、光影甚至音乐(例如《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等有着与动作相同的揭示人物心灵和塑造人物性格的功能。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脱离戏剧理论的框架,称这些电影独有的武器为“银幕动作”。
如果今天我再写那本小书的话,我就不会称它们为“银幕动作”。我会明确地指出,“动作”这个剧作元素只是电影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元素之一(即便在电影艺术中它依然是最最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它不象戏剧那样就是全部。除了动作之外,电影还有其它揭示人物心灵和性格的手段。而将这些独特的手段纳入剧作家的构思和写作应该是剧作家的责任,不能把它们推卸给导演或摄影师。
内心生活的物化
在很多时候,剧作家不能只写剧中人物的动作。比如有时即便一个人内心冲突很激烈或者他很痛苦,却被深深地掩盖着。这时,从表面上看你就无法看出他心灵中的真正情感。然而这正是一个人物最最准确真实的情感表现方式,如果你硬要演员通过形体动作来表现,比如说,让他痛苦或歇斯底里,就太令观众反感。我认为,编剧在这时还有很多比求助于人物动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人物的内心生活物化。在现代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使用“闪回”直接将人物内心转换成画面,或者运用画外音形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说给观众听。当然,这些手法用得巧妙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的。但必须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人的内心生活是复杂的、混乱的、片段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如果表现得太客观、太有逻辑、太冷静、太直白就会变成一种简单的图解,令人生厌。例如:《阿Q正传》中出现了阿Q的梦境,就有图解的意味。相比起来,法国电影《老枪》中的处理就好得多。当男主人公向德国人举起枪的那一瞬,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他与已经被德国人杀害的妻子过去生活的短暂闪回,而那些闪回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时刻,反而是他吃妻子醋的片断,这就不得不使观众发挥了自由的联想。我国影片《人鬼情》中的“戏中戏”运用得也很好。锺馗的唱段恰到好处地烘托着剧中女主角秋芸的心情。现在的编剧不是不用闪回的问题,而是滥用和乱用闪回的问题。关于如何使用时空交错式结构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电影剧作理论中一个没有足够研究的领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想将它放到以后再展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非什么时候都应该使用“闪回”,我们还有更加绝妙的方式来将人物的心灵展现给观众看。例如在《城南旧事》中有一场戏是疯子秀珍对小英子诉说自己往昔的遭遇。在原来的剧本中,这些东西就是通过“闪回”来表现的。但如果一个疯子能如此从容地、有逻辑地回忆过去,显然就有失真实。这样也无法揭示今天秀珍那种神经质的感情状态。在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是高明的,他抛开了“闪回”,却利用了从秀珍视点出发的空镜头,那镜头在神经质的画外音中轻轻地拉开,又悄然地推向空空的房屋,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情感节奏,使我们与秀珍的心灵合而为一。在这里,同时起着作用的就不仅仅是秀珍的动作和语言,而是摄影机运动的节奏。这样的处理本来就应该是编剧的责任,可惜的是现在由导演来完成了。
在很多的时候某个物件道具也会成为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对象化途径。在前边,我们举过的普多夫金《母亲》中那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那一刻,母亲的心情正是通过悬壶洗手器中慢慢滴落的水滴表现出来的。水滴的节奏与人物心灵的感情节奏形成了一种模拟的关系,就好象我们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细雨打在芭蕉或梧桐叶子上的声音节奏来表现愁绪一样。在意大利影片《我们曾如此相爱》中有个更有趣的例子:影片中三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子是很好的朋友,二战后,女青年与三个男青年中最富有的一个恋爱,却最终被他抛弃。当她与另外两个同样爱着她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却为了她而争吵起来。这时,我们看到这个女青年的动作和表情似乎并没有过多的痛苦,她甚至蛮有兴致地走进了街边的自动照相亭照相去了。但当那两个青年人最终到照相亭找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不在。就当二人也要离开的时候,自动照相机发出了“喀、喀”的声音,一联四张照片从机器里边逐一地被“吐”了出来,上面都是那个女孩儿:第一张是她不太痛苦的脸,甚至还挂着笑容;第二张上的她就出现了愁容;第三张已经是痛苦的表情了;而第四张竟是她捂住脸痛哭的照片……在这里,编剧巧妙地利用了自动照相机这一道具,将人物隐藏得很深的痛苦内心揭示给我们,竟然比直接看到她哭的动作更加令人心碎!
如果一个编剧有这样的主动性,他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道具是能用来揭示人物心灵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剧作意识,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比如,我的一个学生曾经作过一个构思:一个小镇里生活的男孩,他的父亲是个粗暴的酒鬼,经常殴打他、他的妈妈和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但他太弱小了,却不可能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只能在内心里对父亲咬牙切齿。他每天躲出家门,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混在游戏厅里借打游戏来消磨时光……总之,故事很一般,因为当一个孩子只在心里冲突着的时候,我们观众是无法感觉到的。如果硬用表情或动作或台词表现出来,那就太直白了。后来,我们想到了他每天玩儿的那些个游戏机是个很好到道具,因为那个小男孩只有在打游戏机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强者。这时屏幕的光线照射在他仇恨的、被父亲打出青伤的脸上,不安地闪动着各种色彩。在屏幕里,他操纵着的武侠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击倒,人物那些庞然大物在倒下去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叫声。观众很容易就感觉出他实际上在向着自己仇恨的父亲使出拳脚,这便是他心灵的隐秘。我们找到了将它外现的物化方式。
在剧本中创造出感情的节奏
事实上,对于一个编剧说来,讲好一个故事固然难,用一种富有节奏感和旋律感的语气来讲故事就更难。我的一位学生问我:“老师,电影剧本是不是只要实打实地写出看到的和听到的就行了?”我告诉他:“是的。但那只是初级的认识。因为在一开始你必须改变文学思维的习惯,学会用画面和动作讲故事。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电影剧作的灵魂是虚的,那是一曲统一的但又分成乐章的旋律,它有着动人心魄的节奏。”法国国立声画学院的院长卡里埃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铁皮鼓》、《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等等都是世界影坛上的精品。在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在饭桌上问我:“在你教学生写作剧本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节奏。”他听后大叫:“我们是一样的。”确实,让学生理解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直到现在我国几乎大多数的编剧们依然只会忙着讲故事情节,而在他们讲述情节的时候依靠的依然只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就象德国电影心理学家于果.明斯特伯格指出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还是片面和狭窄的。我们仅仅探讨了电影演员及其表达情感的手段,而且我们的研究自然只限于对其身体反应的分析。但是尽管我们周围的人除了体态表达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手段来表达?约旱母星楹颓樾鳎缬熬缱髡呖隙ú挥κ艿秸庑┫拗频氖康摹!彼髡啪缱髡哂Ω醚罢乙恢纸谛那楦小胺涞缴硖逡酝狻薄ⅰ吧⒎⒌街芪Щ肪持小钡姆绞健@澄?慕西纳克也说:“很少有人懂得赋予一部影片以节奏和赋予画面以节奏有着相等的重要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写作剧本时,就试着把这种节奏安排进某些数学的比例关系中,即赋予某种节拍。”
伯格曼所拍摄的几乎所有影片的剧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显然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编剧。当我最初看到伯格曼的电影剧本时,心中很是诧异。因为在他的剧本中经常会写下一些无法变成视听形象的文字,例如:
“夜幕降临,暑热稍稍减退。黎明的时候,一阵热浪掠过了灰暗的海面。
……(略)
骑士回到沙滩,跪下来。他闭上眼睛,紧锁双眉,开始早祷。他紧握双手,嘴唇无声地念着祷文。他神情由于而悲痛。他睁开眼睛直视着东升的旭日,它象鼓胀的、将死的鱼从晨雾弥漫的海面上一跃而起。天空灰暗,沉滞不动;象一座坟墓的穹顶。一片乌云上方隐约可见一只海鸥,张着一动不动的翅膀,在空中飘翔。它发出古怪的、觳觫不安的鸣声。”
——《第七封印》
您着觉得奇怪吗?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导演,难道他不知道在他写下的第一句话里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我们如何从夜幕降临一直拍摄到黎明?更何况我们也无法为“暑热减退”和“热浪掠过”造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偶然,但当我读了他很多剧本(象《野草莓》)以后却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我终于知道了对于他说来,一个剧本真正应该记录的并不是那些看得到的和听得到的,而是一种能够形成情感传递的节奏。他是在演奏情感的音乐!
剧作家应该象贝多芬一样为他的作品付出节奏方面创造性的劳动,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的影片,它的剧作正是节奏的典范。下面是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创作的剧本《裸岛》的开场段落,我们立刻能读出它多特有的节奏感:
“2、黎明
海还在沉睡。
人也在沉睡。
晨雾中传来橹声。
一只小舢板靠近岸边。
船上有一对贫苦的农民夫妇,那是千太和阿丰。
……
3、大岛上的小河
晨雾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两人加快步子走近河边,开始往木桶里打水。
在默默打水的两人的头上,冰山一样陡峭的梯田的山,仿佛要刺透黎明的天空一样,高耸入云。
村里已经有人起来干活了。
打水的夫妇,朝着田间小道的人,恭敬地行礼,又继续打水。
打满了水,两人掮着压弯了的扁担,又急忙顺着来的路往回走。
4、岸边
两人气喘吁吁地走来,把装了水的桶挑到船上。
他们小心谨慎地搬运水桶,那水好象宝贝一样贵重。千太把住橹,阿丰解开系在岸边的绳子,伸手推开岸边的岩石。
缓缓漾开的涟漪。
鱼从仍然沉睡的海里,阵阵跃出水面。
5、大海
蔚蓝的大海,轻波缓浪。
岛屿还在晨雾之中,但东方已经亮了。
缓慢而单调地摇着橹的千太粗壮的手臂。
阿丰解下掖在腰上的毛巾擦汗。
小舢板的前方,有个手掌大小的岛,隐隐约约显现在眼前。
……”
他的剧本突出的个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因为那行为只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一对夫妇在黎明十分划着小舢板到一个大岛上去打水。”他在这里分明是在演奏第一乐章的主旋:轻柔、平和、欢快、明朗……所有视听元素在这里结构成为有机的节奏。在后面,整个节奏发生了变化:
“20、烈日当空
万里无云。
灼热的太阳当头。
21、海滩上
缓缓三轻波,反复进退。
静得使人昏昏欲睡。
清澈的波浪冲到沙滩上,又慢慢地退下去,小松球被晃荡得仿佛要睡着了。
22、梯田
憋住气使足劲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阿丰。“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23、干旱的大地
千太小心翼翼地浇水。
24、海滩上的松球
松球仍然好象陷入沉睡之中,单调地随着波浪漂来漂去。”
剧作家范文篇2
剧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参加到电影剧本创作的队伍中来的人都会问到的,可是人们的回答却很不一样。很久以来就流行着一种观点,电影编剧的责任应该就是创作出故事情节,运用人物动作和对话来塑造出丰满立体的性格,至于蒙太奇、拍摄方法、用什么景别来表现、声音和画面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方面的事情就交给导演来处理吧!表面上看,这还真有点分工合作的道理,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所谓的“道理”阻碍了电影编剧整体水平的发展。
电影动作的意义
确实,电影剧作家应该有责任讲好故事并运用结构技巧铺排好情节,他们更应该把塑造出性格扎实可信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最最重要的责任。但是,剧作家用什么来塑造人物呢?传统的说法喜欢笼而统之道:“动作。”也许,这在过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定律,然而我们今天却不能不重新考虑它的真理性。
动作,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戏剧。对“动作”这个概念作出最全面的也是最具影响的论述者应该是贝克,他对动作所总结出的理论成为沿用至今的定理。他甚至认为动作比其它剧作元素都要重要。他说:“‘情感交流’是一切好剧本的公式。所谓情感交流,是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把感情先流到观众身上,那么,这就非靠动作不可,因为动作是激动观众感情最迅速的手段。”是他首次明确地将动作分为内部动作(也作“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两大方面的。他的失误在于没能正确地说明内心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物能够不用外部动作就可以将内心动作表现出来,例如他在舞台上一动也不动。后来者多次指出他的这一失误,因为内心动作是外部动作产生的依据,外部动作是内部动作的反映,内部动作只有通过外部动作才能得到揭示,而他所谓的“一动也不动”,其实就是人物在那一时刻的外部动作。那时,人们还把人物的形体动作(其中包括表情动作)看作是外部动作的全部内容,但到后来,人们开始觉得语言动作(对话)也是外部动作的一部分。因为在戏剧舞台上,人物可以发挥的形体动作(尤其是表情动作)实在是有限,而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更主要地依靠着对话。所以,戏剧对于对话的写作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动作性。对话只是内心动作的外部表现,并非内心动作的全部的、直接的反映,对话的“潜台词”就产生于对话与内心动作之间的差异。
总之,在戏剧的剧作理论中,“动作”这一概念便是人物塑造的全部武器。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向戏剧学会叙事的。戏剧的叙事经验曾经就是电影编剧的罗盘经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有着同样的定律,那就是动作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唯一法宝。除了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你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动作。所以我们至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导演将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全部努力都用在了演员身上,为了说明那个剧中人物此时是痛苦的,便让演员作出嚎啕大哭之类的痛苦状来。但也有很多高明的导演越来越发现电影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有着很多与戏剧不同的办法。比如,在最初,人们发现的(这也是最最容易发现的)是就人物动作中的形体动作而言,在戏剧舞台上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细微的表情和手势动作却在电影里成为揭示人物心理更重要的武器。例如弗雷里赫就曾经指出:“摄影机善于摄录极其细小的动作、极其微妙的细节、难以捉摸的语调、眼睛的闪动、睫毛的颤动;善于选取出最最重要的东西,用一个单独的场面把它突出出来——摄影机的这些能力决定了银幕上的戏剧动作的性质。”
很快,人们就发现电影与戏剧在揭示人物内心方面的差异还不仅仅是动作幅度上的问题,例如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当尼洛夫娜坐在丈夫的棺材前陷入令人窒息的悲哀的时候,导演并没有指示演员嚎啕大哭,甚至他不让演员流一滴泪,只是木然地静坐在那里。当然,前面我们说过,静静地坐着也是人物的外部动作,但仅仅靠这样的动作就很难揭示母亲此时的内心痛苦了。这时,导演聪明地在母亲的脸的镜头之后接入了一个特写镜头:水从悬壶洗手器中慢慢地滴下来,一滴又一滴。水滴的形象和节奏十分巧妙地将人物此时此刻那种绝望的、欲哭无泪的悲哀揭示了出来。现在要问:滴落的水滴是人物的动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情况纳入剧作理论呢?
电影剧作理论家们在这一方面似乎有点保守,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他们通常能够指出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的方法与戏剧的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依然不敢贸然地抛开戏剧理论已成的“动作”概念。他们依然将那些电影艺术中出现的新武器叫作“动作”,只不过有了点小小的改良。例如:劳逊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就英明地发现,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内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包括将这个动作展现给观众的方式。他以卓别林的影片《巴黎一妇人》举例说:“他(卓别林饰演的人物)的妻子因为他啫酒而离弃了他。我们看到他背对着摄影机,望着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肩膀上下抽动,好象在伤心地啜泣。之后我们却发现他正在摇动一瓶香槟酒。”在这时,揭示人物性格和引起观众笑声的不是人物的动作。如果你一开始就从正面将卓别林开香槟的动作直接表现给观众看就绝对不能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劳逊指出:“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这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应该是重要的发现。他甚至还指出:“构图决不只是动作的注解。它本身就是动作。”这同样是英明的。但是,他依然将这些发现统称为“动作”,只不过在“动作”前面加上了“电影”两个字用以区别戏剧的“动作”概念。他定义说:“电影动作就是用光和影表现出来的活动。”
弗雷里赫将劳逊的发现向前推进了,他除了前边我们提到的他关于电影在表情和手势动作方面与戏剧的不同外,还指出:“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准备让演员来表演,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把这表演拍摄下来。”显然,他认为,对于戏剧说来,动作本身就是一切,而对于电影说来,在表情达意方面摄影机表现动作的方式也许更加重要。他这样要求电影的编剧:“电影剧作家在下笔以前也应该先在自己头脑中看见所设想的动作,但他在想象中仿佛预先看到了演员的表演,以后被摄影师拍成许多镜头,又被导演剪辑成统一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电影动作’这一概念之中。”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本文一开始提到过的夏衍先生对电影编剧的要求,就不难发现,弗雷里赫对电影编剧的要求扩大了很多,他将景别、摄法(是固定拍摄?还是运用推拉摇移的运动拍摄?)甚至于蒙太奇方式都交给了电影编剧。但是,他依然将所有这些都称作“银幕上的戏剧动作”或“电影动作”。
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苏联电影剧作理论家瓦依斯菲尔德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发现,他在《电影剧作家的技巧》一书中的“动作”一节中问道:“影片中的动作跟舞台剧或小说中的动作又和区别呢?”接着他就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重点放在了电影的平行蒙太奇上。他认为在舞台上是无法充分表现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的,而电影的平行蒙太奇却很好地利用它来增强了动作的表现力了戏剧性。然而,他依然认为电影的这些武器是“动作”的范畴。
其实,我本人在最初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在我1986年完成的《你了解这门艺术吗?——电影剧作常识100问》一书中,我论述了主观镜头、摄影机的运动、光影甚至音乐(例如《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等有着与动作相同的揭示人物心灵和塑造人物性格的功能。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脱离戏剧理论的框架,称这些电影独有的武器为“银幕动作”。
如果今天我再写那本小书的话,我就不会称它们为“银幕动作”。我会明确地指出,“动作”这个剧作元素只是电影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元素之一(即便在电影艺术中它依然是最最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它不象戏剧那样就是全部。除了动作之外,电影还有其它揭示人物心灵和性格的手段。而将这些独特的手段纳入剧作家的构思和写作应该是剧作家的责任,不能把它们推卸给导演或摄影师。
内心生活的物化
在很多时候,剧作家不能只写剧中人物的动作。比如有时即便一个人内心冲突很激烈或者他很痛苦,却被深深地掩盖着。这时,从表面上看你就无法看出他心灵中的真正情感。然而这正是一个人物最最准确真实的情感表现方式,如果你硬要演员通过形体动作来表现,比如说,让他痛苦或歇斯底里,就太令观众反感。我认为,编剧在这时还有很多比求助于人物动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人物的内心生活物化。在现代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使用“闪回”直接将人物内心转换成画面,或者运用画外音形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说给观众听。当然,这些手法用得巧妙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的。但必须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人的内心生活是复杂的、混乱的、片段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如果表现得太客观、太有逻辑、太冷静、太直白就会变成一种简单的图解,令人生厌。例如:《阿Q正传》中出现了阿Q的梦境,就有图解的意味。相比起来,法国电影《老枪》中的处理就好得多。当男主人公向德国人举起枪的那一瞬,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他与已经被德国人杀害的妻子过去生活的短暂闪回,而那些闪回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时刻,反而是他吃妻子醋的片断,这就不得不使观众发挥了自由的联想。我国影片《人鬼情》中的“戏中戏”运用得也很好。锺馗的唱段恰到好处地烘托着剧中女主角秋芸的心情。现在的编剧不是不用闪回的问题,而是滥用和乱用闪回的问题。关于如何使用时空交错式结构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电影剧作理论中一个没有足够研究的领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想将它放到以后再展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非什么时候都应该使用“闪回”,我们还有更加绝妙的方式来将人物的心灵展现给观众看。例如在《城南旧事》中有一场戏是疯子秀珍对小英子诉说自己往昔的遭遇。在原来的剧本中,这些东西就是通过“闪回”来表现的。但如果一个疯子能如此从容地、有逻辑地回忆过去,显然就有失真实。这样也无法揭示今天秀珍那种神经质的感情状态。在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是高明的,他抛开了“闪回”,却利用了从秀珍视点出发的空镜头,那镜头在神经质的画外音中轻轻地拉开,又悄然地推向空空的房屋,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情感节奏,使我们与秀珍的心灵合而为一。在这里,同时起着作用的就不仅仅是秀珍的动作和语言,而是摄影机运动的节奏。这样的处理本来就应该是编剧的责任,可惜的是现在由导演来完成了。
在很多的时候某个物件道具也会成为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对象化途径。在前边,我们举过的普多夫金《母亲》中那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那一刻,母亲的心情正是通过悬壶洗手器中慢慢滴落的水滴表现出来的。水滴的节奏与人物心灵的感情节奏形成了一种模拟的关系,就好象我们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细雨打在芭蕉或梧桐叶子上的声音节奏来表现愁绪一样。在意大利影片《我们曾如此相爱》中有个更有趣的例子:影片中三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子是很好的朋友,二战后,女青年与三个男青年中最富有的一个恋爱,却最终被他抛弃。当她与另外两个同样爱着她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却为了她而争吵起来。这时,我们看到这个女青年的动作和表情似乎并没有过多的痛苦,她甚至蛮有兴致地走进了街边的自动照相亭照相去了。但当那两个青年人最终到照相亭找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不在。就当二人也要离开的时候,自动照相机发出了“喀、喀”的声音,一联四张照片从机器里边逐一地被“吐”了出来,上面都是那个女孩儿:第一张是她不太痛苦的脸,甚至还挂着笑容;第二张上的她就出现了愁容;第三张已经是痛苦的表情了;而第四张竟是她捂住脸痛哭的照片……在这里,编剧巧妙地利用了自动照相机这一道具,将人物隐藏得很深的痛苦内心揭示给我们,竟然比直接看到她哭的动作更加令人心碎!
如果一个编剧有这样的主动性,他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道具是能用来揭示人物心灵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剧作意识,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比如,我的一个学生曾经作过一个构思:一个小镇里生活的男孩,他的父亲是个粗暴的酒鬼,经常殴打他、他的妈妈和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但他太弱小了,却不可能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只能在内心里对父亲咬牙切齿。他每天躲出家门,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混在游戏厅里借打游戏来消磨时光……总之,故事很一般,因为当一个孩子只在心里冲突着的时候,我们观众是无法感觉到的。如果硬用表情或动作或台词表现出来,那就太直白了。后来,我们想到了他每天玩儿的那些个游戏机是个很好到道具,因为那个小男孩只有在打游戏机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强者。这时屏幕的光线照射在他仇恨的、被父亲打出青伤的脸上,不安地闪动着各种色彩。在屏幕里,他操纵着的武侠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击倒,人物那些庞然大物在倒下去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叫声。观众很容易就感觉出他实际上在向着自己仇恨的父亲使出拳脚,这便是他心灵的隐秘。我们找到了将它外现的物化方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剧本中创造出感情的节奏
事实上,对于一个编剧说来,讲好一个故事固然难,用一种富有节奏感和旋律感的语气来讲故事就更难。我的一位学生问我:“老师,电影剧本是不是只要实打实地写出看到的和听到的就行了?”我告诉他:“是的。但那只是初级的认识。因为在一开始你必须改变文学思维的习惯,学会用画面和动作讲故事。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电影剧作的灵魂是虚的,那是一曲统一的但又分成乐章的旋律,它有着动人心魄的节奏。”法国国立声画学院的院长卡里埃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铁皮鼓》、《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等等都是世界影坛上的精品。在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在饭桌上问我:“在你教学生写作剧本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节奏。”他听后大叫:“我们是一样的。”确实,让学生理解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直到现在我国几乎大多数的编剧们依然只会忙着讲故事情节,而在他们讲述情节的时候依靠的依然只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就象德国电影心理学家于果.明斯特伯格指出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还是片面和狭窄的。我们仅仅探讨了电影演员及其表达情感的手段,而且我们的研究自然只限于对其身体反应的分析。但是尽管我们周围的人除了体态表达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手段来表达?约旱母星楹颓樾鳎缬熬缱髡呖隙ú挥κ艿秸庑┫拗频氖康摹!彼髡啪缱髡哂Ω醚罢乙恢纸谛那楦小胺涞缴硖逡酝狻薄ⅰ吧⒎⒌街芪Щ肪持小钡姆绞健@澄?慕西纳克也说:“很少有人懂得赋予一部影片以节奏和赋予画面以节奏有着相等的重要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写作剧本时,就试着把这种节奏安排进某些数学的比例关系中,即赋予某种节拍。”
伯格曼所拍摄的几乎所有影片的剧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显然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编剧。当我最初看到伯格曼的电影剧本时,心中很是诧异。因为在他的剧本中经常会写下一些无法变成视听形象的文字,例如:
“夜幕降临,暑热稍稍减退。黎明的时候,一阵热浪掠过了灰暗的海面。
……(略)
骑士回到沙滩,跪下来。他闭上眼睛,紧锁双眉,开始早祷。他紧握双手,嘴唇无声地念着祷文。他神情由于而悲痛。他睁开眼睛直视着东升的旭日,它象鼓胀的、将死的鱼从晨雾弥漫的海面上一跃而起。天空灰暗,沉滞不动;象一座坟墓的穹顶。一片乌云上方隐约可见一只海鸥,张着一动不动的翅膀,在空中飘翔。它发出古怪的、觳觫不安的鸣声。”
——《第七封印》
您着觉得奇怪吗?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导演,难道他不知道在他写下的第一句话里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我们如何从夜幕降临一直拍摄到黎明?更何况我们也无法为“暑热减退”和“热浪掠过”造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偶然,但当我读了他很多剧本(象《野草莓》)以后却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我终于知道了对于他说来,一个剧本真正应该记录的并不是那些看得到的和听得到的,而是一种能够形成情感传递的节奏。他是在演奏情感的音乐!
剧作家应该象贝多芬一样为他的作品付出节奏方面创造性的劳动,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的影片,它的剧作正是节奏的典范。下面是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创作的剧本《裸岛》的开场段落,我们立刻能读出它多特有的节奏感:
“2、黎明
海还在沉睡。
人也在沉睡。
晨雾中传来橹声。
一只小舢板靠近岸边。
船上有一对贫苦的农民夫妇,那是千太和阿丰。
……
3、大岛上的小河
晨雾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两人加快步子走近河边,开始往木桶里打水。
在默默打水的两人的头上,冰山一样陡峭的梯田的山,仿佛要刺透黎明的天空一样,高耸入云。
村里已经有人起来干活了。
打水的夫妇,朝着田间小道的人,恭敬地行礼,又继续打水。
打满了水,两人掮着压弯了的扁担,又急忙顺着来的路往回走。
4、岸边
两人气喘吁吁地走来,把装了水的桶挑到船上。
他们小心谨慎地搬运水桶,那水好象宝贝一样贵重。千太把住橹,阿丰解开系在岸边的绳子,伸手推开岸边的岩石。
缓缓漾开的涟漪。
鱼从仍然沉睡的海里,阵阵跃出水面。
5、大海
蔚蓝的大海,轻波缓浪。
岛屿还在晨雾之中,但东方已经亮了。
缓慢而单调地摇着橹的千太粗壮的手臂。
阿丰解下掖在腰上的毛巾擦汗。
小舢板的前方,有个手掌大小的岛,隐隐约约显现在眼前。
……”
他的剧本突出的个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因为那行为只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一对夫妇在黎明十分划着小舢板到一个大岛上去打水。”他在这里分明是在演奏第一乐章的主旋:轻柔、平和、欢快、明朗……所有视听元素在这里结构成为有机的节奏。在后面,整个节奏发生了变化:
“20、烈日当空
万里无云。
灼热的太阳当头。
21、海滩上
缓缓三轻波,反复进退。
静得使人昏昏欲睡。
清澈的波浪冲到沙滩上,又慢慢地退下去,小松球被晃荡得仿佛要睡着了。
22、梯田
憋住气使足劲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阿丰。
23、干旱的大地
千太小心翼翼地浇水。
24、海滩上的松球
松球仍然好象陷入沉睡之中,单调地随着波浪漂来漂去。”
剧作家范文篇3
剧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参加到电影剧本创作的队伍中来的人都会问到的,可是人们的回答却很不一样。很久以来就流行着一种观点,电影编剧的责任应该就是创作出故事情节,运用人物动作和对话来塑造出丰满立体的性格,至于蒙太奇、拍摄方法、用什么景别来表现、声音和画面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方面的事情就交给导演来处理吧!表面上看,这还真有点分工合作的道理,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所谓的“道理”阻碍了电影编剧整体水平的发展。
电影动作的意义
确实,电影剧作家应该有责任讲好故事并运用结构技巧铺排好情节,他们更应该把塑造出性格扎实可信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最最重要的责任。但是,剧作家用什么来塑造人物呢?传统的说法喜欢笼而统之道:“动作。”也许,这在过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定律,然而我们今天却不能不重新考虑它的真理性。
动作,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戏剧。对“动作”这个概念作出最全面的也是最具影响的论述者应该是贝克,他对动作所总结出的理论成为沿用至今的定理。他甚至认为动作比其它剧作元素都要重要。他说:“‘情感交流’是一切好剧本的公式。所谓情感交流,是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把感情先流到观众身上,那么,这就非靠动作不可,因为动作是激动观众感情最迅速的手段。”是他首次明确地将动作分为内部动作(也作“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两大方面的。他的失误在于没能正确地说明内心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物能够不用外部动作就可以将内心动作表现出来,例如他在舞台上一动也不动。后来者多次指出他的这一失误,因为内心动作是外部动作产生的依据,外部动作是内部动作的反映,内部动作只有通过外部动作才能得到揭示,而他所谓的“一动也不动”,其实就是人物在那一时刻的外部动作。那时,人们还把人物的形体动作(其中包括表情动作)看作是外部动作的全部内容,但到后来,人们开始觉得语言动作(对话)也是外部动作的一部分。因为在戏剧舞台上,人物可以发挥的形体动作(尤其是表情动作)实在是有限,而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更主要地依靠着对话。所以,戏剧对于对话的写作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动作性。对话只是内心动作的外部表现,并非内心动作的全部的、直接的反映,对话的“潜台词”就产生于对话与内心动作之间的差异。
总之,在戏剧的剧作理论中,“动作”这一概念便是人物塑造的全部武器。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向戏剧学会叙事的。戏剧的叙事经验曾经就是电影编剧的罗盘经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有着同样的定律,那就是动作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唯一法宝。除了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你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动作。所以我们至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导演将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全部努力都用在了演员身上,为了说明那个剧中人物此时是痛苦的,便让演员作出嚎啕大哭之类的痛苦状来。但也有很多高明的导演越来越发现电影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有着很多与戏剧不同的办法。比如,在最初,人们发现的(这也是最最容易发现的)是就人物动作中的形体动作而言,在戏剧舞台上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细微的表情和手势动作却在电影里成为揭示人物心理更重要的武器。例如弗雷里赫就曾经指出:“摄影机善于摄录极其细小的动作、极其微妙的细节、难以捉摸的语调、眼睛的闪动、睫毛的颤动;善于选取出最最重要的东西,用一个单独的场面把它突出出来——摄影机的这些能力决定了银幕上的戏剧动作的性质。”
很快,人们就发现电影与戏剧在揭示人物内心方面的差异还不仅仅是动作幅度上的问题,例如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当尼洛夫娜坐在丈夫的棺材前陷入令人窒息的悲哀的时候,导演并没有指示演员嚎啕大哭,甚至他不让演员流一滴泪,只是木然地静坐在那里。当然,前面我们说过,静静地坐着也是人物的外部动作,但仅仅靠这样的动作就很难揭示母亲此时的内心痛苦了。这时,导演聪明地在母亲的脸的镜头之后接入了一个特写镜头:水从悬壶洗手器中慢慢地滴下来,一滴又一滴。水滴的形象和节奏十分巧妙地将人物此时此刻那种绝望的、欲哭无泪的悲哀揭示了出来。现在要问:滴落的水滴是人物的动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情况纳入剧作理论呢?转电影剧作理论家们在这一方面似乎有点保守,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他们通常能够指出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的方法与戏剧的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依然不敢贸然地抛开戏剧理论已成的“动作”概念。他们依然将那些电影艺术中出现的新武器叫作“动作”,只不过有了点小小的改良。例如:劳逊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就英明地发现,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内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包括将这个动作展现给观众的方式。他以卓别林的影片《巴黎一妇人》举例说:“他(卓别林饰演的人物)的妻子因为他啫酒而离弃了他。我们看到他背对着摄影机,望着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肩膀上下抽动,好象在伤心地啜泣。之后我们却发现他正在摇动一瓶香槟酒。”在这时,揭示人物性格和引起观众笑声的不是人物的动作。如果你一开始就从正面将卓别林开香槟的动作直接表现给观众看就绝对不能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劳逊指出:“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这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应该是重要的发现。他甚至还指出:“构图决不只是动作的注解。它本身就是动作。”这同样是英明的。但是,他依然将这些发现统称为“动作”,只不过在“动作”前面加上了“电影”两个字用以区别戏剧的“动作”概念。他定义说:“电影动作就是用光和影表现出来的活动。”
弗雷里赫将劳逊的发现向前推进了,他除了前边我们提到的他关于电影在表情和手势动作方面与戏剧的不同外,还指出:“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准备让演员来表演,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把这表演拍摄下来。”显然,他认为,对于戏剧说来,动作本身就是一切,而对于电影说来,在表情达意方面摄影机表现动作的方式也许更加重要。他这样要求电影的编剧:“电影剧作家在下笔以前也应该先在自己头脑中看见所设想的动作,但他在想象中仿佛预先看到了演员的表演,以后被摄影师拍成许多镜头,又被导演剪辑成统一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电影动作’这一概念之中。”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本文一开始提到过的夏衍先生对电影编剧的要求,就不难发现,弗雷里赫对电影编剧的要求扩大了很多,他将景别、摄法(是固定拍摄?还是运用推拉摇移的运动拍摄?)甚至于蒙太奇方式都交给了电影编剧。但是,他依然将所有这些都称作“银幕上的戏剧动作”或“电影动作”。
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苏联电影剧作理论家瓦依斯菲尔德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发现,他在《电影剧作家的技巧》一书中的“动作”一节中问道:“影片中的动作跟舞台剧或小说中的动作又和区别呢?”接着他就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重点放在了电影的平行蒙太奇上。他认为在舞台上是无法充分表现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的,而电影的平行蒙太奇却很好地利用它来增强了动作的表现力了戏剧性。然而,他依然认为电影的这些武器是“动作”的范畴。
其实,我本人在最初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在我1986年完成的《你了解这门艺术吗?——电影剧作常识100问》一书中,我论述了主观镜头、摄影机的运动、光影甚至音乐(例如《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等有着与动作相同的揭示人物心灵和塑造人物性格的功能。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脱离戏剧理论的框架,称这些电影独有的武器为“银幕动作”。
如果今天我再写那本小书的话,我就不会称它们为“银幕动作”。我会明确地指出,“动作”这个剧作元素只是电影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元素之一(即便在电影艺术中它依然是最最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它不象戏剧那样就是全部。除了动作之外,电影还有其它揭示人物心灵和性格的手段。而将这些独特的手段纳入剧作家的构思和写作应该是剧作家的责任,不能把它们推卸给导演或摄影师。
内心生活的物化
在很多时候,剧作家不能只写剧中人物的动作。比如有时即便一个人内心冲突很激烈或者他很痛苦,却被深深地掩盖着。这时,从表面上看你就无法看出他心灵中的真正情感。然而这正是一个人物最最准确真实的情感表现方式,如果你硬要演员通过形体动作来表现,比如说,让他痛苦或歇斯底里,就太令观众反感。我认为,编剧在这时还有很多比求助于人物动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人物的内心生活物化。在现代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使用“闪回”直接将人物内心转换成画面,或者运用画外音形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说给观众听。当然,这些手法用得巧妙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的。但必须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人的内心生活是复杂的、混乱的、片段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如果表现得太客观、太有逻辑、太冷静、太直白就会变成一种简单的图解,令人生厌。例如:《阿Q正传》中出现了阿Q的梦境,就有图解的意味。相比起来,法国电影《老枪》中的处理就好得多。当男主人公向德国人举起枪的那一瞬,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他与已经被德国人杀害的妻子过去生活的短暂闪回,而那些闪回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时刻,反而是他吃妻子醋的片断,这就不得不使观众发挥了自由的联想。我国影片《人鬼情》中的“戏中戏”运用得也很好。锺馗的唱段恰到好处地烘托着剧中女主角秋芸的心情。现在的编剧不是不用闪回的问题,而是滥用和乱用闪回的问题。关于如何使用时空交错式结构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电影剧作理论中一个没有足够研究的领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想将它放到以后再展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非什么时候都应该使用“闪回”,我们还有更加绝妙的方式来将人物的心灵展现给观众看。例如在《城南旧事》中有一场戏是疯子秀珍对小英子诉说自己往昔的遭遇。在原来的剧本中,这些东西就是通过“闪回”来表现的。但如果一个疯子能如此从容地、有逻辑地回忆过去,显然就有失真实。这样也无法揭示今天秀珍那种神经质的感情状态。在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是高明的,他抛开了“闪回”,却利用了从秀珍视点出发的空镜头,那镜头在神经质的画外音中轻轻地拉开,又悄然地推向空空的房屋,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情感节奏,使我们与秀珍的心灵合而为一。在这里,同时起着作用的就不仅仅是秀珍的动作和语言,而是摄影机运动的节奏。这样的处理本来就应该是编剧的责任,可惜的是现在由导演来完成了。
在很多的时候某个物件道具也会成为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对象化途径。在前边,我们举过的普多夫金《母亲》中那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那一刻,母亲的心情正是通过悬壶洗手器中慢慢滴落的水滴表现出来的。水滴的节奏与人物心灵的感情节奏形成了一种模拟的关系,就好象我们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细雨打在芭蕉或梧桐叶子上的声音节奏来表现愁绪一样。在意大利影片《我们曾如此相爱》中有个更有趣的例子:影片中三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子是很好的朋友,二战后,女青年与三个男青年中最富有的一个恋爱,却最终被他抛弃。当她与另外两个同样爱着她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却为了她而争吵起来。这时,我们看到这个女青年的动作和表情似乎并没有过多的痛苦,她甚至蛮有兴致地走进了街边的自动照相亭照相去了。但当那两个青年人最终到照相亭找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不在。就当二人也要离开的时候,自动照相机发出了“喀、喀”的声音,一联四张照片从机器里边逐一地被“吐”了出来,上面都是那个女孩儿:第一张是她不太痛苦的脸,甚至还挂着笑容;第二张上的她就出现了愁容;第三张已经是痛苦的表情了;而第四张竟是她捂住脸痛哭的照片……在这里,编剧巧妙地利用了自动照相机这一道具,将人物隐藏得很深的痛苦内心揭示给我们,竟然比直接看到她哭的动作更加令人心碎!
如果一个编剧有这样的主动性,他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道具是能用来揭示人物心灵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剧作意识,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比如,我的一个学生曾经作过一个构思:一个小镇里生活的男孩,他的父亲是个粗暴的酒鬼,经常殴打他、他的妈妈和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但他太弱小了,却不可能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只能在内心里对父亲咬牙切齿。他每天躲出家门,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混在游戏厅里借打游戏来消磨时光……总之,故事很一般,因为当一个孩子只在心里冲突着的时候,我们观众是无法感觉到的。如果硬用表情或动作或台词表现出来,那就太直白了。后来,我们想到了他每天玩儿的那些个游戏机是个很好到道具,因为那个小男孩只有在打游戏机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强者。这时屏幕的光线照射在他仇恨的、被父亲打出青伤的脸上,不安地闪动着各种色彩。在屏幕里,他操纵着的武侠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击倒,人物那些庞然大物在倒下去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叫声。观众很容易就感觉出他实际上在向着自己仇恨的父亲使出拳脚,这便是他心灵的隐秘。我们找到了将它外现的物化方式。在剧本中创造出感情的节奏
事实上,对于一个编剧说来,讲好一个故事固然难,用一种富有节奏感和旋律感的语气来讲故事就更难。我的一位学生问我:“老师,电影剧本是不是只要实打实地写出看到的和听到的就行了?”我告诉他:“是的。但那只是初级的认识。因为在一开始你必须改变文学思维的习惯,学会用画面和动作讲故事。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电影剧作的灵魂是虚的,那是一曲统一的但又分成乐章的旋律,它有着动人心魄的节奏。”法国国立声画学院的院长卡里埃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铁皮鼓》、《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等等都是世界影坛上的精品。在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在饭桌上问我:“在你教学生写作剧本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节奏。”他听后大叫:“我们是一样的。”确实,让学生理解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直到现在我国几乎大多数的编剧们依然只会忙着讲故事情节,而在他们讲述情节的时候依靠的依然只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就象德国电影心理学家于果.明斯特伯格指出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还是片面和狭窄的。我们仅仅探讨了电影演员及其表达情感的手段,而且我们的研究自然只限于对其身体反应的分析。但是尽管我们周围的人除了体态表达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情绪,电影剧作者肯定不应受到这些限制的束缚的。”他主张剧作者应该寻找一种将内心情感“辐射到身体以外”、“散发到周围环境中”的方式。莱翁.慕西纳克也说:“很少有人懂得赋予一部影片以节奏和赋予画面以节奏有着相等的重要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写作剧本时,就试着把这种节奏安排进某些数学的比例关系中,即赋予某种节拍。”
伯格曼所拍摄的几乎所有影片的剧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显然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编剧。当我最初看到伯格曼的电影剧本时,心中很是诧异。因为在他的剧本中经常会写下一些无法变成视听形象的文字,例如:
“夜幕降临,暑热稍稍减退。黎明的时候,一阵热浪掠过了灰暗的海面。
……(略)
骑士回到沙滩,跪下来。他闭上眼睛,紧锁双眉,开始早祷。他紧握双手,嘴唇无声地念着祷文。他神情由于而悲痛。他睁开眼睛直视着东升的旭日,它象鼓胀的、将死的鱼从晨雾弥漫的海面上一跃而起。天空灰暗,沉滞不动;象一座坟墓的穹顶。一片乌云上方隐约可见一只海鸥,张着一动不动的翅膀,在空中飘翔。它发出古怪的、觳觫不安的鸣声。”
——《第七封印》
您着觉得奇怪吗?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导演,难道他不知道在他写下的第一句话里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我们如何从夜幕降临一直拍摄到黎明?更何况我们也无法为“暑热减退”和“热浪掠过”造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偶然,但当我读了他很多剧本(象《野草莓》)以后却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我终于知道了对于他说来,一个剧本真正应该记录的并不是那些看得到的和听得到的,而是一种能够形成情感传递的节奏。他是在演奏情感的音乐!
剧作家应该象贝多芬一样为他的作品付出节奏方面创造性的劳动,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的影片,它的剧作正是节奏的典范。下面是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创作的剧本《裸岛》的开场段落,我们立刻能读出它多特有的节奏感:
“2、黎明
海还在沉睡。
人也在沉睡。
晨雾中传来橹声。
一只小舢板靠近岸边。
船上有一对贫苦的农民夫妇,那是千太和阿丰。
……
3、大岛上的小河
晨雾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两人加快步子走近河边,开始往木桶里打水。
在默默打水的两人的头上,冰山一样陡峭的梯田的山,仿佛要刺透黎明的天空一样,高耸入云。
村里已经有人起来干活了。
打水的夫妇,朝着田间小道的人,恭敬地行礼,又继续打水。
打满了水,两人掮着压弯了的扁担,又急忙顺着来的路往回走。4、岸边
两人气喘吁吁地走来,把装了水的桶挑到船上。
他们小心谨慎地搬运水桶,那水好象宝贝一样贵重。千太把住橹,阿丰解开系在岸边的绳子,伸手推开岸边的岩石。
缓缓漾开的涟漪。
鱼从仍然沉睡的海里,阵阵跃出水面。
5、大海
蔚蓝的大海,轻波缓浪。
岛屿还在晨雾之中,但东方已经亮了。
缓慢而单调地摇着橹的千太粗壮的手臂。
阿丰解下掖在腰上的毛巾擦汗。
小舢板的前方,有个手掌大小的岛,隐隐约约显现在眼前。
……”
他的剧本突出的个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因为那行为只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一对夫妇在黎明十分划着小舢板到一个大岛上去打水。”他在这里分明是在演奏第一乐章的主旋:轻柔、平和、欢快、明朗……所有视听元素在这里结构成为有机的节奏。在后面,整个节奏发生了变化:
“20、烈日当空
万里无云。
灼热的太阳当头。
21、海滩上
缓缓三轻波,反复进退。
静得使人昏昏欲睡。
清澈的波浪冲到沙滩上,又慢慢地退下去,小松球被晃荡得仿佛要睡着了。
22、梯田
憋住气使足劲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阿丰。
23、干旱的大地
千太小心翼翼地浇水。
24、海滩上的松球
松球仍然好象陷入沉睡之中,单调地随着波浪漂来漂去。”
剧作家范文篇4
剧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参加到电影剧本创作的队伍中来的人都会问到的,可是人们的回答却很不一样。很久以来就流行着一种观点,电影编剧的责任应该就是创作出故事情节,运用人物动作和对话来塑造出丰满立体的性格,至于蒙太奇、拍摄方法、用什么景别来表现、声音和画面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方面的事情就交给导演来处理吧!表面上看,这还真有点分工合作的道理,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所谓的“道理”阻碍了电影编剧整体水平的发展。
电影动作的意义
确实,电影剧作家应该有责任讲好故事并运用结构技巧铺排好情节,他们更应该把塑造出性格扎实可信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最最重要的责任。但是,剧作家用什么来塑造人物呢?传统的说法喜欢笼而统之道:“动作。”也许,这在过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定律,然而我们今天却不能不重新考虑它的真理性。
动作,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戏剧。对“动作”这个概念作出最全面的也是最具影响的论述者应该是贝克,他对动作所总结出的理论成为沿用至今的定理。他甚至认为动作比其它剧作元素都要重要。他说:“‘情感交流’是一切好剧本的公式。所谓情感交流,是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把感情先流到观众身上,那么,这就非靠动作不可,因为动作是激动观众感情最迅速的手段。”是他首次明确地将动作分为内部动作(也作“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两大方面的。他的失误在于没能正确地说明内心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物能够不用外部动作就可以将内心动作表现出来,例如他在舞台上一动也不动。后来者多次指出他的这一失误,因为内心动作是外部动作产生的依据,外部动作是内部动作的反映,内部动作只有通过外部动作才能得到揭示,而他所谓的“一动也不动”,其实就是人物在那一时刻的外部动作。那时,人们还把人物的形体动作(其中包括表情动作)看作是外部动作的全部内容,但到后来,人们开始觉得语言动作(对话)也是外部动作的一部分。因为在戏剧舞台上,人物可以发挥的形体动作(尤其是表情动作)实在是有限,而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更主要地依靠着对话。所以,戏剧对于对话的写作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动作性。对话只是内心动作的外部表现,并非内心动作的全部的、直接的反映,对话的“潜台词”就产生于对话与内心动作之间的差异。
总之,在戏剧的剧作理论中,“动作”这一概念便是人物塑造的全部武器。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向戏剧学会叙事的。戏剧的叙事经验曾经就是电影编剧的罗盘经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有着同样的定律,那就是动作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唯一法宝。除了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你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动作。所以我们至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导演将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全部努力都用在了演员身上,为了说明那个剧中人物此时是痛苦的,便让演员作出嚎啕大哭之类的痛苦状来。但也有很多高明的导演越来越发现电影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有着很多与戏剧不同的办法。比如,在最初,人们发现的(这也是最最容易发现的)是就人物动作中的形体动作而言,在戏剧舞台上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细微的表情和手势动作却在电影里成为揭示人物心理更重要的武器。例如弗雷里赫就曾经指出:“摄影机善于摄录极其细小的动作、极其微妙的细节、难以捉摸的语调、眼睛的闪动、睫毛的颤动;善于选取出最最重要的东西,用一个单独的场面把它突出出来——摄影机的这些能力决定了银幕上的戏剧动作的性质。”
很快,人们就发现电影与戏剧在揭示人物内心方面的差异还不仅仅是动作幅度上的问题,例如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当尼洛夫娜坐在丈夫的棺材前陷入令人窒息的悲哀的时候,导演并没有指示演员嚎啕大哭,甚至他不让演员流一滴泪,只是木然地静坐在那里。当然,前面我们说过,静静地坐着也是人物的外部动作,但仅仅靠这样的动作就很难揭示母亲此时的内心痛苦了。这时,导演聪明地在母亲的脸的镜头之后接入了一个特写镜头:水从悬壶洗手器中慢慢地滴下来,一滴又一滴。水滴的形象和节奏十分巧妙地将人物此时此刻那种绝望的、欲哭无泪的悲哀揭示了出来。现在要问:滴落的水滴是人物的动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情况纳入剧作理论呢?
电影剧作理论家们在这一方面似乎有点保守,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他们通常能够指出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的方法与戏剧的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依然不敢贸然地抛开戏剧理论已成的“动作”概念。他们依然将那些电影艺术中出现的新武器叫作“动作”,只不过有了点小小的改良。例如:劳逊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就英明地发现,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内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包括将这个动作展现给观众的方式。他以卓别林的影片《巴黎一妇人》举例说:“他(卓别林饰演的人物)的妻子因为他啫酒而离弃了他。我们看到他背对着摄影机,望着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肩膀上下抽动,好象在伤心地啜泣。之后我们却发现他正在摇动一瓶香槟酒。”在这时,揭示人物性格和引起观众笑声的不是人物的动作。如果你一开始就从正面将卓别林开香槟的动作直接表现给观众看就绝对不能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劳逊指出:“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这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应该是重要的发现。他甚至还指出:“构图决不只是动作的注解。它本身就是动作。”这同样是英明的。但是,他依然将这些发现统称为“动作”,只不过在“动作”前面加上了“电影”两个字用以区别戏剧的“动作”概念。他定义说:“电影动作就是用光和影表现出来的活动。”
弗雷里赫将劳逊的发现向前推进了,他除了前边我们提到的他关于电影在表情和手势动作方面与戏剧的不同外,还指出:“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准备让演员来表演,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把这表演拍摄下来。”显然,他认为,对于戏剧说来,动作本身就是一切,而对于电影说来,在表情达意方面摄影机表现动作的方式也许更加重要。他这样要求电影的编剧:“电影剧作家在下笔以前也应该先在自己头脑中看见所设想的动作,但他在想象中仿佛预先看到了演员的表演,以后被摄影师拍成许多镜
头,又被导演剪辑成统一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电影动作’这一概念之中。”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本文一开始提到过的夏衍先生对电影编剧的要求,就不难发现,弗雷里赫对电影编剧的要求扩大了很多,他将景别、摄法(是固定拍摄?还是运用推拉摇移的运动拍摄?)甚至于蒙太奇方式都交给了电影编剧。但是,他依然将所有这些都称作“银幕上的戏剧动作”或“电影动作”。
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苏联电影剧作理论家瓦依斯菲尔德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发现,他在《电影剧作家的技巧》一书中的“动作”一节中问道:“影片中的动作跟舞台剧或小说中的动作又和区别呢?”接着他就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重点放在了电影的平行蒙太奇上。他认为在舞台上是无法充分表现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的,而电影的平行蒙太奇却很好地利用它来增强了动作的表现力了戏剧性。然而,他依然认为电影的这些武器是“动作”的范畴。
其实,我本人在最初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在我1986年完成的《你了解这门艺术吗?——电影剧作常识100问》一书中,我论述了主观镜头、摄影机的运动、光影甚至音乐(例如《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等有着与动作相同的揭示人物心灵和塑造人物性格的功能。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脱离戏剧理论的框架,称这些电影独有的武器为“银幕动作”。
如果今天我再写那本小书的话,我就不会称它们为“银幕动作”。我会明确地指出,“动作”这个剧作元素只是电影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元素之一(即便在电影艺术中它依然是最最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它不象戏剧那样就是全部。除了动作之外,电影还有其它揭示人物心灵和性格的手段。而将这些独特的手段纳入剧作家的构思和写作应该是剧作家的责任,不能把它们推卸给导演或摄影师。
内心生活的物化
在很多时候,剧作家不能只写剧中人物的动作。比如有时即便一个人内心冲突很激烈或者他很痛苦,却被深深地掩盖着。这时,从表面上看你就无法看出他心灵中的真正情感。然而这正是一个人物最最准确真实的情感表现方式,如果你硬要演员通过形体动作来表现,比如说,让他痛苦或歇斯底里,就太令观众反感。我认为,编剧在这时还有很多比求助于人物动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人物的内心生活物化。在现代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使用“闪回”直接将人物内心转换成画面,或者运用画外音形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说给观众听。当然,这些手法用得巧妙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的。但必须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人的内心生活是复杂的、混乱的、片段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如果表现得太客观、太有逻辑、太冷静、太直白就会变成一种简单的图解,令人生厌。例如:《阿Q正传》中出现了阿Q的梦境,就有图解的意味。相比起来,法国电影《老枪》中的处理就好得多。当男主人公向德国人举起枪的那一瞬,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他与已经被德国人杀害的妻子过去生活的短暂闪回,而那些闪回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时刻,反而是他吃妻子醋的片断,这就不得不使观众发挥了自由的联想。我国影片《人鬼情》中的“戏中戏”运用得也很好。锺馗的唱段恰到好处地烘托着剧中女主角秋芸的心情。现在的编剧不是不用闪回的问题,而是滥用和乱用闪回的问题。关于如何使用时空交错式结构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电影剧作理论中一个没有足够研究的领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想将它放到以后再展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非什么时候都应该使用“闪回”,我们还有更加绝妙的方式来将人物的心灵展现给观众看。例如在《城南旧事》中有一场戏是疯子秀珍对小英子诉说自己往昔的遭遇。在原来的剧本中,这些东西就是通过“闪回”来表现的。但如果一个疯子能如此从容地、有逻辑地回忆过去,显然就有失真实。这样也无法揭示今天秀珍那种神经质的感情状态。在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是高明的,他抛开了“闪回”,却利用了从秀珍视点出发的空镜头,那镜头在神经质的画外音中轻轻地拉开,又悄然地推向空空的房屋,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情感节奏,使我们与秀珍的心灵合而为一。在这里,同时起着作用的就不仅仅是秀珍的动作和语言,而是摄影机运动的节奏。这样的处理本来就应该是编剧的责任,可惜的是现在由导演来完成了。
在很多的时候某个物件道具也会成为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对象化途径。在前边,我们举过的普多夫金《母亲》中那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那一刻,母亲的心情正是通过悬壶洗手器中慢慢滴落的水滴表现出来的。水滴的节奏与人物心灵的感情节奏形成了一种模拟的关系,就好象我们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细雨打在芭蕉或梧桐叶子上的声音节奏来表现愁绪一样。在意大利影片《我们曾如此相爱》中有个更有趣的例子:影片中三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子是很好的朋友,二战后,女青年与三个男青年中最富有的一个恋爱,却最终被他抛弃。当她与另外两个同样爱着她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却为了她而争吵起来。这时,我们看到这个女青年的动作和表情似乎并没有过多的痛苦,她甚至蛮有兴致地走进了街边的自动照相亭照相去了。但当那两个青年人最终到照相亭找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不在。就当二人也要离开的时候,自动照相机发出了“喀、喀”的声音,一联四张照片从机器里边逐一地被“吐”了出来,上面都是那个女孩儿:第一张是她不太痛苦的脸,甚至还挂着笑容;第二张上的她就出现了愁容;第三张已经是痛苦的表情了;而第四张竟是她捂住脸痛哭的照片……在这里,编剧巧妙地利用了自动照相机这一道具,将人物隐藏得很深的痛苦内心揭示给我们,竟然比直接看到她哭的动作更加令人心碎!
如果一个编剧有这样的主动性,他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道具是能用来揭示人物心灵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剧作意识,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比如,我的一个学生曾经作过一个构思:一个小镇里生活的男孩,他的父亲是个粗暴的酒鬼,经常殴打他、他的妈妈和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但他太弱小了,却不可能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只能在内心里对父亲咬牙切齿。他每天躲出家门,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混在游戏厅里借打游戏来消磨时光……总之,故事很一般,因为当一个孩子只在心里冲突着的时候,我们观众是无法感觉到的。如果硬用表情或动作或台词表现出来,那就太直白了。后来,我们想到了他每天玩儿的那些个游戏机是个很好到道具,因为那个小男孩只有在打游戏机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强者。这时屏幕的光线照射在他仇恨的、被父亲打出青伤的脸上,不安地闪动着各种色彩。在屏幕里,他操纵着的武侠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击倒,人物那些庞然大物在倒下去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叫声。观众很容易就感觉出他实际上在向着自己仇恨的父亲使出拳脚,这便是他心灵的隐秘。我们找到了将它外现的物化方式。
在剧本中创造出感情的节奏
事实上,对于一个编剧说来,讲好一个故事固然难,用一种富有节奏感和旋律感的语气来讲故事就更难。我的一位学生问我:“老师,电影剧本是不是只要实打实地写出看到的和听到的就行了?”我告诉他:“是的。但那只是初级的认识。因为在一开始你必须改变文学思维的习惯,学会用画面和动作讲故事。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电影剧作的灵魂是虚的,那是一曲统一的但又分成乐章
的旋律,它有着动人心魄的节奏。”法国国立声画学院的院长卡里埃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铁皮鼓》、《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等等都是世界影坛上的精品。在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在饭桌上问我:“在你教学生写作剧本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节奏。”他听后大叫:“我们是一样的。”确实,让学生理解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直到现在我国几乎大多数的编剧们依然只会忙着讲故事情节,而在他们讲述情节的时候依靠的依然只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就象德国电影心理学家于果.明斯特伯格指出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还是片面和狭窄的。我们仅仅探讨了电影演员及其表达情感的手段,而且我们的研究自然只限于对其身体反应的分析。但是尽管我们周围的人除了体态表达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手段来表达?约旱母星楹颓樾鳎缬熬缱髡呖隙ú挥κ艿秸庑┫拗频氖康摹!彼髡啪缱髡哂Ω醚罢乙恢纸谛那楦小胺涞缴硖逡酝狻薄ⅰ吧⒎⒌街芪Щ肪持小钡姆绞健@澄?慕西纳克也说:“很少有人懂得赋予一部影片以节奏和赋予画面以节奏有着相等的重要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写作剧本时,就试着把这种节奏安排进某些数学的比例关系中,即赋予某种节拍。”
伯格曼所拍摄的几乎所有影片的剧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显然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编剧。当我最初看到伯格曼的电影剧本时,心中很是诧异。因为在他的剧本中经常会写下一些无法变成视听形象的文字,例如:
“夜幕降临,暑热稍稍减退。黎明的时候,一阵热浪掠过了灰暗的海面。
……(略)
骑士回到沙滩,跪下来。他闭上眼睛,紧锁双眉,开始早祷。他紧握双手,嘴唇无声地念着祷文。他神情由于而悲痛。他睁开眼睛直视着东升的旭日,它象鼓胀的、将死的鱼从晨雾弥漫的海面上一跃而起。天空灰暗,沉滞不动;象一座坟墓的穹顶。一片乌云上方隐约可见一只海鸥,张着一动不动的翅膀,在空中飘翔。它发出古怪的、觳觫不安的鸣声。”
——《第七封印》
您着觉得奇怪吗?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导演,难道他不知道在他写下的第一句话里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我们如何从夜幕降临一直拍摄到黎明?更何况我们也无法为“暑热减退”和“热浪掠过”造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偶然,但当我读了他很多剧本(象《野草莓》)以后却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我终于知道了对于他说来,一个剧本真正应该记录的并不是那些看得到的和听得到的,而是一种能够形成情感传递的节奏。他是在演奏情感的音乐!
剧作家应该象贝多芬一样为他的作品付出节奏方面创造性的劳动,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的影片,它的剧作正是节奏的典范。下面是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创作的剧本《裸岛》的开场段落,我们立刻能读出它多特有的节奏感:
“2、黎明
海还在沉睡。
人也在沉睡。
晨雾中传来橹声。
一只小舢板靠近岸边。
船上有一对贫苦的农民夫妇,那是千太和阿丰。
……
3、大岛上的小河
晨雾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两人加快步子走近河边,开始往木桶里打水。
在默默打水的两人的头上,冰山一样陡峭的梯田的山,仿佛要刺透黎明的天空一样,高耸入云。
村里已经有人起来干活了。
打水的夫妇,朝着田间小道的人,恭敬地行礼,又继续打水。
打满了水,两人掮着压弯了的扁担,又急忙顺着来的路往回走。
4、岸边
两人气喘吁吁地走来,把装了水的桶挑到船上。
他们小心谨慎地搬运水桶,那水好象宝贝一样贵重。千太把住橹,阿丰解开系在岸边的绳子,伸手推开岸边的岩石。
缓缓漾开的涟漪。
鱼从仍然沉睡的海里,阵阵跃出水面。
5、大海
蔚蓝的大海,轻波缓浪。
岛屿还在晨雾之中,但东方已经亮了。
缓慢而单调地摇着橹的千太粗壮的手臂。
阿丰解下掖在腰上的毛巾擦汗。
小舢板的前方,有个手掌大小的岛,隐隐约约显现在眼前。
……”
他的剧本突出的个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因为那行为只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一对夫妇在黎明十分划着小舢板到一个大岛上去打水。”他在这里分明是在演奏第一乐章的主旋:轻柔、平和、欢快、明朗……所有视听元素在这里结构成为有机的节奏。在后面,整个节奏发生了变化:
“20、烈日当空
万里无云。
灼热的太阳当头。
21、海滩上
缓缓三轻波,反复进退。
静得使人昏昏欲睡。
清澈的波浪冲到沙滩上,又慢慢地退下去,小松球被晃荡得仿佛要睡着了。
22、梯田
憋住气使足劲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阿丰。
23、干旱的大地
千太小心翼翼地浇水。
24、海滩上的松球
松球仍然好象陷入沉睡之中,单调地随着波浪漂来漂去。”
剧作家范文篇5
剧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参加到电影剧本创作的队伍中来的人都会问到的,可是人们的回答却很不一样。很久以来就流行着一种观点,电影编剧的责任应该就是创作出故事情节,运用人物动作和对话来塑造出丰满立体的性格,至于蒙太奇、拍摄方法、用什么景别来表现、声音和画面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方面的事情就交给导演来处理吧!表面上看,这还真有点分工合作的道理,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所谓的“道理”阻碍了电影编剧整体水平的发展。
电影动作的意义
确实,电影剧作家应该有责任讲好故事并运用结构技巧铺排好情节,他们更应该把塑造出性格扎实可信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最最重要的责任。但是,剧作家用什么来塑造人物呢?传统的说法喜欢笼而统之道:“动作。”也许,这在过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定律,然而我们今天却不能不重新考虑它的真理性。
动作,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戏剧。对“动作”这个概念作出最全面的也是最具影响的论述者应该是贝克,他对动作所总结出的理论成为沿用至今的定理。他甚至认为动作比其它剧作元素都要重要。他说:“‘情感交流’是一切好剧本的公式。所谓情感交流,是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把感情先流到观众身上,那么,这就非靠动作不可,因为动作是激动观众感情最迅速的手段。”是他首次明确地将动作分为内部动作(也作“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两大方面的。他的失误在于没能正确地说明内心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物能够不用外部动作就可以将内心动作表现出来,例如他在舞台上一动也不动。后来者多次指出他的这一失误,因为内心动作是外部动作产生的依据,外部动作是内部动作的反映,内部动作只有通过外部动作才能得到揭示,而他所谓的“一动也不动”,其实就是人物在那一时刻的外部动作。那时,人们还把人物的形体动作(其中包括表情动作)看作是外部动作的全部内容,但到后来,人们开始觉得语言动作(对话)也是外部动作的一部分。因为在戏剧舞台上,人物可以发挥的形体动作(尤其是表情动作)实在是有限,而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更主要地依靠着对话。所以,戏剧对于对话的写作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动作性。对话只是内心动作的外部表现,并非内心动作的全部的、直接的反映,对话的“潜台词”就产生于对话与内心动作之间的差异。
总之,在戏剧的剧作理论中,“动作”这一概念便是人物塑造的全部武器。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向戏剧学会叙事的。戏剧的叙事经验曾经就是电影编剧的罗盘经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有着同样的定律,那就是动作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唯一法宝。除了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你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动作。所以我们至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导演将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全部努力都用在了演员身上,为了说明那个剧中人物此时是痛苦的,便让演员作出嚎啕大哭之类的痛苦状来。但也有很多高明的导演越来越发现电影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有着很多与戏剧不同的办法。比如,在最初,人们发现的(这也是最最容易发现的)是就人物动作中的形体动作而言,在戏剧舞台上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细微的表情和手势动作却在电影里成为揭示人物心理更重要的武器。例如弗雷里赫就曾经指出:“摄影机善于摄录极其细小的动作、极其微妙的细节、难以捉摸的语调、眼睛的闪动、睫毛的颤动;善于选取出最最重要的东西,用一个单独的场面把它突出出来——摄影机的这些能力决定了银幕上的戏剧动作的性质。”
很快,人们就发现电影与戏剧在揭示人物内心方面的差异还不仅仅是动作幅度上的问题,例如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当尼洛夫娜坐在丈夫的棺材前陷入令人窒息的悲哀的时候,导演并没有指示演员嚎啕大哭,甚至他不让演员流一滴泪,只是木然地静坐在那里。当然,前面我们说过,静静地坐着也是人物的外部动作,但仅仅靠这样的动作就很难揭示母亲此时的内心痛苦了。这时,导演聪明地在母亲的脸的镜头之后接入了一个特写镜头:水从悬壶洗手器中慢慢地滴下来,一滴又一滴。水滴的形象和节奏十分巧妙地将人物此时此刻那种绝望的、欲哭无泪的悲哀揭示了出来。现在要问:滴落的水滴是人物的动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情况纳入剧作理论呢?
电影剧作理论家们在这一方面似乎有点保守,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他们通常能够指出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的方法与戏剧的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依然不敢贸然地抛开戏剧理论已成的“动作”概念。他们依然将那些电影艺术中出现的新武器叫作“动作”,只不过有了点小小的改良。例如:劳逊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就英明地发现,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内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包括将这个动作展现给观众的方式。他以卓别林的影片《巴黎一妇人》举例说:“他(卓别林饰演的人物)的妻子因为他啫酒而离弃了他。我们看到他背对着摄影机,望着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肩膀上下抽动,好象在伤心地啜泣。之后我们却发现他正在摇动一瓶香槟酒。”在这时,揭示人物性格和引起观众笑声的不是人物的动作。如果你一开始就从正面将卓别林开香槟的动作直接表现给观众看就绝对不能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劳逊指出:“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这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应该是重要的发现。他甚至还指出:“构图决不只是动作的注解。它本身就是动作。”这同样是英明的。但是,他依然将这些发现统称为“动作”,只不过在“动作”前面加上了“电影”两个字用以区别戏剧的“动作”概念。他定义说:“电影动作就是用光和影表现出来的活动。”
弗雷里赫将劳逊的发现向前推进了,他除了前边我们提到的他关于电影在表情和手势动作方面与戏剧的不同外,还指出:“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准备让演员来表演,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把这表演拍摄下来。”显然,他认为,对于戏剧说来,动作本身就是一切,而对于电影说来,在表情达意方面摄影机表现动作的方式也许更加重要。他这样要求电影的编剧:“电影剧作家在下笔以前也应该先在自己头脑中看见所设想的动作,但他在想象中仿佛预先看到了演员的表演,以后被摄影师拍成许多镜头,又被导演剪辑成统一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电影动作’这一概念之中。”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本文一开始提到过的夏衍先生对电影编剧的要求,就不难发现,弗雷里赫对电影编剧的要求扩大了很多,他将景别、摄法(是固定拍摄?还是运用推拉摇移的运动拍摄?)甚至于蒙太奇方式都交给了电影编剧。但是,他依然将所有这些都称作“银幕上的戏剧动作”或“电影动作”。
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苏联电影剧作理论家瓦依斯菲尔德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发现,他在《电影剧作家的技巧》一书中的“动作”一节中问道:“影片中的动作跟舞台剧或小说中的动作又和区别呢?”接着他就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重点放在了电影的平行蒙太奇上。他认为在舞台上是无法充分表现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的,而电影的平行蒙太奇却很好地利用它来增强了动作的表现力了戏剧性。然而,他依然认为电影的这些武器是“动作”的范畴。
其实,我本人在最初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在我1986年完成的《你了解这门艺术吗?——电影剧作常识100问》一书中,我论述了主观镜头、摄影机的运动、光影甚至音乐(例如《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等有着与动作相同的揭示人物心灵和塑造人物性格的功能。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脱离戏剧理论的框架,称这些电影独有的武器为“银幕动作”。
如果今天我再写那本小书的话,我就不会称它们为“银幕动作”。我会明确地指出,“动作”这个剧作元素只是电影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元素之一(即便在电影艺术中它依然是最最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它不象戏剧那样就是全部。除了动作之外,电影还有其它揭示人物心灵和性格的手段。而将这些独特的手段纳入剧作家的构思和写作应该是剧作家的责任,不能把它们推卸给导演或摄影师。
内心生活的物化
在很多时候,剧作家不能只写剧中人物的动作。比如有时即便一个人内心冲突很激烈或者他很痛苦,却被深深地掩盖着。这时,从表面上看你就无法看出他心灵中的真正情感。然而这正是一个人物最最准确真实的情感表现方式,如果你硬要演员通过形体动作来表现,比如说,让他痛苦或歇斯底里,就太令观众反感。我认为,编剧在这时还有很多比求助于人物动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人物的内心生活物化。在现代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使用“闪回”直接将人物内心转换成画面,或者运用画外音形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说给观众听。当然,这些手法用得巧妙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的。但必须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人的内心生活是复杂的、混乱的、片段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如果表现得太客观、太有逻辑、太冷静、太直白就会变成一种简单的图解,令人生厌。例如:《阿Q正传》中出现了阿Q的梦境,就有图解的意味。相比起来,法国电影《老枪》中的处理就好得多。当男主人公向德国人举起枪的那一瞬,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他与已经被德国人杀害的妻子过去生活的短暂闪回,而那些闪回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时刻,反而是他吃妻子醋的片断,这就不得不使观众发挥了自由的联想。我国影片《人鬼情》中的“戏中戏”运用得也很好。锺馗的唱段恰到好处地烘托着剧中女主角秋芸的心情。现在的编剧不是不用闪回的问题,而是滥用和乱用闪回的问题。关于如何使用时空交错式结构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电影剧作理论中一个没有足够研究的领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想将它放到以后再展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非什么时候都应该使用“闪回”,我们还有更加绝妙的方式来将人物的心灵展现给观众看。例如在《城南旧事》中有一场戏是疯子秀珍对小英子诉说自己往昔的遭遇。在原来的剧本中,这些东西就是通过“闪回”来表现的。但如果一个疯子能如此从容地、有逻辑地回忆过去,显然就有失真实。这样也无法揭示今天秀珍那种神经质的感情状态。在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是高明的,他抛开了“闪回”,却利用了从秀珍视点出发的空镜头,那镜头在神经质的画外音中轻轻地拉开,又悄然地推向空空的房屋,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情感节奏,使我们与秀珍的心灵合而为一。在这里,同时起着作用的就不仅仅是秀珍的动作和语言,而是摄影机运动的节奏。这样的处理本来就应该是编剧的责任,可惜的是现在由导演来完成了。
在很多的时候某个物件道具也会成为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对象化途径。在前边,我们举过的普多夫金《母亲》中那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那一刻,母亲的心情正是通过悬壶洗手器中慢慢滴落的水滴表现出来的。水滴的节奏与人物心灵的感情节奏形成了一种模拟的关系,就好象我们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细雨打在芭蕉或梧桐叶子上的声音节奏来表现愁绪一样。在意大利影片《我们曾如此相爱》中有个更有趣的例子:影片中三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子是很好的朋友,二战后,女青年与三个男青年中最富有的一个恋爱,却最终被他抛弃。当她与另外两个同样爱着她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却为了她而争吵起来。这时,我们看到这个女青年的动作和表情似乎并没有过多的痛苦,她甚至蛮有兴致地走进了街边的自动照相亭照相去了。但当那两个青年人最终到照相亭找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不在。就当二人也要离开的时候,自动照相机发出了“喀、喀”的声音,一联四张照片从机器里边逐一地被“吐”了出来,上面都是那个女孩儿:第一张是她不太痛苦的脸,甚至还挂着笑容;第二张上的她就出现了愁容;第三张已经是痛苦的表情了;而第四张竟是她捂住脸痛哭的照片……在这里,编剧巧妙地利用了自动照相机这一道具,将人物隐藏得很深的痛苦内心揭示给我们,竟然比直接看到她哭的动作更加令人心碎!
如果一个编剧有这样的主动性,他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道具是能用来揭示人物心灵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剧作意识,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比如,我的一个学生曾经作过一个构思:一个小镇里生活的男孩,他的父亲是个粗暴的酒鬼,经常殴打他、他的妈妈和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但他太弱小了,却不可能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只能在内心里对父亲咬牙切齿。他每天躲出家门,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混在游戏厅里借打游戏来消磨时光……总之,故事很一般,因为当一个孩子只在心里冲突着的时候,我们观众是无法感觉到的。如果硬用表情或动作或台词表现出来,那就太直白了。后来,我们想到了他每天玩儿的那些个游戏机是个很好到道具,因为那个小男孩只有在打游戏机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强者。这时屏幕的光线照射在他仇恨的、被父亲打出青伤的脸上,不安地闪动着各种色彩。在屏幕里,他操纵着的武侠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击倒,人物那些庞然大物在倒下去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叫声。观众很容易就感觉出他实际上在向着自己仇恨的父亲使出拳脚,这便是他心灵的隐秘。我们找到了将它外现的物化方式。
在剧本中创造出感情的节奏
事实上,对于一个编剧说来,讲好一个故事固然难,用一种富有节奏感和旋律感的语气来讲故事就更难。我的一位学生问我:“老师,电影剧本是不是只要实打实地写出看到的和听到的就行了?”我告诉他:“是的。但那只是初级的认识。因为在一开始你必须改变文学思维的习惯,学会用画面和动作讲故事。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电影剧作的灵魂是虚的,那是一曲统一的但又分成乐章的旋律,它有着动人心魄的节奏。”法国国立声画学院的院长卡里埃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铁皮鼓》、《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等等都是世界影坛上的精品。在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在饭桌上问我:“在你教学生写作剧本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节奏。”他听后大叫:“我们是一样的。”确实,让学生理解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直到现在我国几乎大多数的编剧们依然只会忙着讲故事情节,而在他们讲述情节的时候依靠的依然只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就象德国电影心理学家于果.明斯特伯格指出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还是片面和狭窄的。我们仅仅探讨了电影演员及其表达情感的手段,而且我们的研究自然只限于对其身体反应的分析。但是尽管我们周围的人除了体态表达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手段来表达?约旱母星楹颓樾鳎缬熬缱髡呖隙ú挥κ艿秸庑┫拗频氖康摹!彼髡啪缱髡哂Ω醚罢乙恢纸谛那楦小胺涞缴硖逡酝狻薄ⅰ吧⒎⒌街芪Щ肪持小钡姆绞健@澄?慕西纳克也说:“很少有人懂得赋予一部影片以节奏和赋予画面以节奏有着相等的重要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写作剧本时,就试着把这种节奏安排进某些数学的比例关系中,即赋予某种节拍。”
伯格曼所拍摄的几乎所有影片的剧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显然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编剧。当我最初看到伯格曼的电影剧本时,心中很是诧异。因为在他的剧本中经常会写下一些无法变成视听形象的文字,例如:
“夜幕降临,暑热稍稍减退。黎明的时候,一阵热浪掠过了灰暗的海面。
……(略)
骑士回到沙滩,跪下来。他闭上眼睛,紧锁双眉,开始早祷。他紧握双手,嘴唇无声地念着祷文。他神情由于而悲痛。他睁开眼睛直视着东升的旭日,它象鼓胀的、将死的鱼从晨雾弥漫的海面上一跃而起。天空灰暗,沉滞不动;象一座坟墓的穹顶。一片乌云上方隐约可见一只海鸥,张着一动不动的翅膀,在空中飘翔。它发出古怪的、觳觫不安的鸣声。”
——《第七封印》
您着觉得奇怪吗?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导演,难道他不知道在他写下的第一句话里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我们如何从夜幕降临一直拍摄到黎明?更何况我们也无法为“暑热减退”和“热浪掠过”造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偶然,但当我读了他很多剧本(象《野草莓》)以后却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我终于知道了对于他说来,一个剧本真正应该记录的并不是那些看得到的和听得到的,而是一种能够形成情感传递的节奏。他是在演奏情感的音乐!
剧作家应该象贝多芬一样为他的作品付出节奏方面创造性的劳动,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的影片,它的剧作正是节奏的典范。下面是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创作的剧本《裸岛》的开场段落,我们立刻能读出它多特有的节奏感:
“2、黎明
海还在沉睡。
人也在沉睡。
晨雾中传来橹声。
一只小舢板靠近岸边。
船上有一对贫苦的农民夫妇,那是千太和阿丰。
……
3、大岛上的小河
晨雾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两人加快步子走近河边,开始往木桶里打水。
在默默打水的两人的头上,冰山一样陡峭的梯田的山,仿佛要刺透黎明的天空一样,高耸入云。
村里已经有人起来干活了。
打水的夫妇,朝着田间小道的人,恭敬地行礼,又继续打水。
打满了水,两人掮着压弯了的扁担,又急忙顺着来的路往回走。
4、岸边
两人气喘吁吁地走来,把装了水的桶挑到船上。
他们小心谨慎地搬运水桶,那水好象宝贝一样贵重。千太把住橹,阿丰解开系在岸边的绳子,伸手推开岸边的岩石。
缓缓漾开的涟漪。
鱼从仍然沉睡的海里,阵阵跃出水面。
5、大海
蔚蓝的大海,轻波缓浪。
岛屿还在晨雾之中,但东方已经亮了。
缓慢而单调地摇着橹的千太粗壮的手臂。
阿丰解下掖在腰上的毛巾擦汗。
小舢板的前方,有个手掌大小的岛,隐隐约约显现在眼前。
……”
他的剧本突出的个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因为那行为只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一对夫妇在黎明十分划着小舢板到一个大岛上去打水。”他在这里分明是在演奏第一乐章的主旋:轻柔、平和、欢快、明朗……所有视听元素在这里结构成为有机的节奏。在后面,整个节奏发生了变化:
“20、烈日当空
万里无云。
灼热的太阳当头。
21、海滩上
缓缓三轻波,反复进退。
静得使人昏昏欲睡。
清澈的波浪冲到沙滩上,又慢慢地退下去,小松球被晃荡得仿佛要睡着了。
22、梯田
憋住气使足劲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阿丰。
23、干旱的大地
千太小心翼翼地浇水。
24、海滩上的松球
松球仍然好象陷入沉睡之中,单调地随着波浪漂来漂去。”
剧作家范文篇6
剧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参加到电影剧本创作的队伍中来的人都会问到的,可是人们的回答却很不一样。很久以来就流行着一种观点,电影编剧的责任应该就是创作出故事情节,运用人物动作和对话来塑造出丰满立体的性格,至于蒙太奇、拍摄方法、用什么景别来表现、声音和画面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方面的事情就交给导演来处理吧!表面上看,这还真有点分工合作的道理,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所谓的“道理”阻碍了电影编剧整体水平的发展。
电影动作的意义
确实,电影剧作家应该有责任讲好故事并运用结构技巧铺排好情节,他们更应该把塑造出性格扎实可信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最最重要的责任。但是,剧作家用什么来塑造人物呢?传统的说法喜欢笼而统之道:“动作。”也许,这在过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定律,然而我们今天却不能不重新考虑它的真理性。
动作,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戏剧。对“动作”这个概念作出最全面的也是最具影响的论述者应该是贝克,他对动作所总结出的理论成为沿用至今的定理。他甚至认为动作比其它剧作元素都要重要。他说:“‘情感交流’是一切好剧本的公式。所谓情感交流,是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把感情先流到观众身上,那么,这就非靠动作不可,因为动作是激动观众感情最迅速的手段。”是他首次明确地将动作分为内部动作(也作“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两大方面的。他的失误在于没能正确地说明内心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物能够不用外部动作就可以将内心动作表现出来,例如他在舞台上一动也不动。后来者多次指出他的这一失误,因为内心动作是外部动作产生的依据,外部动作是内部动作的反映,内部动作只有通过外部动作才能得到揭示,而他所谓的“一动也不动”,其实就是人物在那一时刻的外部动作。那时,人们还把人物的形体动作(其中包括表情动作)看作是外部动作的全部内容,但到后来,人们开始觉得语言动作(对话)也是外部动作的一部分。因为在戏剧舞台上,人物可以发挥的形体动作(尤其是表情动作)实在是有限,而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更主要地依靠着对话。所以,戏剧对于对话的写作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动作性。对话只是内心动作的外部表现,并非内心动作的全部的、直接的反映,对话的“潜台词”就产生于对话与内心动作之间的差异。
总之,在戏剧的剧作理论中,“动作”这一概念便是人物塑造的全部武器。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向戏剧学会叙事的。戏剧的叙事经验曾经就是电影编剧的罗盘经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有着同样的定律,那就是动作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唯一法宝。除了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你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动作。所以我们至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导演将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全部努力都用在了演员身上,为了说明那个剧中人物此时是痛苦的,便让演员作出嚎啕大哭之类的痛苦状来。但也有很多高明的导演越来越发现电影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有着很多与戏剧不同的办法。比如,在最初,人们发现的(这也是最最容易发现的)是就人物动作中的形体动作而言,在戏剧舞台上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细微的表情和手势动作却在电影里成为揭示人物心理更重要的武器。例如弗雷里赫就曾经指出:“摄影机善于摄录极其细小的动作、极其微妙的细节、难以捉摸的语调、眼睛的闪动、睫毛的颤动;善于选取出最最重要的东西,用一个单独的场面把它突出出来——摄影机的这些能力决定了银幕上的戏剧动作的性质。”
很快,人们就发现电影与戏剧在揭示人物内心方面的差异还不仅仅是动作幅度上的问题,例如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当尼洛夫娜坐在丈夫的棺材前陷入令人窒息的悲哀的时候,导演并没有指示演员嚎啕大哭,甚至他不让演员流一滴泪,只是木然地静坐在那里。当然,前面我们说过,静静地坐着也是人物的外部动作,但仅仅靠这样的动作就很难揭示母亲此时的内心痛苦了。这时,导演聪明地在母亲的脸的镜头之后接入了一个特写镜头:水从悬壶洗手器中慢慢地滴下来,一滴又一滴。水滴的形象和节奏十分巧妙地将人物此时此刻那种绝望的、欲哭无泪的悲哀揭示了出来。现在要问:滴落的水滴是人物的动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情况纳入剧作理论呢?
电影剧作理论家们在这一方面似乎有点保守,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他们通常能够指出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的方法与戏剧的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依然不敢贸然地抛开戏剧理论已成的“动作”概念。他们依然将那些电影艺术中出现的新武器叫作“动作”,只不过有了点小小的改良。例如:劳逊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就英明地发现,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内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包括将这个动作展现给观众的方式。他以卓别林的影片《巴黎一妇人》举例说:“他(卓别林饰演的人物)的妻子因为他啫酒而离弃了他。我们看到他背对着摄影机,望着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肩膀上下抽动,好象在伤心地啜泣。之后我们却发现他正在摇动一瓶香槟酒。”在这时,揭示人物性格和引起观众笑声的不是人物的动作。如果你一开始就从正面将卓别林开香槟的动作直接表现给观众看就绝对不能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劳逊指出:“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这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应该是重要的发现。他甚至还指出:“构图决不只是动作的注解。它本身就是动作。”这同样是英明的。但是,他依然将这些发现统称为“动作”,只不过在“动作”前面加上了“电影”两个字用以区别戏剧的“动作”概念。他定义说:“电影动作就是用光和影表现出来的活动。”
弗雷里赫将劳逊的发现向前推进了,他除了前边我们提到的他关于电影在表情和手势动作方面与戏剧的不同外,还指出:“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准备让演员来表演,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把这表演拍摄下来。”显然,他认为,对于戏剧说来,动作本身就是一切,而对于电影说来,在表情达意方面摄影机表现动作的方式也许更加重要。他这样要求电影的编剧:“电影剧作家在下笔以前也应该先在自己头脑中看见所设想的动作,但他在想象中仿佛预先看到了演员的表演,以后被摄影师拍成许多镜头,又被导演剪辑成统一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电影动作’这一概念之中。”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本文一开始提到过的夏衍先生对电影编剧的要求,就不难发现,弗雷里赫对电影编剧的要求扩大了很多,他将景别、摄法(是固定拍摄?还是运用推拉摇移的运动拍摄?)甚至于蒙太奇方式都交给了电影编剧。但是,他依然将所有这些都称作“银幕上的戏剧动作”或“电影动作”。
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苏联电影剧作理论家瓦依斯菲尔德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发现,他在《电影剧作家的技巧》一书中的“动作”一节中问道:“影片中的动作跟舞台剧或小说中的动作又和区别呢?”接着他就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重点放在了电影的平行蒙太奇上。他认为在舞台上是无法充分表现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的,而电影的平行蒙太奇却很好地利用它来增强了动作的表现力了戏剧性。然而,他依然认为电影的这些武器是“动作”的范畴。
其实,我本人在最初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在我1986年完成的《你了解这门艺术吗?——电影剧作常识100问》一书中,我论述了主观镜头、摄影机的运动、光影甚至音乐(例如《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等有着与动作相同的揭示人物心灵和塑造人物性格的功能。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脱离戏剧理论的框架,称这些电影独有的武器为“银幕动作”。
如果今天我再写那本小书的话,我就不会称它们为“银幕动作”。我会明确地指出,“动作”这个剧作元素只是电影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元素之一(即便在电影艺术中它依然是最最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它不象戏剧那样就是全部。除了动作之外,电影还有其它揭示人物心灵和性格的手段。而将这些独特的手段纳入剧作家的构思和写作应该是剧作家的责任,不能把它们推卸给导演或摄影师。
内心生活的物化
在很多时候,剧作家不能只写剧中人物的动作。比如有时即便一个人内心冲突很激烈或者他很痛苦,却被深深地掩盖着。这时,从表面上看你就无法看出他心灵中的真正情感。然而这正是一个人物最最准确真实的情感表现方式,如果你硬要演员通过形体动作来表现,比如说,让他痛苦或歇斯底里,就太令观众反感。我认为,编剧在这时还有很多比求助于人物动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人物的内心生活物化。在现代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使用“闪回”直接将人物内心转换成画面,或者运用画外音形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说给观众听。当然,这些手法用得巧妙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的。但必须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人的内心生活是复杂的、混乱的、片段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如果表现得太客观、太有逻辑、太冷静、太直白就会变成一种简单的图解,令人生厌。例如:《阿Q正传》中出现了阿Q的梦境,就有图解的意味。相比起来,法国电影《老枪》中的处理就好得多。当男主人公向德国人举起枪的那一瞬,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他与已经被德国人杀害的妻子过去生活的短暂闪回,而那些闪回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时刻,反而是他吃妻子醋的片断,这就不得不使观众发挥了自由的联想。我国影片《人鬼情》中的“戏中戏”运用得也很好。锺馗的唱段恰到好处地烘托着剧中女主角秋芸的心情。现在的编剧不是不用闪回的问题,而是滥用和乱用闪回的问题。关于如何使用时空交错式结构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电影剧作理论中一个没有足够研究的领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想将它放到以后再展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非什么时候都应该使用“闪回”,我们还有更加绝妙的方式来将人物的心灵展现给观众看。例如在《城南旧事》中有一场戏是疯子秀珍对小英子诉说自己往昔的遭遇。在原来的剧本中,这些东西就是通过“闪回”来表现的。但如果一个疯子能如此从容地、有逻辑地回忆过去,显然就有失真实。这样也无法揭示今天秀珍那种神经质的感情状态。在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是高明的,他抛开了“闪回”,却利用了从秀珍视点出发的空镜头,那镜头在神经质的画外音中轻轻地拉开,又悄然地推向空空的房屋,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情感节奏,使我们与秀珍的心灵合而为一。在这里,同时起着作用的就不仅仅是秀珍的动作和语言,而是摄影机运动的节奏。这样的处理本来就应该是编剧的责任,可惜的是现在由导演来完成了。
在很多的时候某个物件道具也会成为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对象化途径。在前边,我们举过的普多夫金《母亲》中那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那一刻,母亲的心情正是通过悬壶洗手器中慢慢滴落的水滴表现出来的。水滴的节奏与人物心灵的感情节奏形成了一种模拟的关系,就好象我们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细雨打在芭蕉或梧桐叶子上的声音节奏来表现愁绪一样。在意大利影片《我们曾如此相爱》中有个更有趣的例子:影片中三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子是很好的朋友,二战后,女青年与三个男青年中最富有的一个恋爱,却最终被他抛弃。当她与另外两个同样爱着她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却为了她而争吵起来。这时,我们看到这个女青年的动作和表情似乎并没有过多的痛苦,她甚至蛮有兴致地走进了街边的自动照相亭照相去了。但当那两个青年人最终到照相亭找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不在。就当二人也要离开的时候,自动照相机发出了“喀、喀”的声音,一联四张照片从机器里边逐一地被“吐”了出来,上面都是那个女孩儿:第一张是她不太痛苦的脸,甚至还挂着笑容;第二张上的她就出现了愁容;第三张已经是痛苦的表情了;而第四张竟是她捂住脸痛哭的照片……在这里,编剧巧妙地利用了自动照相机这一道具,将人物隐藏得很深的痛苦内心揭示给我们,竟然比直接看到她哭的动作更加令人心碎!
如果一个编剧有这样的主动性,他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道具是能用来揭示人物心灵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剧作意识,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比如,我的一个学生曾经作过一个构思:一个小镇里生活的男孩,他的父亲是个粗暴的酒鬼,经常殴打他、他的妈妈和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但他太弱小了,却不可能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只能在内心里对父亲咬牙切齿。他每天躲出家门,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混在游戏厅里借打游戏来消磨时光……总之,故事很一般,因为当一个孩子只在心里冲突着的时候,我们观众是无法感觉到的。如果硬用表情或动作或台词表现出来,那就太直白了。后来,我们想到了他每天玩儿的那些个游戏机是个很好到道具,因为那个小男孩只有在打游戏机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强者。这时屏幕的光线照射在他仇恨的、被父亲打出青伤的脸上,不安地闪动着各种色彩。在屏幕里,他操纵着的武侠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击倒,人物那些庞然大物在倒下去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叫声。观众很容易就感觉出他实际上在向着自己仇恨的父亲使出拳脚,这便是他心灵的隐秘。我们找到了将它外现的物化方式。
在剧本中创造出感情的节奏
事实上,对于一个编剧说来,讲好一个故事固然难,用一种富有节奏感和旋律感的语气来讲故事就更难。我的一位学生问我:“老师,电影剧本是不是只要实打实地写出看到的和听到的就行了?”我告诉他:“是的。但那只是初级的认识。因为在一开始你必须改变文学思维的习惯,学会用画面和动作讲故事。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电影剧作的灵魂是虚的,那是一曲统一的但又分成乐章的旋律,它有着动人心魄的节奏。”法国国立声画学院的院长卡里埃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铁皮鼓》、《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等等都是世界影坛上的精品。在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在饭桌上问我:“在你教学生写作剧本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节奏。”他听后大叫:“我们是一样的。”确实,让学生理解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直到现在我国几乎大多数的编剧们依然只会忙着讲故事情节,而在他们讲述情节的时候依靠的依然只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就象德国电影心理学家于果.明斯特伯格指出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还是片面和狭窄的。我们仅仅探讨了电影演员及其表达情感的手段,而且我们的研究自然只限于对其身体反应的分析。但是尽管我们周围的人除了体态表达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情绪,电影剧作者肯定不应受到这些限制的束缚的。”他主张剧作者应该寻找一种将内心情感“辐射到身体以外”、“散发到周围环境中”的方式。莱翁.慕西纳克也说:“很少有人懂得赋予一部影片以节奏和赋予画面以节奏有着相等的重要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写作剧本时,就试着把这种节奏安排进某些数学的比例关系中,即赋予某种节拍。”
伯格曼所拍摄的几乎所有影片的剧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显然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编剧。当我最初看到伯格曼的电影剧本时,心中很是诧异。因为在他的剧本中经常会写下一些无法变成视听形象的文字,例如:
“夜幕降临,暑热稍稍减退。黎明的时候,一阵热浪掠过了灰暗的海面。
……(略)
骑士回到沙滩,跪下来。他闭上眼睛,紧锁双眉,开始早祷。他紧握双手,嘴唇无声地念着祷文。他神情由于而悲痛。他睁开眼睛直视着东升的旭日,它象鼓胀的、将死的鱼从晨雾弥漫的海面上一跃而起。天空灰暗,沉滞不动;象一座坟墓的穹顶。一片乌云上方隐约可见一只海鸥,张着一动不动的翅膀,在空中飘翔。它发出古怪的、觳觫不安的鸣声。”
——《第七封印》
您着觉得奇怪吗?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导演,难道他不知道在他写下的第一句话里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我们如何从夜幕降临一直拍摄到黎明?更何况我们也无法为“暑热减退”和“热浪掠过”造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偶然,但当我读了他很多剧本(象《野草莓》)以后却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我终于知道了对于他说来,一个剧本真正应该记录的并不是那些看得到的和听得到的,而是一种能够形成情感传递的节奏。他是在演奏情感的音乐!
剧作家应该象贝多芬一样为他的作品付出节奏方面创造性的劳动,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的影片,它的剧作正是节奏的典范。下面是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创作的剧本《裸岛》的开场段落,我们立刻能读出它多特有的节奏感:
“2、黎明
海还在沉睡。
人也在沉睡。
晨雾中传来橹声。
一只小舢板靠近岸边。
船上有一对贫苦的农民夫妇,那是千太和阿丰。
……
3、大岛上的小河
晨雾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两人加快步子走近河边,开始往木桶里打水。
在默默打水的两人的头上,冰山一样陡峭的梯田的山,仿佛要刺透黎明的天空一样,高耸入云。
村里已经有人起来干活了。
打水的夫妇,朝着田间小道的人,恭敬地行礼,又继续打水。
打满了水,两人掮着压弯了的扁担,又急忙顺着来的路往回走。
4、岸边
两人气喘吁吁地走来,把装了水的桶挑到船上。
他们小心谨慎地搬运水桶,那水好象宝贝一样贵重。千太把住橹,阿丰解开系在岸边的绳子,伸手推开岸边的岩石。
缓缓漾开的涟漪。
鱼从仍然沉睡的海里,阵阵跃出水面。
5、大海
蔚蓝的大海,轻波缓浪。
岛屿还在晨雾之中,但东方已经亮了。
缓慢而单调地摇着橹的千太粗壮的手臂。
阿丰解下掖在腰上的毛巾擦汗。
小舢板的前方,有个手掌大小的岛,隐隐约约显现在眼前。
……”
他的剧本突出的个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因为那行为只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一对夫妇在黎明十分划着小舢板到一个大岛上去打水。”他在这里分明是在演奏第一乐章的主旋:轻柔、平和、欢快、明朗……所有视听元素在这里结构成为有机的节奏。在后面,整个节奏发生了变化:
“20、烈日当空
万里无云。
灼热的太阳当头。
21、海滩上
缓缓三轻波,反复进退。
静得使人昏昏欲睡。
清澈的波浪冲到沙滩上,又慢慢地退下去,小松球被晃荡得仿佛要睡着了。
22、梯田
憋住气使足劲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阿丰。
23、干旱的大地
千太小心翼翼地浇水。
24、海滩上的松球
松球仍然好象陷入沉睡之中,单调地随着波浪漂来漂去。”
剧作家范文篇7
剧作家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参加到电影剧本创作的队伍中来的人都会问到的,可是人们的回答却很不一样。很久以来就流行着一种观点,电影编剧的责任应该就是创作出故事情节,运用人物动作和对话来塑造出丰满立体的性格,至于蒙太奇、拍摄方法、用什么景别来表现、声音和画面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方面的事情就交给导演来处理吧!表面上看,这还真有点分工合作的道理,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所谓的“道理”阻碍了电影编剧整体水平的发展。
电影动作的意义
确实,电影剧作家应该有责任讲好故事并运用结构技巧铺排好情节,他们更应该把塑造出性格扎实可信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最最重要的责任。但是,剧作家用什么来塑造人物呢?传统的说法喜欢笼而统之道:“动作。”也许,这在过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定律,然而我们今天却不能不重新考虑它的真理性。
动作,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戏剧。对“动作”这个概念作出最全面的也是最具影响的论述者应该是贝克,他对动作所总结出的理论成为沿用至今的定理。他甚至认为动作比其它剧作元素都要重要。他说:“‘情感交流’是一切好剧本的公式。所谓情感交流,是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把感情先流到观众身上,那么,这就非靠动作不可,因为动作是激动观众感情最迅速的手段。”是他首次明确地将动作分为内部动作(也作“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两大方面的。他的失误在于没能正确地说明内心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物能够不用外部动作就可以将内心动作表现出来,例如他在舞台上一动也不动。后来者多次指出他的这一失误,因为内心动作是外部动作产生的依据,外部动作是内部动作的反映,内部动作只有通过外部动作才能得到揭示,而他所谓的“一动也不动”,其实就是人物在那一时刻的外部动作。那时,人们还把人物的形体动作(其中包括表情动作)看作是外部动作的全部内容,但到后来,人们开始觉得语言动作(对话)也是外部动作的一部分。因为在戏剧舞台上,人物可以发挥的形体动作(尤其是表情动作)实在是有限,而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更主要地依靠着对话。所以,戏剧对于对话的写作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动作性。对话只是内心动作的外部表现,并非内心动作的全部的、直接的反映,对话的“潜台词”就产生于对话与内心动作之间的差异。
总之,在戏剧的剧作理论中,“动作”这一概念便是人物塑造的全部武器。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向戏剧学会叙事的。戏剧的叙事经验曾经就是电影编剧的罗盘经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和戏剧艺术有着同样的定律,那就是动作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唯一法宝。除了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语言动作,你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动作。所以我们至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导演将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全部努力都用在了演员身上,为了说明那个剧中人物此时是痛苦的,便让演员作出嚎啕大哭之类的痛苦状来。但也有很多高明的导演越来越发现电影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有着很多与戏剧不同的办法。比如,在最初,人们发现的(这也是最最容易发现的)是就人物动作中的形体动作而言,在戏剧舞台上没有多大发挥余地的细微的表情和手势动作却在电影里成为揭示人物心理更重要的武器。例如弗雷里赫就曾经指出:“摄影机善于摄录极其细小的动作、极其微妙的细节、难以捉摸的语调、眼睛的闪动、睫毛的颤动;善于选取出最最重要的东西,用一个单独的场面把它突出出来——摄影机的这些能力决定了银幕上的戏剧动作的性质。”
很快,人们就发现电影与戏剧在揭示人物内心方面的差异还不仅仅是动作幅度上的问题,例如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当尼洛夫娜坐在丈夫的棺材前陷入令人窒息的悲哀的时候,导演并没有指示演员嚎啕大哭,甚至他不让演员流一滴泪,只是木然地静坐在那里。当然,前面我们说过,静静地坐着也是人物的外部动作,但仅仅靠这样的动作就很难揭示母亲此时的内心痛苦了。这时,导演聪明地在母亲的脸的镜头之后接入了一个特写镜头:水从悬壶洗手器中慢慢地滴下来,一滴又一滴。水滴的形象和节奏十分巧妙地将人物此时此刻那种绝望的、欲哭无泪的悲哀揭示了出来。现在要问:滴落的水滴是人物的动作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情况纳入剧作理论呢?
电影剧作理论家们在这一方面似乎有点保守,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他们通常能够指出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的方法与戏剧的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依然不敢贸然地抛开戏剧理论已成的“动作”概念。他们依然将那些电影艺术中出现的新武器叫作“动作”,只不过有了点小小的改良。例如:劳逊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就英明地发现,在电影艺术中,揭示人物内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包括将这个动作展现给观众的方式。他以卓别林的影片《巴黎一妇人》举例说:“他(卓别林饰演的人物)的妻子因为他啫酒而离弃了他。我们看到他背对着摄影机,望着他的妻子的照片。他的肩膀上下抽动,好象在伤心地啜泣。之后我们却发现他正在摇动一瓶香槟酒。”在这时,揭示人物性格和引起观众笑声的不是人物的动作。如果你一开始就从正面将卓别林开香槟的动作直接表现给观众看就绝对不能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劳逊指出:“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这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应该是重要的发现。他甚至还指出:“构图决不只是动作的注解。它本身就是动作。”这同样是英明的。但是,他依然将这些发现统称为“动作”,只不过在“动作”前面加上了“电影”两个字用以区别戏剧的“动作”概念。他定义说:“电影动作就是用光和影表现出来的活动。”
弗雷里赫将劳逊的发现向前推进了,他除了前边我们提到的他关于电影在表情和手势动作方面与戏剧的不同外,还指出:“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准备让演员来表演,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把这表演拍摄下来。”显然,他认为,对于戏剧说来,动作本身就是一切,而对于电影说来,在表情达意方面摄影机表现动作的方式也许更加重要。他这样要求电影的编剧:“电影剧作家在下笔以前也应该先在自己头脑中看见所设想的动作,但他在想象中仿佛预先看到了演员的表演,以后被摄影师拍成许多镜头,又被导演剪辑成统一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电影动作’这一概念之中。”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本文一开始提到过的夏衍先生对电影编剧的要求,就不难发现,弗雷里赫对电影编剧的要求扩大了很多,他将景别、摄法(是固定拍摄?还是运用推拉摇移的运动拍摄?)甚至于蒙太奇方式都交给了电影编剧。但是,他依然将所有这些都称作“银幕上的戏剧动作”或“电影动作”。
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苏联电影剧作理论家瓦依斯菲尔德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发现,他在《电影剧作家的技巧》一书中的“动作”一节中问道:“影片中的动作跟舞台剧或小说中的动作又和区别呢?”接着他就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重点放在了电影的平行蒙太奇上。他认为在舞台上是无法充分表现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的,而电影的平行蒙太奇却很好地利用它来增强了动作的表现力了戏剧性。然而,他依然认为电影的这些武器是“动作”的范畴。
其实,我本人在最初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在我1986年完成的《你了解这门艺术吗?——电影剧作常识100问》一书中,我论述了主观镜头、摄影机的运动、光影甚至音乐(例如《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等有着与动作相同的揭示人物心灵和塑造人物性格的功能。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脱离戏剧理论的框架,称这些电影独有的武器为“银幕动作”。
如果今天我再写那本小书的话,我就不会称它们为“银幕动作”。我会明确地指出,“动作”这个剧作元素只是电影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元素之一(即便在电影艺术中它依然是最最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电影艺术说来,它不象戏剧那样就是全部。除了动作之外,电影还有其它揭示人物心灵和性格的手段。而将这些独特的手段纳入剧作家的构思和写作应该是剧作家的责任,不能把它们推卸给导演或摄影师。
内心生活的物化
在很多时候,剧作家不能只写剧中人物的动作。比如有时即便一个人内心冲突很激烈或者他很痛苦,却被深深地掩盖着。这时,从表面上看你就无法看出他心灵中的真正情感。然而这正是一个人物最最准确真实的情感表现方式,如果你硬要演员通过形体动作来表现,比如说,让他痛苦或歇斯底里,就太令观众反感。我认为,编剧在这时还有很多比求助于人物动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让人物的内心生活物化。在现代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使用“闪回”直接将人物内心转换成画面,或者运用画外音形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说给观众听。当然,这些手法用得巧妙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的。但必须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人的内心生活是复杂的、混乱的、片段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如果表现得太客观、太有逻辑、太冷静、太直白就会变成一种简单的图解,令人生厌。例如:《阿Q正传》中出现了阿Q的梦境,就有图解的意味。相比起来,法国电影《老枪》中的处理就好得多。当男主人公向德国人举起枪的那一瞬,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他与已经被德国人杀害的妻子过去生活的短暂闪回,而那些闪回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时刻,反而是他吃妻子醋的片断,这就不得不使观众发挥了自由的联想。我国影片《人鬼情》中的“戏中戏”运用得也很好。锺馗的唱段恰到好处地烘托着剧中女主角秋芸的心情。现在的编剧不是不用闪回的问题,而是滥用和乱用闪回的问题。关于如何使用时空交错式结构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电影剧作理论中一个没有足够研究的领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想将它放到以后再展开。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非什么时候都应该使用“闪回”,我们还有更加绝妙的方式来将人物的心灵展现给观众看。例如在《城南旧事》中有一场戏是疯子秀珍对小英子诉说自己往昔的遭遇。在原来的剧本中,这些东西就是通过“闪回”来表现的。但如果一个疯子能如此从容地、有逻辑地回忆过去,显然就有失真实。这样也无法揭示今天秀珍那种神经质的感情状态。在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是高明的,他抛开了“闪回”,却利用了从秀珍视点出发的空镜头,那镜头在神经质的画外音中轻轻地拉开,又悄然地推向空空的房屋,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情感节奏,使我们与秀珍的心灵合而为一。在这里,同时起着作用的就不仅仅是秀珍的动作和语言,而是摄影机运动的节奏。这样的处理本来就应该是编剧的责任,可惜的是现在由导演来完成了。
在很多的时候某个物件道具也会成为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对象化途径。在前边,我们举过的普多夫金《母亲》中那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那一刻,母亲的心情正是通过悬壶洗手器中慢慢滴落的水滴表现出来的。水滴的节奏与人物心灵的感情节奏形成了一种模拟的关系,就好象我们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细雨打在芭蕉或梧桐叶子上的声音节奏来表现愁绪一样。在意大利影片《我们曾如此相爱》中有个更有趣的例子:影片中三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子是很好的朋友,二战后,女青年与三个男青年中最富有的一个恋爱,却最终被他抛弃。当她与另外两个同样爱着她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却为了她而争吵起来。这时,我们看到这个女青年的动作和表情似乎并没有过多的痛苦,她甚至蛮有兴致地走进了街边的自动照相亭照相去了。但当那两个青年人最终到照相亭找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不在。就当二人也要离开的时候,自动照相机发出了“喀、喀”的声音,一联四张照片从机器里边逐一地被“吐”了出来,上面都是那个女孩儿:第一张是她不太痛苦的脸,甚至还挂着笑容;第二张上的她就出现了愁容;第三张已经是痛苦的表情了;而第四张竟是她捂住脸痛哭的照片……在这里,编剧巧妙地利用了自动照相机这一道具,将人物隐藏得很深的痛苦内心揭示给我们,竟然比直接看到她哭的动作更加令人心碎!
如果一个编剧有这样的主动性,他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道具是能用来揭示人物心灵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剧作意识,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比如,我的一个学生曾经作过一个构思:一个小镇里生活的男孩,他的父亲是个粗暴的酒鬼,经常殴打他、他的妈妈和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但他太弱小了,却不可能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只能在内心里对父亲咬牙切齿。他每天躲出家门,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混在游戏厅里借打游戏来消磨时光……总之,故事很一般,因为当一个孩子只在心里冲突着的时候,我们观众是无法感觉到的。如果硬用表情或动作或台词表现出来,那就太直白了。后来,我们想到了他每天玩儿的那些个游戏机是个很好到道具,因为那个小男孩只有在打游戏机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强者。这时屏幕的光线照射在他仇恨的、被父亲打出青伤的脸上,不安地闪动着各种色彩。在屏幕里,他操纵着的武侠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击倒,人物那些庞然大物在倒下去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叫声。观众很容易就感觉出他实际上在向着自己仇恨的父亲使出拳脚,这便是他心灵的隐秘。我们找到了将它外现的物化方式。
在剧本中创造出感情的节奏
事实上,对于一个编剧说来,讲好一个故事固然难,用一种富有节奏感和旋律感的语气来讲故事就更难。我的一位学生问我:“老师,电影剧本是不是只要实打实地写出看到的和听到的就行了?”我告诉他:“是的。但那只是初级的认识。因为在一开始你必须改变文学思维的习惯,学会用画面和动作讲故事。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电影剧作的灵魂是虚的,那是一曲统一的但又分成乐章的旋律,它有着动人心魄的节奏。”法国国立声画学院的院长卡里埃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铁皮鼓》、《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等等都是世界影坛上的精品。在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在饭桌上问我:“在你教学生写作剧本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节奏。”他听后大叫:“我们是一样的。”确实,让学生理解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直到现在我国几乎大多数的编剧们依然只会忙着讲故事情节,而在他们讲述情节的时候依靠的依然只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就象德国电影心理学家于果.明斯特伯格指出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还是片面和狭窄的。我们仅仅探讨了电影演员及其表达情感的手段,而且我们的研究自然只限于对其身体反应的分析。但是尽管我们周围的人除了体态表达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情绪,电影剧作者肯定不应受到这些限制的束缚的。”他主张剧作者应该寻找一种将内心情感“辐射到身体以外”、“散发到周围环境中”的方式。莱翁.慕西纳克也说:“很少有人懂得赋予一部影片以节奏和赋予画面以节奏有着相等的重要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写作剧本时,就试着把这种节奏安排进某些数学的比例关系中,即赋予某种节拍。”
伯格曼所拍摄的几乎所有影片的剧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显然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编剧。当我最初看到伯格曼的电影剧本时,心中很是诧异。因为在他的剧本中经常会写下一些无法变成视听形象的文字,例如:
“夜幕降临,暑热稍稍减退。黎明的时候,一阵热浪掠过了灰暗的海面。
……(略)
骑士回到沙滩,跪下来。他闭上眼睛,紧锁双眉,开始早祷。他紧握双手,嘴唇无声地念着祷文。他神情由于而悲痛。他睁开眼睛直视着东升的旭日,它象鼓胀的、将死的鱼从晨雾弥漫的海面上一跃而起。天空灰暗,沉滞不动;象一座坟墓的穹顶。一片乌云上方隐约可见一只海鸥,张着一动不动的翅膀,在空中飘翔。它发出古怪的、觳觫不安的鸣声。”
——《第七封印》
您着觉得奇怪吗?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导演,难道他不知道在他写下的第一句话里就包括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我们如何从夜幕降临一直拍摄到黎明?更何况我们也无法为“暑热减退”和“热浪掠过”造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偶然,但当我读了他很多剧本(象《野草莓》)以后却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我终于知道了对于他说来,一个剧本真正应该记录的并不是那些看得到的和听得到的,而是一种能够形成情感传递的节奏。他是在演奏情感的音乐!
剧作家应该象贝多芬一样为他的作品付出节奏方面创造性的劳动,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的影片,它的剧作正是节奏的典范。下面是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创作的剧本《裸岛》的开场段落,我们立刻能读出它多特有的节奏感:
“2、黎明
海还在沉睡。
人也在沉睡。
晨雾中传来橹声。
一只小舢板靠近岸边。
船上有一对贫苦的农民夫妇,那是千太和阿丰。
……
3、大岛上的小河
晨雾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两人加快步子走近河边,开始往木桶里打水。
在默默打水的两人的头上,冰山一样陡峭的梯田的山,仿佛要刺透黎明的天空一样,高耸入云。
村里已经有人起来干活了。
打水的夫妇,朝着田间小道的人,恭敬地行礼,又继续打水。
打满了水,两人掮着压弯了的扁担,又急忙顺着来的路往回走。4、岸边
两人气喘吁吁地走来,把装了水的桶挑到船上。
他们小心谨慎地搬运水桶,那水好象宝贝一样贵重。千太把住橹,阿丰解开系在岸边的绳子,伸手推开岸边的岩石。
缓缓漾开的涟漪。
鱼从仍然沉睡的海里,阵阵跃出水面。
5、大海
蔚蓝的大海,轻波缓浪。
岛屿还在晨雾之中,但东方已经亮了。
缓慢而单调地摇着橹的千太粗壮的手臂。
阿丰解下掖在腰上的毛巾擦汗。
小舢板的前方,有个手掌大小的岛,隐隐约约显现在眼前。
……”
他的剧本突出的个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因为那行为只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一对夫妇在黎明十分划着小舢板到一个大岛上去打水。”他在这里分明是在演奏第一乐章的主旋:轻柔、平和、欢快、明朗……所有视听元素在这里结构成为有机的节奏。在后面,整个节奏发生了变化:
“20、烈日当空
万里无云。
灼热的太阳当头。
21、海滩上
缓缓三轻波,反复进退。
静得使人昏昏欲睡。
清澈的波浪冲到沙滩上,又慢慢地退下去,小松球被晃荡得仿佛要睡着了。
22、梯田
憋住气使足劲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阿丰。
23、干旱的大地
千太小心翼翼地浇水。
24、海滩上的松球
松球仍然好象陷入沉睡之中,单调地随着波浪漂来漂去。”
剧作家范文篇8
【正文】
“电影制作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
——杰克·瓦伦蒂(前美国电影委员会主席)
“你知道声望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就是不挣钱的电影。”
——美国电影《长丝袜》台词
美国《综艺》(Variety)杂志曾对好莱坞2002年以前的100部总收入最高的电影做过一项非正式调查,表明大多数电影都是从以前的作品中获得灵感。
在好莱坞,大约50%的电影是改编自电视节目、漫画书、戏剧或电子游戏,也有一些影片是给以前成功的影片拍续集,或者搞旧片重拍,新瓶装旧酒。
一些人说,好莱坞是不知道创新为何物的城市——这一问题在业内外已引起了注意。电影制作方依赖不断回炉的想法来拍片,已成为一种趋势。
不过就算是被多次使用的创意也是创意。那它们都是从哪来的呢?——有的是来自制片厂内部的制片人、经理、作家或者是导演,有的则是来自外部。
剧本交易中的衍生业务
开发内部创意的方式相对简单。制片厂买下一个文学著作的所有权,然后雇一个剧作家。这个作家在制片厂项目开发人员的指导下准备剧本(至少是第一稿)。
如果制片厂从外部的剧本市场获得一个剧本,情形则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些起重要作用的机构和人物。
公司
公司在剧本交易中起中介作用。典型的公司的职责主要是协商用工合同,购买剧本,帮助寻找资金,或者在需要项目合作的公司之间做中间人。公司的标准佣金是10%,所以《综艺》杂志干脆把这些机构称为“百分之十”。有些电影将来有可能拍出其他版本,比如电视版。如果这样,机构会得到版税或重播酬劳。
加利福尼亚州依照该州《人才法案》来对这些机构颁发执照和进行管理。机构由同业公会颁发证书,或者是这些公会的签约方。一些机构为业内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另一些机构则专门经营某些领域,比如只为演员或剧作家服务。机构在业内的影响举足轻重,它们的无形资产难以估量。
生意自20世纪末期开始显现其强大的实力。麦克尔·奥维兹于1975年成立的创作人员公司(CreativeAssociatesAgency)极大地扩张了生意的市场。最初它是组织电视节目拍摄的重要机构,后来又扩张到电影、投资银行和广告业,由此成为好莱坞重要的机构。20世纪80年代,该公司还承揽了几个好莱坞大片的销售业务。此外,它还成功组织拍摄了《雨人》、《侏罗纪公园》等影片。
经纪人公司
最近经纪人和管理公司已发展成为好莱坞的重要角色。与公司的作用相似,不过经纪人公司的佣金更多,有15%或者更高,目前它们正积极地侵入机构的领地,有的甚至获准开发和制作影视项目。这样就能在更大范围上为自己的客户服务,在这一点上它们比公司更具优势。
娱乐律师
好莱坞不是每个人都有机构或经纪人,但很多位高权重的人物,都聘用律师来跟日益复杂的娱乐市场打交道。有一些专攻电影法律的律师,大多在洛杉矶、纽约和其他电影业务繁忙的地区独立工作。过去几年里,跟好莱坞打交道的律师数量激增。200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洛杉矶地区有400多名娱乐律师。
在电影的制作发行过程中,要签署很多协议和合同。因为在好莱坞,一个创意很快就成为一种资产。又比如,剧本中描绘的某个人物引起联想,就有可能被指控侵犯隐私和毁坏名誉。
电影名的选择也有可能会引起诉讼。尽管保险赔偿包括这些范畴,人们还是想通过法律途径尽量避免这些问题。美国电影委员会有一个电影名注册局,电影制片厂甚至在开拍一部电影之前就把电影名注册上了。制片厂之间达成协议,避免跟已注册的电影名字相近。如果一个电影名极有可能商品化,就有可能被注册成商标。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综上所述,机构、管理公司、娱乐律师等机构和人物是在好莱坞剧本市场上起重要作用的角色。那么电影剧本是怎样到制片厂手里,并被开发出来的呢?
多级开发的剧本市场
好莱坞剧本市场比较复杂,因为剧本来自不同的渠道。一个创意或者一个完整的电影剧本可能出自一个剧作家之手,也可能来自一个机构、一家制作公司,或某位经纪人、制片人、导演甚至制片高级主管。有鉴于此,在好莱坞,剧作家的定义比较含糊。因为每个人似乎都在提出创意,导演或制片人兼剧作家是很正常的事。
说不好好莱坞有多少人声称自己是剧作家,更难说有多少人在这个行当中靠写作维生。美国剧作家公会(WritersGuildofAmerica)的数据显示,4525名会员在2001年上报了收入,而8841名会员在这年的至少一个季度里公布了收入。
在2001年,一个原创剧本的价码最低在29000美元左右。通过讨价还价,往往能得到更高的价钱。剧作家做故事处理、改第一稿、重写、润色现有剧本都能得到报酬,每次电影重映剧作家也能得到一些收入。另外还有版税。2001年,美国作家公会西部办公室的数据表明,剧作家总收入达7.821亿美元。25%的剧作家在这一年的收入只有2.8万美元多一点,55%的剧作家的年收入则超过56万美元。
剧作家在业界没有多少影响力。过去他们多是跟制片厂签约,最近,剧作家则是跟机构或经纪人合作向制片人销售创意或剧本。制片人再想办法使制片厂高级主管对这一创意产生兴趣,从而签署开发协议。制片人也可能会买下某个选题,或者暂时买下一个剧本的产权。
出卖创意和剧本有时要以口头投稿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剧作家向项目开发经理或其他可能的买家描述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口头投稿越来越难,这种方式对已成名的剧作家可能性比较大。
有些剧本则是已经写作完成,希望被制片人或制片厂购买。这种剧本叫特制剧本。通常制片厂会找来读者或剧本分析员拟出剧本概况,因为制片厂没有时间阅读每一个剧本。剧本概况包括剧情简介,剧本的级别(从差到优秀),还要给它一个整体评估。几乎99%的剧本都能得到推荐。剧本的读者大多是实习生,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想成为剧作家的人。这些人可以在家里工作,每读一个剧本的报酬是25~50美元。
机构也可以把特制剧本往外发送,然后尽力炒作,制造一个投标的战争。上世纪90年代,特制剧本销售情况火爆,价钱也相当可观。1990年,创作《致命武器》(LethalWeapon)的剧作家申·布莱克以175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最后的童子军》(TheLastBoyScout)。此后,“百万美元剧本”司空见惯。几年以后,布莱克的《特工狂花》(TheLongKissGoodnight)卖了400万美元。尽管制片厂试图把剧本控制在较低的价位上,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百万美元剧本”根本就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名不见经传的人都能成功地卖出特制剧本。比如当时的好莱坞新人奈特·沙马兰,凭《第六感》(TheSixthSense)赚得225万美元,而且该片当即投产。
特制剧本投标使人担忧剧本质量的问题,因为投标的过程会提高平庸剧本的吸引力,从而造成哄抬价格。据说,几乎所有的特制剧本在投拍之前都要重新改写,有些剧本很差,因为筛选过程不合理。谈到剧本质量,老牌剧作家威廉·戈德曼的话很精辟:这行只注意这样的剧作家——用他们的剧本拍出的电影在商业上能有收获。
最成功的剧作家或制片人不用通过特制剧本的筛选过程。有些有成功经历的机构或人物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缩短标准的项目开发程序,单单根据自己的兴趣就能通过一部电影的开发计划。
的确,每个人都期待着下一个热点和大片,或者是下一部能衍生出商品和续集的电影。但是没人知道什么样的电影能引起轰动,这样,一个剧本能否被选中就取决于其给制片厂挣钱的潜力而非质量。换言之,利润意识占主导地位。再说,还有“恐惧因素”——管理人员害怕自己会丢了工作,便只关注他们购买的剧本是否有造星的潜能。现在那种高度概括性的电影(HighConceptFilm)成为一种趋势。这种电影通常是动作片或情节剧,故事几句话就能说清,往往起用明星,极具可卖性。只要能够挣钱,平庸又何妨?
尽管特制剧本制度为新的作家提供了机会,市场的选择性还是很强的。2002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以近5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麦克·里奇顿小说《黑影地带》(Prey)的电影版权。福克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拿到手稿之前,手稿持有方就版权的事跟他们多次接触,在一个周末达成了协议。这本书只送到了福克斯公司,这在好莱坞可是少见的事。在这里,文学作品的版权往往是要到处搜寻开价最高的投标人,最后传遍几家公司。
剧本一旦开始在好莱坞流传,就会有重要的角色介入来决定这个剧本的命运和归属。在一个价值4000万美元的协议中,环球和幻想娱乐公司(UniversalandImagineEntertainment)的高级主管布兰·戈里兹买下了《内部人物》(InsideMan),这是新手卢梭·戈沃兹的特制剧本。戈沃兹由律师转行写剧本,创作了一个惊险的犯罪故事。有好几家公司对这个剧本感兴趣,但环球和幻想娱乐公司的高级主管斯科特·斯达波和多娜·朗格力设法劝说剧作者的态度发生倾斜,最终将剧本卖给他们。
制片厂每年在剧本上会花费很多钱。有多少电影和剧本的想法最后没有机会被搬上银幕无从知晓。多伦多资深电影人比尔·马克斯说,100部剧本最终被正式投拍的往往只有1部,另外那99部则被束之高阁。
演职员字幕对于很多好莱坞剧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字幕关乎他们的声誉、奖金和酬劳。片头字幕的顺序往往是这样的:发行公司,制片人,制片公司,导演,主要明星,然后是电影片名。不过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字幕和付款的问题是用工合同中协商的重要内容。行业工会建立了详细而又复杂的条款。比如,美国剧作家工会要求,第一稿的剧作家如果想把自己的名字打上字幕就必须对剧本做33%的贡献,其后的作者们必须做50%的贡献。不过,如果项目负责人也成了修改稿作者,他就得做出比50%更多的贡献。
项目开发环节
创意一旦被选定,就进入项目开发环节,这是把创意转变成剧本的过程。具体步骤包括组织思想,获得版权,准备提纲,写剧情简介,写作,润色和修改剧本。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典型的开发过程应该是先签署开发协议。它表明制片厂和制作公司同意为剧作家、制片人和导演提供资金。各个项目所得到的资金数量不同,有的资金甚至都不能支付项目开发阶段的开支。项目开发的资金来自各个渠道,有的是制片厂的钱,独立制片公司资金来源更广。开发协议有时还包括电影正式投拍之前的应急费用。这一过程,有时只需八个月,有时则要长达两年。
剧作家范文篇9
【正文】
“电影制作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
——杰克·瓦伦蒂(前美国电影委员会主席)
“你知道声望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就是不挣钱的电影。”
——美国电影《长丝袜》台词
美国《综艺》(Variety)杂志曾对好莱坞2002年以前的100部总收入最高的电影做过一项非正式调查,表明大多数电影都是从以前的作品中获得灵感。
在好莱坞,大约50%的电影是改编自电视节目、漫画书、戏剧或电子游戏,也有一些影片是给以前成功的影片拍续集,或者搞旧片重拍,新瓶装旧酒。
一些人说,好莱坞是不知道创新为何物的城市——这一问题在业内外已引起了注意。电影制作方依赖不断回炉的想法来拍片,已成为一种趋势。
不过就算是被多次使用的创意也是创意。那它们都是从哪来的呢?——有的是来自制片厂内部的制片人、经理、作家或者是导演,有的则是来自外部。
剧本交易中的衍生业务
开发内部创意的方式相对简单。制片厂买下一个文学著作的所有权,然后雇一个剧作家。这个作家在制片厂项目开发人员的指导下准备剧本(至少是第一稿)。
如果制片厂从外部的剧本市场获得一个剧本,情形则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些起重要作用的机构和人物。
公司
公司在剧本交易中起中介作用。典型的公司的职责主要是协商用工合同,购买剧本,帮助寻找资金,或者在需要项目合作的公司之间做中间人。公司的标准佣金是10%,所以《综艺》杂志干脆把这些机构称为“百分之十”。有些电影将来有可能拍出其他版本,比如电视版。如果这样,机构会得到版税或重播酬劳。
加利福尼亚州依照该州《人才法案》来对这些机构颁发执照和进行管理。机构由同业公会颁发证书,或者是这些公会的签约方。一些机构为业内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另一些机构则专门经营某些领域,比如只为演员或剧作家服务。机构在业内的影响举足轻重,它们的无形资产难以估量。
生意自20世纪末期开始显现其强大的实力。麦克尔·奥维兹于1975年成立的创作人员公司(CreativeAssociatesAgency)极大地扩张了生意的市场。最初它是组织电视节目拍摄的重要机构,后来又扩张到电影、投资银行和广告业,由此成为好莱坞重要的机构。20世纪80年代,该公司还承揽了几个好莱坞大片的销售业务。此外,它还成功组织拍摄了《雨人》、《侏罗纪公园》等影片。
经纪人公司
最近经纪人和管理公司已发展成为好莱坞的重要角色。与公司的作用相似,不过经纪人公司的佣金更多,有15%或者更高,目前它们正积极地侵入机构的领地,有的甚至获准开发和制作影视项目。这样就能在更大范围上为自己的客户服务,在这一点上它们比公司更具优势。
娱乐律师
好莱坞不是每个人都有机构或经纪人,但很多位高权重的人物,都聘用律师来跟日益复杂的娱乐市场打交道。有一些专攻电影法律的律师,大多在洛杉矶、纽约和其他电影业务繁忙的地区独立工作。过去几年里,跟好莱坞打交道的律师数量激增。200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洛杉矶地区有400多名娱乐律师。
在电影的制作发行过程中,要签署很多协议和合同。因为在好莱坞,一个创意很快就成为一种资产。又比如,剧本中描绘的某个人物引起联想,就有可能被指控侵犯隐私和毁坏名誉。
电影名的选择也有可能会引起诉讼。尽管保险赔偿包括这些范畴,人们还是想通过法律途径尽量避免这些问题。美国电影委员会有一个电影名注册局,电影制片厂甚至在开拍一部电影之前就把电影名注册上了。制片厂之间达成协议,避免跟已注册的电影名字相近。如果一个电影名极有可能商品化,就有可能被注册成商标。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综上所述,机构、管理公司、娱乐律师等机构和人物是在好莱坞剧本市场上起重要作用的角色。那么电影剧本是怎样到制片厂手里,并被开发出来的呢?
多级开发的剧本市场
好莱坞剧本市场比较复杂,因为剧本来自不同的渠道。一个创意或者一个完整的电影剧本可能出自一个剧作家之手,也可能来自一个机构、一家制作公司,或某位经纪人、制片人、导演甚至制片高级主管。有鉴于此,在好莱坞,剧作家的定义比较含糊。因为每个人似乎都在提出创意,导演或制片人兼剧作家是很正常的事。
说不好好莱坞有多少人声称自己是剧作家,更难说有多少人在这个行当中靠写作维生。美国剧作家公会(WritersGuildofAmerica)的数据显示,4525名会员在2001年上报了收入,而8841名会员在这年的至少一个季度里公布了收入。
在2001年,一个原创剧本的价码最低在29000美元左右。通过讨价还价,往往能得到更高的价钱。剧作家做故事处理、改第一稿、重写、润色现有剧本都能得到报酬,每次电影重映剧作家也能得到一些收入。另外还有版税。2001年,美国作家公会西部办公室的数据表明,剧作家总收入达7.821亿美元。25%的剧作家在这一年的收入只有2.8万美元多一点,55%的剧作家的年收入则超过56万美元。
剧作家在业界没有多少影响力。过去他们多是跟制片厂签约,最近,剧作家则是跟机构或经纪人合作向制片人销售创意或剧本。制片人再想办法使制片厂高级主管对这一创意产生兴趣,从而签署开发协议。制片人也可能会买下某个选题,或者暂时买下一个剧本的产权。
出卖创意和剧本有时要以口头投稿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剧作家向项目开发经理或其他可能的买家描述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口头投稿越来越难,这种方式对已成名的剧作家可能性比较大。
有些剧本则是已经写作完成,希望被制片人或制片厂购买。这种剧本叫特制剧本。通常制片厂会找来读者或剧本分析员拟出剧本概况,因为制片厂没有时间阅读每一个剧本。剧本概况包括剧情简介,剧本的级别(从差到优秀),还要给它一个整体评估。几乎99%的剧本都能得到推荐。剧本的读者大多是实习生,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想成为剧作家的人。这些人可以在家里工作,每读一个剧本的报酬是25~50美元。
机构也可以把特制剧本往外发送,然后尽力炒作,制造一个投标的战争。上世纪90年代,特制剧本销售情况火爆,价钱也相当可观。1990年,创作《致命武器》(LethalWeapon)的剧作家申·布莱克以175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最后的童子军》(TheLastBoyScout)。此后,“百万美元剧本”司空见惯。几年以后,布莱克的《特工狂花》(TheLongKissGoodnight)卖了400万美元。尽管制片厂试图把剧本控制在较低的价位上,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百万美元剧本”根本就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名不见经传的人都能成功地卖出特制剧本。比如当时的好莱坞新人奈特·沙马兰,凭《第六感》(TheSixthSense)赚得225万美元,而且该片当即投产。
特制剧本投标使人担忧剧本质量的问题,因为投标的过程会提高平庸剧本的吸引力,从而造成哄抬价格。据说,几乎所有的特制剧本在投拍之前都要重新改写,有些剧本很差,因为筛选过程不合理。谈到剧本质量,老牌剧作家威廉·戈德曼的话很精辟:这行只注意这样的剧作家——用他们的剧本拍出的电影在商业上能有收获。
最成功的剧作家或制片人不用通过特制剧本的筛选过程。有些有成功经历的机构或人物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缩短标准的项目开发程序,单单根据自己的兴趣就能通过一部电影的开发计划。
的确,每个人都期待着下一个热点和大片,或者是下一部能衍生出商品和续集的电影。但是没人知道什么样的电影能引起轰动,这样,一个剧本能否被选中就取决于其给制片厂挣钱的潜力而非质量。换言之,利润意识占主导地位。再说,还有“恐惧因素”——管理人员害怕自己会丢了工作,便只关注他们购买的剧本是否有造星的潜能。现在那种高度概括性的电影(HighConceptFilm)成为一种趋势。这种电影通常是动作片或情节剧,故事几句话就能说清,往往起用明星,极具可卖性。只要能够挣钱,平庸又何妨?
尽管特制剧本制度为新的作家提供了机会,市场的选择性还是很强的。2002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以近5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麦克·里奇顿小说《黑影地带》(Prey)的电影版权。福克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拿到手稿之前,手稿持有方就版权的事跟他们多次接触,在一个周末达成了协议。这本书只送到了福克斯公司,这在好莱坞可是少见的事。在这里,文学作品的版权往往是要到处搜寻开价最高的投标人,最后传遍几家公司。
剧本一旦开始在好莱坞流传,就会有重要的角色介入来决定这个剧本的命运和归属。在一个价值4000万美元的协议中,环球和幻想娱乐公司(UniversalandImagineEntertainment)的高级主管布兰·戈里兹买下了《内部人物》(InsideMan),这是新手卢梭·戈沃兹的特制剧本。戈沃兹由律师转行写剧本,创作了一个惊险的犯罪故事。有好几家公司对这个剧本感兴趣,但环球和幻想娱乐公司的高级主管斯科特·斯达波和多娜·朗格力设法劝说剧作者的态度发生倾斜,最终将剧本卖给他们。
制片厂每年在剧本上会花费很多钱。有多少电影和剧本的想法最后没有机会被搬上银幕无从知晓。多伦多资深电影人比尔·马克斯说,100部剧本最终被正式投拍的往往只有1部,另外那99部则被束之高阁。
演职员字幕对于很多好莱坞剧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字幕关乎他们的声誉、奖金和酬劳。片头字幕的顺序往往是这样的:发行公司,制片人,制片公司,导演,主要明星,然后是电影片名。不过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字幕和付款的问题是用工合同中协商的重要内容。行业工会建立了详细而又复杂的条款。比如,美国剧作家工会要求,第一稿的剧作家如果想把自己的名字打上字幕就必须对剧本做33%的贡献,其后的作者们必须做50%的贡献。不过,如果项目负责人也成了修改稿作者,他就得做出比50%更多的贡献。
项目开发环节
创意一旦被选定,就进入项目开发环节,这是把创意转变成剧本的过程。具体步骤包括组织思想,获得版权,准备提纲,写剧情简介,写作,润色和修改剧本。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典型的开发过程应该是先签署开发协议。它表明制片厂和制作公司同意为剧作家、制片人和导演提供资金。各个项目所得到的资金数量不同,有的资金甚至都不能支付项目开发阶段的开支。项目开发的资金来自各个渠道,有的是制片厂的钱,独立制片公司资金来源更广。开发协议有时还包括电影正式投拍之前的应急费用。这一过程,有时只需八个月,有时则要长达两年。
剧作家范文篇10
一方面是戏曲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成熟,另一方面是苦闷文人无处申诉的情怀,频繁进出瓦舍勾栏的文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施展才华、表达悲愤与抗争的天地。“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元杂剧作家对杂剧兴盛所做出的贡献是研究者们所公认的,“不少具有正义感和富有才华的文人便投身到杂剧剧本的创作中来”,“对于北杂剧在元朝之能成为一代的文学(俗称元杂剧),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邓绍基在《元杂剧的形成及繁荣的原因》中说道:“众多的知识分子从事或参与戏剧活动是元杂剧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条件。”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五《送李良甫同知北上序》便有这样的记载:“山东兵难,衣冠转徙。士族子弟失其故业,流为吏商,降为农隶者多矣。”在这样的困境下,读书人同市井中人朝夕相处,共同面对苦难的人生,体会着下层社会的悲欢忧乐、世态炎凉。《录鬼簿》收录当时的杂剧作家152人,嗣后《录鬼簿续编》又收录元明之际的杂剧作家71人,两书合计共收录223人,可谓名家云集。钟嗣成曾在《录鬼簿》序言中写道:“今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录,岁月糜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曾有学者李春祥总结过,元杂剧作家们的贡献,一是编写了大量剧本,使得剧团有戏可演;二是组织杂剧书会,推动创作与演出。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才子佳人的韵事涌出,常出入勾栏瓦舍,使得这些文人“能词章,通音律”,“明曲调,善讴歌”,不仅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对杂剧业务也很熟悉,如关汉卿,会吟诗,会弹丝,会品竹,也会唱鹧鸪,舞垂手。明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中亦说他“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
二、杂剧是文人情绪的宣泄
元文人与青楼女子的关系也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对于纵情声色的元代剧作家来说,前代同样沉湎于温柔乡的杜牧和柳永自然成了他们歌咏的对象。在生活中不如意,而在风流场上却较为得意,这使得文人们乐在其中。白朴曾在散曲《[中吕]阳春曲·题情》里写道:“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读书,相偎相抱取欢娱。”他还在《梧桐雨》中,对唐明皇珊瑚枕上、翡翠帘前的风流生活作了细致的描写。关汉卿也是对风月场中的浪漫赞不绝口,他在《[南吕]一支花·不服老》中说:“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也许这种外在的放浪是为了掩饰其内心的羞辱和不平,但是在剧作家的眼中,青楼女子不再是应当轻歌曼舞供文人雅士借酒助兴的工具,更非可以肆意玩弄的对象,而是有情有义的“人”。杂剧作者塑造了一个个独具性格的女性形象,着重表现她们的觉醒和抗争,如《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她一反传统女性的惟命是从,文雅娴静,而是敢爱敢恨,侠骨柔肠。作者通过这个角色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篱的突破,闪耀着反传统的新的思想光芒。元杂剧作者通过写历史剧借古讽今,用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来书写自己的苦闷。例如,郑光祖《王粲登楼》中的王粲,才华横溢却无人赏识,在动乱的汉末,他奔荆州投刘表,却不被重用。羁留异乡,功名不遂,于是生不逢时、命运不济的感慨顿由心生。在一个萧条的暮秋,他登高远眺,借酒消愁,感叹“空学成补天才却无度饥寒计”、又“登楼意,恨无上天梯”。在很多历史剧中,杂剧作者一旦涉及“仕途”这一题材时,便充满了压抑悲凉的情绪,在没有科举、文人备受歧视打压的大背景下,作品中的人物都被塑造成了失意而郁郁寡欢的形象。元杂剧作者也写登科及第这样的题材,但是所表达的却是另外一个意思。这类剧目,通常讲一个文人在得志之前主要是玩味爱情,陶醉在佳人对自己才华的欣赏之中,而得志后则高高在上地占有,甚至于玩弄女性,如《破窑记》、《潇湘雨》等。文人在不得志、穷困潦倒时是别人嘲笑、侮辱的对象,一旦高中,他们又反过来对他人睚眦必报,如在《冻苏秦》、《王粲登楼》、《裴度还带》、《渔樵记》等几部杂剧中,主人公对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人所说过的话又一字不差地还于对方,可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相关文章
导演电视剧作品思想继承与批判 2022-02-14 08:37:42
封闭空间电影及剧作叙事特点研究 2022-01-05 03:37:45
影视戏剧作品与学生德育关系研究 2022-07-02 03:49:16
电视剧作品音乐元素分析 2022-04-14 02:57:20
浅谈歌剧作品艺术形象的塑造 2022-08-29 04:21:50
浅析艺术创作剧作结构 2022-02-26 03: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