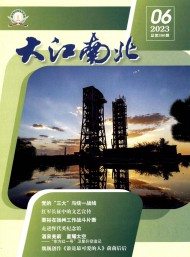江南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14:32:35
江南范文篇1
水是江南水乡环境的母体,亦是自然景观中的文脉。水的灵性、水的气质、水的形态巧妙,构成了江南古镇的结构线,并成为与周围环境有机贯通的特殊介质。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美,文化根基深厚,经济活动繁荣,交通条件便利。特别是江南地区拥有密布的河湖水系,为江南古镇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重要良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水乡民居,依水而建,小桥街巷沿水延伸,江南丰厚的水源与粉墙黛瓦的民居建筑构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的水乡生活风情画面。它既是江南水乡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语汇,更是一道完整的江南地方文化景观。
一、江南古镇水岸建筑景观的构成要素
(一)水。江南水乡因水而生,所谓“无水不成吴越,无桥不显水”,可见水是江南水城、水镇、水村、水路、水巷形成的最根本的物质条件。水是江南古镇的灵魂,纵横交错的河道是江南古镇的动脉。水的存在形成了江南独有的水网空间,传承着水乡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没有水就没有水乡文化,因此,水是构成江南水乡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最基本的元素。
(二)桥。江南水乡,河多桥多。桥作为水陆交通联系的纽带,既是主要的水陆通道,又是江南水乡独具魅力的形态要素。桥的平面布局因河道、地势、位置、功能而异,有直的、斜的,形态不拘一格,力求方便实用。桥作为生活的中心,在桥上建庙、建屋、建亭、建廊,使得桥的功能和形式千变万化。家家邻水枕河,户户近桥通舟,江南的桥不仅是古镇的一道别致的美景,更多的时候它承载了江南的历史、江南的风俗以及江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三)街巷。江南水乡素有“流水周于舍下”“车从门前入,船从后院出”的场景描述。河岸、水景构成江南古村镇建筑景观环境的主体脉络。因水成市、因水成街,水街相依,水路与陆路交织,交通与生活合一,水巷和街巷构成了江南水乡城镇整体空间系统的骨架。街巷与水巷的主要交汇点是各式桥梁,水陆交通的节点多为休闲广场式的重要集聚场所。可见,街巷是江南水乡建筑景观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人们文化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民居建筑。江南水乡建筑以其特有的水环境为依托,不仅在建筑本体的结构形制上精美绝仑,而且从多方面显现出清新淡雅的江南韵味。江南地区文化底蕴浓厚、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建筑受封建伦理、儒学传统、风水习俗的影响,在空间布局上尽量发挥地域优势,最大限度地体现天人合一的亲自然营造理念,形成了高低错落、秩序井然的建筑群体风貌,创造出了质朴典雅的独特建筑风格。
1.建筑布局
(1)由单条河道形成的带状古镇,这种城镇一般规模较小,建筑整体布局由一条河道呈线性延展,如江西婺源李坑。(2)由十字形河道形成交叉式星形城镇,规模较前者略大,城镇布局多是四方延展态势,并具有纵横交错的水运交通条件,如南浔。(3)由网状河道形成的团形城镇,此种为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江南水乡古镇平面布局形态,其规模较大,建筑布局也较为丰满完整,多为商业繁荣、经济发达、人流集中的中心聚集区,如江苏周庄、同里,浙江乌镇、西塘。
2.建筑特点
(1)结构:以传统的硬山式样为主,多为穿斗与抬梁混合式构架。一般中部的构架(正贴)为抬梁式,山面的构架(边贴)为穿斗式。基础采用石材,墙体一般采用空斗墙。(2)高度:建筑层数一般以一两层为主,偶尔也有多层者。(3)色彩:建筑整体风格多为灰白色(无彩色),素有粉墙黛瓦之称,色彩面貌相对朴素淡雅。(整理4)用材:建筑用材多以地方性优质木材为主,不拘泥于一种选材形式,并有“才分八等”之选材、用材标准。斗拱的用材等级较高,梁柱则次之。建筑主体结构采用木结构,围护结构采用砖石结构。
江南水乡建筑无论从外在的表层形态,还是蕴涵于建筑内部的深层文化,都着力诠释中国传统营造学与古代哲学的高度统一,并蕴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历史文化韵味。
二、江南水乡名镇品读
(一)梦境水乡,烟雨西塘
西塘古镇地处江、浙、沪三市交界处,属于浙江嘉兴市,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就有“吴根越角”之称。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在唐宋年间就建成大量村落,人们沿河营造房屋,依水聚居生活;南宋时期村落规模基本形成,并逐步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荣;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这里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清代中期徽商东进,将徽派建筑文化带到太湖流域,出现许多带有风火墙的建筑,并在民间营造活动中,将原来徽派建筑中平直的墙体改造成马头形,衍生出了“马头墙”。
西塘素以弄多、街多、廊多而闻名,古镇中最著名的风景线是一道长达千米、造型古朴的廊棚。西塘的廊棚多为沿湖河营建的砖木结构建筑,黛瓦盖顶、青石铺路,木构架结构配以休闲长凳,既可驻足观景又可遮风避雨。连续性的沿河式轴向布局在烟雨中依稀可见,使人心情愉悦。此外,西塘的河埠、高阶沿、观音兜也从不同层面上构成了西塘建筑形制与景观布局的诸多特点。
西塘是儒商文化与平民文化的交接点,其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人才辈出,无论是建筑形态还是水岸景观布局,无一不显现出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美丽乡村,生态婺源
婺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山区,东临浙江衢州市,南通上饶,西接景德镇,北临黄山,古为文风鼎盛之所,今为皖、浙、赣三省交通要地。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婺源因“地当婺水之源”而得名婺源,隶属安徽歙州。宋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婺源基本上隶属于安徽徽州。虽然在1949年5月1日以后划归江西至今,但由于长期历史文化的积淀,这片地区无论是村庄的选址布局还是民间建筑形制,无论是生产生活习惯还是民俗民风,都带有明显的徽派风格特征。
婺源,山清水秀,素有“八分半山一分天,半分水陆和庄园”之称,是典型的江南古镇。当年徽商营造的村落与壮美的自然景观相交融,形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山水画卷,著名的古村落李坑就是婺源乡村的典型代表。婺源的村落布局讲求背山面水,李坑村落的选址就遵循了这一原则:四周群山环绕,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村外两条山溪在村中汇合为一条小河,河流两岸粉墙黛瓦的古建筑鳞次栉比,布局有序,形态优美。河上建有石、木、砖各种桥梁数十座,形成了便捷的人流交通路径。另有“两涧清流”“柳碣飞琼”“双桥叠锁”的景致在其中。秀美的山光水色与古朴的民居建筑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构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风景画。李坑村的民居沿村中溪流为主轴线布局,溪流的自然走向与两岸的古建筑混成一体,形成了“沿溪而息、大吉大利”的水岸建筑景观。其古民居形制与其他徽派民居建筑一样,为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结构,屋面灰色筒瓦、硬山顶、马头墙,整体色彩以黑白灰为主,体现出古朴淡雅的视觉美感。
(三)生态之源,水韵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黔县西北角。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汪氏六十六世祖汪彦济历经二十年建成十三间楼,定名弘村。清乾隆二年(1737年)改名宏村。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汪氏七十六世祖汪思齐、胡重夫妇率族人挖水圳,引来西溪水,掘月沼,建村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汪氏后人历时三年,于村南掘成20247平方米的南湖,形成了集生活饮水、农田灌溉、防火浣汲、游览赏景于一体的古生态水系景观。
宏村古民居建筑布局堪称徽派民居的精品之作。古镇以月沼为村心,形态雅致的古建筑绕水环峙,建筑与水景构成了虚实得当、形影相随的视觉效果。月沼如明镜,镜中见景、古意盎然、景色别致。宏村的南湖横跨东西,环堤古树,水绕古宅,石桥小径,风荷月影,诗画意浓,可谓是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有机融合。
宏村的建筑与街市更能反映出徽州民居的极致特色,其中承志堂、南湖书院、三立堂亦是建筑中的精品。宏村的古建筑多为两层,偶尔也有三层楼。结构以明三间为主,最大创新设计在于其“廊步三间”的设置。宏村的古建筑尤为重视大门口门楼的营造,古人云:“宅之受气于门,犹人之受气于口也,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因此,“千斤门楼四两屋”的说法造就了宏村古建筑各色精美绝伦的建筑门楼。宏村的古巷纵横交错、曲折迷离,幽深狭长的石巷与两侧高耸的马头墙形成了空间尺度上的对比,显现出古巷森严的空间层次感。宏村古建筑中最具特色和神秘感的就是天井,大小天井,通风采光、日易月移、秋霜雨雪,皆得益于“天人合一”之灵气的天井。水枧接雨水,四水归明塘,暗沟排水、通风、采光、理水均达到精致绝美的水平。另外,宏村古建筑的三雕艺术更是中国古建筑艺术中的奇葩。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悠长的情结、朴实无华的民风,一并诠释出宏村的特定文化内涵和巧夺天工的技艺,并使人叹为观止,赏心悦目。
江南古镇建筑在长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与其特定的地域性特征相适应的建筑形态,并烙上了深深的历史文化印记。无论是建筑总体布局还是建筑本体形态、细部装饰,无论是水岸景观的营造整理还是商业街巷的形成,无不体现出江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道法自然的传统哲学思想。
江南范文篇2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课本上关于《哀江南》的介绍。《哀江南》选自《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这个“余韵”相当于现代戏剧或小说里的“尾声”。既然课文选自“尾声”,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全剧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
师:同学们通过预习了解到,《桃花扇》这个名字里的“桃花扇”象征着爱情。《桃花扇》也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我们刚刚学过《长亭送别》,现在就来比较一下《桃花扇》与《西厢记》在故事情节上的异同。我们一起来看投影。(投影1)
师:古典戏剧在爱情题材上基本都遵循着一个基本的故事情节模式。第一步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西厢记》里的张生与崔莺莺是这样,《桃花扇》里的侯方域与李香君也是如此。侯方是明末名士、复社文人,在文化界和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李香君是秦淮河边的名妓,色艺双全,才艺俱佳,两人果然是一见钟情。第二步是“风云突变,节外生枝”。美好的爱情注定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侯李二人生不逢时。明末崇祯皇帝即位后着力整顿朝政,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代中兴之主。他清除魏忠贤,魏忠贤余孽四处流。有一个流窜到南京来的阮大铖,如丧家之犬,急着要与以复社文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修复关系。明末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他抓住侯李成婚的机会,给侯方域送了一份厚礼,但是却遭到李香君的拒绝。句古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这话用在李香君身上就很不公平,李香君是个很有气节和见识的女子。李香君的拒绝在侯李与阉党余孽之间埋下了矛盾的伏笔。正在这个时候,李自成入京,崇祯皇帝带着他的后妃女眷自尽了。作为陪都的南京,就上演了一出立新主子的闹剧,结果阮大铖这些阉党占了上风。他们成了一个偏安朝廷。历史上的东晋和南宋都是偏安朝廷,毕竟还做了一些复国土的努力。这南明王朝却只顾窝里斗,只顾争权夺利,醉生梦死。于是,侯李的苦难也就开始了。侯方域被逼逃亡,李香君先是被逼改嫁他人,不从,以死相拼,血洒宫扇。这扇子便是侯方域送给李香君的定情之物。有人稍加点染,勾勒成“桃花”样子,这便是“桃花扇”的来历。这就是第三个阶段,我把它叫做“一波三折,苦苦相争”。侯李二人对爱情忠贞不屈,苦苦相思,与张生崔莺莺无二。
师:大家知道,张生与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就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大团圆”结局。那么,《桃花扇》是这吗?
生1:不是。侯方域与李香君最后虽然相见,最后却又分手,两个人双双入道了。
教师:知道为什么吗?
生1:好像是国家灭亡了。有一个世外高人指点他们,他们意识到连国家都没有了,爱情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醒悟了,就出家了。
师:是啊。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个高人是怎样点拨这一对男女的。(投影2)
师:就是这句话叫两个痴情男女幡然醒悟。原来,正当侯李二人双双沦落的时候,清兵南下,南京岌岌可危。阉党和他们的主子仓皇逃亡。国家亡的时候,侯李二人却大团圆了。从爱情的角度来看,他们终于修成正果,但是孔尚任却让这一对男女双双入道,可见作者另有寄托。这就是“课文导读”里提到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戏剧表现的重点是“兴亡之感”。
师:知道了故事梗概,我们就来看课文。课文由宾白与曲词两部分构成。中国古典戏曲以唱为主,所以“白”叫做“宾白”,“宾”就把“”的作用讲得很清楚。这与西方尤其是古希腊戏剧不同。古希腊戏剧以“白”为主,而“唱”(合唱队)往往作背景而出现。但是,“宾白”是戏剧的有机部分,读曲品曲必须注意宾白。我们来读这段宾白。我想请三位同学来诵读这段宾白。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声音比较适合朗读这段宾白?
众生:沧桑的/悲伤的/低沉的/成熟的……
师:是啊,虽然我们都还不够成熟,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沧桑,但我们可以揣摩人物的心态,体验人物的情感。情感的体验是可以超越时空和年龄的。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配乐,名字叫“哀郢”这是根据一首同名诗谱写的曲子。这是谁的诗作?
生2:屈原。“郢”是楚国的故都。这是屈原在秦国灭亡了楚国后因怀念祖国而写的诗歌。师:这个同学知识面很广。曲子表达的也是深沉的亡国之悲。曲子用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演奏。当代作家贾平凹说过“埙”能表现旷古的悲凉与沧桑。现在我们就在配乐朗诵中体验这旷古的悲哀和绝世的伤感。(生分角色朗诵)
师:在朗诵中我们可以体验出人物的心情。读宾白,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这段对白中出现了哪些人物,他们的身份分别是什么?
生3:苏昆生,樵夫;柳敬亭,渔翁。还有一个老赞礼。
师:要注意“渔樵”二字的组合。你们在哪篇文章里见到过这种组合?
生4:《赤壁赋》。“渔樵于江渚上,侣鱼虾而友麋鹿”
师:对,“渔樵”在汉语里本来就有隐逸的意味。推荐一支古曲《渔樵对话》,也是表达逍遥、遁世、逸的。值得一听。
师:第二个问题:苏昆生诉说自己的所见所闻,他在南京究竟过哪些地方?
生5:明孝陵,明故宫,长桥、旧院等秦淮河一带。
师:他的情是什么样的?
生6:哀,恸,还有伤心。
师明白了这些,我们就来读以下七支曲词,看看下面这些曲子是怎样与宾白的这些信息对应的,又是怎样表现这种“哀”“恸”与“伤心”的?我们先来一起朗读,读的时候思考一下,这七支曲子在抒情方式上有什么不一样。
(齐读七支曲词)
生7:前六支曲子是间接抒情是寓情于景,第七支则是直抒胸臆,所谓“放悲声唱到老”,也就说明了抒情时不加掩饰,痛快淋漓。
师:很好。既然是“放悲声唱到老”,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放声朗读第七支曲子,如何?
(生齐声再读第七支曲词)
师:这段里哪些句子最能打动你?
生8:“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师:这是“谁”在“看”?
生8:苏昆生。
师:好像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他以这样一个局外人的语气来表达,说明他对南明王朝的极端恨和失望。
生8:统治者忙着醉生梦死,忙着大兴土木,忙着穷奢极欲,挥霍享乐,也正是这些忙碌,决定了他们必然灭亡,讽刺了南明这个短命王朝的必然命运。排比句给人一种很急促的感觉,好像历史盛衰在一瞬间发生。
生9:“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最让我感慨。我想起了刘禹锡的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物是人非。莫愁湖是那时南京的繁华市区,现在却了无人烟,晚上只有鬼哭了,很恐怖,很阴森。前后对比,叫人感慨。
师:两位同学的分析很到位,让我们心里很有感触,我们再来读一遍吧。
(生齐读)
师: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前六段,鉴于时间关系,我们做一个分工。每个人选取自己最欣赏的一段来谈谈,作者是怎样表达那个“哀”“恸”与“伤心”的?
(学生读书。思考。组织表达语言。)
江南范文篇3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的材料和已发表的论文表明,用“到”类字作持续体标记的方言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普遍分布在吴语、湘语、赣语、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区的多数方言点,闽语、粤语、客语区也有分布。长江以北的部分四川、重庆方言也有表持续的“到”,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的湖广移民传去的,是受长江以南的方言影响造成的。主要用字有“到[tau0]”“倒[tau0]”“哒[ta0]”“得[te0]”“底[ti0]”“的[ti0]”“老[lau0]”“牢[lau0]”等。这些持续体标大多数可以同时用作完成体标记,本文只论述它们表持续的用法。例如:
(1)江西南昌话:坐到[tau0]吃比站到吃好些。
(2)湖北武汉话:他先找了老张,跟倒[tau0]又找了小李/他站倒说
(3)四川成都话:莫得活路做,只好在屋头耍倒[tau上声]/他说倒说倒就哭起来了
(4)贵州贵阳话:好好听倒[tau上声]/围倒他要糖吃/讲倒讲倒的笑起来了/顺倒
(5)安徽宿松话:椅到[tau上声],不要动。
(6)湖南华容话:手抓倒[tau上声]绳子!/你顺倒这条路走
(7)浏阳话:钱留倒[tau0]搞么哩?留倒讨婆娘/桌上放倒一本书
(8)临武土话:含到[tau上声]眼泪/坐到咬好,还是椅到咬好
(9)沅陵乡话:他牵倒[tao0]那条牛/望倒吾笑/坐倒[tau0]食比竖到食好
(10)广西柳州话:张老师上到[tau上声]课,你等一下/想到想到自己都好笑/按到他讲的去办
李蓝认为西南官话贵州话表持续的“倒”的本字是“到”。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卷的描述,在“到”读成“倒”的地区,方言轻声都不明显,口语中词后缀常是重音或中音,调查者将“倒”多记作53或54调值,实际上,上述地区后缀“倒”发音短暂模糊,相当于普通话的轻声。在普通话里,动词后的结果补语“到”就是读轻声的(如“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另外,在古代汉语中,“倒”是“到”的通假字,“到”记作并读成“倒”不足为奇。
除“到”外,江南表持续的体标记还有“哒[ta]、得/的[te]、底[ti]、老[lau]、牢[lau]”等。如:
(11)湖南长沙话:你跟我徛哒[ta0]/坐哒看书/治哒治哒就治好哒/照哒咯条路笔直走
(12)辰溪话:我向哒[ta上声]他在/车子上装哒好多萝卜/讲哒讲哒在就困着了
(13)山西武乡话:他点的[te0]灯作饭咧/门口立的一大群人
(14)湖南江永土话:义老大再复记倒[lau阴上]了“好吧”/跪倒
(15)江苏苏州话:对牢[l?覸阳平](对着)
(16)浙江杭州话:对牢[l?蘅阳平]/我扶牢你走/你坐牢不要动(以上例句来自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
上述例句出现的持续体标记,处于“动词+X+处所名词”或“动词+X”结构,表示动作本身持续或由动作所产生结果的持续,本身没有词汇意义。
江蓝生认为“动词+X+处所名词”结构中的X位置上的“得”“的”“底”是介词“著”语法化过程中产生的由舌上音读作舌头音的逆向音变,但多数学者认为该结构中的“得”“的”“底”源自介词“到”的轻读音变。石毓智认为: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常会导致其语音形式的弱化。就汉语来说,语音弱化表现在声调的失落、韵母的简化或者央元音化、声母向舌尖音靠拢等。“到”的弱化方式如下:“到[tau]”失落韵尾→“哒[ta]”→央元音化→“得[te]”→元音高化→“底/的[ti]”,或者按另一种方式弱化:“到[tau]”声母边音化→“牢[lau]”→失落韵尾成“牢[l?覸]”→元音后高化成“牢[l?蘅]”。本人认为后种解释与历史音变方向相符,应该可信。而且,在第一部分的方言例句中,“到”除了表示动作的动程和方向外,由于前面的动词表示的动作本身或动作产生的结果都是可以持续的,它还可以表示动作后的状态或结果,具备“在”的语法意义。因此“动词+X+处所名词”结构中X位置上的“到”具备这两种语法意义,表持续的体标记“哒[ta]”“得[te]”“底[ti]”“老[lau]”“牢[lau]”等与“到”的语法意义一致,实际都是“到”语法化过程中在不同方言点的语音弱化现象。
三、持续体标记北方方言中的持续体标记“着”“子、之、仔”的分布
梅祖麟认为北方方言中持续体标记“之、子、仔”是方言记音字,本字是“着”,因此,“着”“子、之、仔”实际上是同一字的语音变体。
罗自群在《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中的研究显示,持续体标记“着”“子”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汉语方言里,如北京、河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宁夏、青海、安徽、江苏等地,用法与普通话中体标记“着”的用法相同,都用在动词和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例如:开着会/低着头说/门开着/矮着一大截/围着一群人四、有关现代汉语南北方言持续体标记不同的原因讨论
持续体标记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动词演变而来的,是一个实词进行一系列语法化的过程。从理论上说,语法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任何一个虚化成分只要其语法化程度没有达到极限,都有再语法化的可能。
根据何乐士等学者的研究,动词“到”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是从春秋-两汉时期开始的,而动词“着”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则是在魏晋南北朝,并且当时它的语义和语法作用相当于趋向补语“到”。石毓智指出,每个动补结构从句法关系变成形态关系都需要一定长度的时间和特定句法环境,一个动补结构出现的时间决定了它形态化的早晚,出现早的动补结构形态化的时间也早。我们不妨推测,体标记“到”的产生应早于“着”。历史语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李讷、石毓智的研究,“真正的表示进行态的‘着’在宋代还没有出现,其用法还只限于‘存在’和‘两个动作同时进行’……这时期表示状态持续的用法也已经有了”。例如:
(17)百理具在,平铺放著(《二程集》)。
(18)人虽睡著,其识知自完……(《二程集》)
“着”真正表示动态行为的正在进行的用法元以后才逐渐出现,例如:
(19)见他战笃速惊急列慌慌走着(《陈季卿悟道竹听舟[元刊]》)。
(20)冯妈妈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金瓶梅》三十八回)。
(21)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红楼梦》三十三回)。
北宋时期,持续体标记“到”已经出现,并见于官方文献中,并一直延续至现代南方汉语方言:
(22)臣等窃闻昨夜萧禧在驿,与馆伴执到白札子商量王吉地、义化辅、黄嵬大山、石长城、瓦窑坞等处已定(《乙卯入国奏诸》)。
(23)帖黄。……臣等早来赞资政殿进呈白札子一道,并续签帖到事节,谨具缴连进呈(《乙卯入国奏诸》)。
持续体标记“到”的轻读音变形式“地”“得”“的”“底”在宋以后更是大量出现:
(24)只见他在那里住地,依旧挂招牌做生活(《碾玉观音》下)。
(25)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简帖儿来,与他浑家(《简帖和尚》)。
(26)赵宣子齐整穿了朝服要出朝去,看天色尚早,端坐的堂上,十分恭敬(《皇明诏令·武士训戒录》)。
(27)西门庆已在前厅坐的(《金瓶梅词话》)。
(28)在屋里坐的听唱(《金瓶梅词话》)。
(29)那河边住的塔塔儿一种人(《元朝秘史》卷1)。
就持续体标记“着”产生的地点来说,应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区产生,原因是:以“着”为代表的持续体标记在现代方言里主要分布在北方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兰银官话等北方区域。由于北方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体标记“着”虽然在元以后才逐渐出现,但代表官话语素,加上官话方言是一种整合力较强的语言,所以“着”在近代汉语助词系统内部的调整和规范中胜出,成为元以后持续体标记的书面用字,广泛见于近代白话小说。
曹广顺认为在唐五代动态助词(即体标记)产生的初期,大多数助词都有相似的发展过程,造成了某些助动词在表示动作获得结果、完成、持续等几种功能上的重合,后来经过调整和规范,恢复了平衡。唐五代动态助词产生初期,表示持续态也许主要是由现代方言中存在的体标记“到”“起”“住”“紧”“着”等共同担任的,但多个成分担当同一个功能,与语言简明、精密的要求相背离,造成了系统内的不平衡,所以必须进行调整。调整的结果,由于南方所处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封建势力的割据,南方方言往往呈现出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持续体标记并存的情况,比如说,在湘语区,“哒”“倒”和“起”可能并存;在吴语,除了用动词后面加介词短语的形式表示持续意义以外,一些地方还有使用“仔”或“倒”的情况;在粤语区,“紧”“住”和“倒”可能并存;在客家话中,“紧”和“稳”可能并存、“紧”或“稳”和“倒”可能并存;而由于北方地形的平坦、交通条件的便利和政治上的相对统一,北方方言的整合力较强,许多地方只用一种持续标记。
为什么持续体标记“着”在江南没有得到大量推广呢?
根据刘晓南和大多数方言学家的观点,历来南方方言的形成是受北方影响,南方方言代表了较早的汉语方言层次,北方方言代表了较新的汉语方言层次。由于持续体标记“到”比“着”产生得早,随着历史上几次规模较大的北方移民南渡长江,先于持续体标记“着”传播到了广大南方地区,显示了汉语方言较早的历史层次,而持续体标记“着”反映了汉语方言较后的历史层次,是汉语后起的用法。我们可以从以“到”为代表的[t]声母的持续体标记(如“到、得、的、底”)遍布全国现象找到这一推测的证明。而自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中原移民不再发生,代之以由东至西的移民,南北方言进入了自身内部发展演变时期,现代汉语中出现这种持续体标记分南北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唐五代—宋朝时期是近代汉语助词体系形成、新助词全面产生、调整并稳定下来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产生时间、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移民先后和方言的影响力等因素的不同,南北方言持续体标记呈现不同分化:北方趋向统一,以持续体标记“着”为主;南方呈现多样,以持续体标记“到”分布最多最广。
参考文献:
1.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载《语言研究》2004年第1期。
2.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武汉、成都、贵阳、南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李蓝:“大方话中的‘倒’和‘起’”,载《毕节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4.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载《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第3期
7.何乐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8.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
9.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石毓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刘晓南:“中古以来的南北方言试说”,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2.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刘进:“汉语语法化理论综述”,载《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
14.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江南范文篇4
【关键词】民俗文化;保护视角;江南古镇;旅游发展
江南古镇是当前我国古镇旅游的重要地区,以周庄、乌镇以及西塘作为代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宣扬了优秀的民俗文化和旅游文化,形成了浓郁的水乡文化、古建筑文化等。但是在古镇旅游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因此,本文针对当前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从民俗文化保护视角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为江南古镇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和依据。
一、当前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江南古镇属于特色旅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具有很强的古文化底蕴,但是受到传统经营模式的影响,存在不少对问题,严重降低了江南古镇旅游发展的价值,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下面主要针对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存在的的问题展开论述。
(一)缺乏科学的规划
在当前江南古镇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制定长期合理的发展规划,存在过度开发和重复开发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江南古镇旅游业日益繁荣,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当地人们的收入。但是在旅游资源过程中,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无法满足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破坏了原有的民俗文化。并且江南古镇具有优秀的历史文化内涵,由于当地政府没有站在整个地区旅游业发展战略的全局,对当地旅游文化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论证,导致不同地区各自为战,存在大量重复开发和重复建设的问题,对江南古镇旅游未来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为了发挥江南古镇在旅游业中的重要的作用,当地政府要整合当地旅游资源,融入更多的民俗文化,大力发展特色民俗文化旅游业,进一步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价值和商业价值,推动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江南古镇民俗旅游产品开发比较单一
对江南古镇而言,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不仅要创造丰富的旅游内容,而且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激发游客的旅游动机。但是在当前民俗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旅游产品开发比较单一。以西塘古镇为例,民俗旅游产品开发占有整个旅游业产品价值的25%,而香港旅游民俗产品的价值却占到了60%以上。由此可知,在我国古镇民俗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产品开发价值比较低,主要由于江南古镇民俗文化商品开发品种单一,不能体现当地民俗文化的特点,对民俗文化旅游商品价值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而言,可以体现当地民俗特色和特有的地域文化,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帮助江南古镇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根据江南古镇旅游业发展现状,没有建立完善的旅游开发体系,旅游民俗文化产品生产基础比较薄弱,缺乏创新意识,不能充分体现当地特有的民俗文化。在当前江南小镇民俗旅游文化开发过程中,旅游文化商品经济收益水平比较低,发展阶段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导致很多民俗文化工艺品做工十分的简单,存在同质的问题,并且质量差,缺乏地方文化特色。有的古镇民俗旅游产品依然以土特产为主,涉及民俗文化产品种类比较差,含金量比较低,让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脱离当地的特色和个性。再加上当地人不重视对民间艺术传承不重视,没有真正把民俗文化转化成产品,影响了江南古镇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江南古镇民俗资源产品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的开发,积极打造民俗文化品牌,提升旅游价值,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
(三)受到大众旅游的冲击
近些年来,江南古镇旅游日益兴盛,提升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能力,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并且形成了特色旅游文化。但是在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江南小镇传统的封闭性被打破,提升了我国旅游的开放程度,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他们把固有的民俗文化带到江南小镇,对当地的旅游民俗文化产生非常明显的冲击,让江南古镇特色文化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和特色,从个性逐渐走向共性,降低了旅游者对江南古镇的好奇心,对当地原有旅游文化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文化损失。对江南古镇而言,民俗文化的旅游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具有很高的文化开发价值,但是在实际开发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的限制因素和不利因素,江南古镇旅游管理单位需要针对当地实际情况,针对民俗旅游文化开发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明确自身民俗文化发展目标,推动当地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俗文化保护视角下的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对策
为了体现江南古镇旅游特色,在江南古镇实际发展过程中,当地需要重视对传统优秀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开发,进一步整合和优化当地资源,推动传统旅游业朝着更高水平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因此,下面主要针对民俗文化保护视角下的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对策展开论述。
(一)打造具有民俗文化特色江南古镇
江南古镇在发展旅游过程中,需要在开发商业经济价值的同时,重视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以周庄为例,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经过长期的发展,商业日益繁荣,逐渐形成了江南河街式贸易集镇,因此,对周庄而言,需要深入挖掘和保护传统的贸易文化,继承优秀的经营模式,体现当地特色民俗文化。乌镇具“诗画乌镇”的称号,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茅盾先生的《林家铺子》就是描写民国时期的乌镇,这可以作为乌镇对外宣传的文化品牌。西塘从自由生活进行定位,游客通过自己游览当地的民俗文化,比如河岸边洗菜的人们、古色的建筑以及如画的人文风景。因此,在江南古镇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从而民俗文化的角度出发,进行重新的文化定位,积极打造特色古镇,既要忠于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又要体现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创造特色民俗文化,做好宣传,提升江南古镇的核心竞争力,在保护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旅游价值。
(二)不断加强政策支持
就目前而言,我国旅游业发展主要是在政府主导和支持下进行的。因此,当地政府需要针对江南古镇的特点,进一步完善指导职能,建立完善的旅游管理法律条例,加大对传统旅游项目开发的监管。同时政府要为当地旅游民俗产品和文化开发提供保障,增加资金方面的支持,为江南古镇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要发挥行政协调的作用,针对江南古镇旅游开发建立专门的旅游可持续发展促进委员会,做好当地旅游发展开发审批许可的管理,制定民俗文化旅游的保护规划,积极扶持特色文化旅游项目,对江南古镇旅游工作进行全面的考核。另外,当地政府要做好基础调研工作,从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全局进行宏观方面的指导和监督,进一步协调地方旅游管理之间的关系,整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降低能源消耗,推动当地民俗文化旅游行业的良性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提升江南古镇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三)不断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江南古镇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制定长远的发展目标,坚持“大产业、大发展、大旅游”的理念,进一步推动当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产业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企业联动性作用,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对旅游服务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延伸江南古镇民俗旅游产业链,从而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有效提升江南古镇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做好民俗文化保护工作。同时当地旅游企业需要根据政府制定的产业化经营策略,建立具有丰富旅游功能的产业化集团,针对民俗文化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做好民俗文化宣传工作,建立极具特色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推动旅游业的市场化发展,实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良性循环,从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四)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
江南古镇包含丰富的优秀民俗文化。因此,政府要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制定长远的开发计划,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做好调查工作,然后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针对已经遭到腐蚀或者破坏的民俗文化,当地政府需要采取紧急补救措施,最大限度对原有的民俗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在进行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坚持完善的开发管理机制,规范开发程序,防止出现过度开发的问题,避免对民俗文化产生二次破坏。因此,对民俗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当地政府要针对江南古镇的特色,把保护工作贯穿旅游业发展全过程。另外,针对民间民俗文化,比如民间舞蹈、手工艺以及民间戏曲等,在这些民俗文化传承过程中,政府需要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分类和整理,进行集中的管理,提升民俗文化资源管理的长久性,从而带动当地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当前江南古镇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民俗文化保护视角下的江南古镇旅游发展进行分析和论述,然后针对实际的问题,提出开发保护策略,进一步打造具有民俗文化特色江南古镇,推动民俗文化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丽敏,黄震方,曹芳东,周玮.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J].地理研究,2015(03)
[2]胡旺盛,谭晓琳,潘理权.古镇旅游真实性感知对游客行为意向影响研究———以安徽三河古镇为例[J].财贸研究,2014(06)
[3]黄睿,曹芳东,黄震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文化古镇旅游商业化用地空间格局演化———以同里为例[J].人文地理,2014(06)
江南范文篇5
关键词:江南水乡;建筑元素;餐具设计
一、背景
江南水乡,一个依水而立,依河而存的地方,其各种文化无不与水密切相关。自从江南水乡出现建筑以来,各方学者都对水乡建筑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文化价值无疑是社会的富贵财富。陶瓷作为一种餐具,与中国文化相生相承,民以食为天,故它与生常生活最为密切,将餐具融入特色的地域性文化要素,既可以让当地文化传播,又可以丰富人们的审美价值。尤其在打造江浙菜系品牌,扩大江南水乡古镇的影响力上具有重要作用。
二、水乡建筑文化概述
水网密布,或呈线型,或呈十字型,或呈网状形,河流或深或浅。“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清代诗人阮元通过古诗描绘了一幅江南美景图,描述了江南水乡的地域特色,可以说是水造就了江南建筑形态的基本样式。在这种样式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临水而筑、形体高大、粉墙黛瓦、黑白相间。“粉墙黛瓦乡村画”是六大古镇民居的真实写照:白色的类似马头一样的墙,青色黛色的瓦片,排列得紧密而有秩序,两边檐牙高高翘起,建筑建造在一起,形成了高与低的对比,黑与白的对比。粉墙黛瓦的古镇民居建筑,给人以婉然一新的视觉感受;尤其是黑与白的简单色调,构成了古镇简单的美景;这些建筑与河流配合在一起,透明与不透明相协调,极具美感。[1]江南水乡的建筑与北京的四合院部分相似,但由于江南水网密布,错综复杂,所以建筑在形态和元素上更多了一些个性。江南的气候也相对潮湿,故底层多为砖墙或大块条石,上层以木材为主,多为雀替和斗拱之类结构作为支撑。以上多为民居建筑,江南园林建筑也是一大特色,但基本建筑结构与民居建筑大同小异,也具有瓦当、直棂窗、硬山式屋顶或者卷棚式屋顶、院墙等要素。[2]小桥流水人家、亭台楼阁以及黑白灰色彩的砖墙成了水乡建筑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三、餐具设计中水乡建筑文化元素的具体应用
纵观当今的餐具,造型上千篇一律,在纹样的装饰上过于随意,不能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色。江南水乡建筑文化以其优雅淡然的风格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示出一种简约不张扬的格调。此外,饮食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多样化使得人们更多的追求餐具的别样。[3]针对当下餐具少有兼具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的情况,寻求新的设计语言来对餐具加以修饰,设计出既满足功能需求又有独到的文化特色的餐具是很有意义的。[4](一)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元素的提取。1.纹样我国传统纹样也极富象征性,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它既可以表达自然情趣,也可以表达文化内涵,历史观念形态以及人文精神。从动态的角度来说,传统纹样的意义在于,随意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它更多的以装饰图案的形式存在于物体之上。[5]在不同时期内所表达的意义不完全相同。江南水乡的建筑主要用三种构成要素,一是瓦片,二是窗框,三是砖墙。(图1)粉墙黛瓦构成了水乡建筑的主体,木结构的门窗完善了建筑的具体构成。瓦片的排列体现了空间上点线面的基本构成。“点”是平面构成造型元素的基本要素[6],一片瓦可以看成“点”,一排瓦在形式上主要以“线”的特征出现,而且这种“线”在整个房屋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一排排瓦构成了建筑的顶面。无疑,取瓦片纹样运用于餐具是理想的选择方案之一。古典园林建筑中的窗“隔而未隔,界而未界”,体现了古典造园的思想,更彰显了窗在古典建筑中的重要作用。[7]窗棂上的图案蕴含了江南水乡建筑古色古香的气息,运用于餐具纹样设计中,可以带来浓厚的文化审美情趣。古典窗棂的图案形态各异,各有喻义,因此被广泛地运用家具、产品和包装设计之中。因此将这些元素融入餐具设计当中,或许也可以为餐具的气质增添一笔光彩。砖是江南水乡建筑运用得最多的材料,不加掩饰的砖墙由一块块青砖交错叠加,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就是像一种自然天成的纹样,简约而不简单。2.色彩江南水乡的建筑主要以青砖黛瓦白墙为主。江南古镇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文荟萃的地方,就古镇之一湖州而言,古时曾因“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而扬名天下。文人墨客用书画传达情感,书画作品也以黑白为主。而陶瓷餐具以白色为底,再加上黑色和白色的点缀,可以更好的突显江南水乡的建筑情调,从这个角度来说,黑白灰是永不过时的色彩。如果说线表达的是一种基本的内心情感,那黑白灰三种色彩就是它外在的表面”。黑白灰和点线面的关系就像是内在和外在的联系,点线面是是设计餐具造型的前提,黑白灰就是餐具在完成基本形态设计赋予其装饰之意。[8]纹样的设计也同样先有点线面,后有黑白灰等色块,在色彩的表达思路上是一致的。3.造型从宏观层面看,良好的产品造型可以表达其所蕴含的特质,硬朗大气有棱角的风格表达产品的简洁干练,富有曲面形态的风格可以表达产品的优雅和柔顺,造型的目的是新的形式来满足大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以及视觉体验,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传承文化理念。江南水乡,一个隔绝世俗喧嚣,留下的更多的是缠绵的吴侬软语,以及缓缓流淌的悠悠乡水的地方,所以餐具定位风格更多的以曲面为主。此外造型也应该具有简约的视觉效果。从微观层面看,应对江南建筑存在的造型风格以及细节元素进行提炼和抽象,通过模拟建筑的整体造型、局部的结构以及装饰的图案,并将应用到餐具设计当中。就窗棂而言,江南园林窗户的独到在于它的扇形窗,而民居建筑的窗以棋盘格结构为主。瓦片呈拱形,将其反转后与餐具的曲面类似,亦可以作为餐盘造型考虑。江南建筑中还有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等多种形状的宝塔,塔檐的形状最具有代表性,包含了江南建筑瓦片和木结构特点。江南民居整体布局和四合院有些相像,但建造得更紧凑,天井是江南房屋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由于紧密而显得更加玲珑细致。江南水乡牌坊在建也同样丰富了建筑文化。江南水乡石拱桥为不可缺少的建筑物,石桥与倒影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相得益彰的美景。此外还有八卦井、石梯等水乡建筑主要要素。农家生长碧湖头,打桨真从镜里游,船虽然不属于建筑,但也是江南水乡建筑文化中所匹配的重要因素,有了船的元素,或许可以使餐具在丰富形式上增添浓厚的一笔。节孝牌坊被毁前是用吉首炮台山的青石材雕刻而成,后重建的牌坊采用的是永顺产的石材。虽然牌坊的建筑材料丰富多样,有木材、石材、砖块和琉璃等。但是由于乾州节孝牌坊地处湖南省西部的吉首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潮湿多雨。石材所具有的防潮湿,不易腐烂,坚固稳定,永久保存等特点,以及牌坊结构精简、构造合理、造型挺拔等优点都很好地迎合了纪念性旌表牌坊的特质。(二)江南水乡建筑元素在餐具设计中的方法归纳。1.形态模拟———形似形态模拟,指的是将已有的元素形态进行抽象或再设计,在本文中指的是将传统的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元素精髓通过汲取其形态的方法运用在餐具设计中。[9]例如扇形窗是江南园林建筑的典型特色,扇形意为文昌,代表地位,扇形窗体现了江南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对扇形窗造型及其装饰图案的筛选,尤其是对弧形边界曲率的调整,考虑形状在餐具设计当中的适用性是很有必要的。将扇形的直线与曲线进行适当长度恰当比例的组合,使餐具富有流畅感,既很好地突出了餐具的美感,同时也展现了江南水乡的缠绵情怀,更显现了江南水乡建筑元素的文化底蕴。以此类推,对其他的典型元素及造型也采用形态模拟的方法进行再设计,运用于餐具设计之中,达到形似的感觉。(图2)2.色彩架构———神似色彩架构指的是运用色彩的固有属性,在产品表达出该产品的原料质感,使其看上去更真实,更接近实际表达的要素。这种方法在很多表达质感的产品上广泛应用。例如在本餐具设计中,将江南水乡粉墙黛瓦的色彩感观做为设计元素,大气简约的砖形纹样整齐划一,加上利用色彩架构的设计手法,将黑白灰重新搭配运用,重现江南水乡建筑的视觉形态,黑色的瓦片、青灰的砖、白色的墙组成比例进行重构,让餐具看上去厚重又坚实,而且更加体现出水乡建筑的风格和水乡文化气息,达到神似的效果。3.元素再现——彰显文化内涵元素再现指的是将提取的元素通过重新解构,变换排列方法,或者元素组合方法,通过与产品本身材料的融合,突出产品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以及产品的和而不同。本设计是指将黑色边纹、灰色砖纹以及以白色打底的底色在面积比例,构成方向和元素排列上进行适当的变化,以适应于具体形态的餐具,到达和谐的效果。餐具往往为系列化或套装为主,形似神似,但不完全一致的系列餐具恰好体现了水乡建筑群落的整体性。如图为笔系列化套装产品中的菜碟和筷子。(图3)4.logo创造———丰富产品理念贤哲说:“只有是民族的,才会是世界的”。因此推广文化元素产品时,一定要注重产品所有囊括的附加体系,比如包装,logo等,在设计logo时也同样要与产品相联系,共同突显文化要素。只有多重结合,才能让产品更具有活力[10]笔者将江南水乡建筑文化餐具与logo相结合,可以更加突出产品的文化元素。笔者结合了江南水乡建筑的基本形态以及周边船,亭台、水榭等配套建筑,对细节元素进行抽象,再通过借鉴江南建筑造型,通过元素的解构和重构法设计出logo“江南”二字,此标志所采用的为江南亭台楼阁元素。(图4)
四、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在餐具设计中的价值体现
研究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对餐具设计的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诚然设计的目的也在于追求某种对应的价值,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认知,商业和审美这四方面,前者体现在视觉效果上,后者体现在对文化潜移默化的传播上。餐具设计中的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元素首先表达的是人文价值,让人们在传接受并传递地域文化的同时也感受了美食的熏陶,就江南本土百姓而言,有一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餐具装一方菜系的感觉,而对外来人来说,无意中增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让他们更加地了解江南古镇的人文和物产,当然餐具作为产品也和商业有一定的联系,被赋予文化内涵的餐具更容易获得人们的青睐,餐具被摆放在餐桌上后,商家的效益也得到一定的提升。诚然审美价值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无从造型到色彩再到纹样,再到元素细节,无不透露着江南建筑文化元素的审美价值,这也是餐具设计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重点。
五、结语
笔者通过前期的调研,中期色彩方案及纹样方案的选择与提炼,以及后期作品的完成,对江南水乡建筑文化运用于餐具设计作了浅论。诚然,在设计结束后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对元素提炼过细,造成餐具种类偏多,(如图5)这将在今后的设计中进一步研究。江南水乡建筑可以算是一种蕴含着中国风以及独特人文气息的非物质遗产,将这些具有审美情趣的元素运用餐具设计中,无疑可以将当地文化发扬光大,尤其是菜系文化,当菜系文化与产品相结合,一方面可以增加餐具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唤醒人们对当地各类文化的认知,对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丁琦.江南六大古镇文化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9.
[2]宋文.中国传统建筑图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3]韩琳,闫强.基于徽州文化的日用陶瓷餐具设计[J].艺术科技,2016,(10):10-11.
[4]李正安.陶瓷设计[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5]张蕾.浅探中国传统纹样的象征性[D].南京师范大学,2012.
[6]吴卫.平面构成(图说本)[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7]王莉莉.中国古典窗格的平面构成形式研究[J].设计艺术,2008,(11):45-46.
[8]迟茜.基于用户体验的产品包装设计策略[D].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15.
[9]汪小卉.徽文化元素在酒类包装设计中的运用[J].现代装饰,2015,(12):9.
江南范文篇6
直接导致瘟疫的致病微生物,如病毒、细菌、原虫和蠕虫等,乃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不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也是影响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因子。自人类的形成开始,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关系着人类的成长,美国著名的世界史家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曾指出:“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1]显然,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基本而深刻的,而它最直接后果不外是生病或死亡,因此,人口的损伤无疑应是瘟疫众多影响中最直接和明显的。然而,由于瘟疫乃至疾病一直是史学界缺乏关注的因素,故长期以来,这一影响一直很少受到应有的关照,以至我们今天对瘟疫究竟对人口具有怎样的杀伤力,或者对人口的成长具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基本仍是一头雾水。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瘟疫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不过对瘟疫的人口影响大多以“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等词概括之。近年来,一些疾病史研究的先行者,往往也会概略性地极言瘟疫的危害以表明自身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张剑光在其《三千年疫情》的“前言”中谈到:“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人,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2]。另外也有少数研究者开创性地对某场瘟疫的杀伤力作出了较为明确的估测,如曹树基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晋、冀、豫)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疫死率近四成[3]。这样一些笼统的记载和论述以及个别相对精确的估算,似乎都在向人们暗示,过去史学界一向忽视的瘟疫其实是历史上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它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也必将是结构性的。可以肯定,这些论述在提请人们关注疾病史的研究方面的贡献殊不可没,但它们大多缺乏确实证据的支持,不能不令人感到疑问。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历史上瘟疫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即使我们承认个别研究者论述属实,高达四五成的疫死率是非常偶然的现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等等,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清代江南是一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瘟疫发生也相对频仍的时空区域[4],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区域的探索,对目前一些论述展示的图景作出个案性的检视,并对以上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由于历史上缺乏系统而准确的人口统计,因此几乎不可能对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做出精确的判断,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挖掘现存的相关资料,并通过排比分析,对清代江南人口的损失状况作出相对清晰的说明。
首先应该指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死亡人数较多,比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已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5]。有的则病死率很低,比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间,“杭州城内,时疫流布,几于无人不病。大都发热头眩,热退则四肢发红斑,然死者甚少”[6]。而且就是同一次瘟疫,在同一个较小的区域内,比如县、乡乃至村,疫情也不是平均分布的,甚至近在咫尺,也差异明显。比如,嘉庆年间,在娄县和嘉善交界的枫泾发生了这样一则故事:
嘉庆某年,夏古圣堂巷旁有人夜卧楼上,畏热启窗取凉。夜过半,闻喁喁如人语声,楼故临街,起而窥之,不甚了了,心知为鬼,急以溺器投之,忽作鬼啸声,向南而去。既而疫大作,凡自巷以北,无一人染者[7]。
这则故事虽未必一定真实,但至少反映出,疫情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在当时是存在的。又如,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在常昭,“忽甚于彼,忽甚于此”[8]。同治二年(1863年),常熟又大疫,“人死甚众”,但《庚申避难日记》作者所在地较轻,只是“病者甚多”[9]。因此,即使是在清代江南这样一个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比较狭小的时空范围内笼统地谈论瘟疫的人口影响可能也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故还是先根据掌握的资料情况以及瘟疫本身的影响力,选择了以下九个时空点,来探析瘟疫对人口的具体影响。
1.康熙二年(1663年)松江之疫。据叶梦珠记载:
康熙二年癸卯六月至十月终,疫疾遍地,自郡及邑,以达于乡。家至户到,一村数百家,求一家无病者不可得;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者,亦为仅见;就一人则有连病几次,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若病不复发,或病而无害,则各就一方互异耳。此亦吾生之后所仅见者[10]。
这一记叙与姚廷遴在《历年记》中所述基本一致[11],姚之妻子就几度“死去复苏”,而且全家感染,“家无健人”。据姚称,上年八九月份,该地曾“疫痢盛行,十家九病”。当年,“春雨连旬,夏间甚凉,至秋疾病时行,连村合户俱病倒”。具体为何种疾病,并不明确,不过从感染率如此之高这一情况来看,是菌痢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痢疾杆菌生存能力较强,而且该病不能产生持久的免疫力,而且菌群与菌群之间无交叉免疫力,容易重复感染和复发[12]。像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应该就是可能由于急性痢疾治疗不彻底而引起的慢性菌痢患者。菌痢虽感染率较高,但预后较好。叶未提到人口死亡情况,而姚一家亦仅其年迈的母亲病故,另外其亲属中还有三人罹难。可见,这一瘟疫,虽然发病率极高,病死率却低,对人口影响也较小。
2.康熙十七年(1678年)华娄之疫。在康熙十七年前后,苏南和浙西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疫情,不过,各地人口死亡情况多未获见有资料提及,惟《阅世编》云:
又华、娄二邑,自六月望后起,至十一月,大疫。吾乡家至户到,病殁者甚多,或一村而丧数十人。予有薄田在泖上,佃户不过六、七家,病殁者男妇凡三人,大概可考知矣[13]。
六七户人中死三口,若以一般而言的每户五口计,死亡率当为近10%。一般来说,佃户生活总体上处于中下水平,疫病死亡率应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作者所在之乡这次瘟疫是家至户到,估计是全县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故华娄两县的疫死率应远低于这一数字。
3.雍正十一年(1733年)苏松大疫。雍正十一年大疫起因于上年之潮灾,始于三月,盛行于五六月,立秋后渐息[14]。是清生苏南地区一次较为严重的疫情。关于这次疫情的人口损失情况,徐大椿记载说:
雍正十年(当为十一年之误——引者),昆山大疫,因上年海啸,近海流民数万皆死于昆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气,触之成病,死者数千人[15]。
当时昆(山)新(阳)两县的人口数约为二三十万[16],从这一数字看,死亡人口最高不会超过总人口的4%。另据民国《太仓州志》记载:
(太仓州镇洋县)五月大疫,死者无算。州县令地方每日册死者之数,一日至有百数十口。因虔祷城隍神驱疫,自是递减,至立秋乃已[17]。
一日百数十口当是瘟疫流行高峰期的数字,一般高峰期的时间不会超过半月到二十天,疫病的盛行期是五六两月,约60天,如果我们设定高峰期每日以150人计,持续期为20天,另外四十天平均死亡人数为高峰人数的三分之一,即50人,则死亡人数约为5000人,与昆山的数千人一致,不过太仓州镇洋县人口较昆山少些,约为十二三万[18],人口损失率为4%左右。太仓靠海,是这次风潮和瘟疫的重灾区,因此,整个苏松地区疫死率当在4%以下。
4.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江南大疫。这次大疫流行范围较广,有关人口死亡的记载也较多,比如前引同治《苏州府志》云“死者不可胜计”,苏州的潘亦隽在自订年谱中也言“死者盈路”[19]。究竟死了多少呢?当时的一部医书说:
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莩,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20]。
当时所说的吴中,一般是指长元吴三县,当时三县的人口约为二百万[21],以累万计,说的相当模糊,但总在1—9万之间,若取其中间值5万,则死亡率为2.5%左右,最高不会超过4.5%。另据光绪《丹徒县志》记载:“乾隆丙子,岁饥,继以大疫,其时贫不能殓,死者无归者,在在多有。(陈)志学仿古人掩骼埋胔之意,率先倡设会局,……一时枯骨收埋不下二千余口。”[22]一般来说,瘟疫死者以贫者居多,但对施棺涉及面显然不能估计过高,假设实际收埋的枯骨只有无人或无力归葬尸骨的一半,而全社会有三分之一的尸骨无人或无力归葬,那么当时丹徒县的死亡人口为12000人,而丹徒人口约为四五十万[23],则死亡率在2—3%之间。如此看来,这次大疫在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人口损失率最多也不会超过5%。
6.嘉道之际江南大疫。这次大疫是凶猛的真霍乱首次光顾江南,也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和破坏最大的一次瘟疫[24]。文献中常常出现“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日尽殁者”[25]之类的记载。但到底有多少人口死亡,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据郑光祖称,常(熟)昭(文)城里在元年六月中下旬,“南门坛上一日而死数十人”,不过,总体上,“死者实不及十之一,病者则多”[26]。也就是说不到10%。而在宝山罗店,“六月氛侵入里,日渐炽,里中死者一日多至二十七人,而四乡不计也。……八月始退舍。”[27]由于感染霍乱后所获得的免疫力能持续数月,故同一年中,很少会多次感染,而且霍乱的病死率又较高[28],所以虽然各地就总个地区来说,瘟疫持续时间往往达三四个月之久,但对某个小地方来说,疫情猛烈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月,比如,常昭的“城内外莫甚于六月中下旬”,而郑光祖所在的“张墅自五月十七八日至六月初疫颇重”[29]。罗店日死27人,应是最高数字,假设该地高峰期的日死人数平均20人,那半个月为300人,再加零星死亡人数,估计100人当为合理数字,则总共400人,罗店镇上人口估计为5000人[30],则死亡率为8%。与常熟的情况接近。又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夏秋间,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31]。镇海当时人口约三十余万[32],就以九千人计,则死亡率最高也不到3%。镇海在这次瘟疫中,两度波及[33],第二次的死亡率应低于第一次,故总共不会超过4%。另外,在元和的周庄,“镇中死者日数人”[34]。周庄人数与罗店相仿,死亡率显然就应该低一些。由此我们可以大概明了,在这次瘟疫中,灾情严重地区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过10%,而一般地区,当在5%以下。
7.咸同之际江南大疫。曹树基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占70%。”[35]据曹本人的分析,战争期间,江南人口损失率为57%[36],霍乱的疫死率至少为四成。当时江南人口就以比较确定的嘉庆二十五的数字38,100,000计[37],死于霍乱的人数就在1,500万以上,这实在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字。这次大疫发生的瘟疫并不止真霍乱一种,真霍乱外,至少还包括疟疾、菌痢、类霍乱和天花等[38]。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当时真的疫死那么多人口,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真霍乱。对于战争期间江南的人口损失,曹的估计可能不算过分。那是不是疫病而死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真的有那么大?笔者结论是否定的。首先,这场大疫共波及江南78个州县中的44个,占总数的56%,考虑到可能存在记载缺失的情况,波及区域当在六七成之间。这样一来,疫灾区的实际疫死率会更高,达五成以上。然而真霍乱即使不加任何救治,病死率也不过50%以上[39]。故要达到这样高的疫死率,就必须是当时没有任何治疗,在疫区,人人染疫,而且还是真霍乱,这显然不符合史事。其次,一般来说,某种疫病对一个地区危害程度会随着该疾病对这一地区光顾次数的增加而减弱。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真霍乱首次肆虐江南时,疫区的死亡率最多也不过10%,这次对大多数地区来说,至少已是第二或第三次大流行,即使考虑到战争因素,但危害程度会超过第一次时的5倍以上,不太可能也不大。何况除霍乱以外的其他疫病,病死率都相对较低。再次,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时人并没有把瘟疫作为当时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比如
(咸丰十年)秋冬之间,大瘟疫,死者甚多。难民饿死、冻死者充满道路,盖自四月以至十一月,或杀死,或缢死,或死于水火,或死于病疫,人民几去其半[40]。
(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田坂地角及干枯丛中皆有死尸。盖自前月廿六日逃难而出,至是已二旬日,而贼犹未退,即有囊资,亦告罄矣。其无囊资者,安得不死[41]。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杭人在城者,向查门牌有七十余万口,饿死者几半,被掳者闻十二万有余,存者不过二三分而矣[42]。
自壬戌(同治元年)四月至癸丑(当为癸酉,同治二年)已逾一年,田率汙莱,数百里无人烟,土著之人幸存者十之二,劳苦病饿致死者大半,被掳及转徙死者居一[43]。
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纪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同治三年)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已[44]。
(同治三年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经理善后者设施粥局于南栅,食粥者以千计,死者每日以五六十人为率,而食者日死日增,盖以逃难者多,粮绝故也[45]。
以上文献,大都对瘟疫较为关注,然而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完全看不出瘟疫对人口损失有何特别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未予提及。从这里,我们好像只能看到漂泊和饥饿才是最为重要的凶手[46]。如果疫死率真的高达五成以上,而不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当时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例究竟有多高呢?这次疫情始自咸丰十年(1860年),同治元年(1862年)达到高潮,以后渐趋回落,延至三年而结束。咸丰十年之疫,多发生于苏南浙西一带,基本为真霍乱。沈梓记录下了当时嘉兴府濮院发生的情形。他于九月初十记曰:“是时吾镇(濮院镇)死者日必四五十人,棺木贵不可言。”十五日又云:“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阴惨之气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病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直至廿三四雨止,疫稍稀。”十月初九日再记:“是时镇上疫气稍息。”[47]可见当时濮院的疫情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从九月初六至廿四这十八天,前面言日死四五十人,后言五六十人,以50人计,共死亡900人,此后十五天渐趋减少,若以平均每日25人计,则为375人,以后当还有零星死亡人数,总计为400人。这样,濮院当年死亡人口就在1300人左右。濮院当时的人口约为9000人[48],死亡率为14%。明显高于和平时代的疫死率。沈梓在此前还曾去过湖州和嘉兴交界的乌青镇,七月,那里也发生了疫情,“每十家必有死者二”[49]。若以每家五口计,死亡率不过4%,疫情比濮院要轻得多。另在同年七月,常熟的难民营中,“有邻近移来病者,因限额不能滥收,甚至投河而死;且有疠气所蒸,十死其二、三,其余惧而他行者”[50]。这里的十死二三,显然不完全是疫病而死者,因为其言“且有”,说明疠气只是原因之一。即使我们把当时难民死亡主要原因归于疫病,假设疫死率为二成,那也只是难民中情况,从龚又村的记叙看,当地人的疫情并不严重,他家只是沾染痢疾而已。所以当地社会总的疫死率肯定不高。同治元年的疫情,总体上更为严重,比如,常熟“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51]。《庚癸纪略》七月初六记吴江等地情形云:“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52]《小沧桑记》谈松江情形:“加以疫疠盛行,日有数十家,市榇为之一空。”又曰:“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者。”[53]从龚又村关于常熟的记叙中,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当时的疫死率不是特别高,而且他自家有六人得病,仅幼女一人死亡。吴江的情形,一个县日死数十人,即使延续三个月,总人数也不会超过一万,故死亡率只会在5%以下。有关松江记载中,一家丧三四口属于特殊情况,正常的应该是一二口,以每户五六口计,死亡率为20—30%,不过还有一二成家庭为全家幸免的。故实际死亡率最多也就在20%左右,不过这也只是松江城内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县。当然,有不少县不止一次遭受瘟疫,其中嘉兴的濮院等五个地区五年中有三年以上出现疫情。每年的疫情,不可能同样严重,假设这些地区每年有10%的人口疫死,死亡人数最多也不可能超过50%。而这还是对极个别地区相当高的估计。对整个疫区来说,平均每个县受疫灾次数不会超过两次,即使以较高10%的死亡率来估计,这次大疫中,疫区因瘟疫而死的人也不过20%,而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则就更低,约15%上下。而从前面分析可看出,一般的疫死率只有5%左右,若这样,则总的也就约是8%。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8—15%之间,最高不会超过20%。也就是说,当时的死亡人口中,有二三成人死于疫病已是相当高的估计了。
8.光绪十三年(1887年)剡源之疫。光绪十三年前后,江南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疫情,疫病主要为真霍乱,特别是在浙东,显得尤为严重,当年,绍兴的上虞、山会与宁波府的大多数县都有瘟疫流行。是清代浙东疫情较为严重的一次瘟疫[54]。这次瘟疫的人口损失情况,奉化剡源的一部地方志有则较为明确的记载:
(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隄、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原注)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55]。
当时剡源乡的人口,史料缺乏记载,不过该地方志有该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村人口的详细记录,两个年代相隔14年,疫后损失应该已有所弥补,故二十七年的数字应大体接近和略低。二十七年时,三村的人口数分别为:沙隄村1,090人,公塘村820人,康岭村858人,共计2768人,全乡41,251人[56]。即使我门以略低的二十七年数字计,疫情最为严重的三个村的死亡率为14.5%,全乡则在2.4%左右。从这部方志对这次疫情的特别关注来看,这应该是当地至少是较为晚近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而且霍乱也是清代江南最为凶猛的疫病。故在和平年代10%以上人口损失率在某个较小社区中虽可能发生,但已是非常严重的。而在较大的区域中,要达到2%的疫死率已属不易。
9.清末上海之疫。上海自开埠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和人员流动的不断频繁,瘟疫爆发的频度也急剧上升,据统计,上海县在咸丰以前一共发生瘟疫16次,而咸丰以后竟多达18次[57]。晚清上海瘟疫发生的次数虽多,但对人口的危害似乎并不大。由于《海关十年报告》中录有瘟疫死亡人数确切的记载,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当时上海瘟疫的危害性。现将其中有关的记载转录如下:
在这十年(1892—1901)中,上海曾两度流行天花:一次在1893年,11名外国人和184名中国人因罹是疾而死亡,另一次在i899年的上半年,9名外国人和183名中国人死亡。市政当局对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经常给予极大的关心。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中国人、占总人口很大比重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竟能如此成功。霍乱在公共租界绝迹整整三年之后,1895年夏季又重新出现,这一次有20名外国人和约930名中国人死亡,大部分是在8月份。(公务员之家整理)
1902年流行猩红热病,这年夏天因而死亡的约1500人。随后几年,这种疾病重复出现,但严重程度减轻了[58]。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总人口为1,289,353,其中租界为617,487[59],几百上千人疫病死亡人数,实在可以说微乎其微。
经过以上分析,现在我们认为,清代江南的瘟疫对人口的危害虽然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情况下多多少少会带来一定的人口损伤。在和平年代,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较为严重的可能达到2—3%。特别严重的瘟疫,比如像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在个别较小社区中,导致的死亡率虽可达15%左右,不过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则一次瘟疫所损失的人口很难达到5%,即使连续两年或以上发生疫情,也一般不会超过10%。在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当然这里所说的比例是针对疫区而言,若要说某次瘟疫对整个江南地区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相信除了乾隆二十一年前后、嘉道之际和咸同之际这三次基本涉及全区域的瘟疫外,比率会是很低的,估计绝不会超过1%。当然有必要指出,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对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小数字。在一个较小的社区中,即便只有几个人染疫而亡,人人自危的恐惧和紧张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有关数据的估算尽管是概略性的,但应该不妨碍总体上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实际上,除咸同之际因有战争的因素外,其他像在乾隆二十一年、嘉道之际等发生全区域性大疫的年份,我们很难发现人口发展曲线有何明显变化[60]。这说明,尽管每次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其实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但瘟疫显然没有对清代江南的人口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使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的,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疫病模式[61]。清代江南除出现了前所未遇的真霍乱的打击外,总体上应该是个疫病模式相对稳定时空区域。以上所论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反而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当然,清代江南不代表一切,我们显然不能否定历史上确曾出现瘟疫大规模杀伤人口的例子。比如,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62]。但毕竟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疫病模式的稳定时期要远长于调适期。因此,尽管我们认为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而且重视历史进程疫病因子也非常必要,但并不能因此过分夸大瘟疫的影响,而应该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审慎对待它。
注释
[1]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262页。
[2]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2页。
[3]《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1页。
[4]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2000年,第34—36页。
[5]同治《苏州府志》卷149,《杂记》,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5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6册,第3516页。
[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8页。
[7]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10,《拾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1992年,第2本,第147页。
[8]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1990年,第23a页。
[9]佚名著:《庚申避难日记》附录二,《灾异记》,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4册,第599页。
[10]叶梦珠:《阅世编》卷1,《灾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11]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86页。
[12]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科技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13]叶梦珠:《阅世编》卷1,《灾祥》,第18—19页。
[14]有关这次疫情的详细情况,参阅拙稿:《雍正癸丑:烂喉痧流行的开始?》,《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待刊。
[15]徐大椿:《洄溪医案·瘟疫》,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311页。
[16]据道光《昆新两县志》,雍正初年人口数为225728人(卷6,《户口》,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本,第77页),这是赋役册上的数字,应偏低,而且,雍正十一年,无疑会有所增长,故估计为二三十万。
[17]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见“丛书·华中”,第176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6册,第1967页。
[18]据民国《太仓州镇洋县志》卷4,《赋役·户口》,乾隆二十年人口数为146894(见“丛书·华中”,第176种,第1册,第103页),故估计当时人口为十二三万。
[19]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同治九年刊本,第5a页。
[20]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406页。
[21]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长元吴三县共有丁口2,975,313(卷13,《田赋二》,第1册,第350页),按此估算,当时三县人口为二百万上下当不为过。
[2]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见“丛书·华中”,第11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册,第687页。
[23]据光绪《丹徒县志》,乾隆六十年(1795年),该县丁数为295,941(卷12,《户口》,第1册,第213页),乾隆初丁与口的比例,据王跃生的研究,为1:2.35(《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的变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6期,第17—25页),若按此比例计,则口数为695,461,故估计当时人口数为四五十万。
[24]这次疫情的详细情况参阅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立足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待刊)。
[25]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见“丛书·华中”,第457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3册,第927页。
[26]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2b—23a页。
[27]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见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6—327页。
[28]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4页。
[29]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30]宣统二年,罗店人口为54,899(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户口》,见“丛书·华中”,第172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1册,第58页),这包括农村人口。不过,“罗店市镇最巨,为全邑冠。……其地东贯练祁,运输灵便,百货骈阗,故虽处腹里而贸易繁盛,综记大小商铺六七百家,……市街凡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同上卷1,《市镇》,第1册,第50页)。就以上情况看,罗店镇区人口占全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高当完全可能。而据吴建华最新的研究,在江南多数地区,宣统年间的人口数大致余嘉庆末年的相当。(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20页。)宝山属于人口损失较少地区,估计嘉道之际人口会略少于宣统年间,故按5,000人计。
[31]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见“丛书·华中”,第478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8册,第2885—2886页。
[32]据民国《镇海县志》,宣统三年镇海人口数为320702人(卷6,《户赋·户口》,第2册,第457页),据吴建华的最新说法,估计当时人口亦为三十余万。
[33]参阅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立足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34]光绪《周庄镇志》卷6,《杂记》,见乡镇志专辑,第6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93页。
[35]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第31页。在这篇文章中,这一认识只是为了说明明清之际华北疫死人口而提出,并未给予具体的说明,在此只能就其结论提出意见。
[36]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清民国时期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曹在文中没有明确的说法,这一数字系吴建华根据曹的论述加以统计而得。(参见氏著《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第28页。)
[37]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本,第二分,1999年6月,第376—377页。
[38]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77—84页,以下涉及本次疫情情况而未注明出处的,均源于此。
[39]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7页;浙江医科大学主编:《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第84页。
[40]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41]沈梓著:《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86页。
[42]沈梓著:《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07页。
[43]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见乡镇志专辑,第4本,第68页。
[44]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同治十三年刊本,第40a页。
[45]沈梓著:《避寇日记》卷5,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313页。
[46]近人徐映璞在谈到杭州的情况时,也把饿死当作第一位的因素,他说:“杭州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李秀成攻占后,迄今二年又三月矣,兵火交加,粮食乏竭,饿死、疫死、锋刃死者,不知凡几。”(徐映璞:《太平军在浙江》,见氏著:《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
[47]沈梓著:《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6—48页。
[48]濮院镇的人口,笔者未发现明确的记载,据现代人编的《濮院镇志》称,乾隆年间,有人口万余户(陈兴蓂主编,上海书店,1996年,第369页)。以户均五口计,则为5万余口,若按浙江省乾隆中(设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到咸丰末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全省的人口数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4页),则为92,000人,濮院是当时嘉兴府有名的巨镇,镇区人口按罗店的十分之一计,则为9000余人。
[49]沈梓著:《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27页。
[50]龚又村(常熟人)著:《自怡日记》卷19,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358页。
[51]龚又村(常熟人)著:《自怡日记》卷2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53页。
[52]《太平天国资料》,第105页,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31页。
[53]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鼎文书局,1973年,第6册,第507、513页。
[54]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宁波府》,第229页。
[55]民国《剡源乡志》卷24,《大事记·祥异》,见乡镇志专辑,第24本,第513页。
[56]民国《剡源乡志》卷4,《氏族》,见乡镇志专辑,第24本,第529—530页。
[57]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松江府》,第210—214页。
[58]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7、170页。
[59]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
[60]江浙两省各个时段人口增长状况可参阅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第26页。
江南范文篇7
【正文】
一、清代江南人口增加对人口住房造成压力
在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中,有两点应该说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共识。第一,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江南的界定还不统一,范围有宽有窄,但是,以苏州(包括清代太仓直隶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江南核心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第二,尽管目前对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的认识和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明初洪武时代到晚清咸同战争之前,江南的人口数量呈现绝对增加,已是无论主张人口危机,还是认为人口低速增长的学者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对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和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共识之上。
了解明初的人口是研究清代人口的基石。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连同镇江、应天(南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大约870万,清代人口最多的道光三十年(1850)约为3635万。大略而言,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3600万,即增加300%。又经过推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人口约为2000万,属于明代江南人口最多时期的数字。从1620年到1850年,江南人口增加了80%。
依据《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南各府不连江宁,滋生人口约为2460万(注:据姜涛(1993)的研究,江宁府所在的江宁布政使司以人丁为统计单位,与苏、松、太、常、镇所属的江苏布政使司所用的以人口为统计单位不同。故不在此并列。)。从表1嘉庆二十五年的全国分府州人口密度统计,可以看出,1820年全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人的府州共有15个,其中江南地区的苏、松、太、常、镇、杭、嘉、湖八府州全都入选。江南弹丸之地成为全国人口高密度区,特别是苏州府以1073人的高密度,和位居其次、同处江南、同是人口高密度的嘉兴府拉开了距离,更不用讲与全国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的差距了。清代江南人口的高度密集毫无疑问。
表1嘉庆二十五年全国人口密度前16府州
人/平方公里
序号府州人口密度序号府州人口密度
1江苏苏州1073.219江苏镇江522.54
2浙江嘉兴719.2610四川成都507.80
3江苏松江626.5711浙江杭州506.32
4浙江绍兴579.5512浙江湖州475.21
5安徽庐州563.1113江苏常州447.79
6山东东昌537.6914山西蒲州423.88
7江苏太仓537.0415安徽太平410.96
8浙江泞波523.2616湖北武昌394.53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甲表88。
据李伯重(2000)的估计,江南人口的城乡分布中,城镇人口1620年约为300万,1850年约为720万。同时,农村人口1620年约为1700万,1850年约为2880万。从1620~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增加420万,农村人口增加1180万。
笔者(1988)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世代居住于常州府武进县(今武进市)的庄氏家族,在历届修谱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男性人丁原始的统计数:1580年32人,1723年1000余人,1805年1500余人,1856年1400余人。很明显,从雍正、嘉庆到咸丰年间,人口的绝对数量处于持续增加或稳定的状态。嘉庆十年(1805)人丁最旺。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研究,笔者认为,既然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清代江南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农户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人口的城乡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动(吴建华,1996),那么,维持原有水平的人均房屋居住面积就会缩小,居住拥挤,必然促动农村及城镇大规模建房,使住房增加,村庄稠密度加大,会改变农村及城镇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又造成耕地减少,土地使用面积绝对萎缩。在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一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阳湖县(今常州市武进市)著名人口学家洪亮吉忧虑的高祖、曾祖时一户,到曾孙、元孙时“不分至十户不止”。“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而田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五倍而止矣”。从而“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以二十余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注: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第六。)。
按他前一种推算,户口增长比率为1:10~20,田地、房屋增长比率为1:1~3~5。户口与田地、房屋比值差距很大。初时1:1,渐至10~20:1~3~5,差至4~10倍。依他后一种估算,20:10:100即2:1:10,1人半间屋5亩地,必不敷用;而10:10:100,即1:1:10,1人1间屋10亩地,生活仅仅足而已。时间愈长,户口愈增,而房屋、田地臻于尽地,入不敷出,拥挤不堪,成为必然。这仅是根据人口世代的生活常识所做的推理。如果一个社会或地区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它必然产生房屋、田地紧张以至匮乏,可能逼迫生产变动、经济变化,而人们分房建屋,另开家宅,势在必行。
二、侵占了耕地的清代江南人口住房建设
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地区的村庄除去一部分世代居住的土著,很多是由南宋以来外省移民居住形成的聚落。随着人口的繁衍,住房建设的推进,一方面旧有村庄的外沿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旧有母体村庄中不断裂生出众多子体型村庄,渐成连片之势。江南地方志中记载的村庄地名可以明显看出上述趋势。我们可以使用湖州府乌程县和苏州府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庄变化说明这一问题。
万历《湖州府志》卷3《乡镇》开列乌程县有乡12个,市镇4个,村104个。同治《湖州府志》卷22《村镇》则已按自然地名的区、庄、村加以分层,共分区23个,分庄199个,庄下分村636个。除4个市镇之庄的10个地名,计有乡村之庄626个地名。村庄比万历时期增加了601.92%,亦即增长6倍多,可见村庄裂变之巨。与此同时,湖州府的其他县分如归安(万历时期村110个)、长兴、德清等分庄也很繁多。只因万历之后记载欠详,致使它们无法取得与乌程县相似的比较村庄增长的形象效果。但村庄增长的趋势在300年内类同于乌程县是可以肯定的,可能只是增长的比率不同而已。
将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有关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巷地名两相比照,不难看出住房建造增多,村庄增长速度和密度的变化(见表2)。
表2吴长元村巷地名增长
县名乡数同治苏州府民国吴县志增加总数
志地名数新增地名数(%)
吴县22城内7249867426.983172
附郭1
长洲13城内72581176368.314344
附郭2
元和16城内7223640318.022639
附郭1
总计517315282438.8210155
资料来源: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
表2统计显示的吴、长、元境内村巷地名的增加幅度以位于苏州城东部的长洲县为最大,高达68.31%;元和最小,仅为18.02%;3县平均数在38%左右(总平均38.82%,3县累计平均37.77%)。地名从7315个累计急增至10155个,共计增加2840个,59年内平均每年递增48个。
观察表明,村庄地名的裂增主要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苏州府城内的地名由于划分7个乡,附郭2乡分归3个县共管,坊巷名称变化滋生极少。村庄地名的剧增则反映了清代人口密度最大的苏州吴中地区的农民以房屋为重,稍有积余,即投资于婚姻和生活必需的居住固定资产建设,占去的耕地愈来愈多。如果以民国《吴县志》面积(已并长、元2县)3729平方公里计算,则同治13年(1874)吴、长、元3县年均每平方公里1.96个村庄(地名),到民国22年(1933年)已增加到每平方公里2.72个村庄(地名),增加138.8%,还是很有可能的。江南水乡平原每平方公里2~3个村庄的稠密分布几乎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数个村庄联袂成片,组成一个个庞大的村落群。但地名还是保存旧称,具有独立性,以示区分。由于吴县包涵着座落在洞庭东、西山等山的太湖地区的6个乡都,所以其平原地区的村庄密度还要稠密些。
至于每个村庄的户口人数则各因其规模的大小而异,很难全面精确的估计。吴县靠近洞庭东山的渡村,“民居三千余家,为西南一大村落”(注:民国《吴县志》卷21。),仍然设村而未建镇。刘石吉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江南最大的村。光绪30年(1904),《常昭合志稿》卷5《市镇》刊列出市镇80个,估计的户数有18500,附近带管村庄368个,则每个村镇平均户数50.27。若依每户5人计,每村有251.35人。这是很不精确的村庄人口估数,很多人可以居住在市镇而非附近的村庄上。但也可见村庄人口的一般规模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5、139页。笔者据此又进行了统计。)。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列出的宣统3年(1911)自治筹备公所进行的户口调查成果,有助于了解清末隶属太仓州今属上海地区的乡村户口数量的一般情况。
当时嘉定县划分城乡自治区34个,总计有市镇30个,村庄2964个,户数46964,口220632,户均4.69口。若平均计算,则每个村庄15.84户,74.44人,显然混淆了市镇的人户数于农村之中。由于市镇人口密度一般大于乡村人口密度,因此,以上这一平均村庄的户和口数属于偏高的估计。没有市镇的乡自治区可以见得更加真切的村庄户口数规模。嘉定县34个自治区中共有8个这样的乡区(见表3)。
表31911年嘉定县乡村户口统计
区名村数户数户/村口数口/村
白荡716839.62324045.63
六里桥555369.75241943.98
封滨120177114.76848970.74
江桥2447319.71208286.75
陈店80110313.79508863.60
真圣堂139178912.87864262.17
西胜塘3741711.27200154.08
吴巷3966517.05283172.59
总计565743713.163479261.58
资料来源: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
表3所列的8个乡区没有市镇,在清末近于上海大都市的嘉定县中应该是比较闭塞穷僻的乡村,更带有自然滋生人口的性质。其平均每户4.68人,同全县家庭规模相近。其村庄规模合计平均13.16户,61.58人一村。这个数值小于前述连同市镇人口在内的全嘉定县2964个村庄的平均村庄规模(15.84户,74.44人),但差别居然不大。可见即使包含了全部市镇人口在内的平均乡村规模也不会过大。
湖州和苏州地区的村庄膨胀、住房建造增加以及嘉定的一般村庄情况告诉人们,清代江南农村人口的住宅建筑一直在持续地增多,迫使可耕地减少。而分宅而居,自立门户,村庄裂变增生,新村不断涌现,稠密度增大,是当地居住结构习俗的实况,农村居住聚落结构改观的景观模型。
然而,农村住宅村庄建设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没有很好的规划。大多数村庄属于在旧庄附近另立门户,搭建新宅。因而地名上只稍作变化以示区别,常带母子分裂之意,容易辨认。或由方位,如前、后陆巷;里、外浜;河北、河东、河南村;内、外村等。南、北、东、西张村即由一分四;上、中、下潭则顺水势别分作三。
住房是人口衣食住行的必要成分,在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那么,清代江南人口要有多大的住房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一般住房的一室面积有多大?
江南盛行砖瓦平房,或带木板的阁楼。通常的苏式建筑,如果正间1丈4尺,两次间1丈2尺,共开间3丈8尺。内四界1丈6尺,前后双步共1丈6尺,共进深3丈2尺。这一套稍微像样的普通民居用房面积共合12方丈1尺6寸(注:姚承祖:《营造法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9年,第2页。该书使用的是鲁班尺。鲁班尺的长度各地区不同。据该书第113页,苏州鲁班尺每尺合27.5公分,则每方丈合7.5625平方米。)。达官贵人、富商豪绅士人等人家的住房面积更大,建筑精致考究,但不一定都会豪华庸俗。尤其是园林别墅宅第,密布太湖城乡,成为苏州园林苏式建筑传世的普遍背景。
可是,大规模建房筑室必然大量侵占土地,引起原有已达开垦饱和的土地减少和耕地紧张,连最高统治者也虑及此点。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讲道,“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一》。)。
三、清代江南人口住房的扩张和人均住房面积:常熟邹氏的个案
面对人口数量的增加,村庄增加,人口耕地紧缩,江南人口的住房怎样建设?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怎样发展,我们目前几乎找不到现成的资料。
在整理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时,我们发现了常熟邹氏家族的石刻家谱资料。经过阅读分析,发现它包含了丰富的人口与住房的资料。可以说,清代苏州府常熟县邹氏由家庭扩展成宗族,住宅不断兴建,形成邹氏族居聚落的过程,具体生动地再现了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关系的变化图景(注:以下邹家资料均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171~183号,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在目前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研究严重缺乏资料的情况下,邹家的例子或许是探讨清代江南人口增加、人口耕地紧张的背景之下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人口住房建设、人口与住房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邹氏原居常州府无锡县后宅,继迁苏州五龙桥。康熙年间第七世邹耀卿因避渠区水匪,始迁常熟县,结庐于洞泾桥(又名陈埭桥)东,开始了耕读传家的艰苦创业历程。
耀卿生1子公玠。公玠生3子。公玠因为多子,住房紧张,必须建房。他建造凝秀堂7间3进,以东半授长子辅侯(即廷佐),西半授次房。傍屋隙地,各自执管。三房授始迁老屋。这样的分房分家,符合民间“哥东弟西”的习惯,也是以东为上,长幼有序的礼义文化的日常生活体现。一个大家庭终于出现在新迁的土地上,兄弟仨两处排开,但他们只以耕种为业,还没有功名官职人物出现,属于富裕农民一类。
辅侯于凝秀堂东面增建履庆堂7间4进,比凝秀堂规模还大,多了1进,房屋外观有了参差不齐。但这种格局延续到他的儿子振远(即鹏翔)没变。
振远子沛霖,号华西,生4子:珏(竹亭)、珍(荻芗)、球(玉韶)、琛(采轩),住房危机因男丁骤增而增大。于是,华西开始了邹家迁居常熟后的第三次建房,也是规模最大的扩建活动。
他在履庆堂东面兴建履和堂5间4进,又得到东首隙地,直到谢家浜为止。在一个田野乡村必须傍河,解决生活用水以及生产、卫生问题。这时,邹家向住房周围扩展,只好把眼光盯向村边近河的地段,到了河浜边,邻接村地边缘,已把可得之地基作了最好的利用。华西的经营能力允许他占地建房,解决多子的居住空间。(公务员之家整理)
道光八年(1828),二房将凝秀堂西半房屋及隙地并归给华西,使华西有机会扩充旧房。他建成履厚堂7间4进,傍西又建履福堂5间4进。这样,凝秀堂由原来的7间3进扩建了1进,与其余搭墙房屋都为4进截齐,便于分家,让诸子无怨。华西把4处房屋分授4子:长子珏得履庆堂,次子珍得履福堂,三子球得履和堂,幼子琛得履厚堂。奇怪的是长子、幼子均得7间4进,次子、三子各得5间4进。看来华西的分家遵循了这样的原则,长子先成家,得了7间,紧挨凝秀堂东半房,这是华西首次娶儿媳,自然要有气魄体面。长子的优势也在于此,是一家的颜面所在。而凝秀堂东半房原来是华西夫妇分得的祖产老屋,直到中间的两个儿子分家住上东西边缘的两块住宅,即履和堂、履福堂,才能最后把和幼子同居共爨的老祖产连同扩建的凝秀堂西半房交给幼子继承。在老夫妻存活之世,幼子只得到凝秀堂的西半,就是从二房兄弟那里继让的房产与边隙地产。但房子嫌小,在兄弟间肯定不公平。因此,华西只得把房子扩大1进,与其他房间拉平。等到老夫妻过世,幼子则可得到原先住房稍小的补偿,达到与长兄同等的水准,比二、三两兄多了2间住宅,总体上还是平衡平等的。华西分家的住宅顺序与儿子的次序原应基本相符,却因为建造的房子条件不同,而进行了调整。长子得房多,但无法住最东边,转而由老二住最东边,老三住最西边,符合农村分居文化的规矩。
华西是耀卿的曾孙振远之子,共有房屋24间,其中新造10间。
在华西曾祖公玠时代,每子有相当于新房的3.5间,共10.5间。而华西的4子平均每子6间住房,实际上2子各得7间,2子各得5间。家庭人口比公玠时增多,人均住房面积不减反增,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时正是乾嘉道年间,人口增加的高峰期。华西家因为人口增多与住房紧张出现大规模营造住房,新建了10间,扩建7间各1进。比公玠时增加1子,房间却扩大了至少1.3倍,解决了住房的大问题,而且人均住房比公玠时代宽敞将近1倍。住房面积的扩大肯定减少了村落隙地以及耕地的面积,乾嘉道时期的人口增多导致的住房拥挤,致使有力之家扩大住房建造无疑是普遍的现象。否则,只有减少人均居住面积,降低生活质量。
华西还有环秀弄寓处一所,小河下、东仓街店面及栈房共两所。他似乎已经亦乡亦城或在市镇居住,经营也亦农亦商了。从耀卿始迁到华西,已传到十一世,传了四代。从康熙到嘉道时,由1人分至多少人,因为资料不足,难以得知。但从公玠、辅侯一支到华西的旧宅新居的3次扩大,可见人口的增加与住房扩展的关联了。
然而,华西的家庭连同耀卿的其余子孙,已在洞泾桥形成了相当的人口规模。道光23年(1843)华西子珏建义庄、家祠于陈埭桥北隅,又自置河北仓房一所。珍自置仓房一所于履福堂之西。到光绪二年(1876),“综计四房整齐屋房合庄祠约有四百余间,膏腴田亩合庄祠约有九十余顷”。
华西能够扩房,与他的发家致富密不可分。华西甫弱冠即丧父,家产不会殷厚。因为他的父亲振远想立义田都立不成。不过,华西很精干,“殚精竭虑,减膳节衣,历数十年”,到道光时已积义田1070余亩,书田200亩。因病临终时,他遗命4个儿子以建义庄为重。他的资产极为雄厚,“扩先人遗业,共积良田七千余亩,临终前四子各授田千亩”,“以赀雄于其乡”了。三、四两子的年龄与长、次子相差很大,只能与孙辈(长、次子之儿)“就傅读书”。
耀卿的后代传至第三代即九世廷佐、十世鹏翔都成了国学生,赠奉直大夫。鹏翔还被旌表孝义。十一世华西则是邑痒生,布政司经历加二级,阶奉直大夫,旌表孝义。廷佐、鹏翔的国学生是靠钱捐来的。他们知道除了财力,还应向社会地位的梯级爬进。鹏翔曾想效法范文正公,设立义田,却似乎财力不济,赍志而殁。
邹家在迁居常熟之后的200年中由家而族,成为地方乡绅。李兆洛、董国华、林天龄、林则徐、庞钟璐、翁同龢、李葆桢等地方高官名流纷纷为邹家撰书题碑,抬高了声誉。显然,邹家的兼并良田、扩建住房活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认与保护。
清代江南苏式民居建筑的格式如前所述,一套普通民居用房为3间6架面积共合12.16方丈,比一般房子要大。一般一步架为5~6尺。苏式一步架则为8尺,大了2~3尺。可能江南地方潮湿,房子宽敞些为好。但3间开间即中间的明间,两旁的各一次间,还是很狭窄,一般有能力之家便放到5间开间。9间开间已很大,11间以上很特殊了(注: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建筑辞典》,中国书店,1992年,第29、98页。一般一步架长5~6尺。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和林光征、陈捷:《中国度量衡》(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清朝工部营造尺计,每尺合32公分,则一步架为160~192公分。苏式一步架为8尺,以苏州鲁班尺计,则为220公分。故苏州一般一步架比他处一般一步架大28~60公分。)。
邹沛霖的住房2处为5间开间,2处为7间开间,都有4进。如果以正间1.4丈,次间1.2丈计,则5间开间共6.2丈。7间开间共8.6丈。进深以一进通进深3.2丈计,则4进的通进深12.8丈。因此,每处5间4进用房面积是79.36方丈,每处7间4进用房面积是110.08方丈。2处5间4进与2处7间4进,共占地面积378.88方丈。
公玠的凝秀堂是7间3进,用房面积为82.56方丈。由长、次子平分。三子住在老房,应不低于诸子分家的平均面积。这样,公玠的3个儿子住房面积至少应有123.84方丈。辅侯建的履庆堂7间4进,增加了用房面积110.08方丈。连同凝秀堂的东半房屋41.28方丈,共有住房面积151.36方丈。
以公玠住房的面积为基数,则辅侯的住房面积增加了22.22%。到华西时增加了205.94%。华西每子平均各得94.72方丈。比公玠的3子平均住房面积的41.28方丈增加了129.46%,多53.44方丈。可见随着人口增加,邹家住房面积也在增加,一方面是财力许可,造成住宅的宽裕。另一方面实际住房的占地面积扩大了,影响到耕地的使用。邹家连房边隙地也用上,把住房扩到河边了。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公玠分家与华西分家后诸子的小家庭有人口的多少,会稀释分家时总和住房的面积,这也是邹家扩大建房的动机。
以华西的长子珏为例。他在同治八年(1869)去世时73岁,生有2子。长子文灏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染病早逝,年23。他已娶妻陆氏,生子一已殇,女一,适同邑黄氏。陆氏于咸丰三年(1853)卒。次子文瀚已结婚生有3子。他以长子钟桂承嗣文灏。另外文瀚已有孙子3人。如果从文瀚分家所得的住房计算,珏分得华西的房产94.72方丈,2个儿子分家,各得47.36方丈,几乎回到了公@①分授诸子房屋的水平。以文灏一家3人计,平均每人得15.79方丈。道光初年,邹珏家的住房状况仍和康熙时期相当。
但随着文灏一家不幸夫妻早亡,女儿出嫁,房产由文瀚继承,实际上回到了文瀚一家的名下。文瀚到光绪元年(1875)十月之前,一家至少有夫妇2人,3子3孙,3子中以2子已婚计,则共有10人。他父亲卒于同治八年,母亲在同治十一年(1872)之前也卒,则又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小家族。各子分居,成为大家庭。按平均分房计算,3子仍有94.72方丈可分,则每子得房31.57方丈,比公玠、邹珏分家给诸子的住房面积分别减少9.71与15.79方丈,比华西分家时诸子的住房面积减少63.15方丈。似乎文瀚又得另置房屋了。如果按人头计,文灏一家3人平均每人15.79方丈,文瀚一家10人则人均住房只有9.47方丈。
常熟邹氏从康熙时耀卿始迁洞泾桥立家,境况不会太好。第二代公玠首次兴建住房,分授3子,平均每子分得41.28方丈。第三代辅侯第二次扩建住房,因不知有几子,无法估算平均的儿子分家面积。第五代华西第三次大规模扩建房屋,分授4子,平均每子得94.72方丈。这是邹家最为辉煌的时期:田产隆盛,人口众多,住房宏壮。但第六代邹珏兄弟4人把心血财力花在义庄义田等宗族公益事业上,并得到孀母的大力支持,自己似乎没有扩建住宅。邹珏分给2子的住房面积有所减少,几乎回复到公玠所在的康熙时的水平,2子各得47.36方丈。文瀚分家,则各子仅有31.57方丈。随人口增加,财力不济,住房也紧张起来。
从康熙到同治的200年中,邹氏传了九代,家族人口愈众,有了设立义庄进行同族救济的必要。每个分支的家庭愈分愈多,住房愈建愈繁。但每家人口的住房面积应视其家庭财力与投向以及人口使用的状况而定。邹珏、文瀚时,人均住房面积从停滞走向减少,但仍能保持生活的必要空间,甚至较为宽敞。
以上根据常熟邹家的住房变化所反映的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关系的变化只是一个案例,至于说邹家的人口住房标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上属于何种水准,还须做进一步的材料挖掘、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总之,本文所述的历史事例表明,虽然清代江南(以农村为主)村庄的增多和住房聚落分布结构的改观并不都是当地人口增加的直接后果,它与人们的财力、生活志趣、甚至经济的转型还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多少反映了江南地区人口数量增多或变化之下人们住房扩张的轨迹,江南农村人文地理面貌的重大变化,构成近现代农村住宅景观的基础。因为,住房总是人口生活的基本资料,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后果、人口的生活状态总会在住房问题上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增长探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5期。
3.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及其人口结构变动》,《城市史研究》,第11~1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江南范文篇8
【正文】
一、清代江南人口增加对人口住房造成压力
在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中,有两点应该说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共识。第一,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江南的界定还不统一,范围有宽有窄,但是,以苏州(包括清代太仓直隶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江南核心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第二,尽管目前对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的认识和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明初洪武时代到晚清咸同战争之前,江南的人口数量呈现绝对增加,已是无论主张人口危机,还是认为人口低速增长的学者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对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和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共识之上。
了解明初的人口是研究清代人口的基石。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连同镇江、应天(南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大约870万,清代人口最多的道光三十年(1850)约为3635万。大略而言,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3600万,即增加300%。又经过推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人口约为2000万,属于明代江南人口最多时期的数字。从1620年到1850年,江南人口增加了80%。
依据《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南各府不连江宁,滋生人口约为2460万(注:据姜涛(1993)的研究,江宁府所在的江宁布政使司以人丁为统计单位,与苏、松、太、常、镇所属的江苏布政使司所用的以人口为统计单位不同。故不在此并列。)。从表1嘉庆二十五年的全国分府州人口密度统计,可以看出,1820年全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人的府州共有15个,其中江南地区的苏、松、太、常、镇、杭、嘉、湖八府州全都入选。江南弹丸之地成为全国人口高密度区,特别是苏州府以1073人的高密度,和位居其次、同处江南、同是人口高密度的嘉兴府拉开了距离,更不用讲与全国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的差距了。清代江南人口的高度密集毫无疑问。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甲表88。
据李伯重(2000)的估计,江南人口的城乡分布中,城镇人口1620年约为300万,1850年约为720万。同时,农村人口1620年约为1700万,1850年约为2880万。从1620~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增加420万,农村人口增加1180万。
笔者(1988)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世代居住于常州府武进县(今武进市)的庄氏家族,在历届修谱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男性人丁原始的统计数:1580年32人,1723年1000余人,1805年1500余人,1856年1400余人。很明显,从雍正、嘉庆到咸丰年间,人口的绝对数量处于持续增加或稳定的状态。嘉庆十年(1805)人丁最旺。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研究,笔者认为,既然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清代江南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农户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人口的城乡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动(吴建华,1996),那么,维持原有水平的人均房屋居住面积就会缩小,居住拥挤,必然促动农村及城镇大规模建房,使住房增加,村庄稠密度加大,会改变农村及城镇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又造成耕地减少,土地使用面积绝对萎缩。在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一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阳湖县(今常州市武进市)著名人口学家洪亮吉忧虑的高祖、曾祖时一户,到曾孙、元孙时“不分至十户不止”。“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而田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五倍而止矣”。从而“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以二十余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注: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第六。)。
按他前一种推算,户口增长比率为1:10~20,田地、房屋增长比率为1:1~3~5。户口与田地、房屋比值差距很大。初时1:1,渐至10~20:1~3~5,差至4~10倍。依他后一种估算,20:10:100即2:1:10,1人半间屋5亩地,必不敷用;而10:10:100,即1:1:10,1人1间屋10亩地,生活仅仅足而已。时间愈长,户口愈增,而房屋、田地臻于尽地,入不敷出,拥挤不堪,成为必然。这仅是根据人口世代的生活常识所做的推理。如果一个社会或地区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它必然产生房屋、田地紧张以至匮乏,可能逼迫生产变动、经济变化,而人们分房建屋,另开家宅,势在必行。
二、侵占了耕地的清代江南人口住房建设
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地区的村庄除去一部分世代居住的土著,很多是由南宋以来外省移民居住形成的聚落。随着人口的繁衍,住房建设的推进,一方面旧有村庄的外沿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旧有母体村庄中不断裂生出众多子体型村庄,渐成连片之势。江南地方志中记载的村庄地名可以明显看出上述趋势。我们可以使用湖州府乌程县和苏州府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庄变化说明这一问题。
万历《湖州府志》卷3《乡镇》开列乌程县有乡12个,市镇4个,村104个。同治《湖州府志》卷22《村镇》则已按自然地名的区、庄、村加以分层,共分区23个,分庄199个,庄下分村636个。除4个市镇之庄的10个地名,计有乡村之庄626个地名。村庄比万历时期增加了601.92%,亦即增长6倍多,可见村庄裂变之巨。与此同时,湖州府的其他县分如归安(万历时期村110个)、长兴、德清等分庄也很繁多。只因万历之后记载欠详,致使它们无法取得与乌程县相似的比较村庄增长的形象效果。但村庄增长的趋势在300年内类同于乌程县是可以肯定的,可能只是增长的比率不同而已。
将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有关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巷地名两相比照,不难看出住房建造增多,村庄增长速度和密度的变化(见表2)。
表2统计显示的吴、长、元境内村巷地名的增加幅度以位于苏州城东部的长洲县为最大,高达68.31%;元和最小,仅为18.02%;3县平均数在38%左右(总平均38.82%,3县累计平均37.77%)。地名从7315个累计急增至10155个,共计增加2840个,59年内平均每年递增48个。
观察表明,村庄地名的裂增主要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苏州府城内的地名由于划分7个乡,附郭2乡分归3个县共管,坊巷名称变化滋生极少。村庄地名的剧增则反映了清代人口密度最大的苏州吴中地区的农民以房屋为重,稍有积余,即投资于婚姻和生活必需的居住固定资产建设,占去的耕地愈来愈多。如果以民国《吴县志》面积(已并长、元2县)3729平方公里计算,则同治13年(1874)吴、长、元3县年均每平方公里1.96个村庄(地名),到民国22年(1933年)已增加到每平方公里2.72个村庄(地名),增加138.8%,还是很有可能的。江南水乡平原每平方公里2~3个村庄的稠密分布几乎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数个村庄联袂成片,组成一个个庞大的村落群。但地名还是保存旧称,具有独立性,以示区分。由于吴县包涵着座落在洞庭东、西山等山的太湖地区的6个乡都,所以其平原地区的村庄密度还要稠密些。
至于每个村庄的户口人数则各因其规模的大小而异,很难全面精确的估计。吴县靠近洞庭东山的渡村,“民居三千余家,为西南一大村落”(注:民国《吴县志》卷21。),仍然设村而未建镇。刘石吉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江南最大的村。光绪30年(1904),《常昭合志稿》卷5《市镇》刊列出市镇80个,估计的户数有18500,附近带管村庄368个,则每个村镇平均户数50.27。若依每户5人计,每村有251.35人。这是很不精确的村庄人口估数,很多人可以居住在市镇而非附近的村庄上。但也可见村庄人口的一般规模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5、139页。笔者据此又进行了统计。)。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列出的宣统3年(1911)自治筹备公所进行的户口调查成果,有助于了解清末隶属太仓州今属上海地区的乡村户口数量的一般情况。
当时嘉定县划分城乡自治区34个,总计有市镇30个,村庄2964个,户数46964,口220632,户均4.69口。若平均计算,则每个村庄15.84户,74.44人,显然混淆了市镇的人户数于农村之中。由于市镇人口密度一般大于乡村人口密度,因此,以上这一平均村庄的户和口数属于偏高的估计。没有市镇的乡自治区可以见得更加真切的村庄户口数规模。嘉定县34个自治区中共有8个这样的乡区(见表3)。
表3所列的8个乡区没有市镇,在清末近于上海大都市的嘉定县中应该是比较闭塞穷僻的乡村,更带有自然滋生人口的性质。其平均每户4.68人,同全县家庭规模相近。其村庄规模合计平均13.16户,61.58人一村。这个数值小于前述连同市镇人口在内的全嘉定县2964个村庄的平均村庄规模(15.84户,74.44人),但差别居然不大。可见即使包含了全部市镇人口在内的平均乡村规模也不会过大。
湖州和苏州地区的村庄膨胀、住房建造增加以及嘉定的一般村庄情况告诉人们,清代江南农村人口的住宅建筑一直在持续地增多,迫使可耕地减少。而分宅而居,自立门户,村庄裂变增生,新村不断涌现,稠密度增大,是当地居住结构习俗的实况,农村居住聚落结构改观的景观模型。
然而,农村住宅村庄建设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没有很好的规划。大多数村庄属于在旧庄附近另立门户,搭建新宅。因而地名上只稍作变化以示区别,常带母子分裂之意,容易辨认。或由方位,如前、后陆巷;里、外浜;河北、河东、河南村;内、外村等。南、北、东、西张村即由一分四;上、中、下潭则顺水势别分作三。
住房是人口衣食住行的必要成分,在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那么,清代江南人口要有多大的住房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一般住房的一室面积有多大?
江南盛行砖瓦平房,或带木板的阁楼。通常的苏式建筑,如果正间1丈4尺,两次间1丈2尺,共开间3丈8尺。内四界1丈6尺,前后双步共1丈6尺,共进深3丈2尺。这一套稍微像样的普通民居用房面积共合12方丈1尺6寸(注:姚承祖:《营造法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9年,第2页。该书使用的是鲁班尺。鲁班尺的长度各地区不同。据该书第113页,苏州鲁班尺每尺合27.5公分,则每方丈合7.5625平方米。)。达官贵人、富商豪绅士人等人家的住房面积更大,建筑精致考究,但不一定都会豪华庸俗。尤其是园林别墅宅第,密布太湖城乡,成为苏州园林苏式建筑传世的普遍背景。
可是,大规模建房筑室必然大量侵占土地,引起原有已达开垦饱和的土地减少和耕地紧张,连最高统治者也虑及此点。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讲道,“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一》。)。三、清代江南人口住房的扩张和人均住房面积:常熟邹氏的个案
面对人口数量的增加,村庄增加,人口耕地紧缩,江南人口的住房怎样建设?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怎样发展,我们目前几乎找不到现成的资料。
在整理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时,我们发现了常熟邹氏家族的石刻家谱资料。经过阅读分析,发现它包含了丰富的人口与住房的资料。可以说,清代苏州府常熟县邹氏由家庭扩展成宗族,住宅不断兴建,形成邹氏族居聚落的过程,具体生动地再现了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关系的变化图景(注:以下邹家资料均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171~183号,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在目前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研究严重缺乏资料的情况下,邹家的例子或许是探讨清代江南人口增加、人口耕地紧张的背景之下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人口住房建设、人口与住房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邹氏原居常州府无锡县后宅,继迁苏州五龙桥。康熙年间第七世邹耀卿因避渠区水匪,始迁常熟县,结庐于洞泾桥(又名陈埭桥)东,开始了耕读传家的艰苦创业历程。
耀卿生1子公玠。公玠生3子。公玠因为多子,住房紧张,必须建房。他建造凝秀堂7间3进,以东半授长子辅侯(即廷佐),西半授次房。傍屋隙地,各自执管。三房授始迁老屋。这样的分房分家,符合民间“哥东弟西”的习惯,也是以东为上,长幼有序的礼义文化的日常生活体现。一个大家庭终于出现在新迁的土地上,兄弟仨两处排开,但他们只以耕种为业,还没有功名官职人物出现,属于富裕农民一类。
辅侯于凝秀堂东面增建履庆堂7间4进,比凝秀堂规模还大,多了1进,房屋外观有了参差不齐。但这种格局延续到他的儿子振远(即鹏翔)没变。
振远子沛霖,号华西,生4子:珏(竹亭)、珍(荻芗)、球(玉韶)、琛(采轩),住房危机因男丁骤增而增大。于是,华西开始了邹家迁居常熟后的第三次建房,也是规模最大的扩建活动。
他在履庆堂东面兴建履和堂5间4进,又得到东首隙地,直到谢家浜为止。在一个田野乡村必须傍河,解决生活用水以及生产、卫生问题。这时,邹家向住房周围扩展,只好把眼光盯向村边近河的地段,到了河浜边,邻接村地边缘,已把可得之地基作了最好的利用。华西的经营能力允许他占地建房,解决多子的居住空间。
道光八年(1828),二房将凝秀堂西半房屋及隙地并归给华西,使华西有机会扩充旧房。他建成履厚堂7间4进,傍西又建履福堂5间4进。这样,凝秀堂由原来的7间3进扩建了1进,与其余搭墙房屋都为4进截齐,便于分家,让诸子无怨。华西把4处房屋分授4子:长子珏得履庆堂,次子珍得履福堂,三子球得履和堂,幼子琛得履厚堂。奇怪的是长子、幼子均得7间4进,次子、三子各得5间4进。看来华西的分家遵循了这样的原则,长子先成家,得了7间,紧挨凝秀堂东半房,这是华西首次娶儿媳,自然要有气魄体面。长子的优势也在于此,是一家的颜面所在。而凝秀堂东半房原来是华西夫妇分得的祖产老屋,直到中间的两个儿子分家住上东西边缘的两块住宅,即履和堂、履福堂,才能最后把和幼子同居共爨的老祖产连同扩建的凝秀堂西半房交给幼子继承。在老夫妻存活之世,幼子只得到凝秀堂的西半,就是从二房兄弟那里继让的房产与边隙地产。但房子嫌小,在兄弟间肯定不公平。因此,华西只得把房子扩大1进,与其他房间拉平。等到老夫妻过世,幼子则可得到原先住房稍小的补偿,达到与长兄同等的水准,比二、三两兄多了2间住宅,总体上还是平衡平等的。华西分家的住宅顺序与儿子的次序原应基本相符,却因为建造的房子条件不同,而进行了调整。长子得房多,但无法住最东边,转而由老二住最东边,老三住最西边,符合农村分居文化的规矩。
华西是耀卿的曾孙振远之子,共有房屋24间,其中新造10间。
在华西曾祖公玠时代,每子有相当于新房的3.5间,共10.5间。而华西的4子平均每子6间住房,实际上2子各得7间,2子各得5间。家庭人口比公玠时增多,人均住房面积不减反增,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时正是乾嘉道年间,人口增加的高峰期。华西家因为人口增多与住房紧张出现大规模营造住房,新建了10间,扩建7间各1进。比公玠时增加1子,房间却扩大了至少1.3倍,解决了住房的大问题,而且人均住房比公玠时代宽敞将近1倍。住房面积的扩大肯定减少了村落隙地以及耕地的面积,乾嘉道时期的人口增多导致的住房拥挤,致使有力之家扩大住房建造无疑是普遍的现象。否则,只有减少人均居住面积,降低生活质量。
华西还有环秀弄寓处一所,小河下、东仓街店面及栈房共两所。他似乎已经亦乡亦城或在市镇居住,经营也亦农亦商了。从耀卿始迁到华西,已传到十一世,传了四代。从康熙到嘉道时,由1人分至多少人,因为资料不足,难以得知。但从公玠、辅侯一支到华西的旧宅新居的3次扩大,可见人口的增加与住房扩展的关联了。
然而,华西的家庭连同耀卿的其余子孙,已在洞泾桥形成了相当的人口规模。道光23年(1843)华西子珏建义庄、家祠于陈埭桥北隅,又自置河北仓房一所。珍自置仓房一所于履福堂之西。到光绪二年(1876),“综计四房整齐屋房合庄祠约有四百余间,膏腴田亩合庄祠约有九十余顷”。
华西能够扩房,与他的发家致富密不可分。华西甫弱冠即丧父,家产不会殷厚。因为他的父亲振远想立义田都立不成。不过,华西很精干,“殚精竭虑,减膳节衣,历数十年”,到道光时已积义田1070余亩,书田200亩。因病临终时,他遗命4个儿子以建义庄为重。他的资产极为雄厚,“扩先人遗业,共积良田七千余亩,临终前四子各授田千亩”,“以赀雄于其乡”了。三、四两子的年龄与长、次子相差很大,只能与孙辈(长、次子之儿)“就傅读书”。
耀卿的后代传至第三代即九世廷佐、十世鹏翔都成了国学生,赠奉直大夫。鹏翔还被旌表孝义。十一世华西则是邑痒生,布政司经历加二级,阶奉直大夫,旌表孝义。廷佐、鹏翔的国学生是靠钱捐来的。他们知道除了财力,还应向社会地位的梯级爬进。鹏翔曾想效法范文正公,设立义田,却似乎财力不济,赍志而殁。
邹家在迁居常熟之后的200年中由家而族,成为地方乡绅。李兆洛、董国华、林天龄、林则徐、庞钟璐、翁同龢、李葆桢等地方高官名流纷纷为邹家撰书题碑,抬高了声誉。显然,邹家的兼并良田、扩建住房活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认与保护。
清代江南苏式民居建筑的格式如前所述,一套普通民居用房为3间6架面积共合12.16方丈,比一般房子要大。一般一步架为5~6尺。苏式一步架则为8尺,大了2~3尺。可能江南地方潮湿,房子宽敞些为好。但3间开间即中间的明间,两旁的各一次间,还是很狭窄,一般有能力之家便放到5间开间。9间开间已很大,11间以上很特殊了(注: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建筑辞典》,中国书店,1992年,第29、98页。一般一步架长5~6尺。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和林光征、陈捷:《中国度量衡》(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清朝工部营造尺计,每尺合32公分,则一步架为160~192公分。苏式一步架为8尺,以苏州鲁班尺计,则为220公分。故苏州一般一步架比他处一般一步架大28~60公分。)。
邹沛霖的住房2处为5间开间,2处为7间开间,都有4进。如果以正间1.4丈,次间1.2丈计,则5间开间共6.2丈。7间开间共8.6丈。进深以一进通进深3.2丈计,则4进的通进深12.8丈。因此,每处5间4进用房面积是79.36方丈,每处7间4进用房面积是110.08方丈。2处5间4进与2处7间4进,共占地面积378.88方丈。
公玠的凝秀堂是7间3进,用房面积为82.56方丈。由长、次子平分。三子住在老房,应不低于诸子分家的平均面积。这样,公玠的3个儿子住房面积至少应有123.84方丈。辅侯建的履庆堂7间4进,增加了用房面积110.08方丈。连同凝秀堂的东半房屋41.28方丈,共有住房面积151.36方丈。
以公玠住房的面积为基数,则辅侯的住房面积增加了22.22%。到华西时增加了205.94%。华西每子平均各得94.72方丈。比公玠的3子平均住房面积的41.28方丈增加了129.46%,多53.44方丈。可见随着人口增加,邹家住房面积也在增加,一方面是财力许可,造成住宅的宽裕。另一方面实际住房的占地面积扩大了,影响到耕地的使用。邹家连房边隙地也用上,把住房扩到河边了。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公玠分家与华西分家后诸子的小家庭有人口的多少,会稀释分家时总和住房的面积,这也是邹家扩大建房的动机。
以华西的长子珏为例。他在同治八年(1869)去世时73岁,生有2子。长子文灏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染病早逝,年23。他已娶妻陆氏,生子一已殇,女一,适同邑黄氏。陆氏于咸丰三年(1853)卒。次子文瀚已结婚生有3子。他以长子钟桂承嗣文灏。另外文瀚已有孙子3人。如果从文瀚分家所得的住房计算,珏分得华西的房产94.72方丈,2个儿子分家,各得47.36方丈,几乎回到了公@①分授诸子房屋的水平。以文灏一家3人计,平均每人得15.79方丈。道光初年,邹珏家的住房状况仍和康熙时期相当。
但随着文灏一家不幸夫妻早亡,女儿出嫁,房产由文瀚继承,实际上回到了文瀚一家的名下。文瀚到光绪元年(1875)十月之前,一家至少有夫妇2人,3子3孙,3子中以2子已婚计,则共有10人。他父亲卒于同治八年,母亲在同治十一年(1872)之前也卒,则又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小家族。各子分居,成为大家庭。按平均分房计算,3子仍有94.72方丈可分,则每子得房31.57方丈,比公玠、邹珏分家给诸子的住房面积分别减少9.71与15.79方丈,比华西分家时诸子的住房面积减少63.15方丈。似乎文瀚又得另置房屋了。如果按人头计,文灏一家3人平均每人15.79方丈,文瀚一家10人则人均住房只有9.47方丈。
常熟邹氏从康熙时耀卿始迁洞泾桥立家,境况不会太好。第二代公玠首次兴建住房,分授3子,平均每子分得41.28方丈。第三代辅侯第二次扩建住房,因不知有几子,无法估算平均的儿子分家面积。第五代华西第三次大规模扩建房屋,分授4子,平均每子得94.72方丈。这是邹家最为辉煌的时期:田产隆盛,人口众多,住房宏壮。但第六代邹珏兄弟4人把心血财力花在义庄义田等宗族公益事业上,并得到孀母的大力支持,自己似乎没有扩建住宅。邹珏分给2子的住房面积有所减少,几乎回复到公玠所在的康熙时的水平,2子各得47.36方丈。文瀚分家,则各子仅有31.57方丈。随人口增加,财力不济,住房也紧张起来。
从康熙到同治的200年中,邹氏传了九代,家族人口愈众,有了设立义庄进行同族救济的必要。每个分支的家庭愈分愈多,住房愈建愈繁。但每家人口的住房面积应视其家庭财力与投向以及人口使用的状况而定。邹珏、文瀚时,人均住房面积从停滞走向减少,但仍能保持生活的必要空间,甚至较为宽敞。
以上根据常熟邹家的住房变化所反映的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关系的变化只是一个案例,至于说邹家的人口住房标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上属于何种水准,还须做进一步的材料挖掘、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总之,本文所述的历史事例表明,虽然清代江南(以农村为主)村庄的增多和住房聚落分布结构的改观并不都是当地人口增加的直接后果,它与人们的财力、生活志趣、甚至经济的转型还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多少反映了江南地区人口数量增多或变化之下人们住房扩张的轨迹,江南农村人文地理面貌的重大变化,构成近现代农村住宅景观的基础。因为,住房总是人口生活的基本资料,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后果、人口的生活状态总会在住房问题上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增长探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5期。
江南范文篇9
关键词:牖;古典园林;园林设计;空间营造
牖在源远流长的古典园林历史文化艺术长河中,具有独具特色的东方神韵以及非常浓厚的艺术美学价值。作为把人、建筑以及景观相连接的重要的设计艺术手法,其在园林空间营造中的价值非常值得研究。本文将会从空间渗透、虚实设计、视界超越这三个方面深入讨论研究牖在江南古典园林空间营造中独特的艺术价值。通过对牖的研究,使相关设计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园林当中的空间艺术设计表达,也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一、牖的释义
《说文•片部》曰:“牖,穿壁以木为交窗也。从片、户、甫。谭长以为,‘甫’上‘日’也,非‘户’也,牖所以见日。”段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之窗也。在墙曰牖,在屋曰窗。”牖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中构成建筑装饰的主要元素,最开始指人类穴居时洞穴顶上为了满足通风以及采光的需要所开的洞,开在立面的窗则出现得比较晚。牖最初是为满足室内生活需要而出现,后来随着人们精神层次、审美情趣的不断提升,开始在其身上注入了新的功能和灵魂,逐渐将其功能性作用转化为装饰性作用,造型、纹饰、材质都在不断变化,并且在江南古典园林中承担着营造景观空间的功能,超脱最初存在的意义。
二、牖在江南古典园林空间营造中的作用
(一)空间渗透。在江南古典园林中为了解决空间与空间的阻断性问题,让其存在连续性、流通性,从而增加景的层次感,产生“无限”的景,造园人常常打破实体建筑的“实”,在墙面上设置牖,通过在相邻的实体之间留有空间,使人透过间隙看到更多的景象,从而达到“实中有虚”。在空间上打破“实”,也是为了在有限空间环境中表达更多的意境、营造丰富的景观层次而常用的一种处理手法,通过设计让有限的空间给人“无限感”,使人在其中游览时感受到景观层次的变化。1.牖在合围空间中的渗透作用合围空间指的是结合墙体和建筑,围合出比较规整的空间的空间类型。墙体的分割性让整体空间存在了划分,由一变二,由少变多。在墙体中设置牖就会让这样的小空间存在渗透性,让内空间与外空间存在联系性与互动性。外空间的光线可以透过牖引入内空间中从而带来更加丰富的变化,同时透过牖可以把视线引导到外空间中保持视觉上的通透感,以这样的方法打破内外环境的阻断,让人的视线有更多着陆点。王向荣设计的四盒园可以充分体现这样的空间处理手法。四盒园是利用夯土墙将花园围合起来,然后再利用石、木、砖建造了四个“盒子”,分别代表四季,体现出四季的不同变化。设计师运用非常简单的设计语言在最狭小的空间中创造出变化莫测的景观花园空间,让人在身临其中时可以有不同的体验与感知,从而感受到浓郁的诗意和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情趣。在这四个园子当中设计师都把古典园林的牖进行了现代化应用,每一个盒子都巧妙地进行了开窗的设计。在春盒中人们可以坐在长椅上透过墙上的门窗观赏到主庭院的景色,木质的园门可以开启和关闭,不同的开合方式给游人带来不同的景观游览体验。秋盒中的墙体设计了一个个正方形的窗洞,形成一个个框景,打破空间的局限性,让空间与空间产生联系与互动,人在身临其中时不仅仅可以感知到此空间的景色,还可以透过开口观赏到对面空间的景色从而有了更多的遐想的空间。合围空间的空间渗透让狭小的空间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开窗的设计更是从视觉上去弱化了空间本身的体量,让空间与空间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增加了层次感。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可以为现代景观设计提供一个新的解决有限空间矛盾的思路。2.牖在线性空间中的渗透作用线性空间指的是依托于墙体进行分割的空间。这类空间具有很强的导引功能,被频繁地运用于江南古典园林中。在空间布局的影响下,建筑、院落、墙体相互穿插围合从而形成了很多的线性空间,连续不断的墙体在引导着人们前行的同时,对空间进行分割阻碍处理,让人对前方的景色有了更多的想象。墙体上开窗的设计更是打破墙体本身的“实”,透过牖可以看到对面空间的景色,把人的视线从本身的线性空间引导到另一个空间中去,丰富了景观层次。墙体上连续不断的开窗布置让人在动态行走中透过牖看到不同的景观变化,形成一种具有连续性的景观序列。江南古典园林中的线性空间处理手法在现代空间设计中也有比较好的应用案例。王向荣在设计竹园时通过一道折线形的白粉墙和一道曲直兼备的青石贴面墙相互穿插,划分出前院和主院两个院子。不同尺度与方向的墙体引导着游览者的脚步,墙体上的开口让围合的封闭空间实现了内外虚实的空间变化与空间的连续性,动态的走廊形成动态的走势并引导出动态的流线,让人透过墙体的开口体验流转变化的时空感。(二)虚实设计。虚与实作为既抽象又概括的范畴,诗词、绘画、雕塑、文学等一些艺术领域都会有所涉及。所谓“虚”,即空,或者可以说成无;所谓“实”,即代表一种质实。前者是不易于被人所感知的,后者呈现的是有形的、具象的效果,这两者在江南古典园林空间造景中相互依托互为依靠,而牖在江南园林虚实空间营造中更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化实为虚作为一种空间处理手法,常常被应用在设计中,其中的虚实大多并非指建筑实体,而是构成空间的实体界面,即实界面与虚界面的比例关系。当我们漫步在园林中时,即使景色在那里不动,但是随着人行走路径的不断变化,透过牖所看到的景色也在不断变化,此时的景是流动性的,为虚。“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达到情感上的虚实结合,以实为虚,才能获得无穷的意味,达到幽远的境界,有虚有实,才可以让空间更好地流通起来。在江南古典园林中,牖的类型多样,形式是“有”实,表现园主人对于美好事物的期待,透过牖所见的景致为“无”虚,通过有限达到无限。在当代的园林创作实践中,虚实结合的原则更应该体现在园林设计的总体规划当中。“实”即是把客观真实化为创作的形象;“虚”即是通过真实的形象引起人的联想与想象。直接与间接的相互碰撞,意象与意境的相互转换,让整个空间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江南古典园林中,墙代表的是“实”,园林中的一些门窗、走廊、孔洞等设计代表的是“虚”,虚与实产生视觉上的对比,营造出半虚半实的景观效果。而牖的出现在虚实空间中承担的是过渡的功能,透过墙体或建筑的牖以实望虚,让空间在心理上有扩大的效果,在现代景观设计研究中设计师也会为了营造更悠远的空间感而运用这种空间处理手法。红砖美术馆的庭院设计中,以砖砌成的墙为“实”,在墙上设计出圆形、长方形、扇形漏窗及复合型漏斗窗等不同形式的孔洞,透过这些孔洞看到另一个空间的景象为“虚”,人在院落中行走游览时可以随着孔洞的变化看到对面空间中景象的变化。同时,设计师在设计孔洞的位置时进行了创新,把孔洞与孔洞之间进行正框和斜框的不同处理,让人在透过孔洞进行观赏时不仅仅是平视的角度,还加入了俯视和仰视,这样随着人的视觉角度的变化,所观看到的视觉景象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让景观有了更加丰富的视觉观赏点以及层次性。这样的处理手法可以合理地利用在景观空间设计当中,让现代景观设计有新的方向和突破点。(三)视界超越。为了可以把有限的空间扩大化,古人在造园时对如何去突破局限的、封闭的、有限的空间做了很多的探索。比如将视野扩展到院外,是视界超越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把自然山水纳入牖之内的空间意识的实践化,这样可以突破院墙视野的局限性,直接观照自然,这就是从有限中观照无限的观照法。在江南古典园林中我们会在园墙上发现许多的漏窗,漏窗的形式以及纹饰的变化让其更具有古典园林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本来园墙是无窗的,但是加上漏窗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漏窗观察到园内的景色,从一个定点观赏到外景,并且因为漏窗纹饰的不同以及位置的不同,我们观赏到的景色也不同,给人留有许多想象的空间。正是这种不知远方景致如何的想象让整个院子有了更多的曼妙之感,让人有更多探索它的欲望。透过牖的空隙,我们可以从此空间望到另一空间,将本来有限的视野扩大,形成“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视觉效果。牖除漏景之外还有借景的功能,即巧妙地运用借景将远处的景借过来从而使有限的视界变宽变广,将外面的广阔空间和美丽的景色通过借的方式收罗在眼底,使视界又加深一个层次。在现代园林设计中我们同样可以去学习江南古典园林中这种扩大空间感的设计手法,在有限的空间中找到让视域可以更加开阔的方法,可以把远处的景通过牖引借到此空间中,从而产生更多想象的空间。
三、结语
牖作为园林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装饰的功能,其重要价值还在于空间效果的营造。为此本文从空间渗透、虚实设计、视界超越三个方面去探讨,希望通过对牖在江南古典园林空间营造中的应用的分析,为其在现代化设计当中的应用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王玫.空间往复与对景设计[D].天津大学,2018.
[2]胡华中.浅析苏州古典园林空间设计手法[J].美术大观,2017(1).
江南范文篇10
关键词:江南;耕作农具;土壤耕作
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
Abstrac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sanessentiallinkofthefarmcropssystem,whichhascloserelationwithcropsplantersystem.Thisarticlewillaima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Firstly,wewillcarryontheconcretesoilcultivationlinkofeachmaincrops,thendiscussthecultivationsystemindifferentcropsdistributionareacombiningwiththecropsplantersystem.
keywords:Jiangnan;cultivationfarmtools;soilcultivation
土壤耕作制度简言之就是土地如何耕作的问题,实质在于通过犁、耙等工具的机械作用改变土壤耕层构造和地面状况,以调节土壤水肥气热等因素,为作物播种、出苗、生长与发育提供适宜的土壤环境。其由一系列的技术环节所构成,主要有翻耕、耙地、耖田、起垅、开沟、筑畦、中耕、耘耥等[1]。从历史上来说,土壤耕作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对此诸多前贤学人已有相关研究[2]。对于江南所在的中国南方水田的土壤耕作制度而言,以郭文韬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他认为古代中国南方水田的耕作系统大体分为三个环节,即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开垅作沟及套复种的免耕播种。具体来说,又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稻麦两熟田的水耕与旱耕结合,即耕耙耖耘与开垅作沟的结合,另一种是套种田的耕与不耕结合[3]。不过,虽然诸多前贤学人已有开创之作,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总体性的,故对于作物种植过程中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问题却论述不多。基于此,本文就力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时空范围则限定在近代的江南东部平原地区[4]。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先对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进行简要论述,然后再对各主要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具体土壤耕作环节进行探讨[5],最后再与作物种植制度相结合以探讨不同作物分布区内的土壤耕作体系问题。
1、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
土壤耕作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耕作农具,而这些农具又是与一个地区的环境特征及具体的作物种植相适应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耕作农具也应该是土壤耕作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近代江南地区的土壤耕作农具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畜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犁、耙、耖,由畜力牵引进行;一个是人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铁搭,由人力使用进行[6]。当然,这两个系统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相互结合,如在冬播作物的种植过程中,前期的土壤耕作可凭借畜力或人力进行,但后期的开垅作沟与中耕管理环节却通常只能由人力进行。
畜力耕作系统的最主要工具就是犁。与自然环境与具体的作物种植制度相适应,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犁型,即小犁与大犁,也就是水地犁与旱地犁。水地犁主要用于水稻播种及插秧前的水田耕作,而旱地犁主要是用于耕稻板田,也就是割稻后的土地耕作,另外棉花等旱作也是使用这种犁。水地犁犁头为尖形,犁耳为鱼背状,这样在耕作时土就自然会向左右两侧分散。旱地犁的构造略同于水地犁,惟是犁底较短,犁辕较长,犁身稍偏于后,原因在于旱地犁较水地犁耕作时费力,所以犁身较短,这样耕作时就能减少负土量。同时,旱地犁重量较轻,犁辕较长,则这样耕作时拖拉才会更加有力[7]。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水地犁在江南地区的应用中占优势地位。犁外,就是耙与耖。耙的作用在于把大土块弄碎以利于作物种植的进行。耖则是水稻耕作过程中的特有农具,其作用在于进一步把土块弄碎,起熟化水田土壤的作用。对此,《王祯农书》云:“耖,疏通田泥器也,耕耙后而用此,泥壤始熟矣。”但其更主要的作用还在于把泥浆荡起混匀,再使其沉积成平软的泥层,以利于插秧的进行。正如邝璠所云:“耙过还要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摊得匀时好插秧,摊弗匀时插也难。[8]”对于秧田整治而言,又有一种称为耱的农具。耱又名耢,用于摩平整细田面,通常是一块平板,摩刮起的泥土运至凹处逐渐填放、刮平。在江南水田地区这项作业通常被称“落平”[9]。对此,《王桢农书》亦有言:“平板,平摩种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版,长广相称,上置两耳,系绳连轭架车,或人拖之。摩田须平,方可受种。即得放水浸渍匀停,秧出必齐。”
铁搭是人力土壤耕作的主要农具,其也有多种形制,以适应于不同环境与不同工作环节下的工作。如在浙江平湖县,每年秋收之后,为种植春花作物,此时须将田土翻转一次,俗称翻寒田,工具就向用大铁搭,亦称铁耙(俗称寒田铁搭),此种为铁搭中之最大者,四股之端各有铁角,翻土最为有力。春花收获后,在种水稻前,田地亦须翻转一次,俗称翻白田,相比之下,翻寒田是深耕,故用大铁搭,而翻白田较浅,只用中等铁搭(俗称尖刺),其股端为尖形。种水稻所用工具则为小号铁搭(俗称摊耙),功用在于将田土摊匀。又凿沟所用之铁搭,名带翘,大小略小于寒田铁搭,股较细,为防止折断,在尽头横套铁条一枝[10]。嘉善县,铁搭则有满封、套封、平齿、尖齿之分类,满封、套封用于水田翻耕,而尖齿、平齿大多用于旱地耕作[11]。铁搭整地后,通常再用相同的工具弄碎泥块,也有用人力拖拉耙进行的,在耙上放大石条,由人拉动耙田。
曹幸穗先生认为,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种简单化趋势,即人力代畜力,从“犁耕文化”倒退到了“锄耕文化”[12],而其实质就是人力耕作系统对畜力耕作系统的代替。当然,这种趋势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而是很早就已出现。如据曾雄生的研究,南宋以后,由于人口的迁移、增长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熟制的推行,江南地区能够用于饲养耕牛的土地日益减少,于是耕牛的饲养量也就日渐降低。到了明代,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以致于人们不得不以铁搭代替耕牛耕地,所以《沈氏农书》与《补农书》也很少提到养牛的情况[13]。只是到了近代这种趋势更趋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土地零细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因而单靠人力加简单的铁搭就足以胜任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耕牛的使用也就变得没有必要。如在崇德县:“耕地面积狭小,又无荒山草地,平时耕种,人力足以胜任,故牛之饲养尤少,几云绝迹。[14]”开弦弓村,也是“农田较小,每户的土地又是如此分散,以致于不能使用畜力,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鎝’的工具”[15]。常熟兴隆镇亦存在同样的情形,“田少劳多,历史上很少养牛,个别富裕人家偶有饲养”[16]。对于这种情形,德国人瓦格纳也说:“南方的稻田常是极小,以致兽力无所施,这上面固然全靠锄头(即铁搭——笔者注),即在较大的田地上,锄头的使用也是完全普遍的。[17]”与之相反,在那些相对耕地面积较多而人力较少的地方耕牛的饲养就会增多。如在吴江县,其东北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多,故全县的耕牛基本上就都分布于此[18],自然畜力耕作系统也就更为盛行。当然,这种趋势并非是直线进行下去的,在某一短暂时期内也曾有所反复。如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地区的耕牛饲养就一度有增长的迹象[19]。之所以如此,除移民习惯的因素外,背后的关键原因可能还在于人口大量死亡所导致的战后人地关系的相对松弛。
2、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水稻整地,分秧田与本田两种。秧田整地,多选择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冬闲田或绿肥田为之,细细耕耙。如果是冬闲田的话,一般都要冬翻,预备播种前再行翻垦,灌水后反复耙碎,然后进行掏秧沟的工作(据笔者所见,此项工作通常用脚踏进行)。通常沟深半尺左右,两沟间即为撒播稻谷的畦面(俗称秧扇),有时为保证秧沟笔直,先用草绳对面拉直,再沿绳掏出秧沟。秧沟做好后平整田面,并去除稻根等杂物,再用推秧板推平田面,然后便可播种了[20]。为防止过多的稗草混于秧苗间,有时会采取如下措施:“将面泥丕刂去,扫净去之,然后垦倒,临时罱泥铺面,而后以所浸谷下之。[21]”据笔者在江南农村所见,每条秧畦宽约1.5米左右。秧田整地的基本技术要求,姜皋认为要“宜平宜松”[22]。
本田整地,因前作的不同而有多种形式,如《双林镇志》所载:“冬日刈稻后即将田垦转,以深为贵,至来春三月重加翻劚,谓之钞田,欲其土块细碎得水易融合也。有冬不及垦,直至插秧时爬转者,曰筅箒田,以稻本尚留也。又有垦板田,有虽垦而未加钞者,曰镬蓋田,以土片大如镬蓋也。又有并不垦转,蓄水在田,近夏至径插青,谓之烂水田,此皆惰农所为,良农不出此。至若得种春花之田,菜麦既收,翻平沟稜而细削之,谓之折麦稜。[23]”不过总体言之,主要分为三种,即冬闲田、绿肥田与冬作田,此外还有一种就是长期渍水的冬水田,只是在江南地区并不占重要地位。但不管哪种形式,具体耕耙耖的三个环节基本不变,只是每一环节进行的次数各不相同,通常耖只在插秧前进行一次,耕与耙则可能需要进行多次[24]。
冬闲田,俗称白板田,一般先要进行冬耕,但不耙。对于冬耕的基本要求是力求早,正如农谚所言:“正月犁田是块金,二月犁田是块银,三月犁田是块铁,四月犁田是个鳖”[25],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冻融与曝晒,土壤疏松,又可除草沤肥与消灭害虫,因而对于春种有极大的好处。正如宋应星所言:“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使宿藁化烂,敌粪力一倍。[26]”而对于冬闲田的具体耕作环节问题,包世臣曾有详细论述:“刈稻即起板,勿耢。……入春冻解,又耕之,及时,又耕之,乃耢。冬不耕者,老土耗下泽,流土刮上膏,土板不经冻,块硬稻柔,不能起土,收常减。春不耕者,土性冻涩不和,亦减收。[27]”是为三耕一耙。当然,各地情况并非整齐划一,如吴兴县第六区,先冬耕或春耕一次,分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第九区则是先冬耕,然后临插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则在这两个地方耕作环节为两耕一耙[28]。而在桐乡县,传统习惯则是多不从事冬耕:“农民狃于习惯,每年种稻一次后,多不从事冬耕,坐令大好空间,逐年荒废,殊堪惋惜。[29]”
对于绿肥田,通常为二耕一耙,立夏至小满时节犁转土地直接把绿肥翻入土中,或者先把绿肥作物砍成二至三段再翻耕。第一次通常干耕,几天后灌水以让绿肥充分腐烂,然后插秧前再浅耕一次,耙耖后便可插秧[30]。对于绿肥田的土壤耕作,松江县广大农民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早车(耕)田,慢种秧”,就是说翻耕红花草和移栽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间隔,以利红花草充分腐熟[31]。其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为:小满前一周左右时,把绿肥翻入土内七八寸深,小满时节再用水车向田内车水,当田内积水到达一定程度时再用牛牵引进行耕田,耕过之后再用耙进行碎土作业;没有耕牛的农家则用铁鎝进行耕翻[32]。
冬作田则通常为两耕两耙,冬作物收获后随即平整沟稜,先干耕,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进行一两天的晒田作业,然后灌水耙田,待插秧前再进行一次耕耙作业,随后耖平即可插秧。在旧松江府地区,冬作田的具体耕作环节为:耕田开始前先整理田畴,然后犁翻土地,有用牛力,亦有用人力者,耕后耙,是为第一次;耙后灌水入田,四五日后再犁、再耙,是为第二次;也有少数农家为力求精细而进行第三次者[33]。嘉善县冬作田的传统大田耕作亦多为两耕两耙[34]。
而对于长期渍水的烂水田,一般是一年只种植一季水稻,水稻收获后通常不耕,只是到来年插秧前再行耕耙耖的工作,一般只进行一次。对于这种田块,由于常年积水而又只耕耙一次,因而对于作物的生长很是不利,所以曾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说:“耕作仅限于种稻之前幾时,……土壤的耕作这样少,而土壤的流通空气也很少,结果便看见这种长在水中的土地完全普遍的发生一种沼铁,很有害于植物的生长。[35]”
以上我们主要从畜力耕作系统的角度论述了近代江南地区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环节。与之相比,人力耕作系统由于没有畜力等外力的协助,因而在具体的耕作环节上可能就相对简单一些。如在开弦弓村,人们先用铁鎝翻地,“翻地以后,土地粗,地面不平。第二步就是耙细和平地,使用同一工具。一个人翻耙平整一亩地需要四天”。平整土地后灌水入田,每亩田再用一天的时间加以平整,然后就可以插秧了。也就是说,具体的耕作环节只有一耕两耙,并不进行冬耕。至于铁搭耕地的具体过程,则如下[36]:
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搭”的工具,它的木把有一人高,铁耙上有四个齿,形成一个小锐角。农民手握木把的一端,把耙举过头先往后,再往前甩,铁齿由于甩劲插入泥土,然后向后拉耙,把土翻松。
平湖县的人力翻垦工作,也只是在春花作物收获之后、将种水稻之前,用铁搭将田翻转一次,然后用摊耙将田土摊匀,即行插秧[37]。吴兴第一区,本田整地也是只靠人工进行,虽亦为冬闲田,但冬季多不耕地,通常只是于预备插秧时用铁鎝翻土一次,再耧平即可[38]。在此更是只有一耕一耙。至于具体的耕作法及效率问题,光绪《松江府志》则有此记载:“一土大一锄,以旧稻幹根为准,以锄去根二,三锄去根六,所谓三铁搭六稻幹。如此来而往复,一人日可锄一亩。”
对于翻垦稻田的技术要求,沈氏认为一是要深,二是要趁好天气,他说:“古称‘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垦深。切不可贪阴雨闲工,须要老晴天气,二、三层起深。[39]”此外的另一项技术措施就是要力求做得平整,这样才能够使整个稻田都能够均匀的得到水的维护[40]。田整好后插秧,当秧苗长到一定程度时便进行耘耥的工作,以清除田间杂草与疏松土壤。
3、其他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棉花,对于前作而言亦有好几种情形,即冬闲田、草子田与冬作田。冬闲田,一般也要进行冬耕,把表土翻到下层,把底土翻到上面,然后来春播种时再整理一遍。“隔寒将地岔起,以冀害虫冻死,曰岔地。清明后耙松,曰倒地,以牛犁之,曰翻。若土块过粗,再驶一过,曰划。[41]”不论冬季还是春季的整地,“宜多次”,如此才能使“泥土细熟”[42]。当然,在具体的整地环节上可能各地情况不一,如在嘉定,冬闲田就先于冬间翻耕一次,然后到播种前再仔细整地一次[43]。太仓县则不冬耕,通常是于清明前后耕起整地[44]。绿肥田,则到谷雨左右再行耕田,连同绿肥作物翻入田中以做基肥,在川沙就有此种方式施行:“掩入苜蓿头以作基肥,总以土壤匀细、经画井然为合宜。[45]”冬作田,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元麦、蚕豆等冬播作物的话,则到立夏左右收获之后再行耕耙土地。如在嘉定就是如此,春花收获后直接用犁耕地,然后用铁耙(又称为划耙)弄碎土块,并平整土地[46]。太仓县具体环节亦同[47]。如果是小麦、油菜等冬作地,由于小麦与油菜的收获期要到小满左右才开始,而这通常已错过了棉花播种的最佳时机。正如农谚所云:“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花正当时”、“立夏花,大把抓;小满花,不回家。[48]”为把握农时,人们便采取了免耕播种的方法,即在冬小麦收获前一二十天把棉籽播于麦田内,待小麦收获后再行发育。对此,包世臣曾说:“沟塍种小麦者,及小满可于麦根点种。刈麦,棉长数寸,锄密补空,每窝三茎,深锄细敲,无减专种。[49]”在川沙这种方式被称谓“攒花”,只是小麦通常要条播方可。但由于可将“花子及时播入”,因而也就“毋庸翻垦”[50]。
与水稻整地相比,棉花整地过程中没有耖的工序,耕耙次数也没有那么多,相对较为简便一些。但棉花种植过程中需要做畦开沟,这项工作要在耕耙之后进行。在南汇,做畦的工作俗称分畹,“令土凸起成行,畦背之阔无过六尺,高七寸,此行与彼行交错如犬牙,俾一泄水”,但通常是“阔以三尺为度”,且“尤须中高边低,取其泄水”。做好畦播种后开沟。沟分两种,即直沟与横沟,直沟是与畦相平行的沟,横沟又称腰沟,与畦相垂直。“每塍周围务开极深水沟一条(深一尺五寸阔一尺),其在田心每隔三四畹开沟一条(较周围之沟略浅狭),每畹头开小水沟一条(长约五六尺),尤须开浚极深腰沟一条,不然多雨时恒恐水积伤苗。[51]”与南汇相比,嘉定的畦宽在1.5米至3米之间,通常在2米左右,也是中间稍高、两边稍低以便于泄水,畦与畦之间为排水沟,沟深在10到20厘米之间,每隔二三畦的沟开得稍微深一些,畦的两头也分别开沟一条,类似于腰沟的开浚。棉花播种于畦的中间,临近排水沟的两侧则种植大豆[52]。畦做好后播种,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再进行多次的中耕锄草工作。
麦类作物,水稻收获前几天先排水干田,收获后随即耕翻土地,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进行耙的作业[53]。即使耙的话,由于时间紧促,一般也只能是一耕一耙,然后作畦开沟,畦宽通常与上述棉花畦相类似。沟也分两种,即横沟与腰沟。正如《王祯农书》所言:“起土仑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畛。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对于麦田整理的技术要求,《农政全书》有言:“玄扈先生曰:耕种麦地,俱须晴天,若雨中耕种,令土坚土各,麦不易长,明年秋种亦不易长。南方种大小麦最忌水湿,每人一日只令锄六分,要极细,作垅如龟背。”沈氏则认为:“垦麦棱,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种。”张履祥亦说:“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埨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54]”畦做好后播种,在作物的生长过程中要注意适时清沟理墒,对此徐光启曾言:“冬月,宜清理麦沟,令深直泻水,即春雨易泻,不浸麦根。[55]”在此过程中有时还同时进行敲菜麦沟的工作,就是用铁锹拍打麦的畦棱以使之紧实,一方面起壅土的作用,一方面也有利于行水。
其他一些冬播作物,如油菜、蚕豆等,与小麦的整地技术基本相同,在此不赘述。只是就油菜来说,在某些地方畦可能要作的比麦窄一些,如笔者在湖州所见的油菜畦,大约只有50——60厘米宽,高约30厘米左右,畦面很窄,宽约十几厘米左右,极为类似于北方的红薯沟。草子,一般都是采取免耕播种的方式进行播种。“于稻将成熟时之时,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将草籽(红花草)撒于稻肋内,到斫稻时,草子已青,冬生春长,三月而花,蔓延满田,垦田时翻压于土下,不日即烂,肥不可言。[56]”
桑树[57],作为一种多年生植物,对于已成型之桑园自然翻耕无法用牛力进行,只能由人力用铁搭进行。按照沈氏的记述,一年之中,桑园的翻土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秋后、冬季前进行,称为垦,“垦地须在冬至以前,取其冬月严寒——风日冻晒。必照垦田法,二三层起深”。第二次是在春季进行,称为倒,也就是按与第一次相反的方向进行,“若倒地,则春天雨水正多,地面又要犁平(即扒平——陈恒力注),使不滞水,背后脚迹,尽数揉平”。对于垦地与倒地,要在晴朗天气时进行,“非天色极晴不可。若倒下不晒一日,即便逢雨,不如不倒为愈”。此外,桑园还要随时锄草,称为丕刂,亦是“尤要天晴,尤要草未生而先丕刂”[58]。包世臣也认为:“凡桑田皆宜春秋两耕,隔间三尺。[59]”当然,每一个地方不一定都是完全按照包氏、沈氏等所说的方法进行,如在吴兴,翻耕就只在冬季进行一次[60]。
4、余论
土壤耕作制度是与一个地区的作物种植制度紧密相连的,有什么样的作物种植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土壤耕作制度与之相配套,以达到用地与养地的有机结合。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江南地区可大体分为三个作物分布区,即桑稻区、稻区及棉稻区[61]。棉稻区,作物种植夏作以棉稻为主,轮作方式以一年棉一年稻与两年棉一年稻占主要地位。同时,由于地势较高,受水害的程度轻,因此本区冬季作物的种植就相对比较普遍,但由于冬播作物的种植主要是在轮种水稻时才种植,棉花播种后则通常是休闲或播种绿肥,而棉花又是本区最主要的作物,所以总体的作物种植制度以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为主。稻区,则由于地势过于低洼很大程度上并不利于冬季作物的种植,因此本区大部分地区是以一年一熟为主,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但由于本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及开垅作沟与良好的水利设施等保障措施的实行,水稻——麦油等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在本区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桑稻区,则一方面由于地势低洼,另一方面也受蚕桑高收益的影响,冬季作物的种植也并不普遍,在种植制度上则以一年一熟制占优势地位,绝大多数地方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62]。
由于作物种植制度的不同,则各区间土壤耕作体系也必然就有所不同。棉区,棉稻轮作,则土壤耕作体系结合了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耕耙与开垅作沟及棉麦套种与草子撒播过程中的免耕播种环节。具体耕作环节为:一年棉一年稻,则结合方式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两年棉一年稻则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稻区,一年一作的话,则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一年两作,则为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桑区,由于桑的情形比较特殊,只有人力垦倒这一环节,而对于粮食作物而言,由于一年一作占优势地位,则土壤耕作制度主要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由棉区至桑区,土壤耕作制度呈现逐渐简化的趋势。棉区由于冬季作物种植广泛,且夏作物采取水旱轮作的方式,因而土壤耕作制度也就最为复杂;桑区,田以一年一熟为主,地也只是以人力垦倒,因而也就最为简单;稻区,即有大量的一年一熟制,也有相当程度的一年两熟制,因此土壤耕作体系处于两者之间。
-------------------------------------------------------------------------
[1]刘巽洁等:《中国耕作制度》,农业出版社,1993年05月第1版,第195页。
[2]如郭文韬:《中国古代的农作制与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1年12月;(日)天野元之助:《中国传统耕作方法考》,载华南农学院主编:《农史研究》第3辑,农业出版社,1983年4月。
[3]郭文韬:《略论中国古代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4]大体相当于原苏、松、嘉三府、太仓直隶州全部及湖州府大部。
[5]对于大豆,由于一般是间作于其他作物行间,土壤耕作方式也就与其间作的作物相同,因此不予以专门论述。
[6]受资料所限,在论述过程中将主要围绕畜力农具耕作系统展开进行,对人力农具耕作系统只能简单论及。虽然就实际情形而言,由于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一个人力代畜力的趋势,因此人力耕地在近代江南地区或许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实在有限,因此只能简单提及。
[7]《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07号,1927年4月9日,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92页。
[8](明)邝璠:《便民图纂》卷1《耖田》。
[9]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第18卷《农机具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3月,第50页。当然,耱并非完全由畜力来牵引,在缺少耕畜的地方亦有用人力拖拉的。同样,耙也有用人力拖拉进行的。
[10]据《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07号,1927年4月9日,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94页;刘大钧:《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9月,第156——158页。
[11]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224页。
[12]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03—106页。
[13]曾雄生:《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14]赵文彪:《崇德、德清兽疫防治之经过及畜产调查》,《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9期,1935年3月,第14页。
[15]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25页。
[16]常熟市兴隆镇志编纂委员会:《兴隆镇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81页。
[17](德)瓦格纳:《中国农书》,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第232页。
[18]吴江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吴江县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年7月,第191页。
[19]如《乌青镇志》卷7《农桑》所载:“清咸丰庚申、同治甲子吾乡两次兵燹以后,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豫、楚、皖及本省宁、绍、台之客民咸来垦荒,其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亦省功,乡民亦有用牛力耕田者。”
[20]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32—133页。
[21]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
[22]姜皋:《浦泖农咨》。
[23]《双林镇志》卷13《农事》。
[24]当然,各工作环节在每次操作时可能并非只进行一遍。
[2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197、198页。
[26](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27](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任土》。
[28]何庆云、熊同龢:《吴兴的稻麦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
[29]《拟请督导各乡农民,从事冬耕期增副产而除螟患案》,1946年7月28日。桐乡市档案馆,档案号:M8—12—65。
[30]邹超亚主编:《南方耕作制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31]《上海市松江县城东单季晚稻丰产经验调查研究报告》(初稿),1959年12月25日,上海松江区档案馆,档案号:6—11—20。
[32]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第82页。
[33]《松江米市调查》,1936年7月1日,第41页。要指的一点是,由里面的论述可知此处的松江指的是原松江府,而非单纯指松江县。
[34]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33页。
[35]瓦格纳:《中国农书》,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38页。
[36]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5—126页。
[37]张宗弼:《浙江平湖农业调查报告》,《统计月报》第1卷第3期,1929年5月。
[38]何庆云、熊同龢:《吴兴的稻麦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
[39]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40]F.H.King:FarmsofFortyCenturies。
[41]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
[42]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9《风俗志二·物产上》。
[43]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6页。
[44]满铁:《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8页。
[45]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农业》。
[46]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6页。
[47]满铁:《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8页。
[48]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农业出版社,1980年5月,第507页。
[49](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作力》。
[50]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农业》。
[51]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9《风俗志二·物产上》。
[52]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3页。
[53]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东大农科1924年所作的《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苏常道属及金陵道属)里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所有的春花作物来说,这一点似乎很普遍。
[54]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7月,第39、106页。
[55](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6《树艺·谷部下》。
[56](清)姜皋:《浦泖农咨》,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7]严格来说,桑并不能算做大田作物,不过考虑到桑树在近代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及大面积种植,因此在此把其作为一种大田作物对待。
[58]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42——43页。
[59](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任土》。
[60]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编《农林畜牧·蚕桑》,(丁)174页。
相关文章
江南古典园林空间营造分析 2022-11-18 04:09:12
民俗文化保护视角下江南古镇旅游发展 2022-11-27 08:34:08
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元素研究 2022-03-24 08:37:49
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探讨 2022-07-05 10:00:04
汉代江南城市经济发展因素 2022-01-07 06:07:00
诠释江南地区房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 2022-09-09 08: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