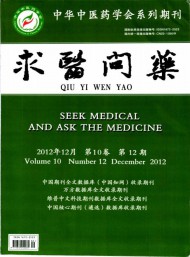本权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06:18:24
本权范文篇1
关键词:公民养老权宪法权利权利谱系
公民养老权是指公民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年龄界限,或者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依法有权享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物质帮助以及家庭的赡养和扶助。
一、生存权与公民养老权
生存是人类的第一基本需要,是人类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生存权是指公民享有要求国家保障维持、延续其生命及其安全和最低生活需要的权利。生存权是各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它是其他基本权利得以存在和行使的基础。“生存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能过像人那样的生活,以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确保人的尊严;其主要是保护帮助生活贫困者和社会的经济上的弱者,是要求国家有所‘作为’的权利。”
徐显明认为,作为明确的法的概念,生存权最早见于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1886年写成的《全部劳动史论》,该书认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群——经济基本权的基础。生存权此时被揭示为:在人的所有欲望中,生存的欲望具有优先地位。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的一般标准,这种由个人按照生存标准提出而靠国家提供物质条件保障的权利就是生存权。
本文认为,公民养老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生存权对于老年人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老年人当中,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是生活贫困者和社会经济上的弱者。养老保障制度其实质是对老年人基本生存的保障。中国政府一直非常关注对公民生存权的社会保障。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强调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将生存权列于中国人权体系之首。新中国先后颁布的四部宪法都有关于退休职工生活保障权和老年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的规定。如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以宪法为依据,我国《劳动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有关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由此,以生存权为核心的公民养老权应当得到全社会的确认和法律的保障。
二、平等权与公民养老权
平等在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平等就是正义。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平等与自由、博爱的理念一道被当作几个世纪以来经过无数革命早已形成的一切事物的完整总结,甚至“平等这个词成为一种原则、一种信条、一种信仰、一种宗教”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被推崇为理想的生活方式。
平等是人权的思想精髓,同时平等也在制度中表现为平等权。平等原则起源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该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是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后的宪法将这一原则确立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法律的立场来看,平等是指在利益方面或无利益方面都没有差别,亦即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没有差别,但并非是指绝对平等,而是法律禁止根据不合理的理由而进行区别对待。主要体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受法律的平等保护,禁止歧视,即在法律上不合理的区别对待。”我国1982年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民养老权与平等权有密切的关系。平等权为公民养老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公民养老权则丰富了平等权的内容。所谓公民养老权平等主要是指公民年老时在享受养老社会保障方面应当是平等的,不论是城镇的老年人还是农村的老年人;不论是男性老年人还是女性老年人。
三、社会保障权与公民养老权
“社会保障来源于社会公正理念下的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即和谐社会赖以存在的个人生活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和谐。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防止社会成员因不可预测因素导致其生活水平的降低,以保障公民在生活发生困难时仍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障的价值在于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通常认为,“社会保障”一词,最初是在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联邦社会保障法》中使用,至少是在法律背景下使用。它反映了国家支持目标的一个概况:从有条件的保险——局限于参保工人——到“为所有贫困和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保护的社会保护制度。”此后,英美两国1941年签署的《大西洋宪章》、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国际劳工组织1944年的《费城宣言》,以及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都先后使用了“社会保障”一词。国际劳工组织积极推动国际性社会保障政策,1952年第35届国际劳工大会专门通过了《社会保障公约》,规定了社会保障的基本准则。从此,“社会保障”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
以保障公民生存权的形式出现在各国立法中的社会保障权是指在公民由于年老体弱、疾病、伤残、失业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发生暂时困难的情况下享受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物质保证,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强调国家的责任,体现了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依赖,赋予政府一种广泛的社会责任,也为公民享有其他基本权利与自由创造了条件。公民养老权既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逻辑起点。依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工伤保障、失业保障、生育保障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换言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障制度,而养老保障制度是公民养老权实现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国家根据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职工工资增长的情况增加养老金。”并规定,对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老年人,或者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能力和抚养能力的老年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制度。
四、劳动权与公民养老权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是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劳动权的内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劳动权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宣示的权利,狭义的劳动权仅指宪法规定的有关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及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在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劳动权的确立是晚近的事情。”
本权范文篇2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消极法治主义观念下,普遍认为“干涉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各国立宪时,在宪法条文中规定的基本上是公民的“反向自由权”,以此来划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防止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因此,自由基本权利是从消极意义上对抗国家权力的基本权利。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集中、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30年代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矛盾,大量失业者出现,工人和公民生活极度贫困化,劳工运动不断发生,他们的存在,不仅会影响经济景气的恢复,而且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影响国民生活的安定,其结果,将动摇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甚至还会威胁其本身的继续存在。为此,政府一改以往“守夜人”的角色,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产业复兴计划,直接或间接保障他们能过上像人那样的最低生活,这样才能消除社会的不安因素,使社会秩序正常化。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宪法中规定了社会基本权利①,以彰显国家的福利政策。因此,在此背景下的社会基本权利,其目的本质上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基本权利就成了对自由基本权利的一种补充物,但另一方面,社会基本权利也承担着保障立宪主义下的宪法秩序的功能,在本质上是与自由基本权利具有同样功能的法的规范。
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认识和反省资本主义“阳光面”和“黑暗面”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宪法中也规定着自由基本权利和社会基本权利,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规定的社会基本权利在制度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权有很大差异,其不是作为自由基本权利的补充物而出现的,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所要实现的价值,因此,在此种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社会基本权利与自由基本权利是并行的,它们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车子的两轮,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基本特征。
二、社会基本权利的效力
自由基本权利是以对抗国家权力侵害的姿态而存在于宪法历史舞台的,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在其受到国家权力侵害时,公民可以请求司法救济,通过宪法诉讼或司法审查,以恢复原先的权利状态。因此,自由基本权利是可以主张的具体性权利,也就是可宪法裁判的权利。然而,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要求国家权力的积极介入为前提的,如果公民发现国家没有积极回应其要求时,公民是否也可请求司法救济呢?以生存权为例,弱势群体靠个人自身努力根本无法维持其生存,为此,需要靠国家提供生活保障和福利资助,才能维持其作为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面临生存危机,如果国家没有主动积极提供必要的生存照顾时,弱势群体公民个人能够以其宪法上的生存权没有得到国家充分保障为由提起宪法诉讼或司法审查呢?也就是说,社会基本权利是否是具体性权利,是否是可主张宪法裁判的权利?
对此问题,在德国和日本有三种学术上的见解。第一,视社会基本权利为“纲领性规定说”。该说认为,宪法社会基本权利“并非是赋予具体的请求权,国家也并未被赋予相应的具体性义务,因而在现实性措施实质上并没有给予国民个人以这种权利之时,国民不能通过诉讼来得到救济”。即社会基本权利只是宣示了国家在法律上的政治性与道德性义务,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要以国家的经济状况及其财政预算为基础,国家采取何种保障措施或如何在行政上将其加以具体化,均应委任于立法裁量或行政上的自由裁量。②第二,视其为“抽象性权利说”。该说认为,国民对于国家享有要求其在立法和其他国家政策上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其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然而,该权利只是“抽象性的规定,需要有立法将其具体化,据此国民请求保障具体生活的权利才能获得保障”,在具体化立法“未能进行之际,国民还是不能以该规定为依据,通过诉讼来主张具体的权利”。也就是在具体化立法后,如果违反法律的诉讼得以成立,也可以一并主张违反宪法的诉讼。
所谓权利,是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特定的利益就是法律上的特定利益,也就是法益,法律之力就是法律所许可向他人主张的力,所以权利义务是对应存在的,如果国家不负有保障公民社会基本权利的义务,宪法社会基本权利的规定只是宣示了国家的政策方针,只是规定了国家的政治性和道德性义务,那么将社会基本权利人微言轻的规定只是宣示了国家的政策方针,只是规定了国家的政治性和道德性义务,那么将社会基本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形态之一规定在宪法中将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的宪法只是“写着公民基本权利的纸”而已。此举将破坏宪法规范作为法律规范之一的最高性、最具权威性特征。而且“纲领性规定说”立论的理由是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归结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预算等国家政策性问题,此立论在逻辑上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其主张把国家预算和国家政策等宪法下位阶的法律规范(国家预算属于立法范围)是否宪法位阶的社会基本权利保障。因此,“纲领性规定说”站不住脚。“抽象权利说”也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该说将社会基本权利的权利效力的有无取决于是否具体化立法,如果具体化立法,宪法社会基本权利就获得了可司法裁判的请求权效力,如果没有具体化立法,社会基本权利就不是具体性权利,这一逻辑也是以低位阶的立法左右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另外,“纲领性规定说”认为“具体化立法后,如果违反法律的诉讼得以成立,也可以一并主张违反宪法的诉讼”。此时的“违法法律诉讼”的对象只要指在行政上的措施而言,也就是行政措施违反法律,进而违反宪法,它不包括法律本身,因为不存在“法律违反法律”的诉讼。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如果存在法律规定以及立法不作为的合宪与否的场合时,“抽象权利说”无法充分解决问题。“具体权利说”的立法初衷是可取的,如果该学说能够成立并被国家权力部门所接受,将极大推动人权保障的发展,并积极督促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采取更为可取的姿态。但这是期盼,其本身不能回避实际问题。“具体权利说”最为致命的缺陷是,在制度层面上各国均没有立法不作为违宪确认诉讼制度③。这一诉讼制度的建构需要国家权力部门(三权)间权力一定程度的调整。即使在建立后,司法判决对立法机关和行政
机关产生多少实际规范效果,以及是否会存在司法权侵入立法权的作用领域的嫌疑,都有待于权力部门间(特别是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政治实践的检验。
以上是对社会基本权力是否具有规范国家权力的效力、是否具有要求国家权力积极作为的效力等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所阐述的一些观点。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该些问题及其观点的提出都是实行三权分立,存在宪法诉讼或司法审查国家下进行的,把这些问题和观点拿到我们国家就不一定可行,因为,我们国家不存在宪法诉讼制度,这一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我国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作用只能停留在“徒法”的层面上。④然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虽然国民经济取得了十足的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劳动力大量失业,一些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等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也会反映到宪法社会基本权利规范上⑤,反映出宪法规定的公民社会基本权利是否具有效力以及效力程度如何等问题,进而,也只有从宪法层面上理顺宪法社会基本权利规范的效力问题,才能根子上从法律角度提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途径。那么,对这一问题,我们国家宪法规定到底能够为我们带来何种信息呢?
三、我国宪法社会基本权利的效力
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自此,‘尊重和保障人权’便由一个政治规范提升为宪法规范,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执政党提升为‘国家’,获的了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规定在宪法中,除了表达国家对人权最基本的态度,以表明它是一个国家在政治方面的最高道德以外,从宪法规范解释学角度分析,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按照权利状态的标准,人权可以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应有人权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凸现人权的价值性,应有人权往往是法定人权的道德依据和理性说明。法定人权是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的人权,是道德意义上的应有人权法定化过程,但同时,何种应有人权转化为法定权,受到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实有人权是能够被人意识到并实际享有和行使的人权,其实际享有程度受到人权主体主观上认识、社会条件和主体行为能力的影响。人权法定化过程的形式之一是人权的宪法化,宪法化的人权就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因此,人权的存在形态包括宪法基本权利。进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涵义之一就是“国家尊重和保障宪法基本权利”。人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其内涵的制度表达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人权不仅包括宪法化的基本权利,而且包括那些尚未宪法化,但随着条件的成熟应该宪法化的人权,因此,人权具有创造功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打破了我国先前宪法基本权利列举式规定所带来的略显僵化的局面,为人权推定提供了宪法规范基础,表明宪法基本权利是开放性的权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在我国宪法第33条中,该条是宪法基本权利的基础性和统领性规定,人权保障条款加入其中,使宪法规范结构更加合理,整合了先前基本体系相对松散的局面。
回到自由和社会基本权利问题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有何意义呢?上面已经分析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涵义之一是“国家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尊重”是尊敬和重视的意思,尊重表明国家权力行使要受到合理限制,国家负有消极不侵犯基本权利的义务。这一点对于自由基本权利和社会基本权利都是适用的。自由基本权利本来就是以消极防止国家权力侵害存在的,尊重基本权利正好回应了这一权利效果。然而,社会基本权利也有同样的效果,社会基本权利除了要求国家权力积极介入的权利效果以外,还有消极防卫的权利效果的一面,如公民的受教育自由(受教育权),劳动自由(劳动权)不受国家权力侵犯。因此,社会基本权利具有复合权利效果。我国宪法条文中多处有“保障”规定。“保障”是指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保证相应目标的实现。对于自由基本权利,在其受到国家制度保障功能。对于社会基本权利,国家要运用国库预算和其他手段积极有效地保障其实现,此时,社会基本权利具有受益权功能和制度保障功能(国库预算及其配套手段本身是以国家《预算法》为基础的)。宪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因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国家”主要指的是国家机关,即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从上面分析得出,宪法基本权利具有规范国家权力的效力存在,这一点正好呼应了宪法序言“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的规定。然而,这只是宪法基本权利效力有无的一个方面问题,另一方面是,基本权利的效力程序如何的问题。具有到社会基本权利,就是社会基本权利在具有规范效力的情况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要求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其实现的问题。上文已经提到,在国外对社会基本权利是否是可司法裁判的具体性权利,存在着“纲领性规定说”,“抽象性权利说”和“具体权利说”,并且三种学说都存在着不足,并且作者指出这三种学说是在实行宪法诉讼或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我国在由于不存在宪法诉讼制度,因此,这三种学说不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然而,实际上不全都反应制度存在和制度设计,我国宪法规范条文规定来看,不全然没有可以凭据的制度因子。
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如果这一制度真正实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社会基本权利保障相违背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我国宪法第3条和第128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并监督审判机关,如果人民法院的司法判决违背了宪法社会基本权利保障的规定,也是可以被撤销的。宪法第62条第11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不适当的决定,其中包括违法反宪法社会基本保障宗旨的法律,因此,也可以被撤销。具体到这里,宪法所能提供的制度信息已经用尽,宪法规范中没有可以撤销全国人大制定的违背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宗旨的规定。
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社会发展的某一个特定阶段,社会基本权利的内容客观上会有一定的标准存在,一旦这些阶段性条件具备,如果还承认宪法规范最高效力的话,国家应该努力实现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宗旨,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议,使社会基本权利成为可操作的具休权利,并且任何国家机关只能往更充分保障社会基本权利的方向立法或修改法律,不能任意废除己获保障的法律或使保障的条件变差,剥夺已经是公民具体权利的社会基本权利。与此同时,任何权利的充分实现都存在的代价,代价之一是社会成本。“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⑥社会基本权利的阶段性特征也决定了,在某一阶段是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要求不能超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库收支状况,社
会基本权利具有过程性,需要逐步实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纲领性规定说”、“抽象性权利说”和“具体权利说”的部分结合。社会基本权利具有规范国家权利的效力,通过对“人权保障条款”和我国宪法规范中法律审查制度因子的分析,说明它是具体性的权利,而不是“纲领性规定说”所主张的方针性条款;然而,仅仅停留在宪法规范上,社会基本权利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内容和标准存在,因此,需要具体化立法,但是,这一具体化立法是在承认社会基本权利具体性权利基础上的“自上而下”立法,而不是,“抽象性权利说”所主张的通过“自下而上”的立法,进而推导出宪法社会基本权利性存在的;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其具体内容具有客观性,对这一客观性的内容是公民所可以主张的,但同时也不能超出这一水平,而为过分苛刻的要求。因此,社会基本权利又具有纲领性的要素存在。
参考文献
①例如德国宪法“基本权利”一章中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工作权、受教育权及“财产权负有义务”等。
②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③具体参见阿部照哉等编著《宪法》(下),周宗宪译,元照出版公民2001年版,第211页。
本权范文篇3
多少人还在对这个兴趣浓浓?有多少人还对这个深信不疑?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3.15的维权讲座似的宣传,老百姓的心里早已明白原来
有这么多黑心商家在侵犯着他们的利益,原来有这么多的霸王条款在欺凌着他
们的权益,原来他们是可以通过法律通过消费者协会来与此抗争的。但同时,
那些不法商贩们不知道么?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的努力是有了一定的成效的。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许多造假者的手段更加高明,黑心商贩们的技巧也日渐成熟,而我们的消
协却始终固守着老一套的规矩没有太多的变化。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买到了
一件有问题的商品,与商家的交涉无果,于是投诉到消协,消协首先要做得先
要与商家协商,如果对方买了这个面子,还好,事情算是顺利解决,如果同样
不能,这时候就会要求消费者到有关部门去对商品作技术上的鉴定,鉴定的费
用也要有消费者自己承担,况且作技术鉴定的费用有时会超过商品本身的价
格,那么就算消费者最终投诉成功,得到了赔偿,这期间耗费的时间,花掉的
精力,也使得这种赔偿变成了得不偿失。单这一点,就会让很多人打了退堂
鼓。耗不起这个精力,时间,还有金钱。除非是向王海那样的职业打假者,或
者是商品的价格不菲,不然,平头百姓谁会经得起如此的折腾?
也正因为这一点,造成了很多人吃了亏就自认倒霉,导致一些不法商家的不
法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
所以我认为,维权工作应该从这些方面考虑一下,一些原本有消费者去做的
事情,比如商品的技术鉴定等,是否可以改变一下,与其让消费者去证明这个
商品有问题,不如改为由商家来证明自己的商品没有问题,这样既可以降低消
费者维权过程中的难度,又可以对不法商贩们起到震慑的作用。毕竟买到有问
题的东西错不在消费者。
国家花了大力气去打假是在为百姓做实事,如果这个实事能够从百姓的角度
多考虑一下,那么就更能得到百姓的认可,也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同
本权范文篇4
虽然我国的宪法规范和人权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但是人们对防御权功能所体现的基本权利的价值却仍然缺乏深刻体认。我们仍然习惯于“国家应当保护基本权利”之类的表述,习惯于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国家权力与公民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真正意识到“消极无为”才是基本权利对国家权力最为根本的要求。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对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的概念意涵、宪法地位以及防御权功能所针对的国家的消极义务等内容的分析阐释,厘定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
一、防御权功能的概念
由于防御权乃是基本权利最原始和最根本的功能,所以学者们对防御权概念的界定就不像其他功能那样歧义丛生。[4]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可以定义如下:防御权功能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权能,指公民得要求国家不侵犯基本权利所保障的利益,当国家侵犯该利益时,公民得直接依据基本权利的规定请求停止侵害。防御权功能又可被称为“国家不作为请求权”功能或“侵害停止请求权”功能。对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考察之:
1、防御权功能是基本权利的一项权能。防御权功能只是基本权利的权能之一,本身并非基本权利,而学者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直称为“防御权”,这并非是将之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而仍是指基本权利的一项权能。
2、防御权功能以“国家不作为”为请求内容。防御权是要求国家不为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故而是一种“国家不作为请求权”功能。如国家以积极行为侵害了基本权利,防御权的意义就在于请求国家停止侵害。
3、防御权功能针对的是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义务。防御权功能是防止国家的积极侵害行为,故而国家只须无所为,其针对防御权功能的义务就已实现。国家对防御权功能所负的义务是消极义务、不作为义务。
4.防御的对象是违法侵害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依据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公民可以请求排除国家权力所为的各种侵权行为。其中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侵害基本权利的法律,行政机关侵害基本权利的行政处理和司法机关侵害基本权利的裁判等。
二、防御权功能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与界定
(一)防御权与自由权
很容易看出,防御权与自由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二者就是相同的概念,防御权不过是自由权的别称罢了。自由权在其最基本、最狭窄的意义上就是个人排除国家介入私人领域,以确保个人自由决定与自由行动的权利。这种狭义的、纯消极性的自由权与防御权功能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要求国家不作为,防止国家对权利的侵害。
这里有一个显然的问题:既然防御权与自由权在根本意义上是一致的,那么“防御权功能”是否是一个冗余的概念。我们知道,概念只是理论思考的工具。任何一个崭新概念的提出,都应当有所助益于思考的深入,如果使用旧有的概念就可以准确地描述和分析问题,那么新概念就是徒增无益的,应该被哲学的“奥卡姆剃刀”剔除。实际上,德国宪法理论之所以概括出“防御权”这一概念并逐渐为各国宪法学所接受,是有其理论上的必然性的。之所以在基本权利研究中需要这样一个概念,乃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首先,防御权只是自由权的功能的一个方面。按照传统的理解,自由权所对应的是国家的消极义务,也就是国家不必对自由权作任何的行为。但实际上,自由权也要求国家履行积极的义务。这种积极义务包括两个方面:(1)自由权的实现要求司法机关提供司法救济。也就是当自由权受到侵害的时候,自由权人得请求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裁判以排除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乃是应自由权人的请求为特定的积极行为——裁判行为,国家对自由权履行的是积极义务。如果国家不承担此种积极义务,自由权就无法实现;(2)自由权的真正实现,往往需要国家直接的积极作为。例如,美国学者唐纳利认为,不受虐待的人身自由通常被看作是典型的消极权利,只是要求国家不要侵犯个人的自由与身体。“但是,确保这种侵犯不会发生,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要求重要的‘积极’计划,它包括训练、监督和控制警察和安全部队”。[5]“自由权仅仅作为一种消极性权利无法实现”。[6]又比如许多国家宪法规定的“知情权”。知情权最早是从“表达自由”中发展出来的,人们表达意愿的自由本来就是以“接受者”的存在为前提的,由此“接受者”也就有接受意见的自由。所以,知情权在其本来意义上是一种自由权,是个人排除国家干预的权利,国家的义务形态是不作为。但是,随着资讯在当代社会中重要性的大大提升,资讯对于个人发展的意义也大为增加,而个人获取资讯的能力却相对地减弱了。这种情况下,知情权就发展出要求国家积极地公开资讯,提供资讯的性质。[7]所以,知情权就既是具有防御权功能的在获取资讯上不受防碍的权利,也是具有“受益权功能”的要求国家积极地公开情报的权利。相应的,国家对知情权的义务就既有不侵犯的消极义务,也有积极提供资讯的积极义务。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由权的实现并不只是要求国家不侵犯,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求国家采取积极的行动。所以,防御权只是自由权所具备的防止国家干预的功能,尽管这仍然是自由权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重要的功能所在,但并不是自由权之全部。防御权与自由权并非完全重合的概念。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自由权在现代的宪法理论下已非意义单一的概念,“自由权”已不足以作为当代宪法学分析基本权利问题的“元素性”概念。当我们说“A权利是一项自由权”时,我们并不明确与此项权利相对应的国家义务是消极义务还是积极义务。而如果我们说“作为防御权的A权利”,或者“A权利的
防御权功能”时,其涵义才是单一和明确的。图示如下:
国家的消极义务
自由权防御权功能国家的消极义务
国家的积极义务
所以,由于基本权利性质的综合化,我们以包括防御权功能在内的“基本权利的功能”作为性质上更为单纯的元素作为分析基本权利的工具就具有必然性。
第三,防御权功能不仅是自由权所具有的功能,同时也是其他种类的基本权利的重要功能。例如,以要求国家为积极的促进行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权”,同样也具有要求国家不侵害的功能。这一点,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中进行详细的说明。
(二)防御权与受益权
我们知道,除要求国家不为侵害行为的“防御权功能”外,基本权利还有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以促进基本权利实现的功能,这些功能中最重要的是“受益权功能”。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是指公民基本权利所具有的请求国家作为某种行为,从而享受一定利益的功能。[8]受益权功能所针对的乃是国家的积极义务,也就是国家要以积极的作为,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服务或者给付,所给付的内容可以是保障权利实现的法律程序和服务,也可以是对公民在物质上、经济上的资助。[9]受益权功能是与防御权功能在规范内涵上完全不同功能,防御权要求的是国家的不作为,而受益权要求的是国家的作为,前者要求的是国家不侵犯基本权利,而后者要求的是国家积极干预基本权利以促成其实现。受益权功能与前述的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是价值理念完全不同的概念。防御权功能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国家可能对基本权利进行的侵害,是要求国家不作为,体现的是“自由法治国”的理念;而受益权功能的目的则是要国家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中承担更为积极的角色,通过各种积极的作为去帮助基本权利的实现,所针对的是国家的作为义务,体现的是“社会法治国”的理念。可以这么说,同样是对国家活动的一种要求,防御权功能是要“限制国家”,要防止国家成为专制的、残暴的、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而受益权功能是要“鼓励国家”,让国家成为帮助和促进人们享受幸福生活的积极力量。
防御权功能和受益权功能是各基本权利所普遍具有的两项功能,也就是说,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一方面要求国家不为侵害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求国家通过一定的作为促进乃至直接实现基本权利。不同的基本权利往往都同时具有这两项权能,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
三、防御权功能的地位
前文对防御权功能的概念和内涵作出基本说明。下面,本文将讨论防御权功能的宪法地位。对此问题,本文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首先,防御权功能的意义在于排除国家对公民自由的干预,那么防御权功能是否只是自由权所独有的一项功能,抑或是各类基本权利所普遍具有的功能;其次,在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各项功能当中,防御权功能居于怎样的地位。分述如下:
(一)防御权功能是基本权利所普遍具备的功能
虽然防御权功能主要是从自由权所导出的,或者说防御权功能主要体现的是基本权利的自由价值。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权利的基本功能,防御权功能是基本权利所普遍具有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哪些主要是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也同样具有要求国家不侵犯该项权利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宪法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分三个层次来说明:
1、宪法第三十五条——四十条及第四十七条第一句
这些条文确立的是公民的自由权,从中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我们可以从这些条文的用语中得出这种认识。例如,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这显然是说明宗教信仰自由有排除国家权力干预的功能。又如第三十七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种表述显然意指公安机关在无检察院批准或法院决定的条件下,不得限制人身自由,这体现的也是人身自由防御国家侵害的功能。而其他各条款都是以“禁止国家行为”、“不得(作为)”这样的规定方式来确保公民的自由,体现的也都是个人权利防御国家侵害的功能。
2、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一条
这两条分别规定了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公民的申诉、控告、检举、批评、建议权,这两项权利在性质上无疑是更具积极性的。选举权利除去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一层民主的涵义外,主要是要求国家为特定给付,也就是要求国家组织选举的权利。但这一条款的“但书”部分却说明:选举权、被选举权也具有防御权功能。第三十四条“但书”规定:“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一规定可以作如下解释:公民的政治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可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加以限制,但在一般情况下,“制定法律”之外的国家行为不得剥夺公民选举权利。这说明,选举权、被选举权也具有防御权的功能。
而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检举、控告、申诉”等权利无疑也是更具积极性的,这从四十一条二款的第一句话也可以看出,“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无疑是说国家对这样权利负有为特定积极作为的义务,在这种意义上,这几项权利并非“防御国家的权利”。但四十一条二款第二句却说明了这些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对于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显然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侵害公民的检举权等权利,这些权利本身也具有排除国家侵害的防御权功能。
(三)第四十二条至第五十条
这些条款主要是规定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和对特殊主体的保护。若从权利性质来看,这些权利无疑是最具积极性的权利,是要求国家为各种积极的行为,去保证和促成这些权利的实现。所以,若从这些条款的文字来看,无法找出“禁止”、“不得”、“不受侵犯”这一类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的用语,所以无法从中直接导出防御权功能。但是若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却可以发现这些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中隐含着防御国家侵害的功能。
以劳动权为例,虽然该权利的主要意旨在于要求国家通过各种积极措施,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劳动保护,提高劳动报酬与福利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为积极的行为去禁止公民就业,禁止公民劳动!同样的,国家对休息权、退休人员保障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所负的义务是以积极行为去保证和促进这些权利的实现,但这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以积极的行为去禁止公民休息,禁止退休人员、受物质帮助人员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得经济上、生存上的保障,或者禁止公民接受教育。[10]所以,可以说防御权功能乃是社会权必然具有的一项功能,只不过社会权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个人的积极义务,因而并不将公民拥有“劳动的自由”、“休息的自由”、“谋生的自由”、“受教育的自由”等在法条中加以明示
罢了。
在这些条款中,第四十七条最鲜明地表现了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双重属性和这些权利具备的“防御权”和“受益权”的双重功能。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前一句说明了“文化活动自由”具有排除国家干预的防御权功能,而后一句则说明了“文化活动”具有要求国家积极介入的受益权功能。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防御权功能是各类基本权利所普遍具备的一项权能,任何一项基本权利的规定都意味着公民可以依据这项权利去对抗国家的侵害,“防御公权力的侵害”乃是一切基本权利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防御权功能在基本权利功能体系中的地位
基本权利除具有防御权功能外,还具有受益权功能、制度性保障功能、程序保障功能等多项功能,[11]那么,防御权功能在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呢?我们应当首先明确的是,防御权功能是基本权利的各项功能中唯一的“纯消极性功能”,而其他的各项功能都是积极性的功能,(例如,受益权功能是要求国家提供物质的或其他的给付,制度和程序保障功能是要求国家建立各种可靠和有效的制度、程序以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所以,防御权在基本权利功能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的关系问题。
国家应当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或者说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实现上,是仅仅做到不去侵害权利就已足够,还是需要以各种积极的作为去促成,这是政治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各国宪法的规定也都会体现出与其民族传统和立宪精神相关联的不同的国家观念,本文无法一一尽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在这一问题上构成了差异的两极。所以,本文将通过这一宪法类型上的基本分类,探讨基本权利防御权功能的地位。
1、资本主义宪法中防御权的地位
在西方宪法中,防御权功能被看作是基本权利最根本的功能,相应的消极义务被认为是国家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义务。资本主义宪法特别强调基本权利是为防御国家侵害而规定的,强调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不侵犯的义务”。而国家对基本权利的积极作为,即使不是侵犯行为,而是帮助和促进基本权利实现的积极作为,也往往被认为是危险的。在西方宪法观念看来,帮助、促进基本权利实现的行为与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之间并无绝对界限。因为,西方宪法学说对国家的一切积极行为都持一种谨慎和怀疑的态度,这在西方各国宪法中都有体现,而尤以美国宪法最为典型。美国《权利法案》实际上确立了这样一种规范模式:“(国家)不得侵犯某权利”或“某权利不受侵害”,这种规范模式体现了对国家积极行为的概括性怀疑,强调消极义务在国家的各项义务中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所以,基本权利首先意味着防御国家的侵害是西方宪法观念中深入骨髓的认识,故而西方宪法理论将防御权看作基本权利最根本的功能。
但是,随着宪法内容和实践的发展,西方宪法理论也开始认识到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实现有着积极的意义,国家消极义务的绝对中心地位似乎有所松动,这一变化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社会权在各国宪法中的出现。但是,在西方宪法上,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仍然被认为是根本性的,消极义务也仍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义务。在一些人看来,尽管国家的积极义务已被认为是基本权利实现所必需,但积极义务仍然只是辅助性的。德国学者提出一种“辅助性原则(DasSubsidiaritaatsprinzip),认为国家只有在个人和社会无法自行达到公共利益时才负有积极作为义务。相对于国家消极无为之下的”社会与个人自发性行为“而言,国家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承担的积极义务只是辅助性的,[12]只有在公民穷尽了自己的一切手段仍不足以实现自己权利时,才会在防御权之外动用基本权利的其他权能,国家履行积极义务始为必要。[13]将消极义务作为国家的根本性义务而加以强调的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一些国家宪法理论滞后于宪法实践。比如美国,在美国的宪法实践中,各种社会权利(美国称之为”福利权利(welfarerights)“)已经大量地由法院通过对”平等保护条款“的阐释而实际上成为公民权利的内容,但宪法规定和一些宪法理论却仍在坚持消极义务的根本性地位。在罗斯福新政以后,”四大自由“已成为美国社会政策不可回避的内容,国家为保证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已在向大量失业者、老人和无自立能力的人提供着物质和经济上的帮助。[14]但这种国家的积极作为却并不被一些人认可,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各种促进权利实现的积极措施,而只不过是慈善,而非法律上的义务。”国家可以给予或者撤回,只要它高兴。提供公共福利的任何行为既不是法律上无法实现的义务的履行,也不是超越义务要求的行为。“[15]这种观念依然否认积极义务是国家义务,而强调消极义务才是国家根本义务。而日本学者在定国家积极义务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也强调在考虑基本权利问题时,”仍不能不以‘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的思想为基本“。[16]这些都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将国家的消极义务作为国家义务中最根本的内容,而防御权功能也依然是基本权利功能体系中最根本的部分。
2、社会主义宪法中防御权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却从来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防御国家侵害的工具。社会主义宪法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取得统一与和谐,个人与国家在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社会主义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并非资产阶级宪法中的基本权利那样是个人对抗国家的工具,而是个人与社会整体共同努力、共同参与、共同分享之权利。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依靠国家与社会的努力。所以社会主义宪法最为重视的基本权利的功能应该是“受益权功能”,最为重视的国家义务是国家的积极义务,是国家积极协助以促进实现社会主义者的人格的义务。而“防御国家侵害”并不被社会主义宪法学说看作是基本权利最根本的功能所在,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宪法理论中,国家与个人的利益被认为是一致的,国家不会有意去侵犯个人权利,所以也就不必强调具有防御国家侵害的作用。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规定来看,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以劳动、休息、生存、受教育权等社会经济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如苏联1936年宪法),这种权利构造强调的是国家帮助和促使公民权利实现的积极义务,与资产阶级宪法将自由权作为最核心内容而格外强调国家的消极义务是不同的。
但是社会主义宪法并非孤立的和静止的,在社会主义宪法的发展中,基本权利“防御国家侵害”的作用和国家消极义务的地位又被重新考虑。这是因为,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完全统一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将是极为漫长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认识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和国家不侵犯的消极义务是极为必要的。例如苏联1977年宪法第五十七条对国家义务进行规定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尊重”
的义务,这一条规定实际上是提升了消极义务在国家义务体系中的地位。而我国刚刚完成的修宪也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内容,其中的“尊重”这一用语体现了对消极义务重要地位的再认识,也是从反面对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作出了规定,这是我国基本权利的实践与理论的重大进步。但是,从宪法的这条规定却无法看出防御权这一“纯消极性功能”和其他的积极性功能之间应当是怎样的关系,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不侵犯义务”和“保护义务”之间应当如何协调,如何防止“保护”异化为“侵害”,这些都是需要宪法理论与实践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四、防御权功能所针对之国家消极义务
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可以导出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消极义务”,也就是国家负有不侵犯基本权利的义务。但是消极义务的内容是不作为,我们无法从正面去说明不作为,我们只能从其反面,也就是国家机关对基本权利的“侵害”的角度去界定各机关的消极义务。也就是说,只要能界定国家机关的哪些行为是“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我们也就能够明确各国家机关对基本权利的“不侵犯义务”是什么。
(一)立法机关的消极义务
立法机关对防御权的消极义务是指,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任何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实际上,防御权也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来自于宪法的规定和基本权利自身。如果立法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理由和方式对基本权利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就应该是正当的,不应该被看作是对“消极义务”的违反。而相反地,如果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不是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式和理由进行的,则立法机关就违背了其“消极义务”,其行为也就是“侵害行为”。所以,立法机关对防御权的不侵犯义务并非是是指立法机关不得对基本权利作出任何限制,而是指立法机关不得违背宪法规定的条件而对基本权利加以恣意的限制。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宪法规定的限制基本权利的条件,来界定立法机关消极义务的范围。凡立法机关不符合此条件而对基本权利进行的限制,就是对“消极义务”(或“不侵犯义务”)的违反。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限制所须符合的条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7]
第一,限制方式——法律保留。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立法机关才可以对基本权利作出限制。除此以外,以其他任何方式对基本权利进行的限制都只能被认为是侵犯基本权利,是对立法机关的消极义务的违反。
第二,限制理由——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只有为了防止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才可以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限制,除此以外,以任何理由对基本权利进行的任何限制都是违反国家“消极义务”的行为,都是对基本权利的侵害。
(二)行政机关的消极义务
在一个法治主义得到严格遵循的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不侵犯义务”主要是针对立法机关的。这是因为,如果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没有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只是在法律之下执行和适用法律,自然也就不会侵害到基本权利。但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其活动中都有可能违反法律,造成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同时在它们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也有可能侵害公民基本权利。所以,在理论上应明确的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遵守法律之外,还有遵守宪法,尊重公民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义务。
1、违法的“干预行政”
干预行政,又称侵害行政,是指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干预公民权利,限制公民自由与财产,或科以公民义务或负担的活动。[18]例如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都属于这种直接干预或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行政”。干预行政由于是直接干预公民的权利,故而受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除了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外,干预公民权利的行为还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19]从相反的角度讲,如果行政机关对公民的权利的限制或剥夺是严格地依据法律明确授权而进行的,行政机关的行为就不应被视为违反了宪法上的“消极义务”,受限制的个人此时只能主张立法机关的法律违宪,主张是立法机关违背了其“不侵犯义务”。只有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的行为,才是行政机关违反消极义务的侵权行为。举例说明,按照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集会、游行妨碍交通,不听民警指挥的,可以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贰佰元以下罚款。如果行政机关依据这些规定对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给予处罚,则行政机关并不违背其对宪法中公民“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所负的“不侵犯义务”,当事人如认为自己的此项权利受到侵犯,只能主张这三项规定违反宪法,主张是立法机关违背“不侵犯义务”而对此项自由作出了过度的限制。行政机关只有在集会、游行并未妨碍交通的情况下作出处罚决定,才是对“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侵犯,是违背了自己的“不侵犯义务”。
2、违反比例原则
尽管行政机关在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时必须遵从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或者说法律必须对干预行政作出明确的规定与授权。但无论如何,法律的授权必须给予行政机关以一定的裁量权,比如在规定行政机关的处罚权时规定一个范围,如“十五日以下拘留”、“贰佰元以下罚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行政机关如何“合理”行使裁量权的问题,如果行政机关限制公民权利是合乎法律规定的,但是并不合理,也应被认为是违反了“不侵犯义务”的侵害行为。关于行政行为“合理性”的认定,各国公法学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我认为其中最可供我国借鉴的是德国的“比例原则”。一般说来,比例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20]
第一、适当性原则,又称“合目的性原则”。是指干预行政的作出,必须合乎宪法的目的。在我国宪法下考虑适当性原则,应当是指,行政机关干预公民基本权利应符合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第二、必要性原则。是指在能够达到维护“公共利益”这一目的的各种手段中,行政机关应当选择其中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少的手段。以前文所举的限制游行、集会的例子来说,如果集会、游行妨碍交通,行政机关处以罚款足以使得集会游行人认识错误而自我纠正,就不必选择更为严厉的“拘留”作为处罚手段。
第三、狭义比例原则。这是指虽然为了实现公益目的,必须选择某种手段,但是该手段所引起的公民负担的增加和副作用与所欲达到的目的显然不成比例时,可以考虑放弃此目的,也就是不采取这种手段。仍以集会游行为例,如果集会、游行已妨碍交通且十分严重,此时除拘留游行集会人员外无法恢复“交通秩序”这一“公共利益”,但是这样大面积的拘留会使很多人丧失人身自由或会激起更激烈的冲突,此时,行政机关应放弃维护交通这一目的。
以上三点都是对行政机关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性条件,是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规定。如果行政机关的行为只是合乎法律的规定,但是不合乎这些“合理性”原则,仍然应该被认定是违反了对基本权利的“消极义务”,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
。
(三)司法机关对防御权的消极义务
司法机关违反消极义务,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枉法裁判
这是指法律并没有限制和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法院却错误的适用了法律,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限制。这种行为就是违背对基本权利的“消极义务”而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法院进行了枉法裁判,当事人可以提出上诉,由上级法院予以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将法院的枉法裁判行为看作是违反宪法上“消极义务”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当法院的枉法裁判是终审的裁判时,当事人所遭受的权利侵害就无法在普通司法程序中获得救济,此时将枉法裁判看作是法院违反宪法上的“消极义务”的行为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当事人可以主张法院违反了宪法,向宪法法院或者其他的违宪审查机关要求救济。[21]所以,强调司法机关对基本权利负有“消极义务”的主要意义是违宪审查层面的。
2、滥用司法裁量权
如同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时有裁量权一样,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也有裁量权,而且司法裁量权也会被滥用。也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可以作几种不同的解释,而法院却选择了与宪法相违背的那种,并作出了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法律违宪,而是法院对法律的解释违宪,是法院滥用了司法裁量权。[2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应认定法院的裁判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是法院违背了宪法上对基本权利负有的“消极义务”。
3、违法的司法强制
除了前述的两种错误裁判有可能被认定是违反“消极义务”的侵害行为以外,司法机关还有可能因为在司法程序中违法使用司法强制措施而被认为是违反了“消极义务”。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规定了“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规定法院可以对有违反法庭秩序、伪造毁灭证据、妨碍调查取证等行为的诉讼参加人和其他人进行罚款、拘留等司法上的处罚和强制。这些司法强制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如果法院违法实施了这些司法强制措施,也应当被看作是违反了其在宪法上的“消极义务”,对基本权利进行了侵害。
注释:
[1]BVerfGE7,198.在这一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宣称:“基本权利主要在于确保个人的自由领域免于遭受公权力的干预;基本权利是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御权。”资料来源:www.oefre.unibe.ch/law/dfr/bv007198.html
[2]与德国宪法学有着不同的权利理论和概念体系的美国宪法学,也开始接受和使用这一概念。See,DavidP.Currie,PositiveandNegativeConstitutionalRights,53U.Chi.L.Rev.868(1986)。
[3]参见陈宝音编著:《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17-118.
[4]关于防御权功能的定义,参见,李惠宗:《宪法要义》,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页91;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页62-63;许宗力:“基本权的功能与司法审查”,《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页156.
[5]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王浦劬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32-33.
[6]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210.
[7]芦部信喜:《宪法》,李鸿禧译,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页172.
[8]曾康繁:《比较宪法》,三民书局,1978年第三版,页119.
[9]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页63-67.
[10]关于受教育权的防御权功能,可以参考温辉博士对“受教育自由”的研究“。温辉:《受教育权入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7以下。
[11]参见理查德·巴乌姆林等编:《联邦德国基本法释义》,赫尔曼·卢西特罕德出版社1984年版,页249-267.中文资料可参见,庄国荣:“西德之基本权理论与基本权的功能”,《宪政时代》第十五卷第三期,页32-33.
[12]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作者自版,1997年修订六版,页23-24.
[13]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223.
[14]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291-293.
[15]CarlWellman,WelfareRights,RowmanandLittlefieldpress(1982),p3.
[16]芦部信喜:《宪法》,李鸿禧译,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页102.
[17]“法律保留”和“公共利益”是确定基本权利界限的基本原则,也是立法机关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两个原则都是宪法理论中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另文探讨。
[18]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页327.
[19]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30.
[20]参见蔡震荣:《行政法理论与基本人权之保障》,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5月二版,页105-106.
本权范文篇5
一、第三人效力是德国问题吗?
基本权是否(Ob)对私法产生效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如何(Wie)产生效力并且产生哪些(Welche)效力1,即是本文所追踪的目标--基本权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问题。在德国,这个问题也常常在"基本权与私法"标题下讨论2;也有人称其为水平效力(Horizontalwirkung)3问题,水平意指私主体间的平等关系,相对应的是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垂直的上下位关系(vertitaleUnterordnung),而这种上下位关系与德国基本法人民主权理念严重冲突,所以"水平效力"一语不应使用4。
第三人效力问题在深受德国法影响的日5、韩、台6照搬照抄应该不算奇怪,可美国7、南非8宪法学界也争论这个问题,可见它不仅仅是大陆法或成文法的问题;第三人效力被奥地利9、瑞士10、荷兰11、比利时、葡萄牙12、意大利13、爱尔兰和西班牙14等欧盟国家所接受不算意外,但是欧洲人权法院15和欧盟法院16也接受这一范畴,可见它不仅仅是内国法问题;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吵了五十年仍乐此不疲,现在中国宪法学界也要拿此开题,可见它不仅仅是基督教文化问题。它是每一个宪政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宪法的效力与界限的问题,宪法诉讼的基础问题。
第三人效力问题的原产地在德国,准确地说是基本法生效后的德国。依照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区格,基本权问题产生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其功能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公权力侵犯。私法制度处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充分地体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所以长时间以来,基本权和私法关系并没有任何瓜葛。尽管通信自由是否拘束私法主体在1919年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时代即被讨论过17,由于那时基本权还没有拘束力,所以讨论没有实际意义。到了纳粹时代,践踏公民基本权的现象成为社会常态。1945年二战结束,道德反省与法制重建压力下,恢复发展基本权理论成为法律理论与实务界首要任务。由于托管因素的存在,直至1949年10月联邦共和国这一新的国体(国家组织法的研究对象)才出现,也正是这一时间差造成了50年代的基本权理论大讨论与大繁荣18。第三人效力之争便是这理论大潮中的第一浪。
二、第三人效力之争
这一场讨论并非开端于自由基本权问题,而是源自一个平等权问题。1949年刚刚被选出的第一届联邦议会(Bundestag)在将宪法所确认的重要内容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化的任务上表现懈怠19。1950年H.C.Nipperdey在其名篇"妇女的同工同酬(问题)"20中第一次提出:基本权应该具有直接第三人效力(unmittelbareDrittwirkung),以司法保护解决立法不足。由于这一观点是Nipperdey针对当时具体问题的权益之计,该观点论证先天不足。不久,Nipperdey和他联邦劳动法院的同事们(Nipperdey是联邦劳动法院首任院长兼第一庭庭长)等来了一个合适的案子:一个希望接受培训成为护士的女孩在与她所工作的一家私立医院签订了劳务与培训合同,合同中有一条:一旦女孩结婚,院方可以辞退她。后来她结婚了,医院依合同辞退了她。她以解雇行为侵犯了她婚姻家庭自由(基本法第6条第1款)、人性尊严(基本法第1条第1款)和人格自由发展权(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为由提起诉讼。联邦劳动法院于1957年5月5日,认定该合同因侵犯原告上述基本权无效。随后,陆续确认了观念自由(Meinungsfreiheit),平等权(Gleichheitssatz)对私法关系的直接拘束力21。
有趣的是,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却在第一时间对与Nipperdey针锋相对的GuenterDuerig的"间接第三人效力说(mittelbareDrittwirkung)22"作出了积极反应23。1950年,汉堡媒体俱乐部主席ErichLueth向影片发行与制作商发出呼吁,联合抵制纳粹时期一著名反犹导演的新作。该导演依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Lueth违反善良风俗造成其损失为由起诉,在民事法院环节Lueth被认定侵权。联邦宪法法院在Lueth提起宪法诉讼后,推翻了民事法院的判决,认为该判决侵犯了Lueth的言论自由权(基本法第5条第1款)。"基本法不是价值中立的秩序(wertneutraleOrdnung)…在其基本权部分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objektiveWertordnung)被设定…这一价值体系必须作为宪法基本决定对所有法领域有效;立法、行政和司法要从中获得指示(Richtlinien)与动力(Impulse)。它当然也影响民法,任何民事法规不得与它相冲突…"
从Nipperdey与Duerig五十年前的第一次交锋到现在,基本权对私法产生影响已是共识24,关于"如何产生和产生哪些影响"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25,德国学界为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热情26。相对而言,司法界表现得比较理性,1984年起联邦劳动法院不再承认直接第三人效力27;至2002年2月为止28,在联邦宪法法院的100多卷本的裁判中,涉及第三人的有220个29,直接提到Drittwirkung(第三人效力)的只有两次30。那么为什么宪法法院没有再提这一概念呢?难道Schwabe说对了,第三人效力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可能出于两点原因:一个是司法实务希望摆正与基本权Dogmatik的关系,另一个是第三人效力问题消融在基本权Dogmatik论战之中,它变成了每一种基本权理论都必须要处理的,同时也不再独立的一个问题。
Dogmatik是一个中文中无法翻译的概念,无论是"释义学"、"教义学"、"学理"还是"教条"都不能准确反映其德文愿意。Cremer在"自由基本权"一书中写到,"Dogmatik是法学家从司法裁判中提炼出来的,通过一致的结构与概念将规范分类化和典型化,为司法实务工作者在规范应用过程中提供标准程序和标准观点,可以减轻论证负担的一套理论"3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Dogmatik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套标准化流程。任何一个法学家在提出自己的Dogmatik、"学说(Lehre)"和"理论(Theorie)"的时候,都应是建立在司法实务的基础上的,即使所持观点是批评性的。如果该理论偏离实务观点太远,即不是或不再是Dogmatik,而是法学家自己的法律解释(Auslegung)。个人以为,在第三人效力问题上,联邦宪法法院在表明观点后,慎用Dogmatik名称是在有意与理论争执保持距离,维护自身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依照联邦宪法法院的一贯判决,"基本权首先是公民针对国家的防御权32"。Lueth判决后,客观价值秩序说拓展出基本权客观法功能(objektivrechtlicheFunktionen):国家基本权保护义务(diegrundrechtlicheSchutzpflichtdesStaates),原始的或者派生的给付请求权(originaereoderderivativeLeistungsrechte),组织和程序(保障)请求权(RechteaufOrganisationundVerfahren),制度保障(Einrichtungsgarantie)和第三人效力。宪法法院所主导的这次基本权功能扩张导致了当代德国基本权学说分裂为三大流派:接受上述新功能的是多元功能派(FunktionalerPluralismus),最新发展重点在国家保护义务;Alexy的原则理论虽然本质上也是多元功能论,但其完美的体系、超强的包容性和有组织地深化,显得多元功能派论者象是一群散兵游勇;最顽强的,2000年以来收获最丰的是Schlink所领导的防御权重构派。下面,我将对以上提到的各家理论给与简要介绍,希望能够勾勒出德国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讨论的概况。
三、直接第三人效力说
HansCarlNipperdey从"基本权含义流变(BedeutungswandelderGrundrechte)"理念出发,认为"即使不是所有基本权,但是最少有一系列的重要基本权不仅仅是针对国家的自由权,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秩序原则(Ordnungsgrundsaetze)33",它们不需要法律(Gesetz)作解释性中介(interpretatorischeVermittlung)34,对公民间的私法关系即具有直接效力"35,基本权必须成为私法权利(privatrechtlicheBefugnisse)的标尺(Massstab)和界限(Grenze)36。在现代社会必须承认"社会强力(SozialeMacht)"的存在37,个人在面对具有社会强力的私主体时(政党、垄断性企业、工会、银行等)会象个人面对国家一样无力38。在一个开放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无论是企业内部管理行为,还是公民间合同或者私人单方面所作出的法律行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基本权39。理论界,Leisner40在"基本权与私法",Ramm41在"意愿形成自由",Gamillscheg42在"劳动法中之基本权"等著作中分别表述了支持直接第三人效力说的立场。有些学者也使用了"绝对43(absolute)或者直接44(unmittelbare)效力(Wirkung)","绝对45或直接有效46(Geltung)"或者仅仅"有效"等措辞,但是很难泛泛地认为他们是Nipperdey基本权直接拘束私人理论的支持者47。
Nipperdey学说的核心概念在于基本权对私法主体的"拘束(Bindung)"。Bindung在法律德语中表示"直接施加义务(direktverpflichten)"。一个可以直接施加义务的规范是不需要进一步在规范性上更具体化(ohneweiterenormativeKonkretisierung)即可明确规定义务内容的规范48。如果赞成基本权拘束私法主体,就表明其承认私人对私人有独立的要求尊重其基本权的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Nipperdey认为基本权不仅拘束国家,而且拘束私法关系主体。但是他所说的拘束,并不是直接施加义务,而是很象Alexy在"基本权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原则(Prinzip)"-基本权规范必须经由法律的具体化才能明确私法主体的义务的内容49。Nipperdey的Bindung偏离了正常或通常语义。
另外,Nipperdey还忽略了:那些已经由法律具体化了的基本权规范和那些立法者尚未顾及的基本权条款对法官的拘束是有重大差别的50。对基本权规范进行了具体和明确化了的法律(强制性)要求法官在既要尊重宪法又要忠诚于法律(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Alexy将这一要求概括为,原则(Prinzip)要通过(durch)法律规则(RegeldeseinfachenGesetzes),而不是抵制(gegen)法律规则而适用51。联邦宪法法院也在Lueth判决中将这一要求发展为"相互影响学说(Wechselwirkungslehre)52"。
Ehmke在"经济与宪法"(1961)一书中批评道:"直接第三人效力严重威胁到私法自治53,先为私法引入错误的标尺(falscheMassstaebe),随后又将错误的标尺引回到宪法之中54。"直接说也严重破坏了法的稳定性和权力分立。公民在商业活动中,卖谁不卖谁,什么价格卖是无法援引平等权来决定的。"原本隶属于立法者的通过对宪法进行解释发生的社会形成权被转移到司法机构",立法机构被架空,"司法国家55(Justizstaat)"产生了。
四、间接第三人效力说
Duerig认为基本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秩序(Wertordnung)"应该在对民法的概括条款(Generalklauseln)-例如,诚实信用(德国民法典242条)、善良风俗(GuteSitten德国民法典826条)--的解释中受到关注56,只有通过概括条款的"中介(VermittlungoderMediation)",基本权才能对私法关系产生影响。如果法官出于疏忽或者理解错误没有采用与基本权保持一致地解释适用民法规范,即构成对基本法第1条第3项(基本权条款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违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57,公民有权提起宪法诉讼(Verfassungsbeschwerde)。私法相对于隶属于宪法的基本权是并行的两个体系,基本权客观价值秩序的引出不是要解体私法并以公法替代之,私法应保有独立性(Eigenstaendigkeit)58。但是也应承认,私法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因基本权客观价值秩序而相对化,基本权通过客观价值秩序对一般法(einfacheRechte)产生影响(所谓的辐射效力Ausstrahlungswirkung)59。
Bachhof,Scholz,Merten,Reimers,Wintrich,Vogt,Flume,Hueck,Jellinek,Gallwas,Hesse,Magen,Otto,Pieroth/Schlin,Schramm这些不同时代的宪法大家分别在其Kommentar(评论),教材或专著中对间接第三人效力说表示了支持60。无论是Nipperdey的秩序原则(Ordnungsgrundsaetz),还是Duerig的客观价值秩序(objektiveWertordnung),都是建立在基本权价值功能(grundrechtlicheWertfunktion)的基础上。整个第三人效力争执的致命点就在"客观价值秩序",基本法中哪一条可以推导出这一价值秩序,基本权主体之间为什么存在价值冲突,价值冲突会对基本权主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61?至今还没有十分有说服力的回答。
五、第三人效力伪命题说
Schwabe对第三人效力讨论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从结果上看,他和赞成直接第三人效力的学者们一样,承认基本权对私法关系的直接有效性,但是其论证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进路。他认为,基本权只能是针对国家的公权利62,但是基本权也可以对私法产生影响63。原因在于,整个法律秩序-即使私法关系-最后也要由国家以司法审判和强制执行等方式确认或落实64。基于私法请求权的私法基本权侵害(privatrechtlicheGrundrechtsbeeintraechtigungen)与基于国家权利以诫命(Gebote)和禁止(Verbote)作出的公法基本权侵害没有本质差别65,任何私人行为之至责任都可回溯到国家的容忍诫命(staatlicheDuldungsgebot)。在现代社会,媒体对于某产品质量的不实报道和卫生检疫部门对产品质量所做的错误鉴定所引发的企业主财产损失并无差别,无论国家命令公民容忍哪一种侵害,国家都应承担责任66。
Schabe的规责国家理论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批评。其主张将任何侵害他人法益的私人行为(Handeln)与不作为(Unterlassen)都依据基本法第1条第3款归责于国家是没有说服力的。国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应该为经由其许可而发生的基本权侵害与作出侵害行为的私主体负共同责任(Mitverantwortung)乃是防御权的意义所在-请求国家不作为。Schwabe认为对国家的不作为也可主张防御权,实际上是混淆了防御权与保护请求权。
六、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
保护义务(Schutzpflicht)与第三人效力具有内在相关性67,处理的都是私主体间利益冲突(InteressenkonfliktPrivater)的问题68。当受到他人侵犯的个人可以从基本权直接获得保护的说法受到否定时,人们普遍赞成例外一种保护途径,国家应该(应个人请求或主动)制定颁行一般法(einfachrechtliche)层面上的保护规范(Schutznormen),使行政和司法部门能够依照该规范防止和保护个人不受他人侵犯(Uebergriff)。69保护义务理论无需把现有基本权拘束对象从国家扩展到私人,又绕开了客观价值秩序这些非法律术语。国家有义务不仅仅对形式自由(formaleFreiheit)而且对实现实质自由70(realeFreiheit)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进行保障。如果公民对国家有请求保护的权利,直接说中基于公民受基本权拘束而产生的私权利(subjektivePrivatrechte)71和间接说中防止保护漏洞产生的一般人格权(allgemeinesPersoenlichkeitsrecht)都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主流说法已将第三人效力作为国家保护义务的分支功能来看待72。
2003年WolframCremer在他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自由基本权73"中指出,现在理论界讨论的众多基本权功能中真正独立的、对所有自由权有效的只有防御权功能和保护功能。原始给付请求权(originaereLeistungsansprueche)只在特殊领域有效,分享权(Teilhaberechte)属于平等权范畴。制度保障(Einrichtungsgarantie)应该彻底废弃,组织和程序(保障)权(RechtaufOrganisationundVerfahren)从来不是一种基本权功能,而只是一种请求样态。不存在专门的基本权第三人效力,基本权依照基本法第1条第3款已经拘束民事立法者和民事法官,需要研究的只是基本权的防御权功能和保护功能如何在私法背景下发挥而已。
七、第三人效力三层说(Drei-Ebenen-ModellderDrittwirkung)
Alexy以博士论文"法学论辩理论(TheoriederjuristischenArgumentation74)"和教授资格论文"基本权理论(TheoriederGrundrechte)"奠定了他在法理和宪法领域的地位,也为基本权原则理论(Prinzipientheorie)大厦打下了基石。其弟子Sieckmann的"法律体系中的规则模型与原则模型75",Borowski的"基本权作为原则76",Raabe的"基本权与认识77"批判发展了原则理论,使之成为当代基本权第一理论。对原则理论的质疑在于,是不是所有规范都能清晰地区分为原则和规则,如果所有法律问题都可简化为原则冲突与权衡,其它的Dogmatik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正是出于原则理论包容性考虑,Alexy及弟子从未对宪法法院的判决提出批评,总能在将其消化在自己的框架之内。在第三人效力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类似的处理。
原则理论在第三人效力问题上首先肯定了直接说、间接说和伪命题说对于私法与基本权关系这一复杂问题所作出的重要揭示,但同时也认为三种学说都过于片面,无法提供完整充分的解读方案78。Alexy为弥补这一缺憾,提出了区分国家义务、公民针对国家的权利和私法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三层说79。对应国家义务的是间接第三人效力说,基本权规范作为客观原则或客观价值体系对所有法领域有效,国家有义务在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尊重基本权。第二层与司法相关,基本权作为防御权和保护请求权直接有效。公民之间适用直接第三人效力说。三层说在基本权对私法具有哪些(Welche)效力的问题上作了全面地回答。
八、防御权(dasAbwehrrecht)与第三人效力
防御权是基本权的"传统"功能,这里所说的传统仅仅五十几年而已。Abwehrrecht作为一个针对国家的(甚至可以防止立法侵犯的)有制度保障的基本权Dogmatik形式当然是从联邦宪法法院成立开始,从这时起我们可以称Abwehrrecht是防御权80。
防御权是否是唯一的基本权功能?如果防御权能够理论上自足,并能满足实践需要,其它功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当然也不存在第三人效力作为与防御权并列的基本权功能的问题了。将基本权功能多元化首先要论证单一基本权功能的不足和新功能的完善。遗憾的是,理论界对基本权客观功能的内容、结构和有效范围至今仍未达成共识81。平等权Dogmatik建构上也遇到类似问题。于是,在承认功能多元论的情况下,将防御权所具有的"保护领域(Schutzbereich)--干预(Eingriff)--限制(Schranken)"的检索路径向客观功能和平等权推广便是最直接的路径。Luebbe-Wolff在教授资格论文"基本权作为干涉防御权"中对给付请求权82,Murswiek在"科技危险之国家责任"中对保护义务83,Huster在"法与目标"中对平等权依照干预(Eingriff)模型分别进行了重构84,实际上这些努力恰恰证明了客观基本权功能说理论上匮乏,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BernhardSchlink在1984正式提出重构传统基本权功能的口号85,延续Schwabe论证脉络,彻底将客观价值秩序这样的非法学概念剥离出去。2000年Koch的"涉及第三人的基本权保护-基本权作为防御权之重构86"和2003年Poscher的"基本权作为防御权87"连续两本教授资格论文的出现让人看到的绝对不仅仅是单一防御权理论的复苏,而是沉寂了多年之后的一次反攻--基本权客观功能理论有致命伤。
Koch和Poscher论证进路完全不同。Koch首先指出了传统干预(Eingriff)概念的特征并对其进行了批判:1、限于两极(国家与公民),忽视多极法律关系;2、限于国家针对公民的单边行为,忽视国家组织行为、行政合同、非正式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权的可能性;3、限于以命令或禁止方式设定行为义务,不承认事实行为(Realakt);4、限于国家机关要有针对公民的直接故意,不考虑副作用(Nebeneffekt)和对其他人造成的损害。所以,对干预必须针对实务发展进行扩张性解释。如果国家同意或者容忍私人行为造成第三人伤害也作为干预而被认可,则国家侵犯了第三人的防御权。具有与自由敌对倾向的国家保护义务Dogmatik完全多余,防御权是唯一基本权功能。Poscher认为无论是原则理论还是多元功能主义都有将整个法律体系宪法化的趋势88。他一方面强调基本权的全面性(Totalitaet),任何限制公民自由的国家行为都要经过防御权之正当化检验,生活中不存在基本权保护盲点;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向其他两类基本权理论一样出现完全宪法化的状况,Poscher提出了基本权权行使之反射性(Reflexivitaet)的观点:基本权规范国家的规范行为。基本权不直接处理公民间的冲突,但是基本权规范处理冲突的国家行为;基本权之反射性为一般法(einfacheRechte)之规范预留了自由空间;基本权反射性要求对基本权问题的思考要突破"国家-个人"两极模式,必须在多极化"国家-公民-公民"模式中探讨防御权之检索方法。
Koch和Poscher两人都谈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多极法律关系。不仅防御权一派学者重视这个问题,实际上多元功能理论中的保护义务本身既是"国家-被保护人-侵权者"三角关系。关于多极法律关系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Schmidt-Assmann的"一般行政法作为秩序观念与体系"89和Schmidt-Preuss的"行政法中相冲突的私人利益"90,历经十余年的理论酝酿和实践操练,在2006年2月举办的第一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奥地利宪法法院、列支敦士登国家法院、瑞士联邦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和欧盟法院经验91交流会上,多极法律关系中基本权和人权保护之控制密度(KontrolldichtedesGrund-undMenschenrechtsschutzesinmehrpoligenRechtsverhaeltnissen)92成为第一个议题。如果我们承认多极法律关系是新的基本权问题观察模板,那么第三人效力问题探讨就真的多余了!
九、第三人效力问题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1.齐玉苓案并不是宪法诉讼案、宪法司法案,只是一个涉及到基本权条款能否适用(第三人效力)问题的民事案件。该案件所引发的理论探讨起到了宪政发展大潮第一浪的作用,与德国发展历程相暗合。
2.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句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四十一条也直接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明确表明我国基本权拘束对象不仅仅是国家而且还有个人,而不是"扩散到个人93"。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效力问题讨论没有价值,因为第三人效力讨论前提是"基本权是公民针对国家的权利"。
3.我国基本权还不具备防御权功能,在宪法法院缺位的情况下,我们对基本权Dogmatik的准备只能依赖进口。模版的选择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a.版本高的不见得好,简单易学可操作更重要;
b.防止异体反映,价值秩序、价值决定这些以文化为依托的非法律术语最好不要;
c.要尊重我们的宪法,严格区分Rechtsdogmatik与Rechtspolitik,我们的职责在解释宪法而不是改变宪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将德国单一防御权理论之多极法律关系作为我国基本权Dogmatik构建参考模版较为可行。
注释:
1Ruefner,Grundrechtsadressaten,in:Isensee/Kirchhof(Hrsg.),HandbuchdesStaatsrecht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BandV,Heidelberg1992,§117,S.551
2Nipperdey,FSMolitor,S.17ff.;Canaris,AcP1984,S.201ff.
3Saladin,GrundrechteimWandel,2.Aufl.1975,S.307;Denninger,Ak-GG,Bd.1,1984,Rdnr.31vorArt.1;Bethge,ZurProblelmatikvonGrundrechtskollisionen,1977,S.19;Suelmann,DieHorizontalwirkungdesArt.3IIGG,S.14
4Heinz-GerdSuelmann,DieHorizontalwirkungdesArt.3IIGG,1994
5T.Abe-M.Schiyake,JOERn.F.Bd.26(1977),S.613f.
6庄国荣:《西德之基本权理论与基本权的功能》,《宪政时代》第十五卷第三期,第40页。
7传统上美国最高法院也认为基本权是仅仅针对国家的权利,第14修正案仅适用于国家行为(stateaction)。但在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建筑基地合同、公共信息公布、媒体登记等私法事物上却承认基本权的适用。参见SupremeCourt,326U.S.88;NewYorkTimesCo.vs.Sullivan,376US.254,84S.Ct.710(1964);AmalgamatedFoodEmployeesUnionvs.LoganValleyPlaza,391U.S.308,88S.Ct.1601(1986),详见Barby,"Die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imVerfassungsrechtderVereinigtenStaaten,DVBl.1971,333ff.
8vanAswegen,TheImplicationofaBillofRightsforthelawofContractandDelict,SAJHR1995,p..50ff.;Strydom,ThePrivateDomainandtheBillofRights,SAPR/PL1995,p.52ff.
9Novak,EuGRZ1984,133(134f.);Loebenstein,EuGRZ1985,365,(387)
10Mueller,DieGrundrechtederVerfassungundderPersoenlichkeitsschutzdesPrivatrechts,1964,S.160ff.;Wespi,DieDrittwirkungderFreiheitsrechte,Zuerich1968。但是瑞士宪法法院没有形成统一观点,基本权之间存在适用差别,参见SchwBGE86II365ff.;91II408;111II54;SchwBG,EuGRZ1988,132
11DeBlois-Heringa,GrREurUSA,Bd.I,1986,S.511(541ff.).
12Thomashausen,GrREurUSA,Bd.I,S.591(627)
13Ritterspach,EuGRZ1987,417f.
14V.Muench/Coderch/Riba,Zur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1998;Sopmmermann,DerSchutzderGrundrechteinSpaniennachderVerfassungvon1978,Bonn1984,S.235
15Moser,DieeuropaeischeMenschenrechtskonventionunddasbuergerlicheRecht,1972
16Graber,DieunmittelbareDrittwirkungderGrundfreiheiten,VVF,2002;Forsthoff,DrittwirkungderGrundfreiheiten,in:EuropaeischesWirtschafts-undSteuerecht,2000,S.389-397
17H。P。Ipsen,in:Neumann/Nipperdey/Scheuner,DieGrundrechte,Bd.2,Berlin1954,S.138.
18参见v.Muench,in:v.Muench/Coderch/Riba,Zur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S.11.
19Oeter,"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unddieAutonomiedesPrivatrechts.AOER1994,531,532
20Nipperdey,GleicherLohnderFraufuergleicheLeistung,RdA1950,S.121ff.
21BAGE1,185,193f.;4,274,276f.;7,256,260;13,168,174ff.;16,95,100f.
22Duerig,GrundrechteundZivilrechtsprechung,FSH.Nawiasky,1956,S.157
23BVerfGE7,198ff.,205(Lueth-Urteil);赞成间接第三人效力的判决:BVerfGE10,173,178;12,113,124;27,278,282ff.;34,269,280;37,132,141;49,89,142;73,261,269;明确否认直接第三人效力说:BVerfGE42,143(DGB-Beschluss)
24Ruefner,Grundrechtsadressaten,in:Isensee/Kirchhof(Hrsg.),HandbuchdesStaatsrecht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BandV,Heidelberg1992,§117,Rd。58
25Braczyk,RechtsgrundundGrundrecht,称其为当代基本权理论的危机,S。38;Canaris,AcP1984,S。201,202认为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几乎不可能解决的基础问题。;Hermes,NJW1990,S.1764"司法与理论界争执多年仍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26Alexy,TheoriederGrundrechte,1985,S.475ff.;Rupp,DieUnterscheidungvonStaatundGesellschaft,in:J.Isensee/P.Kirchhof(Hrsg.),HandbuchdesStaatsrechts,Bd.I,1987,§28,S.1187ff.;Starck,in:v.Mangoldt/Klein/Stark,DasBonnerGrundgesetz,Band1,Art.1Abs.3Rdnrn.191ff.;Canaris,?berma?verbotimRechtderGesch?ftsf?higkeitundimSchadensersatzrecht(JZ1987,993);ders.,ZurProblematikvonPrivatrechtundverfassungsrechtlichem?berma?verbot(JZ1988,494);Ramm,Drittwirkungund?berma?verbot(JZ1988,489);Wieser,Verst??t§105BGBgegendasverfassungsrechtliche?berma?verbot?(JZ1988,193);Bleckmann,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DVBl.1988,938ff.;Classen,AoeR,1997,S.65;Hager,JZ1994,373;Langner,DieProblematikderGeltungderGrundrechtezwischenPrivaten,1998;Luecke,JZ1999,377;Oeter,AoeR1994,529;Ruffert,VorrangderVerfassungundEigenstaendigkeitdesPrivatrecht,2001;Stern,StaatsRIII/1,1988,S.1509ff.
27BAGE47,363,(374-376)
28此处引用的是Koch,在DerGrundrechtsschutzdesDrittbetroffenen(2000)中所作的统计
29Poscher,GrundrechtealsAbwehrrechte,S.228
30BVerfGE7,198/204;73,261/269
31Cremer,Freiheitsgrundrechte,2003,S.502
32BVerfGE7,198(204);21,362(371f.);39,68(70ff.);50,290(327);68,193(205).
33Nipperdey,FSMolitor,S.17(23)
34Nipperdey,GrundrechteundPrivatrecht,S.14
35BAGE1,185,193
36Nipperdey,in:GrundrechteIV/2,S.741
37政治学家TheodorEschenburg,在1955年出版了著名的"协会统制(HerrschaftderVerbaende)?"一书。
38Nipperdey,in:DieGrundrechteIV/2,S。752f.
39BAGE1,185,193
40Leisner,GrundrechteundPrivatrecht,1960
41Ramm,DieFreiheitderWillensbildung-ZurLehrevonder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undderRechtsstrukturderVereinigung,S.38ff.
42Gamillscheg,AcP164(1964),S.386ff.,419ff.
43Mueller,RdA1964,121;Krueger,RdA1954,365
44Zippelius,in:BK,3.Aufl.,Art.1Abs.1u.2,Rdn.107。
45Huber,in:Rechtstheorie,Verfassungsrecht,Voelkerrecht,S.139;Laufke,FestschriftLehman,S.148;Leisner,GrundrechteundPrivatrecht,S.287
46V.Mutius,VerwArch.1973,S.75;Saladin,GrundrechteimWandel,S.319:"unmittelbareAusstrahlung".
47Oehler,in:GrundrechteII,605,赞成直接拘束私主体;Linders,UnmittelbareBedeutungderGrundrechtsbestimmungen,S。4,提出要区别"谁"受拘束和私主体间有效这两个问题。
48Floren,GrundrechtsdogmatikimVertragsrecht,S.28
49Nipperdey,RdA1950,S.121
50Floren,GrundrechtsdogmatikimVertragsrecht,1999,S.30
51转引自Floren,GrundrechtsdogmatikimVertragsrecht,1999,S.30,
52BVerfG7,198,209
53Duerig,in:Maunz/Duerig,GG,2002,Art.1IIIRdnr.129;Erichsen,Jura1996,527
54Ehmke,WirtschaftundVerfassung,1961,S.78ff.
55Ehmke,WirtschaftundVerfassung,1961,S.79.f;表示类似担忧的还有Hesse,VerfassungsrechtsprechungimgeschichtlichenWandel,JZ1995,S.265ff.(S.268);Isensee,Bundesverfassungsgericht-quovadis?,JZ1996,S.1085ff.(1090).
56BVerfGE84,192,194
57BVerfGE7,198,207;84,192,195
58Duerig,FSNawiasky,S.164
59所以张翔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第三期)中将第三人效力与扩散作用等同是误解,辐射作用是基本权对整个法体系的作用,不仅限于私法。未见扩散作用德文原文,猜测是辐射作用。
60Bachof,in:GrundrechteIII/1,S.155;Scholz,KoalitionsfreiheitalsVerfassungsproblem,1971,S.5;Merten,NJW1972,S.1799;Reimers,DieBedeutungderGrundrechtefuerdasPrivatrecht,S.20;Wintrich,ZurProbematikderGrundrechte,S.12;Vogt,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S.208-219;Flume,in:FestschriftDJT1960I,S.135;Hueck,DerGrundsatzdergleichmaessigenBehandlungimPrivatrecht,S.96;Jellinek,BB1950,S.425;Gallwas,Grundrechte,Rdn.359;Hesse,GrundzuegedesVerfassungsrechts,Rdn.356;Magen,Staatsrecht,S.148,Abschnitt16.3;Otto,PersonaleFreiheitundsozialeBindung,S.142;Pieroth/Schlink,Grundrechte,Rdn.210;Schramm,Staatsrecht,BandII,S.53
61Bleckmann,NeueAspektederDrittwirkungderGrundrechte,in:DVBl.1988,S.938ff.
62Schwabe,Diesog.Drittwirkung,S.140ff.,148;ders.,in:NJW1973,S.230;ders.in:AOER1975,S.444
63Schwabe,Diesog.Drittwirkung,S.105ff.,140ff.,148.
64Schwabe,Diesog.Drittwirkung,S.17ff.,26ff.,56ff.
65Schwabe,Diesog.Drittwirkung,S.88.
66Schwabe,Diesog.Drittwirkung,S.84.
67Badura,FSMolitor(1988),S.1ff.(9);Canaris,AcP(1984),S.201(205ff.);Herdegen,in:Heckmann-Messerschmidt(Hrsg.),GegenwartsfragendesoeffentlichenRechts,S.161(176);Klein,NJW1989,S.1633(1639);反对意见Isensee,dasGrundrechtaufSicherheit,S.35;Rauschning,VVDStRL38(1980),S.182ff.;Hesse,Verfassungsrecht,Rdnr..353.
68Preu,JZ1991,S。265(267);Canaris,JuS1989,S。161(163);Hermes,NJW1990,S.1764(1765)
69Luebbe-Wolff,DieGrundrechtealsEingriffsabwehrrechte,S.169,174.
70Boeckenfoerde,Staat,Gesellschaft,Freiheit,S.336,(337).
71Nipperdey,in:GrundrechteIV/2,S.741(748).
72Alexy,TheoriederGrundrechte,S.485ff.;Badura,Staatsrecht,C.Rdn.20;Benda,UPR1982,S.241;Bleckmann,DVBl.1988,S.938;Canaris,JUS1989,S.161.
73Cremer,Freiheitsgrundrechte,2003
74Alexy,TheoriederjuristischenArgumentation,3.Aufl.,1996
75Sieckmann,RegelmodelleundPrinzipienmodelledesRechtssystems,1990
76Borowski,GrundrechtealsPrinzipien,1998
77Raabe,GrundrechteundErkenntnis,1998
78Alexy,TheoriederGrundrechte,S.485.
79Alexy,TheoriederGrundrechte,S.485
80Gerber与Laband认为Abwehrrecht有专制反议会倾向,KarlSchmitt认为Abwehrrecht有反社会倾向,50年代以前这个词在法律中没有防御(Defensive)含义,详见Poscher,GrundrechtealsAbwehrrechte,B.I.
81Borowski,GrundrechtealsPrinzipien,1998,S.22
82Lübbe-Wolff,DieGrundrechtealsEingriffsabwehrrechte,1988
83Murswiek,DiestaatlicheVerantwortungfuerdieRisikenderTechnik,1985
84Huster,RechteundZiele,1993
85Schlink,FreiheitdurchEingriffsabwehr-RekonstruktionderklassischenGrundrechtsfunktion,in:EuGRZ1984,S.457
86Koch,DerGrundrechtsschutzdesDrittbetroffenen,2000
87Poscher,GrundrechtealsAbwehrrechte,2003
88Poscher,GrundrechtealsAbwehrrechte,S.415
89Schmidt-Assmann,DasallgemeineVerwaltungsrechtalsOrdnungsideeundSystem,1982
90Schmidt-Preuss,KollidierendePrivatinteressenimVerwaltungsrecht,1992
本权范文篇6
关键词:基本权宪法解释方法论
由于宪法往往宣布的是一些基本原则,因此“对宪法的解释经常比对一般制定法的解释有更大的选择自由。”[1]但宪法解释如果不依据宪法条文本身隐涵的基本原理、宪法哲学,则大有可能迷失方向。[2]宪法的基本原理源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在需要,各种宪法解释方法能否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方法,最终都可以其是否有效地保护了宪法基本权作为检验标准。“人权保障乃人类文化体系中的最高准则,也是当今先进文明社会共同的准绳,故宪法解释必须对此价值秩序做必要的考量,乃属当然之理。”[3]基本权释义学不仅是宪法解释学的一个必然的和核心的内容,而且是宪法解释学区别于一般法律解释学的关键之点。
一、基本权在宪法解释中的地位
宪法的终极目标无疑是保障基本人权,宪法的解释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基本权利的解释。按照卡尔·斯密特的观点,真正的基本权利只能是个人自由权,原则上不受限制,而国家的干预原则上是受限制的、可预测的、可监督的。[4]斯密特对基本权利概念内涵的阐述具有古典自然法观念的背景,他认为一切真正的基本权利都是绝对的基本权利,其内容并非来自法律,相反,任何法律干预都属于例外情况,而且属于原则上受限制的、可预测的、受一般规定制约的例外情况。[5]作为基本权之载体的宪法以基本权为核心内容,宪法核心理论预设了保障基本权利是宪法解释最重要的任务。
斯密特以自然法思想为依据提出基本权利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个人的“自然”权利,这种观点是西方国家对基本权利内涵的传统认识,并对基本权的解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45年的蔡斯证券公司诉唐纳森(ChaseSecuritiesCorp.v.Donaldso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宣称,“今天所说的基本权利就是过去所谓的个人的自然权利。”[6]在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很少在宪法解释中使用自然法语言或赋予新的宪法准则以自然法的依据”,[7]他们已用新的术语如“正当法律程序”取代了自然权利的称谓。而大陆法系国家自进入19世纪以后,在概念法学的影响下,法律实证主义取得压倒性优势,一般都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来自于宪法的规定,因此,基本权利“只是宪法赋予的权利”。[8]自二战后出现了自然法的复兴,但这时人们对于基本权利的观念又与以前的自然法观念有所不同,人们大多不再认为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而是人所固有的权利。[9]
现在,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人们都承认基本权利不仅是个人所固有的、应受宪法保障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需要得到宪法的认可,需要将主观上的权利转化为客观的宪法权利,才有获得保护的可能性,从而才可能成为具有实效性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非常抽象简洁,这使得基本权利成为宪法释义学的核心部分。[10]在德国,一般法律在对宪法基本权加以限制时,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合宪法性解释”原则来解释该法律,考虑被限制的基本权本身及其崇高的价值位阶,基本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保有其优越性,此乃“基本权对于普通法律的影响作用”。[11]不仅宪法对于基本权的规定的抽象性使基本权解释成为宪法解释的核心,而且基本权在整个宪法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它成为宪法解释所围绕的重中之重。从当今世界各国宪法解释的实例来看,基本上可以说宪法解释就是以基本权利为中心的解释。正如大卫·理查德(DavidA.J.Richards)教授所说,“在时光流逝中,宪法解释保持其统一性和稳定性,除了其他因素以外,主要依赖于人权观念在宪法解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2]
二、德国和美国基本权解释的实例
德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相对发达的宪政国家,它们有着十分丰富的基本权解释方面的案例,这为我们认识两国基本权解释理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一)德国基本权解释的典型案例
1950年9月,德国汉堡市举办了一次“德国电影周”。担任汉堡市新闻协会主席的吕特(ErichLüth)公开抵制一位德籍剧作家兼导演哈兰(VeitHarlan)所导演的影片《永恒的爱人》(UnsterblicheGeliebte)参展。制作《永恒的爱人》的电影公司以吕特的抵制行为违反了德国民法第826条的“善良风俗”等为由,要求汉堡地方法院救济。在汉堡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败诉后,吕特以法院的判决侵犯了其《基本法》第5条所规定的“表意自由”权为由,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联邦宪法法院于1958年针对该案提出了于日后的法院相关判决和学界著述经常援引的经典判词:各项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保障个人的自由领域免于公权力的侵害;它们是民众对抗国家的防卫权,基本法无意成为价值中立的体系(秩序),它也在基本权利章中建立起一套客观的价值秩序,且对基本权利的效力做了原则性的强化。这个以人格及人性尊严能在社会共同体中自由发展作为中心点的价值体系必须视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适用于各法律领域。[13]“吕特判决”开启了联邦宪法法院解释基本权利内涵的大门,为基本权释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理论界更是围绕该判词展开了广泛研究和深入讨论,提出了各种关于基本权理论的观点,其中基本权功能的探讨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在1972年的“大学特定学系入学许可名额限制”案中,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权利内涵又作出了新的阐释,提出了分享权(请求国家给付的权利)。[14]联邦宪法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写道:宪法上对教育方面的人数保障,并非仅限于传统上所认定的旨在对抗公权力侵害的自由权,基本权利不只是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卫权而已,现代国家凡是保障社会福利与奖励民众文化越多的,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上,除了保证自由的原始要求外,还会有更多要求在基本权方面保障分享国家给付的要求。”[15]在1974的“堕胎案”中,联邦宪法法院又从基本法关于“人性尊严”规定推导出基本权客观内涵包括国家保护义务。联邦宪法法院在该案中认为:国家的保护义务是广泛的,当然此项义务并非仅是禁止国家侵害正在成长中的生命,而是同时要求国家保护并助长此种生命,特别是要保护此种生命免于遭受来自他人的违法侵害,人类生命于基本法的秩序中有最高价值,其系人性尊严之生命基础以及所有基本权利的先决要件。[16]
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上述案件对基本权的解释不仅对下至普通百姓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切实的影响,而且对上至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美国基本权解释的典型案例
1965年著名的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迪格州案(Griswoldv.Connecticut)。[17]该案的基本情况是,格瑞斯沃尔德是康涅迪格州计划生育协会的执行主任,耶鲁医学院教授布莱克斯顿在该计划生育协会担任医学主任。他们由于向已婚者提供有关避孕信息、指导和医学建议而被捕。该案涉及康涅迪格州综合法典第53条第32款和第54条第196款的合宪性问题,这两个条款分别规定了使用避孕药物、器材和为避孕提供帮助的人都将被罚款或判刑。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二人被认定有罪,并各被处以100美元罚款。他们以所适用的法律条款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为由提起上诉。
道格拉斯(Douglas)大法官在其法院判决意见中认为,有些权利尽管宪法和权利法案没有提及,但通过对宪法第1修正案的诠释发现,它本身就包含在这些权利之中。并认为如没有这些权利,特定权利的安全性就会受到威胁。宪法第1修正案存在着“暗影”,通过这个暗影公民的隐私权得到保护,不受政府行为的干涉。这些暗影是由宪法的明示权利的扩散而形成的,并赋予它们生命和内容。本案与由几个宪法基本权利形成的隐私区域有关,州政府控制或禁止那些宪法规定应由州法律管辖的活动时,其目的不得通过无限制地扩大适用范围,进而侵犯人民的自由的方式而实现,由于该案中州法令违反了这一原则,因而是站不住脚的。法院最后撤消了原判决。
戈德堡(Goldberg)大法官和沃伦(Warren)首法官以及布伦南(Brennan)大法官持赞同意见,尽管他们也认为康州的法令违宪,他们推导隐私权所依据的宪法条款不同。他们认为关于自由概念保护的个人基本权利不仅仅限于人权法案中的明示条款,自由概念包含婚姻的隐私权,尽管这种权利并没有在宪法中明确提及。他们的上述观点来自于宪法第9修正案,他们强调第9修正案是为了支持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第5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免受各州和联邦政府侵犯的自由不应该被局限于宪法第1至第8修正案所明示的权利。因此,婚姻关系的隐私权是基本的、重要的,是一项宪法第9修正案意义下的“由人民所保留的”个人权利。
哈兰(Harlan)大法官的赞同意见则与上述推论过程都不相同。他认为,该案要探求的是,康州的这项法令是否因侵犯隐含于既定自由概念中的基本价值观念而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原则。他认为,第14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在宪法前八个修正中用特定条款明示的,而是存在于某些概念之中的,这些概念包括以生存在社会中为目的、为所有自由政府的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正当程序原则代表了我们国度在自由和社会需求之间构建的一种平衡,我们国家是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假设基础上的。因此,宪法条款之绝对命令的特征必须在比特定条款的更广的语境中才能获得,这一语境并非文字的,而是关于历史和目的,正当程序条款所保障的自由不能仅限于宪法在其他地方规定的特殊保障的准确措辞。
三、德国和美国基本权解释的比较分析
德国和美国不同的制宪背景和法系归属是认识这两个国家的宪法内涵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两国的基本权解释方法。鉴于二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德国基本法异常注重对国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其不仅把基本权利章放在基本法的第一章,而且在基本法第1条第1项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这些规定不但成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案件的“上方宝剑”,而且成为保障国民基本权利的利器。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的普通法,正如肯特所说:“对我们来说,普通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承认和采纳了。”[18]爱德华·S·考文教授认为,美国的宪法和宪政来源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文明中的自然法观念和英国悠久的普通法传统,[19]此言足以证明普通法对美国法的影响之深。另外,德国大陆法系的成文法特征和由此形成的相应法律解释方法对于德国宪法的解释适用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样,尽管美国宪法采取成文宪法的形式,但其宪法解释适用深受普通法特征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影响,反映了英美法系法律制度在宪法解释方法中的实质性特点。
(一)两国基本权解释的差异
1.由两国基本权在宪法规定方式上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这种差异表现为德国的基本权解释较多地体现了一种形式正义的特点,而美国的基本权解释则突出体现了一种实质正义的特点。
德国基本法第1条明文规定了国民基本权利的至上地位,这成为联邦宪法法院裁决案件的法源性依据,其关于“人性尊严”的规定以及关于国家对国民基本权利所承担的义务的规定,是联邦宪法法院阐述基本权利内涵的基础和法源。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前述案例中所提出的基本权利的防卫功能、请求国家给付的功能以及国家保护义务的功能,都是从基本法的明文规定中得出的。也即是说,联邦宪法法院所阐述的那些基本权利的功能都是属于德国基本法第1条或第2条所内含的,内在地属于基本法的客观内容。实际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基本权的解释受到德国基本法的制约,因此,其关于基本法的解释所获得的基本权内涵在德国并未引起太大的争议,相反成为日后联邦宪法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先例和国内学者从事宪法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来源。
然而,美国的情形则非如此。诚如孙斯坦所说,“美国宪法是普通法宪法,其中关键的决定通常是通过类推思考形成的。因此,美国的立宪主义远不是完全受规则约束的,而且许多重要规则都体现在案例中,而非通过宪法文本表述出来。”[20]美国宪法虽然体现了普通法精神,但美国宪法正文中没有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其宪法修正案中虽然规定了一些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措施,但这些规定都是对具体权利的列举,且其中大多是针对刑事案件中的被告而言的。尽管宪法第9修正案言明了“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但由于这种规定并没有像德国基本法那样直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至上地位和国家由此承担的义务,因而并没有为法官在特定情形下发展公民基本权利提供强有力的法源性依据。正是由于上述宪法规定方式上的特征,导致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基本权解释方法上体现出实质正义的特点。如在前述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迪格州案中,虽然法官们从宪法的不同地方来推论隐私权的存在,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隐私权尽管没有直接规定在宪法条文中,但它属于宪法所保护的权利,足见这种解释方法的实质正义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从德、美两国基本权解释方法的推论方式来讨论它们各自特征的。事实上,德国的基本权解释尽管是以基本法为法源性依据,显示出一种形式正义的特点,但从其结果来看,这种通过对基本法条文内涵的阐释而发展出的基本权利功能,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又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一种实质正义的特点。美国宪法基本权解释尽管显示了一种实质正义的特点,但如果从美国宪法本身体现的是普通法精神这一点来说,联邦最高法院在基本权方面所作的解释也反映了一种形式正义的特性。况且,除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外的学者们对法院的解释存有广泛争议之外,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内部,关于某一基本权解释也有许多不同意见,其中有的法官的解释方法体现的是实质正义的特点,有的则体现的是形式正义的特点,这在前述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迪格州案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详见前文对该案的分析)。
2.由两国释宪机关在各自国家中职权和地位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
德国《基本法》第93条和《联邦宪法法院法》第13条关于联邦宪法法院职权的规定中,不仅明确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有审查联邦法和州法是否与基本法相一致的权力,而且还规定了有权审理诸如政党违宪等政治性案件;此外《联邦宪法法院法》第1条第1项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相对于其他宪法机关自主和独立的地位。这些规定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审理相关案件——包括宪法性法律案件和政治性案件——提供了依据。而美国的联邦宪法并没有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有审理联邦法律是否违反联邦宪法的权力,所以尽管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由于遵循先例原则而一直保存至今,但因这一制度缺乏宪法上的权威性基础,所以不仅在其创立之初、而且迄今在理论界仍然存有广泛的质疑和争论。从宪法的规定上来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德国国家机关中具有最高的宪法地位,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则并无优越于其他两个部门的宪法地位,美国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决定了联邦最高法院有限的职权和在国家机关中相应地位,并由此决定了其行使职权的行为方式。
上述因职权和地位的不同而引起的基本权解释上的差异在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由于职能的广泛性,当其从事基本权解释时除了运用一般解释方法外,还会基于其承担的“维持法治国之秩序、功能的责任”[21]而采取超解释的方法,即通过考虑经济和社会上的后果而作政治性的裁判,这种解释实际上已不单是一种法律性的解释,而且是一种政治性解释。例如在1951年的“西南重组”案[22]中,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人民的自决权应受制于更广泛的整体利益,因此裁决第二重组法案并不违宪。该案采取了一种原则解释方法,它不是一般的宪法解释方法,已属于一种超解释的方法,因为在这里要判定人民主权原则从属于联邦主义原则已经不单纯是对宪法的解释,而是基于国家利益上的考虑从事政治性的裁判,用美国学术界的语言来表述就是“非解释主义”。这种解释方法在德国并不会引起争议,因为它是在德国基本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的行为。相反,美国却存在着“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的争议。前者是发现宪法文本中业已存在的含义,后者则超越了宪法文本,不再仅仅是对宪法的解释,而是从当前的政治中引入价值并将其植入司法判决之中。[23]这种争议实际上是因联邦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各部门中的职权和地位所引起的,由于缺乏宪法上的依据,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创造宪法权利的做法才会招来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如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v.Arizona)案[24]中为警察审问犯罪嫌疑人制定著名的“米兰达规则”时,司法部认为第5修正案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米兰达规则实际上在宪法之外创造了实体权利,这超越了法院的职权范围。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可以在一系列案件中得出基本权利在特定情形下的具体内涵为何,这些在特定情形下发展出来的基本权利在德国被赋予“基本权利功能”的地位和称号。宪法法院得出的解释结论获得了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推崇和赞赏,不仅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素材来源,而且为学术界深入讨论提供了契机,使得理论与实践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公法学的发展。而美国则形成相反的情形,法院每在一个案件中对基本权利提出一个新的阐释,便招来一片哗然,质疑与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这种现象除去各自国家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因素之外,主要根源于释宪者的职权与地位对于宪法解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两国基本权解释的共通之点
尽管德美两国基本权解释存有前述差异,但从前面案例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出这两个国家在基本权解释上存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两国在宪法解释中都异常重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解释者实际上充当着基本权利卫士的角色。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一系列的宪法裁决中提出了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该理论中的“客观价值秩序”在德国宪法解释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一些列判词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因为正是这一概念为联邦宪法法院完成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使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基础与理论媒介,它就像一张安全网,有力地保障着公民基本权利免遭国家权力的侵害。同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断变化历史长河里,始终充当着坚定的宪法权利卫士的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最高法院实现“及时转向”之后,采取司法审查的“双重标准”,对于涉及精神自由的国会立法进行“严格审查”,在基本权利保护领域表现出了明显的“司法积极主义”倾向,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基本权利的保障。
在具体案件中涉及基本权解释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方式的多样性的。当有明确的宪法条文规定保护基本权利时,解释者根据相关条文作出解释,并将基本权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予以保护;如果宪法条文的规定因其抽象性和模糊性而有多种解释结论时,则作有利于保护基本权利的解释,而不是相反;当出现基本权利中的人身权与其他基本权相冲突时,则优先保护人身权。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66年审理的“魔鬼案”中认为,“人格权”和“艺术自由”都是德国基本法保护的个人基本权,应以基本法的价值秩序为标准来解决,人格权被包含在基本法第一条所保障的人的尊严中,人的尊严是基本法价值体系的最高价值,也是基本法对艺术自由的内在限制,因此艺术自由应服从上位价值。[25]若是有关基本权利缺乏宪法条文上的明确规定,解释者就发挥其职能所赋予的地位和功能,对于公民基本权利采取肯定的态度,积极地予以保护。对于这一点,不同解释者可能因不同的立场或司法哲学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但从总的来看,他们都赞成在宪法解释中尽可能地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将保护基本权利视为其解释行为的宗旨,这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
Abstract:Basicrights’corestatusinconstitutionandits’
abstractandconcisionperscriptionmadebasic-rights-interpretation
thecoreofconstitutionalinterpretivejurisprudence.Asrelativelyadvancedconstitutionalconstries,theGermanyandtheAmericahaveaccumulatedmanycasesofbasic-rights-interpretation,theyhave
detailedanddeeplydemonstratedtheexpoundandmethodologyof
basicrightsprotection,andhaveenhancedanddevelopedbasic-
rights-interpretationtheroy.Thoughthereexistssome
distinctiones,butthetwoconstries’interpreterareactedas
escortofbasicrights,theyreachthesamegoalbydifferent
routes.
Keywords:basicright,constitutioninterpretation,methodology
--------------------------------------------------------------------------------
[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3页。
[2]参见[日]中野目善则:《宪法解释方法》,金玄武译,载《法律方法》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3]翁岳生:《宪法解释与人民自由权利之保障》,载李建良、简资修主编:《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务》(一),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0年版,第4-5页。
[4]参见[德]卡尔·斯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6页。
[5]前引[4],卡尔·斯密特书,第177页。
[6]ChaseSecuritiesCorp.v.Donaldson,325U.S.304(1945).
[7][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8]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9]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10]参见杨子慧:《德国宪法释义学对我国宪法解释之影响》,载《宪政时代》第30卷第1期,第94—95页。
[1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9页。
[12]DavidA.J.Richards,HumanRightsastheUnwritten
Constitution:TheProblemofChangeandStabilityin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4U.DaytonL.Rev(1979).p300.
[13]转引自台湾“司法院”秘书处编:《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一),台湾司法院1990年版,第106-107页。
[14]案情详请参见台湾“司法院”秘书处编:《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二),台湾“司法院”1991年版,第71-115页。
[15]转引自前引[14],台湾“司法院”秘书处书,第94-95页。
[16]转引自前引[10],杨子慧文,第107-108页。
[17]Griswoldv.Connecticut,381U.S.479(1965).
[18][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9][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20][美]凯斯·S·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07页。
[2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8页。
[22]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以下。
[23]参见[美]基思·E·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初意图与司法审查》,杜强强、刘国、柳建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本权范文篇7
关键词:日本知识产权协会借鉴
在知识经济日益为各国所重视的现代社会中,拥有知识产权并良好地运用知识产权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已成为各国企业的主要手段。专利保护制度在日本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日本许多超一流企业的成长即得益于专利保护制度的实施。日本知识产权协会成立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在日本知识产权领域内一直起着沟通行业关连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和知识产权服务行业之间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桥梁作用,分析与研究日本知识产权协会,可为推动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1.日本知识产权的现状
日本企业认为,专利有助于企业商务活动的成功,进而增长销售额,扩大市场。专利不是一种副产品,不只是一种保护手段,而是一种产品、一种资源,是一种商业财富。专利的三大益处分别是竞争力、利润率及知名度。
日本是个十分讲究精兵简政的国家。企业从不设立多余的机构,但在对待专利管理上却舍得花本钱。日本的大中型企业都设有特许契约部,即专利管理部,小型企业也有管理专利的专职人员和归口部门。企业的“知识产权部”通常受主要领导直接管理,如拥有1.1万名职工的索尼公司的“知识产权总部”,有156名工作人员。即便规模较小的横河电机公司,也有29名专利管理人员。日立制作所从业人员8万人,公司总部的知识产权部有专利管理人员320名,下设五个分部。
有资料统计,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结果。日本企业在世界上引进的先进专利技术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日本企业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正确地处理引进技术与开发专利的关系。日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产生了大量的新专利。例如,从专利申请方面看,1959年比1950年发明专利申请增长2.2倍,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增长2.7倍;1969年比1959年发明专利申请增长2.1倍,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增长1.8倍;1991年比1975年整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增长2.3倍。随着日本专利技术的开发,日本向海外输出的专利越来越多,现已成为技术输出大国。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便成为技术输出大国。目前日本在美国的专利申请占全美专利申请总量的40%,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
日本企业十分重视把研制出来的技术申请和注册专利。根据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统计调查报告,1999年取得美国专利最多的是日本日立、佳能和东芝3个公司。以东芝公司为例,它每年在国内申请专利数为1.3万件,在美国约有1000件专利被获准。近年来日本企业在美国申请注册发明专利的数量急剧上升。根据美国专利局的资料,2000年在美国注册的发明专利总数157497件,其中日本法人注册的发明专利有31296件,占19.9%。日本法人在美国注册的发明专利件数比1997年增长35%。
在上述日本知识产权领域的卓越成就大背景下,近年来日本知识产权协会在推动与发展该国企业知识产权向共同发展、共同创新、共赢互惠等方面的作用与贡献日益突出,不仅在日本国内广受企业界与知识产权界欢迎,而且其触角已伸向欧洲和中国,已渐渐受到其他各国知识产权领域相关机构的注目。认识、了解日本知识产权协会的组织形式、作用特点,将对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2.日本知识产权协会的组织形式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是日本国内的民间知识产权联盟组织,主要为日本国内企业间搭建技术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以及企业与知识产权机构间的交流与沟通平台。目前全职工作人员有二十余人,一半以上来自于日本各大企业,其理事长等管理岗位人员主要来自于日本各超一流企业,如东芝、索尼、三菱等。
该协会会员分为正式会员和资助会员,正式会员来自于日本本土的企业。目前,有900余家企业会员,日本现有的大公司全部为其会员;资助会员则来自于大学、科研机构和专利事务所,有300余家成员单位,中国有十多家知识产权事务所已成为该协会的资助会员。协会下设20个专业委员会,如电子、化工、机械等,由来自于日本200余家企业的700余名委员组成。
该协会以正式会员为活动中心,其工作目标是:使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助于公司经营。
3.日本知识产权协会的工作内容及主要作用
3.1日本知识产权协会的工作内容
1)追踪世界知识产权发展趋势;
2)知识产权制度的探讨与研究;
3)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界(包括中国企业)定期召开知识产权研讨会;
4)开展知识产权研修活动,培养企业内部知识产权人才:
5)出版《知识产权杂志》(协会刊物);
6)与其它社会团体进行沟通与交流,包括法院等。
3.2日本知识产权协会的主要作用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目前已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知识产权联盟组织,日本企业的各种最新技术资讯也往往通过协会会刊对外公布与交流,其主要作用有:
1)团结国内企业,尤其是将同行业企业凝聚在一处,有效提高日企对外整体战略优势;
21技术交流高效充分,使会员单位能即时了解国内企业的技术研发现状、产品现状,从而为本企业制订相应技术与市场经营策略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3)与大学、科研机构和专利事务所充分合作,企业从中能够得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的资讯与支持,而大学、科研机构和专利事务所则可以从与企业交流合作中找到各自的研发方向与服务对象,达成多方共赢的良好态势。4)组织大量的研修活动。据统计,每年参与该协会研修计划的人员超过1.5万以上,而这些人员均来自于日本企业,这类研修活动对于日本企业深入了解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实质,掌握保护本企业知识产权的方法和技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结束语
本权范文篇8
[关键词]宪法;基本权利;宪法诉讼
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和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已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研究与宪政实践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需要完善各项具体立法和制度,而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确立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司法中的直接效力,也是关系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完善的重大举措。
一、宪法诉讼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性的救济途径
宪法诉讼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在与违宪审查同一意义上使用,二是专指作为违宪审查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的,解决违宪争议的诉讼形态。[1]本文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宪法诉讼概念,即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涉及宪法的争议的审判活动。宪法诉讼可以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活动,由专门机关按照宪法诉讼专门程序进行的活动,如宪法法院体制下的宪法诉讼;也可以是与其他的具体法律诉讼并无严格程序区分的诉讼活动,如普通法院司法审查制下的宪法诉讼。笔者认为,宪法诉讼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承认宪法条款的在司法中的直接效力,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解决宪法争议。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的内容。
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之一。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需要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并且通过普通法律的实施得以实现。然而,普通法律并不能完全替代宪法本身对权利的保障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在通过其他诉讼手段不能得到维护或者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得到有效补救时,应当有权提起宪法诉讼,从而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恢复。“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2]宪法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在法律上的权利,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如果因为没有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定不能通过诉讼得到保障,也不能直接依据宪法提起诉讼,那么宪法基本权利的存在也就失去其独立的意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权利救济体系中,诉讼救济是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救济方法,而宪法诉讼则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性的救济途径。诉讼所具有的客观性、中立性、公正性、正当性和高度的程序性等特性,使得宪法基本权利的争议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被侵犯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及时的恢复。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但由于立法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以及成文法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必然发生一些无法通过这三大诉讼制度来解决的权利争议案件。由于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缺乏相应的宪法诉讼制度,也就使得这一部分权利的争议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状态的存在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宪法的。1998年发生在上海的女大学生钱某诉屈臣氏超市搜身案和1999年北京的王春立等诉民族饭店侵犯选举权案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宪法进入诉讼的必要性。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也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政府签署加入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以后,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并为最终批准这两个公约创造条件,已成为众目所注。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既有一个完善各项人权保障的具体立法的问题,而宪法进入司法,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大为提高。在权利被侵犯时,人们更多地、经常地诉诸法律,希望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的弊端与局限也已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须进行改革。
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效力
建立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在理论上首先涉及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诉讼中的直接效力的认定。承认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实行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已成为世界性的宪政惯例,不仅在发达国家被普遍认可,也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群起效法。
在英美法系,宪法基本权利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英国,没有宪法典,但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性法律。基本权利大多表现为宪法判例。宪法判例本身就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司法。美国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则是直接将宪法典作为可由法院来适用的法律。
在大陆法系国家,宪法直接效力的确定晚于英美法系。但在二战以后,也都逐步承认宪法也是法律,确立了宪法具有直接的司法效力的体制。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文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以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在学术界,基本权利可拘束行政机关一切行为的观点已成为通说。葡萄牙1982年宪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关于权利、自由与保障的宪法规定,得直接适用。”欧共体成员国的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受到双重司法保障。成员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甚至可诉诸欧洲人权法院。
在我国宪法理论上,一直存在着宪法效力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分歧。传统的观念认为: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而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宪法的规范具有原则性,且无制裁性规定,宪法只能通过具体立法实现,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条文也不能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直接引用。[3]据此,宪法的基本权利也只能通过具体立法才能实现,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上述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根深蒂固的,从而导致了我国宪法长期以来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
笔者认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其最终实现方式上可以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分。然而从宪法规范的法律效力上来说,从它对行为的约束力上说,不仅是最高的、而且也是直接的,宪法规范对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应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等案件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引用宪法的条文。但这只是说明在具体立法相对完善的条件下,司法机关没有必要或不需要再援引宪法的条文。没有必要或不需要,并不是说不能引用。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正是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而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宪法应当进入司法、建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的重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宪法诉讼的基本特征。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意义不只是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和宣告,还在于它是各项具体的人权立法的基本精神所在,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为司法机关具体适用法律、保障公民权利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指导;同时通过它的原则性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漏,避免出现法律保护的真空。在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诉讼案件中,也已涉及到宪法的原则规定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
宪法规范的原则性与普通法律的具体性是相辅相成的。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需要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而普通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应当以宪法为指导,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在依据普通法律不能解决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时,应当引入宪法或者进行宪法诉讼。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承认宪法的直接效力和司法适用的基础上。确立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诉讼的适用范围
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诉讼,已经成为当代宪法发展的共同趋势。然而在宪法诉讼的适用范围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这与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约束对象和效力范围的传统观念紧密相关。
在西方传统宪法理论中,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是为了保障人民免遭国家权力(公权力)滥用的侵害,是公民对抗国家侵犯的一种“防卫权”,而不是为了防止私人的侵犯。宪法对权利的保障通常只是约束国家和国家机关,私人行为只受法律约束而非宪法的约束。因此宪法诉讼只限于对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非针对个体公民,并不适用于民事领域。如日本学者宫泽俊义认为:“基本人权本来在国家关系上是保障一般国民的权利的”,私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属于私人自治的领域”。[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大量的个人所有的工商企业等法人组织、学校、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产生,就使得这些组织,尤其是一些在社会上拥有“优势地位”的组织及个人,有可能凭借其“压倒的实力”地位,侵犯其他居于“实力劣势”地位的个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在西方国家中引起了人们对国家权力应否介入私人领域,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对私人之间关系的效力的关注。而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司法机关受理传统的私法领域中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例。在美国,基于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一般只是针对政府侵犯,而非私人侵犯,私人行为一般只受法律约束的传统观念,宪法诉讼也主要针对政府机构而非个体公民。但是,带有“国家行为”的私人行为,即私人的所作所为以某种方式和政府相联系,则被认为是一种“例外”。[5]
在德国,学者们提出了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者效力理论”,即宪法基本权利对国家与人民关系外的第三者,亦即私人与私人间的效力。如H……C.Nipperdey提出,基本权利是“最高层的规范”,如不能直接在私人间被适用,则宪法的基本权利之条文,将沦为仅“绝对的宣示性质”罢了;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在私人的法律关系中有“直接效力”,法官可以“直接引用基本权利”的规定,审理民事案件。G?Müller也认为,基本权利乃“首要之规范”,应该在法律的所有领域内获得实现;所谓“市民国家”的时代已过去,宪法所确立“社会国家”原则,要求基本权利能有“对第三者”的效力。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移植”到私人的法律体系,是侵犯了“私法自治”以及“契约自由”等私法体系的“基本价值”。[6]
1957年,德国联邦劳工法院裁判著名的“单身条款案”,法院认定以契约规定“维持单?quot;的条款,违反基本法保障的”婚姻及家庭“制度(第6条第1项)、”人类尊严“(第1条第1项)、以及”人格发展权“(第2条)等,此类契约应为无效。强调民事法是受到宪法所预期的”基本价值体系“所拘束,故民事法不能被视为宪法外之物。在日本也出现了法院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裁决私人间争讼的先例。如在三菱树脂案件中,三菱树脂公司以申请雇佣人员在大学参加过政治活动为理由拒绝雇佣,该申请雇佣人员向法院控诉三菱公司的歧视行为,法院经审理宣告公司的行为违宪无效。
而从我国的宪法传统观念和现实的宪法规定来看,宪法规范不只是调整国家权力的运行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而且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公权力,而且也涉及私权力的领域。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其所涉及的各类社会关系都是直接有效的,宪法诉讼在其范围上,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也应当包括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在内。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国宪法理论宪政实践中,并不存在强调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卫权”的观念。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相对于由国家机关具体行使的权力,是一种制约,然而国家机关不仅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同时还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义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代表和保障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公民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人民(公民)与国家权力的对抗,当然谈不上“防卫”。如果说有对抗,那是针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第二,从我国宪法的具体规定看,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不只是对国家和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有效;而且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行为也具有约束力。例如,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40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4条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8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等等。宪法的上述规定表明了公民基本权利不仅是针对国家机关的,而且也是针对“社会”、“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也都受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约束。
第三,在现实生活中,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不只是来自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学校等社会组织,甚至某些个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社会组织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组织凭借其相对于公民个人的“实力地位”,如经济组织对其所聘用人员,学校对其员工、学生,村民委员会对村民等,实施的侵权行为;另一类是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社会组织还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如选举的组织、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发放、人事档案的管理等等,凭借其实施管理的权力,侵犯被管理对象的基本权利。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主要是受普通法律的约束,承担民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法律责任,但这并不能排除必要时的宪法适用。在普通法律尚不完备、存在某种局限,或者通过民事、行政或刑事的诉讼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完全有必要引入宪法,通过宪法诉讼使得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完善民商立法,建立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但是民事活动也不能违反宪法、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学者认为,从长远目标看,应当是所有的宪法权利都具有直接效力,但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则主张采用“先公后私、先易后难、逐步扩展”的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宪法传统中并不存在基本权利只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卫权”的观念,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也不是约束国家机关的行为,在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上应当不存在“先公后私、先难后易”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民事领域的宪法诉讼要“易”于公权力的领域。
四、建立我国宪法诉讼制度所面临的障碍
宪法诉讼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的习惯的影响,实践中也缺乏与宪法诉讼相关的个案,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第一,宪法本身的规范性程度不高,弱化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一方面,某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本身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程度并不高,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权利保障的需要。例如,对公民财产权的规定,只限于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未能包含债权、知识产权和具有财产性质的公物使用权等权利。在关于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款中,规定了“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然而“禁止”的三种行为并不能涵盖侵害人格尊严的全部行为,难以避免在权利保障上出现遗漏。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宪法缺乏保障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诸如德国宪法“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之类的概括性条款),也不利于宪法诉讼作用的发挥。应当适时修改宪法,完善其规范化的程度。
第二,现行的诉讼制度的局限,也不利于宪法诉讼的有效运行。需要通过宪法诉讼来纠正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大多与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有关。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尤其是基层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有不少是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法院不具有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院应有权裁定其无效。第三,宪法制裁方式在具体运用上的局限。从我国宪法的规定看,宪法的制裁方式主要是撤销和罢免两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也即宣布其无效。而罢免则是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制裁,它只能由法定的机关和单位行使。撤销和罢免的宪法制裁形式,并不能简单适用于宪法诉讼。在法院不拥有违宪审查权的体制下,撤销权的运用范围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在宪法诉讼中适用的制裁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确认行为的违宪,因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这类情况下,往往只要确认行为违宪而无效,公民被侵犯的权利即可得到恢复。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作出的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决定、命令。二是确认基本权利受侵犯的状态,从而判定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具体法律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宪法争议并不涉及行为是否有效,或者说确认行为是否有效并不能使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和补救,需要同时采取其他相应的权利救济手段。例如,发生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侵犯选民选举权案,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无效,并不能使原告的被侵犯的权利得以恢复。
第四,司法人员观念上和素质上的障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宪法不在司法审判中适用,缺乏相应的宪法判例,在司法人员中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建立宪法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要求司法人员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可以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可以在实践中选择较为典型的涉及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通过审判活动形成司法的判例,在最高法院公报中公布,以探索宪法诉讼的经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相应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确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
注释:
[1]在钱某诉屈臣氏公司一案中,两级法院均认定侵权行为成立,但在对侵权行为的性质判定和法律的适用上并不相同。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按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和名誉权来判案,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则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屈臣氏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8条和《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侵犯了钱某的人格权。在法律界引发了能否引用宪法来判案的争议。在王春立等16人诉民族饭店一案中,原告以民族饭店的行为侵犯选举权为由,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王春立等人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案的审理结果表露了,由于宪法不被法院作为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致使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纠纷不能得到合法的解决,因此也失去了法律的有效保障。有关内容可参见: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32-33页;史卫民、雷兢璇著《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87页。
[2]据《参考消息》1998年10月7日报道:在我国政府代表签字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表示欢迎,并呼吁我国“采取额外措施,在批准公约之前就采用公约规定的准则”。
[3]四川省眉山县人民法院在受理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一案中,认定被告第八工程公司与被告罗友敏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施工中发生伤、亡、残事故,由罗友敏负责”,把只有企业才有能力承担的安全风险,推给能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第42条第2款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的规定和《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的规定,该约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不受法律保护,第八公司对原告刘明的工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体现了宪法的原则规定在民事赔偿案件中的具体应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5期,第172-173页。
[4]关于宪法的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可参见拙文《论宪法的适用性》,载《法学家》1996年第3期,第23-24页。
[5]关于德国的“单身条款”案和日本的三菱树脂公司案件,可参见陈新民著的《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下册,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6月版,第82页;张庆福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92页。
[6]有关主张可参见周永坤著的《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一文,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第27页。
[7]如各级人大罢免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选民或选举单位罢免由其产生的人民代表。
[参考文献]
[1]韩大元,刘志刚。试论宪法诉讼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J].法学评论,1998,(3):26-30。
[2]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349。
[3]徐秀义。宪法学与政权建设理论综述[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47。
[4]宫泽俊义。日本国宪法精解:中译本[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162-185。
本权范文篇9
关键词:宪法基本权利,法治,合宪性,合法性
由孙志刚一案引发的对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质疑,在各方的呼吁与压力之下,似乎已随着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自行撤消该《办法》而告终结。但是,该案背后所潜藏的一系列与宪法基本权利及其限制相关的理论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明确与澄清。它们既涉及到宪法与法治的基本概念、原理与原则,也与我国实践中开展的法治国家的进程密切相关。因此,以此案为契机,有针对性地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深化宪法与法治基本理论,促进法治国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无裨益。
一、宪法基本权利能否被限制?谁来限制?限制到何种程度?谁来审查?
孙志刚案的实质是对公民宪法上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问题,这涉及到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能否被限制及与其相关联的一系列宪法基本理论问题。
首先,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可以限制的。作为最高法的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们是政治社会中个人所应享有的,也是国家必须给予保障的个人基本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排他的,也即并非不可以限制。虽然在理念上,这些权利是最高的,是天赋的,受宪法保障,但在实证的意义上,各国宪法基本权利均采相对保障主义,而非绝对保障主义,即基本权利可以依法限制。限制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是个人权利与其他法益冲突的客观存在。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人有相互依从性,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有可能侵害他人的权利或者社会利益,须在不同权利之间进行适度平衡,这就是限制宪法基本权利及基本权利相对保障主义的理论基础。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通讯与住宅不受侵犯这些传统的基本权利来看,其中没有一项是可以不受一般性的法律规则限制的绝对权利。言论自由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造谣、诽谤、欺诈、教唆犯罪或以报警来制造混乱。人身自由也如此,当人身自由与紧急状态之下的国家安全、公共卫生与社会秩序相抵牾之时,人身自由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根据最早则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四条规定:“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力。因此,行使各人的自然权利只有以保证社会的其他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为其界限。这些界限只能够由法律确定。”这一规定既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也包含了基本权利可以受限制,并且只能由法律加以限制的内涵。因此,从理论与法律两方面来看,宪法基本权利都是可以限制的。
其次,宪法基本权利由谁来限制?宪法基本权利可以受到限制,这已确凿无疑,问题是由谁来限制?现代政府构造主要由三个部门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组成,是否这些机构都可以限制基本权利?答案则是否定的。在民主法治及基本权利的发展进程中,各国无一例外地明确了一点,这就是只有“法律”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前述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这些界限只能够由法律确定”已清晰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公民基本权利都以明确的方式或者明文规定的方式受到了宪法保护,“除非依照法律”,否则不得对上述权利做任何限制。“依照法律”即意味着只有法律才可以限制,其后,该理论发展为法律保留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分立或者分工的政府机构中,“法律”并非指一般法理学教科书在阐述法律渊源之时所指的不同位阶的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内的所有规范性文件,而是仅指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并颁布的法律。因此,此处所指的法律,必须具足法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否则便不可以称之为法律。
再次,宪法基本权利限制到何种程度?既然法律可以限制基本权利,那么限制到何种程度才最为相宜?在限制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以限制基本权利为借口,虚化或者抽空基本权利的内涵。果如此,则宪法基本权利无疑会沦为一纸空文,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就丧失其实际价值与意义。从宪法理论与国外的审判实践来看,确立了基本权利的基本内容或者核心不可以限制的原则。德国宪法第十九条(二)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危及基本权利的实质”。意指理论上,承认每一个基本权利中有一些核心内容,是任何法律所不能加以限制的。否则,限制这些核心内容的法律将被宣布为无效。但是,究竟如何掌握核心标准?从实践来看,主要有三个,即残余论、利益论和折衷论。[1]例如,在有关死刑违宪审查理论的讨论中,其中有学者所持的观点就属于此例,认为刑法规定死刑属于违宪,因为法律规定死刑,是法律剥夺个人生命权,生命权处于个人基本权利的核心地位,属于基本权利的实质,受宪法保障,因此不可以被法律剥夺,而规定死刑剥夺生命权的法律也在此意义上构成违宪。
最后,谁来审查?如果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超过了宪法所允许的限度,则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中,或者通过抽象审查,或者通过具体审查,有可能启动一个合宪性审查的程序,对这一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应在法律秩序中继续存在(在抽象审查当中),或者在个案中不适用这一法律(在具体审查当中)。这一审查通常是由法院或者中立机构进行的。并且,在具体审查当中,这一审查是由普通法院在适用法律裁决纠纷的过程中进行的。通过法院或者中立机构的审查,不适当地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被认定违宪而被撤消,个人宪法基本权利得到维护。
二、只有具备形式与实质理性的规范性文件才可称为“法”,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
在前述问题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即“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或者“法治行政”中的“法”为何物?在孙志刚案和其他一些类似案件中,看似主管部门是依据规范性文件做出的决定,但是,仔细考察,这些规范性文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只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性法规。如果按照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它们无权限制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那么,什么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
前文已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法必须是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的具备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规范性文件。所谓法的形式理性,指必须是立法机关按照程序通过的法律文件,法律的成立必须符合包括立法主体合法在内的法的程序要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意味着非立法机关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因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质内涵之一是确立了人民也即立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因此,限制基本权利必须是狭义的人民代表机关-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才可以做的事情。进一步而言,也即只有在经过人民的同意之下,并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宪法基本权利才可以受到限制,
否则,其他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不可限制基本权利。考察法治与权利保障的历史,其一直是对抗皇权与行政机关的专横的过程,因此,法律限制基本权利,也是人民自身对其权利的限制,这一限制具体由人民的代表机关-立法机关-以制定法律的方式进行。
在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程序要件还暗含了这一问题,亦即并不是立法机关或者代议机构以适当方式通过的每一个决议都可以称之为法律,而仅仅是意指那些在符合狭义的条件基础之上通过的文件才可以被称为法律,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因为,法律与决议是不一样的,法律的通过需要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如提议权、三读通过、表决等,而决议则是一个简单程序,其通过并不像立法程序那样严格。这一点,对于考察我国的法治实践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属性具有重要价值。
所谓法的实质理性,是指立法机关按照程序所通过的法律必须符合法的一般要素,如法律必须是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没有追溯力的。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必须不能是针对个案,也不能是对具体事件的处理措施。在限制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严格禁止“个案性法律”和“措施性法律”,[2]因为这样的法律或者是针对具体人定订的,或者是针对具体事件制定的,它们不具备抽象的普遍约束力,不符合法的实质理性。其他实质要件也各有自己的针对性,如法律不得溯及既往。
因此,法律可以限制基本权利,意指只有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的规范性文件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它排除两方面的认识:一是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关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其所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一是并不是立法机关通过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称之为法律,都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只有立法机关严格按照立法程序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并且这一规范性文件必须在具备形式理性的前提下,符合法的实质理性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只有这样,“对各种基本权利所施加的上述那种限制才会具有意义,同时才不至于使‘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受’立法机构‘的干扰变成一句空话,完全丧失作用。”[3]以此观照我国国务院颁布的限制公民人身基本权利的规范性文件,由于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法规,故都应属无效。不独《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办法》,就是有关限制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规范性文件,如有关大学生不得结婚、劳动教养等规定,因其在性质上都属于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违反了权力分工原则,行使了本应由立法机关履行的职责,属于宪法上的越权,故都不具备合宪性基础。
将“法”限定为狭义的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在我国还有重要意义。从法治的历史看,法治是在抵制王权擅断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代议机关-立法机关-法律-权威的过程,亦即确立人民意志主宰和决定国家事务权威的过程;民意机关的意志以法律形式表现,此即为“法治”而非人治。当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此处的“法”既有实定法意义上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人为法的含义,也包含超越人为法意义上的抽象法包括自然法与神法,且人为法还需要接受后者的评判与检验,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实证层面,各国在总体上依然确立了立法机关制定法的权威,管理国家的过程也是“法”的统治过程,不管这一法律存在的哲学与道德基础是什么。而反观我国的现状,各界包括法学理论界、政府机关及司法实务界对“法”的理解始终未形成明确、坚定、清晰、统一和无误的认识,这并非凭空臆断,而是根源于对现实中一些现象的观察与判断。例如,“依法治国”在实践中作为一种口号不断被扩充和庸俗化其内涵,出现了“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照此类推,“依法治国”势必发展为“依法治人”。果如其然,则“依法治国”这一崇高目标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可悲的自我否定式的悖论,而如此庸俗化与可能的自我否定式的结果出现的原因正是基于意识上对“法”为何物不甚明确而产生的、从而消解“法治国家”内涵的表现。
此外,法学教科书在此方面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翻阅目前的法理学教材,几乎所有有关“法律渊源”的阐述都不加区分地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一概称之为“法律”,并对此不加以说明与分析。也许,在西方,这样的表述并不会产生误解。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议会最终成为国家立法机关曾经经历的艰辛斗争过程,使得上至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清楚地意识到“法律”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认识到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产物,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但在我国,这却是一个应引起高度和充分注意的问题。因为中国封建传统是有法制的,且有所谓“法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法律体系-“中华法系”。“中华法系”自成体系,源源流长,持续了几千年并广泛影响了亚洲国家和地区。但是,“中华法系”在性质上属于封建法律体系,其名称虽冠以“法”,但此法非彼法。无论在理念、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等方面,此处的“法”(经、律、刑)都与西方意义上的法相去甚远。首先,在理念上,封建法律不是人民意志的产物,而是君主意志的表现。在封建政治法律制度之下,君主言出法随。其次,在形式理性上,封建制度没有立法机关,封建法律既不是立法机关的制定法,也没有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再次,在实质理性上,封建法律可以不公开,可以朝令夕改,甚或具有追溯力等。因此,如果将一切人说得话都称之为“法”,则“国王在法律之下”这一经典表述也就失去其意义,而倡导“法治”也与“法家”的严刑峻法没有二致。具体到限制基本权利的问题而言,如果不明确法的内涵与外延,则任何一个规范性文件都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宪法基本权利也就失去其意义。
三、行政法规只具备有限的“法”属性,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或者根据
在孙志刚案的讨论过程中,问题还集中在行政法规可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这就需要对行政法规的“法”属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各国行政机关在实施宪法、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可以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虽然对人民也具有抽象和普遍约束力,但是,由于其不具备法律的形式理性,亦即它并不是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颁布的,故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将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统称为“命令”,以区别于立法机关制定与颁布的“法律”(司法机关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则为“规则”)。如日本、德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并且,将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称为“命令”,有助于与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相区别,亦有助于突出行政的机关特性。
以台湾地区为例,所有行政机关制颁的规范性文件都称为命令。具体而言,命令又可分为外部命令与内部规则,包括法规命令、职权命令、行政规则、紧急命令与特别命令。规范外部活动、有法律授权为依据的又可分为“法规命令”(相当于大陆地区的授权立法),和不待法律的授权,依据其组织法上的职权而制定的“职权命令”(相当于大陆地区的行政法规)。职权命令一般是为了执行法律的需要所制定的,通常是为了填补法律的真空、补充法律的不足所制定的对外的行政命令,对人民也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规范行政体系内部行为,如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长官对随员的规范则为“行政规则”。此外,还有“紧急命令”与“特别命令”。[4]这就是说,按照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性质,三机关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别为“法律”、“命令”与“规则”。如日本宪法第七十三条第六项规定内阁的职权为:“为实施本宪法及法律规定之需要制定政令,但政令中除有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政令即是内阁为了实施宪法及法律之规定而的命令。[5]第八十一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其中法律是指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命令是指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也即政令,规则是指法院的规则。总体而言,行政命令具有抽象性和普遍的拘束力,其具体的名称则有规则、细则、办法、纲要、标准、准则、要点、注意事项等。我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一)规定的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这一权力的根据。但是,在理论上,我国却并未明确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命令”性质。
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虽然具有抽象的普遍约束力,但颁布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命令”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相当程度的专断性,因此,其内容既须符合宪法的一般原则,也不得违反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即行政法规须具备合宪性与合法性,特别是有关限制公民权利的行政法规,除非有法律依据或者法律的明确授权,否则,不得有限制基本权利的条款,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是保留给立法机关的法律所为的事情,此即为法律保留。我国这方面还有许多待检讨之处,行政法规中有大量关于限制公民权利的规定。除《收容遣送办法》以外,其它如国务院制定的《社团登记条例》,关于劳动教养等方面的行政法规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法规之中包含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内容的规定。
以劳动教养为例,劳动教养的实质是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按照我国国务院197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四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这一期限与刑法规定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最低刑期-拘役-的期限15天至六个月要高许多,因此,劳动教养是一种较为严厉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分。我国目前有关劳动教养的依据分别是:1957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由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是由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行政法规,而《试行办法》则属于部门规章。无论是按照行政法治的一般原则,还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既不合宪,也不合法。
法治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只有法律才可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行政机关不可以对此加以限制,其实质是除非经人民自己同意,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不可以由行政机关加以限制与剥夺。依法行政原则也要求行政法规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特别是有关限制公民权利方面的内容。我国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这一点。200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此外,国际人权文件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款也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些法律规定都说明,行政机关不得剥夺或者限制公民权利不仅是法治原则的一般要求,也有制定法上的依据。在此情况下,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方面的行政法规就不具有合法性。同时,《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法律规定与本法不符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国务院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明显与本法不符,因此,应按照《行政处罚法》法的规定,修订国务院颁布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颁布的《试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这既说明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法规违反了法治原则,不符合权力分立或者分工原则,不具备合宪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也说明这些限制基本权利的行政法规违反了法律,不具备合法性。
因此,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只是在对人民具有抽象与普遍约束力的意义上具备“法”的属性,它并不具备法的形式理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不可以规定只有“法律”才可以规定的内容。具体到限制基本权利而言,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同时具备合宪性与合法性。首先,行政机关必须符合宪法基本原则,如法治原则,权力分立与分工原则。这些原则要求只有立法机关的制定法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其次,必须坚持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原则。前者要求同样的事情,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有规定,应以法律优先;后者要求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必须保留给立法机关及其制定的法律。再次,限制公民权利的行政法规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者法律根据。
四、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可否限制公民基本权利?
孙志刚案暴露的行政法规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只是冰山之一角,除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以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据统计,在该案出现以后,国务院法制局收集了相关法规规章,发现有191个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立法。[6]如北京市、广东省、河北省等都有类似的收容条例。具体而言,这些地方立法就是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它们分别是由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这些法规的内容也有一个合宪性与合法性的问题。在厘清该问题之前,首先须区分地方性法规与地方规章的性质。
地方性法规是地方立法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其效力只及于地方,且不得与国家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至于地方性法规能否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则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曾就地方自治条例、规章是否可以限制人民权利义务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既是一个法律保留原则问题,也是一个探讨与界定地方立法机关立法范围与效力的问题。依据法律保留理论,应该以“法律”规定之事项,不得以命令规定。而所谓的“法律”,仅指“中央”或者“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地方自治条例与规章。但是,根据台湾地区以往地方自治实务的例子来看,如果不允许地方对于一些重要事项有独立立法且能够限制人民权利义务的权限,则在自治行政上就无法产生因地制宜的功效,所以,其后“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若地方自治团体欲制订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之法,须以自治条例之名义,且限于罚款与其它种类之行政罚,而其它种类的行政罚则限于勒令停工、停止营业、吊扣执照或其它一定期限内限制或禁止为一定行为之不利处分。依据“明示其一即排除其它”的原则,这就是否定其它相关地方自治条例可以对人民自由以及权利加以限制。就地方立法机关立法范围与效力而言,该问题的实质也是地方自治条例不得侵犯“中央”立法机关的权限。各国宪法相关规定一般都可以引申出这一原则:限制人民权利的法律只能由中央立法机关立法决定,地方自治条例不属于法律,无权对此做出规定。如果地方制定了这样的条例,无疑是地方立法机关侵犯了中央立法机关的权能,该条例无效。从两方面的理论来看,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都无权限制基本权利。如果要限制的话,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
大陆地区虽然在理论上不认为下放权力属于地方自治,但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与地方自治条例在性质上并无实质差异,其也是效力只及于地方的,由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地方性法规有其特殊的立法范围,关于限制公民权利的内容不在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范围之内,原则上,地方性法规不得限制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地方性法规不具备合宪性。当然,如果承认地方性法规限制公民权利是开展地方自治或者地方自主的辅助手段,实属必要,那也应该明确那些可以受到限制的权利的范围及幅度。这一问题随着我国地方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活跃,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和必要。
地方规章是指一些地方人民政府的规范本地区事务的规范性文件,它属于行政法源的一种,其效力低于行政法规,也低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7]作为行政法源的一种,地方规章服从行政法制的一般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地方规章不得与法律及上位行政法规相抵触,还特别指地方规章的制定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公民权利的内容与条款,地方规章不可染指。我国宪法原则规定了对地方规章的审查。宪法第八十九条(十四)规定:国务院“改变或者撤消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实践中,以地方规章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利的规定时有出现。2001年4月3日,经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商,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文件(渝劳社办发[2001]79号),就重庆市关于养老保险争议的受理问题做出决定: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都没有缴纳或用人单位没有足额缴纳养老保险金,由劳动者要求补缴的申诉不属于司法管辖的范畴,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规定对此类争议,劳动者可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举报。该文件的最后还写有:抄送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总工会、市经委。2002年5月14日,律师周立太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向重庆市政府法制办提出了撤消这一文件的相关规定的申请,认为79号文只是行政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却排除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违反了《宪法》、《民事诉讼法》、《劳动法》、《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8]
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第79号文件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根据法治原则,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只能由立法机关依法予以限制和剥夺,地方行政机关不得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诉请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是公民宪法上的诉讼权,地方行政机关不可以擅自剥夺和限制。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只是一个地方行政部门,其所颁发的79号文件在性质上属于地方规章,它无权剥夺公民宪法上的诉讼权。其次,根据法治行政原则,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须有立法机关制定法的根据或者授权。如果法律规定或者授权劳动局和社保局可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诉讼权的权力,则它们可以制定这样的规章,而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在制定这样的规章时,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法律授权,这不符合法治行政原则。最后,该文件的制定过程违反了权力分工原则。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是地方行政机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互有分工,二者之间不可以以协商方式,在缺乏宪法和法律根据的前提下,以规范性文件方式剥夺公民诉讼权这一宪法基本权利。
结语
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其限制的实务,需要有坚实的宪法理论作为分析与判断问题的理论指南。同时,尽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进宪法,但是,这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而是需要进一步认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或者“法治行政”之中的“法”的属性。这无疑是在启示我们,我国的宪法与法治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行固难,知岂易乎?
参考文献:
[1]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368页。
[2]关于“个案性法律”与“措施性法律”,可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364—366页。
[3]参见[英]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4]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38页。
[5]参见[日]三浦隆著:《实践宪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6]参见马克:《收容:修正“办法”,还是彻底废除?》,载《南方周末》,2003年6月19日。
本权范文篇10
一、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上的占有
占有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占有首先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占有同本权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在占有同本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大法官在权利确定之前往往维持占有现状的命令,即占有令状。本权人必须提起诉讼才能恢复占有,也就是说,即使占有状态同法律上的应然权利状态相去甚远,法律也不允许私力擅加侵害。在“物件返还诉讼”中,由主张所有权的原告负举证责任,若原告不能举证,作为被告的占有人即可胜诉,从而继续维持其占有。即使所有权人能够举证,善意占有人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可以主张时效取得,且取得时效的期限较短,除土地之外,一般仅为一年。如若善意占有人还是不具备主张时效取得的条件,也可以仅凭其善意而无需返还孳息,对占有物的毁损灭失也不负赔偿责任。
在日耳曼法上,占有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物权,权利被包裹在占有之内,并藉占有来体现,因此,占有被喻为“权利之衣”。由此可见,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同本权并无实质性冲突。正是基于日耳曼法上透过占有即可推定本权的存在这一理念,近代的权利推定效力,动产善意取得乃至时效取得等原则和制度才得以产生,而这些制度和原则在解决占有同本权冲突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占有保护同本权保护的协调原则
古往今来,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民商法亦经历了全方位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财产归属主义到财产利用主义的转变;二是从强调对财产静态权属关系的确认和维护,演绎为对交易安全的尊重和保障。在物权法上,也形成了以所有权为心,所有权分离的权能构成他物权体系的一种权利架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说在物权法上建立占有制度已经成为共识,但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协调占有保护同本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先看一下问题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依上述关系图可看出占有权能和占有的区别与联系。占有权能是所有权的权能之一,它可以与所有权相分离而属于非所有人。非所有人的占有依据有无占有权能分为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无权占有按占有人的主观方面可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合法占有可基于所有权权源,也可基于有占有权能的他物权权源。合法占有也就是本权占有。
非法占有人(包括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可基于占有产生占有权。善意占有人的占有权较为广泛,包括即时取得权,时效取得权和使用收益权等,在一定条件下可对抗本权。笔者认为,对于恶意占有人,法律也应承认其享有一定的占有权,不过其占有权仅限于占有物上请求权。理由很简单,当占有物面临毁损灭失的危险或遭遇他人侵夺的时候,没有人比占有人能更快地作出反应,若不承认其享有一定的占有权,占有人就可能陷入爱莫能助的境地。
该关系图也揭示出了占有保护同本权保护发生冲突的必然性。法律给占有以相当于本权的保护,它从推定一切现实占有为合法占有出发,首先宣布对占有人以普遍的法律保护,再根据占有的样态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这样的逻辑起点不同于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按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的要求,民事主体必须先以法定的方式取得某种物权之后,才能按该种物权的法定内容对标的物进行实际支配。不过应该看到,两种机制对基于本权的合法占有的保护是一致的,而对于非法占有中恶意占有人负返还原物及其收益的责任亦是殊途同归。此时,就需要法律对占有利益和本权利益进行价值衡量和取舍。要正确合理地协调占有保护同本权保护的冲突,需要确立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稳定原则,即占有现状应当稳定,禁止任何人随意改变占有现状。这是从罗马法上得到的启示。占有现状本身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即使是真实权利人,也必须依照合法程序行使权利,若采用敲诈、抢夺、盗窃等手段,同样为法律所禁止。事实上,“尊重占有”的意识早已深植于一般社会观念之中。物上存在的占有外观,对于一般人来讲,至少表明该物上已有他人意志存在,而占有人作为与物最密切的人,被认为是物上他人意志的代表,这种观念符合人类最自然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因此,尊重占有就是尊重人类自身。
第二,善意购买人原则,即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动产占有于善意购买第三人时,即使该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所有权和他物权。善意购买原则的适用结果是善意第三人取得动产的所有权或他物权,而原权利人丧失其权利,这正反映了法律在保护占有和本权之间做出了价值评判和取舍。不过,为平衡利益,善意购买原则的适用条件是极其严格的。
第三,时效取得原则,无权占有人在法定条件下占有他人之物,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即依法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时效取得制度同样也是协调占有保护同本权保护冲突的有力工具。时效取得实际上承认了“事实创造权利”。占有同本权分离的现象很常见,不过这种分离不会长久持续,因为根据一种必然的倾向,当一种事实持续时,它就会在一定条件下自动转化为权利。时效取得的构成要件有:1、占有人对他人的财产须为自主占有、和平占有和公然占有。2、占有人的占有须持续经过法定期间。符合上述条件,即可实现从占有事实到占有权的转化。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业已建立的众多法律关系,另一方面也带有惩罚原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色彩。
上文提及。世界范围内的民商法经历着从财产归属主义到财产利用主义的转变。那么在财产利用方面,法律又该如何协调占有保护同本保护的冲突呢?笔者认为应贯彻物尽其用原则,再辅之以区分善意、恶意的立法手段,以达到利益平衡的效果。
法律担负着促进物最大化利用的使命,应为民事主体依正当方式生财提供最大限度的可能。在资源短缺的当今社会,这点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依照传统所有权理论,秉承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只要所有权人不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任意行使所有权甚至于滥用,他人不得干涉。再加上所有权的弹力性,即与所有权分离的权能最终要回复到所有权,使所有权恢复圆满状态。这样一种理念的流行。使物尽其用受到限制。法律何不寻求一种两全齐美的方法,一方面促进物效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可达到衡平当事人之间利益的效果。笔者认为,区分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并规定不同的权利义务范围,便是一种很好的立法选择。
三、财产动态流转中的占有保护同本权保护
法律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问题。更在于解决问题。上文归纳的几个原则,是否具有实际操作性,能否在权利动作过程中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呢?现在就将该问题置于财产的动态流转中加以说明,且把复杂的交易简化为两种财产流转模式。
(一)情况一:本权人→……→恶意占有人
在这种情况下,原为本权人占有的动产直接或间接流转到恶意占有人手中。不论财产流转程序如何,也不论恶意占有人以何种方式取得动产占有,只要心存恶意,本权人即可向其主张所有物返还或占有物返还,恶意占有人不得拒绝。此时,占有制度对占有的保护同所有权、他物权制度对本权的保护,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效。在实体方面,本权人享有对恶意占有人主张返还原物及其收益的请求权。若基于恶意占有人的原因使占有物毁损灭失的,可向其主张赔偿全部损失的责任。但在程序方面,仍应贯彻稳定原则,本权人须尊重占有现状,提起本权之诉,在诉讼中亦由其来承担证明其权利真实和占有人为恶意的举证责任。
(二)情况二:本权人→……→善意占有人
在这种情况下,原为本权人占有的动产直接或间接流转到善意占有人手中。因占有人为善意,法律倾向于保护其占有利益,这也正是占有保护同本权保护冲突的焦点所在。法律为善意占有人提供了多种有效救济手段:
首先善意占有人可主张善意取得,此即为善意购买原则的适用。不过,此时财产的流转程序应为所有权人一无权处分人(但合法占有)一善意占有第三人。善意第三人须以交易的方式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动产的占有,且无权处分人的占有是基于所有权人的意思而为的占有。条件符合,善意占有第三人即可取得物之所有权。实际上,即时取得的目标之一,是意在通过维护交易安全,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从而实现物尽其用原则。这一法律目标含着这样的假设,善意第三人对物的直接利用将优先于原权利人。
其次善意占有人可主张时效取得。相对于善意取得来说,时效取得的适用并没有财产流转程序和取得方式上的严格限制,善意占有既可以直接从所有人手中取得占有,也可以是无偿取得占有。但其占有须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善意取得和时效取得的适用皆以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它们的适用条件权为严格。那么,在不符合条件即不能主张即时取得和时效取得的情况下,善意占有人是否无计可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法律给予了善意占有人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例如,善意占有人仅凭其为善意就可以享有使用收益权,虽负有返还原物的义务,但仅需返还现存利益,且无需返还孳息。对于非因其原因而导致原物的毁损灭失,亦不负赔偿之责。又如,若善意第三人是在公开市场买受的,则本权人除非向第三人支付相应的价金,否则不得请求返还原物。再如,若该项动产为金钱或不记名有价证券,本权人一律丧失原物返还请求权。
参考文献
[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热门标签
相关文章
行政管理与基本权利 2022-05-27 10:18:00
消费维权基本概况调查汇报 2022-05-18 04:36:00
透视日本知识产权协会作用 2022-12-09 03:10:00
弱势群体基本权的法律保护解读 2022-05-20 10:42:00
农民工基本权益考研报告材料 2022-05-08 11:03:00
小议农民工基本权益状况之调查汇报 2022-05-04 04:58:00